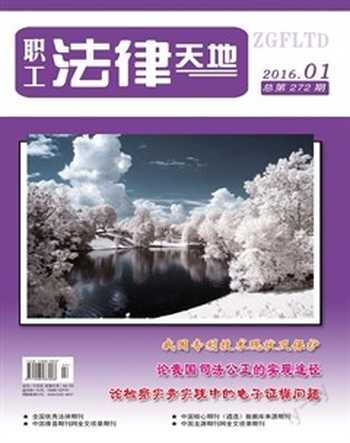虐童案件的刑法分析
摘 要:我国刑法在司法实践中针对频发的虐童案件时显得捉襟见肘,司法实践中多数情况行为人都以无罪释放终结。而学界对虐童现象定罪持多种意见,其中多数学者认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本文就将结合学界争议以及实际定罪情况提出立法完善建议,通过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将“其他具有监护、保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保护人”包括在内,以及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以有效规制虐待儿童的行为。
关键词:虐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侮辱罪;寻衅滋事罪;无罪;立法完善
一、学界定罪争议介评
被曝光的虐童案例越来越多,法律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就此番种种虐童现象来看,學界主要持五种意见,分别为故意伤害罪、虐待罪、侮辱罪、寻衅滋事罪以及无罪。
(一)故意伤害罪
学界第一种观点主张虐童行为应该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故意伤害是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虐童行为客观上对儿童身体上的伤害,主观上是故意,可以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然而实践中主要争议点在故意伤害罪的客体以及客观方面。
故意伤害罪的客体通说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这是故意伤害罪区别于其他人身犯罪的本质特征。刑法意义上的伤害他人身体健康,是指他人的生理健康遭受实质的损害,造成他人精神损害的,不能构成本罪。实践中,损害他人健康是否包含“精神损害”,答案是肯定的。伤害应该包括肉体伤害和精神伤害两种。[1]但是实践中确实应当把思想心里范畴的精神与生理范畴的神经区分开来。
(二)虐待罪
第二种观点主张应以虐待罪加以定罪。虐待罪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以打骂、冻饿、紧闭、有病不给治、强迫从事过度劳动等各种方法。从肉体和精神上肆意进行摧残迫害,情结恶劣的行为。”实践中主要争议点在虐待罪的对象还有主观方面。
本罪的行为对象通说将其理解为按照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在同一家庭生活,有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有相互抚养,相互帮助义务的人。但是是否可以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扩大解释,应该说在实践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度的扩大解释。[2]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虐待儿童的行为符合虐待罪的所有构成要件。
(三)侮辱罪
第三种观点主张应以定侮辱罪加以定罪。根据刑法第246条侮辱罪的规定,侮辱罪是指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贬低他人的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争议点主要有二:一方面是客观方面中公然性的界定;另一方面是情节严重的界定。[3]时下,有人认为,侮辱行为强调的是在公共场所公然地侮辱他人人格,由于上述案件中的虐童行为都发生在相对封闭的教室里,行为看似不具有“公然性”,因而行为性质不属于侮辱。按照刑法的规定,构成侮辱罪应以“情节严重”为必要条件,情节严重是指侮辱手段恶劣、动机卑鄙、侮辱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多次实施侮辱行为、侮辱行为给社会带来极坏的影响等等。因此,如果行为人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虐待儿童,公然侮辱儿童人格,情节严重的,应构成侮辱罪。
(四)寻衅滋事罪
多数虐童案在实践中就是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进行批捕的,也是在四个罪名中争议最大的一个罪名,其中对于社会秩序以及公共场所的争议最为激烈。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罪是由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分解而来的。1997年增设了寻衅滋事罪等一系列罪名。依据寻衅滋事罪的立法沿革以及现行刑法的具体规定,寻衅滋事罪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法益是在以个人及其自由发展为目标进行建设的社会整体制度的范围之内,有益于个人及其自由发展的,或者是有意于这个制度本身功能的一中现实或者目标的设定,法益的抽象程度越高,其包含的内容就越广,处罚的犯罪就越大。
(五)无罪
众所周知,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确立的基本原则,其内涵当然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先要看刑法条文有无明文规定,是否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显然,寻衅滋事罪作为一个口袋罪就成为了一个边缘罪名。既然虐童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我们考虑问题的思路,当然就不能在相关行为明显不符合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仍然勉强选择所谓“最接近”的罪名——寻衅滋事罪加以适用。
二、本文观点
(一)故意伤害罪
在司法实践中,故意伤害罪是处理虐童案中涉及的一种罪名。笔者认为,对于符合故意伤害罪构成要件的虐童案件,应以本罪论。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即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伤害结果的发生。而案件中多是行为人行为的行为随意,就是无故,就是没有任何的原因、理由,殴打行为完全出于一种寻求刺激的冲动。而在客观方面,虐待行为人积极身体作为,对儿童拳打脚踢,损害了儿童的身体健康。当然,对于一般的推拉撕扯行为并不能满足轻伤的入罪标准,此前的西安用锯子惩罚调皮幼童的行为已经损害了幼童正常的生理机能。令人发指的是在今年4月微博上传出的一案件,应以本罪论,教师以学生做不出题目太笨为由用针头刺小学生的生殖器,导致儿童下体疼痛加之心理创伤。这是继去年温岭虐童案之后又一引起广大民众讨论的案件。当案件从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主客体特征看均满足时,情结严重符合条件,即定故意伤害罪。
(二)无罪
司法工作人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务必要转变过去“消化”案件的习惯思路和做法,纠正长期以来形成的凡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一定要以犯罪论处,即使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也要千方百计地想出一个罪名予以处罚的观念。这都会严重地损害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和严肃性。当然,不可否认,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传统刑法观念很难得到突破,在我国要做到这一点确非易事。其次,无罪不代表无责,从其他法律责任层面分析,对于相对轻微,没有达到触犯刑法程度的虐童行为,我们完全可以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对行为人追究民事、行政责任。
三、立法完善建议
(一)扩大虐待罪主体
针对上述描述情况,扩大虐待罪的主体适用范围,而非增设虐童罪,更有利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和刑法体系的完整性。扩大虐待罪的主体适用范围,更有利于维护刑法的稳定性。如果增设虐童罪,虽然刑法条款变得明确具体,但是法律如何让面对现实情况中接踵而至的诸如虐待老人、妇女等的案件,如此一来,刑法必然将变得冗杂。
(二)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
刑法中关于虐待罪的法定刑设立基本犯为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加重犯是两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笔者认为应当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
1.从人权角度看,法定刑过低不利于更好的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诚如上面所说,在亲权和人权的博弈中,人权不应该妥协。由于在虐待现象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往往是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对虐待人有一定依赖性的人,因此,应更好地履行对此类对象的教育、扶养以及照顾义务。
2.从防治效果看,法定刑过低不利于遏制频发的虐待案件
法定刑过低导致惩罚力度不够,既不能通过将惩罚适用于犯罪人,也不能对其起到警醒的作用。纵观今年发生的教师虐童案,曝光后的当事人虽然绝大多数受到了处罚,但是虐童现象仍然屡见不鲜。即使有少数被判处刑罚,其刑罚力度之低,带来的威慑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有必要重新审视虐待罪的立法情况,加重其法定刑,以实现良好的防治效果。
四、结语
我国正处于深度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激烈的社会解构与重构必然带来层出不穷、不断变化的社会现象。与此同时,随着网络、微博等平台的蓬勃发展,民意和舆论获得了充分的表達,民众对社会事件的参与度不断加深。因此,不断曝光的虐童行为所引发的巨大反响乃是情理之中。刑法作为保护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在其他法律尽其效用而不足以调整相关行为时才能将其纳入调整的范围。因此,建立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预防和监督机制,形成完整的、成熟的儿童保护法律体系,设立专门的儿童保护福利机构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焦点和着手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这样才能切实有效地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实现儿童利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倪泽仁.暴力犯罪刑法适用指导书[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261.
[2]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第二版)[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993-994.
[3]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763-764.
[4]周道鸾.张军.刑法罪名精释[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533.
[5]潘信哲.杨华.关于虐待罪问题的探讨[J].理论探索,2004(2):23.
[6]李希慧.刑法解释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98,112.
[7]潘信哲.杨华.关于虐待罪问题的探讨[J].理论探索,2004(2):23
[8]李希慧.刑法解释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5:98-112.
[9]周光权.刑法各论[M].北京:中国人名大学出版社,2011:78-80.
[10]柏浪涛.刑法攻略[M].北京:研究出版社,2012.53.
作者简介:
张丽蓉(1990~),女,甘肃武威人,西北师范大学2014级法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理论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