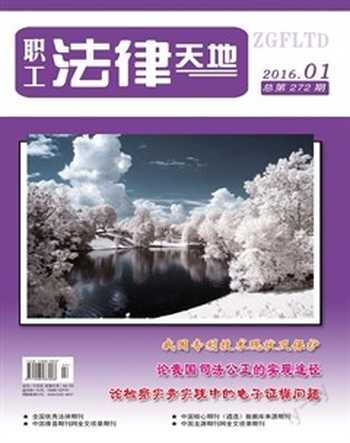论不得自证其罪原则
张云峰
摘 要:《刑事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是,关于该条款究竟是否赋予了被追诉人沉默权,理论界和实务界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依然留有如实供述义务之规定和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的认定范围过窄等两大问题。结合解读我国新刑诉法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引入,提出在我国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法律适用。
关键词:如实回答;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沉默权
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从刑事诉讼均衡的原理来看,程序中的权力制衡、人权保障是程序法基本价值要求,权力必须得到制衡,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应予积极保障,诉讼中保持控辩审大三角均衡态势是实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的前提。可见新刑诉法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规定,不仅仅是对总则中“尊重和保障人权”具体贯彻落实与呼应;更是遏制刑讯逼供、防治非法证据的重要利器。但从蓝图到实践,我们仍任重而道远。这主要体现在新出台的“不得自证其罪”依然留有如实供述义务之规定和如实供述、自愿认罪的认定范围过窄等两大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以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为研究对象,对该理念的深刻内涵进行理解。
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内涵
《刑诉法修正案》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定在了证据章节的第50条中,对于明确举证责任分配、合理规范取证方式的运用以及划定“强迫”的适用范围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我国增设了“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是为了正式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作准备,并且从法条的表述方式上看,明显继受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项庚目的規定。“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属“权利型”条款,是赋予了被追诉人供述(或辩解)与否的权利(自由),而“如实陈述”条款属“义务型”条款,是强加给了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辩解)的义务,显然,无论在立法精神还是内容上,两者都是存在着直接冲突的。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内涵丰富,无论是被追诉人有权拒绝回答归罪性提问,有权获得律师帮助,还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些内容都被具体化到了整个刑事诉讼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阶段和层面,其精神已经渗透到了整个刑事诉讼法的结构体系中。如果仅将其置于证据章节,则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就蜕缩成了一项证据规则,失去了其作为原则的本色,其作用和辐射力无法有效延伸统领到其他诉讼阶段和具体的制度程序中,不利于该原则的彻底贯彻和全面实施。笔者认为,在以后的修订中,可以考虑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作为原则性条款,抽离出证据章节,迁放至刑事诉讼法开篇,作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单独加以确立。
依据体系解释的方法,既然立法者将“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5章第50条之中,且该法条前后条款之内容皆为禁止非法取证手段的运用,由此可推知立法者对于“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主要是作为一项取证制度来设计的。所谓“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不过是对其前文“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重申和强调,意指“不得以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强迫任何人作出有罪供述”。
二、不得自证其罪与沉默权的确立
虽然新《刑事诉讼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但也没有直接规定“沉默权”,我们的规定与公约的精神是一致的。即使是英美法系的国家,近几年由于打击犯罪的需要,也对“沉默权”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因此不必直接规定“沉默权”。真正的抗拒,是嫌疑人在确凿充分的证据面前仍然不认罪,或者避重就轻、推卸责任,甚至嫁祸于人。坦白从宽强调的是,嫌疑人作出真实自愿的供述,法律对他进行宽缓的处理,所以两者并不矛盾。”
尽管对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沉默权产生的具体时间,学界还有不同程度的争论。但是就两者产生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学者们观点则趋于一致。从职权宣誓程序和纠问程序中,根据基督教的学说和教义中产生“不自我控告的权利”,再由此产生“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进而发展出具体的沉默权制度。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在前,沉默权的提出在后,这已渐趋成为学界的共识。
新刑诉法保留了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这样的规定既赋予了犯罪嫌疑人不应证实自己有罪的权利,同时要求其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义务,对于不如实供述自己有罪的,不强迫其供述,也不加重处罚,而对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则依法予以从轻处理,这就实现了鼓励认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在立法思路、理念和技术上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笔者认为,任何权利需要均衡配置,否则会顾此失彼,实践中相关案件比比皆是。如过分强调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保持沉默的权利,并在一开始讯问时就提醒其可以沉默,必然会使得侦查机关对犯罪的侦查力度有所降低,不利于查明事实真相。因此,根据目前的社会状况,我认为选择默示的沉默权制度是比较合适的,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就是这种沉默权制度的法律依据。既符合国际公约的要求,也符合中国的国情、更符合讯问规则中的基本人伦理底线。
三、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法律适用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一《刑事诉讼法》上“干瘪瘪”的条文,如何才能转化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是在《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任务完成之后,每一个法律人都应该深思的问题。鉴于此,笔者认为,秉承传统上的“制定法”理念,我们在未来的刑事案件司法实践过程中坚持以法定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否定如实供述义务,进而在制定如实供述与自愿认罪的认定标准上进行表述,具体如下:
1.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如实供述不影响确认无罪
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如实供述不对其无罪产生实质影响的情况下,不受任何限制的直接宣告无罪将是最佳选择。因为在该种情形下,虽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放弃适用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之权利,如实供述或自愿认罪,但基于我们一般法理上认定的“理性第三人”视角去思考显然违背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事实上无论只是部分认罪还是完全否认,我们就不去考虑是否是受到威逼以及威逼的情形,都应直接认定其无罪,这才是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之原则的准确表达。
2.对确定未受强迫而主动供述之情形的认定
在我们能够掌握资料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未受到强迫而主动供述之情形下,我们应该直接认定这是其放弃援引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不管公安机关是否掌握,不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在何种具体情形下如实供述,更不考虑如实供述是否有助于司法机关完成侦查和实现举证,这就降低了我们检察院在现有立法条件下难以具体掌握的“如实供述的时间节点”和“其他司法机关是否未掌握”两个要素,均认定为如实供述,并一律予以从宽,从而有效彰显出司法的效率原则。
3.自愿认罪情形的谨慎适用
笔者始终认为,我们在对自愿认罪的认定环节上是不应该受审讯的时间与次数规制,其合理性在于程序的简化将有助于我们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自愿认罪之情形,避免遗漏自愿认罪或将自愿认罪转化为如实供述。资源认罪的情形应该慎用,要注重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承认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即要求其对已造产生的犯罪后果,手段、对象和犯罪动机等基本要素的认可,才应当认为是其已经自愿认罪。同时要对其想不起来、对非基本犯罪事实的异议,要采取不影响自愿认罪认定的立场。
参考文献:
[1]郎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与适用》.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
[2]孙谦,童建明主编.《新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
[3]陈光中等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樊崇义等.《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研究报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