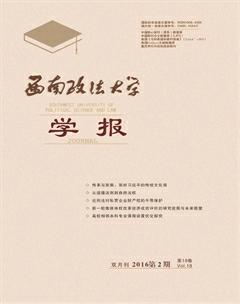唐代佛禅背景下“意境”理论的嬗变
丁红丽
摘 要:“意境”是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文学理论中的“意境”论最早见于唐代王昌龄提出来“三境”论。王昌龄的三境论在结构框架上借鉴了佛教“三别义”论,而其中“意境”的内涵界定又受到禅宗“空”的思想影响。继王昌龄之后,唐代诗论家皎然与司空图对意境理论做出了新的论述,他们的理论也是唐代佛禅思想发展的背景之下形成的。
关键词:佛禅;王昌龄;意境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2.04
一、“意境”理论之概述
“意境”是中国文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审美范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也最有世界贡献的一个方面”[1],它的形成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思想的综合影响。
中国诗学中“意”的概念出现得很早,在《周易·系辞(上)》中就有关于“意”的论述:“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2]这里的“意”是指儒家圣人所要传达的道理。其后庄子进一步阐述了言与意的关系:“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3] “得意忘言”指出了“意”的主体性地位。后来“意”概念往往伴着“象”一起出现,如王充在《论衡》中有这样的论述:“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4]王充此论指出画布上的“熊麋之象”已不是客观之象了,而是承载了“意”的“意象”了。而王弼对言、象、意关系的论述更为详细:“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如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5]王弼受到魏晋玄学影响较大,他主要是从玄学的高角度论述言意关系的,他的目的在于说明“言不尽意”的问题,故他十分强调“象”在传达“意”过程中的重要性,“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圣人所传之“意”以“象”为媒介可以通过语言得以传达。 直到南朝时,刘勰首次将“意”与“象”概念用之于文学:“然后使傅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6]此处的“意”是指作者在生活所中产生的感受,当它们受到外物“象”的感召而发生激荡,与外物“象”相契合,这就形成“意象”,意象是作者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互相渗透融合的艺术形象。
“境”的概念则是与“界”联系在一起的。《周礼·夏宫·掌周》有“凡国都之竟”句,下释说:“境,界也。”《说文解字》中对“界”的解释是:“界,竟也。”段注云:“竟俗本作境,今正,乐曲尽为竟,引申凡边境之称。”可见,“境”与“界”是同义的,均有“界域”之意。佛教传入中土以来,其对“境”的阐释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如《楞严经》有“心存佛国,圣境冥现”[7]之语, “境”来表示一种宗教化的心灵空间,丁福保先生说:“心之所游履攀援者,谓之境。”[8]由此可见,佛教中“境”着重指人的主观心理世界。唐代诗人王昌龄受到佛教“境”概念的启发,将“境” 引入诗学: “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他用“境”则来指诗人主体感受的境域,这是由创作主体带着审美眼光于自然物象中搜寻得来,经过主体审美情感与物象融合而生的一种审美空间。同时,他更进一步将“意”与“境”联系在一起来表达一种诗歌的理想境界:“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这是 “意境”这一术语首次运用于诗歌理论。
可见,“意境”是意与境的统一,是主观情理与客观物象的统一,它是由意象组成的在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结构体系,显示出无穷韵味的审美空间。一方面,这个审美空间里包含着作者无限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思;另一方面,不论如何移情入境,境中含情,这个审美空间都离不开具体物象,它是情与景二者完美融合、互相生发而产生的。而“意境”这一文学理论的形成,除了受到早期传统儒道思想的影响,它的发展完善与佛教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二、王昌龄的“意境”理论的三个层次
唐代王昌龄最早用“意境”说来论诗,他在《诗格》《诗格》是否为王昌龄所作,很长时间一直真伪难辨。最早认为《诗格》是伪书的是南宋时期的陈振孙;后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为后人“依托”所作。但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诗格》为王昌龄所著。中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9]
王昌龄所谓的物境、情境、意境实际上所代表的是三类不同的诗歌类型。
在论“物境”时,王昌龄专门提及山水诗,指出那些画面感强的山水诗,由于物象很明确而需要作者“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意思是创作者应将平时经历游赏过的山水在脑海中复现,并按照自己的审美价值加以选择,并将自己审美情趣投射于其上以形成物象鲜明的意境。这样的诗歌,让人感觉身处其境,而又包含作者的情感,物象明晰。由此可知,王昌龄“物境”论主要表达的是他对山水诗创作的看法,他所认为的理想山水诗应该情景交融而物象鲜明,这是一种以“物”胜的山水境象。
“情境”则是指“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这是指抒情诗歌。“娱乐愁怨”不仅是一种抽象的情感,更要“处于身”,也就是要设身处地深切体验那种令人“娱乐愁怨”的生活情景,再经过“张于意”的艺术审美情感构思,这样才能获得情深意切的好诗,这类诗歌诗情充盈,有感而发。这是一种以“情”胜的诗歌境象。
“意境”是“张之于意,思之于心,得其真矣”,王昌龄对意境的论述最为模糊简短。实际上,通过对“物境”和“情境”的分析可推知,既然“物境”和“情境”分别为山水境象和情感境象,那么“意境”应该是一种由“意”形成的境象,这种境象最大的特点是“得其真”,即达到艺术的真实,合情合理。可是能够达到艺术真实的诗歌,其取材到底是“物”还是“情”呢,“张之于意,思之于心”的究竟是自然物象还是丰富的情感,王昌龄没有明说,但是通过对上述王昌龄 “三境”的理解,可以认为“物”和“情”在获得艺术真实的情况下都可以进入“意境”。
王昌龄在《诗格》中就意境营造的方法提出了“三格”说,他认为意境的获得首先是通过接触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而有所生发而得。自古文章,起于无作 ,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练,发言以当,应物便中[10],不论是自然物象,还是情感激荡,都必须是“无饰练”,也就是真诚不矫饰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产生具有“得其真”的诗歌意境。而且以题材而论,得之于“物境”的山水诗和得之于“情境”的抒情诗,只要做到“得其真”,同样也可以达到浑然意境。如果“物境”和“情境”在追求主客观统一的基础上分别偏重于“以境胜”和“以情胜”,那么,“意境”就是超越了具体有限的事物,进入了无限的时间与空间,形成的一种意在言外、境生象外的审美境界了。
可见,王昌龄的“三境”其实是两个品格层次的诗歌类型:有具体内容规定的诗歌境界与只有审美规定的诗歌境界,“物境”与“情境”是有着具体内容规定性的诗歌境界,而“意境”是具有审美规定性的诗歌境界。清代王国维在论及意境时说:“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11]他认为最上等的意境中,“意”与“境”应该达到一种完美的平衡,而次等意境或以“意”胜或以“境”胜,无论是哪 一种,“意”与“境”二者的平衡都被破坏了,便都是次一等的了。王昌龄“物境”和“情境”则与王国维所谓的“或以境胜,或以意胜”是一致的。也由此可见,“意境”显然是高于“物境”和“情境”的更高的诗歌境界。
三、 王昌龄“意境”论与佛教“三别义”论
王昌龄的“三境论”在结构和内容上都与佛教“三别义”论有相似之处,可能是王昌龄受佛教思想影响所致王昌龄的理论可能受到佛教的影响,学界对此有过探讨,如王振复认为,王昌龄意境论的三个层次与佛教认识世界的层次有关系。(参见:王振富唐王昌龄“意境”说的佛学解[J].复旦学报,2006(2):94-101.)本文在此基础上认为王昌龄“三境”实为两个层次,来进一步分析其与佛教认识世界的层次关系的相似性。
。佛教“三别义”论是佛教对人们认识世界的三种不同境界,《唯识论》中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分为“心”、“意”、“识”三个层次:“处处经中说心意识三种别义,集起名心,思量名意,了别名识,是三别义。”[12]24佛教依人们对世界认识的不同层度而提出这样三个术语,其中“识”指眼、耳、鼻、舌、身、意,这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最初方式,所谓 “了别”意即“了解事物事理的分别”,“了别名识”就是人们通过感官能够认识到物质世界,这是仅止于感官认识的层次,是人们对世界认识最基本和最粗浅的层次。第二层次是“意”,即“思量名意”,指的是第七识末那识。大乘佛学在六识之外又有第七识末那识和第八识阿赖耶识之说,《摩诃止观》说:“对境觉知,异乎木石,名为心;次心筹量,名为意。”[13]这里所说的“心”是第八识,它是人们智慧的最高境界;“意”则为第七识,就是说作为“思量名意”之“意”的第七识与第八识的“心”比起来是次一等的。《楞伽经》中也说“阿赖耶为依,故有末那转”,第七识末那识可转为作为根依的第八识阿赖耶识。那么,作为第七识的“意”究竟是什么呢?依佛经所言,“恒、审思量,正名为意”,即末那识具两大功能:一曰“恒”,即它永“恒”地依止于第八识即种子识,二曰“审思量”,即是指它的“思量”功能,“思虑造作、名思”,它对物质世界做出思量,故也因它未彻底斩断“思惑”而不得无上之智慧。第七识作为“最胜”之“意”,既“能生”前六识,又永“恒”地依止于第八识,因而就其“转识成智”而言,它是由人们认知世界最直观的前六识而转入具有智慧之心的第八识的关键。第三层次“心”,即佛禅所言“集起名心”,“心”指“八识”说之第八识即阿赖耶识,诸法种子之所集起,故名为心[12]25。所谓种子,是能产生前七识的根本原因,即由阿赖耶识生起诸法。若最胜心,即阿赖耶识。此能采集诸行种子故[12]24,因而又称种子识,种子识具有含藏生发前七识的巨大功能,它是前七识的根本,是世界万相存在和运行的根本。
因此,这八识实际上是两个层次,第八识为“种子识”,作为人的自然本性是人人皆有的,这其实便是“集起名心”之“心”(本心、本性),亦是圆成实性。其他七识是人感知世间万相的各种妄觉的通道,又分为两个层级,前五识大致对应于五官感觉,五官感觉为“妄觉”。“妄觉”之“境”的品格与层次是最低的,所谓“妄觉非境界”的意思是前五识远未进入真理境界。第六识所谓“意”识,已具有超乎五官感觉的意味与品性,已开始从“虚妄”不实之境拔离而趋向于“真”,但是并未到达“真”的境地。佛教坚信人人皆有之佛性即“种子”,圆成实性本身作为根因,本然地具有“祛蔽”之品性而回归于本在的澄明之境。不过,这种“祛蔽”与回归,有一动态之中介,便是第六识、第七识,而尤其指与第八识互为依转的第七识末那识。佛教坚信,人的俗念、妄觉即五官感觉必然被消解。这种消解,可以是有时间段(渐修)的,也可以瞬时完成(悟顿)。其根因是因为人之本性(佛性)因本具“依他起性”而可以向相反的两个方向发展,它向下“堕落”便跌入五官妄觉之境,它向上提升,便趋转于“圆成实”境。所以第七识的“思量”有修行之意。
王昌龄的“三境”论显然是借用了“三别义”的论述模式和结构,他也是从两个层次去界定意境的。首先,佛教的“了别名识”是针对“物”世界提出来的,“思量名意”则是针对人的主观世界“情”提出来的。王昌龄的“物境”论是依托于自然物象的生动描绘所运思营构的诗境,它偏向于客观景物的生动描绘,讲究自然生活之景的再现;“情境”论指主体情感向外放射,由情生景创造出来的艺术空间,它偏重于主观情感的传递,这两个层次与佛教中的“识”、“意”是相对应的。更重要的是,王昌龄借用了佛教“三别义”中最高义“心”的内涵来论诗境, “心”是佛教中的最高境界“圆成实性”,其内在规定性便是“真”,它把世间万相都看成虚妄,它认为人只有脱离世间虚妄才能去妄归真,而要想脱离“眼耳鼻舌身”这些由感官可感知的具体物象世界,需要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即“意”,它其实是以“真”去统摄“物世界”与“意世界”。王昌龄论“意境”以“真”作为最本质特征去规定其内涵,其实也是以“意”去统摄 “物”和“情”,与佛教中“心”的层次最高一样,王昌龄“意”的层次显然高于“物”与“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