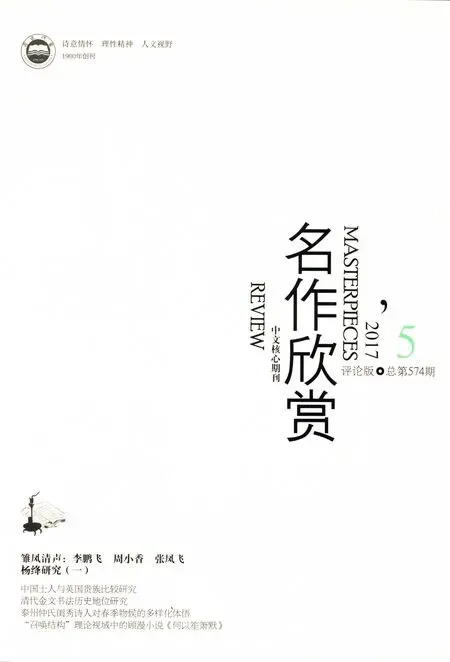“夹缝”里的存在之诗
——漫谈王立世《夹缝里的阳光》
⊙王宁
“夹缝”里的存在之诗
——漫谈王立世《夹缝里的阳光》
⊙王宁
摘要:诗人既是一个锐利的洞察者,又是一个勇敢的思想者。即使诗人仍处于“夹缝”当中,仍属于世界的弱者,依然没有放弃对阳光的思考和追求。王立世的这一类诗,基本上是以口语的形式,在直抒胸臆的基础上完全占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地。他的诗,一直处于“好懂”的状态里,这正是诗人低调、纯朴的个性使然。
关键词:王立世60后诗人《夹缝里的阳光》批判现实主义
一
《夹缝里的阳光》主要收入诗人王立世近三年发表于国内外报刊的一部分诗作,读这部诗集,不能绕开他的代表作《夹缝》,在这首短小而意味深长的小诗中,美好的花、草、鸟、阳光都失去了往日的美好,给人沉重寂寥压抑之痛感,确是写出了人类生存的苍凉。夹缝,是他对自身生存语境的一种认知与确认;而所谓阳光,也只是诗人对艺术与自我确认过程中留下来的隐喻与象征之物。
二
真正的诗人都具有特立独行的品质,一生都在苦苦寻找灵魂的家园,而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又形成了令人压抑的“夹缝”。王立世有一首诗《这些年》,是诗人对世界与自身存在认知的有力佐证。当这个“朋友只剩下几个”的世界一再现形,当“鬼鬼祟祟的市侩”的出没成为常态,诗人关于“命运的安排”,其实更多的是被动和无奈,就像他笔下任人摆弄的《锁子》。也许的确如诗人所说“时光会擦掉一切”;可是“那些最突出的部分”依然在,依然很突出。
三
玛拉美说:贫穷,但是听到风声也是好的。王立世在他的《留在此岸》的“此岸”里,以自己的“风声”,告破于自我的“码头”。不过,中国诗人的“声”,更得益于“隐士一样”的传统文化与内心生活,但不管怎么说,诗意的生活,正是理想的生活之一,而要拥有“二亩薄田”的桃源式生活,必须抛弃很多“掉进漩涡的危险”,或者说,必须剔除那种与艺术丝毫无补的危险性可能。
四
王立世的语言,更多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部分。换句话说,王立世更多的是站在中国的大地上,更多的是以中国文化为写作背景,并一次次去完成诗的。他诗中的意象,从不复杂,也不叠加,而是以单纯的一个面孔出现。单纯,是好的,好在不是单薄,好在这种单纯的“具象写作”,更易为人所接受和理解。
王立世以自己的语言方式,行走在这个世界上。沧桑世故,风云变幻,都在他的诗里得到比较恰当的呈现与表述。也许,写作方式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有效的表达。什么是有效?有效,就是一个诗人——在时间和空间里,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艺术把握;而这种写作,肯定会透露出更多批判主义的思想意识。王立世的诗里,就不时地传达出这种意念,这也是可圈可点的良好部分。
五
实际上,王立世的很多诗都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与意识。他的《胡子》固然很短,却通过对胡子的长与短,对人间某种虚伪的世态进行了艺术性的挞伐,可谓入木三分。还有他的《人兽》《伤口》《发现》等诗,尤其《发现》一诗,当“我”发现“焦虑像一群滚动的石头”,正是人彻底撕掉伪装的时候。这首诗极具自嘲的性质,诗中的“我”既是一个个体,同时又是一个集体的代称;风雨中的脸,既是自我的又是很多人的;而“伪装”,必是诗人彻底撕开世界的伪装。这首诗无不透露着人类生存的极大的无奈性,正如诗人所说“多年来,我只顾埋头赶路/没顾上看一看沿途的路标/有一天,突然发现/离我想去的地方越来越远”。为什么“越来越远”?皆是由于“夹缝”的存在,皆因生存的“夹缝”感,为人类带来致命的挤兑所致。而诗人的存活,更是“夹缝”导致的囚徒的命运。
六
诗人,都是活在一个寻找本真自我的过程。王立世也不例外,他的诗《今天》对自我进行了义无反顾的理想表达——“寻找那颗遗失多年的心”。应该说,这种“心”的存在以及诗人所追寻的理想之境,均有一个难以绕开的前提,那就是诸多红尘里太多的、过于庞杂的“鸟事”的“草丛”。诗人,以一种晴空式的心态来面对“今天”的现实与生活;如果不这样,也就不是诗人了。正是还有一颗纯真之心的存在,所以诗人就具有了“拨开草丛”的力量与灵魂。
七
诗人在这个时代是被挤兑的人种。王立世也不能逃开这种命运,至少诗人的诗几乎完全在裸露这种醒世的觉悟,至少诗人在这个麻木不仁的世界,敢于以正义的眼光来洞穿众生相的糟糕部分。什么是诗人的存在,什么又是诗人的作为,至少一个诗人不能少去一双锐眼。诗人既是一个锐利的洞察者,又是一个勇敢的思想者。即使诗人仍处于夹缝当中,仍属于世界的弱者,依然没有放弃对阳光的思考和追求。王立世的这一类诗,基本上是以口语的形式,在直抒胸臆的基础上完全占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地。他的诗,一直处于“好懂”的状态里,这正是诗人低调、纯朴的个性使然。
八
我关心的始终是诗本身。我注重的一直是诗意的真正现身。无论是怎样的形式或主义,只要是真诗,即具有打动人心的可能。王立世,作为60后这一代诗人中的一个,他背靠中国文化传统,并从中汲取了很多语言的养分,所以,他的诗几乎看不到、闻不出“洋味儿”。他的诗歌身体,依附于中国文化,并一再彰显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诗人通过对现实的深刻关注,对生活以及灵魂,都做了诚实的打探与提纯。
九
诗人在他的《一个殉道者的独白》里彻底而决绝地表述了自己的正义存在。总体上看,王立世的诗行走在一种传统写作的路子上。诗人并不刻意而是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顺乎自然地写出属于自己的语言次序和序列,并以自己已经认知的结构与思想,一次次来完成诗。而“夹缝”,不过是诗人思想与肉体所受的双重的磨难之地,是诗人象形处境的象征性概括之词。诗人从此一次次睁开自己的眼睛,去寻觅阳光去发现阳光去创造阳光。诗人,总是以自己的写作,不遗余力地来告破人类生存的窘境。诗人总是一次次通过有力的诗写,告诫自己,提醒自己,警示自己……
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