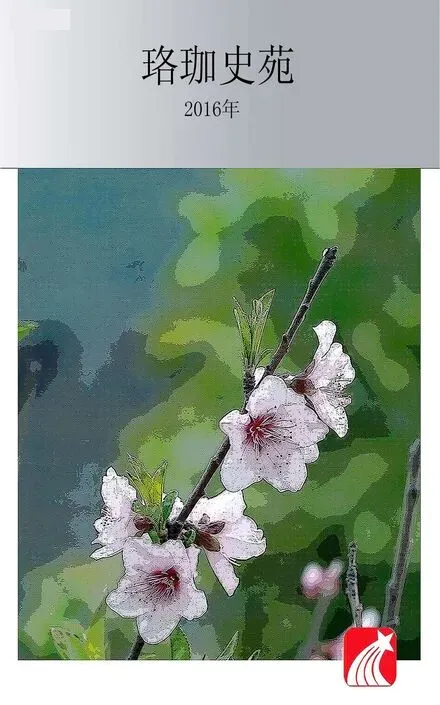承嬗离合
——关于唐代诣阙内容继承与发展的研究
刘林凤
承嬗离合
——关于唐代诣阙内容继承与发展的研究
刘林凤
汉代诣阙基本内容主要包括诣阙上章、四方贡献和征诣公车,唐代基本遵循了汉代这一传统。根据蔡邕《独断》,诣阙上章包括陈事与谢恩两部分,其中诣阙陈事涉及内容十分丰富,有称冤、请罪、褒扬地方官、揭发和告密以及谏言和献策等。四方贡献是指周边国家、藩邦的臣属与朝觐以及对外军事战争中献俘等内容。征诣公车属于汉代征召制度范畴,但是往往需要豪强贵族的举荐方可成功。唐代虽然没有征诣公车之说,但仍存在与之相似的“诣阙自举”的入仕途径。此外,在沿袭汉代诣阙内容基础上,唐代时期的诣阙亦有特色发展,即投匦制度的设立。类似于唐之前的诣阙上章和征诣公车等上书均可以投匦传递,然尽管如此,传统诣阙却与投匦并存发展,并没有偏废其一。
唐代;诣阙内容;继承与发展;投匦制度
一、引 言
“诣阙”是历史上重要的一种政治行为。①“诣阙”从史籍记载看,最早出现在西汉,延续近两千年。现代学者在对其研究的过程中,往往将其视为一种制度,尽管史书和相应朝代的“官志”记载中均没有这一制度;同时,诸多的研究将“诣阙”与“直诉”视为包含关系。本文在论述过程中只称“诣阙”内容,暂不作过多定性。阙即阙门,关于阙门的作用,《后汉书》“光和年间洛阳男子夜龙射阙事”条文下注引《风俗通》中所记载的太尉议曹掾应劭对邓盛的说语,曰:“夫礼设阙观,所以饰门,章于至尊,悬诸象魏,示民礼法也。”①《续汉书·五行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343页。由此知,阙门体现的是天子的权威,起着昭示四方,与诸侯臣子别尊卑,示万民于礼法的作用。因而,诣阙在历史研究中往往受到学者的关注。如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宫阙与园林——三—六世纪中国皇帝权力的空间构成》一文运用天空星象再现了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宫城的空间配置内涵,突出了阙门的重要作用。该文指出皇帝权力空间构成分为北方华林园的“皇帝裁判”与南方阙门“诣阙上书”两部分。②渡边信一郎:《宫阙与园林——三—六世纪中国皇帝权力的空间构成》,《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徐冲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7~125页。松本保宣的文章《从朝堂至宫门——唐代直诉方式之变迁》将诣阙上书纳入直诉范畴进行讨论。他认为上书经历了从朝堂到宫门的发展过程,且朝堂受理上书的职能是在北周到隋之间新获得的,以隋为界限,前后的朝堂内涵颇为不同。唐代的朝堂特征就在于其“受理上书这一职能的制度性发展及其相对化过程”③松本保宣:《从朝堂至宫门——唐代直诉方式之变迁》,邓小南、曹家齐、平田茂树主编:《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306页。。国内相关研究有:程民生《宋代的诣阙上诉》一文指出宋代诣阙上诉包括击登闻鼓和邀车驾两种形式,该文从进京上访的主要内容、官方对进京上访的态度和接待处理、对诉求问题和对象的处理四个方面论述了宋代诣阙上诉的情况。④程民生:《宋代的诣阙上诉》,《文史哲》2002年第2期,第81~91页。
此外,关于直诉制度及其他与诣阙相关的研究,如公车府、登闻鼓、肺石、四色匦等,亦有不少。①王伟歌:《唐代直诉制度职能述论》,《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83~86页。关于诣阙上书与登闻鼓和肺石等的关系,虽然有很多文章进行了研究,但是仍没有将这一问题说清楚,本文亦无意于对此讨论。另外限于内容篇幅,以下仅列一部分相关的文章。温慧辉:《〈周礼〉“肺石”之制与“路鼓”之制考》,《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第126~128页;黄纯艳:《下情上达的唐宋登闻鼓制度》,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下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234页;张军胜:《登闻鼓源流略探》,《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78~80页;赵旭:《论唐宋之际登闻鼓职能的强化与影响》,《唐史论丛》(第十一辑),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5页;马俊民:《唐代匦使院制考论》,《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第45~50页;董俭:《唐宋时期的匦函投书》,《档案学通讯》1991年第1期,第49~50页;杨一凡、刘笃才:《中国古代匦函制度考略》,《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第79~91页;毛蕾:《唐“匦制”设置地点小考》,《唐史论丛》(第十一辑),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9页。其中,刘鸣《“公车上书”之概念源流考》一文较之于之前的研究,其结论值得认可。该文从汉代的“公车”含义出发,否定了《辞海》和《辞源》对于公车的解释,指出公车应有官职和宫门两种内涵。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于公车的职能及其演变作了相关的论述,并指出公车概念的演变与“安车蒲轮”有关。②刘鸣:《“公车上书”之概念源流考》,《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93~96页。
另需注意的是,武则天掌政时期,于垂拱二年(686年)设置的“四色匦”,与诣阙有一定的承继关系;而这点,已有的学术研究多是从内涵相近的角度,笼统地将匦制与诣阙归为一种。关于匦制与诣阙的关系下文将会进一步说明,此处不作讨论。
综上,本文即是依据《汉书》《后汉书》中关于诣阙的记载,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诣阙的史料记载梳理以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而对唐代的诣阙内容及发展进行分析,旨在从侧面揭示唐代诣阙的承嬗离合。
二、汉唐间的诣阙内容
关于“诣阙”行为的最早起源,一般追溯到与诣阙功能类似的、相传夏代之前就已存在的谤木和夏禹时期的谏鼓。①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91页;黎翔凤:《管子校注》,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47页;另外关于谏鼓和五声关系,可参见钟肇鹏:《鬻子校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4页。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诣阙活动一直沿存、发展,并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相继出现了与诣阙关系密切的登闻鼓、肺石等装置。此外,从可见的记载中知,汉代公车司马令职责在于诣阙上书的文书处理以及传递。②《汉书》卷19,中华书局版1962年版,第728页。《后汉书》卷35《百官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79页。直到唐代,公车司马令被废除。公车司马令虽然不存,但是其承担的职能却得以保留,并转移到唐代外朝机构中。③松本保宣:《从朝堂至宫门——唐代直诉方式之变迁》,邓小南、曹家齐、平田茂树主编:《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
《汉书》记载:“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年复为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④《汉书》卷19,中华书局版1962年版,第728页。《后汉书》进一步介绍,云:“公车司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⑤《续汉书·百官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79页由此知,公车司马令的职掌也就是汉代诣阙三项基本内容,分别是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和征诣公车。关于章,蔡邕《独断》中作了解释,曰:“凡群臣上书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章者,称‘稽首上以闻’,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⑥李林甫等:《唐六典》卷8,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41~242页。
这段记载可以明确以下两点:第一,汉代诣阙一般用“章”;第二,谢恩、陈事是诣阙上章的两种行为;且它们使用的文书遵循“章”的格式。按此,结合史书记载,唐代诣阙内容亦大致可分为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征诣公车三种。但是唐代并没有征诣公车之说,而是有与之近似的“诣阙自举”;此外,唐代“群臣诣阙上书”是一种礼仪性活动,与汉代的“群臣上书”中“吏民上章”有内涵上的差异。前者似乎只是后者的一个方面。所以本节将基本遵循汉代诣阙三项基本内容,并结合唐代实际,对唐代史书中诣阙内容的记载加以分析,以明晰较之于唐前,唐代诣阙内容方面的不同以及其作用。
(一)诣阙上章
1.诣阙谢恩
“诣阙谢恩”在史籍中有很多记载,今只按朝代顺序,节举正史中所见记载,如表1所示。

表1 汉至唐的诣阙谢恩①表中所引各书版本分别是:《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陈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版;《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续表

续表
据表1,诣阙谢恩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皇帝视疾于臣民,如皇帝遣医问药于霍光之事;(2)得罪而被赦免,如《晋书》卷33《石苞传附石崇传》中,石崇其兄石统获罪而遇大赦得以免罪,并诣公车门上书谢恩;(3)拜官袭爵,则如吕布被拜为大将军、宋均子宋条获太子舍人官、高丽王袭爵辽东郡公;(4)外邦臣属,诣阙谢恩;(5)还有一种现象是,臣子在病疾情况下,上书谢恩,往往请求的是免官养老,或者为子弟谋求荫官的内容;(6)一些重要礼仪活动,群臣百僚诣阙谢恩,如《后汉书·礼仪志上》中载:“明帝永平二年(59年)三月,上始率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明日诣阙谢恩以见礼遇大尊显故也。”①《续汉书·礼仪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108~3109页。明帝永平二年这次“诣阙谢恩”与唐代“群臣诣阙上表”的性质类似,均是礼仪性质的活动。《通典》“群臣诣阙上表”条下详细描述了上表礼仪及流程:
前一日,守宫设文武群官次于朝堂如常仪。
其日,量时刻文武群官集,俱就位各服朝服。奉礼设群官位于东朝堂之前,近南,文东武西,重行北面,相对为首。设中书令位于群官之北,南向。设奉礼位于群官东北,赞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礼帅赞者先就位。谒者引群官各就位。礼部令史二人,绛公服,对举表案立于奉礼之北,西面。立定,典谒引中书令出就南面位。礼部郎中引表案诣中书令前,郎中取表以授,中书令受表,郎中、举案退复位。奉礼曰:“再拜。”赞者乘传,群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中书令以表入奏,出复位,南面称“有诏”,群官再拜。宣诏讫,又再拜。谒者引为首一人进,北面受表,退复位。舍人引中书令入,谒者引群官还次。②《通典》卷130,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347~3348页。
虽然,《汉书》中没有明确记载类似这种活动的仪式、流程,但是可以推测,汉代时期这类活动即便是与唐代的负责机构不同,但是形式也有类似之处。唐代的诣阙谢恩基本遵循了上述几条内容。除官后须诣阙谢恩基本成为一条定制,如唐代韦处厚拜为兵部侍郎而往思政殿诣阙谢恩等,①《旧唐书》卷159,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84页。以及崔郾在昭愍即位后,选侍讲学士,后转中书舍人,入思政殿谢恩,等等。②《旧唐书》卷155,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18页。类似内容不再逐一列举。但是有一处没有在唐代外的其他正史记载中看到,即《旧唐书》卷150《德宗诸子传·珍王》曰:“旧例,皇姬下嫁……制下礼官定制曰:‘升,北面再拜,跪奠于姑席前。降,东面拜婿之伯叔兄弟姊妹。已而谢恩于光顺门……然后会于十六宅’。”皇家婚嫁是否需要诣阙谢恩,唐之前有无尚且不能肯定。
2.诣阙陈事
诣阙陈事包含丰富的内容,包括有谏言、献策、称冤、褒扬地方官、揭发和告密、请罪等。这些内容不是单一的互不关联的,它们之间有时也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
(1)诣阙称冤、请罪。
史籍中诣阙称冤和请罪的记载不胜枚举,仅节取史籍记载中几例,见表2。诣阙一般以文书为承载,但也有很模糊的情形,如表2中诣阙称冤、诣阙请罪便有。于诣阙称冤,如《汉书》卷44《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中“厉王驰诣阙下,肉袒而谢”;③《汉书》卷44,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36页。《旧唐书》中《来俊臣传》“万岁通天元年,(来)俊臣因令其党罗告斛瑟罗反,将图其吡。诸蕃长诣阙割耳剺面讼冤者数十人,乃得不族”。《后汉书》卷54《杨震传》中有“顺帝即位,震门生诣阙追讼震事”。④《后汉书》卷54,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67页。唐代也有此类情形,如《旧唐书》中《来俊臣传》“万岁通天元年,(来)俊臣因令其党罗告斛瑟罗反,将图其吡。诸蕃长诣阙割耳剺面讼冤者数十人,乃得不族”。⑤《旧唐书》卷186,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40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诣阙称冤情形,与汉代相比并没有什么差异。

表2 诣阙称冤

续表
到了隋朝,对于诣阙称冤这种“越诉”就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①诣阙称冤本质上就是一种越诉,标准在于是否超出当朝法律之外。《隋书》卷25《刑法志》记载:“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自诉。”①《隋书》卷25,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2页。唐代很好地继承了隋朝这一制度,并且加以丰富。《唐六典》卷六《刑部》记载:
凡有冤滞不申欲诉理者,先由本司、本贯;或路远而踬碍者,随近官司断决之。既不伏,当请给不理状,至尚书省,左、右丞为申详之。又不伏,复给不理状经三司陈诉。又不伏者,上表。受表者又不达,听挝登闻鼓。若茕、独、老、幼不能自申者,乃立肺石之下。(本注:若身在禁系者,亲、识代立焉。立于石者,左监门卫奏闻。挝于鼓者,右监门卫奏闻。)②李林甫等:《唐六典》卷6,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2页。
唐代的诣阙称冤沿袭了隋代的制度,但是不同的是唐代对之加以了完善。对于诣阙上表不达则挝登闻鼓;而茕、独、老、幼者不能挝鼓者,则立肺石之下;被拘禁的罪人,则由亲人、相识者代为立肺石下。登闻鼓和肺石虽然不被包含在诣阙基本内容中,纵观魏晋南北朝史籍可知其与诣阙称冤密切相关,限于篇幅,本文对于这种关系暂不作深入探讨。
关于诣阙请罪(详见表3),如《后汉书》卷99上《王莽传》中“张竦与刘嘉诣阙自归,莽赦弗罪”③《后汉书》卷99,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082页。。但是有时候诣阙称冤与诣阙请罪互相为表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后汉书》卷24《马援传》中“严与援妻子草索相连,诣阙请罪”④《后汉书》卷24,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46页。。这里严与援妻子虽是名义为诣阙请罪,实际是希望借此诉冤,乞求获得宽赦。唐代的诣阙请罪亦多是出于乞求获得恩赦的目的,如至德二年(757年),郭子仪“收合余众,保武功,诣阙请罪,乞降官资”;⑤《旧唐书》卷120,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51页。以及唐末“(杨)复光遣判官吴彦宏谕以朝廷释罪,别加官爵,仙芝乃令尚君长、蔡温球、楚彦威相次诣阙请罪,且求恩命”等。①《旧唐书》卷200,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91页。

表3 诣阙请罪

续表
(2)诣阙褒扬地方官与揭发。
褒扬地方官(详见表4),在汉代正史中几乎没有记载,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就不存在。第一次出现在正史记载上的是《梁书》,如卷27《陆襄传》“在政六年,郡中大治,民李睍等四百二十人诣阙拜表,陈襄德化,求于郡立碑,降敕许之。又表乞留襄,襄固求还,征为吏部郎……”①《梁书》卷27,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10页。此外由于政绩优异,民众请求留任的情况也很多。如《梁书》卷29《高祖三王传》记载:“寻有诏征还,民曹嘉乐等三百七十人诣阙上表,称绩尤异一十五条,乞留州任。”①《梁书》卷29,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28页。更有甚者请求为某官升职,如《梁书》卷24《萧景传》中“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诣阙,表请景为郡,不许”。②《梁书》卷24,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68页。其他各朝,如南朝陈、北魏、北齐、北周、隋等均有上述现象,在此不作一一说明。

表4 褒扬地方官

续表

续表
与褒扬地方善政相对的是揭发地方官的行为。唐代之前,记载的百姓揭发地方官很明确的是《魏书》和《隋书》,而且很明确地只有如下几条,分别是《魏书》卷20《安乐王传》,《魏书》卷44《薛虎子传》以及《魏书》卷八十九《郦道元传》;《隋书》卷50和《隋书》卷56(详见表5)。而在这之前的要么不见于正史记载,要么仅限于告发谋反的范畴。对于唐代,不论是褒扬地方官善政,抑或是揭发地方官不法的行为,史书记载均十分丰富,为后人勾画出的是一个较为丰满、生动的王朝形象。

表5 诣阙揭发

续表
(3)诣阙谏言。
诣阙谏言者一般认为只有当朝谏官或者其他官员上谏(详见表6)。事实上,地方官员或者一些知识分子,也往往通过诣阙上章劝谏统治者。如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朱穆得罪宦官而被贬为刑徒,当时的太学生数千人上书谏言,乞求宽赦朱穆;①《后汉书》卷43,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70页。唐代开元五年(717年)河南府人孙平子诣阙上书认为中宗不应迁于别庙之事;①《旧唐书》卷25,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52~953页。则天载初年,俞文俊上书武则天认为新丰因风雷山移动,并不是祥瑞,因此而改新丰名为庆山并不合适②《旧唐书》卷18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83页。。
此外,史书记载中有,通过“讼”或者“自讼”的方式进行上谏,但却是意图洗刷冤屈而作的上书;换言之就是通过谏言的方式进行诉冤。如朱穆案中,《后汉书》记载为“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讼朱穆”。再如东汉孔僖“上书肃宗自讼”。但是这样的表述在后世史书记载中很少出现了。

表6 诣阙谏言

续表

续表
(4)诣阙献策。
诣阙献策,顾名思义即向上级提供策略等建设性意见的行为。如《魏书》中记载:“(太清初年间),(萧)景率军围谯城下,退攻城父,拔之。又遣行台左丞王伟、左民郎中王则诣阙献策,求诸元子弟立为魏王,辅以北伐,许之。”①《梁书》卷56,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40页。唐代的诣阙献策,典型的一例则是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润州人陈磻石诣阙上书解决了当时“湘、漓泝运,功役艰难,军屯广州乏食”的困境。②《旧唐书》卷19,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52~653页。
(5)其他。
诣阙陈事除上述之外,还有辞任和坚决拒绝某些事的内容(见表7)。

表7 诣阙固辞
其他类似情况,如东晋安帝时期,刘裕拒绝天子的封官,即便皇帝亲自去公第挽留、百僚敦劝,刘裕仍惶惧不已,坚决拒绝。①《宋书》卷1,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13页。唐代亦有这类情况。穆宗时“令中使手诏、绯袍、牙笏、绢二百匹,往洛阳惠林寺宣赐。源受诏,对中使苦陈疾甚年髙,不能趋拜,附表谢恩,其官告服色绢,皆辞不受”②《旧唐书》卷18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90页。。
(二)四方贡献
四方贡献指的是周边国家以及藩邦对于中央朝廷的示好、认可、臣属以及军事战争的献俘、献捷活动。这类活动的进行是一种礼仪展示,然本文不意描述这种宏大场面,故表8只就汉至唐时期四方贡献的行为进行梳理。如《汉书》卷七十《傅介子传》中记载元凤中,傅介子出使楼兰,计杀楼兰王,“遂持王首还诣阙,公卿将军议者皆嘉其功”③《汉书》卷70,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02页。记载同样事的还有《汉书·西域传》:“介子遂斩王当归首,驰传诣阙。”(《汉书》卷96,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8页)。《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二十五年(49年):“南单于遣使诣阙贡献,奉藩称臣……是岁,乌桓大人率众内属,诣阙朝贡。”④《后汉书》卷1,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7页。《后汉书》卷二十六《伏隆传》记载:“张步遣使随隆,诣阙上书,献鳆鱼。”⑤《后汉书》卷26,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99页。

表8 四方贡献

续表

续表
(三)诣阙自举
汉代公车司马令承担着选拔人才的重要职责。《汉书》卷71《隽不疑传》中“暴胜之遂表荐不疑,征诣公车,拜为青州刺史”①《汉书》卷71,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35~3036页。;再如《后汉书》卷三十下提及,顺帝时,灾异屡见,于是“阳嘉二年(133年)正月,公车征,凯乃诣阙拜章……书奏,帝复使对尚书”①《后汉书》卷30,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54~1057页。。又如,西汉朱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②《汉书》卷64,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91页。。
从上可以看出,征诣公车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征召(被动);二是诣公车(主动)。据《汉书·隽不疑传》看,其存在受到推荐,随之得到征召并诣公车的轨迹;朱买臣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其最初是待诏公车(说明其之前进行了一些活动希望得到公车令的赏识),但是显然没有成效,随之得到推荐才得以被征召诣阙。郎凯则是在公车征召的情况下,上表拜章得到重用。
上述例子似乎很难体现主动诣公车成功的一面,多是需要一些贵族豪强推荐才得以成功。除此以外便是通过朝廷有征贤良的需求时才有可能被重用。如《汉书》卷51《东方朔传》说到汉武帝初即位,征天下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当时“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衔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③《汉书》卷65,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41页。。
汉代以后,三国时期自不必说,各政权急需有才之士,征用人才没有统一标准。但之后的统一政权里,史书记载中并没有出现“征诣公车”的内容。但是推荐、毛遂自荐的情况还是有的(见表9)。如《晋书》卷48《段灼传》“然于时人士诣阙上书荐莽者不可称纪”④《晋书》卷48,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46页。。
唐代并不存在征诣公车的行为,然有与“征诣公车”近似的“诣阙自举”。诣阙自举没有明显的被推荐迹象,其行为应当更具主动性。《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上》中有“十五年春正月戊寅,制草泽有文武高才,令诣阙自举”⑤《旧唐书》卷8,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0页。。《旧唐书》卷13《德宗本纪下》中“阳城以褐衣诣阙,上赐之章服而后召”;①《旧唐书》卷13,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5页。《旧唐书》卷185下说到“仪凤中,(裴怀古)诣阙上书,授下邽主簿”②《旧唐书》卷185,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07页。。《新唐书》卷197《循吏传》中“宝应初,(罗珦)诣阙上书,授太常寺太祝”③《新唐书》卷19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25页。。由此也可以看出,唐代前期,似乎除科举制度之外,诣阙自举这种强调自我推荐的入仕行为已普遍发展了。

表9 征诣公车④表目仍用征诣公车,以示汉至唐之间的继承变化。

续表
上述各表是在汉代诣阙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对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情况的简单梳理。从中得出结论:汉之后,各朝诣阙内容基本延续了汉代的规定。特别是唐代诣阙内容,通过史书记载,都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三、唐代诣阙内容的外延
与传统诣阙作用类似的另一种制度在唐代被建立,即投匦制度。《新唐书》载:“武后垂拱二年(686年),有鱼保宗者,上书请置匦以受四方之书,乃铸铜匦四,涂以方色,列于朝堂: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丹匦曰‘招谏’,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白匦曰‘申冤’,在西,陈抑屈者投之;黑匦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谋者投之。以谏议大夫、補阙、拾遗一人充使,知匦事;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其后同为一匦。”①《新唐书》卷4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06~1207页。
四色匦包括了诣阙基本内容中诣阙上章(诣阙陈事和谢恩)及征诣公车。但是从史书记载看知匦使等官员似乎只与冤屈有关,不知为何。知匦使职责是“掌申天下之寃滞,以达万人之情状”。②李林甫等:《唐六典》卷9,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82页。知匦使的职掌就是受状后向上递状,紧要事务就自行处分,之外的则递与中书和理匦使来申奏。真正负责匦状处理的应该是理匦使而非知匦使,所谓匦使之“职举则天下之壅蔽所由通也”③《文苑英华》卷496,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2541页。。如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侍御史徐有功上疏论天官秋官及朝堂三司、理匦使失职时,就说到“三司受表及理匦使申冤不速与夺,致令拥塞,有理不为申者,亦望准前弹奏贬考夺禄”④《旧唐书》卷85,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19页。。据《唐六典》,侍御史四人,其职有奏弹、三司、西推、东推、赃赎和理匦六种。资历深者判台事,知公廨杂事;其中一人知西推、赃赎、三司;一人知东推、理匦之事。⑤李林甫等:《唐六典》卷9,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80页。关于知匦使与理匦使官员构成及其发展变化,拟另文探讨。据上,侍御史徐有功弹劾三司和理匦使失职,他本人应不负责三司或者理匦这两种职务。由上也说明,理匦使真正负责案件的处理。
匦的设置及其组成人员的完备,标志着一套新的行政程序的开通。“匦使受状”取代垂拱元年制文中“御史受状”就是这种变化的结果。⑥但从结果看,二者也不是绝对的不同,毕竟匦设置后,匦使官员构成有御史等清白官。原因在于垂拱元年(685年)的“御史受状”取代的是上诉称冤的“登闻鼓和肺石”防守负责人,而四色匦的“匦使受状”又包含诣阙基本内容,如申冤可投匦。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理匦使崔造的建议即可佐证,其曰:
亡官失职、婚田两竞、追理财物等,并合先告本司。本司不理,然后省司。省司不理。然后三司。三司不理,然后合报投匦进状。如进状人未经三处理,及事非冤屈,辄妄来投状者,不在进限。①《唐会要》卷55“匦”条,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956页。
另外,投匦制度的建立并不是完全取代了原先的诣阙内容,在历史记载中随处可见,不通过投匦,诣阙所上之书一样可以传达进宫阙深处,得以处理。投匦制度是诣阙内容顺应时势发展的结果,是诣阙上书内容体系逐渐外延,发展出的更具象的一种制度。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唐代的诣阙内容基本遵循汉代以来传统,基本内容包括有诣阙上章、四方贡献、征诣公车。但是,在沿袭汉制诣阙内容基础上,唐代诣阙亦有特色发展,即匦制的建立。匦函的内容虽然几乎囊括了唐之前一切诣阙上章和征诣公车的内容,但是匦制却并没有取代诣阙上书地位而单独存在。其中原因,不论是从南衙北司两条发展线索来解释,还是从当时皇帝意图集权来看,都揭示了唐代在制度上的发展与探索。特别是,不同于之前的朝代,诣阙内容在唐代普遍得以载于史书中,也正彰显出唐朝的气度以及侧面反映庙庭与草野的互动关系。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