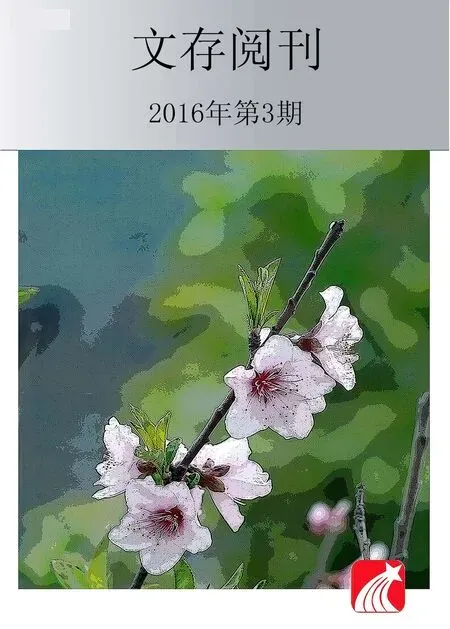两位退翁先生与一条隐秘山谷
陆波
两位退翁先生与一条隐秘山谷
陆波

位于寿安山下樱桃沟的退翁亭,上面有周肇祥题王维诗。
春暖花开的日子,我却躲在房间里写作那条叫樱桃沟的山谷。今人只见莳植花开,携手相游朗朗艳阳天下,春和景明,万象新颜,却已不知这条山涧之中曾经的隐士茅屋,僧家别院,已被岁月漶漫湮灭。时间以不经意的姿态星移斗转,散落的陈年旧事难以寻觅。
北京有两处叫“樱桃沟”的地方:
一处名符其实,以盛产优质樱桃而闻名,即门头沟妙峰山下的樱桃沟村。每年采摘季节,紧锁的樱桃园大门敞开迎客,城里人欢天喜地涌入采摘。采摘的价格必定是昂贵的,但城里人消费的是山村里纯天然的新奇感。
这里虽然地名叫“沟”,实则是一片较为开阔的山间平坝,别墅次第错落,据说这是旧村改造的结果,大概其间也夹杂了不少城里人跑来买地置产。它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闭塞山村,民居别墅化,常年有大动干戈的建房装修,机械轰隆,尘土飞扬,圈墙占院。建筑风格土洋混搭,出位且世俗实用,透着富有者们肆意张扬的个性,以及将金钱堆砌给房屋的快意恩仇。
但实际上,这个村子最值钱的房子,是被关在樱桃园大墙之内的一排破旧民居——清末帝溥仪英文老师庄士敦的别墅,当年这个爱丁堡人偏隐此地消暑度夏。我一直困惑的是如果他五更天骑驴出山,天黑前能赶到西直门吗?如何教授溥仪的英文课程?这栋民房完好保存下来,且好在没有好事者给它续貂装修改造,一副破败飘摇状,正是百年铅华就剩下风骨,倒也另有风情。
现代别墅与清末别墅跨越百年光阴,相映成趣。这时,你只需抬头北望,便明白大家为何青睐此地风水:北山之上赫然矗立着仰山栖隐禅寺,这是金章宗当年所建西山八大水院之一的灵水院,千百年来高僧大寺,声名显赫。
虽然依止大寺,风水显耀,且有樱桃之实,但此樱桃沟的名气却并抵不上另一处不见樱桃的樱桃沟,那是一片位于香山植物园西北处的风景区。遑论香山、植物园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名气,即使是北京市民,一说樱桃沟,想到的也必是植物园、卧佛寺、水源头,一幅百花深处,古佛晨钟,溪流淙淙之画面。如果不是节假日游客云集,找个平常日子,山林里信步游走,定是可以觅得几分世外禅意。
这条香山樱桃沟(也叫植物园樱桃沟)位于卧佛寺西北方向,乃西山诸山谷最深之涧。其实,这里没有樱桃树,且我遍查文献,大多记录均称这里为“退谷”,“樱桃沟”最早见诸文字的是1785年乾隆皇帝《石壁临天池》诗注:“卧佛寺西北樱桃沟有泉至观音阁。”对于游人而言,“退谷”、“退谷”的,名字艰涩又矫情,不如“樱桃沟”活色生香。今天人们看到沟内一碣石上书“退谷”二字乃梁启超重书之墨宝。这里沟深林茂,并不适合栽植果树,倒有可能在沟的入口外——那片呈喇叭口的扇形平坦之地,曾经种植过樱桃,便以此传为“樱桃沟”。
自古以来这一片好风水便使庵寺星布,只这一条樱桃沟,如果从唐代建卧佛寺起算,至明清民国便有十数家庙宇。山林适合清修,但还有那么两位隐居者,虽在寺院门外行走,却也是试图跨出众生三界之边缘,在这山谷里隐居超过数十年。他们不仅是企图隐掉烦扰世间,甚至也是想把自己在作为一个活人的时候,找到一个活人了断的方式。这两位有个共同点就是活得有些长了,活得长就有长的不耐烦甚至耻辱,所谓寿高多辱。但他们内心却纠结于贪恋人生,又想学古避世。
第一位是明末清初之人孙承泽,后世延续清朝官方的观点,持将其“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态度来盖棺定论。虽然他有关北京历史地理、风土方物做过有价值的考察记录,以及他在文物收集方面做出贡献,但关乎大节之事,此等风雅文事便不足挂齿了。
乾隆四十一年(1776),此时,孙承泽已过世百年,乾隆提出编纂附录于《清史列传》卷七十八、七十九两卷《贰臣传》,共收录了明末清初为明清两朝服务的臣子一百二十余人的传记。实际上,这是乾隆对当朝官员保持忠心的警示录,是对一百二十余位曾为两朝服务的人士的一次精神鞭尸。乾隆在修编诏令中说:对于这些大节有亏的人,不能感念他们曾经建立的勋绩,就在生前原谅他们。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后人的人之既死就获得宽宥。今天我批准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这些既仕明又仕本朝的臣子们的所作所为,据实直书,不给他们丝毫隐饰。即让他们的所谓孝子慈孙百世不能篡改他们先人的实情!我这是以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立纲常!此言冠冕堂皇,将君权至上置于道德高点,举臣子效忠唯一君王为最高伦常,即使明臣仕清,也毕竟是亏失了大节,让后人知晓他们不值得尊重。
孙承泽即是“大节有亏”之人。他的事迹记录于《贰臣传》乙编五十。他不仅是“贰臣”,事实上他是三臣,仕明、投李、降清,节操一地,背负“三姓家奴”的骂名。
孙承泽的悲剧在于生不逢时,他于1593年出生在北京一个富裕家庭,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为明朝刑科都给事中,七品官。1644年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景山自缢,许多明朝官员纷纷模仿自尽保节,于是他也在自家书房玉凫堂书架后自缢,他身体肥胖,上吊的绳子恰巧糟粕,便直接重重摔地,引来仆从相救。他悲惧交加,不知如何作出与自己身份相符的合乎节操的“规定动作”。于是他服了几片有毒的药品,但又被自己的肠胃抗拒全部呕出。最后,他偕同长子跳自家水井,当然还是被救下,“吐血水斗余”,最终没有死成。
有后人讥笑他贪生怕死,还要表演如戏,要死就外出死去,何苦在自家院里当着仆从面贞烈殉节。说到底,他的本意实不想死,因为他只是为大明工作得以俸禄养家糊口之人,不应比肩崇祯皇帝上吊殉国的道德高度,毕竟,大明是崇祯皇帝他们朱家的,不是孙承泽家的。
对于人们只有一次宝贵的生命而言,为什么要个体牺牲给一个专权的家族?孙承泽选择向生是对君权至上以及奴化思想的背弃,并无耻辱可言。
后来他被李自成的大顺军抓了去,给胡乱封了个“四川防御使”这个不低的职位。他自称是“绝食不赴任”,但也没见他真饿死。还没等他真去了四川,大清的金戈铁马已冲进北京城。既然已失节于大顺,估计他的心理障碍已清除殆尽,没有再做出多余的不合作姿态。清廷入主北京即下令要求所有在册的明朝官员坚守原位,不必逃亡,清廷一概启用而并不以敌党相待。于是,孙承泽降清。
孙承泽入仕清廷的过程不必细究。因为有相当一批明吏出于各种原因,当然最基本的还是生存的缘由转而为清朝服务。顺治元年,他先任吏科给事中,后历任大理寺卿、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务,这些官职高过他在明朝的职位。清廷作为异族统治者将明吏当作技术性的官员,因为他们可以比较娴熟地操控国家机器的相应部件,但不会得到信任。孙承泽为清廷工作十年后以老病为由请求致仕,此时他已六十一岁,开始了他尚且漫长的二十余年退休生活。
不管怎么说,明朝遗民终是清朝的敏感人物,而他的“三易其主”使其自身的道德建构彻底垮塌,他认为没有更好的理由去谈论经学,并以儒学论道。虽然他是进士出身,却已丧失了可以文论道德文章的资格。于是,如此渴望向生的孙承泽选择了放情山水,桃源隐居的避世生活。但他敏慧的头脑还是要使用的,他不可能放弃立言著说,便转而开始对于文物方志的考察记载并立文研究,以及大量收藏和品鉴散落于乱世的各种书画作品。
他觅得寿安山下一条隐秘山谷,即今天的樱桃沟。那时候,这里有碣石上已写“退谷”二字(有可能是孙自己写的,但出于谨慎,只说来时便有),两侧山上有几处隐蔽的寺庙,他趁势自号“退翁”,修建别墅一幢,起名“退翁书房”,也叫“水流云在之居”,灵感来自杜甫“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的诗句;建造一亭,起名“退翁亭”;还在一石门上书“烟霞窟”三字隶书门额。“水源头一涧最深,退谷在焉。后有高岭障之,而卧佛寺及黑门诛刹环蔽其前,岗阜徊合,竹树深蔚,幽人之宫也。”(孙承泽《天府广记》)他继续写道:“万木森森,小房数楹,其西三楹则为退翁书屋,一榻一炉一癭樽,书数十卷,萧然行脚也。”寥寥数笔,写出了一隐逸老翁清静的山居生活。
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修撰的《日下旧闻考》记录,百余年后,“退翁亭”及“烟霞窟”石门还在,其他余迹均圮废。
孙承泽在这个叫“退谷”的地方读书、写作、会友、发呆,打来泉水烧茶煮饭,幽深静爽,不觉便是二十年已过。虽然他是龟缩起来自觉名声有污之人,但并未枉费天生的好学与勤奋。他可以被称之为著作等身,仅《四库》丛书就收集了他各种著作将近二十种。虽然《四库》对他著作的评价都不高,但这是一脉相承《贰臣传》的偏见与歧视,并不可抹杀其学术价值。孙承泽传于今天的著作有四十余部,倾尽了他毕生所思所见。《春明梦余录》、《天府广记》辑录的大量文献资料,对今天研究明朝及之前北京城市历史、地理演变沿革,方志掌故,以及明朝中央政府各官署的职掌制度都极具价值。而《庚子消夏记》则是一部关于他自己收藏的及生平所见的晋唐以来名人书画的评论集。他热爱并沉溺于那些美妙的古代字画,享受曾经拥有或今生得见那些字画的快乐,正是以此安慰了他名节有缺的沉重人生。正如他自序所言:“沧桑之后,杜门却轨,日以书画自娱,名迹灿然,备著于录。”
一座山谷,孙承泽做“幽人之隐”,却成就了另外一番学问天地,而这其间的书卷字画之乐是否可以洗涤他内心的耻辱感,就不得而知了。他活到八十四岁,在1676年离世,其一生,痛苦在入仕谋生,欢愉在山水书卷,两者相抵了。
隐士的生命毕竟有限,更多的时间山谷属于寺宇。大约从金章宗开始,樱桃沟便有寺院庙庵此起彼消。金章宗的遗迹就在今天水源头再向上方追溯,但今已不可考。在孙承泽时代他是探寻到的:“深入数里,有石洞三,旁凿龙头,水喷其口。又前数十武,土台突兀,石兽甚钜,蹲踞台下。”后人也称此为“金章宗看花台”。还有传言,说这股泉水与玉泉山泉水经地下相通,有人在此倒了油下去,玉泉山那边水出来就冒着油花。乾隆五十年(1785),乾隆皇帝游览樱桃沟水源头,其《石壁临天池》诗注:“卧佛寺西北樱桃沟有泉至观音阁,石壁下蓄有天池,流经寺前,东南引渠至玉泉山垂为瀑布。”倒是印证了这个“玉泉山水乃源自樱桃沟”的说法。
让我们梳理一下与隐士相伴的樱桃沟内外寺院:
建于唐代,历经各朝废建,至今天仍完好保存的卧佛寺(十方普觉寺),游人最爱这里的木质大卧佛以及春寒料峭时的黄腊梅。
隆教寺,成化年间太监邓铿建寺,明宪宗朱见深敕谕寺名。孙承泽时期,这里尚有僧人守寺,称“境地深邈,可供趺跏”,是个修行打坐的好地方。它在卧佛寺之北侧,明碑及古树尚存,这处遗址今天已被修整为一精致花园,有小桥流水,并山墙维护,游人罕至。
观音阁,建造在卧佛寺西的一整块大磐石之上,今天已由“阁”改“亭”了。
广应寺,大致位置在卧佛寺西南一里地,也就是今天植物园温室大棚的西北处,但今天已无任何踪迹。在孙承泽时期尚存,他记载:“寺有白松如雪,箕居其下,望见碧云、香山诸寺。”乾隆年间官员考察尚有遗迹:铁炉、钟磬,均为明朝正德年及弘治年建造。

大磐石上观音阁,1920年代,与周肇祥争水的洋人所拍。
广泉寺,在水源头向上半山腰处,明朝时既已是废寺,清人有诗句:“残碑无字记辽金”,推测可能为辽金时期建造。孙承泽时期尚有古井出水,直至清末。属于山顶之水,用于泡茶,水质上乘。民国后成为枯井,但今天遗址可寻。这里被民国时期周肇祥改为私家墓地。
广慧庵,在樱桃沟南口,即今天卧佛寺琉璃牌坊的西侧。始建明代万历十九年,虽名为庵,实为道观。广慧庵遗留建筑在今天的蜜蜂研究所内。如果说今天叫樱桃沟似乎是与清末民初这一带曾有樱桃树有关。
五华寺,是明清两朝退谷里最主要的寺院,在今天樱桃沟“红星桥”处,沿东侧继续上山前行,没有多远便可到其遗址。该寺明朝宣德年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重修。至1965年中国计量科学院借用五华寺,将仅存的五开间大殿拆除,建了几排平房,五华寺遗迹仅存两统残碑和几个石构件。
五华阁、普福庵,均在卧佛寺东不远,普福庵俗称“红门”,但《日下旧闻考》记录时(乾隆年间)已废弃,今天只留一寺名于世。
可见孙承泽说退谷“后有高岭障之,而卧佛寺及黑门诛刹环蔽其前”。卧佛寺外加上述“黑门诛刹”(庙庵)真不是妄言,这原本就是脱世修行者的一方乐土。
1917年,又有一位自号“退翁”的人来到退谷。他就是前清举人兼前清警务官员周肇祥。虽然他为清朝服务过,也在袁世凯称帝时,授上大夫加少卿衔,但这时他已在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中做事,代理湖南省省长、湖南省财政厅厅长。
这位有权势的人物来到樱桃沟,找到当时的主人,即五华寺的住持和尚商议,很快,这条沟及两侧山林便易主到周肇祥名下。这个过程是否涉嫌巧取豪夺一直为后世诟病,但五华寺自此废弃,而由周肇祥转租他人牟利。
民间传说是“周肇祥巧赚占退谷”,说当时樱桃沟五华寺只有一老和尚奉着香火,周肇祥常带些酒菜与老和尚聊天。当时北京政府正要核验房屋地契,周肇祥不知怎么把老和尚手中的土地房契骗到手,下山把樱桃沟房产土地过户到自己名下。老和尚自然耐不过这有权势的卑鄙之人,于是这段故事传到小说家陈慎言耳中,他据此写了一篇小说《斯文人》,揭露这桩丑闻。这段故事有一定真实性,用历史学家邓之诚的话说“其人实无赖,不足怜也”。
还有一种说法是周肇祥从慈禧寿膳房厨师太监郝常太那里取得退谷,而郝常泰怎么获得此地呢?说是因为他会做一种慈禧爱吃的柳叶面条,慈禧一高兴就把退谷赏给他,让他接老母来京治病居住。这个说法比较荒诞,也不能说清朝的房地产便宜到只值一碗面条钱。
比较可信的说法则出自周肇祥同僚好友许宝蘅的日记。1920年4月10日他受邀去周肇祥的“鹿岩精舍”,问起何以得此山林房舍,周说是三年前(1917)从原内廷太监厉监那里所得,而此时厉太监已经过世,他们饭后还去查看了厉太监坟塔。今天,有户外山友及文物爱好者在附近山上看到过“厉大真人塔”的塔铭,虽然石碑镌刻已漫漶不清,但仍可辨识“开山直接长春脉,出世能还不老丹”之对联,横额:“超以象外”。另外还可以得知这位厉大真人乃山东沂州人。看来他是修道之人,却守着一间凋敝的五华佛寺。民国期间北京寺院登记记录中也印证了这一点,说是五华寺位于寿安山北沟村八号,为光绪年间太监厉理宾购得修建。
看来周肇祥从厉太监处得退谷的说法比较准确,至于手段则定不光彩。因为新中国建立之初,周肇祥即遭追究并下狱,所谓罪行有“弃婢,致婢与其父自尽”,这是出了人命的大事。
周肇祥声称佛教徒,但做事并非遵循佛法仪轨,甚至有简单粗暴不择手段的特点。他曾截断水源头,在鹿岩精舍前修了一座闸桥蓄水,以致断了下游卧佛寺一带的供水。当时租用卧佛寺旁房舍的一群外国传教士便修管道抢水,以致两家发生纠纷。最终由官府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并立碑公示。说来也巧,在这群外国人中有一位是留下大量中国老照片的摄影师西德尼·甘博,即当今世界五百强宝洁公司创始人詹姆士·甘博的孙子,与中国渊源深厚,他竟用相机拍下了这桩公案的“裁决书”,证实了“抢水纠纷”。
周肇祥不愧是“无畏居士”,他干的另一件“蛮事”是阻止故宫文物南迁。周肇祥于1926 年9月至1928年2月担任古物陈列所所长。这个陈列所后来合并至故宫博物院,其于1914年在故宫文华殿和武英殿成立,主要保管、陈列清廷沈阳、热河两行宫文物。所以周肇祥认为自己对国宝文物有绝对发言权。
1933年1月,日军攻入山海关,华北告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担心一旦日军占领北平,故宫文物会有被毁或被劫的危险,于是决定选择精品文物(其中包括陈列所文物)迁往南方保存,当时国民政府批准了这一计划。但周肇祥极力反对文物南迁,他认为大敌当前,古物运出北京且不说损坏的风险极大,此举将会动摇人心,引起社会不安。他像个满血战士般狂慢地呼吁民国政府应去保卫祖国,奋力抵抗,安定民心,而不应该倒腾文物,把古物折腾散掉!他在中南海成立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自任主席,通电全国号召全民反对故宫文物南迁,甚至表示要不惜以武力阻止南迁。鉴于此,国民政府干脆也耍起无赖,派警察将周肇祥秘密逮捕,等故宫文物全部运出北京,才将他释放。
但是,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反对派却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金石文物鉴赏家,文化活动家,京津画派领袖。他晚年潜心金石书画,任团城国学馆副馆长、东方绘画协会干事、委员。与金城等著名画家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自1926年起任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他的作品传世甚多,画风匠心古朴。他指责齐白石是“野狐参禅”,而自视传承传统古韵。同时他还工诗文,精鉴藏,通文史,留下丰厚的国学著作。他不仅是活跃于京城的文化活动家,还是一位学问成就者。他的著作如《柳风堂墓志目》、《石目汇编》、《辽金元官印考》等,与《琉璃厂杂记》、《周养庵日记》等稿本,由后人捐赠,今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此外他还有《鹿岩小记》、《寿安山志》,是他潜心樱桃沟三十年留下的心得笔记,于后世均有裨益。

鹿岩精舍,周肇祥在原来孙承泽书屋的遗址上营建的私人别墅,俗称“周家花园”。
狂慢而风雅之人却也还有另一番沉郁收敛的内心世界,周肇祥试图勘破世间执着烦恼而思索生命无常。周肇祥在得到樱桃沟的第二年——1918年,便开始修建自己的生圹,即活着的时候给自己修墓地。生圹的选址恰在水源头上方山上,疑似辽金废寺的广泉寺遗址,他还顺便将孙承泽时期的满水水井(此时已为枯井)重新修建。他在生圹的碑文里写道,自己是来自南方绍兴的一位佛教徒,幼年皈依佛法,号无畏居士。所得官职不值得记述。自作生圹自古有之,以生前自己建好不劳后人费力。他还伤感地写道:我人生际遇多灾难,未老先衰,在寿安山安身养病,现在得到此地自修坟茔,将来与我的夫人默娴同穴。
事实上,那年他才三十八岁,与他后来离世的七十四岁还相隔很远。后来,此处生圹埋葬了他的夫人默娴、女儿及外甥女,可他并没有机会与夫人同穴。一俟新中国建立,他便锒铛入狱,1954年他已高龄病重,获批保外就医。有友人看望他,破屋破衣老病人,他在继续做着监狱里的劳动——糊纸盒,贫病衰弱,晚景凄凉,落寞终老北京城,绝无机会埋骨樱桃沟了。
周肇祥取得樱桃沟后,根据一个仙人骑白鹿来此山谷修道的传说,在原来孙承泽书屋的遗址上盖起来“鹿岩精舍”并自行题写门额,留名“无畏”,保留至今。今天,“鹿岩精舍”院内小小山坡上有一间雅致茶社,游客可以自带茶叶用山泉水冲泡,闲散地坐在院子里品茗发呆。茶社也经营些非烹炒的饭食,譬如手包水饺、啤酒凉菜以应游人之需。茶社所在的仿古建筑上题额“水流云在之居”,保留了孙承泽当年给书房的命名。而院内南房三间题额“石桧书巢”,是为了呼应沟内一方巨大元宝石及石上松而得名,这两件景物曾被孙承泽记述,有传说曹雪芹亦曾受此自然景象启发,构思了《红楼梦》的“木石前盟”……今天这些书法均为当代书法家舒同的手迹。今天的退翁亭大约也是周肇祥重新建起,他在亭子的两楹书写王维的诗句:“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孙承泽在清廷服务低调龟缩,在努力活到六十岁后便迅速隐身樱桃沟,再抓紧二十年活一次令自己热爱的生命,躲避世间纷扰。他游走西山岭脉,访古追昔,潜心学问获得成就;而生性张扬的周肇祥占有樱桃沟三十年,却依旧贪恋城中红尘,作为活跃在北京文化界的风云人物,也成就了一番文化事业。北京城是凡尘的喧嚣舞台,樱桃沟则可隐逸空谷幽兰。两人的人生截然不同,只是他们对樱桃沟的热爱是一样的深厚,这缘自大自然给予脆弱生命的慈悲与安抚,大概就是每一个人内心深处渴望一片归隐乐土的原因吧。
(作者/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