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与“国民党改造”
李村
“国民党改造”是蒋介石为挽救国民党的覆灭,在台湾发起的国民党再造运动,被称作“由上而下的革命”。根据现有的材料,改造国民党的设想最早是徐复观提出来的。万亚刚在《怀念徐复观兄》里说,徐复观曾告诉蒋介石,“国民党所以不敌共产党,在于共产党有力量,领导全党和国民党斗争;而国民党只靠领袖一人支持全局,党一点发挥不出力量”。蒋介石听了,觉得这话很入耳,便让他“草拟一个改造方案,要改造国民党”。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日记里,也明确记有:“下午,研究徐佛观(按,即徐复观)同志所拟重兴革命方案”,次日又记,“接见徐佛观同志,研讨其所拟重兴革命意见书,并予指示”。
但是曹圣芬在《从溪口到成都》里,谈及国民党改造的缘起时,却对这件事只字未提。反而强调国民党《改造纲要》的主要内容,是蒋介石下野后,经过三个月的“大反省”,在溪口制定的。之后,由陶希圣综合其他人的意见,“汇成一个书面报告”。陶希圣晚年接受中研院访问时,谈到国民党改造,也同样没有提徐复观。说他汇成的这份“报告”,“是党的改造最早的意见,最早的草稿”。两人对徐复观在国民党改造中的地位,显然都故意避而不谈,其中的原因很让人好奇。
有人认为这是徐复观在国民党改造时,得罪了蒋经国。据称蒋介石对他提出的改造方案本来“很满意”,要他与蒋经国商量,拟定一份改造小组成员名单,结果他提出的名单里没有蒋经国。经蒋介石再三提醒,要他“再仔细想想,党内还有什么重要人才被遗漏了”,他依然执迷不悟,“反复看来看去,看不出名单上有什么问题”。这当然让蒋经国不快,铁青着脸站在门口,声明“我从来就没有说我要当什么改造委员”,两人“从此闹僵”。(宋田水《再说刘心皇》)
这件事,徐复观在《垃圾箱外》里也提到过,只是说法略有不同。他说国民党改造开始后,“策划的责任,落在经国兄的头上”。有一次,在汤恩伯家开会,推选“改造小组”负责人,“大家推谷正纲先生担任书记,推经国先生担任组织”。他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说“目前以团结为第一。党内有些部分对经国兄不满意,所以我觉得暂时退后一步较好”。他说,他当时提这个意见,完全是为蒋介石着想,认为“经国同志还年轻,将来还有历练”,“绝没有半丝半毫的他意”。但是他于事后解释这件事,恐怕是知道自己错了,当时未免过于颟顸。
不过他和蒋经国“闹僵”后,关系并没有就此恶化。据唐良雄说,蒋经国对徐复观始终“很念旧谊”,每次见了他,“必问:见过复观吗?他情况如何?”还多次请人转告:“我对复观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所认识的徐复观先生》)徐复观也经常在文章中说,蒋介石“对于经国的信任,是可以了解的。同时,就能力与正义感来说,在国民党中,我认为无一人能赶得上经国”。每次给朋友写信,抒发对台湾现状的不满,最后总要交代一句:“若兄觉得此信不便转交,则径投字纸篓中可耳。若转交,则以少谷、经国两先生为限,他人万可不必。”可见他对于蒋经国的信任,依然远超过对其他国民党人物。所以我怀疑曹、陶两人谈国民党改造,故意对他避而不谈,抹煞他政治上的贡献,原因不在蒋经国,而在于蒋介石。
凡是了解徐复观的人,都知道他在国民党改造之前,“很受老先生的器重,遇事先要听听他的意见”。而他所以受蒋介石器重,从一开始便与国民党改造有关。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他作为军令部驻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参谋,从延安回重庆后,向军令部提交了一份报告,题作“中共最近动态”。报告分三部分,“前段是说延安方面一般情形,中段是说中共‘整风运动及其目的,后段是讲对策”。他在报告中特别提到,根据他这半年对中共的实地考察,共产党成功发展的“秘诀”,就在于“以农民党员为发展组织的对象”。由于中共重视发展农民党员,“以农民之政治坚决性,监督知识分子,故其组织能够深入于社会里层”,形成对于社会的控制力,“于是军队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成为“绝对之战斗体”。
相反,国民党是个知识分子政党,“党员团员之成分,仅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于是党团之组织,亦自然仅以上层为对象”,所以很难深入社会,融入到基层当中,“血液之循环,仅及半身而止”,“党团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最终落入“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反不能独力控制社会”的尴尬地位。致使共产党“以绝对性、全体性对我,而我仅能以有限性应之”。他的结论是“不改造国民党,绝没有政治前途”,国民党在“今后的斗争中,绝不是中共的敌手”。
现在回头去看,他这些观察和结论,都称得上深具政治远见。但当时看在一般国民党人物眼里,却普遍不以为然,认为他“神经过敏,危言耸听”,吃了共产党的迷幻药。他为此还和康泽吵了一架,弄得“彼此都非常不愉快”。他也因此而大为失望,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当时中坚分子的想法,实在相去太远了”,决定离开重庆,回鄂西老家种田去。想不到蒋介石看了却深受触动,从当天下午看到晚上八点,认为他的报告指出了国民党的要害,是“吾党中最正确之报告与最有力之文字”。在启程出席开罗会议的前一天晚上,于深夜十一点召见他,要他打消种田之念,“留在重庆”。而这件事,便成为他“一生荣枯的关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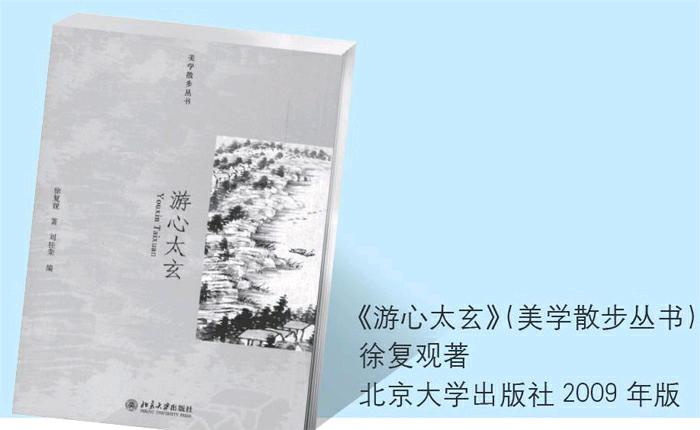
他受蒋介石召见后不久,便被调入蒋介石的侍从室,从此夤缘以进,“由一名军人,变为策士,近身近禁,崭露头角”。在这之后,他又作为蒋介石的随身秘书,出任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副秘书长,“经常出入官邸,参与机务,其地位相当于旧时的小军机”,甚或“成了陈布雷去世后,蒋介石身边最重要的文胆兼谋士”。许多蒋介石下交的重要文件,包括所谓《新剿匪手本》,都是由他起草或参加起草的。他后来将蒋介石对他“这段知遇”,取《史记》中的一句,称作“依日月之末光”,常以“未有涓埃答圣朝”而惭愧。
正因为有这段“知遇之恩”,他进入侍从室以后,便很体念蒋介石的处境,经常觉得“党政高层人物,蒋公几无人才可用”,几乎是孤家寡人。从而有了“轻视朝廷之心,加强改造国民党的妄念”,“想以蒋公为中心,创发新的建国力量”。不时利用接近蒋介石的机会,向蒋介石进言,“希望能把国民党改造成为代表自耕农及工人的政党,实行土地改革,把集中在地主手上的土地,转到佃农贫家手上,建立起以勤劳大众为主体的民主政党”。而蒋介石对他这些想法,也无不点头称善;他“每在口头或书面上提出一次”,蒋介石都“未尝不为之掀动一次”。有一次,他甚至建议蒋介石放弃国民党,“从国民党的派系烂泥中跳出来”,成立一个新组织(党),蒋介石也竟然接受了,说“建立新组织的问题,我认为是需要的,你可以负责进行”(《垃圾箱外》)。他提到的这些细节,蒋介石于日记中也有所记载,称他提出的“改造党政意见书”,“甚有见解,可慰”。并指示蒋经国,“平日对于共产党问题,可与徐佛观互相探讨研究”。可见他当时在改造国民党问题上,曾与蒋介石达到很高的共识。
但是一九四九年蒋介石下野后,下决心改造国民党时,他与蒋介石之间已经出现了分歧。他虽然依旧坚信“中国农民的品德,一向比大多数知识分子为高”,而且这种看法一生没有改变,但是已经不认为“国共斗争的胜败,决定于国民党能否改变自己的社会基础”,将国民党改造的成败,放在清理阶级队伍上,而是相信“只有民主,才能挽救国民党”,“国民党改造之途径,必须自此中求之”。据他交代,他在溪口起草的“中兴方略草案”,其中的主要精神,就是“希望三民主义的信徒能和自由主义者合作”。他说,这是他“个人认识上,一个大的转变”,也是他“后半生政治思想的立足点”(《对殷海光先生的忆念》)。
因此,国民党改造开始后,他接连发表了《党与“党化”》《如何解决反共阵营中的政治危机》《第三势力剖析》《一个错觉》等文章,表达与“改造诸公”的不同意见。他认为国民党“改造的起点,首先是要确定党的性格”,而国民党“不论是自居于革命的政党,或是自居于普通的政党,从三民主义的本质去看,总应该是一个民主性格的政党”。因此,国民党的改造必须从民主做起,通过改造让自己成为更民主的政党。但是目前的国民党改造,正在偏离“党的性格”。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失败,分裂了党员的意志,“国民党中的一部分人,把国民党的失败归咎于民主化得不够;而国民党的另一部分人,则把失败归因于受不负责任的民主要求之牵制,以致失坠了国民党十三年改组的精神,尤其是失坠了复兴社运动的精神。在南京沦陷的前夕,大概是前一看法占多数;迁到台湾以后,后一看法似渐抬头”。而目前的“国民党改造路线,似乎就是后一种看法的实践”。
然而他认为,这“后一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许多人以为,过去社会上向国民党要民主,乃造成大陆沦陷的原因,这当然是事实。但这一事实的解释是这样的:分明训政再也训不下去了,实行民主乃国内外的一致要求;而国民党在外表上不能反对民主,在心情上又要留恋训政,于是对于民主的态度,好像守财奴之对于金钱一样,外面紧一分,我便不得已地吐出一分;吐出得不仅不主动,而且吐出得面有愠色,非常不自然。这样一来,国民党本是向专制要民主的,当时反变成社会向国民党要民主;向国民党要,则有形无形地渐渐以国民党为敌人;国民党受不了这种有形无形的敌视态度,便也不知不觉地渐渐以主张民主者为敌。”最终在社会上孤立起来,被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所打败。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过去在大陆遭遇的局面,如今正卷土重来。“自由中国今日向政府要民主之声,又渐渐开始……此种呼声一出,绝非强力所能压制。因民主自由,不特为大势所趋,亦且为人性所在;使无政策上的转变,则日积月累,其要求必逐渐扩大,政府又要陷入与社会相持之苦境,结果仍为共党所乘。”
所以,国民党要经改造获得“新生”,必须“在过去对民主失掉主动的这一根本原因上去接受教训,而绝不可以对民主的怀疑去接受教训”。而国民党要彻底成为民主政党,就应当有足够的胸襟,走出“一党专政”的误区,允许反对党出现,甚至帮助反对党、扶植反对党。他认为,过去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因为有反对党存在,“而是由于抗战中只有联共的反对党,而没有反共的反对党。及有一部分发展到不联共的时候,也根本不成其为反对党了。……假使抗战中间有一个强大而反共的反对党,则社会的情形,不致形成后来向中共一面倒的形势;而国民党本身,在反对党的激励中,也不致腐烂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除了以上这些意见,他还建议蒋介石早下决心,“党经过彻底改造后,蒋公不必任总裁,而建立一种集体领导制。理由是让蒋公成为各党各派共同的领袖,包容万殊,促成全面大团结”。这也就是他后来所说的,“我赞成他恢复总统的职位,但希望他辞掉国民党的总裁。从国民党的恩怨圈中解脱出来,把过去的恩怨,一刀两断,成为现阶段反共的共同的象征”。
他这些主张显然已经离经叛道,去蒋介石的立场甚远。蒋介石在制定国民党《改造纲要》时,虽然将国民党定性为“革命民主政党”,加强了党纲中的“民主成分”,实际根本不相信民主,更不相信“国民党实行民主,才可以团结反共”,认为“使共产党取胜的并不是民主与真理,而是他们的组织与宣传,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组织与宣传上比不上他们”。所以改造国民党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党内的派系,换言之,消除党内一切民主成分,在组织与宣传上“胜过共产党”(吴国桢《夜来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他要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去做“各党各派共同的领袖”,蒋介石更难以接受。正如唐良雄所说:“这是一创见,也是一种错觉。”因为国民党一向信奉“党国体制”,认为“有党始有国”,将党凌驾于国家之上,蒋介石下野后作为一介平民,还能掌控国家军政大权,靠的就是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他要蒋介石放弃总裁地位,去做宪法之下的总统,无异于要他放下手上的绝对权力,这完全背离了蒋介石改造国民党的用意。
他这些主张一提出来,党内自然一片哗然,批评者有之,谩骂者亦有之。据说蒋介石还将他找来“当面斥责”,“拍桌大骂一顿”。“他多年尽忠于当局,与当局多年爱护他的情分,从此日渐淡薄。”(唐良雄《我所认识的徐复观先生》)从现有的资料看,国民党改造初期他还是党的核心人物,在参加日月潭会议后,又参加了“党的改造研究小组”,参与讨论党的改造方案。据说一九五○年三月,国民党在台北召开改造大会时,先由蒋介石训话,接下来便是他“宣读计划大纲和改造委员(小组成员)名单”。这都说明他这时还“圣眷未衰”,蒋介石对他仍有向用之意。但是一九五○年七月,国民党改造委员名单正式公布时,他已经被排斥在外,不在十六人名单里了。而这十六人当中,有四人是蒋介石的秘书,这更可以说明问题。一九五四年四月,他在香港《华侨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改造国民党,是蒋总统到台湾后的最大工作。改造早经完成,进步谅亦不少。详细内容,当非外人所能了解。”可见他在国民党改造中不仅被边缘化了,最后还成了“外人”。
因此,国民党改造开始后,他便与国民党渐行渐远,反而与“党外人士”越走越近。据他自己说,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对“党外人士”一向“存有菲薄厌恶的心理”,认为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路线,无形总是依违于国、共二者之间”,跟在共产党后面“向国民党要政权”。去掉他们的伪装,无一不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他说,有位在野党领袖,后来良心发现,不止一次地对他说,“这些东西(他们的同志)既无道义,又无干劲;假如国民党真把政权交到他们手上,那真不晓得坏到怎样的地步?”但是面对“改造”后的国民党,他在认识上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认为“党外分子”一概是投机分子,只想趁国民党危难“在政治圈子间讨便宜”(《欣闻国民党革新之议》)。这中间最值得一提的是雷震。
雷震虽然不是“党外人士”,但因为曾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在政协会议前后“负联络党外人士的责任”,被称为“政协余孽”,他对雷震向无好感,同样“存有菲薄厌恶的心理”。不图国民党撤台后,雷震两次来香港安抚留港人士,他经与雷震接触后,“两人的政治观点,在民主这一点上,有了相互了解”。从这以后,他对雷震便只有敬重而无间言,经常将别人不敢发表的文章寄给雷震,刊登在《自由中国》上。他曾在给雷震的信中说:“国家至此,坐牢与不坐牢,实无多大分别,而所谈之事,乃灭子绝孙之大事,故愤写此文。而茫茫天壤间,惟先生可以语此,故即以奉寄。”而雷震收到他的文章,也从不拒绝。例如青年救国团成立时,他写文章批评,因为话题太敏感,直接触犯了蒋氏父子,“毛子水先生反对采用,雷震改动一二句,依然采用了。这种例子不止一次”。
一九五二年他回到台湾,在台中省立农学院执教,雷震每次邀请民、青两党和国民党民主派分子召开座谈会,就台湾政情交换意见,讨论组织反对党,他只要在台北都会参加座谈会,成为“其中的一分子”。黄通说,他还记得有一天,徐复观从台北回来,见了他便说:“这个政府要垮。”他问:“何以见得?”徐复观说:“雷震回来了,我们去欢迎他,大家一面吃早点,一面谈话,吃完早点才分手。我们谈得很多,大家分析的结果,这个政府非垮不可。”(《黄通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可以想见,他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势必会走向国民党的对立面。所以国民党改造开始后,在党员重新登记时,他便决定脱离国民党,称自己“不愿再以一国民党员自居”。
以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他的脱党让很多人不解。怀疑他的脱党是在党内遭人构陷,蒙受不白之冤,不得不“含怨出门”,而“内心之苦,有不待言”(唐良雄《我所认识的徐复观先生》)。据说他也确曾向人透露过,他的脱党与陶希圣有关。陶希圣早就提醒他,“追随总裁的人,有时一下子红得发紫,有时又一下子黑得发紫”,暗示他“不可得意忘形”。但是从他的思想变化看,他脱党完全是自愿的,是他“经过长期内心之矛盾斗争,终不能自加克制的必然结论”。据黄通说,中央改造委员会得知他没有“归队”,曾派第一组主任陈建中专程来台中,说服他回到国民党,结果“好话说尽,他却无动于衷”。
“脱党”是对党的“不敬”,尤其以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这更是“大不敬”之罪。因此,他脱党后“日子很不好过,出门有人盯梢,来往信件被拆封检查”。他还听说“将有人对他不利”,连“教书之饭碗,亦岌岌可危”。只是这样一来,以他的性格,更增了他对国民党的反感,经常发表文章“将政府批评得一塌糊涂”。认为国民党改造全然失败,“改造党的路线,值得根本考虑”。有些文章还直接针对蒋介石,说蒋介石由于执政太久,自以为神圣,养成了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对于人与事的衡量,都以对我的好坏为标准”,“善于我者为善人,恶于我者为恶人”,已经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劝蒋介石以梁武帝为戒,不要因为拒谏自满“而终于国破身亡,为天下僇”(《钱大昕论梁武帝》)。他这些话之口无遮拦,已经严重伤及蒋介石的自尊心。一九五八年,蒋介石七十大寿时,他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的“祝寿文章”,更在台湾政坛引起轩然大波。
在这之后,他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开始大为改观。在国民党改造前,他本来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不仅是思想反共,且长期做着反共的工作,写了许多反共的文章”,脱党后还仍然表示,“除反共之外,国家无出路”,要“更加强个人反共之责任”,但是对共产党的态度事实上发生了改变。开始有人怀疑他的反共,“并非彻底反共,而是在批评中还想为他们(中共)开路,对他们还存在期待之心”(万亚刚《悼念徐复观兄》)。黄通说,有一次他问徐复观,“现在中国有两个政府,这两个政府比较之下如何?”徐复观的回答是:“这个不能比。”而且越到晚年,他心志的转变就越开朗、越明显,达观到了为国家民族利益,可以放弃恩怨、超越党派的程度。
一九七八年十月,他在给翟志成的信中,曾将梁启超一首七律的末联“世界无穷愿无极,海天辽阔立多时”,改为“国族无穷愿无极,海天辽阔立多时”,将他对“国族”的无穷愿望,转移到了共产党身上。他还在同一封信里提到,“文化大革命”当中,有一天,他在聊天时告诉牟宗三,他写文章批评江青集团,“有两个心愿:一是要使孔子恢复文化中的应有地位,二是要使中共走上狄(铁)托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他说,“我虽然没有这种力,但不能没有这种心”。
我想,他的这一段话,既可以适用在这里,也可以适用于他整个后半生。这也是他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思想上的特出之处。
二○一六年四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