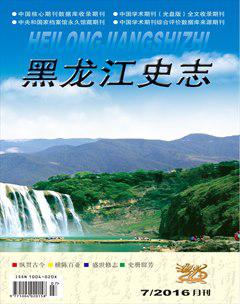从《通志·校雠略》看郑樵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摘 要]《通志》凝结了郑樵毕生的心血,倾注了其“会通”“类例”“成百家之言”等史学创新精神及批判精神。其中《校雠略》所探讨的亦是关乎档案文献编纂的思想。作者从档案文献编纂的角度汲取了其中的“求书之法”、“校书之道”以及“编目之旨”三个方面的思想。遵循这三个指导思想,我们在档案文献编纂时可以既一脉贯通,又采取因地制宜灵活运用的方法。
[关键词]校雠略;通志;档案文献编纂;郑樵
“三通”之一的《通志》,继承并发展了司马迁《史记》纪传体通史的思想,融汇了古人浩瀚典籍中的精粹,其中的《二十略》更常常为后人所谈论学习。纵观《二十略》,史学思想、文献学思想、目录学思想等比比皆是,也是历来被研究和推崇的。虽然古人对郑樵的这种貌似“激进”、“新潮”的思想褒贬不一,但从艺文、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等这些涉猎内容之广泛来看,“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文墨豪情与博学才智油然迸发。本文以《校雠略》为研究对象,发掘其中对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启示之处,探讨其中蕴含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
一、明旨而后学——《通志·校雠略》的核心思想
研究一部宏伟巨著,首先要明白其宗旨,作者究竟围绕了哪个主题来论述,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通志·校雠略》顾名思义,我们可以解读为三个部分:“通”、“志”和“校雠”:
(一)“通”
“通”字可谓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核心思想、主要脉络。这和司马迁《史记》中“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意味是相辅相成的,郑樵解释为“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1],“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2]。如若能将世代帝王将相、诸子百家的言行思想融会贯通,集成于一书,那么这本书将发挥通晓古今的重大作用。章学诚在《申郑》中高度赞扬了郑樵的“会通”精神,“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之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3]。档案文献自收集开始,包括整理分析,校对勘误,引文标注,分类编目以及后世的学习利用都有融会贯通、一气呵成的“会通”之意。
“会通”思想提出历史不是断断续续、杂乱无章的,有时表面看上去藕断,实则丝连,著名史学家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中将郑樵笔下的历史的联系分为三种情形:“一是人类社会的外部条件不会变化”,“二是历史事件前后有相因相依的联系”,“三是各代制度相因,也有损益”[4]。所以不管是历史还是记录历史的档案文献,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联系的事物,从而有章可循。这亦是研究《校雠学》所要秉持的核心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
(二)“志”
郑樵不局限于纯粹史学撰述的文字功底,他的经世致用的修“志”观点也体现在《通志》中。修“志”即有序地记录经国安邦的典章制度,在充分明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后整理出国家“宪章”。在《二十略》中,郑樵将“志”改为“略”,实际上就是深入国家百姓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调查研究,修志立说,“要使史书成为对治国有用的学问,成为国之大典,就要着力研究书志的有关内容,留意宪章”[5]。吴怀祺对郑樵倾尽全力,克服千难万阻修“志”的精神予以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二十略》汇集了郑樵一生的学术精粹。
(三)“校雠”
在研究“校雠”二字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以下两点来理解:第一,这里的“校雠”与现代汉语里的校雠有一定出入。现代汉语理解的校雠仅有校对之意,无校勘之意。而古时人们所说的“校雠”包含了文献学、校勘学、目录学等多门学科,可以说其概念没有界定也较为模糊。笔者认为《校雠略》中关于文献的“求书”、“类例”、“编次”等方法和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要义是基本一致的,正所谓“通古今之变”,我们可以将古人有益的编纂思想提取出来应用于现代工作生活当中。第二,我们要明白这里“校雠”的探讨对象是“部次流别、疏远伦类、考其得失之故”[6],以“类例”之法来划分文献的类别,判定不同文献内容的亲疏远近,考究它的利与弊,所以有关“鲁鱼亥豕之细”的具体文献整理、校勘、编目的方法不在此讨论范围内。
二、编纂亦有道——《校雠略》中的求书、校书、编目方法
《校雠略》是《通志》二十略其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分为21论,包括69篇内容。“册府之藏,不患无书,校雠之司,未闻其法。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故作《校雠略》”[7]。郑樵在《通志·总序》中阐明了他写《校雠略》的宗旨:“册府”即藏书之所,像汉代的兰台、东观,唐朝的秘书省、集贤院等所藏之书数不胜数,但“校雠之司”却不了解这些文献源流,更不懂得文献的收集整理,校对勘误,分类保管之道。“三馆”即昭文馆、集贤院、史馆,作者希望这三馆的官员都能各尽其力,为四库典藏文献的编制作出努力,使经典文献流通于后世。在此宗旨基础上,笔者分析总结了这69篇内容,汲取了相通于档案文献编纂的方法,从求书、校书、编目这三个方面阐述郑樵的校雠思想:
(一)求书之法
所谓“求书”可将其理解为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第一步:收集档案文献。郑樵从24岁开始就四处收集书籍,多年来积累下的书籍为《通志》的撰写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校雠略》开篇警醒我们:“秦不绝儒学”,这个论断实质上表明,历代文献不存于世实际上是校雠人员以及学者自己的疏漏。一般意义下理解的“焚书坑儒”不仅焚烧了众多儒学经典文献,并给秦朝以致命打击。但郑樵却有创新的见解:陆贾、郦食其、叔孙通等儒生也会被秦所采纳任用,“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8],所以造成“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9]这种现象“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10]。由此,我们档案编纂人员亦可以审视出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为了使经典学说、宏伟著作流传百世,首先收集档案文献应遵循“求书八法”:
有关星历的书籍,求之于灵台郎;有关乐律的书籍,求之于太常乐工。如果没有,就向民间懂得星历、乐律的人所探访,“此之谓即类以求”[11]。收集档案文献应有“即类以求”的思想,顺着所求档案的直接所属的全宗或案卷来探求,是顺其自然而又最为简便的方法。
有关“性命道德”的书籍,可以求之于道家;有关“小学文字”的书籍,可以求之于释氏(佛姓释迦的略称)。周易是占卜的书籍,常存于占卜的家庭,而“洪范之书”在“五行之家”往往可以求到,“此之谓旁类以求”[12]。这里的旁类不能字面理解为其他类别的意思,若是这样也就违背了档案中全宗的思想,其实这点是启示我们收集档案文献的时候,顺着相关类别和内容的全宗或案卷查找也许会有新的收获。
孟少主的实录,蜀中之地一定可以找到;王审知的传记,关中一带必定存有。这样根据所要收集的档案文献的出处“可因地以求”[13]。档案文献编纂的收集不仅要从所征内容的类别和相关类别方面考虑,因地制宜也是另一种直接且准确的求书之法。
王春秋讲义虽然没有了,但在王临漳的家中应该能找到;徐寅的文赋,如今在莆田,因为他的家在莆田。搜寻罕见稀有的人物传记或著作的时候“可因家以求”[14],图书馆、档案馆及博物馆的档案文献一般仅仅是流通于公共渠道的,而有时“高手在民间”,所以深入人物的家庭环境,遍及人物生前所涉及的足迹,未尝不是一个收集档案的好方法。
有关礼仪、祠祀、断狱、官制、版图的文献,往往是由官府所掌,属于国家统治者所掌控的国家机器的文献。如果不是在战乱年代,且书籍没有收到战乱的污损,我们就可以从官府的典藏中搜集文献,“此谓之求公”[15]。现在收集属于国家所掌握的权利范围内的档案文献可向政府或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请求协助完成有关档案文献的查找、摘录、影音及借阅的收集工作。
相应的,“书不存于秘府而处于民间者甚多,如漳州吴氏,其家甚微,其官甚卑”[16],卑微的家境人却不卑微,一生写文着墨不断,这样的文献自然要向私人求索,“此谓求之私”[17]。这里郑樵还强调了求书之人要“尽诚尽礼”,工作人员必须用最大的诚意和最高的礼节对待所征之书的主人,向对方说明意图,表明诚意,列举诸如最终能回报广大社会这样的例子来说服对方。
乡人陈氏曾是湖北的监司,在他所掌权的范围内应该会有田氏之书,“若迹其官守,知所由来,容或有焉”[18]是指沿着人物当时所属管辖的官员这条路子,或许能求得相关文献,“此谓因人以求”[19]。现代社会中我们不仅可以向人物所属的街道社区、单位机关征求档案文献,也可以向其亲朋好友等社会关系人员征集档案。
胡旦所著《演圣通论》,余靖所著《三史刊误》,这些书虽然卷帙繁多,但只是当时流行了一阵子,实际上大部分是郑樵所处时代的人所著。“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之人手,何不可求之有?此谓因代以求”[20]。档案文献的收集应有时代感,古时的文献不一定只存在于古时的典籍中,有可能在近代经后人补充著述后发扬光大。
(二)校书之道
郑樵主张对于收集来的图书不能随意地相信和应用,应该进行“核实”和“索像”,核实,指对古书的记载应与实际情况互相印证。索像,指对于历史史迹,应在文字之外加以图像印证。这里我们探讨的是档案文献编纂时整理校对的工作,实际上是对之前收集工作的查漏补缺,系统地排列所求之书,以更加严谨的治学态度辨析正误,补缺记漏。笔者从档案文献编纂的角度将这部分的思想糅合成两部分:怎样对待“亡书”;如何做好“校书之官”。
1.“名亡实不亡”
“亡书”一词在《校雠略》21论的题目中出现了6次,可见其重要程度,实际这里的“亡书”并不是真正消失于世间的书,作者用这样警醒的字眼所要强调的是书并没有亡。郑樵给我们启发了一条思路:
(1)“书有名亡实不亡”。这一论中郑樵开篇点题“书有亡者,有虽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不可求者”[21],接着又用大量的事实阐述为何“书有名亡实不亡”,文言略例、三礼目录、开元礼目录、名医别录等书籍的单行本虽然看似已亡,但是其中有些书被收入了丛书、总集中,实际上还被保留着。整理档案需要第二遍地对档案的完整度做调查分析,若存在“书有名亡实不亡”的情况可以从以下三点考虑:档案是不是被编入了某些丛书或人物传记中;档案是不是曾被其他文献采用或者参照过;其它档案有没有部分内容与之相似的。通过这些思路对我们整理档案时寻找亡书提供了有力的方法。
(2)“阙书备于后世”和“亡书出于后世”。“阙”古书中作“缺”,这里指亡书的意思。郑樵为了证明“古之书籍,有不足于前朝,而足于后世者”[22],举例道《唐志》所收集的旧书卷帙繁多且远远大于隋朝,而这些梁朝的书在隋代大部分已经散失,却又在唐朝失而复得,原因就在于“唐人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搜访图书”[23]。这一论点和“求书八法”中的“因代以求”对比可发现二者相辅相成,档案文献编纂本身就是对前人档案的完善和补充,所以古时遗失流亡的档案往往丰富于后来的时代。在校对这一环节中,应细心整理后人对前代档案的总结,收获会远远大于只追寻原始档案得到的成果。
(3)“亡书出于民间”。郑樵还提到“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24],如陆机正训和隋、唐二志,都出于后世荆州的民间人家田氏,这些都是三馆四库所没有的档案。此论点和“求书八法”中的“求之私”相似,为了完善档案文献资料填补空缺,在校书整理的时候也应考虑民间的亡书,因为“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25],如何将档案编纂真正做到“名亡实不亡”是档案人值得思考的问题。
2.“校书之官”
郑樵认为“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26],书轻易变为亡书,这是校书人员失职的表现。如此批评的字眼在《见名不见书论二篇》的开篇和《亡书出于后世论一篇》的结尾都被反复提起。
《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中,作者用整整一篇论证了求书必须要遣派官员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并且校书之官应是长期任用的、专业的人员。“求书之官不可不遣,校书之任不可不专”[27],专业且长久的档案任职才能有信手拈来的档案编纂工作,。“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28],我们要想编纂出价值高的档案文献必须事事亲力亲为,亲身调查探访得到的档案才会更接近其原始的本真。“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29]刘向父子,世代为校雠人员,虞世南和颜师古相继当上秘书监,令狐德是三朝的修史官员,这些都是校书官员要久任的最好例子。倘若我们档案编纂人员流动性大,那么编纂的档案文献一是失去了其既有的连贯性,二是没有了统一的分类标准,三是编纂出的档案质量不高,缺乏有经验的档案编纂人员。
关于史书的编纂人数方面郑樵的见解也很独特,“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至唐人始用众手,晋、隋二书是矣”[30],郑樵认为“古有一家之学,但其中也有依众人成书的;众人编书,如能各用其长,也能撰成佳作”[31]。“众人成书”的关键在于编纂人员要发挥长处,专攻自己的专业长处,“皆随其学术所长者而授之,未尝夺人之所能,而人之所不及”[32],像李淳风、于志宁就让他们作志,颜师古、孔颖达则擅长传记,如此安排,各尽其位。
现代档案文献编纂对编纂人员的要求提出了新的高度,对待那些时代久远,理解难度大,专业性强的档案更能显示出一名高素质、专业性的档案人员是十分必须的。
(三)编目之旨
档案收集整理之后还处于零散混乱的状态,接下来应该加以注释并分门别类地归纳排列起来,这一步是档案发挥作用的关键一步。郑樵主张用类例中“以人类书”的方法对书籍进行“部伍之法”的分类。在“编次”方法上郑樵有很多标新立异的见解,关于注释的问题也有三篇论述,笔者按照档案文献编纂的思想,将他的编目之旨分为“类例篇”、“编次篇”和“注释篇”。
1.类例篇
“类例既分,学术自明”[33]。类例,就是档案文献典籍的总体分类原则和具体分类方法,应用到档案编纂学上就是对已收集的档案的分类编目工作。郑樵总结并区分了“古今有无之书”,将其分为经、礼、乐、小学等十二个类别,从而突破了经、史、子、集的传统分类方法。笔者总结了郑樵的“类例”之道,将其分为以下几个要点:
(1)分类集中保管。“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不可有所问也”[34],属于同一类别的书应当集合在一处,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唐志》在“仪注”类目里有玉玺和国宝两本书籍,但在“传记”类目中又出现了这两本书,这就是没有遵循集中分类存放的表现。档案收集后应集中统一分类排放,这样既符合有序化的编纂过程,又给档案编纂工作提供了方便。
(2)不可“见名不见书”。郑樵解释道“编书之家,多是苟且,有见名不见书者,有看前不看后者”[35]。档案编纂应综合考虑无论是书名、作者、背景年代、各部分内容以及全篇内容的所有因素。不能仅凭书名武断地判定书的内容和类别,也不能只根据前几篇的内容给书的性质下结论,应纠正这种不严谨的学风。
(3)“以人类书”。唐朝之前的分类编目都是根据书籍本身的内容及相互关系分类,讲求人名写于书名之下,标注上朝代等,把不同类别的书籍分开,这就是“以人类书”。而宋朝人沿用了唐代《隋志》及其以后的分类方法,将人名写在题名之上,再按不同类别划分,即“以书类人”。由于传统的分类受体系结构的限制,郑樵提出应根据问题分类而不拘泥于按作者分类。郑樵的这一创新论述给我们以启发同时以警示,我们在处理档案文献的分类问题时应放开眼界,不管是“以人类书”还是“以书类人”,都应看到它们的优点,取长补短,以更加多样化的分类体系完善档案文献,使编纂的档案适应不同分类需要的读者。
2.编次篇
21论中7次提到有关“编次”的问题,将编次中遇到的“亡书”、讹误、顺序等问题逐一阐述,从中我们了解到郑樵做学问有着严谨求实态度,对待史书的编纂力求做到精益求精。
(1)“编次必记亡书”
在“校书之法”中我们探讨了“亡书”的意义以及如何收集寻找“亡书”,这里谈到的是编次过程中如何对待“亡书”。郑樵借用孔仲尼的例子提出“古人编书,必记其亡阙。所以仲尼定书,逸篇具载”[36],孔子至唐朝以前,古人编书一定会记下“亡阙”之书,并记录下书籍的所属分类等基本信息。自唐朝以后,古人收书只记录存于世的,那些“亡书”则不记录,“是致后人失其名系,所以崇文四库之书,比于隋唐亡书甚多”[37]。可见编次文献时对“亡书”的态度决定了后世流传文献的多少与质量。
(2)“编次失书”
接下来“编次失书论五篇”中郑樵点出了校雠人员没有恪尽职守,“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38],所以才导致了“亡书”的真正灭亡。作者举例提到《唐志》在天文类中有星辰方面的书籍,却没有日月风云气候类的书籍,这并不是说唐朝没有日月风云的气候变幻,而是编次人员编书时失职所致。
(3)编次必追根溯源
首先,记录“亡书”从根本上说保证了文献有真实可信的源流。所谓“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39],这点很好的切合了档案的原始性的特点,讲求档案文献要追根溯源,只有真实完整地记录下“亡书”的基本情况,才能保证文献有根可寻,有源头可溯。此外,郑樵还十分重视第一个进行编次的人员的工作,“是故君子重始作,若始作之讹,则后人不复能反正也”[40],第一个进行编次的档案人员应怀有最严谨的态度,即“重始作”。
(4)“编次有”
档案编纂应讲求有序化,区分前后顺序,按照作者的本意来排列文章。这样做既能充分尊重原著,又反映了作者写作的意图。“隋志每于一书而有数种学者,虽不标别,然亦有次第”[41],下面郑樵说《春秋三传》虽然没有分为三家,但是依然有先后之分,先是《左氏春秋传》,其次是《春秋公羊传》,再次是《春秋谷梁传》。档案文献编纂必须保持档案的原始顺序,因为作者成书有一定的先后次序,那些看似没有先后之分的段落或篇章有时蕴含着作者的写作用意。
3.注释篇
档案文献编目除了原有档案本身的注释需要原文录入外,必要时加入辅助读者理解的词句或解释,能更好地发挥档案的价值和作用。《校雠略》中郑樵连续三篇论述阐明了自己的注释思想:
(1)“泛释无义”:“古之编书,但标类而已,未尝注解,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42],所以那些已经归入经类的就不要解释它是经类的,已经归入史类的也不要再解释它是史类的了,“据标类自检,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说焉?”[43]。作者一连用了两个反问句强调“泛释无义”,档案文献编纂无需为了注释而注释,不拘泥于固定的注释方法,以真实而又实用为宗旨,删繁就简,去粗取精。
(2)“书有不应释”:“凡编书皆欲成类,取简而易晓”[44],有些内容不用一一作释,显得繁琐又无用。《唐实录》有十八部,既然名叫《唐实录》,即是唐朝人所写的,就不用一一注释“唐人撰”。档案文献中如涉及到类似“见名而知义”的常识性问题,就不必注释了。
(3)“书有应释”:“至于杂史,容有错杂其间,故为之注释”[45],郑樵认为像杂史一类间或有错误出现的书籍,应该为它注释。我们将其引申到档案编纂的注释中来,对于欠缺历史考证的档案资料应加强注释工作,这是由档案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档案的原始性是其最根本的性质,对杂乱的档案、缺乏考据的档案、使人迷惑的档案必须有编纂者的注释以备利用者参考。
三、结语
《校雠略》展现了郑樵在文献学、史学、目录学上的杰出思想。“求书八法”涵盖面广、实用灵活地论述了收集文献的方法,校书的人员应具备专业性的素质,长久地担任校书官员。关于“亡书”的讨论则让我们对看似遗失的书籍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处理方法。此外,在分类问题上,“以人类书”的观念让我们重新审视现在的分类标准及分类方法,学会用“类例”的思想编排目录,整理书籍。从短短的21论的文献中,可供我们学习积累的内容比比皆是,我们档案人要继承《校雠略》中有关档案文献编纂的思想,将收集、整理、编目档案文献灌诸于新的思想方法,务实求源,创新进取,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不断进步而努力,为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打开新的篇章。
注释:
[1][2][7]张须著、王云五主编.通志总序笺[M].上海:商务印数馆,1934:1,3,51-52.
[3]<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249.
[4]白寿彝主编、吴怀祺著.中国史学史(第四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23.
[5]吴怀祺.郑樵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33.
[6]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
[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1803,1813,1814,1807,1811,1812,1809,1821-1822,1806,1815,1816,1818,1819.
[31]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8.
参考文献:
[1]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张新民.郑樵目录学思想体系及其广义性论——解读<通志?校雠略>[J].图书情报工作,2009(21):142-145.
[4]戴建业.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论郑樵文献学的‘类例理论[J].图书情报知识,2009(3):18-25.
[5]王利伟.郑樵档案学思想简析[J].档案学研究,2003(2):21-24.
[6]顾志华.郑樵<校雠略>在历史文献学上的价值[J].华中师院学报,1984(1):66-72.
[7]康桂英.从<通志·总序>看郑樵的史书编纂思想[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3):55-57.
[8]黄中业.郑樵对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贡献[J].史学集刊,1998(2):67-71,78.
作者简介:李明娟(1990-),女,河南省鹤壁市,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档案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