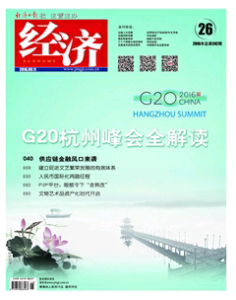消暑在清迈
刘稚亚
从地图上看清迈,不难发现清迈的中心有一个大方格,方格内就是古城区。环绕古城区一周的城墙,于1296年由从清莱迁至该地的孟莱王建立,如今看来,虽大部分已被拆毁,但残留的城门和断垣仍彰显着纳空清迈作为泰北兰纳王朝的昔日辉煌。
大象无形
早起晨跑。我很好奇古城一周究竟有多长,于是决定绕城一周。沿途路过一家餐馆,彼时时间尚早,餐馆还未开门,不过外面贴了一张古旧的清迈地图,泛黄的实景图将破旧的餐馆衬托得颇有气质。地图上细心地画出了5个城门的具体位置,用蓝色的色彩标出了弯弯曲曲的护城河,甚至还贴心地附上了英文的注释:根据那张地图,我才发现清迈古城共拥有5个城门,分别是东门——塔佩门(ThaPae Gate)、东南门——清迈门(ChiangMai Gate)、西南门——松朋门(SuanPrung Gate)、西门——松达门(SuanDok Gate)和北门——昌卜克门(Chang Puek Gate)。
如今还有谁会细看地图、研究外形和计算距离呢?恐怕除了像我这样初来乍到的度假者以外也不会有其他人了吧。人们早已习惯通过谷歌地图去导航——向前走500米,左拐,800米,再右拐,“目的地在您的道路右侧”。机械地按照导航的提示音,可以省去找路的繁琐,用最快的方式到达目的地——却也失去了迷路的乐趣和偶遇的惊喜。有些地方,如果你在地图上观察它们,再通过一番寻找,云开见日后最终见到实景,会使你获得片刻类似于天佑的感觉。
城门始终是历史的印记,被称作HuaVieng Gate的北门是进入清迈的第一道门。在泰语里,“Hua”意味着头,“Vieng”意味着防御。公元1400年以后北门才改名为“ChangPuek Gate”,即为“白象门”。改名是因为宗教。当时信奉佛教的清迈国王为了埋葬高僧所赠的佛骨,便将佛骨由白象背负,并将白象放生。白象缓缓走出北门,一路径直而上到达了素贴山,并止步于此,于是国王将北门重命名为“白象门”,白象止步的地方则是如今鼎鼎有名的素贴山双龙寺。
我一直很难比较,大象对于泰国相当于中国的龙还是马。在中国似乎很难有这么一个实际存在的生物,寄托着国民全部的朝圣与希望——龙和凤终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发展到“马背上的民族”之后,马匹却更多地被看作运输工具,饱受鞭打与折磨。
我只好用一种简单到多半是不正确的方式去理解它——因为信仰。也许在泰国人的信仰中,大象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精神而存在的体系,在该体系中,每一种人类活动的形式,都需要获得特定神衹的认可(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发展出了一大堆规矩:例如进寺庙必须要拖鞋,着装不可穿短衣短裤,脚底板不能冲着佛祖等等……)。大象,这种强壮而又温顺的生物,既能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又能像神灵一样温柔地守护着国民,同时作为神在世间的使者,也顺带解决了形而上的问题——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大象的监督下“净化”自己,等待神的来访。
而“未知生,焉知死”的中国人,则直接跳过了宇宙本原的概念,更乐意去讨论那些人伦纲常,自然不会有什么生物崇拜,就算是烧香拜佛也不过是“有事才去拜,没事搁一边”,菩萨不灵拜观音,观音不灵还有玉皇大帝,反正三十六路神仙拜个遍,管你是如来佛还是吕洞宾,只要灵验就行。给你香火钱,也不过是为了讨个头彩——不像是信仰,更像是一种交易。
路过一间供奉着佛祖的小寺庙,烛光还微微摇晃着,里面睡着一名乞丐。头枕在坚硬的瓷砖上,黑乎乎的脚底对着门口,身上散发着酸臭味。
潦倒如他,却仍不忘记把拖鞋留在庙外。
绿肥红瘦
住的地方是从AirBnB上订的民宿,一座吊脚楼埋在深深的庭院中,院子里什么颜色的花都有,每一处落脚点都藏着小小的心机:秋千前面垂挂着依依杨柳枝;石凳边一对天鹅造型的喷泉布景;慢卷珠帘,倚栏凭望便可看到小园香径;房东早已算好了时间,在屋内角落点上了蚊香,袅袅香炉紫烟,悠悠琴弦佳人。
而且,更重要的是,WiFi一点不卡,浴缸香氛俱全,咖啡洋酒免费。
真可谓诗意其外,摩登其中。
房东是个德国人,操着浓浓的日耳曼口音,语速极快,早已按照约定的时间等候在门口交付钥匙。“清迈是个好地方”,他说,“欧洲太不安全了,到处是难民,天天有恐怖袭击。”简单地介绍了一些设施功能,参观了所有房间,叮嘱了一下安全事项后,他笑道,“这是我布置得最为用心的一间房子了,相信你会舍不得出去玩的。”
被他说中了。
因为刚住进去就下起了大雨。
雨水带走了暑气,拂去了灰尘,打到树叶上,顺着叶子的纹理汇聚而下,嘀嗒、嘀嗒……
饮茶听雨,丝竹红袖,水流心不竟,云在意俱迟。
庭院深深深几许。
一直觉得宋词不应该读出来,而应该唱出来。这3个深,如果用唱的,我相信一定是3种不同的声调,千转回肠。
诗和画不同,虽同为艺术作品,画作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在逃避现实——越是张扬越是阴郁,才越能得到共鸣,它毫无规律可言,甚至不需要多数人的理解。诗作正相反,它必须得符合一种韵律美和语言学上的必要性,它的存在是为了激活现实——就像是一个心灵,寻觅肉体但找到词语,朗朗上口连老妪和幼童都可挂在嘴边。
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记得高中的时候,老师解读这首诗,说欧阳修想表达的是深闺女子在封建社会中受到的压抑和禁锢,即使物质生活很丰饶,也缺乏精神上的自由,无人可以交流,因此是极度苦闷的。可是多么的讽刺,如今我们可以自由地穿梭在世界各地,与不同肤色的人谈笑风生,但这同时也是另一种身不由己——你可以选择不出差吗?可以选择不开会吗?敢不开机吗?此刻,惟有躺在这深深的庭院中,关掉WiFi,静静地听雨水敲打在无重数的帘幕上,才感到了片刻的自由。
忽然又想到晏殊的一首词。小时候一直记不住这个人的名字,也许是因为“晏”字很难写,也许是因为他的词总是排在北宋那一章的最后几页,所以始终背不到,唯一能记住的就是那句著名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他的作品很淡,不像范仲淹那么忧国忧民,也不像柳永那么愁肠百转,更像是记录生活点滴的日记——放到今天,也就是个发个朋友圈,配配字吧。可是高中老师仍然能把他解读为“通过描写司空见惯的现象,启迪人们从更高层次思索宇宙人生问题。”
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宇宙人生问题呢?
一曲新词酒一杯。
喝酒作词,不像是思考宇宙,倒更像一个摇滚歌手,坐在吧台的角落,续上一杯Johnnie Walker,开始拨弄吉他。是不是搞艺术的人都比较喜欢一边创作一边喝酒,这个习惯似乎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变。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有色彩,有意境,就连套路都套得那么真诚:我手里有酒,你有故事吗?
去年天气旧亭台。
晏殊喝着喝着,忽然想到,哎?去年似乎谈了个恋爱,好像也是在这个地方还说过不少情话。呐,这个恋爱蛮好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也就分手了,可是分也分得很自然,分别时不会“无语凝噎”,分手后也不会“衣带渐宽”,就这么淡淡地随风而逝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晏殊伤感了一会,估计是回忆了一下妹子昔日的温存,但随后又自我安慰,算了算了,分就分了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想必也是,作为礼部尚书的他又怎么会缺女人呢?而且他现在,也一定另有新欢了吧,说不定正在给他斟酒呢。
小园香径独徘徊。
道理都懂,可是做不到呀。念到这里,我都能想象出晏殊百爪挠心的模样。居然会这么的不甘心,难道是尚书大人被甩了?
雨停了,高中语文也复习完了。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