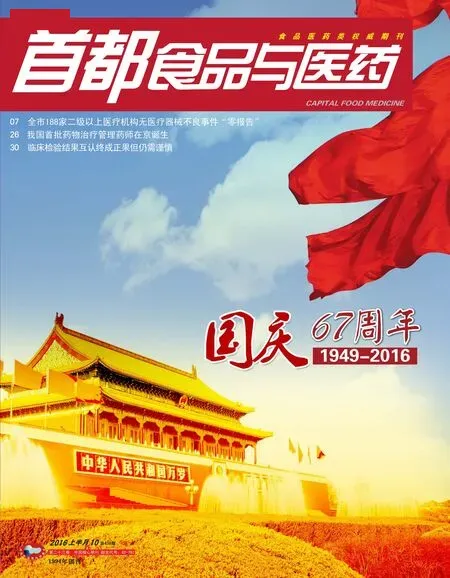《麻醉·人生
——李树人教授50 年的麻醉生涯》(连载)
(接9 月上)
尤其令我佩服的是阿根廷人的淳朴和热情。在阿根廷,乘坐公共汽车的秩序非常好,他们绝对遵循女士、老人优先的原则。有一次我和一个心外科大夫去丹捷勒医生家做客,因为路不熟悉,在问路时碰到一位热心人,他让我们稍等一会儿,然后他把自己家车开出来,直接送我们到了丹捷勒的家。
因为当时中国比较落后,改革开放也才两年的时间,当地的阿根廷人开始都以为我们是日本人,他们甚至不知道中国在哪儿,是什么样子。阿根廷的日侨比较多,华侨比较少,而且大多华侨都是台湾过去的。
平时我一天能四台手术,上午两台,下午两台,周末有2 天可以休息。这对我来说也是难得的,因为当时在中国大陆仍然是六天工作日。阿根廷人的性格较散漫,守时观念不强,无论商务还是私人约会,他们总会姗姗来迟。但他们比较热情,著名的探戈就诞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人视之为国粹。它是集音乐、舞蹈、唱歌、诗歌于一体的综合艺术。阿根廷人酷爱烤牛肉和红酒,在布市主要街道各类烤肉店随处可见。马黛茶被誉为阿根廷的“国茶”。有时候休息,阿根廷的朋友会邀请我和同事们去他们自己家的农场玩,享受一番地道的阿根廷生活。丹捷勒教授本人也是个能歌善舞的人,客人们去他家做客,他常常会放音乐为大家跳上一段阿根廷舞。
打开一张阿根廷地图,可以看到全国织得如蜘蛛网般的铁路线汇聚到一个点上,那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由此不难看出它在阿根廷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

也正是因为阿根廷的城市人口集中,所以城里的人有不少都在郊区有自己的一片庄园或别墅。丹捷勒教授的农场距市区也就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在阿根廷朋友郊区的住所,常常会设有家庭游泳池。节假日不是华人就是麻醉大夫会邀请我和同事们,去他们家或者农场做客,有时候大使馆在休假日也组织大家到郊外去休闲娱乐。在8 个月的学习生活中,我们的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有时候华侨也邀请我们去中国餐馆吃饭,他们都是台湾的华侨,这些人跟大陆使馆的联系还是比较多,每到国庆以及各种节日,使馆就邀请华侨到使馆开就会,每次都有二三十人,多数是从台湾过去的,他们的祖籍都在大陆。
学成归国
当时有华侨打算在阿根廷开医院,就请我留下跟他们共同创业。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心系祖国的我拒绝了华侨的请求,我毅然和医院的同事们回到了祖国,并从此开创了中国大陆麻醉界一片广阔的天地。
在阿根廷的日子里,我一场电影都没看过,游泳池一次也没有去过,始终把学习放在了第一位。归国时,还结余了不少钱,但大家都同意购买一台学习用的录音机(当时国内很难买到),剩下的钱,以及出发时国家给我们做的3 套衣服,我们回国后都统一交回。
友谊医院麻醉科的主要奠基人谭蕙英教授20 世纪50 年代从国外回来后,该院的麻醉科就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她在担任科主任期间做了许多意义重大的工作,也培养了一批人才,我后来在麻醉专业的点滴成绩,和她当年的悉心栽培是分不开的。
1980 年底,我从阿根廷学成归来后,医院考虑由我接任麻醉科主任。当年12月份我就正式担任了北京友谊医院麻醉科主任的职务。因为一直师从谭蕙英教授,而且那时谭蕙英教授是北京麻醉学会的主任委员,我是她的秘书。除了医院的科室工作,我们还负责北京麻醉学会的工作。所以业务上的衔接是比较顺利的。走下工作岗位的谭蕙英教授也一支持我的工作,我也非常尊重这位老师。科里的工作安排我一般都会提前与她沟通,之后再拿到科会上来讨论,我们在工作中步调非常一致。
担任主任后,科室里的医疗、教学、科研以及人才培养由我一人主抓。
很快我就做了开展心脏麻醉手术的计划,要求科室的所有医生,只要担任主治医师后,就有必要掌握心脏手术麻醉这项业务。麻醉科刚开始只有10 个大夫,后来每年补充2 ~3 个人。直到20世纪90 年代,成为有34 位医生的大家庭。
心外手术麻醉的开展
学成归国后,友谊医院麻醉科随即委我以重任,作为项目负责人,开展冠状动脉搭桥和心脏瓣膜转换手术的麻醉新业务。当时手术过程中,麻醉的操作与管理以及术中、术后发生意外情况的应急处理等我都能妥善解决,保质保量完成医疗任务。当时由于北京市属医院还没有开展心脏外科手术,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相应设备的缺乏,如有创的血液动力学的监测仪器∶心排血量监测、肺动脉压测定、IABP 等配套检测。友谊医院既然已经走到了前头,所以从北京市领导到卫生局领导也都希望冠状动脉心脏瓣膜置换业务能够成为全国的排头兵,因而得到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我拟定的采购计划,很快在卫生局获批,并先后从德国和美国引进,及时应用到了手术中。
解决了硬件问题,紧接着就是人员培训的软件问题了。一台冠状动脉搭桥和心脏瓣膜转换手术中,需要麻醉大夫2人、手术室护士3 人,体外循环机需要单独配备2 人。可当时医院在这项业务上除了我自己,别人都没有学过。要是开展这项业务,全体麻醉科的大夫和护士都得跟着我学会心脏外科手术的麻醉技术,而且必须细致到手术遇到问题怎么解决,监护仪器设备哪一项指标是什么意义等知识。我逐一详尽地向全科室同事们普及,同时又重点培养了几位年资较高的主治医生,系统传授了相关麻醉技巧。
当时每台手术都是我亲自去做,2个人在辅助我的过程中边看边学。做手术都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开始的时候一台手术从早上7 点半做到下午2 点左右。熟练以后上午完成一台,下午再做一台。半年里,一个星期3、4 台手术,以后慢慢增加到每周开5 台手术。
刚开始重点培训的小班组通过动物实验了解手术的麻醉过程和配合,经过1年的传帮带,所有人能独立完成操作了,然后再由这些人去帮其他的同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当年友谊医院做的第一例心脏搭桥手术,那一位心绞痛的男病人,60 岁,冠脉堵塞80%左右,搭了2 根桥,手术完成得比较顺利。
随后,我们开展了部分马凡氏综合征的外壳手术治疗,也就是主动脉和冠状动脉置换术。友谊医院麻醉科在这些手术的麻醉技术上,一直处在国内领先的水平。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我们医院心脏外科准备开展对慢性心力衰竭的病人实施手术治疗。这一方法是将病人带着神经、血管的背括肌游离下来,用以包裹心脏,同时植入心脏刺激系统,也就是背括肌来刺激心脏,使得心脏的收缩排血,舒张使血液回心达到正常。所以这一手术的麻醉是很复杂的。我们与心外科合作,从做动物实验开始,摸索背括肌包心以后的电生理与麻醉的关系,尤其是吸入麻醉药、肌肉松弛药,对背括肌电生理的影响。要探索药物影响的时间,停药以后多长时间能恢复。我发现,提前停药,逐步减低浓度才可以保证手术的成功。当时刚开始也是拿狗做实验,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攻克这个难点。
因为白天还要给病人做手术,只有晚上才能继续做实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忙到12 点,把衣服的袖子都磨破了。一天,极度劳累的我在工作台上睡着了,手中的烟头掉到袖子上,从外烧到里,直到烫到肉才醒来,随后我又强打精神,接着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