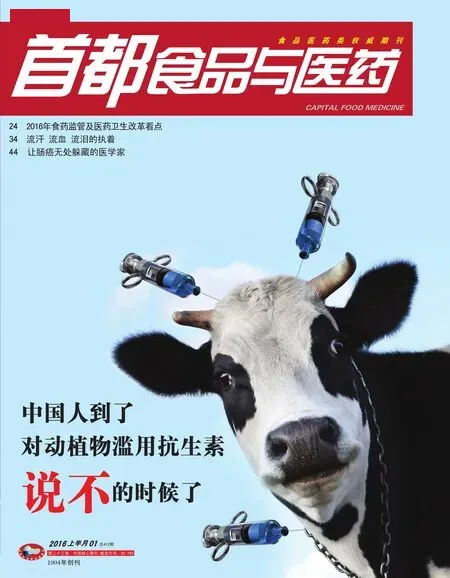让肠癌无处躲藏的医学家
——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科部部长、消化内科主任姜泊教授
●许方霄/本刊记者
为了鼓励中国科学家刻苦钻研,为社会作出更杰出的贡献,香港爱国金融家何善衡、梁琚、何添、利国伟于1994年创立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被社会称为“小诺贝尔奖”。2015 年度的“何梁何利基金”共有52 位优秀科技工作者获得此项荣誉,而医学领域仅有8 位,其中,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姜泊教授就是这8 名医学领域获得者中的一位。姜泊凭借什么成就获得此项殊荣?他在医学道路上有着怎样的经历?对医学为什么始终执着?对未来他又有何规划?近日,记者与姜泊教授面对面交流,听他敞开心扉,倾诉自己的故事。

▲姜泊在为患者做内镜
“引领者”是获得肯定的主要原因
记者:姜教授您好,首先恭喜您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据我了解,您有很多了不起的成就和创新发明,比如,对大肠癌的早期诊断与治疗,研发结肠胶囊机器人、快速检测芯片等,胶囊内镜的研发更被医学界誉为“消化道疾病诊断的第四个里程碑”、消化道检查尤其是小肠检查的金标准。您认为是哪些成就促使您荣获此项荣誉?
姜泊:谢谢。能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是对我个人的一个肯定。我认为,给我颁发这个奖项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在大肠癌的研究过程中,无论从技术和引进观念方面,都扮演着引领者的角色,在这方面的贡献也得到了评委的肯定。
要知道,大肠癌在早期很难发现,癌症萌芽时多无症状,即使有症状也是非相关症状,不能及时就诊,国内以往的早诊技术为基于病灶有出血的大便潜血试验,检出阳性率低,仅20%~30%。国内的学者一直在寻找一些能够串联或并联,甚至替代现有的诊断的方法及检测手段。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寻找快速简便并实用的人群筛查方法,用于迅速标定大肠癌高危人群,并接受大肠镜检查。经过不断攻关,最终我们将研究目标锁定在原有敏感血红蛋白标记结合粪便标本DNA 候选基因及不同阶段可能存在的肿瘤蛋白候选标志物身上,采用Luminex&ram 方法形成组合液体快速筛查芯片,以提高大肠肿瘤病人检出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从而提高早期大肠癌及癌前病变检出率。这种独特的集血红蛋白检测、DNA 和相关表达蛋白检测于一体的筛查方法,也为其他胃肠道肿瘤的筛查提供了开放性思路。此外,我们还于国内率先引进并开展了EMR、EPMR和ESD 等系列的大肠肿瘤内镜下微创治疗技术,形成了实用可靠的内镜下大肠肿瘤诊治平台,不仅使我国大肠肿瘤早诊的关键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将肿瘤的早期治疗也推到了临床前沿。
肠镜检查是确诊结肠疾病的金标准,但传统的结肠镜检查方式常使病人觉得痛苦,检查有时也会对肠道黏膜造成机械性损害,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对胶囊内镜进行了改革,开发了结肠胶囊内镜机器人操作系统,将产学研有机结合,成功开发出可控结肠胶囊内镜,使之成为一种新型的微创、无痛消化道疾病智能诊断设备,可广泛应用于全消化道疾病的诊断,尤其在传统内窥镜不能到达的小肠检查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就像孙悟空变小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可以把肠道的一个小皱褶都看得清清楚楚。目前,项目进展顺利,现在正在临床试验阶段,预计几年后即可完成研究,进入产业化。这也代表了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两位父亲决定人生方向
记者:俗话说“男怕入错行”,您今日在医学界取得的成就,证明您选择医生这个职业是正确的。听说您父母都是医生,那您当初在选职业的时候是受父母影响吗?
姜泊:我父母都是医生,一直以来,我没想过要做别的职业,就是想当医生。我非常喜欢医生这个职业,我始终认为,对于不满足于现状的人来说,医生不啻于最好的工作。医学具有很强的挑战性,每次与疾病“生死角力”,救患者于存亡之际,我都激动异常。
我父亲是医务工作者,我母亲是位儿科医生,医术很好,来找她瞧病的人很多,在我的印象中,她总是起早摸黑,经常半夜三更地被乡亲们叫去急诊。在我刚懂事的时候, 我父亲就被下放到了辽源的一个小镇上,东北的冬夜特别冷,一点不夸张,真是寒风刺骨,但只要一听说哪家小孩有情况,我母亲就像是听到紧急集合的哨响,迅速翻身起床,披上大衣,提着药箱就往外跑,比小孩家属还着急。看着母亲救死扶伤,获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我从小也就有做医生的愿望。但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学医的动力是父亲的离世。1974 年,我五年一贯制毕业,同样是那年,我父亲因肺癌转移而去世,从发病到死亡,仅2 个月时间。我至今都还记得,父亲发病不久后,主治医生拿着CT 片,指着一块阴影无奈地对我们说:“看见没?这就是肿瘤,这东西呀,谁也没法治。”那天,我独自一人悄悄来到东北地区最高的医学学府——吉林医科大学(现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大门口,站在那儿久久没有离去,心想,我得做医生!一定要做医生!

▲姜泊与研究生在实验室验证实验
记者:在这股强烈的力量下,您五年一贯制学习毕业后就顺利地考上梦寐以求的白求恩医科大学了吗?
姜泊:没有。毕业后,我下乡到了当地的一个生产大队当了2 年的“知识青年”,1 年后又回城接了父亲的班,到医院工作。那时候我也曾灰心地想,也许我以后能上中专都不错了,但想进吉林医大学习的念头却从未断过,到医院工作后,想进修、上学的愿望就更强烈了,但当时只有单位推荐的工农兵学员才能上大学,我根本就没有上大学的可能。1977 年,国家宣布高考恢复后,我就搜集相关书本和资料,复习20 天后就参加高考,并很顺利地被吉林医科大学医疗系录取。我们那年大约有570万考生,当时考场老师就说,1 分能压倒1000 人,能考上大学真得很不容易。
记者:当时医科院校都是没有分科的,待毕业后还得到医院轮岗,最后才能定科室。您到消化内科是基于何种机缘?
姜泊:1982 年,我从吉林医科大学毕业了,正赶上国家强化军队医疗,一车皮把连我在内的40 位医学毕业生拉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以下简称301医院),并正式成为一名军人。在301 医院先轮转2 年打基础,然后被分到老年消化科,随后,我又顺利地考上301 医院的硕士研究生,但仍未明确自己的学科研究方向。1986 年,当时我还正在读研,有一天,岳母突然跟我说,我岳父的大便不太正常。可能是职业敏感性,在为岳父看过病后,我认为他的肠道可能存在严重问题,所以就立即带岳父做了进一步检查,检查结果令家里每一个人都吓了一跳——直肠癌。
我父亲生病时我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我们而去;但我岳父患病时我已经是一个消化科医生了,我就想着,我有责任把这些癌症,首先是这令人诅咒的直肠癌给解决了,所以我便将大肠癌确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岳父成了我接手的第一位肠道癌症患者,但在两次化疗后,老人的身体每况愈下,于是我决定运用临床所学,对他采取个体化保守支持疗法,直至如今,老人依然健在。
记者:在301 医院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您却突然去了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并在几年后就获得了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期间又发生了哪些事?
姜泊:在大肠癌研究方面,当时周殿元教授是全国最顶尖、最权威的专家,为了进一步提升自我,在301 医院工作了10 年后,我报考了第一军医大学(现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周殿元教授的博士生,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从此便开始了我22 年的南下生活。
在南方医院,我帮着周殿元教授建立科室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建立细胞凋亡和大肠癌相关的基础研究方法。1999 年,周老师推荐我去日本跟随世界著名的大肠癌专家——日本学者工藤进英教授研修半年的肠镜单人操作法和早期大肠癌诊治。在一家规模不到500 张床的医院,我见证了工藤进英教授做出的世界顶级水平的业绩,并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找到大肠癌变的源头,才能提高大肠癌的治愈率,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定将自己的科研方向进一步调整为“早期大肠癌临床诊治”。
归国后不到一年,我就在国内首次发布了有关大肠侧向发育型肿瘤和大肠锯齿状腺瘤两种新的肿瘤的新发现,建立了大肠黏膜腺管开口分型的新的诊断标准,开展了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和内镜下分片黏膜剥离术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这些技术对于鉴别大肠肿瘤性病变和非肿瘤性病变及早期大肠癌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项成果,2003 年,以我为第一完成人的“大肠癌的早期诊断与治疗”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姜泊在主持内镜高峰论坛
日本学者身上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记者:在日本进修期间,您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和收获吗?
姜泊:我职业生涯的洗礼是在日本,即使现在,我仍将学生或同事频繁送出去,让他们“洗洗脑”。日本是利用内镜诊疗大肠癌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为了深入研究大肠癌,我又先后多次到日本进修取经。
对于大肠癌,我国发现的多为晚期,所以不论技术如何先进,治疗效果总是不甚理想,而日本对于早期大肠癌的检出率高达40%以上(我国当时不到5%),大肠癌的治愈率更是远远高于我国。过去,国内医学界在进行大肠癌早期诊断时,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大肠隆起型肿瘤,如大肠息肉等,然而,在日本进修的过程中,我却观察到一个现象:在对患者进行大肠镜检查时,在常规观察中没有发现异常后国内医生就放过去了,没有主动去找一些可能发生的病变,但日本肠镜操作医生却会用染色方法,一些看似正常的黏膜经染色后就能发现明显的病变。这些常规内镜难以发现的病变多为平坦性肿瘤,与隆起型大肠肿瘤相比,平坦型大肠肿瘤的恶性度更高,如果按当时我国技术水平,这些病变多半会漏诊,如果这类病变没有被及时发现,患者1 年后再到医院检查时,就可能已经发展到进展期,严重威胁到患者的生存。粗略估计,这类患者如果在早期能够得到确诊和治疗,生存基本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医学界对大肠癌早期发生机制的研究是否存在盲区?在进行深入研究后,结合国际上染色内镜的研发和临床应用,而我国并没有胃肠道黏膜染色剂的现状, 为推动我国染色内镜的开展, 我们开始了研发胃肠黏膜染色剂,通过实验室的不断攻关和临床应用,确定了配方,并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时建立了以染色内镜、放大内镜等技术检出早期大肠癌和大肠平坦型病变等一系列实用解决方案。这样一来,以往很多常规检查没有发现的微小病变和平坦性肿瘤都被检测出来了,很多以往被医生“视而不见”的大肠癌早期患者得以及时诊治。
工藤进英教授曾说过:“做临床工作和做研究都要‘精’,要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在学术研究和临床工作上永不松懈。
记者:那您认为,日本学者身上有哪些值得国内专家学者学习的地方?
姜泊:日本医生的敬业精神不得不令人佩服,我认为,决定日本拥有先进技术能够发现早期癌症的,是日本学者那种研究细微病变的专心、细心和坚韧不拔的决心和意识。日本医生有个很令人敬佩的习惯,如果学科带头人不下班,其他人也不会随意下班。当时工藤进英教授常常工作到晚上11 点,在他的带领下,科室里的其他医生也往往会在病房或实验室忙碌到11 点多才离开。
新平台新挑战
记者:就在大多数人仰视您的时候,您再次出人意料地离开您付出巨大心血和满载光环的南方医院,毅然来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为什么会作出这个决定?
姜泊:在我的带动下,南方医院的消化内科从相对的低谷走向了顶峰,长久以来,在全国都可以称得上是位于前列。但一个人总要有逗号和句号,如今我完成了我的一项使命,这也意味着是时候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的确,离开南方医院,很多曾经拥有的东西都没了,但人总是要归于平淡。就如当年我离开301 医院,很多人都说我博士毕业后一定会回去,由于种种原因,我最终留在南方,但仍做着我想做、喜欢做的事。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之前33 年的医学生涯中,我都是在别人做好的平台上工作,我的任务只是将它继续往前推动,而来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一切从零开始,自己重新建立平台。建立内镜室、自己引进人才、组成团队,把四梁八柱建好并逐渐运转,这都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
记者:对未来如今您有何规划?
姜泊:胃肠道与外界相通,每种疾病都牵涉到胃肠菌群的变化,消化道肿瘤、肝脏疾病等,每一项拿出来都单独成病,而肠道微生态环境的改变牵连着诸多要人命的重症。维稳肠道,调整菌群,保持稳定、均衡的状态,在早癌产生之前,就对肠道进行有效的管理。如今,我联盟十几家单位,正在展开全国调研,对菌群中的成员进行了针对性研究,瞄准整体,要建立肠道微生态诊治规范, 确立经济适宜的系列诊治技术。
此外,我还有一个愿望也正在逐步实施和推广——让患者对胃肠镜不再恐惧,因为内镜是发现早期癌症比较重要的工具。我现在正在做“舒适内镜”的工作,让患者获得一种舒适内镜的享受,不要像现在一进内镜室,就感到无比恐惧,我希望把它转化成一件比较舒适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