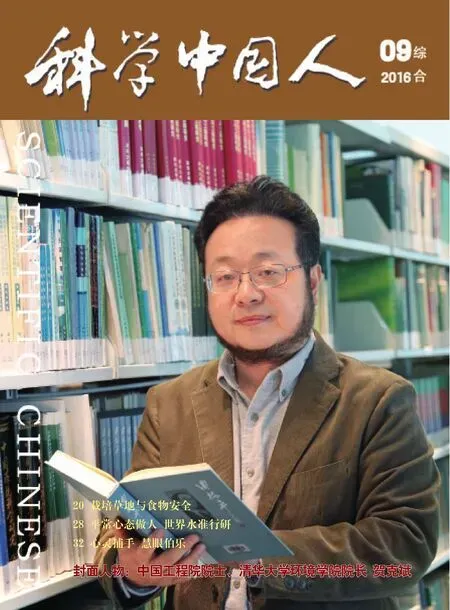平常心态做人 世界水准行研
——记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杨维才
本刊记者 刘 佳
平常心态做人 世界水准行研
——记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杨维才
本刊记者刘 佳

实验中
2016年,他的团队对雌雄配子识别分子机制的系列研究取得了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突破,首次分离了花粉管识别胚囊雌性吸引信号的受体蛋白复合体并揭示其激活的分子机制。该研究通过基因工程手段建立利用生殖关键基因打破生殖隔离的方法,为克服杂交育种中杂交不亲和性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对人类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被评价为“植物生殖领域的重大突破”。
2015年,他与贾鹏飞为向导师郑国锠院士致敬而编著的《郑国锠细胞生物学》(第三版)正式出版,被认为是我国细胞生物学基础教材之一。
他是杨维才——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简称“遗传发育所”)所长,国际拟南芥科学委员会中方成员。长期以来,他投身于植物生殖发育调控机理研究,在Nature等杂志上发表论文65篇,主持的“被子植物有性生殖的分子机理研究”获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是该领域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者。在科学中国人(2015)年度人物评选中,杨维才因其突出贡献当选为生命科学领域年度人物。而只有走近,才会发现,与成绩相比,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的一颗纯粹的赤子之心。
走得再远,初心仍是归来
“第一次接触生殖发育研究,是在兰州大学跟随郑国锠先生读硕士的时候。”杨维才回忆道。与刚入大学时的懵懂不同,到硕士期间,他开始研习雌配子体超微结构等细胞生物学的相关研究,每天会泡在实验室里做切片,进行电镜观察,实验台上所展示的那个世界激发了他对于科学的兴趣。这兴趣,在他心底扎根,经过数年学习的滋养,茁壮成长,渐成参天之势。
1990年年初,杨维才通过了中欧联合培养博士项目的考核,前往荷兰瓦格宁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Ab van Kammen教授和Ton Bisseling教授,主修分子生物学。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对分子生物学的认知,多停留在书本的介绍上。但有了细胞生物学的基础,杨维才在根瘤与固氮研究上上手很快。“我读硕士的时候,郑国锠先生正在编写国内第一本细胞生物学著作,对我们要求很严,每年要看150篇英文文献。经过大量的训练后,我对荷兰的科研生活适应得非常好。”
尽管如此,随着研究的深入,他还是发现在豆科植物里做基因克隆等研究非常困难,而国际上在这方面的相关遗传学研究也不多。他决心解决这些困难,并了解到一个被称为世界生命科学圣地与分子生物学摇篮的研究机构——美国冷泉港实验室,有可能实现他的目标。他的执着追求打动了导师。在导师的鼓励下,1996年1月,杨维才结束了荷兰的博士后工作,飞往纽约,师从Sundaresan Venkatesan。而他的研究对象也从豆科植物转向模式植物拟南芥。
“这就是拟南芥,开花结果之后可以结几千粒种子,平均每个果荚里都有50多粒。用它来做生殖发育以及遗传实验非常方便。”说到拟南芥,杨维才指着旁边的一株植物,开始给记者讲解。当时,拟南芥作为模式生物已经十多年了,但生殖过程研究比较冷僻。杨维才早期在郑先生麾下研究生殖发育的兴趣得以借助该模式生物而体现,并乐享其中。
到冷泉港不久,Venkatesan前往新加坡刚成立的分子农业生物学研究所担任所长,杨维才也跟着一起到了新加坡,继续博士后研究。2000年8月,分子农业生物学研究所的一部分合并到其他单位,剩下的一部分成立为淡马锡生命科学研究所,杨维才在这个研究所担任棉花生物技术和生殖生物学实验室主任(PI),带领课题组开展独立科研。
此时恰逢许智宏院士主持的第一届全国植物发育生物学大会在庐山举行。杨维才也回国参会了。在庐山,他遇到了兰州大学校友薛勇彪(时任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助理)。薛勇彪与他一见如故,并邀请他回国。
回到新加坡,杨维才收到了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寄来的申请表。“10月递上去,12月就批下来了”,出乎意料的速度让杨维才都惊讶了。随后,就是遗传发育所的整合期。从2001年到2003年,原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及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逐渐走到一起,挑起了“遗传发育所”的大旗。也是在2003年,杨维才辞去淡马锡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工作,正式举家迁回北京。
遗传发育所位于朝阳区北辰西路,北四环与北五环之间的奥运村南侧。13年前,杨维才刚刚抵达时,那一带的建设尚未崛起,一眼望去,很是荒芜。“面试的时候刚好遇到SARS,还被隔离了两个星期,印象特别深刻。”即使是“非常”时期,也没有挡住他回来的决定。

指导学生实验
做一流的研究
研究了这么多年,对于植物生殖生物学的发展,杨维才心里自有一本账。早在兰州大学读本科时,杨维才就读过我国著名植物胚胎学专家胡适宜编著的《被子植物胚胎学》一书。“传统的生殖生物学,主要是做结构等方面的研究。以胡适宜先生等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做得很好。”
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将生殖细胞分离出来进行体外受精研究,武汉大学杨弘远院士就是植物有性生殖实验研究的佼佼者。但受限于植物生殖细胞是单倍体的客观状况,随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在相关的遗传学研究上进展缓慢,直到T-DNA和转座子技术的出现。其中,T-DNA可以插入到基因组中产生突变,与物理和化学诱变方法相比,T-DNA通常带有选择标记,更容易对突变进行追踪,并对其分离鉴定。转座子(转座因子)的原理与之类似。当一段DNA顺序从原位上复制或断裂下来,插入到基因组的另一位点,并对其后的基因起到调控作用,就被称之为转座。这段DNA序列则被称为转座子。“转座子突变的效率更高,对生殖发育和遗传学的研究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是冷泉港实验室最先在拟南芥中应用的。我刚好赶上了那个时期,及时介入到这个领域。”杨维才说。但在他看来,90年代中期至今才是植物生殖学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科技的发展,当初的“猜测”都走在被证实的路上。比如,科学家们曾发现,因为不具备动物精子的游动能力,被子植物中胚囊会分泌信号分子引导花粉管定向生长,花粉管将精子细胞运送到胚囊里,进而和包裹在胚囊内的卵细胞结合。
“就像拟南芥”,杨维才开始举例,在拟南芥中,花药和雌蕊是分开的,花粉由雄蕊中的花药构成,它们会通过各种方法到达雌蕊,使胚珠受精。至于其到达过程,几十年来,科学家都在猜测雌配子体中有信号在吸引着花粉管的生长。直到2005年,日本科学家在研究中,从蓝猪儿草和拟南芥两种植物胚囊中分离出一种小的分泌蛋白,称为LURE,可以对花粉管的生长起到导向作用。“我们对这个过程也十分感兴趣”,他说,虽然已经发现了吸引信号,但花粉管对吸引信号的响应机制究竟是什么还不得而知,他希望能够分离到花粉管识别雌性吸引信号的受体。“我们的方法和日本科学家不同,他们采用生物化学方法,我们是将生化、遗传、分子生物学等相关方法都融合在一起去探索。但是一开始,我们分离到的并不是这个受体。”
2011年9月,Plant Cell杂志在线发表了一项成果,文中称杨维才团队首次发现了一个控制花粉管响应的因子,命名为POD1。这一工作表明,内质网蛋白在控制植物细胞—细胞间相互作用过程中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控制节点。“这项工作是由李红菊博士完成的,是我们通过遗传方法找到的第一个控制花粉管响应的因子。”杨维才介绍。这项工作首次揭示了内质网蛋白在花粉管响应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并为下一步分离其它控制花粉管响应的因子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但遗憾的是,这并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而只是位于目标调控上游的一个环节。
“内质网是一个质量控制部门,能够控制富含亮氨酸重复的受体类膜蛋白的折叠,如果这个蛋白没有折叠好,会被强制退回反复折叠,直到达到要求才被允许分泌到细胞表面。”杨维才认为,这些膜蛋白中很可能就有他们要找的受体。可是,花粉管上到底有多少类似的东西?不“看”不知道,一“看”之下,竟然发现了40多个。“简直就是一个大家族在上面,于是我们开始找到底哪一个才是我们的目标。”他们以拟南芥为模式生物,通过反向遗传学等手段,最终在花粉管中筛选到了两个膜表面受体蛋白激酶——MIK和MDIS1,参与花粉管对胚囊信号分子的响应。一系列的生化和细胞生物学实验结果显示,这两个受体蛋白激酶共同接受胚囊的信号,并启动花粉管的定向生长。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转基因手段把其中的一个信号受体导入另一种植物荠菜中,并和拟南芥进行杂交实验,发现,转基因荠菜的花粉管识别拟南芥胚囊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能够找到它们,非常高兴。”杨维才很朴素地描述当时的心情。当这一工作发表在Nature杂志时,已经到了2016年2月,时间又过去了5年。他们的发现,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分离到了花粉管识别雌性吸引信号的受体蛋白复合体,并揭示了信号识别和激活的分子机制,被认为是植物生殖领域的重大突破。一直以来,杂交育种都是人类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的主要技术。杂交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雌雄配子体的有效识别。杨维才课题组通过基因工程手段建立了利用生殖关键基因打破部分生殖隔离的方法,为克服杂交育种中杂交不亲和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除了常规细胞以外,其实还有另外的细胞也参与了调控过程,比如中央细胞。”杨维才课题组早在2007年就首次发现了胚囊中央细胞在花粉管导向中的关键作用,打破了人们认为只有助细胞负责吸引花粉管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李红菊和朱杉杉等人通过生化和分子遗传学等方法找到了一个新的基因CBP1,其突变会导致胚囊不能吸引花粉管,不能受精,并最终提出了花粉管吸引信号产生的非自主调控假说。新成果发表在2015年Plant Cell杂志上。
从一开始,杨维才就站在国际前沿做研究,他们的成果也始终与世界水平保持着一致,中央细胞、植物雌雄识别分子机制等甚至还领先一步。但他的话题中却极少提及赞誉,即使谈到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奖项目“被子植物有性生殖的分子机理研究”,他也表示:“这个项目中,除了被子植物花粉管导向的分子机理研究,还包括生殖细胞发育的分子遗传调控机理和早期胚胎发育的分子调控机理。能够获奖,一是代表了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水平;二是同行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在他眼中,这只是对回国后十年工作的一个总结,而如今他和课题组所做的,也不过是对未来工作的一个铺陈。做科研,做一流科研,平常心当如此。
建设特立独行的平台
2003年,杨维才回国时,遗传发育所刚刚完成合并调整,正值建设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遗传发育所早已不是当日的吴下阿蒙。“它也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我刚回来的时候,所里只有30个课题组,现在早已经翻了番,人才也聚集了一大批。”

杨维才团队合影
的确,目前的遗传发育所已经有81个创新研究组,拥有500多名职工。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振声、李家洋、曹晓风为首,遗传发育所麾下尚有国家“千人计划”3人,“青年千人计划”5人,中科院“百人计划”52人,“973”等国家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18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32人,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5个。其中,李振声曾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李家洋当选美国、英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科学院外籍院(会)士,戴建武被评为“CCTV 2014年度科技创新人物”,高彩霞2016年被授予Nature“中国科学之星”等,可谓是人才荟萃。
用杨维才的话说,80多个课题组汇集起来的力量是巨大的。他们的研究领域交叉融合在一起,揭示出水稻、小麦等基因组表达调控规律、阐明了细胞分化的分子机制和建立新的品种设计理论与技术体系,为解决遗传与发育生物学领域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仅2016年度,研究所就争取主持国家重点研发项目7项。多项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和“中国科技十大进展”,包括最近的“小麦A基因组测序”(2013年)和“阐明独脚金内酯调控水稻分蘖和株型的信号途径”(2014年)。
“我们的文化就是相互支持。”杨维才说道,每当有新人外出答辩或报告,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家里”的专家们会集体讨论给他建议。在遗传发育所,一个人出去,往往都有一个团队在后面支撑。“这样青年人才的成长会比较快。”他自然而然地用“家”来形容这个大集体。
从李家洋院士担任所长开始,遗传发育所就在走一条特立独行的路。“我回国的时候,研究所就已经在做每5年一次的国际评估了,我们是中国最早执行国际评估的研究所。”杨维才说。在这里,所谓的内部考核仅仅是一个参考,研究所更看重研究者们的成果在国内外同行中的口碑,研究者们可以专心致志地沿着自己的研究计划向前走。而从2006年起,就连研究生们都不再被硬性要求发论文才能毕业。“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是全国唯一的单位,当时顶着很大的压力,但通过十年的实践证明,这对研究所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作为现任所长,杨维才介绍说,取消发表论文才能毕业的要求,不是降低研究生培养标准。“一个大的工作常常要5年,甚至10年才能做出来。
从数量到质量,对遗传发育所来说,是在走一条跨越发展的道路。到目前,研究所已经有遗传学、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等6个理学硕士、博士学位培养点,植物营养学和作物遗传育种两个农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培养点以及生物工程一个专业学位硕士培养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在读研究生近700余名。这么多学生要成长,他们在培养环节花了很多功夫,“比如平时会有报告和讨论,指导委员会也会进行严格的中期考核”。研究所对于在国际期刊发表文章并没有额外奖励,在杨维才为代表的研究者们看来,发表文章是研究本身的一个阶段,而每当课题组发表一篇对领域有国际影响的文章,所提升的不仅是研究所的地位,还有个人的学术影响力。至于评估,“我们看重的是更高层次的目标,比如你达到了杰青的要求,或者有什么国际影响力,都会得到我们的认可”。“这些标准,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指导学生实验
十几年来,杨维才见证着遗传发育所的成长,也在这个平台上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从中科院百人计划项目到农业部、科技部重大科技专项,从“973”“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支持的重点项目、杰青项目、创新群体项目等,他的科研日程表安排的满满当当。目前,他所主持的“973”项目“雌雄配子体识别的分子遗传机理”等还在进行中,他希望能够在该研究领域继续领先。“我们将来一方面要完善下游的研究,一方面要做些新的东西”,他表示,“只有思想比别人领先,工作才能走得更远。”
不知不觉中,杨维才担任遗传发育所所长已经两年有余。从“十二五”到“十三五”,我国提出了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三步走”目标。中科院“率先行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对遗传发育所来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进改革和创新是未来必须面对的挑战。“现在处于改革阶段,很多新的工作要做,比如鼓励研究员做成果转化工作等,需要不断地学习了解。”处在新的风口上,杨维才也愈发繁忙,实验室内部管理、学术交流、所里的行政工作等,都被他视为责任和义务,希望能更尽可能多地为遗传发育所的明天贡献更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