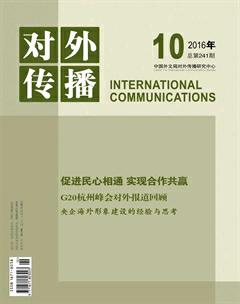中国专家认为大熊猫保护降级为时过早(节选)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近日在美国宣布将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由“濒危”变为“易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将物种的濒危等级划分为7个等级,由高到低分别为灭绝、野外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和无危。IUCN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大熊猫的野生种群数量、栖息地等指标已经全部“超标”,因此,降为“易危”物种是合情合理。
根据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我国现有野生大熊猫1864只,栖息地258万公顷,分别比9年前增长16,8%、11.8%,比低谷时期1985年到1988年的1114只增加了750只。其中,四川分布野生种群1387只,栖息地202.7万公顷,同比增幅均在10%以上。
有“熊猫爸爸”之称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张和民是大熊猫保护“坎坷路”的见证人。“栖息地破碎化仍然威胁着野生大熊猫生存,大熊猫种群交流状况还有待改善,气候变化或会影响竹林,保护管理能力仍需加强。”张和民认为,大熊猫仍是濒危物种,现在将大熊猫保护等级降低还为时过早。
大熊猫人工繁育的成功,是人们对大熊猫认知的阶段性胜利。大熊猫的人工繁育难关在20世纪初已经攻破,从2000年到2006年这期间的人工繁育工作处于技术持续和巩固时期。
“根据遗传学公式,圈养300只大熊猫的目标达到了,说明大熊猫物种在100年内能保持95%以上的遗传多样性,大熊猫可以通过自我维系、自我繁殖来继续繁衍下一代,从而不会灭绝。”张和民说。
然而,在实践中科研人员发现大熊猫圈养种群质量有下降趋势,突出体现在圈养个体的遗传贡献严重不均等。“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圈养大熊猫的遗传多样性已经低于野生种群。”张和民说。
从2010年开始到目前为止,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工作重点转入优生优育和野化放归。目前,该中心一年幼崽出生量要控制在10胎以内,数量会有10到15只,而其中一半要参与野化项目,以保持大熊猫种群遗传多样性。
张和民认为,现阶段是大熊猫野化的最好时机,只有野外种群数量保持稳定持续增长,大熊猫才能真正摆脱濒危境地。“野化放归是对野生大熊猫种群的一种补充、复壮。”张和民表示,通过科学手段,将人工繁育的物种个体经过野化培训后,逐渐适应野生环境,最后放归,是对物种的一种数量补充及繁衍保护。
“如果降低大熊猫保护等级,保护工作一旦出现怠慢和松懈,大熊猫种群和栖息地都有可能遭到不可逆的损失和破坏,已取得的保护成果会很快丧失,特别是部分区域小种群随时可能灭绝。”张和民表示担忧。
而针对大熊猫繁育的另一隐忧就是疫病防治。2014年底,陕西圈养大熊猫发生犬瘟热疫病死亡。“危险一直都在。犬瘟热对于大熊猫来说属于重大疾病,一旦感染,基本上难以存活,而且现在还没有特效药和疫苗。”张和民说,未来大熊猫疫病防治工作更为重要。
“不能说,从濒危变为易危,就意味着大熊猫不需要持续保护了。”卧龙自然保护区木江坪保护站站长施晓刚强调,大熊猫保护工作依旧任重道远。从事了20多年野生大熊猫保护工作的施晓刚认为,这是国际上对中国这么多年大熊猫保护工作的一个肯定,但从我们一线来说,野生熊猫的生存环境,还面临着一定的风险。”
施晓刚和同事们长期在大熊猫栖息地工作,巡护并监测野生大熊猫的行为、健康及繁殖状况。其间,他们遇到了很多实际的问题,这些实际问题是评估专家们无法掌握的。施晓刚说,除了栖息地破碎化这一主要威胁外,大熊猫栖息地环境还受到周边社区的制约,旅游、采药等经济行为也影响着栖息地的保护。
施晓刚说,“降级”或许会对野生大熊猫保护工作产生负面作用,“也有可能出现麻痹懈怠,更甚之造成工作后退”。不过施晓刚强调说,作为一线工作者,他和同事仍将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入保护工作,“以前怎么做,现在还是怎么做,对大熊猫的保护不会因此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