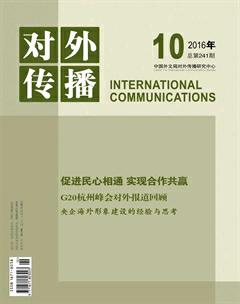澳洲对华偏见从何而来?
苏锑平
2016年8月6日,举世瞩目的第31届里约奥运会在人们的吐槽声中如期举行,然而奥运会刚开幕,人们的槽点很快就转向了澳大利亚。作为澳大利亚地区唯一有转播权的澳大利亚电视台第7频道(Channel 7)在全程转播奥运会开幕式以及各国代表团入场时,却偏偏在中国队入场时插播广告,整个中国运动员的入场式只给了3秒钟,后又在当晚的金牌预测榜中错把智利国旗当成中国国旗。紧接着又有游泳运动员霍顿(Mack Horton)对孙杨的讽刺与挑衅,再加上澳洲媒体火上浇油直呼孙杨为“嗑药的骗子”,这一系列事件让中国乃至整个华人世界愤怒了。对这些事件过分解读甚至上升到民族、国家的层面也许言之过甚,但澳大利亚对华人尤其是华人男性有某种偏见却不言而喻,这种偏见既有现实层面的原因,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现实原因很复杂,因人而异,但历史原因已沉淀在这个民族的基因里。
一、种族偏见
澳大利亚白人主流向来以盎格鲁-撒克逊后裔自居,也遗传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傲慢与偏见。据记载,英格兰人“认为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就没有别人,除了英格兰以外就没有别的世界”①。他们提出“英格兰是英格兰人的英格兰”“英吉利民族的纯洁性可能会由于外来民族的加入而被破坏”②。他们这种种族优越感很容易转变为种族歧视甚至仇恨,当年的英国人如此,澳大利亚白人也是如此。19世纪80年代,他们在当时最有影响的《公报》(Bulletin)上明确喊出“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生于澳大利亚并不必然是澳大利亚人”“支那人、黑鬼、欧洲瘪三都不是澳大利亚人”③之类的话,这种话语与当时英国人的话语简直如出一辙,表达了赤裸裸的种族偏见与歧视。
种族偏见由来已久,18、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还为种族偏见提供了科学依据,“将认定为固定的和遗传的器质的特性和精神的特性相联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将生物的和文化的因素相联系。于是,人之间的区别的自然化完成了……人由于其自然归属于价值不等的种族,价值也不同,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④。欧洲白人对待华人与其他人种的偏见不一样,他们有一种对华人由来已久的恐惧,这种恐惧至少可以追溯到13世纪,欧洲白人在蒙古人的铁蹄下饱受蹂躏,不堪其苦,被称为“鞑靼之轭”。这种历史性的恐惧在19世纪被进一步渲染,俄国的巴枯宁说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英国人皮尔逊则认为“像中国这样的民族……迟早会溢出他们的边界,扩张到新领土上去,并且把弱小的种族淹没掉”⑤。但影响最大的当属德皇威廉二世,他将这种恐惧命名为“黄祸”(Yellow Peril),甚至于1895年请宫廷画师赫尔曼·克纳科弗斯(H. Knackfuss)将其绘制成一幅画,送给大臣及欧洲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威廉二世所说的“黄祸”本意是指日本,但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公关运作,尤其是日本画家久保田米仙(Kubota Beison)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戴奥西(A. Diosy)的著作《新远东》(The New Far East)绘制的《真正的黄祸》(The Real Yellow Peril),成功地将这种形象转嫁到中国人头上,以至于“黄祸”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
澳大利亚白人与华人的接触始于19世纪中期。1851年维多利亚发现金矿,中国东南沿海居民纷纷跨洋过海来到澳洲寻求财富。华人的到来使澳大利亚白人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华人一方面与外界颇少往来,聚集而居,自成村落;一方面生性勤劳、节俭,不仅采金多于白人,而且颇有积蓄。尽管华人主观上无意与白人竞争,他们既不与白人争抢既有金矿,也很少主动探索新金矿,只是跟在白人身后的废矿里淘金,但是白人还是不时地指责华人的淘金活动破坏了当地的水源,指责华人聚居区是疾病的源头,而事实上这些指责并无确切依据。第一次大规模的排华行动发生于维多利亚州的巴克兰(Buckland),2000多名华人被700名欧洲人赶走并成立“反华同盟”。另一次大规模的反华暴乱发生在新南威尔士的蓝坪(Lamping Flat,现改名为Young),他们对华人烧杀抢掠,致使多人受伤死亡。《悉尼晨锋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特派员调查指出,“不能为这种暴行找出任何正当理由,当地的矿工只是普遍地仇视华人”⑥。当时种族主义者的叫嚣反映了澳大利亚白人对华人的恐惧,他们说如果不禁止华人入境,若干年后,澳大利亚将成为中国人的天下。因此1887年张之洞派王荣和与余来澳洲视察侨情,被谣传为将来移送更多中国人做准备,并且已有数万人在中国境内整装待发。澳大利亚白人一面恳请英国政府阻止华人来澳,一面举行排华示威游行。正因为这种恐惧,澳大利亚建国之前的种族政策明显专门针对华人,先是零散地以订立阻止华工入境法令、征收高额人头税、上缴居留税等办法阻止华工入境,之后各州谋求统一应对华人问题,到1888年则制定了统一的排华法案。发展到1901年,变成了对“一切与澳洲文化与生活不同的民族”的移民限制,即“白澳政策”,要把亚洲人和非洲人都排除在外。即使到了“白澳政策”已废除40多年的今天,澳大利亚人仍然对中国和华人有着深深的恐惧。2009年《澳大利亚人报》专职政治漫画家彼得·尼克尔森(Peter Nicoleson)画的一幅漫画就体现了今天部分澳大利亚人的对华恐惧,画面中一艘写有“China”的船上装着整个澳大利亚,下面是一艘小船上几个垂钓的澳大利亚人在嘀咕“这些货轮越来越大,不是吗?”这正是澳大利亚人今天矛盾心态的表现,一方面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一方面又担心中国彻底控制澳大利亚,这也是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呈现矛盾性的原因。
二、经济竞争
英国人皮尔逊(Charles H. Pearson)写道:“中国佬……从事辛苦劳动的能力几乎是没有限度的,而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却是最少的。大部分人民过着一种禁欲主义般的生活,即使把他们放到像在美洲和澳大利亚的英国人那样的生活浪费的种族中间,他们也保持着简朴的习惯。”⑦戴奥西(A.Diosy)也如此写道:“西方工人每天力争少劳多得,他们凭什么来与成千上万勤劳、驯良、节俭、聪明、熟练的中国工人竞争?”⑧对这些英国人来说,华人竞争是想象中的,而对澳大利亚白人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竞争与压力,尤其是对“少劳多得”的投机主义构成强烈的冲击,这也是澳洲白人排华的一个主要原因。
从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开始,大量华人赶赴澳洲,那时没有准确的人口统计,但据当时的华人估计,全澳至少有20万以上的华人。这些人大多出身农民,把土地质押出去或借钱买船票来到澳洲,抵达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努力赚钱偿还欠债,然后再攒钱衣锦还乡。因此他们工作特别勤奋,加之节衣缩食,所得往往在欧洲工人之上,所积累下来的黄金全部运回中国。1856年7月1日至1857年6月30日一年之间,仅由墨尔本运往中国的黄金即达116,900两之多,时值约50万英镑。华人的这些行为无法为那些来自欧洲的喜欢冒险和享乐的白人所理解,他们对此非常反感,认为华人对于当地经济开发并无裨益,这些都成为白人抵制华人的借口。
19世纪70年代金矿资源枯竭以后,那些没有返回中国的华人从采矿区向大城市聚集,尤其是悉尼和墨尔本,并开始转向其他行业,如工商业、贸易、细木工、洗衣等,而那些居留在农村的华人则转向务农,如种菜、伐木、剪羊毛等。华人不管转向哪个行业似乎都能适应,并取得成就,因为无论在哪个行业他们都保持着勤劳简朴的本色,而这恰恰是奉行“少劳多得”原则的澳洲白人工人的大敌,也引起了他们的嫉妒与反对。种菜是当时华人从事的主要行业,当时的人口调查显示,1891年至1911年间新南威尔士与维多利亚多达30%的华人从事种菜行业,几乎形成垄断,白人工人常常抱怨和抗议华人的竞争,指责他们不遵守工作时间,甚至上书劳工部长要求华人菜农实行8小时工作制。他们还指责华人不守安息日,在市场不景气时打价格战等等。
另一个对白人工人构成威胁或形成竞争的行业是细木工。一开始这个行业是欧洲人的天下,19世纪80年代华人进入该行业并生产一些简单廉价的东西。但是中国人的仿造能力与勤奋态度使其很快就在这个行业立足,逐渐占领了低端市场,并且开始向高端市场渗透。华人之所以能占领低端市场,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澳洲白人不屑于进入低端市场,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华人保持竞争优势的法宝:长工时、低工资。之所以能进入高端市场则是他们利用自己的经验进行专业化的流水线生产,各家生产不同的产品,既能保障产品质量又能提高生产效率。华人的低价格高质量产品对从事细木工行业的澳洲白人工人无疑构成了沉重的打击,为此白人工人多次指责华人的“廉价劳动”“血汗工厂”以及违反工厂和商店法。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里,华人与白人之间进行过多次指控与反指控。在竞争不利的情势下,澳洲白人工人祭出了最后的法宝:推动议会制定排华议案,要求把华人作为一个种族来对待,且这些议案仅适用于华人。尽管这些议案没有最终通过,但却产生了实质性的效果。20世纪上半期澳洲华人持续减少,直到二战之后才重新反弹。事实上,直到今天,澳大利亚人对“华人竞争”依然心有余悸,比如尼克尔森(Nicoleson)在2009年画了一幅漫画,画面中一个穿着脏兮兮矿工服的白人对着西装革履的华人管理者叫嚣道:“我们不要该死的中国佬管理力拓”,而华人则回复道:“伙计,总比该死的英国佬好吧。”
三、配偶之争
种族偏见和经济竞争是澳大利亚白人对华人排斥最直接最外显的原因,另一个他们从未明说但显然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女性资源之争。把女性当资源也许会让女权主义者感到不适,但在当时女性对澳大利亚男性来说就是资源,甚至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他们以保持种族纯洁为借口,声称与华人通婚会打破澳大利亚的白人血统。但正如笛福1701年在讽刺小诗《纯种英格兰人》里说的,“纯种英格兰人?——我才不信!字面上是笑话,实质上是幻影”。连英格兰人都没有纯种,更何况澳大利亚人?真正的原因在于配偶之争。
在英国人抵达澳大利亚的100多年里,女性一直都是稀缺资源。1788年菲利普船长率领第一舰队押送第一批囚犯来到澳洲,其中有男性囚犯568名,女性囚犯191名,这是澳大利亚男女比例不均的开始。据澳大利亚学者贝特森(C.Bateson)统计,从1788年至1868年间英国总计输送160,151名囚犯到澳洲,其中女性囚犯为24,568名,约占15.3%。⑨自由民中女性人数也远不如男性多,大多数是男性移民的家眷,直到20世纪初,男女比例才基本实现平衡。澳大利亚作家罗伯特·麦克林(R. Macklin)在著作《黑暗天堂》(Dark Paradise)中记载了诺福克岛及澳大利亚男性为争夺女性所进行的残酷而血腥的斗争,当时被严厉禁止的同性性行为在这里也成为公开的秘密。
然而,与白人相比,华人的男女比例更悬殊。新南威尔士州在1856年共有华人1806人,其中女性6人;1861年华人总数12,988人,女性2人。之后女性人数略有增加,但直到1921年女性才达370人,而华人男性则有6,903人。在华人聚集的维多利亚也是同样的情况,1854年的2,341名华人中没有一个女性,1861年华人男性24,724人,女性才8人,1921年也只有244名女性,南澳、西澳和昆士兰的情况与此相似。由此可见华人男女比例之悬殊,而在澳华人男性又正当壮年,这对澳大利亚白人男性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据1911年的人口统计,全澳共有华人两万多,但只有801人与妻子同居,其中娶中国女性为妻者仅181人,其余皆为澳洲妇女或白人。⑩这个血淋林的现实在一女值千金的澳洲绝对是让人嫉恨和反感的。更有谣传清政府派人赴澳考察侨情的目的就是为以后大规模移民做铺垫,把澳大利亚作为解决国家贫困而人口过剩的安全阀,这让白人生出一股“亡国灭种”的巨大恐惧感。
四、结语
综上观之,澳大利亚的排华与其他种族的排华原因不尽相同,他们并不一定认为华人是一个低等种族,更主要的是来自对华人的恐惧,担心他们的经济竞争和种族入侵。事实上,从史料来看,排华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劳工阶层,华人的到来对他们构成的威胁是最直接的,他们排斥的也是对他们构成直接威胁的劳工阶层,华商以及少数处于社会上层的华人在白人社会颇受好评,甚至有华人菜农在离澳返华时,白人还自发举行全城欢送。由此可见,所谓的“排华”并不完全是种族原因,更多的是因为白人的生存和事业受到威胁。反观这次奥运会上霍顿对孙杨的行为,也是因为孙杨是他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扩而言之,澳人反对中国电网收购澳洲电网(Ausgrid)也是同样的原因。其实,目前世界上的某些对华非议实则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我们对此无需过于在意,我们需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国家实力,同时加强对外宣传。
「注释」
①肯尼思·O.摩根《:牛津英国通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37页。
②John Guy. Tudor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52.
③M. Mckenna. The Captive Republic,CUP,1996:151.
④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16页。
⑤吕浦等:《“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9、100页。
⑥刘渭平《:澳洲华侨史》,星岛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30-42页。
⑦同⑤。
⑧Arthur Diosy. The New Far East, Cassell & Company, 1898: 338.
⑨Charles Bateson. The Convict Ships, 1787-1868, A.H. & A.W. Reed, 1974: 380.
⑩同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