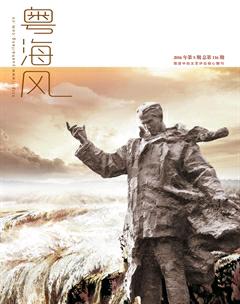清代第一位广东状元庄有恭的宦海沉浮
陈圣争
乾隆四年(1739)的那场科举考试,改变了328人的命运,对当时不少人而言,这一年更是他们的转运年,乾嘉时期不少名人都在是年考中进士,得以步入仕途,世人皆谓得人之盛。年长者如沈德潜,直到乾隆三年(1738)乡试中举,他已考了17次,这一年终于联捷高中二甲第8名进士,此时他已经67岁;年少者如裘曰修,二甲第7名进士,年28岁;袁枚,至乾隆三年乡试他也考了4次,是年联捷为二甲第5名进士,年24岁;更少者蒋麟昌,二甲第9名进士,年仅18岁,不过22岁即去世,如流星划过这片群星璀璨的天空。其中,最耀眼的当属是科状元庄有恭,年27岁。
庄有恭,字容可,号滋圃,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人。先世本福建晋江人,其祖父庄振鸾为避耿精忠乱始迁入广东惠州府博罗县,其父庄承辅(字奕仁,号存斋,后以字行)再迁居广州府番禺县城东,著籍番禺。庄有恭兄弟七人,他排行老二。自幼聪明异常,13岁就通五经,旋选补为诸生,后以贡生考授宗人府教习。
乾隆三年顺天府乡试中举,乾隆四年会试成贡士。是年四月初一殿试,乾隆帝御制策问于太和殿前。依殿试旧例,一般由读卷官进呈前十名试卷供皇帝定夺名次,皇帝通常以读卷官为所定名次为据而微调,但一甲三名,尤其是状元名号,对士子而言是最大的荣耀,则较为谨慎。在乾隆初期,乾隆帝对殿试非常重视,名次改动也较大。因为乡、会试皆由官员出任主、副考官,乡、会试所取士子对其考官、阅卷官等深怀感恩,认作座师、房师之类。虽然清初以来一直禁止科场攀附的“师生”关系,但现实生活中,风气一时难以改变。而殿试的最根本意图,就是让进士们认同“天子门生”的概念,意识到他们的科甲出身最终是由皇帝决定的,所以效忠皇帝、宣力国家才是考取功名的根本。从乾隆元年到乾隆七年这四科殿试卷中,乾隆帝有将第6名置为状元者,如金德瑛;有将第4名置为状元者,如于敏中;有将第2名提至状元者,如金甡;此外,前十名也都基本上由他一一改定,有时甚至将第10名提为探花者,如乾隆二年的探花任端书。
四月初四日,读卷官们将前十名的试卷进呈乾隆帝审夺。据记载,庄有恭廷对试卷中有“不为立杖之马,而为朝阳之凤”一语,时为读卷官尹继善看后大为惊奇,称颂有嘉,遂与诸读卷官推为第一进呈。这一次,乾隆帝没有改换第一,并还对读卷官说:“今次尔等所取之卷无浮泛之习,所拟第一甚为允当。”因为这次的廷试前两天,乾隆帝就意识到此前的廷试有预先撰拟与歌功颂德之弊,因而谕旨说他要亲拟廷试策问之题,不拘旧式,以免有人事先揣摩,而且还规定“诸生策内,不许用四六颂联,但取文理明通,敷陈切当,不必泥于成格、限于字数。”乾隆帝极可能是看了第一名的策问卷后也甚为赞许,才没做改动。当庭拆卷时,第一名为庄有恭,广东人,乾隆帝更是惊喜地说:“广东僻远之省,竟出状元耶?”吏部尚书甘汝来奏曰:“前朝曾有数人,本朝从未曾有。”乾隆帝说:“九卿京堂内并无广东人,今得状元,颇为可喜。”初五日,乾隆帝御太和殿,钦点庄有恭为状元。乾隆帝这次感到惊喜的是,当时六部九卿等京官中没有广东人,状元历来也多为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人士所占,庄有恭在没有攀附或同乡官员的援引下夺魁,实为罕见。自唐代实行科举以来,至清末,广东总共才有九位状元,唐代、南汉、南宋各一位,明代有三位,庄有恭是为清代广东第一位状元。
科举旧例,一甲三人直接授翰林院官,状元授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编修(正七品)。四月二十九日,授庄有恭为翰林院修撰。五月十四日,引见是科新进士,乾隆帝见到新科状元庄有恭“风度端凝”甚为欢喜,便又令入直南书房,后又充日讲起居注官。入直南书房,而非上书房,乃是备乾隆帝文学、顾问用而不是陪皇子读书,可见庄有恭已备受乾隆帝青睐。乾隆五年九月,史贻直奉旨为庶吉士教习,庄有恭因可以入直南书房,便借故经常不到庶常馆学习,惹得史贻直大为光火,愤愤地说:“我二十年老南书房,不应以此绐我”,因此将要奏禀。幸亏庄有恭的乡试房师为彭启丰(按:彭启丰为乾隆三年顺天乡试同考官,会试考官人员并无彭启丰),而史贻直又是彭启丰会试房师(按:史贻直为雍正五年会试主考官之一),庄有恭算是史贻直的小门生,后由彭启丰出面居间婉意调停,才化解掉史贻直的怨气,修复二人关系。
乾隆七年散馆考试,诗题为《赋得春蚕作茧五言八韵限咸字》,庄有恭赋诗有句曰“经纶犹有待,吐属已非凡”(按:袁枚《随园诗话》误为庄有恭未遇时所作,而阮葵生《茶余客话》、梁章钜《试律丛话》皆误作朝考诗),时人颇为传诵,认为不愧是状元语,抱负非凡。同年中沈德潜、裘曰修等皆考得一等留馆为翰林院编修;袁枚则为清书庶吉士,考满文翻译,入末等,外放为知县。从此他们正式迈入仕途,然而各人的际遇不尽相同,尤其是袁枚,在仕途上与他们日益云泥之隔,惟庄有恭与沈德潜在众同年中青云直上。是年,庄有恭四弟庄有信亦中二甲第29名进士,引见时,庄有恭恰好以起居注官侍直,乾隆帝询问庄有恭相关信息后,便将庄有信选为庶吉士。这一下,两兄弟皆入翰林,一时海内传为美谈。是年冬,兄弟二人请告归省,成为当地的盛事。
乾隆八年是庄有恭仕途上突飞猛进的一年,一年之内连升四级,几乎与沈德潜同等待遇。庄有恭假满还朝,即由翰林院修撰迁为右春坊右中允(正六品),又进翰林院侍讲(从五品),擢级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沈德潜是年亦连升四次,由翰林院编修(正七品)升为侍讲学士。如果说沈德潜是乾隆帝刻意扶植的诗坛代理人,历康雍乾三朝而早有诗名,为诗坛耆硕,如此荣升是为了更好地向士林宣传;庄有恭才年过而立,诗名仅在同年中崭露头角,也无甚政绩功劳,却“一岁之中,君恩叠稠”,可见乾隆帝对他的赏识非比寻常。乾隆九年,又擢级升为光禄寺卿(从三品),并赠其父为中议大夫(从三品衔)。是年八月初二日,庄父卒,庄有恭知信后便丁忧回家。然而,乾隆十一年,庄有恭还在守制居家,却特旨授为内阁学士(从二品),这在官场上是极为少见的。通常,丁忧以原官守制,服阙以原官补授,乾隆帝此举真可谓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而庄有恭则得非常之遇。服阙后,入都迁兵部右侍郎(正二品)。十三年,出任江苏学政。十五年又转为户部右侍郎,召还供职,又充是年江南乡试正考官,试后再次留任江苏学政。十六年,并授江苏巡抚,十七年暂署两江总督,成为主理一方的封疆大吏。在任六年,于乾隆二十一年丁母忧请归,乾隆帝只准百日之假回籍治丧,又署以江南河道总督,夺情令治河道。
不过,庄有恭临行时犯了一个错误,将巡抚任内一些自作主张的行为疏闻帝听,却被问责,从此仕途常处沉浮之中,几次被夺官论罪,甚至还被论死刑,因乾隆帝网开一面而劫后余生。疏奏后,被夺官并令归丧后赴军台效力。然而,在赶往谪所途中他又被任命为湖北巡抚,一年之后,再调江苏巡抚,还没赴任,乾隆二十四年又调为浙江巡抚。二十七年,仍调任江苏巡抚,加太子少保(正二品),兼管浙江海塘事。二十九年,擢刑部尚书(从一品),留办巡抚事。三十年,命为协办大学士(从一品),八月,诏还京师,年冬入京,却又再次卷入案件当中。三十一年正月被罢协办大学士,逮系半年余,又被夺官论斩,乾隆帝谕令改为斩监候。八月,官复原职,授为福建巡抚。乾隆三十二年七月二日卒于任。
在庄有恭55岁的寿命中,乾隆四年是他的转运年——他27岁,也是他人生的中分点、他命运的分水岭,此后的28年,他生活在宦海浮沉之中。在乾隆十八年(1753)前,他一直是顺风顺水,乾隆十八年发生“丁文彬逆词案”后,被追查出乾隆十四年江苏学政任时丁文彬曾向他献书《文武记》《太公望传》,但他以为丁文彬是疯子,没有搭理,也没及时上报,此时案发,他才意识到当时犯了渎职罪,便主动请罪,被罚学政养廉银十倍。“养廉银”自雍正初年实行后,根据各地的财政收入不同而数额不一,不过一般学政、巡抚的养廉银为10000~15000两银子。自此,这笔罚款犹如悬在庄有恭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背负到老死才作罢。如今虽难以确知庄有恭到底还了多少银子,但乾隆帝视其办差情况不时地拿出这茬来让庄有恭喝一壶。乾隆二十七年曾免掉了这笔罚款,但乾隆三十一年被论罪时又被追缴,三十二年卒后彻底免掉罚款。
如果说,钱财乃身外之物,罚款是种物质惩罚和精神折磨外,庄有恭还曾两历生死。这两次的箭雨都来自同僚,也与他的性格和办事行为有关,而救他的却是乾隆帝。第一次是归葬母亲临行时主动向乾隆帝汇报的一件案子:他在巡抚期间,泰兴县有个叫朱聃的人犯了主使杀人罪,依律当处以绞刑,但朱聃愿意用钱赎罪,庄有恭同意了。这或许在他看来是“小事”,但却犯了“专擅”之忌,死刑都要上报刑部,由部议决定惩处,地方官即便是巡抚、总督也无权决定死刑的处置方案。于是乾隆帝下令查问,并责问两江总督尹继善是否知情,尹继善在遮遮掩掩中又爆出庄有恭巡抚任内有人科场贿谋联号及斗蟋蟀致讼二事,庄有恭都擅批罚款赎罪,没有上报,只告诉过他的恩师尹继善。乾隆帝大怒,令撤职逮京查办,大学士、九卿议罪当绞(死刑)。然而,乾隆帝却突然袒护庄有恭,认为庄有恭的出发点是好的,只是处理方式有问题,况且赎罪款项并没收归他个人,而是充库用,所以免了庄有恭的死罪,令其母葬后赴军台效力,但在去军台途中又命署湖北巡抚。乾隆帝甚至为了给庄有恭脱罪,还找了个替罪羊,认为作为两江总督的尹继善“是纵庄有恭之情罪而酿成其事,始终皆由于尹继善也”,令将尹继善交部严加议处,九卿议处革职后,却又谕令宽免尹继善之罪。另一次是他在离任江苏巡抚时弹劾苏州同知段成功纵容仆役扰民一案,后经查,他又卷了其中,先免协办大学士职,后又被夺官,还追缴罚款,九卿会审后再次被判斩(死刑),乾隆帝又谕令改为斩监候(死缓),半年后复原官,出任福建巡抚。从这两次生死边缘中,可见庄有恭都是在离任前自曝曾经的擅权和渎职事(用如今网络语来说,有点“作”),但可能他的本意是想向乾隆帝坦诚布公,或邀赚声誉,或摆脱干系;但多疑而精明的乾隆帝却怕臣下不忠诚、结党营私之类,便令严查,一查,庄有恭都难脱干系;而大学士、九卿或有不满者,或过度揣测圣意,下手极狠,两次都把他往死里整;于是乾隆帝又不得不站出来袒护庄有恭,为其开罪,并过一段时间又令复原职。
乾隆帝又为何如此袒护或宠眷庄有恭呢?一则可能是惜才。庄有恭的才华和品格早为时人和史家肯定,乾隆帝也是极为欣赏的。首先是诗文方面,从他的殿试策论和散馆诗,吐语惊人而抱负非凡;甚至连当时傲视群伦的袁枚与庄有恭也倾心交好,回忆他们京城时光时说,“苦忆长安日,群游翰墨场……少年文战锐,倾国饮狂泉。争胜拿相搏,诙谐体类倡”。其次是书法好,其书法专摹颜真卿、米芾,后又学魏、晋法帖,行书出入颜真卿、赵孟頫间,“片楮只字,人争弆以为荣”。当时不仅科场极为讲究楷书书法,入直南书房侍奉宸章的更是名书法家。再次是书画品鉴能力强,曾预修《西清古鉴》。除了文学艺术上的才华,实干能力也非常突出,尤其是在治理江河和海塘方面颇有经验和能力。当时,令乾隆帝经常宵旰之事就是旱涝两灾,尤其是江(长江)、河(黄河)、海(钱塘江海潮)的水患问题,庄有恭可算是继方观承、高斌之后又一治水名臣,因而他长期任江、浙两省巡抚,甚至在调任江苏巡抚后仍兼管浙江海塘事。此外,在行为品格上,经术纯粹,做事主动,为民生干实事而没有贪心,连赎款都分毫不取,充库以用。是以乾隆帝曾一再赠诗以夸赞:“从来庠序储才地,观国之光利用宾。所贵清真兼雅正,莫容牛鬼及蛇神。春华秋实崇经术,廷献家修重大伦。自是此邦文胜质,丁宁致勗务还淳。”(《御制诗二集》卷23)“己未亲为策士文,精抡蕊榜得超羣。起行不负坐言学,率属偏能先已勤。鹤市旧声犹眷眷,龙山新政更殷殷。海塘正是投艰处,盘石维安勉奏勗。”(《御制诗三集》卷21)。由此可见,乾隆帝自期为尧舜,故也期望庄有恭成为“致君尧舜上”的肱股之臣。
再则是乾隆帝的御人术。乾隆帝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帝王,即位之初就表现出了出色的政治能力。然而,由于其父临终遗旨派给了他四位辅政大臣,尤其是鄂尔泰、张廷玉逐渐羽翼丰满,几乎形成了满、汉两派势力。乾隆帝最反感的就是结党营私,逐渐通过他的强势威严及手段将权力收回到他一人之手。他起初看上庄有恭,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朝堂上并无广东人,庄有恭在朝堂上几乎没有靠山或援引之人,而且状元是他钦点的,庄有恭感激的是皇恩浩荡。他在一面清除鄂尔泰、张廷玉党派旧臣时,一面又极为注意培植效忠于自己的新臣,庄有恭就是其中之一,他几年之内连续擢升庄有恭,让他从一个翰林院修撰而升为内阁学士,并开始外放以锻炼其能力。钱大昕在庄有恭的墓志铭中就曾道破关键:“以文学等巍科,不及十年而跻九列、贰六卿,皆圣明亲擢,不由荐援。”庄有恭也自知皇恩优渥,“臣昔蒙特拔巍科,已属忝窃,兹再荷恩,命得侍联句,尤为荣幸”,要尽心报效皇恩。乾隆帝在大权一人在握时,他又发明了一套恩威并施的御臣术,让臣下感恩戴德的同时又诚惶诚恐地尽心宣力。是以在庄有恭身上的罚银、罪与赦,犹如两股缰绳,让庄有恭长期活在战战兢兢当中,有时不免想到“推命”来一窥自己的命运。
然而,正如袁枚指出的“赏善罚恶者,君也”,又岂止赏罚而已?当时的生杀予夺都操柄在乾隆帝手中。庄有恭作为乾隆帝一手扶植起来的重臣典型都尚且如此,又何况其他人呢?不过,总体来看,在宦海浮沉中庄有恭绝对是得“遇”的幸运儿,虽有波折凶险,最后寝疾而终,也算是善始善终,这比当时多少卿贰的结局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