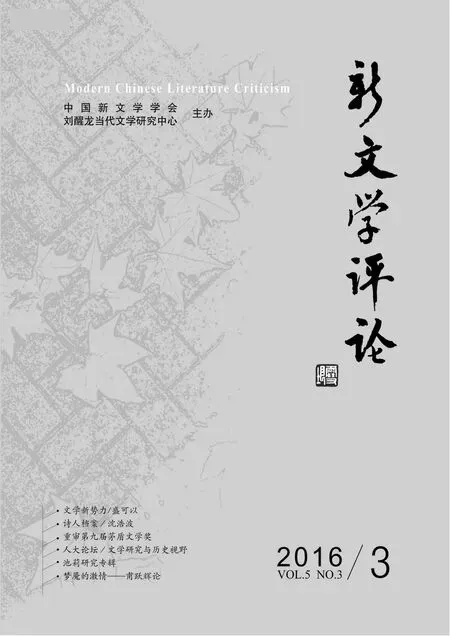怎样的“野蛮”与怎样的“生长”
——评盛可以的新作《野蛮生长》
◆ 刘文祥
怎样的“野蛮”与怎样的“生长”
——评盛可以的新作《野蛮生长》
◆ 刘文祥
一
盛可以是“70后”作家中的翘楚,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寄居深圳,并经历了城市的繁华和人情的落寞,这些都成为她本世纪早期创作的经验。她的作品如《鱼刺》、《青桔子》、《水乳》、《北妹》、《火宅》、《道德颂》等主要表现都市中男女无爱的尴尬和虚伪的人情面纱,诉说底层的艰辛疼痛和欲望悖论。最近几年盛可以也在尝试新的创作可能,尤其是对现实的干预批判日益强烈,如2012年盛可以创作了短篇小说《1937年的留声机》,这是盛可以小说中第一次出现了明确的现代时间;2013年她创作了长篇小说《死亡赋格》,这部兼具虚幻色彩的小说超越早期单一的情感、身体、道德主题,开始迈向这些之外的政治秩序反思等;2015年盛可以又出版了新作《野蛮生长》,传统作品中情感与虚无的底色消退,个体疼痛与社会进程衔接起来,现实与历史真正从隐匿的幕后走上前台,她的转型迹象开始明朗起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野蛮生长》中的一些故事和人物也能在盛可以先前的《致命隐情》、《乡村秀才》中找到故事原型,所以这部作品又具有某种整合和总结性的意味。笔者认为这部作品在盛可以创作历程中应该具有重要的转型意义,一方面盛可以在忠实地记录历史与时代的“野蛮”,揭示了“野蛮”的“生长”过程,表达了属于作家的责任担当;同时盛可以书写“野蛮”,对作家本身来说也实现了新的“生长”。
二
《野蛮生长》是通过一个家族来进行关于“野蛮”故事的讲述的,小说的人物主要由四代谱系构成,这种完整的谱系化的人物群像建构在盛可以的小说中是第一次出现。爷爷李辛亥为第一代,他是个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型人物,整日赌博,并用他仅有的知识掩饰一个文化人的门面;父亲李甲戌和母亲谢银月为第二代,父亲身上的权威意识很重,在家里打骂儿女成为常事,母亲则更有传统女性的温顺色彩;第三代是作者着力建构的子辈群像,其中有姐姐李春天、姐夫刘芝麻、大哥李顺秋、嫂子肖水芹、二哥李夏至,还有叙事者“我”——李小寒,他们这一代有着各自不同的悲剧命运;第四代是姐姐李春天的两个女儿——刘一花和刘一草,很不幸的是这两个年轻人也是悲剧性的存在。中国明清有着悠久的家族小说渊源,家族小说是诉诸伦理建构和意识形态张目的重要手段,从现代文学开始,家族小说也一直是宏大叙事的产物,宏大叙事追求整体化的历史,对家族的解构和重构必然会延伸出政治寓意、现实批判和文化思考等内涵,作品中家族几代人物命运的是漫溢的、交融的、流动的,自然要与广阔的历史相融合,反过来几代人物命运的浮沉本身会形成纵深感,也是形成历史合法性或者悖论的有效证明,比如马孔多布恩迪亚家族的延续与循环本身就印证了拉美历史的前世今生。盛可以早期作品中往往局限于情感的一角、生活的一隅,创作既不追求复杂的人物关系,也不倾向于折射时代的风云变化,即使某些现实化意味很强的作品如《北妹》等也都只是在伦理层面诉诸自尊自爱、公正平等元素,缺乏文本层面的人物关系支撑。而在《野蛮生长》中盛可以构建的这李家四代,且不论其效果如何,从架构上已经折射出盛可以试图把握某种宏大性主题,构建某种开阔性文本场域的冲动,显然对以前的文本有了一定的超越性。
从《野蛮生长》的题目上看,似乎有两个解释,一为某物“野蛮的生长”,主语所指是空缺的;二为“野蛮”本身的“生长”,无论哪种解释,在本书中似乎都离不开“野蛮”一词,盛可以以这个家族为支撑透视了乡村、城市和知识分子所遭遇的“野蛮”。
首先,在乡村生活中遭遇“野蛮”。以往作品中盛可以对乡村生活的揭示也有一些,如《致命隐情》、《上坟》、《乡村秀才》等等,这些作品中乡村其实更多的是背景性的存在,其侧重点还是在于揭示人性的隐秘、生存的荒谬等问题。《野蛮生长》中的乡村生活从我爷爷开始,他是典型的纨绔子弟,不务正业,吃喝嫖赌——当然这些都不是盛可以的批判焦点,她关注的是男性秩序对女性的野蛮伤害,在整个家族中女性是秩序的受害者,无论是爷爷李辛亥还是父亲李甲戌,对女性都是充满歧视色彩,甚至连下一辈的刘芝麻也有总是喜欢打老婆等野蛮行为,而无论母亲谢银月还是姐姐李春天,更多的只能选择温顺投降的方式来逃避惩罚,这种女性启蒙主题在盛可以以前的作品中早已出现,这次通过群像化的方式表达了更为集中的批判。另外一个方面是对父亲李甲戌在家族中实施的野蛮统治进行批判,在父亲的阴影下,所有的子女都没有自己的空间和自由,姐姐被迫早早嫁人,二哥则骂父亲是个暴君,甚至爷爷也被边缘化。但无论父亲与爷爷、二哥、姐姐等关系怎么紧张,血浓于水的感情是随处可见的,乡村与整个时代并没有那么强的紧张关系,生活中虽然也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但是整体上作者是持赞许态度的,虽然贫穷但是不低微,虽然繁忙,但是精神是富足的。在这其中盛可以集中地揭示了乡村生活的日常性元素,比如姐姐的嫁娶、父亲的种菜生活、大哥捉田鸡的夜景等,一些甚至不乏诗意:“黄昏时他们在苦枣树下朗诵诗歌,风吹过时,细如米粒的紫色枣花纷纷飘落,有的跳入茶杯,有的藏入发丛。”①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乡村开始遭遇“野蛮”,随着“严打”等运动的介入,乡村生活的封闭性被打破,年轻人因为捕鱼和游玩被扣上各种犯罪帽子,有的被枪决,有的锒铛入狱,而乡村在严厉的政治环境中只能屈辱地服从。乡村的“野蛮”还表现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姐姐李春天为了生育男孩选择超生,因为交不起罚款而被计划生育组的“八仙”进行大月份引产,孩子没了,姐姐几乎失去了半条命,作品笔下的乡村也从诗性转入颓败:“秋天带着哀悼的表情出现。天空像块灰布,一只黑鸟‘吱’的一声,像支利箭穿透布帛,裂缝瞬间弥合。田野是张百岁老人的脸。池塘和水沟结着薄冰,干黄的菜叶耷拉在裸土上,涂着秋霜。”②
当然对盛可以来说,她在作品中描述的乡村生活也并不是非常丰富,很多描写都是片段化的,呈现着回忆与批判的矛盾心态。作者的重点似乎并不是营造乡村氛围,也不注重乡村品格和乡土精神的营建。作者对乡村生活和伦理关系不是探究式地叙写,而是更注意利用乡村生活形成他们的底层身份,来着重表现他们遭遇“野蛮”的困厄,只是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对乡村生活的眷恋。其实这种描写方式也不是仅在盛可以这里存在的,很多“70后”作家的乡土叙事都是存在着某种缺憾的:“也许是因为缺乏深刻而丰富的乡村经验,‘70后’乡土作家似乎普遍没有形成独立而稳定的文化思想,没有将这种思想贯注到他们的乡土小说创作中。大多数作家的创作还停留在对他们往日乡村记忆的书写基础上,缺乏对个人生活和感情的升华。”③
其次,在都市生活中遭遇“野蛮”。在大哥入狱、二哥死亡、大姐被迫堕胎之后,所有人都被时代驱赶着进入城市,乡村在小说中占的地位已经不再重要,父亲和爷爷的叙事已经退居幕后,乡村逐渐被遗忘,这里也隐含着城市文明对乡村生活的冲击。但是所有人进城的故事都是一部遭遇“野蛮”的血泪史,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他们只能出卖劳动力,人身和财产权益得不到保障,也无法换回应有的补偿,等待他们的都是悲剧:肖水芹辛辛苦苦工作,希望能够为孩子攒下出国的资金,只是因为一次偶然出轨而染上疾病,最终只能选择出卖身体,走向灭亡;姐夫刘芝麻到工地上打工,却发现连自己的辛苦钱都难以讨回,只能诉诸暴力,以“野蛮”抗拒“野蛮”,最终遭遇更严酷的命运悲剧;姐姐和刘一花也只能从事底层工作。这些人在城市中失却了人格,没有尊严可言,城市无法接纳他们,他们成为秩序的异己者。最具典型性的应该是六子这个人物,他跟刘一花进入了南方大都市,却被无端地拉入“收容所”——这个貌似人道实则如同监狱的场所,这里他遭遇各种野蛮的毒打谩骂,人权没有保障,甚至死去都无人问津。
这些进城者所遭遇的“野蛮”不仅仅是现实和制度层面的,还有人性层面的,其中欲望便是很重要的主题。姐姐在进城之后遇到了退休干部孙湘西,孙不断地用香港旅游激发姐姐的城市想象和出游欲望,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刘一花在营救六子的时候遭遇了“特种兵”的无理要求;甚至连叙事者“我”——李小寒也被欲望充斥着,在职业生涯中放浪形骸。书写欲望其实在盛可以的早期作品中非常常见,但在《野蛮生长》中固然还带有着先前女性自我经验书写的某些痕迹,但是这种书写并不是沉迷,而是已经深入时代的深处,揭示在浮躁年代里个人欲望的泛滥,欲望也是形成“野蛮”的重要驱动力,作者在此寄寓了强烈的欲望批判主题。
最后,知识分子遭遇“野蛮”。新世纪以来的女作家们关注的焦点除了底层、日常生活和个人化历史外,在知识分子主题上也有所涉及,比如计文君、徐坤、张懿翎、戴来等人的作品中也都有一定的关注,但是很多作品是在表达对知识分子启示真理与改造社会能力的怀疑和嘲讽,知识分子整体是虚弱的。在盛可以早期小说中知识分子更为特殊,往往都是欲望化的投影,只具有身份和符号意义,直到《死亡赋格》才有了一定的改观。在《野蛮生长》中盛可以第一次比较正面地书写了知识分子形象,主要是哥哥李夏至周边的一群青年人,以“学潮事件”前后为分界,事件爆发之前他们是一群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有着自己的追求,在树下朗诵诗歌,弹奏音乐,但是一切转瞬间天翻地覆,当年充满理想的哥哥已经化作骨灰,这是知识分子遭遇的最早的“野蛮”。等到多年后李小寒求学又重新认识了他们,但他们已经走向了分化,多年后的唐林鹿“已经不会再弹吉他,变成一个手法娴熟的情场老手”④,其实这只是他的表面姿态,“野蛮”带给他们的创伤远未散去,我们能够看出他们潜藏在心底的创伤,“唐林鹿是晦暗天空盘旋的鸟,在自己的航线上慵懒地飞,此时也只是拧着眉头吐烟圈,深不见底”⑤。另一类主要是以《今报》主编喻书中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他以报刊为阵地继续针砭时弊,反抗现实“野蛮”并葆有理想,他的自由意识和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李小寒,但最终在收容制度等一系列的尖锐报道中遭到“野蛮”打压。虽然在对这些人物及生活的刻画中无论是力道和深度还有所欠缺,但是却隐约地还原了新启蒙时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及分化问题,90年代以来很多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大潮中走向了世俗化,在世俗性中忘却历史;有的则是被迫进入冬眠状态,沉溺于往事而一蹶不振,但是精神和思想的反思却由此开始;有的则继续坚守启蒙立场,继续反抗各种不断出现和生长的“野蛮”,为底层呐喊。盛可以描述了当代知识分子边缘化的痛苦历程,更对那些反抗“野蛮”、履行自己的职责的知识分子投去了赞许的目光。但是我们也能够清晰地发现整部作品中知识分子的视角还比较单薄,更显现出一种速写式的概括和叙事者的一厢情愿的崇拜。在他们匆忙的背影中我们看不到心灵的困惑,也就难以形成心灵上的共鸣,所以这就导致了盛可以的这种还原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在客观中还缺乏一种深刻和深沉性。
三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盛可以在着重刻画“野蛮”,对于“野蛮”为何物,我们很难有所指,“野蛮”并不是一种具体存在物,但是又无处不在。“野蛮”更像是历史与现实纠缠所产生的一种暴虐的力量,它侵蚀人的生存,毁灭人的自由和价值,破坏所有平和与安宁,并呈现不断延伸的趋势。“野蛮”覆盖了一切,在乡村、城市和知识分子中间飘荡,所有人都会遭遇这个问题,所有人都难以摆脱其所带来的苦难,“野蛮”不仅仅是无所不在的魅影,还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首先,“野蛮”消灭一切希望。父亲的一生是暴躁和操劳的一生,他寄希望于两个儿子,但是儿子们先后让他失望,大哥李顺秋无端锒铛入狱,二哥遭遇政治事件;嫂子肖水芹一生的愿望便是让女儿李线线出国读书,为她拼命攒钱,却发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全家人都看好的刘一草,却意外被辱而跳楼自杀……可以说在“野蛮”的时代面前,所有人的希望都被打破,被笼罩在希望与不断的失望之间徘徊。这种家族式的悲剧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余华的《活着》,人物一个个离去,亲情关系一步步被解构,活着变成了一种在场的痛苦折磨。但是余华的《活着》更多的是从历史深处探讨死亡悲剧问题,盛可以在这里更多的是考虑现实与人的关系,探讨政治对民间的压榨,更具有当下色彩。
其次,“野蛮”衍生了宿命式的痛苦。我们可以发现《野蛮生长》中“野蛮”衍生的痛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每个人的痛苦总是一环接一环,如姐姐为了逃避父亲选择嫁给刘芝麻,但是却要遭遇刘芝麻的暴力,为了生男孩而被计划生育工作组强制堕胎,还欠了一屁股债,为了还债只能出卖劳动力,越是出卖劳动力越会遭遇更多的苦厄……人物越是试图去反抗“野蛮”,去抗拒苦难,反而越会陷入不可挽回的境地,生活给予他们的希望越来越少。同时“野蛮”带来的苦难还会在代际中传播,上代的悲剧会延伸到下代,爷爷的挥霍导致了父亲的贫苦;姐姐贫穷,连自己的孩子都保不住,并导致了刘一花的底层经历,这样痛苦便带有了某种宿命的意味。命运如同一张网,让所有的人在痛苦挣扎中走向灭亡。
最后,“野蛮”也成为历史的本质。盛可以在直面当下的时候还往历史深处回溯,将“野蛮”上升到历史的本质。《野蛮生长》开篇于我的爷爷李辛亥,他在辛亥革命的呐喊声中成长起来,却只知道赌博,甚至和自己的儿媳妇鬼混,导致父子反目成仇,给这个家族带来了某种不祥的征兆;《野蛮生长》又结篇于我的爷爷李辛亥,他在一百岁生日的时候终于撒手尘寰。爷爷李辛亥是传统文化的象征,他霸道蛮横又纨绔机敏,他知书达理又附庸风雅,他写的对联的被遗弃隐含着传统文化和乡村伦理生活无可挽回的哀歌。一百年的历史囊括了家族子孙的生生死死,整个家族覆盖着悲凉;同时一百年的家族史更是历史进程的隐喻:父权制度的死而不僵、传统文化的行将消亡、政治的波诡云谲、伦理价值的混乱颠倒、自由人权的被蔑视……一百年的历史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美好,不是走向自由,走向富裕,走向幸福,而是一代又一代的“野蛮”悲剧在重演,“野蛮”成为历史最本质的象征物。盛可以自己也表示:“残缺、悲观、幽暗、稍纵即逝的欢乐,痛苦中隐约的温情,这些是我表达的,童话般的美好,大团圆,对生活虚伪的赞歌,不是我的习惯。我试图做这样一个作者:看到本质,像上帝的眼睛,洞察一切。”⑥这里,苦难不仅仅是属于个体的,还是属于家族的,不仅仅是难以反抗的,还是先验宿命式的,这样的叙写对比以前的创作显然是有了深度的拓展。
四
盛可以不仅仅写出了“野蛮”的形态和后果,同时还从诸多的方面写出了“野蛮”是如何“生长”的,特别对“生长”中所表现出来的诸多时代症候给予了批判。
首先,“野蛮”体现出了遗传性的“生长”特征。从爷爷李辛亥开始,他身上就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暴戾、机诈、顽固等“野蛮”的元素,所谓他将自己的母亲所克死便预示着这种文化痼疾的顽劣性。他受传统男权思想的深刻影响,歧视女性,要求家庭中所有的成员都服从自己的权威;同时他的“野蛮”还在于他又不遵守寻常的伦理规则,他僭越伦理,和自己的儿媳妇鬼混在一起。他将这种家族基因又遗传给了儿子李甲戌,李甲戌将这种家族的“野蛮”发挥到了极致,他既打老婆,又歧视女儿,无理干涉女儿的婚姻,即使女儿当牛做马也没有任何的同情,以至于女儿诅咒他病死、淹死、被水牛顶死。他对儿子们也是颐指气使,只要稍微不合心意,便破口大骂。女儿出嫁之后,“野蛮”继续在女婿家里“生长”,女婿刘芝麻将李春天身上打得遍体鳞伤并洋洋自得,李春天在刘家只是充当了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获得不了任何的承认,从这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源自传统文化中的“野蛮”的父权和夫权成为笼罩家族的阴影,并一代代地遗传着,“生长”着。
其次,“野蛮”也在实现扩散性的“生长”。在最初的时候“野蛮”仅仅在家族中“生长”,“野蛮”也仅仅限于爷爷和父亲那里的打骂、歧视、冲突等,几十年的发展中都没有越过这条底线。但是历史进入1980年代之后我们能够发现,“野蛮”开始明显地扩散“生长”起来,开始溢出家族之外。从“严打”斗争开始无数个乡村家族遭遇了非正常的屠戮和冤屈,“野蛮”如同狂风一样摧枯拉朽地冲过乡村:姐姐李春天遭遇了计划生育的“野蛮”;大哥李顺秋被屈辱地劳教,在庸医的误诊下几乎残废;二哥李夏至八十年代末后再也无法返归自己的故乡。“野蛮”此后继续从乡村向城市“生长”,它让乡村逐渐在城市的背影中落伍,它让六子在收容所里死亡,让刘芝麻在暴力抗恶中灭亡,让肖水芹在无意义的奋斗中失去希望,让姐姐在受骗中失落,让刘一花和刘一草如同花草一样过早地凋谢……“野蛮”从家族到乡村再到城市,疯狂地“生长”着,“野蛮”扩散中不断地出现各种的“生长”变体——从身体的、语言的、浅层的个体“野蛮”生长为极端的、隐形的、深层的群体“野蛮”。
最后,“野蛮”在“生长”中还呈现出传染性的特征。故事中所有的人物一方面在遭遇“野蛮”,另一方面也会被传染上“野蛮”,反过来助推“野蛮”的繁殖。如刘芝麻虽然存在着某种的顽劣,但是本质上还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随着李春天进了城市,只能靠在工地上出卖劳动力获得生存,但是当他遇到压榨工人血汗钱的“野蛮”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没有任何可以反抗的手段,只能选择同样的“野蛮”方式来进行抗争,一个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很快被“野蛮”所传染;刘一花在乡村的时候还是个纯真的孩子,但是进入城市之后她逐渐地适应了“城市”的规则,她利用六子的暴力砸了照相馆,也染上了“野蛮”的气质,她发现只有“野蛮”才能够混得风生水起;肖水芹最初在城中辛辛苦苦地挣钱,但是时代却不断地消磨她的希望,最终她发现所有正当的盈利手段都是行不通的,只能通过流行的做暗娼的“野蛮”方式维持自己的生计。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每个人都容易被“野蛮”所熏陶,每个人都会感染上“野蛮”,催动“野蛮”疯狂地“生长”。
“野蛮”会如此疯狂“生长”,是很多原因造成的,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缺少相应的克制力量,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野蛮”裹挟着历史与政治的强力,反抗者本身的力量是难以抗拒的。还是在乡村“生长”的时候,父亲李甲戌的权威就能够俯视一切,家族成员中只能选择规避的方式来对抗,比如母亲的顺从,大姐的出嫁,二哥的偶尔咒骂等,这些都不能消解父亲的“野蛮”;在“严打”中,尽管无数的家庭走向灭亡,但是乡村始终没有发出声音来抗拒“野蛮”的入侵;二哥李夏至只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他们对时代的呼喊遭遇了国家机器的“野蛮”倾轧,毫无反抗的可能。
第二,相比于家族中那种对立的父子“野蛮”,城市中的“野蛮”更加狡诈和隐晦,它总是打着人道和自由的幌子来施虐,仿佛是一只戴着天鹅绒手套的“铁手”。六子从进入收容所开始就被人道的光环覆盖,那里表面上是遣返“三无”人员的处所,其实是毫无人性的野蛮监狱;姐姐李春天遇到了退休干部孙湘西,而孙湘西为了勾引李春天则不断使用花言巧语,这种狡诈的“野蛮”自然让人防不胜防;喻书中在长期的揭露“野蛮”、反抗“野蛮”的过程中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当权者的“野蛮”是他所无法抗拒的——“野蛮”并不直接惩罚他,而是寻找“欲加之罪”的证据让他身陷囹圄。
第三,“野蛮”的疯狂“生长”还和人们对“野蛮”的漠视与忘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长时间的“斗争”、“革命”文化熏陶中,人们已经将暴力的“野蛮”视为常态性的存在,汉娜·阿伦特不断地警告我们:“人们对暴力以及它任意的本性的理解是多么肤浅,对这个问题已经忽视到了何种程度:没人对显而易见的事情提出疑问或进行检测。所有从过去的记载中寻求某种启示的人,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暴力看作是边缘现象。”⑦从乡村枪决中那围观的人群,到城管对刘芝麻的肆意驱逐,再到讨薪农民的喑哑无助,“野蛮”已经深入每个人的意识中,每个人都在亲历着“野蛮”的“生长”,但是每个人却都熟视无睹。就连唐林鹿等亲历了“野蛮”的知识分子,都被迫选择沉迷于自己的私人生活,不愿意选择继续面对“野蛮”,抵抗它的“生长”。
五
从《野蛮生长》中我们能够看到盛可以摆脱了早先创作中的许多弊端,呈现出了一种复杂性和多元性,也为“70后”作家尤其是女作家们更好地走入现实提供一种尝试。这部作品的价值既在于忠实地记录历史与时代的“野蛮”与“生长”,同时对作家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生长”。盛可以通过作品获得的“生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关注领域的拓展。“七零后作家们大多贴着生活写,他们的作品带有浓烈的烟火气息与世俗味道。在那里几乎看不到历史的显著足迹,他们基本上不会费劲去虚构一个历史,拿起笔来直接就写与自己相关的成长和现实成为他们的写作特点。”⑧盛可以的早期作品有着浓厚的女性主体意识,对男性的疏离和抗拒,是创作中比较耀眼的主题,除了《北妹》等作品中现实批判色彩强一些外,其他作品总体上是比较弱的,从《墙》中对城市拆迁的质疑,到《惜红衣》中为了父亲就业而委身于两个男性之间,再到《白草地》中对都市紧张繁忙的生活节奏的反思,这些都没有形成比较鲜明的风格,在对现实的干预上始终没有系统深入。显然在《野蛮生长》中我们看到了盛可以“费劲”的“虚构历史”,它的主题范围、表现方式、书写深度等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超越,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转型和生长意义。而且在当下作家面对宏大叙事和敏感问题表现的疑虑重重的时候,盛可以能够有直面极致的勇气,让我们看到属于她自己的独特反思及对时代的整体思考,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很多的当下作家所缺乏的。盛可以在忠实地记录历史与时代,同时时代也在回馈她,不断催发着她艺术想象力的“生长”。
其次是成熟的反讽笔法。大部分的底层写作都是以沉重的笔调开篇,以此凸显作家的道德姿态,但是盛可以似乎是个另类,她对“野蛮”的批判或者对“野蛮”的“生长”的揭示充满了戏谑化的反讽描写,“辛亥革命第一枪打响,女祖先在血泊中拼掉了命,彼时年方十八。——我的女祖先并非革命牺牲,她死于难产,是我爷爷把她折腾死的”⑨。爷爷在辛亥革命的斗争中成长起来,但是却仍然沿袭着传统纨绔子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俗,他的出生便是对民元历史的最大嘲讽。同时,这种反讽还借助了一种外视角的立场,叙事者在不同的事件和场景中迁移游走,不对一个话题捕捉深入追究,不与主人公同命运共呼吸,不深入心灵探究,尽可能多地囊括历史与现实。我们看到她的每一个章节都非常的短,很多场景往往几笔带过,刻意追求简练中的深刻,并不刻意营造沉重和反思的风格与氛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盛可以的描写是倒退的,笔者反而认为这是一种超越,也即她已经摆脱了依靠控诉赚取眼泪的道德误区,而是有一种超越的批判精神,现实的“野蛮”在眼前能够保持不动声色,更具有匠气感。盛可以宣称要“让语言站立起来”,这里她不仅实现了语言的“站立”,更实现了语言的跳跃。
那么为什么盛可以会出现这样的“生长”,为什么会选择实现这样的转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这是90年代以来文坛创作的多元混杂状况所决定的。从80年代开始我们文学创作就不断地在各种创作潮流和主题中游走,虽然说这些努力有效地恢复了文学本体性,但是对于文学与启蒙、政治、传统、社会等话题都没有深入探究,没有形成有效的沉淀,尤其是对现实的关注力度不是非常大。经过90年代的淘洗,文学场日益变得众声喧哗,统一的元话语基础不再存在,文学空间被重新小众化和蜂窝化,这些给了作家再书写现实的冲动,才会出现现实主义冲击波等潮流。盛可以虽然并有赶上这样的潮流,但是多元混杂的文学场域很容易让她受到感染,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盛可以既有一些先锋性的痕迹,也有现实主义的倾向,还不乏一些女性主义的理念,文坛的复杂凝结到这个起步比较晚的作家身上,盛可以也会不断在这些话语和主题间实验探究,寻找自己的着眼点,所以导致《野蛮生长》更像是一个中心,辐射了女性、政治、历史、人性、现实等诸多的命题。
其次盛可以这种自觉的现实关注,也在和新世纪以来文坛的现实化的潮流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新世纪以来底层群体现实性的生存焦虑问题越来越突出,但是文学表现的力度却一直都非常弱,终于在2005年前后出现了关怀现实的潮流,理论界也在积极地相应,出现了“新人民性”、“新左翼”、“重返现实主义”等理论与口号,很大程度上复活了作家失去已久的现实干预精神,很多作家以新的姿态直面现实;最近几年“非虚构写作”也被提出,很多作家积极地融入现实,比如乔叶和梁鸿等作家的作品都折射了当下现实的诸多问题。在这样的潮流中,盛可以最初只是误入,才创作了《北妹》,但是没有系统地有意识地去参与现实书写、关注现实,对“野蛮”进行系统化拆解应该是她一直以来的心结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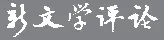
注释:
①盛可以:《野蛮生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页。
②盛可以:《野蛮生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
③贺仲明:《怀旧·成长·发展——关于“70后”作家的乡土小说》,《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④盛可以:《野蛮生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25页。
⑤盛可以:《野蛮生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页。
⑥盛可以、黄伟林、刘铁群、詹丽:《盛可以小说创作对谈录》,《河池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⑦汉娜·阿伦特著,郑辟端译:《共和的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
⑧李运静:《盛可以论》,山东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页。
⑨盛可以:《野蛮生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