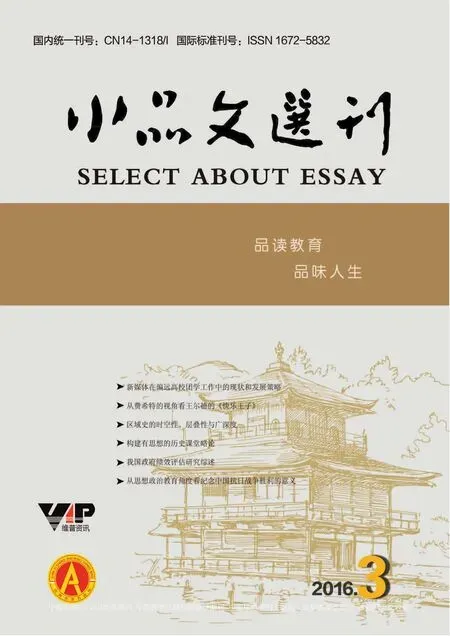生命之轻之悄然承受
——余华《活着》解读
陈佳佳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生命之轻之悄然承受
——余华《活着》解读
陈佳佳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 昆明 650500)
余华一直以先锋立场来描写人在现代社会下的生存状态以及境遇,带有暴力残杀的显在特征,探索人类生存在的某种真实;而90年代的《活着》则以一种现实主义的立场回归,把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时代背景之下,按照传统叙事模式进行描写,以一种冷静克制的笔调展现了特定时期中国底层人民的悲剧性命运、生存困境以及面对人生不可测的偶然性悲剧时的超然态度。余华不再是冷酷绝然的态度,而是怀着悲悯的情怀,平淡而深沉的叙述着一个时代几辈人历经的生存磨难,带着一种深切的人道关怀,在死亡的黑暗与阴影之下,为我们寻找一点生命的光亮。
不管是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还是转变之后的余华,“死亡”一直是他钟爱的母题。余华的每篇小说涉及死亡,而《活着》更是将死亡书写到极致。虽名为“活着”,小说却直接描述了十多人的死亡,其不仅仅是一种生命消逝的表象,非正常的死亡更是人在面对生存困境时的极致体验,使我们不得不去反思生活在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以及生存处境。小说以福贵因赌博而从纨绔地主少爷转变为一个贫苦雇农为开端,从大院老宅搬到破旧茅屋,他一生的悲苦命运拉开了序幕,死亡也如噩梦般如影随形。福贵父亲搬到茅屋第一天就离他而去;因给生病的母亲抓药而被抓去当壮丁,战场上挣扎于生死边缘,目睹无数人横尸疆场;逃离战场回到家乡以后却发现母亲在自己离家两个月后就病重趋势了,女儿也因发烧无钱医治而又聋又哑了;儿子有庆因献血救县长夫人而抽血过度而亡;女儿凤霞终于遇上了好夫家却因难产而死,刚刚有一点喜气的家庭氛围一下子烟消云散,再次笼罩上浓重的阴影;妻子家珍无法承受儿女皆逝的打击,病情加重抑郁而亡;女婿二喜勤劳善良,却因一场建筑工地事故而死于非命;而福贵唯一的寄托苦根也因贫穷而未能摆脱死神的青睐。十余万字的小说却写出了十多人的死亡,“死亡”就像一个魔咒,生活在这个特殊时代的福贵无法挣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人们一个个地相继而去,留下饱经风霜的自己和同样宿命的老牛相依为命,在僻远的乡下田间,淡然洒脱地细数着经年岁月的苦难。
《活着》与先锋时期的作品不同,余华恢复了传统写作模式,把悲剧人物福贵放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刻画,作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福贵只能为自己的细微生活而劳碌奔走,完全不能把握不可测的命运,其情感状态也呈现为一种特殊的状态。
小说以一种冷静克制的笔调展现了特定时期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表面看来福贵的爱恨悲喜似乎平淡如水,而内心则经历了岁月与时代的打磨,是压缩的情感、褪色的情感。生活的艰辛磨难、岁月的冲刷洗礼让饱经忧患的心灵如同水里的砾石,打磨得平滑柔润了,强烈的情感洪流渐渐转化为一种知天命。知天命,对人生的种种劫难与苦痛也能化重为轻、化浓为淡、化悲为喜,以一种平静淡然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福贵妻子家珍死亡的描述让人悲痛难言,家珍的手臂“一截一截的凉下去”,“胸口的热气像从我的指缝里一点一点漏了出来”,写得细腻清淡,而在异常平静的文字中我们却感到深深的不舍与无比的沉重,让人不禁感叹其命运的凄苦与悲惨。“我看见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即使这里的情感经过了淡化处理,但失去至亲的浓重哀伤早已渗透在人物的血液里,人生的苦难都沉潜在了不动声色的平淡之中。这里的平静是自觉的,也是无奈的。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个人的悲剧命运早已被时代挤压抛弃,再深重的苦难也在社会的淡漠之中消退了,这是无奈的选择;然而在动荡的社会与时局面前,个人适应生存却也需保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正因为秉承着中华民族传统中隐忍的精神血脉,福贵才能在历经如此深重的磨难还能安命乐天地活着。尽管生命渺小卑微,轻若鸿毛,但福贵依旧隐忍地活着,平静而乐观地活着。
这位历经沧桑而平淡如水的福贵,让人想起古希腊神话中受神诅咒的西西弗斯,一次次把巨石推向山顶,然而巨石一次次滚落下来,他日复一日、永无休止地与巨石抗争。西西弗斯明明认识到了生命的荒谬与无谓,却依旧与命运顽强地抗争着,超越肉体的痛苦,不断地推巨石上山,带有形而上的意味——与生命的无意义抗争。福贵经历着同样的无意义的悲剧性的命运,以一种顺应与平静的态度去对待命运,他的“活着”是一种乐天知命的超然态度,也是一种质朴的态度,他只要活着,自然地平静地承受着这生命之轻。
《活着》讲述的是福贵死亡和灾难的一生,父、母、子、女、妻、婿、孙七人的非正常死亡以及家庭之外的龙二、春生等人非正常死亡,很容易被理解为是一种单纯的对特殊时代苦难现实的反映。余华在序言中说到受美国民歌的启发而决定写这篇小说,为的是“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福贵所经受的苦难是超越了政治、民族、文化的局限,是一种恒在的苦难,无法逃避,与生俱来。如此,《活着》所表现的不只是苦难的宿命,而是人在这种宿命苦难面前的态度,即人性的态度。
余华有意将各种苦难加于福贵身上,破产、失去双亲、远离家乡、因贫苦将女儿送人、妻子因疾病身亡,儿子因医疗事故而亡、女儿难产而死、孙子因饥饿而离去,这一切的痛苦都沉重地负荷在福贵的身上,抽象的痛苦是可以忍受的,而最令人折磨的是这些痛苦都发生在最善良最美好最无辜的人身上,它将善良的美的东西生生地撕裂,真正达到了悲剧性的效果。而作者在讲述故事的时候,采用的是双重第一人称的视角,主体故事由福贵亲历讲述,外部故事由采风者“我”叙述,读者们既可以在福贵的叙述下感受其苦难悲剧人生,又可以从“我”的叙述中跳出福贵的故事,从现实中超脱出来,不仅看到苦难的社会人生,更看到了福贵的叙述态度、对待苦难的态度。《活着》不仅拥有对现实的穿透力,更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力量,它不局限与对社会人生与时代的理解和批判,更重要的是对人类命运的探索。苦难叙述不是余华的目的所在,承担苦难的能力与态度才是《活着》的正确表达。
《活着》里的福贵是余华塑造的一个受难者形象,与传统意义上的诸神为民众受难不一样,福贵是为自己受难,一个人的受难形象,受难是其成为其自身的本质,是成为其命运的的源始。现实主义的虚幻承诺的理想道德社会无法结束苦难,面对无可逃避逃避、不可抗拒的苦难之时,唯有来自个体的承担和忍受的力量以及意志才能消解,才能自我救赎。《活着》正是通过福贵的受难者形象来告诉人生存的意义,现代主义的人生姿势,以忍受的态度来包容一切,包容幸福和快乐,同样也包容苦难与悲痛,洗尽铅华回归平凡。
陈佳佳(1987-),女,汉族,湖北黄冈,硕士研究生,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I207
A
1672-5832(2016)03-00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