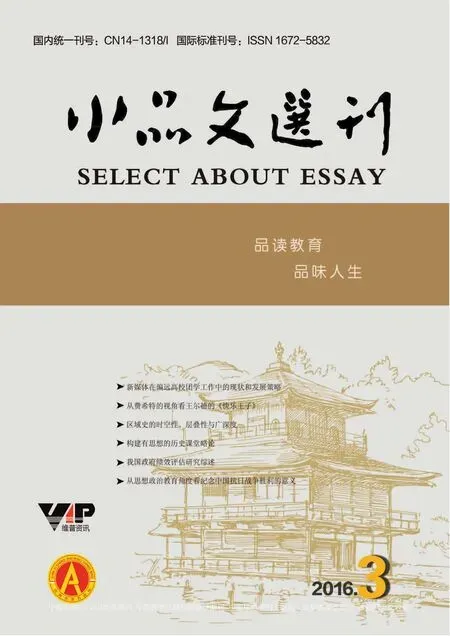中西文化视域下的易装“越界”
——基于中国电影《花木兰》与美国迪士尼电影《Mulan》的比较研究
赵 欣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中西文化视域下的易装“越界”
——基于中国电影《花木兰》与美国迪士尼电影《Mulan》的比较研究
赵 欣
(暨南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2)
易装作为木兰代父从军故事中富有传奇性的一部分,在《木兰辞》上所施笔墨并不多,仅以寥寥几句勾勒出了轮廓,这一留白给了后世作品极大的创作空间。本文选取中国电影《花木兰》与美国迪士尼电影《Mulan》,比较二者在木兰易装部分的不同演绎,并在中西文化视域下分析这一性别“越界”的处理,从而更好地把握中美影片在表现同一经典形象上的差异。
木兰;易装;“越界”;文化
木兰易装这一情节最早源于北朝民歌《木兰辞》:“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①然而由于诗歌体裁的限制,木兰女扮男装的适应过程以及如何在男性群体中成功隐瞒身份等细节并未得到呈现,这给予后世创作极大的填充空间。易装这一题材,在中西艺术作品中并不少见,“许多艺术家之所以使用易装的题材,是因为在中西文化中,服装不仅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而且包含着秩序、权力、性别、等级、符号等文化内涵。”②的确,服装作为人们性别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外在标志,易装不仅实现了日常外貌的改变,而且也打破了由外在皮囊规限下的多条界限,使人物在这其中获得了越界的可能。
1 《花木兰》:男性化向往下的易装
在中国导演马楚成拍摄的《花木兰》中,花木兰未出场,在她的父亲与邻居的交流中便透露了她好读兵书,深得兵法之要义,她回忆儿时的片段更表明她喜欢舞刀弄枪,遇事敢于出头还击的性格。因此,《花木兰》里的木兰在替父从军之前,爱好与性格已表现出了男性化的倾向,这为易装后的木兰在军营训练中如鱼得水的表现作了铺垫。对于木兰,易装是她得以进入军营的通行证,也给了她展示能力的平台,她的不凡身手在平息胡奎的事件中得到展示,由此获得了长官文泰赞许的目光。然而尽管木兰易装后在外貌和体能方面并未表现出不适,但木兰生理方面的限制却无法避免。影片为这一世俗化的发展,设置了身份暴露的情节:木兰在温泉洗浴池与文泰相遇,慌乱中文泰在木兰手背上留下了抓痕。紧接下来胡奎告事玉佩丢失推进了木兰暴露身份的进程,面临在大众面前脱衣搜身的要求,木兰担下罪名以解脱此境,而文泰当场认出抓痕,确定木兰女儿身份,并替其解围。在这两个片段里,影片完成了木兰易装中身份暴露的处理,她的真实身份并未在大众面前暴露,这确保了木兰继续以男儿身行动的可能性。然而是否二次易装,在《花木兰》中巧妙地表现了木兰的选择:文泰在柔然大军来袭时放走了木兰,她本有机会选择回归女性身份,但她还是坚持再次易装,当她身着戎装归来杀敌时,她的易装就不再是简单地替父从军,而是有着对跨越性别藩篱的渴望与肯定。易装颠覆了花父对木兰的劝诫:“花家的人只会在战场上打,你要打,下辈子,做个男子吧!”,让她获得了战场杀敌的合理身份。但在影片价值观念的设定下,仅仅拥有男性般的战斗力显然不能真正实现性别的“越界”,因此《花木兰》的后半段呈现了木兰心理重构的过程。影片中文泰为了让木兰剪掉情感上的牵绊,假借死亡策略试图磨练木兰;儿时伙伴小虎配合文泰,用话语点醒消沉的木兰;包括木兰自己振作后对士兵的宣言……其实这些都是在男性角色规范下去重构木兰的心理。影片中木兰立功归来参见皇上时仍是身着男儿戎装,直至还乡才恢复了女儿装。然而与《木兰辞》不同,《花木兰》中木兰归乡是带着些许忧郁的,影片通过她对纺织车、女性服饰、梳妆台以及对自己征战多年容貌的凝视,捕捉了木兰回归原来性别身份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褪去男儿装的木兰卸下了阳刚特质,不再肩负男性角色的重担,但另一方面,还原女儿身的木兰又唤醒了儿女情长,使其无法抑制对文泰深切的情感。
总之,《花木兰》中的木兰易装无论是替父从军的外在要求,还是再回战场的自我诉求,易装后的她都是按照社会对男性角色的要求来规范自己,而从她的二次易装选择、坚持重塑强大的心理以及回归女性身份的矛盾表现来看,她的内心虽有着女性感性的特质,但也是蕴含着男性化向往的。
2 《Mulan》:女性自我追求下的易装
在美国迪士尼公司发行动画电影《Mulan》中,一开场便设置了木兰相亲的情节,面对媒婆测试,不拘小节的木兰弄得一塌糊涂,她并不具备媒婆眼中传统女性应有的谨慎、端庄、优雅,大大咧咧的她甚至有些莽撞,但这些都与男性阳刚之气相差甚远。这样的木兰决定了易装后的她肯定不似《花木兰》中那般自如,即使她剪掉了长发,换上戎装,但她女性的骨相比起军营里的男性仍是瘦弱许多,在走路姿势、说话声调、行为表现上更是无法适应。体质、能力方面上,影片设置了李翔这一角色与木兰形成鲜明对比,他射击、武术、捕鱼样样精通,木兰却一无所知。然而与其他士兵笨拙懒散不同,女性体质决定了木兰在这些能力上起点比男性还要低,再加上在军营中常受伙伴们的欺负,因此要掌握这些本领就更困难。影片中受刺激的木兰经过一夜的坚持在负重下爬上了木桩的顶端,当木兰高高在上露出胜利的微笑,镜头是通过李翔仰视的视角呈现的,这暗示了对女性能力的赞同。虽然木兰最终熟练地掌握了所有的技能,但事实上这却只代表着她自身能力上的突破。在影片的呈现中,木兰在心理上并未表现出对男性特质的向往,通过木兰的视角,军队男人们的特性大多是挖鼻孔、抠脚指头、纹刺青等,这让易装后的木兰感到恶心并发出了“我想我做不了男人”的感慨。当士兵们歌唱他们心目中的女性,木兰也作了定义:“我喜欢她聪明有智慧,还有自己的主张。”相比于士兵们从男性需求出发定义的女性,木兰道出了自己女性的心声。由此,在《Mulan》影片前半段中,易装后的木兰虽身披戎装却仍有着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这明显与《花木兰》中的易装处理有了很大的差别。
再看影片的后续情节,这样的女性自我观更是进一步被强化了。这首先体现在了木兰身份暴露的发展上,在《Mulan》里身受重伤的木兰在治疗的过程中暴露了真实身份,宰相当众散开了木兰的头发,而这样的性别公示实际上切断了木兰二次易装的可能。其次,影片中设置了大量男性对女性身份歧视的情节和镜头,如宰相嘲讽木兰女扮男装“一个娘们儿,最毒妇人心”并将她摔在雪地上,木兰暴露女儿身的镜头视角是她置身于男性的审问和集体的俯视下;甚至是被木兰救于雪崩险境的李翔,原是心怀感激,但在亲证木兰女儿身份后,却不再理睬木兰并愤怒离开。尽管最终他放了木兰一条生路,镜头的呈现却也是挺立昂头的李翔与屈膝低头的木兰,而这实则更反衬了女性追求自我的必要。影片结尾,木兰以其聪明才智拯救了皇上和大家,而她打败单于的方法,正是依靠了她女性本体的特质,包括外形以及细致周全的思维方式。由此,木兰完成了证明自我的过程,成为了父亲口中那朵虽迟开却最美丽的花朵。
3 中西文化视域下的性别“越界”
王岳川在《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中曾提到:“在理解的过程中,人无法根据某种特殊的客观立场,超越历史时空的现实境遇对文本加以‘客观’理解。”③的确,《花木兰》与《Mulan》中虽同样有木兰易装的情节,但在中西方的文化语境下,却是烙印着不同的“主观”印记。
服装作为区别男女两性的重要手段,在中西方的性别文化中同样存在。然而中西方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毕竟存在差异,中国哲学讲求有机整体性思维,而西方则注重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因此在两部影片中,易装的情节虽都表现出了性别“越界”的意味,使木兰在原有的女性本体之上得以构建另一个男性身份,但在中西性别构成性认识的投影下,这一身份作为一个参照物的存在,在两部影片中却是不同的。《花木兰》中,木兰是以这个参照物作为标杆去效仿的,易装下她在外在能力和内在心理方面的男性化正表明她对这种阳刚气质的依赖。而这样的性别“越界”处理显然是蕴含着中国独特的性别哲学:“在这一哲学意识中,男女互构而与天地齐,男女互动而与天地参,男女相合而与天地一。同时,男女又并非彼此平等,而是比与天地,天上而地下、天尊而地卑,这就有了千古如斯的合于天地的男尊女卑。”④由此,女性在这样的两性关系下即使通过易装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行动力,她却始终还是处于下风位置。的确,影片中木兰能够在男儿装下尝试心理的“越界”,获得如男儿般强大的内心,但支撑她的还是对于男性的情感。结尾木兰的独白“在战场上死去,生命像雨水落入大地,毫无痕迹。如果那时候,你爱上了一个人,希望会从泥土中重新绽放,热烈地拥抱生命。文泰,谢谢你。”这一诠释为木兰恢复女儿身的心理焦虑设置了情感的出口,当木兰无法再借助易装达到具有阳刚强大的心理特质去承受爱人的离去,就只能将这儿女情长化为醇酒,好好在今后的日子中细细品尝,填补这“越界”回归之后的落差。《Mulan》中却不同,木兰虽然也面对着这一阳刚特质的参照物,但她的态度是不屑与之同类的,她仅仅是借助易装完成女性自身能力的提升。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到西方式的性别“越界”,女性在两性之中虽处于“他者”位置,但“20世纪到来,西方女性意识到了这种文化‘阴谋’,她们‘揭竿而起’,为自己的性别‘起义’,‘女性’作为一个政治命题、一个文化命题,在对‘男性’政治与文化进行抵抗的过程中获得了意识形态的意义。”⑤由此女性自我意识一旦觉醒,那么在对抗过程中她虽受到压制却是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改变所处位置的。确实,在这部影片中木兰对于男性的情感是独立且冷静的,这使她即使受到了李翔的冷遇“你不该来这的,回家去吧”,也能回击“你说你相信花平,为什么不能相信木兰”。并且在最终对抗单于的过程中,木兰使男性处于助攻之位,让他们通过男扮女装才能取胜。由于木兰最终是以女性之驱完成了英雄的壮举,因此木兰“越界”回归的心理落差实际上已被成功证明自我的喜悦所取代。
可见,无论是《花木兰》还是《Mulan》,都在木兰易装部分完成了各自的想像建构。而在这其中不仅有着中西性别文化的投影,往往还输出中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这首先就体现在木兰对性别“越界”的心声上,由于木兰易装最初目的是替父从军,因此从木兰易装到暴露女儿身前,她的心声都是被尽孝这一表层给掩盖了。直至木兰在他人面前暴露身份,两部影片才设置了木兰吐露心声的片段:《花木兰》中担下盗窃玉佩罪名的木兰被下令斩首,文泰在临刑前探望她,她卸下心理戒备对文泰强调“你千万不要让他(父亲)知道,我没有战死在沙场”,在临死的关头嘱托这样的要求,可见木兰心中对于战场杀敌的心愿。影片在这其中将木兰的“忠”嵌套在了“孝”之下:替父从军,杀敌卫国,国是木兰最终的指向。而《Mulan》中,在众人面前暴露身份后被抛弃在雪地里的木兰,对着木须坦白:“我不该离家的……也许我不是为了我父亲,也许我只想证明我自己的能力。希望当我揽镜自照时,就会觉得对得起自己。可是我错了,我什么都看不到。”木兰用了多个“我”和“自己”来道明参军的缘由,身份的暴露使木兰恢复了女儿身,无法再获得施展自身能力的平台,这是木兰最为沮丧的。因此,在这影片中木兰性别“越界”最终的指向是自己。
其次,木兰的行动和选择也有所体现:《花木兰》中面对柔然的围攻,身着戎装的木兰决定拼死一搏,而当她回归故乡还原女儿身,面对文泰私奔的决定,她为了国家的安宁,最终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这样情节设定的背后输出的价值观,其实正是中国倡导的集体主义,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取向是围绕着整部影片的,尽管在时代的影响下,影片加入了女性感性矛盾的心理和情感的表现,但只要在中国这一语境下,她始终是一个忠孝两全的花木兰。而《Mulan》中的木兰是忠于自我的,她的所作所为更多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价值。影片里还原女性之身的她凭靠自己的智慧和胆量拯救大家于危难之中,当皇帝赐予木兰金牌“让你家人知道你救了朕”和单于的剑“让全世界知道,你救了国家”,这里的“你”其实点明最高权力者已将木兰个人置于英雄的地位。木兰最终欣然接受这一荣誉并拥抱了皇帝,在大家送别的目光和欢呼声中独自一人骑马离去,这一情节的呈现正表明影片对个人英雄的追捧,她可与最高权力者平等拥抱并受众人的仰视。这其中输出价值观正是西方所崇尚的个人主义,它更突出以人为主体的成长,鼓励通过个人的奋斗实现个人的价值。由此,木兰虽是有着黑头发,黄皮肤的东方样貌,但骨子却是一个追求自我的西方女子。
总而言之,木兰易装的情节提供了女性跨越性别界限的一个艺术想像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无论是东方木兰男性化向往下的易装,还是西方木兰女性自我追求下的易装,其实都是中西文化投影下的具体表现。而在这其中所蕴含的中西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正是需要我们注意,并从中取长补短,更好地发展中国这一精彩的易装传奇。
[1] 黄丙明选注.《古代诗歌选读》[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10.
[2] 郑朝琳.《易装、身体与欲望——女性主义角度下的乔治·桑与〈侯爵夫人〉》[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2015年.
[3] 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4] 王纯菲.《哲学视域下的中西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批评》[J].文艺理论与批评,第42卷第6期,2014年11月.
注解:
① 黄丙明选注:《古代诗歌选读》,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56-157页
② 郑朝琳:《易装、身体与欲望——女性主义角度下的乔治·桑与〈侯爵夫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③ 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8-209页
④ 王纯菲:《哲学视域下的中西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批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年11月,第42卷第6期
⑤ 王纯菲:《哲学视域下的中西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批评》,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年11月,第42卷第6期
赵欣(1991-),女,广西百色人,暨南大学,研究生,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G255
A
1672-5832(2016)03-01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