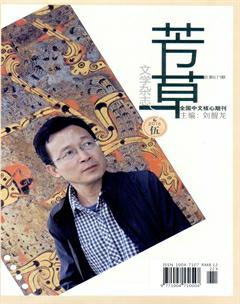苏北:向汪曾祺致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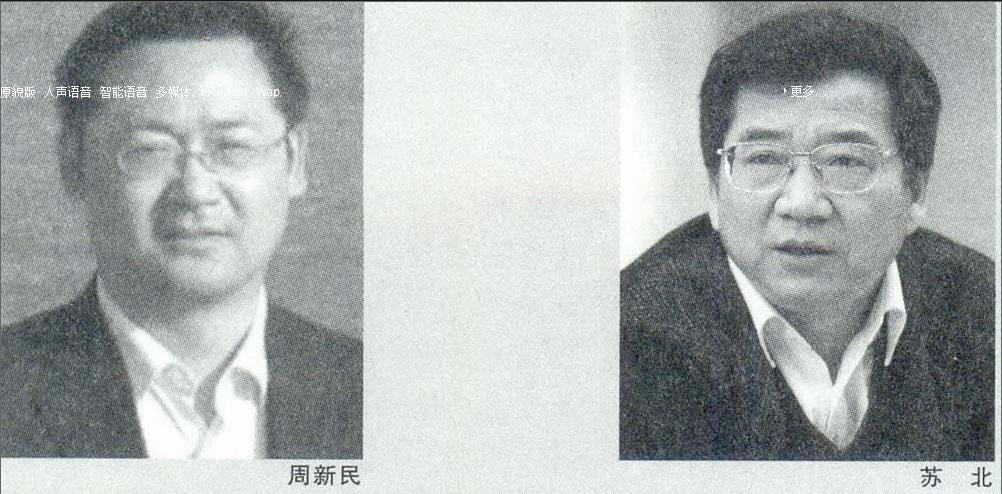
周新民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二00二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二00六年获“中国博士后”证书。兼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新文学评论》副主编、《长江文艺评论》编委、《长江丛刊》评论版编委等学术职务。系武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先后入选武汉市黄鹤英才(文化)计划、湖北省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七个一百”(哲学社会科学类)计划等。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文学评论、学术论文近两百篇,出版著作五部。曾多次获湖北省、武汉市政府奖励。
苏北本名陈立新,一九六二年生,安徽天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十月》《大家》《散文》《文汇报》和香港《大公报》、台湾《联合报》等报刊发表作品一百五十余万字。作品入选多种选本。著有小说集《秘密花园》、散文集《城市的气味》《植点青绿在心田:苏北海外散文七十一篇》、随笔集《书犹如此》、回忆性著述《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忆·读汪曾祺》等。曾获第三届汪曾祺文学奖金奖等多种奖项。
周新民:你长期在金融一线工作,业余写作,你是我访谈众多作家中唯一一位业余作家。你的文学创作之路和那些专业作家相比较,定有许多独特之处。首先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对文学创作产生兴趣。
苏北:文学创作其实没有业余和专业之分。许多作家都是寄托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的。至于我的文学创作,我学习写作,确实起步较晚。在高中之前吧,我就与文学没有缘,一点儿文学的爱好都没有。我小时候也没看过文学书,也没有受过什么外祖母的熏陶。我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数理化还是不错的。那时候我是报的理科班,以第十七名考了进去。因为只有一个尖子班,所以相当于全校十七名。后来在尖子班成绩就往下掉。掉到三十多名。第一次高考没考上,差二十几分吧,这个对自己是一个比较大的刺激。当时同班的小伙伴们都走掉了,他们有考上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还有考到武汉测绘学院(现在和武汉大学并起来了),全国到处都有吧。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第一次放暑假回来的时候,穿着各个学校的汗衫,在我们一个废弃的公园的草地上踢球。我呢,背着个书包补习。他们在踢球,而我在学校里面补习准备第二年高考。第一年我语文考得比较差。物理考了八十几分,语文却只考了五十几分,反正没有及格。在没有补习之前,我还到我父亲任职的那个公社里面去当了一个学期的代课老师。学校说你哪一门差就带哪一门,我觉得语文比较差,就带了语文。带初中一年级的语文。反正每个老师都有一个备课的教辅,我就照着那本教辅讲,反正一通乱讲,孩子们小,也好糊弄。记得还真有几个孩子喜欢我的。主要可能是我比较平和,人也风趣些,孩子们好亲近。
一学期结束,我又回到县里补习,参加第二年的高考。高考的时候我语文还真考得不错,语文考了八十多分。相当于良好。但是,化学又没能考好,化学只考了三十几分。后来回来之后我就准备补习第三年再考,这个时候人就比较有压力了。正好这时银行在高考落榜生中招人,招那种高考差几分的。我便去报了名,后来就到银行系统工作了。经过一个短期的培训,我便被分配到一个小镇——来安县半塔镇营业所工作。
到这个半塔镇上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爱好上文学了。准确地说,爱好上文学,是从高考复习的一本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散文选》开始。这本散文选收录了刘白羽、冰心、朱自清、秦牧等作家的散文,我还将这些人的散文背诵。或者读熟。
周新民:我们常说文学能起到慰藉心灵的作用。在高考失利的这样一个特殊情境之中,文学让你找到一个情绪宣泄的渠道。沉溺其中,你既找到精神安慰,也找到了精神寄托。不过,对于一位以往很少接触文学的人来讲,突然接触到这么多喜欢的文学作品,你有何阅读感受呢?
苏北:我主要的一个感觉是“美”。说明那时候我已经建立了较好的审美系统。冰心的《小桔灯》、朱自清的《绿》、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等作品,意境、词汇都很美。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仿佛外面世界有一种东西在吸引着你。那种东西不是庸俗的生活。是一点儿梦想,一点儿朦朦胧胧的幻象。现在看来,文学实际上给人这么一种力量。怎么说呢?打个比方,为什么一个作家,到老了,到八九十岁了还在那里写,一直写到死。主要就是文学使人变得“心”年轻。比如,我五十多岁了,而自己并不能感觉到,觉得自己还是三十多的样子。“心”是三十多岁的,只是身体变成五十多岁了。——其实后来我也后悔过,文学就是一条不归路,——永远写不完,要一直写到死去。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还有就是这么多年,总体上来讲,我还很天真,也就是说我还很单纯,也很有正义感。这个估计都是文学的力量。文学的这种力量让我痴迷于文学。这么多年来的坚守,让我对文学倍怀感恩!
周新民:如此看来,文学不仅让你在那样一个人生特殊的阶段找到了精神力量,也成为你此后人生的重要支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开始步入繁荣期,也是一个大量向西方文学学习的历史时期,在你开始阅读文学的重要阶段,也一定接触过西方文学作品。你能够回忆起当时你接受到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情形么?
苏北:我进入银行系统工作之后,先在滁州接受了三个月的培训。当时,我一个中学同学在滁州师专中文系学习。我就到他宿舍去玩,他的床上有一本《外国文学名著选读》。同学把这本书送给我了,他还让我在他的书架上挑了《世界文学名著导读》。这两本书是我开始接触外国文学的发端。我还在滁州新华书店买了几十本外国文学名著。有的就在滁州看了,有的就带回我后来工作的小镇半塔。我大概前后看了有四十几本十八世纪的世界名著。但是当时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个就是外国人的名字太长了,看着看着就看混了;第二个呢,那些翻译家虽然都很优秀。但是呢,他们那种翻译的句式和我们现在的这种写作的句式完全是不一样的(欧化的)。那时我们年轻有力气,平时还喜欢练功。在单位院子里的梧桐树上,吊上吊环,没事就在上面翻。同时还练功,还练习鲤鱼打挺。于是我就把一根练功的功带,钉在椅子把上。看书时往腰上一扎,必须看到五十页才能站起来。因为一个晚上五十页,十个晚上就是五百页,一本世界名著大约也就五百页的样子。这样十天就可以拿下一本。就这样用硬功夫去读,在年轻时硬啃了一些书。现在想来,读不读世界名著,还是有差异的。世界名著不是学习写作经验,而是培养一个人的情怀。一个人要有心向远方的理想。否则日子久了,就会流于“俗”,为小利益、小眼光所困扰、所束缚。一个只读文学杂志的人,他的创作,或者说,他的人生境界是不会太开阔的。这是我的一点个人经验。
我呢,就是读了一点世界名著,给了我那么一点儿幻象和梦想。为什么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会给那么多青年带来那么大的影响?青年在里面不是找文学,是找自己,从一个乡下人怎样的进入城市,个人奋斗或者是怎样改变自己的命运吧。我那时实际上也是这样。脑子里面充满了幻象,或者说有点儿梦想吧。
我记得有个同我一起招进银行的同学。他在培训班上同我住一个大宿舍,他是那种白面长身的青年,他身上有反骨,那种力量非常迷人。没有课或者是早晚,他就在走廊上或者阳台上。大声地说,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我说玛利亚是谁呀?后来他老跟我讲聂赫留朵夫,就是《复活》上面的主人公。我觉得他很神奇。后来实际上他并没有写作,但是他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就觉得他还能知道这么多陌生人的名字,而且这些人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相干吧?实际上我大约到一九八六年就不怎么读世界名著了。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大概就几年的时间。但那是我青春年华最好的时候。我后来就转而开始阅读中国文学了。
周新民:你曾如此沉迷于外国文学名著,为了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你还下了那么大的气力。你为何停止了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呢?八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国文学界大量译介外国文学的黄金时期,你的阅读兴趣为何从外国文学转移到中国文学作品的阅读上了呢?
苏北:先是我的一个作家朋友,那时他正风头强劲,有一天他到我这儿来玩,他对我说,中国没有文学,只有一部《红楼梦》。他的话吓我一跳。他走后,我就到书店买了一套《红楼梦》,可是真的看起来,也还是看不下去。但是我觉得他的话是有道理的,于是我跑到街上,又买了一套,我将这一套拆成册页,那时我正上电大,于是我就在课堂上一页一页去抄。这样抄来抄去,我熟悉了,有感情了,就放不下了。一直到今天,我对《红楼梦》仍然喜欢得不得了,可以说是个“红迷”。
之后就是突然一下子发现了汪曾祺。发现汪曾祺的原因不是因为汪曾祺多么好,而是觉得汪曾祺这个人写得简单,好模仿。我见到他的语言,就觉得特别亲切,觉得这个人肯定是我们家乡附近的。那时并不知道他是高邮人。后来知道他和我们是一个语系的。他的家乡是高邮。我的家乡是天长,一个在高邮湖东岸,一个在高邮湖的西岸。我们共饮高邮湖的水。——虽然他十九岁就离开家乡了。
周新民:你在阅读外国文学一段时间后。就转而开始阅读中国文学。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外国文学作品在语言表达方式、叙事方式上与中国文学不同。相比较而言,汪曾祺的文学作品在语言和叙事手法上,显得更加简洁。
苏北:后来也读过许多世界名著,只是不那么集中了。世界名著中也有较简洁的。比如海明威,比如西班牙有一个作家阿左林,他曾影响过汪曾祺,这是一个极其简洁的作家,他写过一本《塞万提斯的未婚妻》,那真是一本极好的小说,真诚,真实。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伊萨克·巴别尔的《骑兵军》,还有卡佛的小说,等等,都比较简洁,这可能与翻译风格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汪曾祺式的简洁,是中国的。记得黄裳先生曾说,“汪曾祺是用写诗的方法写小说,他的一切都是诗。”这句话很有意思,又非常中肯。汪曾祺的小说、散文,都比较“空灵”,比较注重意境。这是外国文学所没有的。这完全是中国人的唐诗宋词式的情绪,而且有汉字的一种特别的美在里面。
像汪曾祺这样的作家往往是以少胜多。是白描。这里还要提一个作家,就是钟阿城。他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当时一出来,就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这三篇小说是非常中国式的,但是里面的精神又是全新的。
周新民:“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任务是把文学当作中国现代性追求的一种方式,文学创作往往受到某种先验观念的制约,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某种观念的传声筒。相比较而言,汪曾祺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汪曾祺的文学追求突出的一点是,他不是看重某种先验的观点,而是追求文学的审美特性。为此,他把文学语言提高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他曾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苏北:我学习他们的写作方法,主要在锤炼语言上,其实那时我最大的苦恼是没有生活,或者说不能发现生活中的小说的因子。就在语言上做文章。我的朋友钱玉亮就批评我语言上疙疙瘩瘩的。就是写了前一句话,后一句话和前面的不连。“离间”得太远。“离间”本来是一种方式,用好了会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太离谱了,就显得太干巴了。其实我这是在训练。我记得我受汪曾祺和阿城的影响,曾写过一篇小说叫《老人与小东西》,我就写我小时候钓鱼的经历,写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孩两个人钓鱼,在池塘边的一点儿冲突,只有三干字。当时就用复写纸复写了四份,先后寄给南京的《青春》、四川的《青年文学》、上海的《萌芽》和北京的《丑小鸭》。反正那个时候人们称之为“四小名旦”吧。过了不久,这些稿子一次又一次地被寄回。我见到这些刊物的信封,《萌芽》的,《青春》的,里面厚厚的,我就知道又寄回来了。里面夹一张退稿信,那个时候还退稿子。后来等了很久,就收到《丑小鸭》的一个信封,一点点儿薄,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我就知道有好事了,撕开来一看,里面写着这篇小说留用,要我提供一张照片和简历,准备第十期给发。当时真的高兴得不得了。我就从滁州坐汽车跑回天长,向文友王明义、钱玉亮他们汇报。果然一九八六年的第十期就发出来了。还有一个编辑评点。这就等于说我发了第一篇小说了。
周新民:最初你是以写小说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你觉得你的小说里面你最满意的是哪几篇?你觉得它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苏北:我的小说都还满意。主要是真诚。要说几篇,大致有中篇《秋雨一场接一场》,发在《上海文学》上的,《小说月报》也转过。后来在《芳草》上发了两篇《恋爱》和《洗澡》。
我从来就是讲以少胜多。对我的这些小说,我没有悲哀过。你别看有的人写了几百万字,他的很多小说都是编的。他写的那些事情并没感动过自己,也不会感动读者。我虽然没有什么才华,写得也不多,但是我这个东西我相信它有生命力。我为什么相信它有生命力呢?我的这些细节是可靠的,是绝对可靠的。原来汪曾祺先生说过,他说,“我从来不写自己不了解的生活。对自己不知道的,从来不以为意。”
我的小说肯定是有些特点的。怎么说呢?我肯定不是以故事取胜的。我多是以情绪和感觉为主。第二个呢,我想,我的小说主要是写入的,里面并没有什么重大事件,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冲突,我就淡淡地让你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又好像什么也没有。你看我的两个短篇《洗澡》《恋爱》,就写孩子的感觉,写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忧伤啊,心理上的一些小波动啊。我觉得文学不是通过一种多么大的力量来拨动人心的,而是通过那种虫子在草叶上轻轻一落、一起飞这种细小的颤动,来颤动人的内心。还有就是语言要干净。我以为小说要有细节的力量。一切的一切,在于细节的力量。
周新民:这说明你的小说还是重情绪,重细节,不重视故事。这些特点和汪曾祺的小说很相似。
苏北:不重视故事,我也没有那个故事,我有故事也把它虚化了,实际上我是受到汪曾祺、沈从文和废名的影响。
周新民:从地域上来讲,你和汪曾祺都是高邮地区的人,你们作品里面肯定带有高邮地区的文化共性。
苏北:“里下河作家群”中著名作家有汪曾祺和毕飞宇等。每个作家,他们当然风格各异。归纳他们的共性,我想,一个是他们写作带有很大的地域性,地域特点明显。第二是“里下河作家群”的作家们的艺术感觉都比较好。他们的小说、散文,包括其他文学种类,多不是以故事取胜,绝大部分是以文学感觉方面取胜。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因为这一群人,都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受到过汪曾祺的影响。
说到汪曾祺的影响,可以讲是广泛而持久的。因为他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了《受戒》和《大淖记事》之后,确实让大家感到十分奇怪,让人眼前一亮。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我现在手头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人民文学》和《小说月报》。我前不久翻了翻,当时在头条发的都是何士光、古华,有的时候《人民文学》一年有两个头条是何士光的,除了《乡场上》,还有什么《种包谷的老人》等。但是呢,我在里面也翻到了几篇汪曾祺的小说,都是摆在三四条的位置,都是在后面。文学就是这么残酷,三十年过去了,《受戒》《大淖记事》在书店里汪曾祺的作品的各种选本中都有,许多八0、九0甚至00后,都知道汪曾祺的名字,知道他的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汪曾祺就等于走进了现代文学史中去了。文学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但受过汪曾祺影响的这些人,其影响再往上追,其实也受到过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的作品量比汪曾祺要大得多。他的小说让人着迷。他所写那些少男少女的纯洁,很迷人。汪曾祺后来在创作谈中说过,为什么写了《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里面的小英子,《大淖记事》里面的巧云,这两个人物是怎么来的。他说在写的时候是没有感觉到的。但回头一想,是受到沈从文的三三、萧萧和翠翠的推动。为什么受到她们的推动呢?因为沈从文那时要编文集,汪先生就把沈先生所有作品都读了一遍,他是为沈从文做事,为他的老师做事。读完之后实际上他并没有想到会为他写《受戒》和《大淖记事》产生推动。中间放了有年把,实际上是沉淀到心里去了,后来《受戒》和《大淖记事》就在他心里活了,他写的时候两个少女在他心中,但是他并没有觉得是受沈先生的影响。过后想想,大致是受了沈先生的这些少女形象的推动。这个心里面孕育的过程它就是这么神奇,所以我的一些小说,里面也写到很多少女,虽然着墨不多,有点恍恍惚惚的,但是这些形象是活的。有的时候一个形象着墨很少,篇幅并不多的,读者反容易记住。
记得汪先生曾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写过一篇散文《吴大和尚和七拳半》,写到卖草炉烧的吴大和尚,娶了一个年轻的老婆,这个吴大和尚经常深夜打老婆,原因是他的小媳妇“偷人”,终于有一天这个小媳妇跟人跑了。曹禺看到后非常感动,就给汪曾祺写信讲:我久久不能忘记这个小媳妇的形象。这也是着墨不多,形象深刻的一个事例。
周新民:你最初发表的作品基本上是小说,你的小说也很有特点,也有很好的社会反响。你后来为何停止了小说创作,主要写散文了呢?
苏北:小说创作停了好多年。主要是感到没什么东西可写。还有一个可能与我到北京工作有关。在北京当记者。主要跑经济、金融。离文学便越来越远了。然而,我写的东西都是有根据的,我没有看到、感受到,我就无法下笔。在北京工作五年,主要做编辑和经济采访,那个时候离文学稍微远了点,但心中并没有丢掉文学。偶尔还在我们报纸的副刊上写一点文字,再后来我调到副刊部当主任,又开始写。集中精力写散文大约是二000年左右,一个是我在报纸上开了专栏。必须写。刚开始多给省里的《新安晚报》《安徽商报》写,写了有几百篇,也给上海的《新民晚报》写。但是呢,我的散文不是专门给报纸写的。我的朋友许春樵说过,苏北虽然给报纸写散文,但他不是报纸散文。我自己知道的,我不是报纸散文,我是有风格追求的散文作家。再后来,写得多了,《文汇报》《羊城晚报》《今晚报》,全国许多著名报纸都写过。同时,刊物上也发得多了,比如《散文》《美文》《大家》等。原来以为《散文》这样的杂志是专门给孙犁、刘白羽这样的人开设的,没想到后来我也能发表。这是过去做梦都做不到的。人的胆子就是慢慢变大的。《散文海外版》和《散文选刊》也开始选我的散文,这样在全国算是撒开了,时间长了,你再说你不是散文家就有点矫情了。《散文海外版》还给我做过几次小辑,一次都是好几篇。这样散文算是写出来了。好像人家都知道有一个叫苏北的在写散文。
周新民:你在北京的五年,因为职业的原因,小说创作再也没有深入下去。因为和汪曾祺的接触,倒是在散文创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应该看作是你文学创作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
苏北:我觉得写小说,靠编故事,我没有这个能力。写那种感觉、情绪是一阵一阵的,我给《芳草》写过两个短篇《洗澡》《恋爱》。刚开始我只写一篇《恋爱》,醒龙让我再写一篇。后来我就又写了一篇《洗澡》。醒龙看了,说这个也不错,就发个小辑吧。年底《小说月报》就将两篇全都转了。这两篇小说后来还获了《小说月报》第十三届“百花奖入围作品”。
周新民:像《洗澡》《恋爱》这种小说,文体特点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你觉得散文和小说两种文体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苏北:别人说我的散文写得很怪。我鲁院有个同学,他看了我的散文,说:“苏北,我一看您的散文,就感觉跟别人的不一样,您写得好怪。”我说:“第一,我是以写小说的方法写散文;第二,因为是小说家的散文,所以这里面我很少抒情。”当然,还有一个将镜头推得远远的方式。这是一种文学的方式。文学的方式不是将镜头拉近。就是将镜头推远。反正眼跟前的是不行的,这样才能更具文学性。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样才有一种隔岸观火的感觉。
我的散文似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通俗明白。有人以为它通俗明白简单。其实它并不简单,这是一种训练过的简单。上海有评论家包括杨扬、王宏图,他们认为我是低姿态写作。是的,我同意这个说法。作为一个写作者,态度要诚恳,文字要诚实。这是基本的。你不要耍花腔。你一浅薄,读者就会揪住你的尾巴,别以为读者是傻瓜。
周新民:我觉得你抓住了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陌生化”。从根上讲,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水准如何,就看他陌生化的能力如何,要看他如何在芸芸众生熟悉的生活中,找到“陌生化”的路径。
苏北:对,陌生化,变形、夸张,不要面面俱到,要局部夸张放大。这些都是基本方法。只要看过马尔克斯的小说。你就会更有感受。我比较喜欢马尔克斯的两本书,一本是《百年孤独》,一本是《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两本书我都比较熟悉。他能把生活弄得那么神奇,你说在现实生活中找一块材料专门来写小说,那太巧合了。不大可能有。真的写起来,你要把生活中的那么多的碎片组合起来。你读完之后,好像真感觉到有这样的生活,其实不大可能有,为什么我们相信?因为生活的可能性太多了。
周新民:的确如此,作家是要围绕“生活的可能性”来做文章。其实,我认为,所谓的“陌生化”就是要作家去充分发挥文学的想象力,找出种种“生活的可能性”。
苏北:对,你能把零碎的生活连接起来,成了一个整块的东西。就好像一棵树,这棵树不是地上长的树,完全是你虚构的。但你种下去之后,它们血脉流通,它就活了。你嫁接了生活,它活了,结果子。所以在生活中,你能把这种神奇的,有文学意蕴的东西,将它们揉结在一起变成活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周新民:作为一名散文家,我觉得你最大的成就是以汪曾祺作为写作对象,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散文。你作为一个散文家。对汪曾祺的观察是带有一种情感的色彩走进去的。也有很多学者写汪曾祺,不过,学者的研究有一种理性的思维,你在写汪曾祺的时候,或在研究汪曾祺的时候把握的是一种怎样的尺度和分寸?
苏北:这个事情说来真是好玩,最早汪曾祺在世的时候,我写过《关于汪曾祺的几个片断》,发在我们自己的《中国城乡金融报》上,我就拿着报纸给先生看了。先生去世后,报道也很多。回忆文章也很多。我就将《有关汪曾祺的几个片断》接着写,写了一万多字,给云南《大家》杂志,配了几张照片,就发出来了。
特别是在汪先生走了之后,你才会发现,这个人对年轻人太好了。那时,我和龙冬与他非亲非故,经常一打电话就去他家,我们又没有文学成就,汪先生只是觉得这两个小青年,人还比较干净,也比较纯粹。反正就是热爱文学的青年吧。
人是一旦失去了,才倍感珍惜。所以,汪先生走了,对他的感情就慢慢升温。后来我就又写了一点。写完之后,我就给一些比较好的报纸发去,这样越发越多。汪先生产生这么大的社会力量,他的影响力肯定和许多现代作家是齐名的,像朱自清啊,郁达夫啊,张爱玲啊。所以他去世后。这种推动力量,姑且称之“汪迷”的推动力量吧,我是其中之一吧。因为我可能把全国的重要报纸都写遍了,都是关于汪曾祺的。
这样写了有近十年吧,陆陆续续的。写了大概有七八万字。有一次在北京,与我的好友顾建平聊天,我说,建平,我散文写了这么多年,也有点影响吧,你给出一本散文集吧。他说,散文不好卖,你写了那么多汪曾祺的文章,都是东一篇西一篇的,你得有计划去写,人家出的是专著,你把它归归类,好好编辑一下。说着,他就找出一张纸,给我列提纲,编目录。建平的建议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回来我就把自己所写的文章进行梳理,梳理之后一看,发现自己写了六七万字,后来我又接着写,包括写《读<受戒>》《读<大淖记事>》。这些都是我有计划地去写的。这样写了有十万字。一次聚会,赵焰建议我给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发过去,很快就定下来了。这样就出版了写汪曾祺的第一本书,叫《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这个书名,也是顾建平兄给起的。
这个书出来之后,影响就很好,许多人都知道有一个汪曾祺的粉丝叫苏北,有许多书评之类的,反正是弄得风生水起。
又过了几年,在汪先生逝世十五周年之际,安徽文艺出版社决定重印此书,我又写了有四万字,将书名定为《忆·读汪曾祺》,还专门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开了一个《纪念汪曾祺先生逝世十五周年暨苏北新著<忆·读汪曾祺>研讨会》,许多学者、专家参加了会议,这个研讨会十分成功,大家畅所欲言,非常尽兴。
周新民:在《忆·读汪曾祺》一书中,“忆”的部分主要是你与他的交往,就是我们常说的记人散文;“读”的部分,就是读文本。你觉得你读汪曾祺和其他人读汪曾祺,主要差别在哪里?你是“怎么”读的?你主要读什么?
苏北:我的这些文字,既不是评论家的文字,因为我不搞评论,我写不出那样的文字,又不是理论研究。那只是一个作家的阅读笔记,或者是阅读感受。我自己总结为“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深情注视”。汪先生原来也说过,“我宁愿看一个作家写另一个作家,也不想看一个评论家写一个作家。”因为评论家写作家。往往将其条分缕析,一分析就弄得很干,而作家写作家,往往是写细节,写感觉,写阅读的这种感受,总体上一句话就是感性的,更容易读,更美,更容易让人接受。
周新民:“忆·读汪曾祺”系列散文,是很好的文化随笔,但不是文艺评论。
苏北:不属于文艺批评,应该归为散文随笔。我刚才讲了,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深情注视”,这里面的文字,更像是一种注视,文本里面带有更多的个性阅读的成分。这种分析往往对小说家很有用。实际上,一个文学青年,想要写小说,看这种东西,更有效。它是个通道,它比理论更有用,它是纯感性的。我对这本《忆·读汪曾祺》,还是有点信心的。也许哪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世界,也许过了若干年之后,人家翻看了这本书会重印,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里面的文字是个性化的,不是随随便便要做就能做出来的。
周新民:“忆·读汪曾祺”系列纯粹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情绪上的一种感受,而不是对汪曾祺这个作家和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理论归纳。
苏北:对。是情绪上的感受。这样一本书,它完全是无心插柳的结果。它是我创作的副产品。如今副产品成主产品了。人家都知道苏北是写汪曾祺的,原来我是汪曾祺的痴迷者、追求者,现在我又似乎成了汪曾祺的研究者。当然我这个研究,完全是私人化的,不带学术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