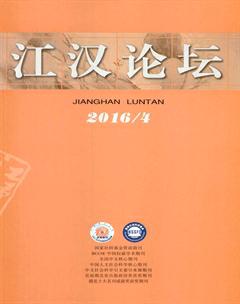选举暴力的治理逻辑
曾水英 殷冬水
摘要:选举暴力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主建设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仍缺乏严谨的学术分析。我国乡村民主选举暴力的发生,主要源于候选人强烈的谋利动机和一些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也源于一些媒体的“失语”。我国乡村民主选举暴力包括语言威胁、身体伤害以及设施破坏三种方式。治理乡村民主选举暴力,需要提高村民的公民意识,运用压力型体制的优势提升地方政府服务选举的能力,规范乡村民主权力。充分合理利用网络这一信息传播和扩散平台。
关键词:乡村民主:选举暴力:治理
中图分类号:D6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04-0035-06
选举暴力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民主建设面临的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仍缺乏严谨的学术分析。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实施村民自治以来。我国乡村民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乡村民主选举的规范化程度在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在增强,民主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正如20世纪初学者们所指出的,“村民自治如今已正式被载入国家法律。执行选举的程序已经出台,各级政府的实施细则也正在制定之中。所有村庄无一例外地每隔三年都要进行一次选举。”然而,作为一项国家主导的政治工程,我国乡村民主发展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选举贿赂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选举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并且呈现不断升级和扩散的态势。“早期的村委会选举暴力事件主要发生在我国东北地区和中西部的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如辽宁、河北、河南、陕西、四川等省份。而近几年发生的暴力事件范围不断扩大。东、中、西部地区均有发生,且地点开始向东部省份和中西部经济较发达的省份集中。”本文运用个案分析方法,研究我国乡村民主选举暴力的发生逻辑、运作方式和治理机制。以期“理解农民的生活”,提升乡村民主质量。
一、典型案例
自开展村民自治以来,选举暴力成为我国乡村民主发展中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产生了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典型案例。
(一)辽宁赵营子村“选举血案”。
2008年4月20日,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广宁乡赵营子村举行村委会主任换届选举,41岁的李东辉作为候选人参加了选举。此次选举实际参选人数为560人,李东辉获得307票,另一位候选人获得215票,作废38票,按规定李东辉当选。就在他准备上任时,同村的叶春祥多次向乡党委举报。称李东辉在选举前给他送了两瓶酒和一个菠萝,构成贿选,这使李东辉没能任职。李东辉产生了伺机报复杀死叶春祥的念头。2008年8月25日晚上8点多,李东辉见叶春祥在本村老秦家商店内与他人玩扑克,回家取来一把尖刀和一把三棱刮刀,乘叶春祥不备持尖刀多次猛刺其头部、面部、颈部等处,致其当场死亡。将叶春祥杀死后,李东辉又在叶春祥家、小商店等处,先后将叶的妻子、母亲、女儿、儿子杀死。连夺五条人命后,李东辉连夜逃往相邻的义县,并于8月26日向警方投案自首。
(二)福建西洋村民主选举中的“黑恶势力”。
2009年8月27日是福建省古田县鹤塘镇西洋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日子。天刚蒙蒙亮,街上就出现了大批不明身份、穿红色上衣的社会青年,每个路口每个街区都有这些青年。身着红色上衣的社会青年穿梭于西洋村的各条街道,引起了当地群众的极大恐慌。这些穿着红色上衣的青年是前任村主任余根杰的马仔。余根杰是鹤塘镇黑社会老大,也是古田县人大代表。在天还未亮时,许多老人遭到不明身份青年的人身威胁。在鹤塘镇天桥下,穿红色上衣的社会青年强行把对方选民拉下车,不让他们去现场投票,受到威胁的选民不敢出门投票。在广场上的村委会选举投票区,两边站满了穿红色上衣的流氓,不让另一方候选人竞选团队的检票员进入投票场所。另一方候选人竞选团队向选举委员会投诉,选举委员会不予解决。另一方候选人团队感到选举的公正性得不到保障,于是到县政府上访。县领导看到事态严重,于是派人到西洋村调查。当日下午县领导到西洋村主持工作,傍晚大批村民在村广场要求领导主持公道。在县领导的协调下,双方候选人同意暂不开箱,等双方协商后再验票,所以当晚投票箱由鹤塘镇派出所保管,并成立调查组对选举的公正性进行调查。
(三)北京前章村选举中的暴力。
2004年7月,北京市海淀区上庄乡前章村开始选举村主任,村民李德文作为候选人参加了竞选。候选人中最具实力的当属34岁的秦思亮。他在前章村有很高的威信。一心想当村主任的李德文为了能压倒秦思亮,拜托其姐夫崔全纠集有前科的舒文革、秦学法等人阻碍选举。李德文授意这些“打手”,在其得票数低于秦思亮时,就立即破坏选举。7月24日选举当天上午,崔全带着携带砍刀、斧头等凶器的舒文革、秦学法等十余人到李德文处会合,李德文设宴款待了崔全等人。席间,李德文先回村打听情况,当得知秦思亮的票数高出自己40多票时,立即电话通知崔全等人马上赶到选举现场哄抢票箱。但当崔全等人赶到选举现场准备破坏时,秦思亮已成功当选。崔全、舒文革见状指使秦学法等人手拿片刀、斧头、木棍等冲上前去围殴秦思亮,随即将其打倒在地,之后这群“打手”仍不肯停手,边打还边喊着“砍死他”。最终秦思亮被打成了失血性休克,经法医鉴定为重伤。
二、发生逻辑
如上三个典型案例表明,选举暴力正成为我国乡村民主发展面临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不管是在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抑或是落后地区的选举中,选举暴力都时有发生。
(一)我国乡村民主选举暴力的发生,主要源于候选人强烈的谋利动机。
在民主政治逻辑中,公共权力是候选人竞选角逐的对象。权力不仅可以服务公共利益,而且也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候选人及其团队谋取个人或团体利益的工具。威权政治与民主政治有不同的政治逻辑。威权政治的权力体系是相对封闭的,而民主政治的权力体系是高度开放的:威权政治的权力握有者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授权方式产生的,而民主政治的权力握有者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竞争性选举产生的。由于有了竞争性的选举,相对于威权政治而言,民主体制下的权力握有者有更多动力来对选举承担责任。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通过承担公共责任来兑现选举时作出的承诺,通过兑现承诺来保障再度当选。
从这一角度说,我国乡村民主的推行,无疑体现了我国政治领域非常重要的进步,因为乡村民主的推行改变了传统的授权方式和权力运行的逻辑,改变了政治生活中公民获取利益的方式。村民自治推行前,我国村一级公共事务的治理,主要依赖乡政府及其代理人村干部来施行。村干部的权力来源于乡政府自上而下的授权,这种授权方式意味着村干部要掌握和运用权力,需要保持对乡政府领导的忠诚,运用各种资源来维系与乡政府领导之间的关系。在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中,村干部主要起着“代理人”的作用,通过承担“代理人”的角色来实现谋利。
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启动了以下放权力为特点的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行村民自治,“农民作为政治主体,有了选举村领导、参与村级公共事务决策和管理的自主权。”村民自治的实行,改变了我国乡村政治的运作逻辑,选举成为村干部获取权力的重要方式,“村干部扮演着政府代理人和村民当家人的双重角色”。在新体制下,为了谋取个人或团体利益,需要获得政治权力;为了获得政治权力,不仅需要和上级政府维持良好关系,而且要充分运用各种资源,赢得竞争性选举;为了赢得竞争性选举,暴力成为一些候选人使用的重要工具。选举中暴力的运用,说明权力竞争异常激烈。候选人竞相争夺权力,要么是获得权力后可支配丰富的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自然资源。要么是获得权力后可支配村庄的集体企业和集体经济,或者在城市化征地中获得巨额利益。经验研究表明,“经济越是发达,村集体的收入也越多,村委会控制的经济资源较多,村委会的选举与村民的利益越密切,更多的人想竞争村十部的职位,村民的参与程度较高,选举竞争也较激烈。”从这一意义上说,正是巨额利益的诱惑,使得一些候选人铤而走险,运用暴力来获取权力,伤害竞争对手或选民。
(二)我国乡村民主选举暴力的发生,也源于一些地方政府的不作为。
民主政治要求选举是自由的、公平公正的、竞争性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自由、公平公正和竞争性的选举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需要一定的条件。自由、公平公正和竞争性的选举,需要运作有序的法治,需要各级政府为选举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
按照我国选举法的规定,地方政府有责任做好选举宣传指导工作,依托村内宣传栏、村务公开栏等普法阵地对与换届选举有关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地方政府也有责任在选举前进行充分的摸底调查,向村干部和党员、群众了解村情民意以及对换届选举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掌握换届前的基本情况,及时向换届选举指导机构反馈农村基层组织动态,为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决策提供重要的基础信息。地方政府有责任调解选举冲突和纠纷,发挥各村级人民调解员的作用,及时做好潜在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对不良倾向和苗头性问题及时采取措施。
实践表明,我国地方政府为乡村民主选举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一些地方政府能为乡村民主选举提供优良服务,维护选举秩序,保障选举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而一些地方政府则缺乏为乡村民主选举提供优质服务的意愿和能力。一方面,作为国家权力的地方代理机构,地方政府必须执行国家政策。然而,由于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资源有限,但其处理的公共事务却异常复杂,这使得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能力为乡村民主选举提供优质服务。另一方面,在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也缺乏为乡村民主选举提供优质服务的意愿。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以CDP为中心,乡村民主选举在绩效考核中并不具有突出位置,这无疑会弱化一些地方政府为乡村民主选举提供优质服务的动机。
(三)我国乡村民主选举暴力的发生。还源于一些媒体的“失语”。更与公民社会不发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相对于其他民生领域而言,我国传媒对乡村民主的关注是相对匮乏的。我国乡村民主启动以来,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三次伟大尝试,“为中国未来民主化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和扩展,其存在的各种问题得以彰显,推行村民自治的难度也超出一些人的想象。推行村民自治的步履维艰,使得一些人对村民自治的未来充满忧虑,对待村民自治的心态经历了从“大喜”到“大悲”的转变。
我国传媒对待村民自治的态度变化也呈现类似的轨迹。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大众传媒在旧家推动村民自治这一政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国家意志的表达者、模范典型的塑造者以及政策法律的普及者。在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大众传媒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大众传媒面临着矛盾:一方面,为了继续推动改革,本着职业规范和社会良知,应以客观中立的姿态,正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为了继续推动改革。产生正面激励。则应对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回避,以减少进一步改革的阻力,增强人们对改革的信心。
选举暴力作为我国乡村民主发展中出现的一个问题,较少受到传媒的关注。曝光乡村民主发展中的选举暴力问题不利于强化改革的共识,也不利于维持公共部门的政治合法性。因而,对于我国乡村民主发展中存在的诸如选举暴力问题,我国传媒一般采取回避的态度。正是这种回避,使得选举暴力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选举暴力在传媒“失语”的状态下得以滋生发展。同时,由于发展时间短,发展空间有限,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对乡村民主选举的介入是相对有限的,公民社会组织为村民自治提供服务的能力也是相对有限的。由于缺乏选举观察团等组织的介入,同时也由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相对缺位,乡村民主选举暴力逐渐滋生和扩散。
三、运作方式
在我国乡村民主选举中,一些地方的候选人正利用暴力这一资源来获取权力,通过语言威胁、身体伤害以及破坏选举设施的方式来赢得选举的胜利。
(一)我国乡村民主选举暴力运用的第一种方式是语言威胁。
暴力并不一定意味着物质性的武力,暴力也以语言的形式存在。在我国乡村民主选举中,以语言威胁方式表现的暴力大量存在。例如,前述福建省西洋村案例中,一些选民遭到不明身份青年的语言威胁:“如果山哥(余根杰)当选不上本届村主任,杀了你全家”,很多受到威胁的选民不敢出门投票。2005年10月19日,哈尔滨市松北区万宝镇某村第七届村委会开始换届选举。村民寇某说,自从第一轮选举开始。候选人刘某就安排了一些打手来到榛柴屯、万宝屯两个投票点。在榛柴屯投票点,另一位候选人田某发现有人重复投票,在制止这种行为时遭到殴打。刘某还嚣张地说:“谁和我争,我就把谁腿打折!”看到这种情况,另两位候选人相继退出选举。这些足以说明,语言威胁是我国乡村民主选举暴力存在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在一定条件下会起到一定的效果。
(二)我国乡村民主选举暴力运用的第二种方式是直接的身体伤害。
身体伤害是暴力运用最为典型的一种方式,通过身体伤害往往能够达到候选人获得权力、破坏选举、报复等目的。前述辽宁赵营子村“选举血案”就是这种身体伤害的典型案例。直接身体伤害这种暴力形式在我国乡村民主选举中还有不少案例。比如:2001年,河北省沧州北关村村委会副主任庞振岭为了争夺权力,两次蓄谋用炸药包炸死村委会主任庞凤歧未果,又与儿子密谋,指使刑满释放人员冯某杀害村委会委员庞瑞龙。2001年1月24日晚,冯某用猎枪将庞瑞龙的妻子强某打成重伤。2002年初,山东省淄博市罗村镇下黄崖村举行三年一届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下黄崖村地处全国重工业基地淄博市,从1988年以来王家奎就是村党支部书记。选举原定于2002年1月20日举行,后来推迟到了28日。这期间,原是村办企业、现归王家奎本人的淄博锦川水泥厂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兼任厂长的王家奎在会上讲,本厂职工投票时。要在选票上写上王家奎的名字,也要写上自己的名字。谁要是敢不投他的票,统统开除出水泥厂,村里也不安排工作,这些人的亲人也别想在水泥厂和村里找到工作。与此同时,他给所有水泥厂职工都发了一箱白酒、一桶花生油,或一桶精品酱油和一捆醋。1月28日选举那天。王家奎带着一帮小青年,开着三辆车来到选举现场。村民常京成对王的行为非常不满,想让他难堪,就当着大伙的面质问他:“村里发东西,怎么没有我的?我是军属呀。”王家奎说,东西是我的钱买的,爱给谁就给谁,你管不着。常京成问:“你给村民发油、发酒算不算贿选?你带着这么多人来威胁村民选举算不算违法?”王家奎气得当时就要打常京成,被他的妻子拉住,只能恶狠狠地指着常京成的脸说,过后再收拾你!6月25日下午,常京成就遭到村支书兼村主任王家奎的猎枪射击和暴打,造成全身40处中散弹,一条肋骨骨折,左肾挫伤,头部皮肤裂伤,缝了20余针,险些丧命。2009年,在河北省南范庄,农民周长顺抱怨村里举行的选举不公平。几天后,有人发现周长顺死在家中。周长顺60岁的妻子和儿媳也惨遭杀害。周长顺不到3岁的孙子后来也被斧头砍死在了医院里。
(三)我国乡村民主选举暴力运用的第三种方式是破坏选举设施。
如果说语言威胁和身体伤害针对的是选举中的行动者,那么,我国乡村民主选举暴力运用的第三种方式则针对的不是行动者,而是行动者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破坏的是选举的设施。例如,2008年4月。广东阳江阳春市潭水镇三星村村委会主任冼大越、双溪村村主任冼业威在换届选举中。在计票现场对选举结果的合法性产生怀疑,遂抢夺选票试图销毁,其过激行为导致选举工作被迫中断。潭水镇纪委给予冼大越、冼业威党内警告处分。2014年9月16日,安徽太湖县徐桥镇西村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村民徐某等人趁现场发生争执之际,将选举箱损毁、选票弄混,将会场的话筒摔坏,电闸关闭,并侮辱、恐吓选举委员会成员,导致选举中断。2010年12月19日,江苏连云港市云台乡丹霞村正式选举村主任。候选人有两名,一名是谢金发,另一名是倪爱华。下午6时许,投票、唱票基本结束。全村参选人数是3807名,谢金发得到1841票,倪爱华得到1789票。这时,大会工作人员招集候选人对140多张部分打“√”的选票回头复议确认。当续唱约20张选票时,倪爱华看到于己明显不利。当即用电话联系在门外的亲友强行跳窗入室,倪将续唱的20余张选票从桌子上抢走,交给妻子江顺丽,倪的小姨江顺华则从工作人员李训碧手中抢走剩余的选票。
四、治理机制
选举暴力正成为我国乡村民主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暴力是由敌意驱动的、故意造成伤害的行为。”选举暴力破坏了民主选举的公正性,“严重干扰了选举,不利于农村的稳定”,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治理。
(一)治理乡村民主选举暴力,需要提高村民的公民意识。
“在长期封建社会历史上,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农民翻身当家作主人。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村民的公民意识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整体说来,村民的公民意识仍比较淡薄。“农民与居民相比,对国家和政治事务的参与程度较低,对政治活动也比较冷淡,农民政治参与的形式比较单调。”选举暴力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村民公民意识淡薄的结果。为了赢得选举,一些候选人采取贿选等欺诈方式,一些候选人公开运用暴力,威胁竞争者,威胁选民。由于公民意识淡薄,一些选民接受选举贿赂,出售选票换取钞票,以牺牲公共利益的方式谋取个人利益。面对选举暴力,一些受害者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不懂得运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这些都足以说明,我国乡村民主选举暴力的发生,和村民公民意识淡薄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提高村民的公民意识成为治理乡村民主选举暴力的一种可行路径。为了提高广大村民的公民意识,要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提高乡村民主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水平,使村民真正参与到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中来,通过政治参与来提升政治效能感。
(二)治理乡村民主选举暴力,需要运用压力型体制的优势,提升地方政府服务选举的能力。
实践表明,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多种资源的支持。公民教育的长期性与治理乡村民主选举暴力的紧迫性之间存在张力。为了缓解二者之间的张力,一种可行路径是发挥压力型体制的优势,强化地方政府服务选举的责任。我国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存在压力型体制的特征,在压力型体制下,“为了完成经济赶超任务和各项指标,各级政治组织(以党委和政府为核心),把这些任务和指标,层层量化分解,下派给下级组织和个人,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在我国,压力型体制得以顺利运行,是因为我国政府实行的依然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各层级政府之间,下级要服从上级,地方要服从中央。在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内部,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具有掌握部门资源的实际权力。党管干部原则使上级政府很容易借助党的组织体系把某些重要任务提升为“政治性”工作,以对负责人职位的改变作为督促其完成的手段。因而,我国乡村民主选举暴力的治理,当下可行之策是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将乡村民主选举质量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进而改变一些地方政府不作为的现状。
(三)治理乡村民主选举暴力,需要规范乡村民主权力。
从选举暴力的发生逻辑看,候选人在选举中运用暴力是为了获取权力,获取权力是为了为个人或团体谋取利益。因而,治理乡村民主选举暴力,需要规范乡村民主权力,使民主权力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少数人利益。治理乡村民主选举暴力问题,不仅应关注权力是如何获取的,而且更应关注权力是如何运用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民主选举并不足以确保民主治理。为了理解乡村中国的民主化,我们不仅需要追问程序是如何被引入和提升的,而且要追问村委会是如何和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其他行为主体互动的。”规范乡村民主权力,关键是要做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协调发展,防止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流于形式。要搞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严格遵守村委会选举的基本原则,严禁暗箱操作。要防止一把手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击报复,防止滥用职权。要实行村务公开,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相关人员的座谈会议,接受村民对村委会及其成员工作的评议,倾听村民的批评和建议。要选举产生民主监督小组,由其具体负责监督工作,同时由法律法规赋予村民举报权,通过村民举报对村委会及其成员的工作实行及时而有效的监督。
(四)治理乡村民主选举暴力,需要充分合理利用网络这一信息传播和扩散平台。
在我国传媒对乡村民主选举暴力事件报道收紧的条件下,互联网是乡村民主选举暴力事件信息传播和扩散的重要公共空间。乡村民主选举暴力的发生,不仅因为选举暴力的使用者在一定程度上可实现其预期,而且也因为选举暴力的“公开”运用被遮蔽,使得施暴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受暴者的冤屈在公共领域得不到申诉。相对于其他传媒而言,互联网发布信息门槛比较低,信息传递更为迅速,监管审查相对宽松。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具有自媒体的特点,即民众可以成为新闻的采编发布者。正是互联网的这些特点,使得它可以在呈现乡村民主选举暴力事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如上分析表明,选举暴力是我国乡村民主发展面临的一个难题,需要集群体智慧来治理。从学术的角度看,研究选举暴力的目的不是去揭示民主发展的阴暗面,更不是要否定和反对民主,而是要正视民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理性而客观地评估民主发展的现状,改进民主,优化民主,提升民主的质量。实际上。选举暴力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民主建设中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早在18世纪的英国选举中,暴力和恐吓就被视为“赢得选举最有效的手段”。值得庆幸的是,选举暴力问题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选举暴力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和治理。这既为我国应对选举暴力问题提供了有益经验,也为我国探索新的选举暴力治理模式提供了重要参照系。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