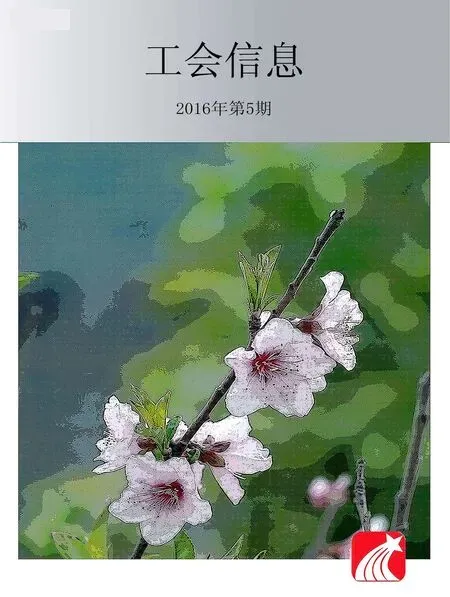儒学大师曾国藩与西学洋务
文/舒彦
儒学大师曾国藩与西学洋务
文/舒彦

曾国藩
曾国藩推行洋务时,虽说已是他的晚年,但他是清朝洋务活动的最早倡导者,也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实践者。曾国藩一生,从理学家到洋务派,从一个封建士人到封疆大吏、名将名相,由治学、修身转而治军、治国,从头到尾走完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
曾国藩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为什么能够成为引进西方科技与近代文化的带头人呢?为什么能成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与开创者呢?原因在于:曾国藩作为理学的最后一位代表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其思想并非全部属于封建主义。除了自觉维护封建主义的一面之外,还不自觉地对封建之道有所舍弃,有所改变;尤其是在文化精神上,迈出了由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蹒跚步履。他既不是西方文化不分良莠不分一概拒绝的封建顽固派,也不是不顾中国国情对西方文化一律照搬的所谓“全盘西化”派,而是主张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中体西用”论者。曾国藩对中西文化,都是持扬弃态度,对彼此打车长短有个清醒的认识,强烈的民族意识使他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主体地位,而辅以西方文化。曾国藩在高扬“卫道”旗帜的同时,把传统儒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发掘出来,形成“义理经济”合一的新格局,给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恢复了其号召士林、维系人心的作用。正是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长短有透彻的了解,他就能够吸取并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能够引进西方科技和近代文化。
可以说,曾国藩的思想开始了由古代文化精神向近代文化精神的转变。这种变化的基本取向是:从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推动自身的变革;其核心思想是:师夷长技与整饬自身。曾国藩认为:西方列强既是侵略者,又是老师,一身二任,只有将西方技力内化为中国自身的实力,才能抗拒侵略。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
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儒学在变,儒学也可以变。如果光从思想本身看,变化是从龚自珍特别是魏源开始的,但是真正付诸行动,或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实际的社会生活,却与洋务运动的领袖们的言行密不可分。而后,洋务派的实践却催化着儒学的变化,“中体西用”学说似成新儒学之端倪。虽未成,却犹如宋明时期,儒学与佛学融合而成理学。
曾国藩作为晚清重臣,其历史责任是挽清廷狂澜于既倒,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矛盾中为当时政权寻求一条新的出路。曾国藩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站在时代潮流的浪尖上,以期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在当时,要突破旧有藩篱,引导中国前进,就必须破除传统观念中的夷夏界限,既尊重中国旧有的文化传统的价值,又能充分吸收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和科学创造,使古老的中国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注入生机,焕发青春。就此而论,曾国藩绝不是顽固的守旧派,因为他既看到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精神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又看到西方科学技术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所必须倚重的东西,而不应盲目地排斥,相反应当努力学习和掌握。对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曾国藩认为不应作急功近利的理解,否则,虽可使中国得纾一时之忧,有利于中国最直接、最近期的利益,但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欲富强,必须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兴办近代工业,只有中国自己的工业基础获得充分的发展,才能彻底摆脱外来势力的压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期永远之利。
曾国藩不仅看到了西方的长处,而且敢于承认,敢于学习。因为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政治家,学习是为了用以解决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主要并不是理学,而是经世之学。他着眼于政府统治阶级之最高利益和兴衰安危,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派的兴旺发达,因而他治学向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都主张全盘接受,融会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习洋人之长,以强化自身”。他虽然出于儒者的本质及对清王朝的尊重,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然而却又不得不说:“独火器不能及也。”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备受“外夷”欺凌,原因何在?曾国藩认为,关键的原因是中国的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与外国有着很大的差距。他亲眼目睹外国侵略者凭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横行无忌,只要在中国沿海架上几门大炮,就可以威逼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且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多借洋人之器,洋人之力,亦取得成效,还尝到了不少甜头,从而增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自信心。
曾国藩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外交必与自强紧密结合。他认为要想自强,就必须通洋务、办洋务。曾国藩谈论洋务的地方很多,而最集中、最典型者则莫过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与同僚宾友的一段谈话。《手书日记》载:“与幕僚诸君畅谈,眉生言及(夷)务。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日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功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正确看待外国侵略问题,即怀德弃怨、化敌为友;一是如何应对外国侵略,即自我振作,师夷长技。实际上包含着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的内容,而内政方面又包含整顿吏治与兴办军工科技两个要点。于此可见,所谓洋务,是由夷务一词转化而来,实际上不仅指外交事务而言,也不仅指造船制炮等西方科学技术,而是包含着如何对待和处理外国侵略问题的全部政策与策略。
曾国藩早期洋务运动是以兴办近代军事工业、训练新式军队、培养洋务人才为主要内容。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为了扭转敌强我弱、被动挨打的困境,曾国藩采用外国军火,认为:“购买外国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1860年底,曾国藩就借助洋兵镇压太平军一事上奏咸丰皇帝,奏折中提到以后可以学习外国技艺、造船制炮,并可收到长久好处。1861年湘军攻占安庆后,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与子弹火药,次年又试制轮船,并制造出中国第一艘木壳火轮“黄鹄”号,后又试制小火轮船。1862年他又提出购买外国船炮,为救时之第一要务。购来之后,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必定成为官民通行之物。”他还提出:“自强之道……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曾国藩的主张得到了恭亲王奕訢及李鸿章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响应。1863年造成“黄鹄”号轮船后,曾国藩为了扩大规模,改进技术设备,以制造更大、更先进的轮船,派容闳赴美国采购机器。1865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容闳回国,将所购机器并入江南制造总局,以后发展为国内最大的兵工厂。1868年曾国藩、李鸿章奏拨专款设立船厂,专门从事新轮船试制工作,将江南制造局迁址扩建,并附设新式学堂和翻译馆,培养洋务人才,使之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好的综合性军事工厂。为了解决养轮乏资的问题,他曾提出将新造商轮租给可靠商人使用的主张,遂成官督商办与轮船招商局之滥觞。除了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购买制造先进武器,曾国藩还积极学习外国的练兵、设防之法,力争做到不打无准备之战。即使到了晚年,曾国藩还念念不忘练兵大计。他曾经提醒西太后:“兵是必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
曾国藩在实践中认识到:“讲求洋务,为当今第一艰巨之事。”而“洋务之棘手,在于人才之匮乏,人才之罕见,由于事略之不明”。于是他从1867年开始,先后聘请外国教师与中国科学家李善兰、徐寿等人筹建翻译馆、印书处,介绍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并积极创办洋务学堂,培养出了一大批外交和科技方面的人才。为了培养居室、尤其是海军需要的人才,1870年曾国藩同意容闳建议,会同李鸿章奏准派遣四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积极筹措经费,成为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首创者。
曾国藩办洋务,目的是力图把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胆设想变为现实。虽然他作为理学大师,满口君臣伦理之道,口口声声强调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事实上他已经认识到中华文明诚然具有数千年灿烂历史,可是在世界进步的洪流中已然落后了一大截。曾国藩从意识到落后,进而以实际行动来图强,使中国迈出了学习西方的第一步。这种变化,对于一个效命于历来夜郎自大、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的重臣来说,的确十分难能可贵。正是曾国藩及诸多洋务派地方大员的不懈努力,中国才终于迈出了这一大胆而艰难的一步,进而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经济、科技、军事的新时代,才有了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旨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才有了孙中山以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王朝,致力实现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伟大社会变革。
曾国藩在兴办军工科技方面所做的具体事情并不太多,他的业绩既不能与李鸿章相比,甚至不能与左宗棠相比。加以左宗棠一贯主张抵抗外来侵略,有收复新疆之功,故其历史形象远比曾国藩为好。然而,无论左宗棠还是李鸿章,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与曾国藩相比。其原因非他,要在开风气之先。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的是他,第一个早出轮船的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的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的是他,第一个上奏促成容闳实现派遣留学生计划的也是他。真可谓: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洋务运动功不可没;在洋务运动中,曾国藩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