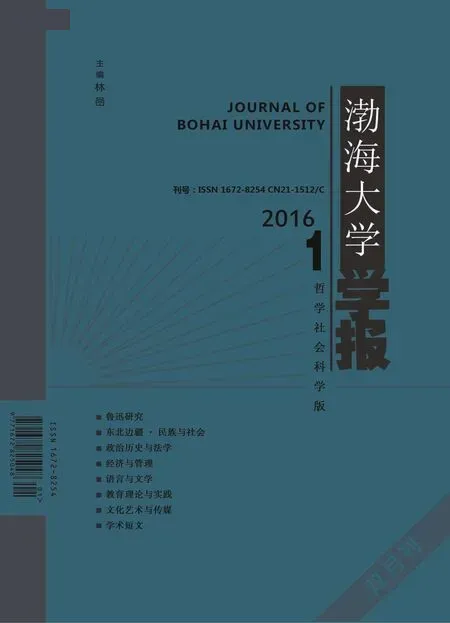麦克尤恩长篇小说中能指与所指的背离
刘 江 (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麦克尤恩长篇小说中能指与所指的背离
刘江 (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摘要:麦克尤恩喜欢用一个名词或介词短语来作为小说的题目,但其所要表达的内容却远远超过题目的表面意思。“能指”与“所指”之间形成的张力,使读者认识到题目的表面含义并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真正意图,在其表面之下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内涵。
关键词:麦克尤恩;题目;能指;所指
伊恩·麦克尤恩1948年出生在伦敦小城爱德肖特(Aldershot),与马丁·艾米斯(Martin Aims)、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并称为英国文学“三剑客”。1975年麦克尤恩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合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以其独特的构思和叙事风格,获得巨大成功,并夺得毛姆文学奖。其中对暴力、性爱以及乱伦等大尺度的描写,震惊了文坛;但老麦所写的决不是地摊上出售的色情文学,他是借此来书写青春的欲望与孤独,从而进一步挖掘人性中的黑暗。
“能指”和“所指”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两个术语,“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1]即“能指”指的是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的就是语言所反映出的事物概念。在此基础上,后人对索绪尔的这两个术语多有发展,之处“能指”与“所指”的相互联系存在着随意性,“所指”不依附于特定的“能指”,而一个“能指”也可以有多个“所指”,从而具有多种含义。在麦克尤恩的小说中,作者往往喜欢采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反讽形式,使“能指”指向“所指”的反面,或使“能指”具有多个阐释意义。从而使读者认识到表层文本的表面叙述并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真正意图,在其表面之下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内涵。
纵观麦克尤恩的长篇小说的题目,可以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事物”题目,如《黑犬》《无辜者》《日光》《时间中的孩子》《甜牙》;第二类,“地点”题目,如《水泥花园》《阿姆斯特丹》《在切瑟尔海滩上》;第三类,“时间”题目,如《星期六》;第四类,“事件”题目,如《只爱陌生人》《爱无可忍》《赎罪》。麦克尤恩喜欢用一个名词或介词短语来作为小说的题目,但其所要表达的内容却远远超过题目的表面意思。
一、“无辜者”与罪恶
《无辜者》(The Innocent)是麦克尤恩又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小说,整部小说融爱情、政治、悬疑、推理等多种元素于一体。故事讲述了一个英国谍报人员伦纳德与德国女子玛利亚相爱,却遭到玛利亚前夫的纠缠,无奈之下将其杀死,并藏尸于伦纳德窃听俄方情报的隧道中。恰在此时,谍战失败,隧道被俄方发现。伦纳德逃回英国,从此与玛利亚天各一方。多年之后,当他故地重游时,收到了玛利亚写给他的信,他才弄清了当年的真相,他由于受到上司鲍勃的包庇才能逃脱罪责并顺利回国,而玛利亚也在自己离开之后嫁给了鲍勃。时间流逝,沧海桑田,伦纳德踏上了寻找玛利亚的道路,但两人是否还能回到曾经,给读者留下了不尽的悬念。
“innocent”一词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中给出的解释如下:1.无辜的;清白的;无罪的。2.无辜受害的;成为牺牲品的。3.无恶意的;无冒犯之意的。4.天真无邪的;纯真的。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完全符合这四个解释。
伦纳德刚出场的时候,与人相处的方式完全是英国式派头。
伦纳德以他那有条不紊的方式,按照问题先后的次序。逐一回答了那些问题。“不,我还没有结过婚。甚至我还从来没有接近过婚姻方面的问题。我还和父母住在一起。我在伯明翰大学上的学,学的是电子。我在昨晚发现,我喜欢喝德国啤酒。我心里想的是,如果你想请人来看看你的那些雷达装置,那么……”
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伦纳德回答问题的方式是“一丝不苟”的,而且非常严谨认真,这正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的显著特点。从他的介绍中也可以了解到,他的人生也是一板一眼,按部就班地运行着。此时的伦纳德绝对是一个“天真无邪的、纯真的”人。战争在他心里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假设,他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构想。然而,如此“纯真”之人却意外成为了分尸者,同他一样善良的玛利亚成了他的帮凶。他们感觉到“他们就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不对的。”[2]但一切都迫不得已,因此,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可是暴力反抗暴力后,沾满鲜血的两人,真能如此“无辜”吗?伦纳德愈发暴躁,他不再被玛利亚所吸引,即使在一起,两人也总是躲躲闪闪、争论不休。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懊悔,从而对自身的道德判断和伦理标准重新审视,不堪良心的折磨,伦纳德始终想一走了之,逃避开自己的罪责,最终他如愿以偿,可他与玛利亚也不得不分道扬镳,抱憾终身。
这一切使两人失去“无辜者”的身份,也使两人的爱情就此终结。上面的引文,不仅表现了伦纳德纯真的一面,也表现出他的拘谨、古板和不自信。因为“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那些英国人的特征,可不像上一代那样,使人觉得那是反映出一个人心里踏实的派头。它却使他觉得自己因此而显得脆弱稚嫩,易受伤害。而那些美国人正好与此相反。他们对自己深有信心,所以处处显得落落大方,无拘无束。”[2](13-14)故事背景描述的是二战后英美两国结成同盟,窃取苏联的军事秘密。可是两国实力悬殊,英国实力被削弱,只能“在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夹缝中生存。”[2](6)伦纳德的不自信,也是英国民族的写照,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英国已再不能主导大局,可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又让他们处处表现得谨慎有理,彰显他们已经变得滑稽可笑的“绅士风度”。随着故事的发展,交代出了苏联早已发现英美两国窃取情报的地道,苏联并未声张,只不过是在故意消耗美军的力量。英国在这场较量中自然成为了“牺牲品”。作为英国谍报人员的伦纳德,与英国一样摆脱不了成为美苏两国争霸的“牺牲品”。“看似无辜的人未必真的无辜,在政治行为的运转中,无辜与罪恶并没有绝对的界限。”[3]
二、“甜牙”与诱惑
《甜牙》(Sweet Tooth)是麦克尤恩在2012年推出的又一部力作。这部小说是麦克尤恩第一次将女性作为中心人物的小说,整个故事基本上是通过女主人公塞丽娜叙述出来的,从她的视角出发来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塞丽娜在大学读书期间,得到恋人坎宁教授的培养,而加入军情五处。之后,塞丽娜接受了“甜牙行动”,在这项任务中,军情五处会以隐蔽的方式为他们选中的作家提供经济资助,希望他们所写的作品能够符合英国政府提出的意识形态要求,从而影响大众思想。塞丽娜在这项行动中的主要任务便是引诱作家汤姆·黑利接受这项资助。然而,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塞丽娜与汤姆深陷爱河,自此,塞丽娜也开始了在间谍与情人双重身份间的挣扎。读到小说结尾,麦克尤恩再一次给予我们震撼,汤姆早已知晓塞丽娜的身份,他让自己同塞丽娜一样扮演着间谍与情人这两种角色。
“sweet tooth”在英语中本指“喜吃甜食的人”,那么甜食便对这些人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在小说中,“甜牙”是塞丽娜执行的特工任务的代号,金钱与美女对于汤姆这样的作家来说同样具有无限的诱惑;对于塞丽娜来说,事业有成、收获爱情,是其努力奋斗的目标。不管是对甜食还是对金钱、爱情等的渴望,都可以看作是欲望对于人们行动的驱使。欲望的无限扩大和升级使塞丽娜和汤姆陷于两难的境地而无法自拔。
塞丽娜作为叙述者,通过第一人称叙述将自己的所见、所感叙述出来,而在其叙述中存在着大量“双声话语”现象,这更将塞丽娜矛盾、苦闷的心情充分暴露出来。“双声话语”是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提出来的,所谓“双声话语”指的是“话语在其中有着双重指向——指向言语对象,把它作为通常话语;以及指向别人话语、他人言语。”[4]“指向别人话语、他人话语”强调的不仅仅是话语中的言外之意、话外之音,而是应该注意到“任何一种言语只要被纳入双声语的范畴,它便不仅要行使其表意功能,同时必须体现出另一种声音的存在;它所说出的每一个词句,都应针对另一种显在或潜在的声音而发,都要具有引出另一种声音与之争辩的作用。”[5]
塞丽娜并不是出于喜爱才来到军情五处工作的,她只是为了实现情人坎宁对自己的期望才来到这里。她对这里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所以当她得知自己只能做低级文员的时候,她才会如此沮丧。
甚至在跟琼道别之前,我已经打定主意,我不想要这份工作。这是在侮辱我,一个低等文秘的职位,薪水却只有此类工作惯例的三分之二。如果当个女侍应,加上小费我的收入还能翻倍呢。他们自己留着这职位好了。我会给他们留张条子的。
这段独白发生在塞丽娜得知自己并不能被招募为女特工之后,她在拼命地说服自己放弃这份令她失望的工作。她不停的与自己“对话”,仿佛在回答另一个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并与其争论。我们可以把这段独白展开为如下的对话形式:
另一个塞丽娜:你打算怎么做呢?
塞丽娜:我已经打定主意,我不想要这份工作。
另一个塞丽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塞丽娜:这是在侮辱我,一个低等文秘的职位,薪水却只有此类工作惯例的三分之二。如果当个女侍应,加上小费我的收入还能翻倍呢。他们自己留着这职位好了。我会给他们留张条子的。
通过上面的对话,可以看到对话各方在一个声音里纠缠混合,于是就出现了塞丽娜那段自我表述。在这假想的问答中,我们可以看出塞丽娜内心的焦虑、无奈。而在第一段问答中,塞丽娜坚决要放弃这份工作。而通过阅读整个故事,我们知道,在当时,来自各方的压力都迫使塞丽娜急需这份工作。这不禁使读者同“另一个塞丽娜”一样对此产生疑问:塞丽娜为什么想要这样做?在第二段问答中,塞丽娜强调这份工作对自己是一种“侮辱”,因为尽管工作体面,但收益甚微,而且只有“工作勤勉、提拔及时,那我也许能升到文职助理。”[6]这份工作使塞丽娜感觉卑微、无望,与她的特工梦想相去甚远。尽管对这份工作如此不满,塞丽娜却只是想到“给他们写张条子”,而不是当面拒绝这份工作。如果塞丽娜真的只“写张条子”来拒绝这份工作,那么这样的拒绝自然没有当面拒绝强硬,纸条甚至有可能未被看到,于是就会给塞丽娜反悔留有余地。这样看来塞丽娜并不是真心想要拒绝这份工作,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她渴望这份工作。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塞丽娜如此复杂、矛盾的情感呢?主要在于父母对其职业前景的关注。在小说伊始便交代了塞丽娜酷爱文学,想要报考英语专业,而这遭到了母亲的极力反对,认为她“险些就要荒废人生了。”[6](4)希望她“一定得在理工科或者经济领域里干出点像样的事业。”[6](4)自此,“像样的事业”便一直是塞丽娜热心追逐的目标,而这份工作恰好符合母亲的期望。不仅如此,这份工作还能为她赢得父亲的关注,这对塞丽娜来说是极大的诱惑。父亲笃信宗教,潜心于自己所热衷的宗教事业,对塞丽娜姐妹的态度十分冷漠,于是两姐妹总是想尽办法吸引父亲的注意。而这份体面的工作正好能博得父亲对自己的青睐,所以塞丽娜才会在拒绝时有所犹豫。此外,对于坎宁强烈的爱情,也是造成塞丽娜举棋不定的重要原因。塞丽娜认为自己理应按照坎宁为其设计的人生轨迹前行,不管是加入军情五处,还是之后自己对工作的尽职尽责,都是“向我爱过的男人致敬,是我应尽的职责。”[6](68)这些无形的因素都迫使塞丽娜去接受这份自己并不满意的工作,以期会获得更多的认可。
出于以上种种原因,塞丽娜一直在寻找能够展现自己的机会,所以她才会在接下“甜牙行动”时如此兴奋,“我可不能后退,我渴望极了。”[6](125)正是塞丽娜无限膨胀的欲望,使其又一次卷入对于新身份认可的烦扰中。
这事根本无法避免:如果我不说,那就会有别人告诉他。我那么懦弱,就必然要接受这样的惩罚。这下我会显得多么可恶多么可笑啊,被迫大白于天下,竭力用诚实的口气说话,拼命为自己开脱。亲爱的我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爱你。我害怕失去你。哦,不错,真是天衣无缝。我哑口无言,他丢尽颜面。我恨不得直奔火车站,赶上下一班去伦敦的火车,从此淡出他的人生。好啊,让他独自面对风暴。这样岂不是更懦弱了?话说回来,以后他也不会再想让我靠近他。
塞丽娜的身份此时已被媒体曝光,汤姆接受军情五处资助的事情自然也要大白于天下,两人的爱情在这时已走上了绝境。而在这段独白中,塞丽娜首先极力想要将自己伪装得冷静、镇定。然而伪装的冷静、镇定反将塞丽娜的话语不断拉长,更为直接地暴露出内心的恐惧、慌张,她并不是将这些话语指向他人,而是转向自己。塞丽娜要将刊登着这些内容的报纸拿给汤姆,她告诉自己:“这事根本无法避免。”她在自我鼓励,她要根据事态的发展进行表演,作出正确的选择。但是冒号之后,作为解释说明的内容撕毁了她的伪装,暴露了她真实的想法:她希望没有人告诉汤姆真相,这样她就不必去面对可能发生在他们之间的对峙。之后她虚拟出自己与汤姆的对话,对汤姆的言语进行模仿,虽然只是猜测,但塞丽娜为汤姆选择了一种带有嘲讽的语气来回答自己的解释。此时的声音与塞丽娜之前佯装冷静、镇定的声音不仅不能融为一体,反而互相矛盾,这更加暴露了塞丽娜焦躁不安的内心世界:她惧怕自己预期的情况真的发生。最后,从塞丽娜与缺席的应答者之间的问答中可以看到,塞丽娜决心与汤姆并肩迎战。这也恰恰反映出了塞丽娜言语前后矛盾的根本原因,就是她对汤姆的爱。正因为她渴望获得汤姆的认可,希望能够与汤姆名正言顺的在一起,所以她才会患得患失、焦躁惶恐。
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塞丽娜渴望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以此获得他人对自己的认可。而随着欲望的不断胀大,塞丽娜被卷入了一段新的关系中,自此,她便具有双重身份:间谍与情人。两种身份如同甜食一样,对塞丽娜充满了诱惑。然而并存的两种身份只能使塞丽娜的内心时时充满了矛盾、焦虑与痛苦。从而与汤姆的关系陷入僵局之中。
三、阿姆斯特丹与“幸福”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是用地名作为小说的题目,它是荷兰的首都。荷兰以其开放而闻名世界,被称为“世界性都”。正是在这样一个开放的国家,“安乐死”首先被合法化。在互联网中是这样定义“安乐死”的:“‘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从“安乐死”被采用的本意来看,是应用于医疗中,帮助病人减轻痛苦,让人有尊严地死去。但在小说中“安乐死”却成为了两位好友谋杀对方的手段。
莫莉的死让弗农和克莱夫两人对不尊严的死亡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于是两人订下了这份“死亡契约”。克莱夫祈求弗农:“在这个国家做这种事,是违法的。假如你同意,我也不想让你触犯法律。但是办法有的是,地方也有的是。到了那天,我想让你用飞机把我送到那儿。”[7]而且克莱夫的“千禧年音乐会”也将在阿姆斯特丹举行,那么这里就是两人谋杀对方的首选了。克莱夫提前来到阿姆斯特丹打电话联系到“那位高明的医生”,编造好友的病情,以使自己的动机看起来具有合理性。医生不仅为他解答了所谓的“治疗事宜”,还提供了如何让对方服用的方法,也就是让克莱夫的谋杀设想具有可实施性的方案。而弗农也以克莱夫丧失理智为由,将这套把戏重新上演了一遍。“医生”在他们两人的谋杀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难怪事后加莫尼和乔治做出这样的批判:“事实是,这儿有一些不负责任的医生,把有关安乐死的法律推至了极限。他们大多数人通过杀死雇佣者的年迈亲戚来赚钱。”[7](186)“安乐死“的实施是要经过正规的法律诉讼程序,而且一定要经过反复考虑,一再获得病人的认可,才可以实行。然而,法律对克莱夫和弗农本人是否自愿接受“安乐死”并未予以干涉,而且都是在两人已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下,签署他们的“医疗协议”。不难看出,作者在这里对荷兰医疗体系中的漏洞大大嘲讽了一番。在阿姆斯特丹这个繁华的城市中,开放本应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然而,对死亡的放宽,却违背其本意,成为人们互相残杀的方式。本应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却成为凶杀中真正的操作者,阿姆斯特丹也成为人们规避罪责,摆脱道德束缚的绝佳谋杀地。
更具嘲讽性的是,克莱夫在昏迷之际,幻想看到了莫莉,并且对他的作品大加赞扬,而且莫莉的新情人,克莱夫在事业上的竞争对手兰纳克,是其崇拜者。弗农在昏迷中,看到莫莉与弗兰克在一起,在现实生活中,弗兰克在报社中一直觊觎他的主编位置,还出卖、设计他,使他失去工作。而梦中,弗农仍是主编,弗兰克正卑躬屈节的向他借钱。在梦境中他们都获得了事业上的满足,却殊不知,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签下的是对自己死亡的判决。两个人的尸体被冷清地停在一间小小的停尸房里,无人问津,而停尸房外面的阿姆斯特丹依然繁华、喧闹。克莱夫本想在阿姆斯特丹举行“千禧年音乐会”,迎来他事业上的顶峰,然而这里却成为他事业的终结,他的音乐会在他死后被取消了,还被人们指出其抄袭贝多芬的《欢乐颂》,这对他是何其讽刺。
四、“陌生人”与慰藉
《只爱陌生人》(The ComfortofStrangers)还可译为《陌生人的慰藉》。从题目来看,就给读者留下巨大的悬念,为何只爱陌生人?要像陌生人寻求怎样的慰藉?“comfort”在英语中除有“慰藉”之意,还有“舒服、安逸、舒适”的意思,看到题目,读者容易主观认为作者可能讲述的是一个温馨的故事,可能是主人公陷入困境,从陌生人那里得到了帮助。然而,温馨路线从不是麦克尤恩的风格,这个故事依然延续“恐怖伊恩”的讲述方式。
罗伯特和卡罗琳深陷S/M性爱关系中无法自拔,尤其是卡罗琳在这段关系中扮演着受虐狂的角色,还兴奋地享受着变态性爱带来的快感。在她与罗伯特感情出现危机时,她提出将科林作为性幻想的对象,以此来挽救他们濒于崩溃的婚姻。因为对于受虐狂来说“性欲是情感宣泄的最常用的手段之一,所以他也很容易给予它过高的评价,会觉得性欲是万能的,它能解决一生中碰到的所有问题。”[8]卡罗琳作为受虐狂,容易对人和事物产生依赖性,她期望被罗伯特爱,因此她更是牢牢抓住科林出现的契机,借此改变她与罗伯特已经陷入僵局的性关系。她让玛丽参观偷拍的科林的照片时,坦言道:“我们重新又越来越亲近了。把它们挂在这是我的主意,这样我们只要一抬头就能尽收眼底。……你怎么都不会相信我们都编制了多少计划。”[9]此外,罗伯特与卡罗琳结婚多年却没有孩子,而心理学认为,孩子的数量是女性成为受虐狂的主要原因,尤其当罗伯特非常渴望成为父亲时,这一点便至关重要。不能生育所带来的歉疚感迫使卡罗琳长期屈服于罗伯特的暴力之下,尽管后来证明没有孩子并非是卡罗琳的过错,但此时她已深陷被虐的快感中无法自拔。来自科林(陌生人)的慰藉,使他们的生活重新焕发了生机。
科林与玛丽虽然察觉到了罗伯特夫妇的真正意图,但仍然没有能够阻止他们一步步陷入罗伯特夫妇的圈套。第一次从罗伯特夫妇家回来,他们的感情有了新的变化,“他们的做爱也让他们大吃一惊,因为那种巨大的、铺天盖地的快乐,那种尖锐的、几乎是痛苦的兴奋——就像当天傍晚他们在阳台说起的——简直就是七年前初识时体验到的那种激动。”[9](96)在隐约感觉到罗伯特夫妇的变态性关系后,他们甚至有些向往,虽然他们并未实践,但他们将想象的S/M关系讲给对方,来为两人已经趋于平淡的感情寻找新的刺激。他们再次拜访罗伯特夫妇,其实是希望通过“陌生人的慰藉”来延续这种刺激。
单看小说的题目,我们并不能获得如此多的信息,甚至我们会得出过于简单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图相反的结论。在我们细读文本后,发现一切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单纯美好,在题目这个“能指”中,蕴含着具有深刻含义的“所指”,在快乐美好的背后,隐藏着血腥、凶杀和变态等一系列邪恶因素。
参考文献:
[1]索绪尔.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02.
[2]伊恩·麦克尤恩.无辜者[M].朱乃长,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288.
[3]王悦.镣铐中的舞蹈: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与不可靠叙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94.
[4]米哈伊尔·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刘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203.
[5]黄肖嘉.论卡夫卡小说《一份致某科学院的报告》的“微型对话”特征[J].保定学院学报,2010(3):69.
[6]伊恩·麦克尤恩.甜牙[M].黄昱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48.
[7]宋艳芳.小说何为——从麦克尤恩的《星期六》看小说的功能[J].国外文学,2013(3):121.
[8]卡伦·霍妮.女性心理学[M].王怀勇,译.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9:173.
[9]伊恩·麦克尤恩.只爱陌生人[M].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48.
(责任编辑陈方方)
作者简介:刘江(1989—),女,渤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9-15
中图分类号:I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254(2016)01-009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