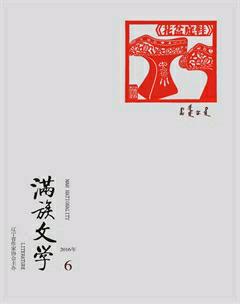友谊七十年
〔满族〕路地
1
姜涛与我之间的友谊已70年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俩结交长达70年之久,可谓友谊长存了。
我们没有经过换帖、拜把子,也不曾祭酒焚香,义结金兰;我们是在茫茫人海之中,两个孤独者偶然相遇,逐步走近的;有如一条小河,虽无惊涛拍岸,却也是爬坡过坎儿,细水长流而不息。
曾见有的朋友会面,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好生热烈,然后推杯换盏,高谈阔论一番,自当有其乐趣。我俩见面时,平静如常,有时连手也不握,他先拿给我一些报刊,然后系上小围裙下厨去了,他乐于琢磨做菜,每次都加俩菜,一荤一素,十几分钟出勺。就餐时我有固定位置,旁边放着啤酒、白酒,他不喝酒,也不让我,有时我自斟一盅白酒,啜完为止。餐桌上无话,谁先吃完谁就撂筷。
到客厅落坐,我自带茶饮,他喝开水,开始唠嗑。他是市政府的秘书长,是官员,我是省作家协会的刊物编辑,是文人,从职业上看互不搭界,但却有话可说,无论家事、友事、往事、时事,唠得不断捻儿,但从不谈他的政事。他们夫妇有早睡早起的习惯,我8时前告辞回旅馆,次日回沈阳。每次大致如此。
等我们离岗之后,再来鞍山时,就住在姜家了。
我曾与老伴老曹同来,老姜老郑夫妇陪同,姜家长子舒放,是个孝顺孩子,又是摄影家(省摄影家协会会员),不仅全程导游,且随时取景留影。我们同游玉佛苑,岫岩玉被称为“国玉”,此玉佛是用重260.76吨的整块岫岩玉雕成,乃世界之最,已入吉尼斯世界记录。这里是佛文化与玉文化集于一身,海内外的游客专程至此参谒者多多。同游千山时,四个老人各拄一杖入山。千山全称“千朵莲花山”,奇峰异景,鬼斧神工,释道同山,寺观分列。自古以来,游人如织。清帝康熙出关祭祖时,曾三次入山游览,并写了三首御制诗留传至今。人称“压倒三江”的王尔烈,出生辽阳,通称“王翰林”,留下的字与联随处可见。其他名人雅士至此留诗留字者甚多。如今游人至此,或站或坐,不经意间,会与古人的足迹或身影相重合而不自知。文化氛围浓郁,令人赞叹。
姜涛夫妇曾偕舒放(我们视他为自家孩子)来丹东我家小住。同游中朝界河鸭绿江及朝鲜战争遗迹——鸭绿江断桥;明万里长城东端起点——虎山长城。还曾到宽甸满族自治县的青山湖一游,这里须乘船穿越青山湖登岸入村,有如来到南国水乡。我们入住一户山坡上的独家,男主人整日在湖上使船,只有女主人接待游客。居室内外整洁。电冰箱内鸡鱼肉蛋齐备,但我们更愿意随主人入地里掰包米,入园中摘果菜。餐桌上摆满各种绿色菜品,尽尝农家风味。晚饭后,在小院闲坐聊天,将门灯一闭,庭院尽被夜色笼罩,山夜深深。小鸟入林了,山脚下的青山湖入睡了,山月出来了,如同湖水洗过的一般清明。这里远离人嚷车喧,远离市声躁气,姜涛说这里“出奇的静”。是的,这奇静盖源于如置身“世外”,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心无杂音,心静则处处皆静。分手时曾相约再来,其实已垂垂老矣,加之舟车劳顿,再来谈何容易。
在漫漫红尘中,我俩坚守着这一份友谊:淡如水、诚如石、无所图、重情义,自是别有一番情味。
2
两只出笼鸟他乡相遇。姜涛家住辽阳农村,我家住岫岩农村。他父是清末秀才,民国时期的税官,生活并不困难;我出生于满族中等地主家庭,生活也不困苦。他幼年丧母,四姊(两姊已婚)三兄多在城里住校读书(长兄务果园),只他一个少年在家,加之其父对封建礼教护持甚严,动辄即遭呵斥,如同笼中之鸟,孤苦难言。我家祖父母生有四男二女,不仅游手好闲(老叔在外谋职),且有五人(含祖母)吸食鸦片,一片破败景象;我少年丧父,伴着寡母的冷颜生活,加之祖母对满族礼法管教甚严,动辄即遭呵斥,亦如笼中之鸟,无自由无乐趣。幸逢祖国光复,回归祖国的怀抱,立志要求学报国,遂不约而同各自逃离家庭,来到沈阳。谁知国统区多有不平之事,竟然求学无门,流浪街头,他卖过报纸,当过校对;我卖过报纸和电影票,赖以糊口,令人心寒。后来他经三姐夫协助,进入“沈阳中学进修班”(公费学校)学习。我则巧遇从未谋面的族叔教授协助,也进入同一学校。老姜比我早来一个多月,两只出笼鸟在此相遇了,由于种种经历的相似,互有同情,且乐于交谈,遂逐步走近了。
我俩都是伪满“国高”未毕业,奴化教育以劳动为主,入高中二年文科(有数学,无物理、化学,加新课英语),仍觉各门课程都很吃力,疲于奔命。某一星期日,我持数学难题去问老姜,他看了也说不会,说等晚自习时求助其他同学。此时他正在洗衣服,就将我的衣服随手脱下入水搓洗,我只能将洗过的衣物用清水漂净晾晒。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引我到他的宿舍,从衣箱里取出一套衣服,不容分说就帮我穿上(日后常穿他的衣服)。我离家时只穿身上的一套衣服,只能等周日夜洗晨穿,显然对此他已观察在心了。衣服穿在身上,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鼻子酸酸的。这就是向往已久的友谊来临了。我只身来到偌大的沈阳城,如同海上漂泊的一叶小舟,除整日追赶课程外,常是一人独处(我插入初中同学宿舍),尽尝孤独之苦。今遇姜涛,如同走夜路遇见旅友,从此得以结伴而行,成为患难之交。
后知,中山中学近期即将由四川迁校来沈阳,并已决定收编我校学生。果于1947年春,经编班考试,同学们皆进入中山中学。我俩同入高中41班(高二文科)学习。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是“九一八”事变后,专为招收东北流亡青年在北平成立的学校。虽几经艰苦流亡迁徙而不辍,满怀“惟楚有士,亡秦必楚”,“我来自北兮回北方”的决心(见《校歌》),与抗日烽火相伴始终,具有抗日爱国的光荣传统和勤学爱校的优良校风,被誉为名校。沈阳同学了解了中山中学的光辉校史、校风,感触颇深,多暗下决心要好好学习,不负于母校。姜涛与我,能进入这所难得的名校学习,暗自庆幸好运来临。从此,我俩的友谊又有了新的故事:日后我俩参加了地下工作组织,已成为兄弟加同志的关系。
3
亲情为友情加厚。姜涛出生时,生母忽患偏瘫,其父认为是母子相克,遂将幼儿交由李家奶母寄养。养父母待之如己出,日夜操劳,百般疼爱。转眼间九年过去,姜家要接回孩子上学,养父母与养子双方都难舍难离,养母一夜之间愁白了头。李家小哥哥、小姐姐待小弟如同手足,整日伴玩,一旦分离,伤心不已。即时常到小弟上学的路上等候见面,并带给一些糖果,直到一年后转学外地为止。童年的记忆是铭刻于心的。多年之后,老姜得知李姐在某医院当护士,我俩便常去看望,李姐嘘寒问暖,姐弟情深依旧。又多年之后,李姐结婚生子,儿子也长大成人,每见到我俩仍亲切地口称舅舅,亲情传递下一代。
老姜的三姐家住沈阳。三姐夫曾帮助老姜进入中学进修班学习。三姐早年读“国高”时,曾因反满抗日罪名被捕入狱,一位女青年早有爱国之心,甚为可敬,我俩常去看望。三姐夫妇有时周日外出,我俩即去看门守夜,自炊自食,自由自在。三姐有一回拿出一些钱(约合人民币二三百元),让我俩课余在校外摆个小烟摊,可以补贴些零用钱。结果两个月不到,烟卖光,本钱也赔光。三姐笑着说:“你俩都不是这里的虫儿。那就好好求学报国吧。”多年后,逢三姐六十大寿,我俩两地相约去庆寿,寿星满面红光,家中子孙满堂,将我们这两个舅舅待为上宾。到三姐八十大寿时,我因病未能去祝寿,嘱老姜代捎一份寿礼,情意犹存。
这里对三姐夫补叙一事。1948年5月(此前姜涛已去辽南解放区)某星期日下午,我按规定时间来与地下组织单线领导人郁其文汇报工作。每次都准时,这次奇怪,竟房门挂锁。正猜疑中,听里院有人叫我,便门开处见是三姐夫,他悄声说:“老郁昨天被捕了,再别来啦。”我听了一惊,转身就走,他急忙扯住我,并先到街口左右张望后,才摆手让我离开。多亏三姐夫关心,告知此事(老郁被捕,我处于危境,即偕四同学逃往辽北解放区,我又被单独指派潜回沈阳等后续故事见拙文《辽北行》)。后知三姐夫妇也在做秘密情报工作。
老姜的三哥是抗日干部,在东北地区曾几度调动工作,后定岗于中科院沈阳某研究所任所长,我俩也几次去看望。三哥将他出版的著作《辽海沧桑》赠我。此书是他研究东北自然地理及历史,以及生态科学方面的论文合集,有专业水平。可贵的是他多年前即有很强的环境保护意识,心存高远。此书1993年5月10日签名赠我,至今藏于书橱中。
老姜与我同去会见亲属,如同为我又分得一份亲情。我俩关系愈加亲密。
此间,我俩曾多次相约去沈阳看望地下工作领导人郁其文夫妇,也曾看望王明(老郁的上线)夫妇。曾同行或分别去看望地工战友:包头屈连璧、长沙饶弘范、沈阳于文成、兰州孙辑六、北京袁钟声、公主岭李智山、北票王绍叶(在鞍山见面),却因未及看望石河子盖大北为憾。可惜学弟林杉早逝。地工战友情深,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终生难忘。
此外,我有三位1948年时东北大区文工团的老战友:鞍山有陈玙、熙明、沈阳有刘岚,我们四人受战友委托编辑文工团纪念文集《岁月回眸》出版。因此常在鞍山集会议事。由于我的引见,这三位作家也已成为姜涛的朋友,时有来往,并合影留念。这是一种友谊的互动。可惜陈玙兄已逝。
以上种种,可见亲情与友情同构,而亲情为友情加厚。
4
姜涛比我大五个月。我俩同为1928年生,属龙,他是二月初二生,我是七月初六生,他比我大五个月零四天。他是我的兄长。
在中山中学读书时,他知道我喜爱文学,就将我引荐给他认识的《沈阳日报》副刊编辑郁其文,经老郁的指点,我于1947年夏即有诗文在报上发表。老郁不仅是文学良师,也是启迪我思想的益友。郁其文于1947年5月参加了由东北局城工部领导的地下学联,任秘书,由于老姜力荐我,老郁先后发展了姜涛与我,并指定我俩为中山中学学运负责人。从此我俩携手走上了革命路。
由于老郁曾数次亲临我校指导,借学生自治会改选之机,经过秘密串连,地工人员屈连璧终于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老姜也进入自治会当文艺部长。这步棋对开展地下工作很重要。老姜对我说:“你留在自治会外做隐蔽工作,不能都在外面露着。”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分出明里暗里二条战线,是必要的。他的头脑很清醒(见姜涛、路地、于文成合写的《中山中学在沈阳的学生运动》一文,收入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迎接黎明》一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在光陆电影院召开“敌区工作总结大会”。此会开得很好。东北局领导陶铸同志到会讲话,对沈阳地下党的工作给予很高评价。但会后宣布地下组织一律解散,草草收场。我对此有意见,日后曾对姜涛说过。他说:“咱们既然自愿参加革命,担风险做地下工作也是作了贡献,不必去多想了。”几年后我又提起此事,姜涛又一次规劝于我,我由衷地接受了他的劝言。人生须得学会“放下”。他能抛开“自我”来劝人戒己,吾不如也。多年后,由组织部门行文:“路地同志参加革命时间为1947年6月”。最终落实了政策。
还有一件事。几年前我曾遇到不公正待遇,无法接受,即准备材料上诉。我跟他说了此事。他曾劝我说:“咱们这么大岁数了,着急上火的,影响健康,不值得。我看算了吧。”道理说的对,但我还在犹豫中。事隔多日,老姜来电话说,鞍山市组织老干部来丹东旅游,在此只停1小时,邀我速到江边会面,他当时说的全是劝我的话。最后又说:“我看算了吧。”此时此刻,他还惦记着我的事,真是难得其诚。那就“算了吧。”姜涛是个稳重内向的人,说话不多,其实打动人心的话何须多!直到晚年,我依然觉得他比我大五个月。
5
与姜涛相处这么多年,我从未有求于他,这次有事非求他不可。他在市委组织部长任上,正在住院中。我说,我的一位老战友在“文革”中被错定,下乡后停发了工资,如今平反昭雪,但停发的工资至今未补。他说他正管这件事。让我将其姓名、单位及联系方式留下,我就回沈阳了。不久,老战友来信说,问题很快解决,给予赔礼道歉,并补发了工资,十分感谢。等我再次来鞍山时,老战友定让我领其到老姜家致谢。老姜说,这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不给解决是失职,解决了是本份,“你告诉他,对谁也不用说谢。”
又有一次,是为这位老战友的儿子事去找他。这孩子由一所重点工科大学毕业,成绩优秀,一心想到鞍钢工作。老姜说:“鞍钢已不进人了。”等他看了学生成绩资料后,高兴地说:是个好青年,可与鞍钢商量看是否作为储备人才接收?次日他高兴地告诉我,鞍钢同意了,拿这封信去办手续吧(此君后成为市里某部门的中坚)。我的老战友因为前后两件事都办成了,老话又重提,非让我领他去老姜家致谢不可。我说,我不领他来他都生气了。老姜说:“这次是他为鞍钢输送了人才,应该感谢他。上次那件事属于落实政策,我现正忙于平反冤假错案,也有的老同志说感谢的话,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文革中给定了错案,让人家吃了苦遭了罪,反过来还让人家来道谢,我们还有没有良心?是人民公仆吗?”连老姜这种不常激动的人都激动了,这是彻底封门了。
有一次,老姜夫人老郑对我说,他家二女儿的青年点,一个一个往回调人,就是二女儿没有动静,孩子着急上火。“老路,你跟姜涛说说,管管这事。”这是母亲的心,可以理解。我跟他说了此事。他说:“老郑跟我说过一回,我没吱声。孩子往回调是早晚的事,不用着急。让我跟‘青年办说说,我说不出这种话。老路啊,咱的官不大,可也得有个原则。我家俩儿俩女,关于他们升学、考试、就业、转岗、入团入党,我从来没说过一句话,凭他们自己去奋斗。我的两个儿媳,至今还是‘大集体职工……”啥也不用说了,这就是清官的底线。
6
姜涛晚年编印了一本书《我的这一生》。此书是用二百多幅照片和二万多文字编成的自传体图集。(1)具有认识价值。有在革命岗位上服从调动,做什么都全力做好的光彩形象,也有在执行错误路线时,“不理解也得执行”,从而苦苦挣扎的心理彷徨。(2)眼睛向下看。有不少与同级、下属及勤务人员的合影,却无历届现任正副市长及其家属的照片。(3)重情重义。在每张照片的注解中,将同志、战友的优良品德作多方表述,并引为亦师亦友。(4)为官尽职,不求升迁。1983年申请退二线,1985年申请离休,此间与几位老同志通力合作,不辞劳苦,用十年时间编纂出版鞍山地方史志书三百余万字,成绩斐然。也收获一份身心的愉悦。(5)编撰《鞍山近现代历史图录》。由2002年起,用三年时间,跑遍鞍山、沈阳、长春等诸多城市,收集大量相关资料,与长子舒放进行分类编排,又与史志界的行家协力完成后期制作,编成此书。为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献礼。(6)旅行家。其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7)有个和谐幸福的家庭。夫妻和睦,子孙之间和谐相处,从无失和之虞。附有一张四世同堂、二十一口人全家福的珍贵照片。(8)自谴自责。1957年市政府办公厅错定了三名“右派”,这并非某一人之过,且已逾半个世纪,却话又重提,说“内心一直有一种沉重的负疚感”,感到“痛心”不已。事已年深日久,如今仍能如此真诚地自谴自责的人,不知能有几许?
有人类在,就有友谊在。友谊总是温馨的。友谊是人生的驿站,走累了进来歇歇脚,也可消解些旅途的落寞。在苍茫的尘世,纯真的友谊有如出水芙蓉,自有那么一抹冷香而独守。
姜涛与我的友谊已七十年了。历经大大小小的“运动”,所幸皆平安着陆,这要以终身的正直做人为前提。而历经种种的是非曲直,非一文所能尽述,而况友谊还在延续。友谊七十年,回望之甚长,细品之尚短;聚首时,即使相对无言,亦觉有人格的磊落在相互烛照;分别后,亦觉有信息传来,予生命以悄然的鼓舞。“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份友谊,我们有幸一生珍藏。虽然,两个凡人的友谊不足以为他人增益什么,但也决不会减损什么。比如一块山石,或可为游山人驻足小憩,或可为渡河人垫脚搭桥,如此而已。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