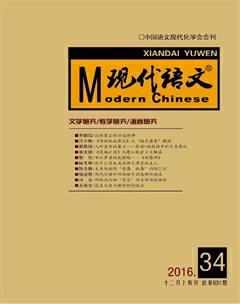解读《桃花源记》中陶渊明的感情倾向
摘 要:《桃花源记》是晋代大诗人陶渊明最为世人传诵的一篇文章,文章试从此文的创作背景、创作手法、创作主体等方面来看陶渊明的感情倾向。
关键词:陶渊明 感情倾向 人格德操
《桃花源记》是晋代大诗人陶渊明最为世人传诵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他晚年根据其家乡一代人民为生活所迫而“逃亡去就,不避幽深”的事实,并结合前人有关追求美好境界方面的思想材料,以及自己多年的乡居生活经验,加以想象、虚构而成的故事。文中展现了一个人人自食其力、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在讲授该篇时,学生对文中时代背景和渔人形象提出质疑,从而引发了笔者对这篇作品的思考。
一部作品,无论是写实还是虚构,都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有的是直接地、鲜明地将“我”置于作品之中,有的则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平静地讲述,但只要仔细研读探索作者的创作手法,依据作者所处的时代,作者的人格德操、审美情趣,就能判断他的感情倾向。
一、从创作背景看
陶渊明生年,上距东晋王朝的建立(公元317)四十八年,晋宋易代之后,陶渊明又生活了七年。《桃花源记》系陶渊明晚年所作,是在当时现实的基础上,加以想象虚构而成的,是当时现实的产物。历来对其主旨的权威解释是:对当时黑暗生活的不满,对理想生活的向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所针对的具体是什么时候的黑暗生活,就需要仔细研究。就陶渊明本人来说,他对东晋王朝是有感情的,陶渊明忠于晋朝是他的一贯言行,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忠君思想主宰着他的灵魂,支配着他的言行。在陶渊明早期的作品中的确可以发现一些美化东晋生活的诗篇。因此笔者在此强调的是陶渊明认为与桃花源中相背的黑暗现实的制造者是刘裕。这种感情在很多诗中都有反映,例如《归园田居》第四首:
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此诗中描述了田地荒凉,村中一片废墟的情况,村中的老百姓几乎都死光了,为何有这种情况呢?“晋安帝元兴三年(公元四零四年,甲辰),(陶渊明)四十一岁,刘裕起兵讨恒玄,玄逃入蜀被杀。晋政权腐败,豪族侵夺人民,加之战乱连年不断”(《陶渊明诗稿》)。于是陶渊明就用诗歌表现出了这一现状,并表现了对这种现状的极端不满。
“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公元四一七年,丁巳),(陶渊明)五十三岁,刘裕北伐,收复长安,灭后秦。刘裕急于当皇帝,不顾亡秦父老苦留,匆忙东还,只留其幼子刘义真及部将守之。”当年陶渊明作《饮酒》诗三十首表现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对政事的感慨和归隐到底的决心,和对晋宋易代政治局面的不满。
“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四零二年,庚申),(陶渊明)五十六岁,刘裕即帝位,废晋恭帝为零陵王,东晋亡”;第二年,刘裕杀晋恭帝,陶渊明作《桃花源诗并序》。文中所展现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是当时刘裕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的反面折射,作者隐晦地把矛头指向了不顾人民死活与民族存亡而篡权夺位的刘裕。
二、从创作手法看
作为一篇记叙文,《桃花源记》中穿插了对比手法,通过文中渔人与村民的对比和渔人和刘子驥的对比可以破译陶渊明的潜在话语。
(一)渔人与村民的对比
故事从渔人的出场开始,但他的出场让人觉得有一种游手好闲的感觉,根据史书记载,东晋时代封建剥削和压迫异常残酷,战争频繁,税收繁重,人民生活困难,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以捕鱼为职业的渔人,应该为整个家庭的生计犯愁,无暇顾及周围的美景才对,但他竟然显得如此悠闲,首先就对其作为人民的勤劳性和责任心作出了否定。而桃花源中的村民是以忙碌的身影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相命肆农耕,日落从所息”(《桃花源诗》)人人都劳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正因为人人劳动,从而得以丰衣足食,让“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过着自食其力,自给自足的生活,作者分别让渔人与村民以特有的方式出场,其中褒贬不言自明。
村民是热情好客的,渔人的到来,村民“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给予这个不速之客以热情友好的款待,让一向为生计发愁的渔人好好享受了一回酒食无忧的快乐生活。
村民是纯朴善良的,他们非常乐于当时安乐恬淡的生活,然而渔人的出现是对他们这种生活的极大冲击,他们面临着宁静生活被打破的威胁,临别时,他们对渔人并未提太高的要求,只一句“不足为外人道也”,可见他们认为并相信渔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然而与“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的桃花源中人相比,渔人是浅薄的,是不讲信用、背弃承诺的,源中人谁会想到他一离开桃花源不仅“处处志之”,还“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呢。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如此不讲信用、背弃承诺的渔人,亵渎了村民们的热情和友好。
“《拟古》写作于宋初二年辛(公元四二三年),《桃花源记》并《诗》也是同时所作,这年陶渊明五十七岁”(王瑶编著《陶渊明集》)。可见陶渊明晚年的生活状态是不容乐观的:“复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自会而作》)、“饥来驱我也,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他深知温饱没有着落的痛苦;另外他也深知耕作的不易:“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陶渊明诗全集》),“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就在作者有这样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写出了在当时生产力还不高的情况下温饱没得到解决的渔人,受到了村民们拿出自己辛苦劳动果实的款待,而且作者反复渲染“杀鸡作食”这一情节,这本该渔人感激涕零的,可事实恰恰相反,他恩将仇报,在村民们热情、淳朴、善良的光环下显得极其卑微,虽说作者不着一词,但在鲜明的对比中,已透漏作者潜在的情感倾向。
(二)渔人和刘子驥的比较
作品以渔人“不复得路”和刘子驥“未果,寻病终”作结,以往于这一点的说法是:给“世外桃源”抹上了神秘色彩,使人觉得仙源难寻、可望而不可即,笔者认为作者让刘子驥出场的目的不在于此,渔人去了桃花源回家时“处处志之”,结果是“不复得路”,这足以显示桃花源的神秘和可望而不可即。笔者认为刘子驥在此有两个作用:1.与渔人形成鲜明对比,反衬出渔人的动机。2.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
通过“高尚人士”刘子驥的传说将文章的中心转移到对渔人人品的否定,来表明对渔人批判的立场以达到劝诫世人的作用。
三、从创作主体看
作家是文学创作主体,从作家和作品的关系说,作家是作品的创作者、是创作实践的主体,文学作品是作家精神劳动的艺术产品。艺术作品是作者精神的物态化,是保存作家人格德操的精神化石。因而作者的人格、德操就成了内在的衡量作品中人物的标准和尺度。
陶渊明二十九岁时出仕为官,亲历了官场的种种丑恶,官场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恶浊空气让他窒息,陶渊明一直强调自己质性自然、不愿迁就世俗,扭曲自己正直的人格,于是就有了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佳话。“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陶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萧统《陶渊明》)。陶渊明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从此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有的彷徨,以其高洁的人格操守面向世人。
钟嵘《诗品》中评析套诗曰“每观其文,想其人德”。的确,我们读陶渊明诗,能够从字里行间看到他的人格操守。
陶渊明在其诗作中多提到“固穷”(《治语·卫家公》:“君子固穷,以穷斯滥矣。”即“君子能安于贫困境遇,而小人则因穷而为非”之意)。如“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道》),“不赖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咏贫土》)等。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以“君子”自况,表明着“固穷”的德操。这种“固穷”的德操,是出于一种情感与人格的凝聚,陶渊明恰恰还在“固穷”中感受到了无穷的乐趣。
回到《桃花源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渔人与创作主体——陶渊明人格德操的巨大反差。
渔人以捕鱼为业,自从他去了桃花源后,他就不再安于现状,一出桃花源,就“诣太守,说如此”,如此迫不及待,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一直在寻求发财致富的捷径,只不过在此之前未能如愿而已。而现在正好借对太守的阿谀奉承来改变原来贫困的生活状态,实现他的人生目标。而陶渊明在“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情况下,能安逸平静地度完自己的一生。不知“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对渔人是同情还是鄙视呢?
《桃花源记》不管是真是假、是虚是实,都是作者心中的真实,都是作者心中的客观实在,因而我们就可以结合时代背景,作者个人的人格德操、创作手法去破译作者的情感。以上是笔者对破译《桃花源记》的情感倾向作的一点浅显的尝试,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参考文献:
[1]吴云.陶渊明论稿[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萧统.陶渊明传[M].海口:海南国际出版中心,1995.
[3]王瑶.陶渊明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56.
(朱国琴 江苏省扬州市汤汪中学 22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