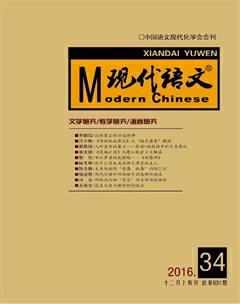从文学伦理学视角看《恶童日记》中“恶”的实质
谌天++盘媛
摘 要:匈牙利当代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在欧洲文坛享誉盛名的三部长篇著作“恶童三部曲”中尤以《恶童日记》广为人知。关于《恶童日记》之“恶”的解读有很多种,且不同解读之间甚至没有交叉之处。文章拟从《恶童日记》最后一章关于恶童和父亲逃往国外的叙述着手展开探究,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尝试揭示“恶”的实质。
关键词:《恶童日记》 路卡斯 “恶” 自我麻痹
匈牙利当代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在欧洲文坛享誉盛名的三部长篇著作“恶童三部曲”——《恶童日记》《二人证据》《第三谎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于1956年爆发的匈牙利革命为写作背景,借记叙路卡斯这一位战争的弃儿短暂而颠沛流离的一生的故事痛斥战争的罪恶。三部作品分别记叙了路卡斯寄居边境外婆家、路卡斯孪生兄弟克劳斯留在祖国生存、老年路卡斯流亡国外多年后返还祖国寻觅亲人的三段经历。三部作品人物、地点、时间乃至叙事手法都不尽相同,可谓各具特色。但这三部作品中,要数《恶童日记》最广为人们熟知。
虽然国内关于《恶童日记》这部作品的研究暂时匮乏,但关于该作品“恶”的解读并不鲜见。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下几种:一是该作品的译者简伊玲在该作品《译序》谈到的,“我想,真正的‘恶就在面对‘恶时的无感与冷漠。”[1];二是李道全在《<恶童日记>中的病态儿童》所阐释的,“虽然没有亲历战场的血腥屠杀,但是双胞胎兄弟在战争的后方也没有幸免战事的荼毒。他们健康成长的土壤已经被无情地铲除。童年的记忆成了世事险恶,而要在那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他们无奈地蜕化成了‘恶童。……双胞胎兄弟的战时成长经验就深刻痛斥了战争的滔天罪愆。”[2];三是张娟在《创伤记忆衍生恶之花》里认为,“‘恶是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却并不是主题,‘恶是残酷现实促生的结果,即便是强大如双胞胎,练习恶的时候先经历了巨大的心灵之痛。所以我认为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表面的‘恶,而是深层的‘创伤记忆,创伤首先来自一个家庭碎裂的悲剧,是战乱大背景的残生存,悲剧促生了三个痛点:残疾、乱伦、死亡这些痛楚的记忆埋伏在心里,随时触动,随处爆发,于是这些变态成为一种常态,每个人物都多多少少与此相关,正是对童年创伤不同层面的影射”[3]。
以上三位对“恶”实质的揭示不尽相同,简伊玲和李道全认为“恶”乃小说的主题,并将恶归咎于战争带来的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荼毒,张娟否认恶为主题,而认为是表面上的“恶”背后的创伤记忆。从这几种解读不难看出,关于《恶童日记》的“恶”的实质的揭示是存在明显争议的,而且似乎各自均言之有理。那么究竟哪一种观点更为接近作品文本所呈现出来的“恶”的本来面目,或者说是否有新的观点能够更为合理揭示“恶”的实质呢?
作为一种明显区别于其他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能够利用自身独特对文学中各种社会生活现象进行客观的伦理分析和归纳。[4]借助文学伦理学的相关理论来审视《恶童日记》,或许能够寻觅到关于“恶”的实质的真正答案。
一、谎言:利用父亲逃亡国外
《恶童日记》最后一章所叙述的事件可谓骇人听闻。被寄居在国家边境外婆家的双胞胎与父亲重逢,两人设计诱使一心想逃往国外的父亲率先穿越边境,导致父亲被地雷炸死,而双胞胎之一克劳斯踩着父亲的尸体逃往国外。但据“恶童三部曲”第三部《第三谎言》中交代,这一段经历并不属实。
《恶童日记》中具体叙述如下:首先,双胞胎骗父亲毁掉了所有证件。他们这样对父亲讲,“不能让人认出你的身份,如果你发生什么事,别人又知道你是我们的爸爸,我们就会被人以共犯的罪名逮捕”;其次是关于爸爸穿越边境的记叙:“爸爸把那两块木板夹在腋下向前走去……‘轰!爆炸了”;最后,双胞胎坦白他们本来目的:“是的,有一个方法可以通过边界,就是叫某个人走在前面”[5]。
而在《第三谎言》中,当事人路卡斯却提供了另外一套说辞。这名逃亡边界的男人与路卡斯并不相识。路卡斯交代,“我在车站遇见那个想穿越边界的男子”。扔掉所有证件的行为也并非路卡斯诱导,而是男子要求的,“喏,把这些(指该男子身份证和其他证件)都丢进你的炉里烧掉!”男子甚至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路卡斯,不过也被路卡斯扔进了炉火中。路卡斯表示欲与男子一起穿越边界,而在穿越边境的时候,也并不是路卡斯引诱男子先行穿越。他提供的说法是这样的,“那男子走在我前面,他的运气很不好。在第二道栅栏附近地雷爆炸了,那男子被炸翻了。我就在他后面,所以很安全”[6]。
以上两处对于同一事件的记叙是截然不同的。在《第三谎言》里,路卡斯有一段自我陈述,“其实,这整件事的所有内容只不过是个谎言。我相当清楚,在这个镇上,在外婆家的时候,我早就是独自一个人了。即使在当时,也只不过是我在幻想,幻想是两个人,也就是我的兄弟和我,好让自己能熬过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孤独”[7]。如果承认《第三谎言》里所陈述的是事情真相原委,那么可以认为,以上两段叙述中,《恶童日记》的叙述是虚构的,换言之即路卡斯所说“谎言”。《恶童日记》该段叙述有这样几处“谎言”:一是死者是与路卡斯和素不相识的男人,并非父亲;二是不存在设计的销毁证件、引诱男子先行然后踏过尸体逃亡国外的阴谋诡计;三是整个事件前后只有路卡斯一人,并不存在所谓的双胞胎。
由这样几处谎言不难形成几个疑点。一是路卡斯强行将素不相识的男子虚构为自己的父亲,并在虚构中实施令人瞠目结舌的谋杀的行为背后有怎样的原因;二是《恶童日记》中的双胞胎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存在,那么两人分离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时候分离的。据《第三谎言》揭示,双胞胎的确存在,只是在路卡斯四岁时两人便因为路卡斯受伤送往康复中心而分开。而战火导致康复中心被炸毁,路卡斯被送往边境一个老农妇家,至此路卡斯与父母、兄弟彻底失联。而路卡斯受伤的原因是父母因父亲外遇而起争执,母亲拿出手枪射击父亲时,误伤上前劝阻的路卡斯。而《恶童日记》是多年以后,流亡国外的路卡斯回乡寻亲期间不堪忍受飘零一人的孤寂结合自身经历所创作。综上看来,对父亲的虚构并在虚构中将其谋杀是路卡斯内心深处做出的伦理选择。这一看起来荒诞令人费解的伦理选择的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二、困境:弃儿与流亡国外
前文提出观点,认为《恶童日记》最后一章所虚构的内容体现了路卡斯的伦理选择,而这种伦理选择与路卡斯多种尴尬身份有关。
首先,他的双胞胎出生身份是极为特别的。我们可以看到,双胞胎两兄弟在《恶童日记》中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整体。整部小说下来,除了小说结尾两兄弟一个逃亡国外一个留守K镇至此分开外,两人的行动完全一致。正因为两人完全一致的行动,小说通篇以“我们”作为叙述者,而作者甚至没有透露双胞胎的各自姓名。而双胞胎出生给路卡斯毕生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路卡斯在流亡国外的时候向当局上报的姓名是化用兄弟名字科劳斯的克劳斯。选择“克劳斯”这个化名当然是刻意之举。在《恶童日记》语境中的战争里,是没有所谓真与假,谎报姓名是一种自我保护、隐藏身份的行为,对于独自一人流亡国外的路卡斯来说选择化名是他必要的保护自我的措施。选择使用“克劳斯”表面上看是出于对孪生兄弟的思念的一种表达;深层次来看,由于是双胞胎,他得以通过复制自己的方式来幻想其实兄弟一直在身边,以逃避现实的孤独和麻痹自己敏感脆弱的神经。
第二,他是一个身患残疾的弃儿。路卡斯的脊椎因父母争吵母亲开枪射击父亲时误伤,因而被送往医院,后又送至康复中心被当做小儿麻痹症患者治疗。在康复中心的经历给他很深影响。“我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我对那段日子的记忆相当清晰。”[8]在医院,由于颈椎受伤,他接受着非常痛苦的治疗,他被要求用一根皮带支撑身体在一个输送带样的机器行走、挂在一些吊环上以及踩踏一种固定式的脚踏车,“跨在上面即使踩到痛得快要哭出来了,我还是得继续踩下去。”而伴随着住院生活的长久和父母兄弟迟迟不来看望导致路卡斯心理状态发生严重变化。他在康复中心开始做坏事、说坏话:在口袋中装满表皮光滑的果子,去丢护士和监视阿姨;因为同房间小男孩吵闹,他施以暴力,“我给那些爱哭鬼几记耳光”;给小孩子读信时,故意念错信,“通常,我念的内容和信上写的正好相反,例如‘亲爱的孩子,希望你最好别痊愈。没有你,我们全家一样过得很好,一点儿也不会寂寞……”;向来访的其它孩子的父母宣告他们的孩子已死亡;在一位老太太戳穿了他的真实想法即“你做出这些事情是因为你父母从没来看过你,是吗?”“他们从不写信给你,也从不寄包裹给你,所以你在其他孩子身上进行报复”[9]随后,他拿起手杖击打老太太。身患残疾的病痛和自卑加上亲人一直不闻不问使得路卡斯对身边在他看来是幸福的孩子们进行打击报复。而在他看来,这种恶言恶行激化人们对他的憎恶,而对他残疾和弃儿身份的鄙视与嘲笑相应淡化。
第三,他多次被收养。在康复中心被战火炸毁后,路卡斯被送往边境小镇的老农妇家寄居。在《恶童日记》中,作者不惜大量笔墨描绘这个破旧肮脏的小屋和它的女主人。恶童称女主人为“外婆”,而这位外婆毫不讲究卫生,“从来不洗澡也不洗脸,她只有在吃完东西或喝过东西后才抓起头巾的一角随便一抹嘴巴……外婆的衣服从来没有换过”,“一边做饭一边用袖子擤鼻涕,擤完了不洗手”;屋内也是肮脏无比,“厨房的每一件东西都脏。不规则的红色地板砖总是粘住我们的脚,大餐桌常弄得我们双手双肘一团黏糊”[10]。本身在这样肮脏的环境下生存已经十分艰难,这位巫婆似的外婆凶狠、吝啬,称恶童为“狗养的”,要求恶童必须帮她做事,“否则她就不给我们东西吃,而且会赶我们到外头睡觉”[11],并把寄给恶童的衣物变卖换成钱。在这种恶劣生存条件的胁迫下,恶童开始绝食、自虐、杀生,由干净漂亮的小孩逐渐蜕变为肮脏、早熟、作恶多端的恶童。而在逃亡国外后,他再次被收养。几经收养的路卡斯的心理状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四,长年流亡国外。路卡斯在逃到国外后,为了谋求生存,他隐藏了真实姓名和年龄,上报给当局的个人信息全部是虚假的。流亡国外的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和亲情的长期缺位造成了其流亡生活的困顿。
三、实质:谎言是一种伦理选择
路卡斯的人生经历是极为坎坷复杂的,上述分析的他的多种伦理身份的存在使得他从一开始就面临诸多困境。正是这些致他陷入诸多困境的多种尴尬身份影响了他的许多行为。按这样的观点,再回头审视前文提及的《恶童日记》中关于利用父亲逃亡国外的伪陈述实际上是路卡斯做出的一种伦理选择。
前文提到,该段叙述有两处大的谎言:一是死亡的男子并非其生父;二是并不存在的双胞胎。
首先来看将男子认作生父这一行为。《恶童日记》中的记叙为恶童引诱父亲先行穿越边境封锁线,先行者引爆地雷后被炸死,恶童得以踩着父亲的尸体安全穿越封锁。实际上,路卡斯生父为其母亲所射杀,原因是父亲有了外遇并企图逃避对家庭的责任。而正是在射击父亲时,路卡斯上前阻拦受伤,导致后来的与亲人的离散。这件事情给路卡斯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成为其一生的阴影。作为该事件无辜的受害者,这件事是不堪回忆的,想到父亲真实的死因会引起他巨大的痛苦,倒不如用自己亲手设计谋杀父亲的方式来隐瞒真相,麻痹自己的痛苦与孤寂。而在内心里将父亲杀死体现了路卡斯对父亲的憎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俄狄浦斯情结”。而将男子认作父亲也对他在逃到国外后圆谎并获得监护起了很大的帮助。
再来看虚构双胞胎这一做法。前文曾引用过路卡斯的自白,可以得知《恶童日记》中的双胞胎不过是路卡斯的虚构,路卡斯正是通过这样虚构的方式来复制自己,以幻想自己的兄弟,让自己能熬过孑然一身的可怕的孤独;路卡斯在国外是用的克劳斯的名字,这个名字与其兄弟科劳斯发音相近,充分寄托着路卡斯对孪生兄弟的无比思念,这也得以解释路卡斯多年后回到故国无法忍受物是人非和最终踏上寻找兄弟的征程。
所以可以认为,路卡斯在《恶童日记》所撒的谎并不是无凭无据的编造,而是经过他深思熟虑过后做出的伦理选择。这样的伦理选择一方面起到了麻痹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是无法消除的整个悲剧给路卡斯带来的沉重折磨。所以在《第三谎言》中,路卡斯几经彷徨,最终找到科劳斯并上门拜访,但出于对因误伤儿子而无法原谅自己并因此陷入精神失常的母亲的保护,不让“安静生活”被打扰,科劳斯否认和拒绝了路卡斯。在得以与亲人重逢、回归故居和被拒绝、二次与亲骨肉分离的大起大落后,路卡斯选择了自杀,这才得到了最终的救赎。
四、环境:路卡斯悲剧背后的战乱
《恶童日记》可以被视为是路卡斯悲剧的一种虚构性表达,而造成路卡斯悲剧的罪魁祸首,正是在《恶童日记》中表现得血淋淋的战争。
在战争环境下,生存大于一切。在《恶童日记》中,战争带来的是随时随地的轰炸、敌人军队的肆意掠夺与侵犯、随处堆积的尸体和生活物资的匮乏。硝烟弥漫的战争沦陷区没有一片安居乐业的净土,人人自危,为了生存,获取生活物资,所有人面目全非。
战争还造成了人们信仰的崩塌。《恶童日记》中《神父》一章双胞胎这样对神父说道,“不,我们不遵守十诫,也不会有人遵守的。上面写着‘你不可杀人,结果所有人都在杀人”[12],从这句话便可知,战争下,宗教信仰、人生信条都不再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有效工具。连神父自己也做着不可告人的龌龊事,并因猥亵小兔子遭到双胞胎的恐吓与勒索。战争下,信仰荡然无存。
可以看到,《恶童日记》里的社会秩序在战争的破坏下变得混乱、失控。伦理禁忌不复存在,在《恶童日记》中,充斥着杀人、放火、人兽交媾、娈童癖、受虐癖、轮奸等严重违背伦理规范的情节,社会失去了应有的正常的秩序,人人行恶,没有道德,没有善恶。正是战争和战争造成的社会紊乱催生了恶童的生长。
五、结语
经过以上分析,《恶童日记》之“恶”的实质或许得以揭示。再看文首提及关于“恶”的理解的三种说法,其中张娟的看法可能更符合作者的原本表达。但从文学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创伤记忆”这个观点不够准确,的确,《恶童日记》是路卡斯根据自己真实经历加以艺术改造的文学创作,但“创伤记忆”无法解释诸如开头提及的关于路卡斯利用父亲逃往国外经历的伪陈述。经过对路卡斯伦理身份的探求、由伪陈述发掘的其伦理困境,结合路卡斯生活着的因战争导致的伦理丧失的环境,可以得知“恶”是存在于路卡斯的记忆中,由于《恶童日记》的伪陈述和《第三谎言》隐藏大量真相的原因,其在《恶童日记》中所实施的诸多恶行究竟是否真实发生,无法做出肯定的判断。但可以确定的是,路卡斯对“恶”的书写是对伦理困境的逃避与自我麻痹,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才能得以独自一人面对因战争带来的噩梦般的世界,支撑着活下去。
战争导致了原有伦理秩序的崩溃,对生存的渴求造成人性的扭曲,谎言与真相无法辨别,而谎言背后,是主人公路卡斯对伦理困境的逃避与自我麻痹。或许这才是作者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所控诉战争给人带来无法磨灭的毁灭性的创伤的地方。
注释:
[1]简伊玲译,[匈牙利]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恶童日记·译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2]李道全:《<恶童日记>中的病态儿童》,世界文化,2010年,第6期。
[3]张娟:《创伤记忆衍生恶之花》,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期。
[4]聂珍钊:《第一章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基本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014年版,第15页。
[5]简伊玲译,[匈牙利]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恶童日记·别离》,《恶童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至164页。
[6]简伊玲译,[匈牙利]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第三谎言》,《恶童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至374页。
[7]简伊玲译,[匈牙利]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第三谎言》,《恶童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5页。
[8]简伊玲译,[匈牙利]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第三谎言》,《恶童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4页。
[9]简伊玲译,[匈牙利]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第三谎言》,《恶童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2页。
[10]简伊玲译,[匈牙利]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恶童日记·污垢》,《恶童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11]简伊玲译,[匈牙利]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恶童日记·差事》,《恶童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12]简伊玲译,[匈牙利]雅歌塔·克里斯多夫:《恶童日记·神父》,《恶童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参考文献:
[1]简伊玲译,[匈]克里斯多夫(Kristof,A.).恶童日记:珍藏纪念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李道全.《恶童日记》中的病态儿童[J].世界文化,2010,(6).
[4]张娟.创伤记忆衍生恶之花[J].中国图书评论,2014,(1).
[5]杨革新.伦理选择与丁梅斯代尔的公开忏悔[J].外国文学研究,2009,(6).
[6]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J].外国文学研究,2004,(5).
[7]聂珍钊.文学理论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
(谌天,盘媛 湖北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