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室铭》作者问题释证
孙思旺
《陋室铭》作者问题释证
孙思旺
《陋室铭》虽不列于梦得文集传世刻本,但古今学人一向视为刘氏遗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于北山、卞孝萱、吴小如等先生纷纷撰文,断为伪托,遂使其作者问题渐有演为公案之势。今考诸家之说,颇拾宋僧孤山智圆遗绪,以人品文风之好恶臆断真伪,殊不足取。所欲论者有三:其一,传世刘集可以为《陋室铭》提供一系列文本内证;其二,唐人的陋室之咏集中产生于刘禹锡的交游群体;其三,被辨伪者援以为据的唐观音寺界碑实系伪刻,抄撮村言俗语说并不成立。
《陋室铭》;作者问题;观音寺界碑;文本内证;时代共性

与上述怀疑论交错出现的,是捍卫刘氏著作权的各种辩护说。譬如,吴汝煜先生以为,《陋室铭》当撰于刘氏分司东都、息肩洛阳之时;王鹤、李晓丽两先生则以为,此文当撰于和州刺史任上,经柳公权书碑后刻石流行。此外,颜春峰、汪少华两先生专就段塔利文提出的崔沔作铭说,逐条加以驳斥*以上诸说参见吴汝煜:《谈刘禹锡的〈陋室铭〉》,《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王鹤、李晓丽:《〈陋室铭〉作者祛疑》,《古典文献研究》第15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颜春峰、汪少华:《〈陋室铭〉的作者不是刘禹锡吗?》,《寻根》1996年第6期。。
以上诸文的具体论述无烦详引,所须注意者有三。其一,有些辨伪结论(比如明人作伪说、元明以前之书虽录全文然未系之刘禹锡说)之所以得出,是因为所见文献资料不广之故。这一点,钱大昕早已藉梁元帝之言提出过批评,今人应当引以为戒*钱氏谓:“崔沔尝作《陋室铭》,在刘禹锡之前。李德裕有《秋声赋》,在欧阳公之前。梁元帝《金楼子》有一条云:‘桓谭有《新论》,华谭又有《新论》。扬雄有《太元经》,杨泉又有《太元经》。谈者多误,动形言色。或云桓谭有《新论》,何处复有华谭?扬子有《太元经》,何处复有《太元经》?此皆由不学使之然也。’”参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陋室铭》,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第395页;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卷六《杂记篇第十三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24页。。其二,有些辨伪动机的产生,是基于雅人不能有俗作、高士不能有浅文的认识观念。此种观念之荒谬姑且不论,即就史书对刘禹锡其人、读者对《陋室铭》其文的评价而言,本身便是极具争议的话题。其三,正反双方对某些关键材料的解读相去甚远。比如,所谓刘禹锡撰、柳公权书和州《陋室铭》一事,质疑者以为伪,辩护方以为真,在没有实物碑拓可供甄别的情况下,继续纠结于此等材料,不可能一杜论者之口。

一、唐观音寺界碑当系伪刻,抄撮俗语说不足据

此碑原立于蔡河镇兴旺村观音寺,碑文收入1990年新编《应山县志》。其寺与碑,旧嘉靖县志、康熙县志、同治县志均不载,各种常见金石书也未述及。观碑文内容,除上揭“盖闻”四句附庸风雅外,其余部分尽与田产寺界有关,产业置办者及立碑人均系“净乐”和尚,勒石日期为“大唐贞观四年三月”。笔者通读碑文之后,觉得有如下问题值得关注。
其一,对建寺历史的记述不似当时实录,更像后世托古之辞。碑文说:“永阳邑北隅,离城五十里许,有观音寺建自大唐,其庙宇俱系释子净乐创修。”若净乐果有其人的话,其刻石纪事正在唐初,以唐初之人而云建自大唐,辞气颇为不顺。若说此语出自后世人之口,仅仅是在作伪时未能消泯其“追述”痕迹,一切疑点便可释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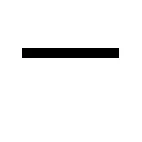

其四,碑文中有与时代不符的避讳字。创业者暨立碑人署名“宏法沙门比丘净乐”,“宏法”当作“弘法”,改“弘”为“宏”是历史上常见的避讳方式。唐代也曾为孝敬皇帝李弘避“弘”字,但那是唐中宗神龙复辟以后的事情。后世避“弘”字较为著名而彻底者,一是宋避太祖、太宗之父赵弘殷之讳,二是清避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之讳。

至此,我们可初步得出以下结论:唐观音寺界碑系后世伪刻,“当时”“顺口溜”云云纯属伪命题;并非《陋室铭》抄录了碑中“顺口溜”,而是此碑在作伪之时套用了《陋室铭》所创造的的流行句式。
二、《陋室铭》刘集内证梳理
前文已经谈及,《陋室铭》抄撮当时俗语以成开篇四句之说绝不可信。接下来,我们再从创作习惯的角度,探讨一下此四句的典故来源,以及刘禹锡文集中的类似表述。《铭》文其他部分,亦仿此四句,依次叙说于后。
(一)“在A不在B”
若将开头四句浓缩还原,便是一种“在A不在B”式的经典表述。这种表述模式通常用来指明,易见的外在属性与不易见的内在属性之间何者为决定性因素,从而使事物的意义所在与问题的解决途径简明扼要地彰显出来。

刘禹锡向以用典严肃著称,他的类似表述显然是从《左传》等书化用而来。传世刘集中的相近例证并不难找,比如,在其连州刺史任上,曾有嗜名书生曹璩因遍干“东诸侯”未果来见,欲“依名山以扬其声,将挂帻于南岳”。刘禹锡棒喝道:“在己不在山。”*刘禹锡:《送曹璩归越中旧隐》,《刘梦得外集》卷八,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本。这条例证与经典原型高度吻合。接下来我们且看稍有变易的另一例。《佛衣铭》云:“佛言不行,佛衣乃争,忽近贵远,古今常情……坏色之衣,道不在兹,由之信道,所以为宝。”*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三十,《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本。这几句话简言之即“在言不在衣”,只是因涉及高僧遗物、宗教信仰,措辞较为尊重而已。此外,若细加品味的话,上引《佛衣铭》与《陋室铭》的语言风格极为相近。盖因铭之作,本为自警警人,行文宜取平实精炼,利于唇吻,不必故作高深晦涩,使人望而远之。
回过头来再看《陋室铭》起首几句,稍稍变易其体,即山之名“在仙不在高”,水之灵“在龙不在深”,人之馨“在德不在室”。考诸经典,渊源有自;求诸刘集,辙迹相通。
(二)陋室·君子
通常而言,陋室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贫而无力为之,一是俭而无意为之。经典中书及此语,往往是用来衬托君子固穷守约的人格力量。《铭》中之陋室,自然是由经典用法沿袭而来。
卞孝萱先生以为,此典当出于《论语·雍也》,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1997年第1期。惟卞先生受王念孙父子影响,必解“陋巷”为陋室,似犹有可商。。就颜回的生活境况而言,居室之狭陋不难想见,《雍也》之文的确与此典相合。蒋建波先生则以为,其语源当在《荀子·儒效》,所谓“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蒋建波:《〈陋室铭〉中“陋室”考辨》,《语文学刊》2012年第9期。。以上两说俱见卓识。但若对“陋室”二字更作苛求的话,《韩诗外传》的说法不应该忽略:“彼大儒者,虽隐居穷巷陋室,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争名矣。”*屈守元笺疏:《韩诗外传笺疏》卷五,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447页。
因为上揭载籍的权威表述,“穷巷”、“陋室”云云遂演变为反衬君子德行的明谦暗褒之辞。当然,历史上通常与此类褒辞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孔门高弟颜回,或者以颜回为模型抽象出来的命世大儒;《铭》文所说的躬耕南阳时的诸葛亮、草创《太玄》时的扬子云,自然都在陋室君子之俦,只不过后两者是无意为之而已。《铭》文最末一句出自《论语》,仍是呼应开头的“在德不在室”这一点。《论语·子罕》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九,台北:艺文印书馆,2011年,第79页。

传世刘集中也曾言及“陋室”一词,《上杜司徒书》云:“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瘠田可耕,陋室未毁。”*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十四。但就所表实物而言,《书》、《铭》两文中的陋室恐不可等量齐观。前者特指先祖旧居,后者可能更近乎王龟的书斋隐舍*笔者在另一文中已经述及,王龟是王起之子,“父职京师,则于永达里建书斋;父镇河中,则于中条山起草堂;父保厘东都,则筑松斋于龙门;父节度山南,则立隐舍于汉阳”。见拙文《〈唐书辑校〉指瑕》,《湖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是随其宦途所在而设的起居修养之所。
(三)莓苔·青草
莓苔、青草皆是幽静中富于生机之物,文人雅士吟咏及之殊不鲜见。论者或以为“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两句是南方气候写实,“北方干燥,房屋左右前后少见青苔”,由此又推导出浙省文士伪托说等结论*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1997年第1期。卞说的问题在于,观点B(铭必作于南方)本不成立,由观点B推导出观点C(南方文士伪托),又需以观点A(铭为伪作)为前提,而观点A本亦不成立;但就字面关系看,B、C却又成为佐证A成立的依据。有关卞先生的具体论述,王鹤、李晓丽两先生有较为详细的针对性分析,参见前揭《〈陋室铭〉作者祛疑》一文。。然刘禹锡再游长安玄都观题诗,而云“百亩中庭半是苔”;与裴度、白居易、张籍在长安兴化坊联句,而云“新暑石添苔”;与裴度、白居易在洛阳联句,而云“石径践莓苔”*分别见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绝句》,裴度、刘禹锡、白居易、张籍《宴兴化池亭送白二十二东归联句》,裴度、白居易、刘禹锡《予自到洛中与乐天为文酒之会时时构咏乐不可支则慨然共忆梦得而梦得亦分司至止欢惬可知因为联句》,《刘梦得文集》卷四,《刘梦得外集》卷二,《刘梦得外集》卷四。末首联句题名参据他本迻录。。可见征诸文字,其说并不成立。况且笔者即北人,焉不识苔藓之为物,每逢雨季,墙头檐边阶角树下极易滋生。要之,仅凭上揭两句中的苔痕草色,并不能将北方摒除于可能的创作地点之外。
还是回到本文的关注范围,从创作习惯的角度考察传世刘集中的文本内证。隔帘草色意象的构设,不仅见于《陋室铭》,还见于刘集中的《伤愚溪三首》*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十。。愚溪,实即柳宗元在永州辟建的“陋室”,刘禹锡在引言中记述道:“故人柳子厚之谪永州,得胜地,结茅树蔬,为沼沚,为台榭,目曰愚溪。”柳宗元去世三年后,有游僧话及愚溪光景,刘氏悲不自胜,因赋诗三首以“寄恨”。其第一首云:“隔帘惟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所引上句几乎可以看作“草色入帘青”的主客反写,只是借“惟见”二字渲染了“草堂无主”之悲。
其第三首云:“柳门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所引下句与《铭》文“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二句物象略同,但在此诗意境中,空宅荒废已久,野草青苔任其滋蔓,迥不似《铭》中“上阶”、“入帘”之色恬静可喜。
对于莓苔生长蔓延的动态化描述,我们可以从刘氏《和乐天早寒》一诗中,为《陋室铭》找到相近之例。前者云:“雨引苔侵壁,风驱叶拥阶。”“侵壁”、“上阶”两语在意境营造中的趣味几乎全同。试以白居易原诗《早寒》之句——“黄叶聚墙角,青苔围柱根”作比较,其属辞偏好之不同便可分晓*分别见《刘梦得外集》卷一;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六,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宋刊本,第672页。。
(四)鸿儒·白丁
围绕“鸿儒”、“白丁”两句,论者之疑主要有三:一是措辞明显“瞧不起群众”,与刘禹锡思想作风不符;二是对环境的描述有悖常识,“苔多草长”表明“人迹罕至”,与“谈笑有鸿儒”自相抵牾;三是“缺乏逻辑”,“‘有仙则名’是崇尚道教,‘阅金经’是崇尚佛教,而来陋室‘谈笑’的是‘鸿儒’,不是和尚、道士”*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1997年第1期。。问题在于,其一,有否上述弊病与此铭是否为伪作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表里关系或因果关系,而历史上从境界品格、创作技巧等方面对刘氏提出尖锐批评者绝不鲜见,倘若依据上揭标准为断的话,传世刘集中的伪作恐怕也要十居二三;其二,前述三疑所指摘的弊病,或是以辞害意,或是以今律古,征诸刘集、唐史,其说并不成立。
先看疑之一。是否瞧得起群众并与群众打成一片,是富于阶级性、革命性、近代民主性的是非标准,用它来衡量一千多年前的士大夫官僚,超越了时代限制。况且铭文在这里主要是对理想志趣的表达,而爱民如子在中古时期最多也就是劝课农桑、敦厚风俗而已,并非要与“白丁”培养共同的生活情趣。凡此姑置不论,在传世刘集中亦不乏相似表述。比如,《赠别君素上人》云:“穷巷唯秋草,高僧独扣门。”高僧独至,与“鸿儒”、“白丁”两句意同,只是行为主体变更为宗教人士而已。又如,《送湘阳熊判官孺登府罢归钟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云:“何武劾腐儒,陈蕃礼高士。”*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六。诗以何、陈比裴堪,兼有自明本志之意。若据陈蕃独设徐孺子之榻以推,此诗的交游原则实比鸿儒白丁更为严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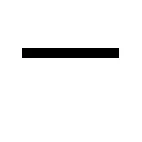

(五)案牍·丝竹·素琴

官司有繁重闲散之别无庸赘说。刘禹锡任朗州司马多年,司马即闲散之官。其《送王司马之陕州》云:“案牍来时唯署字,风烟入兴便成章。”元稹任通州司马时亦赋诗云:“睡到日西无一事,月储三万买教闲。”*分别见《刘梦得文集》卷六;元稹:《通州》,《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6页。其后,刘氏又出刺连、夔、和、苏等州。刺史总揽一州之政,自非司马可比,其苏州诗云:“云水正一望,簿书来绕身。”又云:“将吏俨成列,簿书纷来萦。”然而,政务繁忙并不代表毫无寄兴之暇,刘禹锡在给令狐楚的和诗中说:“簿书盈几案,要自有高情。”实际上,这也是和者的夫子自道之语。上揭“勤政不得逍遥”之疑事关和州,然而翻检文集可知,刘氏在和州撰写的唱和诗为数并不少,其中不乏“历阳秋色正澄鲜”、“对此独吟还独酌”之句*分别见刘禹锡:《到郡未浃日登西楼见乐天题诗因即事以寄》、《早夏郡中书事》、《和令狐相公春早朝回盐铁使院中作》、《张郎中籍远寄长句开缄之日已及新秋因举目前仰酬高韵》,《刘梦得外集》卷二、卷三、卷六。。
问题的关键在于,《铭》文所寄之兴,其实只是对某种生活片段的感悟和欣赏,远不等于作者生活状态的全部。换言之,属辞造境中的陋室之“无”,反衬的恰恰是仕宦生涯中的官场之“有”。正因为平日治公有案牍之劳形,广座应酬有丝竹之乱耳,故而陋室之中的宁静和解脱才值得再三吟唱。

然而,刘禹锡毕竟是有政治追求的士大夫官僚,他的个性之中又深植了乾健不息的豪迈基因,因此,陋室调琴的隐逸情趣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精神按摩,并不意味着他对案牍簿书、丝竹应酬果持鄙薄厌恶之情。即以前揭《罢郡归洛阳闲居》为例,在咏完花间酒、月下琴之后,刘氏仍以“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收尾,可见他的确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而在《昼居池上亭独吟》“法酒”、“清琴”句之后,刘氏又吟叹道:“浩然机已息,几杖复何铭。”后面这两句尤为有趣,一则机息云云绝非写实,这从他临终前犹作《子刘子自传》、为贞元朝士辩解可以看出;二则由此可知,铭文字面与作者本心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论者若以为控缰必不欲马跑,进而据之考求文义史实,恐不免南辕北辙之讥。此系题外话,不赘。
三、陋室题材的时代共性
前文所述,是《陋室铭》与传世刘集在文本上的关联契合,重在从创作个性的角度证其为真。接下来,则试就中晚唐文士对陋室题材的普遍吟唱略加分析,以便从时代共性的角度破除伪作晚出之疑。

崔、刘之外的同题创作,史无详书,无由征实。但在诗中咏及陋室以表深意者,则不难考见。此类吟咏可藉刘禹锡之言剖判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悲其不遇,无成而亏”;另一种是“悲其不幸,既得而丧”。接下来,笔者谨就两种情况次第说明之。

深得韩愈赏识的鬼才李贺亦有近似表述,其《绿章封事》云:“金家香衖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骨埋蒿里。”秋为肃杀萧条之象,秋室即陋室。清人王琦《汇解》云:“富贵之家,生前奉养,志意满足,可以无恨。惟穷约之士如扬雄者,陋室萧条,赍志以没,不能不抱恨于地下……盖为士之不遇者悲乎?特借扬雄一人以概其余矣!”*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8页。而李贺本身便是不遇之尤者,当他元和三年(808)赴长安应“礼部试”之际,有妒才者攻讦道:“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虽有韩愈为之作《讳辩》,终不免失意落第之局。其后李贺谋得奉礼郎小官,在长安任职三年,郁郁不得志,《绿章封事》诗即当作于此时*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收入《梦苕盦专著二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4、40、48页。。



上述诸人中,崔沔属于生年不相接的前辈,但他的孙子崔植却是刘禹锡的同辈人,且相互间有宴游交往、联句应酬;李贺属于晚生近二十年的后辈,但他的亡故却早于刘氏之卒逾二十年,文名互知不难想见;至于韩柳元白,皆与刘禹锡有密切关系,其中柳宗元、白居易更是刘氏早、晚年的兰交挚友。
再看刘禹锡的人生轨迹。他早年科举得意,仕途看好,一旦卷入高层政争,遭遇失败,遂被贬斥遐荒二十余年,其“既得而丧”之悲与柳、元、白并同,但蹉跎岁月之漫长则远远过之。而其经济上的拮据,又恐不让于崔沔,一则谪宦蛮陬、官俸有限,二则鳏居甚早、抚养丁口甚多(己子、柳氏遗孤、韦绚等)。因此,即便晚年宦情好转,仍不免有乏金之叹。白居易《酬梦得贫居咏怀见赠》云:“厨冷难留乌止屋,门闲可与雀张罗。病添庄舄吟声苦,贫欠韩康药债多。日望挥金贺新命,俸钱依旧又如何?”*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三十五,第908页。刘氏原诗仅存白注所引残句“若有金挥胜二疏”,咏贫之意已瞭然可见。在此番唱和之前数年,刘氏已有类似调侃,《酬乐天闲卧见忆》云:“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刘禹锡:《刘梦得外集》卷四。
由上文所述可知,其一,唐人的陋室之咏或出于仕途坎坷,或出于生活贫困,而这两种因素在刘氏生命中都有极为深刻的体现,从早岁受谴到晚年贫居,刘氏几乎一直面临此类窘迫的创作诱因;其二,传世唐人诗文集中的陋室主题或辞句,至少以鸟瞰式考察来看,几乎全部集中于上揭文学群体,究其根由,一方面,是因为时代背景相同,人生际遇近似,另一方面,除崔沔以外,余者皆是同时代交往甚密的文学巨擘,相互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程度的切磋或影响。
[责任编辑 渭 卿]
孙思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研究馆员(湖南长沙 410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