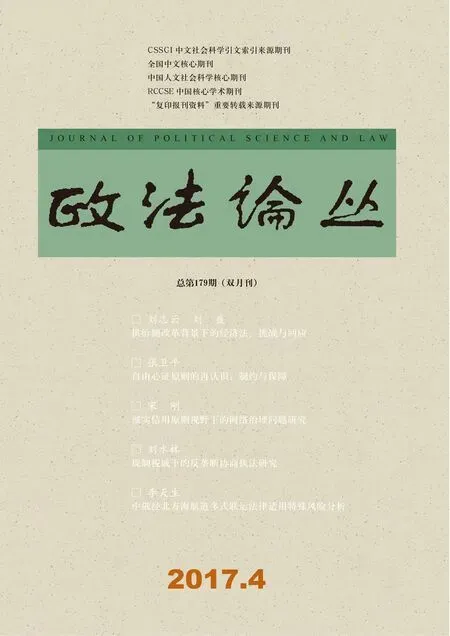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经济法:挑战与回应*
刘志云 刘 盛
(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经济法:挑战与回应*
刘志云 刘 盛
(厦门大学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随着我国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转变,传统凯恩斯式的需求侧短期干预已经无法使我国迅速摆脱国内外经济增长双重疲软的境况,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V字型反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亟需从需求侧拉动的“单腿支撑”向供给侧为主,适度扩大需求侧的“双腿走路”迈进。当前中央对供给侧改革的多项部署,对缘于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之校正和寻求政府与市场博弈均衡解的经济法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需要经济法主体制度通过制度性变革来推动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明确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独立性,完善产权、社会分配等制度来保证市场主体的权益。需要经济法宏观调控制度从具体的财政法、金融法、产业政策法和发展规划法出发,推动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之形成。需要经济法市场规制制度通过完善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市场竞争法律体系来建构宽松的投资经营环境,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供给侧改革 经济法 经济法主体 宏观调控 市场规制
一、导论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2011年以后,我国经济便已经告别两位数增长状态而进入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新阶段[1],在经济高速发展背后长期积聚的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突出矛盾和问题暴露无遗,集中表现为近期的“四降一升”现象,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2]随着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城镇化步入后期、产业结构逐步调整、一般技术水平的发展等要素的变化,以往支撑经济强劲发展的大规模投资刺激、人口红利、低起点经济体的“后发优势”等动力源逐渐偃旗息鼓。传统单纯依靠需求侧“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已然失灵,我国经济亟需一场“驱动革命”来重焕生机。从2013年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到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经济新常态,再到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提出的供给侧改革。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理性认知不断深化,应对路径逐渐明晰,提出了“在适度扩大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3]的“双驱动变革”。
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改革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面部署,包括实施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支柱;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把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三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等相关内容。权威人士将之解读为“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对供给侧改革进行了深化部署,要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指出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并重点部署了“三去一降一补”、农业供给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等具体任务。
无疑,经济增长速度的减缓是我国当前下行经济形势的最直接表现,而其深层次的“病因”则主要在于结构性、制度性的矛盾,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一剂从源头出发的标本兼治“药方”。从宏观层面来看,其有利于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转变;准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协调两者关系;扭转供给需求的错配,提升两者的适应性;激发各主体活力和创新潜能,刺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等等。就微观层面而言,则有助于推进国有企业深度改革;更好地处置僵尸企业以化解过剩产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等等。这不仅是推动我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需要,更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显然,无论对供给侧的质量改进还是结构性的优化调整,都必须以改革作为落脚点,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摆脱对以往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建立起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机制,以此保证和推动供给侧管理和结构优化调整。而在法治国家,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变革、保障和引领则必然是以法律为归依的,与经济密切联系的经济法无疑将在这场经济引擎的变革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完全竞争市场体制的假设早已被常态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现实所击溃,在“看不见的手”出现失灵(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缺位等)的情形下,国家的适度干预就显得尤为必要。而国家干预行为的具体行为者——政府也远非万能,其经济人的本质所带来的有限理性和政府部门如影随形的“帕金森定律”极易使得政府也陷入失灵的沼泽之中。经济法正是在这两者的双重困境中应运而生,其一方面要克服市场的失灵,另一方面也要遏制政府的膨胀。但实际上,我国经济法的制度供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均表现出极强的政策性和浓重的自上而下的公法气息,公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已然成为默认模式,这固然保证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却也助长了结构性动力的偏颇。
当前供给侧改革所具体要求的政府治道变革、供给侧为主的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内容,从根本上说就是要重新认知和厘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两者以往错配角色的转换。一方面,要矫正以往政府对资源的过多或不当干预,调整各类政策和制度安排,为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环境,尊重市场的决定性地位;另一方面,也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多做“干预减法”,将“有形的手”作用于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法治框架的搭建之上。这无疑对缘于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之矫正,寻求市场与政府博弈之均衡解,并长期被公权力浸染而扭曲的经济法提出了重大挑战,这些挑战和要求,将最直接地反应在经济法的各项基本制度之中。
经济法主体制度需要从如何实现各主体权义的合理界分、保障地位的形式与实质平等、激励主体活力和创新能力等方面进行变革;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则要对如何更好地协调供给侧与需求侧、保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等方面进行回应;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则要着眼于对宽松的投资经营环境、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秩序、生产要素的顺利流通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等方面提供制度保障。
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经济法面临的挑战
作为一种“因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需要而产生,因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实践而发展的国家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活动的基本法律形式”[4],与经济的密切联系使得经济法将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扮演一个异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对社会发展模式所进行的供给侧改革给经济法各项具体制度所带来的挑战推动了经济法的适应性变迁,使之更具时间、空间上的有效性,指明了经济法的进化方向;另一方面,经济法也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在引领改革进程的同时,对改革行为进行约束,并以其确定性将改革成果固化。
(一)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经济法主体制度面临的挑战
通常认为,经济法主体即经济法律关系主体,是指参加经济法律关系、拥有经济权限的当事人。[5]P118在现代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正逐渐由一种彼此制约的状态向彼此依存的状态转化:一方面是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过多干预,另一方面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市民社会对国家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权力分享,这便是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的双向运动。[6]P47过程和结果双重正义的要求促成了国家对社会干预的社会国家化,而国家社会化则表现为管理社会权力中心的多元化,团体社会开始作为代表一定社会利益的权力载体出现,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在这样一种理论趋势下,经济法主体制度开始向“三元化”变迁,即国家干预主体、社会中间层主体和市场主体的三足鼎立。无疑,结构性的变革和供给质量的提高都将通过主体的一系列作为来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主体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基点,供给侧改革的全部制度革新,都是为了通过打破以往扭曲的权义配置和制度枷锁来重新调整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唤醒主体的活力和创新动力。其在经济法的语境下具体表现为:要求政府主体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实现向法治政府的转型,搭建良好、宽松的政策环境;要求中间层主体确保其独立性和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向矫正作用的发挥,刺激本行业创新动能;要求市场主体激发企业家精神、加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投入、提升供给质量。这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给经济法主体制度的变革提出了挑战:
一是要求通过制度刺激来激发主体创新活力。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早已为大家所认知,其原因不仅包括需求侧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消费的疲软,也包括供给侧以往的廉价要素,如劳动力、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的成本上升。此时,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型,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主体一方面要充分调动自身纵向维度的中央与地方、横向维度的不同部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另一方面也承担着通过培育市场化的创新机制、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私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营造有利于主体创新的软环境等方式来刺激其他主体创新活力的责任;社会中间层主体则需要以其“特定社会利益的权利载体”这一特性,通过提供准公共产品等方式来刺激相关主体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的形成;市场主体则应当通过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注重创新人才的培育、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等方式来激发自身的创新能力。当前的经济法主体制度,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主体积极性和创新活力的发挥(如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且挤占资源、民营银行长期没有入口等),同时也阻断了制度对主体创新欲望的刺激作用(如制度性成本的居高不下、知识产权保护的欠缺等)。由此,经济法主体制度一方面应当保证各主体创新能力的正当发挥,另一方面更要通过制度安排激发各主体的创新活力,其对市场各主体的权义分配、相互关系等设计则将在包括强化市场主体的创新主导地位、明确政府与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分工、对创新的激励和保护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二是要求通过制度矫正来保障主体地位平等。无疑,形式与实质的平等是提升主体创新能力和激发主体积极性的重要基石,但当前所存在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政策区别、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融资差异、行政力量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错位等现象却无一不在控诉着实质的不平等充斥于每个角落,制约着主体创新的欲望和能力。供给侧改革所提出的鼓励和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明确企业的创新和投资的主体地位、全面开放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等具体政策,不仅是对实质不平等问题的回应,同样也是对经济法主体制度的变革要求。与以市场为单向度进行体系构建进而关注市场主体抽象平等性的私法不同,以对政府与市场这对基本矛盾关系整体性回应为基点的经济法必须考虑“政府”与“市场”两个向度,在此种“二元架构”之下的经济法主体制度呈现出天然的不平等特性,不仅表现在不同向度内部,也凸显于两种向度之间。供给侧改革对各主体地位平等的要求无疑与经济法主体制度基于二元架构下实质平等的关注相契合,面对当前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供给侧改革的要求,经济法主体制度理应按照不同的主体视角,从市场准入、财政税收调控、机会平等、私权保护等方面来进行制度矫正。
三是要求通过制度调整来纠正主体角色配置。实践表明,需求侧引擎下的政府全面刺激方式的边际效益正在显著减弱,而政府有形之手对各类要素的过多干预也扭曲了市场经济模式下各主体的正当角色安排。在我国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从简单分工向复杂分工的转变,传统凯恩斯式的需求侧短期干预已经无法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的境况下,经济引擎由需求侧单向拉动转变为以供给侧为主、适当扩大总需求的双向拉动成为必然。而在这一进程中,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则成为了矫正各主体角色的当然导向。以经济法的视角观之,就是要以法律的方式重新廓清政府主体、社会中间层主体、市场主体的角色,明确地位,厘定界限。这至少需要经济法主体制度从缩减政府权力、规范行使程序、均衡政府权责;立法明确行业协会等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独立地位;确立企业在市场上的主体地位;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等四方面进行制度调整。
(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经济法宏观调控制度面临的挑战
无论是在“需求侧”拉动还是在“供给侧”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市场所固有的自然垄断、外部性、信息失灵等缺陷其自身无法克服,需要政府通过宏观或微观的行为对其进行修正。即便是在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历次论战中,也没有任何一种学说完全杜绝政府与市场任何一方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某种程度而言,现代经济就是一种调控的经济。无疑,经济的结构性变革离不开政府“为实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平衡,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而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对社会经济进行的宏观调控”[7]P200,同时也需要宏观调控法“来防止宏观调控中的主观恣意、政府失灵和调控失败,保障宏观调控关系的规范、科学和高效运行”[8]。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需要在宏观调控法的实体和程序规则下实施,总体来看,当前的供给侧改革对政府宏观调控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而这同样也是对经济法宏观调控制度所提出的挑战。
首先是要注重协调供给侧与需求侧。当前的结构性变革,是一种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着力进行供给侧改革的结构性变革,供给侧与需求侧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互为条件,相互转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但鉴于当前的结构性矛盾是主要矛盾,故而应当以供给侧改革为主,扩大需求为辅。具体而言,一方面要紧扣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来提升供给质量,推进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优化消费环境、鼓励消费品和服务创新、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扩大有效投资等方式扩大需求总量和调整需求结构,促进供给需求的有效对接。这些目标的达成,显然离不开宏观调控法的作用,例如,要通过财政法、税法正税清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产业政策法要明确通过何种方式、对何种产业进行扶持;社会保障法如何发挥“稳定器”作用,更好地保障民生,等等。
其次是要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现代经济是宏观调控的经济,政府通过总量控制的方式进行的宏观调控对市场主体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的重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在供给侧改革这样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中,政府的宏观调控不仅需要引导市场主体沿着进行结构转变、提升供给质量的道路行进,更承担着稳步跨过转型阵痛期,稳定社会心理预期的重任。例如,去产能的推行无疑能够促进优胜劣汰,优化要素配置,却也造成了“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场面(尤其是对“僵尸企业”的处置),政府不仅要依法完善退出机制,也要妥善解决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等问题;在去库存过程中,政府一方面要通过推行户籍改革、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来缓解库存压力,另一方面也要鼓励房地产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降低价格,进行优化重组,提升集中率;在补短板方面,要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包括多方面开展农业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脱贫攻坚措施、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对此,宏观调控法也应当作出相应的考虑,在引导市场行为方面,产业政策法不仅要注重三大产业的合理配置,更要注重促进农业现代化、向制造强国转变、推动服务业发展,引导生产要素流向,提升供给品和服务的质量;财税法要注重制度性费用的降低和税制改革,为实体经济让利,引导市场主体加大对技术要素的投入;价格法要充分发挥其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促进生产和消费机构的合理化等。在稳定社会心理预期方面,要通过预算法、税法、货币法等相关法律的完善,厘清政府宏观调控权力的界限,防止行政权力对市场的恣意扭曲,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尽早出台发展规划法,将发展规划纳入法制化轨道,明确阶段化的发展目标和产业规划,防止发展政策的恣意妄为和朝令夕改。
最后是要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供给侧改革这样一场关键性的深刻变革中,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历次的供给侧改革相关会议多次提到要保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宏观政策要稳也赫然成为五大政策支柱之一。具体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提高财政赤字率主要用于减税降费、提高政府适当投资的质量、加快分税制改革;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继续保持并灵活适度,调节好货币闸门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足、完善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并保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改革、稳妥推进民营银行发展、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对此,经济法宏观调控制度无疑应当作出回应:预算法要推动预算更加科学合理,既要降低企业税负,又要保障政府民生兜底作用的发挥,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税收法律要正税清费,保障分税制改革、营业税改增值税的稳步推进;货币法律要保障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准备金率、再贷款等各类货币政策工具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运作,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金融法律一方面要破除国家对金融行业过多限制而造成的金融行业垄断集中、金融资源严重错配现象,优化融资环境,另一方面也要注重监管体系的改革,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
(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市场规制制度面临的挑战
狭义地看,与调整宏观经济的法律相对,市场规制法是对微观经济进行规制的法律,其勃兴于放任自由市场条件下被形式平等掩盖的实质不平等日益凸显而导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偏离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具体而言“是指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为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对影响市场秩序、偏离市场经济要求的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规范的总称”[5]P227,其核心在于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规则性和经济状态稳定性的强调。良好的市场秩序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市场主体内在的自我调控与自我约束能力;二是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外部规制。[5]226实践表明,单纯依靠市场的自发秩序极易使得市场主体在逐利本性的引导下背离社会利益,进而造成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毕竟“作为一种自发的秩序,它的有序性并不取决于它有单一的目标序列取向,因此它并不保证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它来说,凡是它认为重要的,就会优于次要者”[9]P347。良好市场秩序的保证需要市场秩序和外部规则的共同作用,这一外部规则的运作应当建立在充分尊重市场秩序和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决不能越俎代庖地取代市场秩序的主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中的自发秩序被本身就具有强烈利益偏好的外部管制所压制,资源配置长期扭曲、市场主体积极性严重挫伤。市场自发秩序与外部规制的双重扭曲,显然有悖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无益于经济结构的转型。在供给侧改革的进程中,无论是对结构性调整的推进、要素配置的矫正,还是供给质量的提高、消费需求的刺激,均对市场规制法律制度提出了要求和挑战,具体而言包括:
一是刺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供给侧视角观察,经济活动总量(Y)是由劳动力总量(L)、资本总量(K)和效率水平(A,即TFP)等三个基本因素决定的,即Y=A·Kβ·L1-β。[10]P8随着我国人口“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逐步凸显,继续依靠劳动力增量和资本投资增量这两大供给要素的投入已经无法支撑我国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状态,必须依靠效率水平(TFP,也即全要素生产率)所包含的制度供给和科技创新来适应当前的经济新常态。而如何“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11]P153,不仅需要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变革来为营造稳定的市场环境、开放要素市场、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刺激消费者潜力提供良好的规则供给,同时也需要通过这种制度供给来促进科技创新,提升供给质量。具体可以包括:通过《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法律的完善,把控供给质量,制定激励性规则刺激企业主体加大对产品创新、技术进步的研发投入;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根据形势变迁,通过对市场交易主体权利义务的倾斜性配置和纠纷解决方式的创新等手段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实现对消费潜力的间接刺激等。
二是推动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物竞天择是自然界的铁律,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供给侧改革所提出的市场主体创新能力的激发、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有效供给的提升等要求均离不开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但市场内生规则的必然发展方向是沿着自然垄断的道路越走越远,需要通过一个公平、有序、透明、开放的市场竞争规则来从外部对其进行纠偏,这同样也是供给侧改革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制度供给创新的要求。“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一直坚守的一个重大方针政策,同时也在不断强调不同所有制主体的平等地位,但长期以来的实践表明,非公有制主体的平等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不仅体现在行政垄断行业的门槛上,也凸显于具体的经营过程中。这无疑不利于非公有制主体的活力激发和全社会创造力的聚合,可以通过全国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建立来打破行业门槛、破除市场壁垒。同时,完善竞争法律体系,打破地区和行业封锁,规制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的横向与纵向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助推经济引擎的顺利转变。
三是厘清政府市场规制权边界,保障市场基础作用的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现代经济关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实践中,政府对市场的适当干预已然成为共识,这一适当的标准,便是市场失灵。在当前的供给侧改革过程中,无论是五大政策的持续推进还是“三去一降一补”任务的重点开展,都离不开政府对市场的能动作用。例如,微观政策要活需要政府通过价格、产品、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调整来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去产能方面要加大对“僵尸企业”的处置力度,在严格执行环保、安全、质量、技术指标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基础上,推动企业的兼并重组,等等。但显然,这一能动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充分遵守市场规制法律的基础之上,而对于市场规制法律来说,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政府权力边界的清楚界定来保证市场的主体地位。毕竟作为一种兼具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政府的市场规制权力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极易异化为一种扭曲市场秩序的强制性权力。“市场缺陷只是国家干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国家干预只具有修复市场失衡、使市场均衡的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失灵问题都可以由国家干预,当国家干预不经济时,国家干预成为不必要。”[12]P26也即,政府的市场规制权只是在市场自发秩序失范的情形下的一种“修补”(或者说暂时的替代性手段),而非永久的取代性规则,市场规制法律所确定的其作用的前提和范围应当是市场秩序失灵的领域。例如,放开电力、石油、电信、天然气等行业的准入门槛,减少行政干预设置的壁垒;通过在市场准入、金融体制、要素配置等方面创造便利条件的方式支持中小微企业更好地参与市场公平竞争,等等。
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经济法对挑战的回应
制度会因国家的能动作用或新获利机会的引诱而出现强制性变迁或诱致性变迁。虽然中国社会的整体制度性安排日益发达,几乎覆盖社会的所有领域,但当现实社会结构分化及冲突所造成的不确定风险来临时,现有的制度资源供应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够既具合法性又有正当性地给予有效应对。[13]而结构性动力转型这一变量的加入则进一步激化了制度供给和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由此,实践中关联制度的适应性变迁便显得毋庸置疑。供给侧改革给作为正式规则的经济法的主体法律制度、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市场规制法律制度所提出的种种挑战,实际上就是要求其进行“均衡——非均衡——均衡”的制度变迁,从而在特定的时空内完成对各主体活力的“制度抑制”到“制度松绑”再到“制度推动”的过程,为供给侧改革增添助力、保驾护航。
(一)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经济法主体制度对挑战的回应
制度的创新与变革是当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义,面对供给侧改革所提出的激发主体的创新活力、保障主体的平等地位、纠正主体的角色配置三大挑战,我们可以从不同类型的主体视角对经济法主体制度的变革进行考量。
首先是国家干预主体制度。如果说以往的“需求侧引擎模式”强调了政府“有形之手”的干预作用,那么当前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大力弱化政府对要素的控制,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历次相关会议所提出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制度性成本”、“通过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来指导产业发展方向”等内容和陆续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方案(要点)的通知》等文件均体现了对这一要求的实践回应。经济法的宗旨之一是界定国家(政府)权力、规范国家(政府)行为和明确国家(政府)责任,它规定什么样的国家(政府)机关才能作为经济管理机关介入市场成为经济法的主体。[14]P203由此,经济法主体制度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的明确政府地位、厘清政府权责、规范权力行使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其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变革以确保政府作用的稳步转换:一是以制度形式确立和落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政府以往的父爱式干预理应得到遏制,其应当作为一个宏观政策的制定者而非微观政策的实施者。例如,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审批程序、规范中介服务、开展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等等以降低市场主体的制度性成本;以企业为主体,市场机制为基础,政府辅助推动的方式化解产能过剩;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允许基层开展差异化探索,发挥基层首创精神等。二是通过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构建来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建设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在于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其是削减和弱化政府过重的经济管理职权。[15]以往对政府权力的正面列举和责任的原则性规定极易造成“挂一得万”式的权力膨胀与“互相推诿”的责任模糊,需要在削减政府权力的基础上,逐一明确各项权力的法律依据、实施主体、具体权限等内容,并与相对应的责任主体、责任方式等内容相匹配。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模式能够很好地杜绝政府在“空白地带”的矫揉造作,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则很好地体现了“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理念,无疑能够极大地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三是创新监管网络以优化监管机制。包括监管理念、监管主体和监管手段的优化,监管理念方面,要完全地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建立责任明确、职能清晰、程序规范的监管制度;监管主体方面,充分调动各主体的意识,构建一张包括政府监管、企业监管、社会监管以及舆论监管在内的多主体、多层次监管网络;监管手段方面,应当注重运用大数据、云平台等技术手段对数据进行搜集,提高监管效率。
其次是社会中间层主体制度。社会中间层主体主要是指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市场主体之间起到“润滑”作用的组织,包括社会团体、专业性服务组织和行业协会等机构。社会中间层的兴起不但有对抗政府权力干预的作用,而且在经济法价值目标——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中还是重要的实施主体与利益承担主体。[16]在供给侧改革的进程中,各主体创新活力的激发、平等地位的保障、权义的界分与均衡均离不开社会中间层主体对市场与政府缺陷的双向矫正和作用之发挥,例如,市场主体不完全竞争情形下的非政府性协调、资源配置扭曲下的第三方矫正、激励创新的准公共产品的提供等等。总体来看,经济法主体制度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调整来保证社会中间层主体在供给侧改革中正当作用的发挥:一是以立法明晰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独立地位,在以往“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之下,我国社会中间层主体被异化为延伸政府干预权能的触角,不仅类型欠缺、毫无独立性可言,更成为一种政府对市场发号施令的“单向通道”。由此,在以权力和责任清单厘清政府权责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明确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独立性地位就成了发挥其正当作用的充要条件。2015年7月印发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二是通过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的模式来规范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权力与责任,同时确保其具有一定的职能可以提供包括激励创新、消除地方与行业壁垒、促进同质主体平等、减少恶性竞争等内容在内的准公共产品。
最后是市场主体制度。市场主体主要指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和个人。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市场门槛、运作规则、退出机制以及资源配置的强势干预造成了其他市场主体主观能动性的严重缺乏,企业产品同质化、产能过剩、粗犷生长、技术滞后;消费者因信息不对称、维权意识缺乏等问题屡屡被侵权;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护等问题比比皆是。随着改革红利的消失,政府作用的边际效益递减,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亟需由需求侧拉动向供给侧拉动转变,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市场主体自身的变革必不可缺,而经济法主体制度的良好制度供给也显得尤为重要。第一,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体权利、机会、规则等层面的平等地位。此处主要涉及到消除当前对民营企业的差异化待遇,包括放宽准入,凡是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都应当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通过惩罚性或激励性措施消除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的问题;严格查处侵犯非公有制经济体或个人的合法权益的行为等。第二,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对产权的良好保护能够为市场主体通过对技术要素的投入来提升供给质量注入强劲动力,对其进行制度化的确定则更是以其确定性保障了市场主体对其利益获取的预期。第三,构建体系化的社会分配制度,以强行性规定明确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初次分配和以税收为主要手段的第二次分配,以激励性手段刺激富人在自愿的基础上为穷人提供帮助的财富第三次分配。第四,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稳妥推进去产能。在继续去除钢铁、煤炭等行业过剩产能的过程中,也应当防止已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加快处理僵尸企业。创造条件推动企业的兼并重组,完善市场化的退出机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的审理,并将之制度化。第五,持续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混合所有制变革、落实企业董事会职权、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经营者、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实现国有企业提质增效。
(二)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对挑战的回应
无疑,宏观调控法并不是要去准确预测一个国家的经济形势,也不是去界定一个国家经济波动的样式和幅度,更不可能去事先规定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应选择什么样的手段或者如何组合这些手段。[17]当前的供给侧改革需要政府在行使宏观调控权力的同时注重形式和方式的创新,强化区间、定向和相机调控,统筹运用财政、货币、产业、投资、价格等方面的政策工具来提供手段支撑。在我国宏观调控基本法律缺位的情形下,经济法宏观调控制度应当根据供给侧改革的要求,在重新审视各项具体法律制度中宏观调控权力的配置、手段的规范和程序的正当化等问题以保障政府宏观调控权力的合法合理运作的基础上,对如何纠正角色配置、实现权责平衡、协调经济结构、维护经济环境稳定等内容进行具体的制度性考量。
首先是财政法律制度。按照一般的经济法分类,财政法律体系主要包括税法、预算法、国有资产管理法、政府投资法等相关法律制度,在此我们以税法和预算法为例。对税法来说,其至少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科学推进分税制改革。我国当前财税体制中税权、分配权的集中体制和实践中“事权不断下压,财权不断上收”的现状使得地方政府不仅在税权和收益权等方面处于极端的弱势地位,也导致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严重失衡。这一方面促使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增加非税收入,从而加重企业的负担,另一方面也挫伤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且没有足够的财力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这无疑有悖于供给侧改革降成本、补短板的要求。对此,税法应当在严格遵循税收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厘清中央与地方的事权,按照事权分配财权,以法律而非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形式明确规定税收立法权、征管权和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收益的具体划分制度。二是持续推进结构性减税,降低税率,简化税则。企业税负过重一直是影响我国企业创新能力、扭曲企业要素配置、加重企业负担的重大问题,在供给侧改革充分发挥主体创新能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供给质量等要求下,结构性减税依然是税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对此,税法应当在降低流转税率,减并税率档次;个人所得税向综合所得税方向转变;减少重复征税,精简税种等方面提供制度性保障。三是合理利用减税、退税、抵免的方式完善税收优惠体制。我国长期以来对国有大型企业较多的财政投入和税收优惠不仅造成了市场上的“马太效应”,也扭曲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造成资源的浪费。在此方面,税法应当将税收优惠的决定权、运作程序、适用条件等内容予以透明化、确定化,一方面实现税收优惠的实质公平,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加合理地运用该手段支持企业创新,提升供给质量、促进小微和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化解过剩产能、将房贷利息支出增加为抵扣项目以减少库存压力,等。
预算法作为一种规范财政收支总体安排的法律,已然成为反映国家对公共资源的统筹和支配能力,以及治理方式的最重要规范。2014年8月31日,历经四审的新预算法最终获人大通过,其在推行全口径预算、实施公开透明的预算运行机制、规范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债务、强化人大监督等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很好地体现了“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立法指导思想。这些新举措对供给侧改革不无裨益,但“法律一经制定便落后于时代”,在深入推行供给侧改革的进程中,2014年预算法显然还有不少值得改进的地方,例如,从授权、限权和程序等方面进一步细化与规范地方政府发债、政府性基金和中央转移支付的规范,防范地方职务风险,厘清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增强地方政府融资渠道以更好地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完善预算编制过程的公众参与和实施过程的公众监督机制,保证渠道畅通,以稳定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提升政府公信力等。
其次是金融法律制度。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促进金融体制的革新。当前国家对金融行业门槛的过多限制无疑是调控过度的表现,促成了金融行业垄断集中、金融资源严重错配。金融体制改革是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之一,相关金融法规应当在明确政府对金融业宏观调控基本权力的基础上注重对该项权力的削减和规范,当前民营银行准入的放开就是很好的开端。二是提升金融监管能力。控制总杠杆率、防范金融风险、优化融资环境等内容无疑是供给侧改革推行的重要方面,这预示着政府的监管能力需要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升级。具体而言,监管理念要向实施审慎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和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双峰监管理念转变;监管模式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迈进;优化监管工具,建构与完善风险评级机制、风险预警机制和问题金融机构处理机制等,更好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构建稳定的金融环境以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顺利推行。三是规范货币工具的合理运用。现阶段的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的结构化转型,作为一种典型的总需求管理手段,货币工具无疑具有异常重要的作用。对此,货币法律应当为政府合理运用货币工具从而促进供给侧改革提供制度支撑,例如,完善授权,保障公开市场业务、存贷款基准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灵活与针对性开展,以强化流动性调控、降低实业的融资成本、扶持“三农”与小微企业;限制政府过度干预,尊重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推进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完善等。
最后是产业政策法和发展规划法。“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等,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3]是供给侧改革中产业政策要准的具体内涵之一。作为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明确各产业部门的地位和发展方向、规范政府对产业调控行为的产业政策法,应当着重通过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引导而非政府指令性的规定来促进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合理布局和优化升级,以市场化的方式化解过剩产能,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扶持中小微企业、高新企业的发展。发展规划法的长期缺位使得我国在规划编制的过程中常常出现规划体系不完整、审批主体不明确、中央与地方规划不协调、具体规划变动性大等问题。尽早出台发展规划法以明确规划体系、编制程序、实施机制、权责分配等内容就成了必然,而这实际上,也是防止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出现政出多门和朝令夕改,增强政府公信力、稳定社会预期的必然要求。
(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市场规制制度对挑战的回应
作为规制市场交易秩序和市场竞争秩序的各项法律制度的综合,市场规制法不仅是对市场自发秩序失灵时的矫正,也是对政府市场规制权界限与强度的明确,针对前文所述的供给侧改革所提出的挑战,市场规制法至少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首先,完善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以保障供给质量的提升。作为一种致力于加强产品质量监管、提高产品质量监管、明确产品质量权责的法律,《产品质量法》无疑是最直接地作用于提升消费品、工业产品、服务业供给质量的规则,该法的完善必然对供给侧改革产生极大助力。第一,提高质量标准并与国际接轨,在消费品方面,促进内外销产品的同标同质,倒逼企业增加技术投入,增加高水平供给;在工业产品方面,推动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与企业的联动共治,建构全面的质量安全评级体系;在电子商务等新业态领域,充分利用既有的互联网技术支撑,建构质量追溯、信息采集、风险预警等系统,提升新业态的供给品质。第二,充分完善和利用生产许可制度,严格控制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的新增产能,淘汰落后产能。第三,当前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已经成为主流,这就要求《产品质量法》进一步保障质量安全,推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的发展以提升产品品质、创设品牌并增强粘性。第四,通过在产品质量抽查运作程序的统一、联动抽查机制的构建、产品质量全程追溯机制的设立、风险全程监控制度的完善等方面的改革来加大产品质量监管力度,完善监管体系。第五,构建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从反面制约某些企业对产品的“粗制滥造”以保证供给质量。在有关食品安全法律方面,除了要通过食品安全诚信体系、惩罚性赔偿、安全风险交流、自我规制、责任追溯等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来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民生外,还应当着重注意实施农产品标准化与品牌战略、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与监管体制、强化风险分级管理和属地责任等,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助推农业供给侧改革。
其次,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刺激消费能力提升。无疑,当前的结构性改革并不是在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做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应当在适度扩大“消费、投资、出口”的同时,着力进行供给侧改革。在激发消费潜能方面,除了提升供给质量的正向刺激之外,也应当注重优化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反向作用。具体而言,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从惩罚性赔偿金计算基础的优化、将赔偿主体扩大至缺陷产品生产者、明确惩罚性赔偿金的参考因素等方面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包括金融交易冷静期制度的具体安排、金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统一规定、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教育宣传等;明确产品信息的披露方式、顺位,并以反向列举的方式规定披露内容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等。
最后,完善市场竞争法律体系以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刺激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市场竞争促成了资源的最佳配置,但实现效率的市场本身并不能同时关注公平与效率,反而容易形成自发的垄断。此时规制市场的外部规则便有了用武之地,但外部规则如果干预不当也容易造成人为的垄断和资源配置的扭曲,典型的就是我国大量存在的行政垄断。当前我国许多要素领域便存在着自然或人为的垄断、资源配置的扭曲等现象,极大地遏制了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阻碍了供给质量的提升。无疑,优化竞争法律体系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来助推供给侧改革就成了必然。第一,化解产能过剩与去除房地产库存的任务暗含了少破产清算、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整合优势产能的要求,这固然有利于生产要素更有效率地流通、配置和利用,却也容易出现垄断情形,妨碍市场竞争。对此,相关的竞争法律应当在进一步优化监管体系与手段,加强审查力度,扩大惩罚权实施的广度与深度的基础上,着重考虑如何与产业政策相协调,把握行业集中与市场垄断之间的最佳中点。第二,构建与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无疑,国务院于2016年6月1日印发的《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为杜绝行政机关滥用权力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构建统一开放、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体系,激发主体创新动能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进一步的改进方向应当包括出台实施细则规范审查标准、方式与程序;明确自我审查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监督的内外部审查机制,并充分发挥上级监督性审查和群众审查的作用等。第三,农业反垄断豁免制度的完善。对农业进行反垄断豁免早已成为各国共识,而推动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发展更是进行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我国《反垄断法》对该制度进行了原则性规定,有必要从豁免主体、范围、类型等方面将该规定进行明确与细化,同时应当反向明确农业生产者或农村经济组织不得实施类似于排除竞争、过度提高价格等的恶性竞争行为。
四、结语
早在1996~2000的“九五”计划时期,我国便已经提出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但为何直到现在仍处于改革的“攻坚战”和“深水区”时期?有学者指出,“其关键在于能不能通过改革建立起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机制”[10]P11。无疑,与经济紧密相关的经济法将会是这一体制和机制的最好载体之一。
供给侧改革的推进离不开主体活力的激发,而通过制度变革的活力激发是提升各主体创新动能的基本外部要素。经济法主体法律制度需要在保障各主体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实现权义的清晰界分和正当均衡,进而激励主体的创新活力。应当通过制度性的变革推动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明确社会中间层主体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完善产权、社会分配等制度来保证市场主体的权益。
现代经济是调控的经济,供给侧改革需要政府通过其宏观调控权力来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协调、引导市场行为和稳定社会心理预期,作为规制该项权力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应当对财政法、金融法、产业政策法和发展规划法等规则进行优化升级,促进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形成。
供给侧改革既需要政府在宏观和微观层面的调控,更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任何层面的外在调控都应当是建立在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的合法合规的依法调控。在微观层面,供给侧改革所要求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宽松的市场投资和经营环境的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架构和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均需要市场规制法律制度从完善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和市场竞争法律等方面发力,打造一个公开、公正、有效、合理的市场规制法律体系。
无疑,经济法的各项具体制度应当作为一个整体被看待,而非割裂地进行自顾自地制度性变迁,在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进程中应当立足于整个经济法制,追求经济法治的实现,防止和反对局部制度的冒进变革损害整体效果的实现,同时,也应当注重各项具体制度的特征,通过制度变革更好地适应供给侧改革,充分发挥局部的作用,形成良好的制度合力。这不仅是供给侧改革的要求使然,也是延续经济法自身良法性质的内在选择,更是在法治社会下推动社会变革的必然要求。
[1] 贾康等. “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改革[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5, 6.
[2] 龚雯,许志峰,王珂. 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N]. 人民日报, 2016-01-04(2).
[3] 佚名.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10/c_1117099915.htm, 2016-11-23.
[4] 许健. 论可持续发展与经济法的变革[J]. 中国法学, 2003, 6.
[5] 李昌麒主编. 经济法学(第二版)[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6] 李昌麒主编.经济法理念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7] 徐孟洲. 耦合经济法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8] 胡光志. 宏观调控法研究及其展望[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5.
[9]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哈耶克文选[M]. 冯克利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10] 吴敬琏.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选择[A]. 吴敬琏等著. 供给侧改革: 经济转型重塑中国布局[C].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1] 刘世锦. 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A]. 吴敬琏等著. 供给侧改革: 经济转型重塑中国布局[C].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12] 种明钊主编. 国家干预法治化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9.
[13] 杨力. 认真对待法治思维[J]. 政法论丛, 2015, 2.
[14] 邱本. 经济法研究(上卷: 经济法原理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15] 刘云亮. 权力清单视野下规制政府有形之手的导向研究[J]. 政法论丛, 2015, 1.
[16] 曹胜亮. 社会转型视阈下经济法价值的实现理路研究[J]. 政法论丛, 2016, 3.
[17] 胡光志, 靳文辉. 金融危机背景下对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再思考[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3.
TheeconomiclawUnderthebackgroundofsupply-sidereform:ChallengesandResponses
LiuZhi-yunLiuSheng
(Law School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long with the process of our country’s economy development mode changing from extensive to intensive, simple division to the complex, the traditional Keynesian short-term intervention in demand side can no longer help our country rapidly get rid of the double weakness dilemma that our country’s economy is slack both in and out of the country, let alone to achieve the economic V-rebound in the short term.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needs to be pulled from the demand side "single leg support" to the supply side which moderately expand demand side like a man walking on two legs. Contemporary reform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e supply side pose a major challenge to the economic law which stem from rectification of the double failure of market and government and to seek a balanced outcome of the gam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A structural reform of Economic law subject system is needed to push our government to simplify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delegate power to lower levels,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authority, defin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subject of social intermediary, improve the system of property rights and social distribution ensur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arket participants. We need the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system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stable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specific laws such as fiscal law, financial law, industrial policy law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law. Also needed is the regulation system of economic law to foster a loose investment and management environment and to bolster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 of the market in the proces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via perfecting the legal system to protect product quality, food safety,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nd the market competitio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economic law; the subject of economic law;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market regulation
1002—6274(2017)04—003—11
DF529
A
本文系国家社会基金项目“新发展理念下中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问题研究”(17BFX009)的阶段性成果;厦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720151038)成果。
刘志云(1977-),男,江西瑞金人,法学博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金融法、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刘 盛(1990-),男,江西于都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法。
(责任编辑:唐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