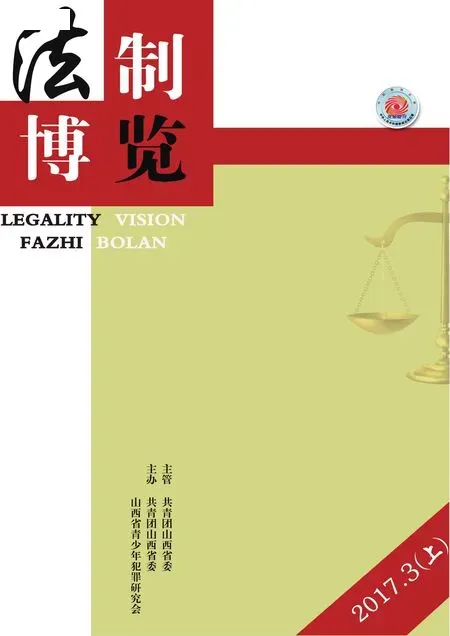论作品元素商品化的著作权法规制
陈伟凯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论作品元素商品化的著作权法规制
陈伟凯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于作品元素的商业化利用已经日趋普遍。然而我国法律中尚未规定商品化权或其他保护作品元素权益的权利,实践中出现的具体纠纷又迫切需要法律的规制。对商品化权的认定及立法是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作品元素的商品化权应当作为一种著作财产权进行规制和调整。《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中应当对商品化权加以明确,在立法上宜采取技术性规定。
商品化权;著作权;作品元素
Analysis on Copyright Regulation of Merchandising Right in the Elements of Works Abstract: Followed by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the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f works’ element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mon.However,in our positive law there is no merchandising right or other rights which can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works’ elements.But the disputes happening in real life badly need the regulations on it.The recognition and legislation of merchandising right is urgent affairs.The merchandising right in the elements of works should be defined and regulated as a kind of property rights in a work.It is time that merchandising right should be clarified in the third revision of
一、问题的提出:作品元素的商品化权
近日,著名作家金庸起诉江南《此间的少年》著作权侵权一案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该案将于2017年2月16日于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本案起因在于,被告江南在小说《此间的少年》中未经原告金庸的授权许可,大量使用了金庸小说中的人物角色,并且在人物关系及性格设置上有诸多相似之处。被告此后又将该小说出版,并获取商业利益。原告就此认为,被告此举侵犯了其著作权,并且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提出的其中一项诉讼请求即为判令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500万元。
对于《此间的少年》这类利用其它知名作品中的人物角色进行情节改编创作而成的新作品,网络上常称之为“同人小说”。“同人小说”的作者,未经原作者授权,对作品角色的商业性使用是否构成侵权,究竟侵犯何种权益?
一般认为,作品中的角色或形象属于作品元素,是作品中的组成部分而非作品本身。实践中,借用大众对原作品的熟知,使用作品元素为商业辅助行为或交易行为的情况其实并不罕见。在学理层面,这种因为商业目的,将作品元素投入商业用途使用的权利称之为商品化权。然而,我国法律中尚未规定商品化权或其他保护作品元素权益的权利,而实践中出现的具体纠纷又迫切需要法律的规制。因此,笔者认为对商品化权的认定及立法是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
二、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对“功夫熊猫”商标行政诉讼案分析
(一)案情回顾
“功夫熊猫”商标案起自于胡某在“方向盘罩”等商品上申请注册“KUNGFUPANDA”商标。原告梦工厂公司提出其由于同名动画片《KUNGFUPANDA》而享有的在先“商品化权”,因而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异议。
2013年11月11日,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关于第6806482号“KUNGFUPANDA”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商评字〔2013〕第105133号)。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商品化权”在我国并非法定权利或者法定权益类型,且梦工厂公司并未指出其请求保护的“商品化权”的权利内容和权利边界,亦不能意味着其对“KUNGFUPANDA”名称在商标领域享有绝对的、排他的权利空间。①
本案中,原告梦工厂公司最主要的诉讼主张即为其对“KUNGFUPANDA”享有在线的“商品化权”,因而因当适用《商标法》第三十一条中保护在先权利的规定,主张异议商标注册无效。这也是本案争议焦点之所在。终审法院认为:电影名称或电影人物形象及其名称可构成“商品化权”并给予“在先权利”保护,其考虑因素包含两点:1.电影名称或电影人物形象及其名称因具有一定知名度而不再单纯局限于电影作品本身,与特定商品或服务的商业主体或商业行为相结合;2.电影相关公众将其对于电影作品的认知与情感投射于电影名称或电影人物名称之上,并对与其结合的商品或服务产生移情作用,使权利人据此获得电影发行以外的商业价值与交易机会。
法院表明做出如此判定的目的在于,一是防范其他经营者的商标抢注行为,二是为了规范市场秩序,第三也有利于鼓励创作热情。②
(二)案例反思
本案中,首先原告并未主张对“KUNGFUPANDA”这一文字表达请求为独立作品之认定。对于实践中某些尚未申请商标的简短词汇短语,如标题性文字、刊物名称以及网络热词,其能否被认定为单独的作品,实际是存在争议的,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法院对于其独创性的评价。“KUNGFUPANDA”作为两个英文单词“KUNGFU”和“PANDA”构成的复合单词,要被视为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尚且存疑。但是《KUNGFUPANDA》这一电影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是不存在疑问的,基于对于作品中的元素是否能受到著作权效力荫蔽或者其他权利保护的讨论,就有了所谓的“商品化权”。
商品化权是指将具有商业价值的真实人物形象、虚拟角色及其他因素付诸商业性使用,吸引大众注意力,以达到商业促销目的而形成的权利。③笔者认为,应当对商品化权中保护的形象作限缩性解释,特指在作品中使用的形象。其原因在于,对于非作品中出现人物形象,民法的人格权中早已有肖像权、名誉权甚至隐私权加以系统性保护,商品化权再无单独因商业性目的而为特殊保护之必要。
我国对于商品化权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我国知识产权的发展滞后也有一定关联。在一些知识产权领域保护领先的国家,如美国和日本,早在20世纪早期和中期就有了相关的研究。④我国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开始逐渐承认了作品元素的商品化权,但是在判决中体现的更多是说理性内容,其实缺乏现行法律上的依据,对之后的案件不具备法律上的拘束力。同类案件审判结果也缺乏统一性,存在事实上“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要避免这种法律规范不明的情况,一方面必须厘清商品化权的权利属性,明确其性质和范围;另一方面,要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统一司法实践中的做法。
三、商品化权:一项重要的著作财产权
将商品化权归于现有权利或者与现有权利相近似的学说,主要有四种,即“版权说”,“商誉说”,“类版权说”,“综合说”。⑤
“版权说”认为,商品化权所保护的客体作品元素本身即为作品的组成部分⑥,而且其认知上的牵连性也使得其与作品不可分割,其商业价值的产生也依托于作品。因此,该学说主张,对作品元素的保护归根到底是基于对作品的保护,故应将商品化权作为著作权的权能,其本质上是著作权人的一项财产性权利。
“商誉说”是澳大利亚、英国在判例法中所持观点。该观点认为,作品元素之所以能够产生商业价值是因为受到了作品的宣传效应的影响,进而人们将对作品的喜好情感通过作品元素的桥梁作用迁移到商品或者服务之上,表现为一种商业信誉。因此,对于这种权益的保护应当适用于商誉的保护规则。
“类版权说”认为,商品化权中的作品元素限于的形象,商品化权是形象权的一部分,包括了真人形象和虚构的形象,且该形象应当具有知名度。商品化权是使用该形象为商业目的而适用并谋取利益的权利,是介于人身权、版权、商标权、商誉权之间的权力领域。⑦但是该说法界限较模糊,且难以涵盖到实务中出现的作品名称等作品元素的保护。
至于“综合说”,该说将角色商品化分为卡通人物的商品化、文学作品人物的商品化、电影作品人物的商品化以及真人形象的商品化。⑧卡通人物形象和文学作品人物形象的商品化在符合一定标准时受到版权的保护,真人形象由类似于我国肖像权的公开形象权进行保护,而电影作品人物形象视作品情况由版权或者公开形象权进行保护。排除真人形象的保护,“综合说”本质上与“版权说”相类似,其实际做法都是要求将商品化保护纳入著作权。
以上四种学说均是依托其他权利来保护商品化行为。也有学者认为商品化权是一种新型权利,主要有“新型人格权说”、“新型知识产权说”以及“无形财产权说”。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根据“功夫熊猫”案中,法院的说理将商品化权作为公众对作品“移情”于具体元素而产生的商业价值的保护,其所采取的也是将作品和作品元素相分离的态度,但也没有明确否认商品化权属于著作权的财产性权利。
笔者认为,商品化权对于作品元素的保护实质上与作品本身的保护具有一致性。首先体现在商品化权的权利人与著作权人具有一致性。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一经产生其作者往往就自动取得了著作权,而作品元素作为作品的有机部分伴随作品的产生而产生,与著作权产生的时间具有同一性。即便单论作品元素中的虚拟角色,其形象是放在特定作品中才有意义的,脱离作品使用后一般大众对其认知也是与原作品紧密相连的,其商业属性应当附属于原作,而作品名称等其他元素更是如此。故而,商品化权具有从属性,其从属于著作权。此外,将商品化权作为著作权权利束中的一支在规范上也存在可操作性,商品化权是一种财产性质的权能,同著作权中的其他财产性权能具有可比性。商品化权的实现途径本身就是通过自己基于商业用途使用作品元素或者许可他人将作品元素用于商业行为。因此,商品化权与其他财产性权能一样涵盖使用权和许可权。至于商品化权的转让,权利人完全可以基于意思表示将自己享有的使用权和许可权让渡他人,在不违反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法律上不存在限制商品化权处分的理由。基于商品化权的使用、许可、转让而产生的经济利益,自然可以得出其另一权能,即权利人获得报酬的权利。综上可以得出,商品化权同其他著作权下的财产性权利在功能上具有一致性。
因此,笔者同意“版权说”的意见,将商品化权视作著作权的权能之一。一方面,这是实际存在的市场需求所呼吁的,另一方面这也利于市场经济中财产要素形式多样化的要求。
除此以外,从主要国家的保护模式上来看,商品化权也更接近于著作权的财产性权利。
美国的商品化权发展起自于1953年的“海兰”案,自此商品化权从隐私权中独立出来,被定义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就美国的综合保护模式而言,其依照形象类象分别确定了文学作品角色的保护标准、卡通角色的保护标准以及影视作品角色的保护标准。
文学作品角色的保护是对完全由文字描述的作品中的角色形象的保护,并且其形象要求是虚构的。在具体审判实践中,美国法院在该项保护上形成了两个标准,即“充分描述标准”和“故事讲述标准”。⑩在符合相应标准时,法院可以判定著作权侵权。
对于卡通角色的保护则更显便捷,卡通人物角色由于其自身特征的显著性,往往不难对其作出具有独创性表达的评价,故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偏向将其视为独立作品由著作权加以保护。
对于影视作品角色的保护,美国法院也未形成统一的判定标准,究其原因,影视作品角色兼具情节性和外观显著性,涵盖文学作品角色及卡通角色之双重特征。故,在判例中往往分作两派,一派偏向文学作品标准,而另一派采纳卡通角色标准。
美国的“综合保护模式”对作品角色进行分类保护,但实质上并未脱离著作权这一范畴,不管是文学作品中的两个标准还是卡通形象的独立作品,对其侵权行为之认定最终还是体现为著作权侵权。因此,笔者认为,美国这种保护模式其实蕴含着将商品化权归入著作权权能的前提。
相对于这种基于著作权的综合保护模式,独立保护模式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人格权、著作权、商标权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分别保护与交叉调整的不足。部分国内学者指出⑪,我国在立法上可以考虑两步走:近期可借用已有的民事法律制度,对作品元素的利益提供保护;如若超出知识产权法的现有规定,相关案例仍然可以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列明的一般条款进行处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则应考虑以民事特别法的形式,制定专门法律制度。然而,这种立法调整模式首先要依附于现有其他权利,然后再进行进一步的权利“剥离”和“独立”,且不论其现实的可操作性,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通过知识产权法的现有规定解决纠纷本身就承认了知识产权法对于商品化权调整的可能性。而其中最主要的法律还是著作权法,现行著作权法之所以无法完全解决此类纠纷,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在立法上的规定不够明确。故此,大可以通过对著作权法进行修改,以明确规定商品化权之方式将其纳入调整范围,再无必要舍近求远,凭空设置新的权利和新的法律。
四、商品化权的立法:对我国商品化权一些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一)商品化权的保护客体
长期以来,不管是国外的司法判例还是国内的学者讨论,往往将商品化权的保护客体限定为作品中的角色或形象。然而,在具体案例中不难发现其他作品元素也可能成为受侵害的对象。如“功夫熊猫”案中法院判决所提出的“电影名称”亦可作为商品化权的保护客体。对于达到何种标准的作品元素才能为商品化权所保护,实际上,在“功夫熊猫”案中,二审法院已经结合具体事实对商品化权的认定标准作出解释,首先是作品元素凭借作品本身知名度与商事行为结合,并具有商业价值。其次是一般大众能够“移情”于该作品元素且发生使经营者获利的潜在诱因。笔者认为,作品元素若要得到商品化权之保护,必须要与其所依附的作品紧密联系,足以使特定范围内的群体通过该作品元素直接联想到作品。要满足此要求,首先作品需有一定知名度,至少在某个特定地域或群体范围内享有认可度。其次,作品元素本身具有独特性,换言之,具有身份标识。某些作品元素在作品畅销期间可能使一般大众产生作品元素与作品之间的牵连性认识,但其本身的标识性较弱,使用较为泛化,当作品热度丧失时,此种牵连性认识也即随之丧失,在此情况下,也不应认可对该作品元素的商品化权保护。
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作品元素受商品化权保护的认定标准应该涵盖几个方面:一是作品元素与作品之间的较为稳定牵连性,对于该牵连性的判断需要从特定市场范围内的一般大众的角度出发;二是作品元素自身的身份标识性,这要求受保护的作品元素不能是普遍存在的较为泛化的概念或形象,而应当带有一定的区分性;三是商业价值性,即该作品元素存在为商业行为所利用之可能性,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此种价值的判断,不需要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价值为必要条件,相应的侵权行为也不要求侵权人存在实际的盈利结果。
(二)商品化权应当于《著作权法》中加以规定
商品化权对作品元素的保护是对作品本身的间接保护,不管保护的直接对象为何物,在权利未经转让授权之时,最原始的权利人应当为著作权人。这一点,不管是否承认商品化权为著作权的权能,都不应当否认。商品化权,在权利的行使、处分以及救济模式上与其他著作权下的财产性权利具有相似性,将其作为著作权人的一项财产性权利,在立法上与其他权利并列,有助于完善权利体系,便于权利人主张和行使自己权利。
(三)商品化权在立法上应当做技术性规定
在“功夫熊猫”案中,商标评审委员会所作裁定中的一个理由就是,被请求保护的“商品化权”的权利内容和权利边界不明。诚然,不同类型作品中的元素千差万别,其中又包含有显著商业价值和无明显商业价值两类,而随着市场发展的需要,其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究竟如何确定商品化权的保护范围,笔者认为在立法层面可以做技术型规定,采取列举加概括的模式,首先概括保护对象的总体特征,即存在为商业目的而加以必要性保护的作品元素,再根据纠纷的频发性及权利保护的必要性列举出最主要的作品元素,最后辅之以兜底性条款。
[ 注 释 ]
①商标评审委员.商评字〔2013〕第105133号.<关于第6806482号“KUNGFUPANDA”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
②北京市高级人名法院.(2015)高行(知)终字第1969号.<梦工厂动画影片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其他二审行政判决书>,第7页.
③刘亚军,曹军婧.虚拟角色商品化权法律保护刍议[J].当代法学,2008(4).
④刘亚军,曹军婧.虚拟角色商品化权法律保护刍议[J].当代法学,2008(4).
⑤郭玉军,甘勇.论角色商品化权之法律性质[J].知识产权,2000(6).
⑥郭玉军,甘勇.论角色商品化权之法律性质[J].知识产权,2000(6).
⑦郑成思.版权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300.
⑧郭玉军,甘勇.论角色商品化权之法律性质[J].知识产权,2000(6).
⑨吴汉东.形象的商品化与商品化的形象权[J].法学,2004(10).
⑩林雅娜,宋静.关国保护虚拟的法律模式及其借鉴[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9).
⑪吴汉东.形象的商品化与商品化的形象权[J].法学,2004(10).
[1]刘亚军,曹军婧.虚拟角色商品化权法律保护刍议——美国实践的启示[J].当代法学,2008(4).
[2]吴汉东.形象的商品化与商品化的形象权[J].法学,2004(10).
[3]刘红.商品化权及其法律保护[J].知识产权,2003(5).
[4]林雅娜,宋静.关国保护虚拟的法律模式及其借鉴[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9).
[5]郭玉军,甘勇.论角色商品化权之法律性质[J].知识产权,2000(6).
[6]郑成思著.版权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
[7]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D
A
2095-4379-(2017)07-0013-04
陈伟凯,西南政法大学,在校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