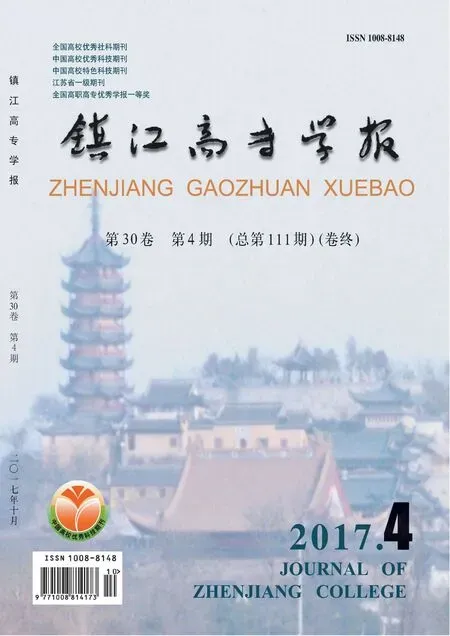论鱼复侯萧子响之死
袁 庆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论鱼复侯萧子响之死
袁 庆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齐武帝萧赜为了加强对宗王的控制,进一步强化了典签职能。典签秉承皇帝旨意,充当伺察藩镇诸王的耳目,很容易造成典签与宗王之间矛盾加剧。齐武帝第四子鱼复侯出镇荆州期间与典签矛盾激化,最终被逼反叛,不久兵败而亡。此外,萧子响之死与宗室内讧也有一定关系。
齐武帝;典签;萧子响;宗室内讧
高敏先生认为:“典签制度是南朝实行的一种重要而又特殊的政治制度。在南朝皇权政治不断强化,宗王政治、士族政治、寒人政治等多种政治因素相互交织彼此消长的历史背景下,典签制度也随着南朝政局发展变化而变化,并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250齐武帝即位后强化了典签的职能以加强皇权。但这样做,典签与宗室之间的矛盾就会加剧。鱼复侯萧子响出镇荆州以后,与典签之间矛盾加剧,最终反叛。细绎发现,萧子响反叛与典签虽有关系,但他的死也与宗室内讧有一定关系。
1 鱼复侯萧子响之反叛
鱼复侯萧子响是齐武帝第四子,“勇力绝人,开弓四斛力,数在园池中帖骑驰走树下,身无亏伤”[2]704。可见其武力显著。齐武帝曾将萧子响过继给萧嶷为养子。“豫章王无子,养子响。后嶷有子,表留为嫡。”[2]704齐永明六年(488年),萧子响还属本宗。齐武帝委以重任,“七年,迁使持节、都督荆、湘、雍、梁、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镇军将军、荆州刺史”[2]705。萧子响坐镇荆州,施政颇有违制。《南齐书·鱼复侯子响传》载:
至镇数在内斋杀牛置酒,与之聚乐。令内人私作锦袍绛襖,欲饷蛮交易器仗。长史刘寅等连名密启,上敕精检。寅等惧,欲秘之。子响闻台使至,不见敕,召寅及司马席恭穆、咨议参军江悆、殷昙粲、中兵参军周彦、典签吴攸之、王贤宗、魏景渊于琴台下诘问之。寅等无言。攸之曰:“既以降敕旨,政应方便答塞。”景渊曰:“故应先检校。”子响大怒,执寅等于后堂杀之。以启无江悆名,欲释之,而用命者已加戮[2]705。
有学者指出:“出镇宗王有庞大的府、州、国僚佐系统,府主有很大的辟举权力,加之观念上的君臣名分,很容易形成独立的势力集团。”[3]154然而,萧子响在荆州期间,却并未得到其僚佐的支持与拥戴。征诸史载,长史刘寅、司马席恭穆、咨议参军江悆、殷昙粲、中兵参军周彦、典签吴攸之、王贤宗、魏景渊等,虽均属于萧子响军府僚佐,却充当皇帝伺察藩王之耳目。而萧子响对于军府僚佐背叛自己的行为毫不知情,这充分暴露了他与军府僚佐貌合神离之关系。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典签吴攸之等人可与军府长史刘寅等人“连名密启”府主萧子响违制之事,但在台使奉敕检校的关键时刻,典签吴攸之、魏景渊等人敢于坚持敕命,不畏祸端,似较其他军府僚佐有更大的职责[1]255。清代赵翼在《廿二史剳记》卷一二“齐制典签之权太重”条指出:“齐制,诸王出镇,其年小者,则置行事及典签以做之,一州政事以及诸王之起居饮食,皆听命焉,而典签尤为切近。”[4]251由于出镇的幼王羽翼未满,故而典签对他们的控制相对容易。但对成年出镇的宗王而言,在这种皇权极度强化的情况下,宗王个人权力难以得到伸张。作为与皇权此消彼长的政治势力,宗王不甘寂寞。他们不甘心受制于典签,并且试图摆脱典签的束缚,然而,他们尝试摆脱典签的行为必然与皇权相抵触,那么宗王政治与皇权政治之间的摩擦将难以避免。萧子响于上游诛杀僚佐之事传至建康,“方镇皆启称子响为逆”[2]531。齐武帝闻之大怒,派遣军队直指江陵。上游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2 萧子响之死与萧齐宗室内讧
齐武帝派遣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中书舍人茹法亮率领军队逆流而上直驱荆州,同时,调遣雍州的杨公则、南平内史张欣泰等将领出兵江陵。齐武帝下令:“子响若束手自归,可全其性命。”[2]705萧子响出镇荆州时间短促,立足未稳,无力与朝廷军队相抗。他“白服登城,频遣信与相闻”[5]1108,亮明自己归降之态度,以示坦诚无间。然而,胡谐之、尹略等人对此视而不见。萧子响不得不“又送牛数十头,酒二百石,果馔三十车”[5]1108,慰问朝廷军队。而尹略却“弃之江流”[5]1108,“萧子响胆力之士王冲天不胜忿,乃率党度洲攻垒斩略,而谐之、法亮单艇奔逸”[5]1108。朝廷军队一战即溃。不久,齐武帝继续增兵。《南史·鱼复侯子响传》载:
上又遣丹阳尹萧顺之领兵继之,子响即日将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初,顺之将发。文惠太子素忌子响,密遣不许还,令便为之所。子响及见顺之,欲自申明,顺之不许,于射堂缢之[5]1109。
萧子响不想坐以待毙,欲顺流而下奔至国都建康。文惠太子萧长懋“素忌子响”,并借助萧顺之杀害了萧子响。萧子响至死前仍“欲自申明”,力求摆脱谋反罪名。然而,萧子响最终还是被杀害。
细绎发现,萧子响死于萧长懋之手绝非偶然,背后隐藏的是皇族内部残酷的权力争夺。萧长懋“素忌”萧子响的原因,可能与萧嶷有关。有学者指出,可能是萧长懋与萧嶷之间存在嫌隙的缘故[6]73。萧长懋与萧嶷的恩怨由来已久,《南齐书·江谧传》载:
太祖崩,谧称疾不入,众颇疑其怨不豫顾命也。世祖即位,谧又不迁官,以此怨望。时世祖不豫,谧诣豫章王嶷请间曰:“至尊非起疾,东宫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计?”世祖知之,出谧为征虏将军、镇北长史、南东海太守。未发,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谧前后罪曰……诏赐死[2]570-571。
江谧是萧嶷重要的僚佐,由于官场不得志,因此积极劝说萧嶷夺取皇位。如果萧嶷夺取皇位成功,萧长懋太子之位自然遭受威胁。江谧所言“东宫非才”,盖是萧长懋在朝中根基尚浅,即使即位,也很难控制朝局。而萧嶷则不同,他既具备继承皇位的资格,又具有稳定朝局的能力。齐武帝知道了江谧的阴谋,萧嶷夺取皇位最终没有成功。经过此事件,表面上萧嶷在各方面被予以优崇,实际上却逐渐被逐出中枢,淡出权力中心。原先与萧嶷密切相关的人,或是被诛戮,或是被远调地方,萧嶷的政治势力逐渐被分化[7]。与之相反,萧长懋的政治势力不断积聚,“既正位东储,善立名尚,礼接文士,畜养武人,皆亲近左右,布在省闼”[2]399。至此,萧嶷与萧长懋的政治轨迹不同。然而,萧长懋与萧嶷之间“夙嫌”一直存在。萧子响曾过继给萧嶷作为养子,萧嶷对他有养育之恩,故而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加之萧子响得以还本,备受齐武帝重用,有可能会威胁自己太子的地位,萧长懋对萧子响起了杀心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萧子响坐镇荆州施政颇有违制,这为萧长懋杀害萧子响提供了契机。齐武帝派遣讨伐萧子响的主要人物有胡谐之、萧顺之等。从表面上看,胡谐之、萧顺之等人受命于齐武帝,然而仔细分析起来,却并非如此。
胡谐之,“盆城之旧”成员之一[2]543,“世祖顿盆城,使谐之守寻阳城,及为江州,复以谐之为别驾,委以事任”[2]656。可见,胡谐之与齐武帝关系非同一般。后来,齐武帝以“谐之心腹,出为北中郎征虏司马、扶风太守,爵关内侯”[2]656,辅助萧长懋镇守雍州,胡谐之“在镇毗赞,甚有心力”[2]656。齐永明三年(485年),胡谐之为太子右率,遂成为萧长懋亲信。胡谐之受命讨伐萧子响之时任职卫尉[8],实际上为最高军事统帅。齐武帝曾下令“子响若束手自归,可全其性命”。胡谐之率军至江陵,却无招降萧子响之意,致使萧子响被逼而反。从某种角度来说,胡谐之敢于违背齐武帝旨意,正是有其背后萧长懋的支持。
萧顺之,萧齐旁支宗室成员,追随齐高帝萧道成东征西讨,颇有功勋。“齐武帝在东宫,皇考尝问讯,及退,齐武帝指皇考谓嶷曰:‘非此翁,吾徒无以致今日。’”[5]168由此可见萧顺之与齐武帝关系之紧密。后来,萧顺之任职太子詹事一职,应与萧长懋关系较为亲近,而且萧长懋是通过萧顺之将萧子响杀害的,这说明萧顺之已成为萧长懋的心腹。萧顺之也对齐武帝的命令——“子响若束手自归,可全其性命”视而不见。从某种角度来说,胡谐之与萧顺之敢于违背齐武帝旨意,正是由于萧长懋的支持。
概而言之,胡谐之与萧顺之都是萧长懋的心腹,致使萧子响之死的背后主导者正是萧长懋。萧子响落难时处境为艰,萧嶷曾想方设法营救萧子响。萧子响杀僚佐消息传至建康,而且“方镇皆启称子响为逆”,情况十分危急。“时巴东王子响杀上佐,都下匈匈,人多异志。而豫章王镇东府,多还私邸,动移旬日。”[5]1416-1417萧嶷频繁往返于东府与私邸,不排除有营救萧子响的可能。另外,方镇中也有对萧子响表示同情的。《南齐书·垣荣祖传》载:
巴东王萧子响事,方镇皆启称子响为逆,荣祖曰:“此非所宜言。政应云刘寅等孤负恩奖,逼迫巴东,使至于此。”时诸启皆不得通,事平后,上乃省视,以荣祖为知言[2]531。
垣荣祖甚至上书齐武帝,试图为萧子响说情,却因“诸启不得通”不了了之。需要指出的是,垣荣祖为青齐豪族将领,他与萧嶷关系十分紧密[9]。由于萧嶷在争储中失败,垣荣祖遂得不到齐武帝重用,只委以边防之任,远离政治权力核心。在萧子响事件中,从他表明的态度来看,显然倾向于萧子响。由于萧嶷的失势,垣荣祖对萧子响的帮助收效甚微。此外,在萧子响叛乱之中,胡谐之也是颇为关键的人物,可以说,他是萧长懋杀害萧子响的得力助手。
综上所论,萧长懋与萧嶷之间的矛盾无疑是存在的,但矛盾并没有上升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萧长懋集聚的政治势力远远超过了萧嶷。萧子响被害使萧长懋与萧嶷之间矛盾一度凸显,可以说萧子响的死乃是萧长懋阵营与萧嶷阵营较量之结果。
3 结束语
齐武帝萧赜为了加强对宗王的控制,进一步强化了典签职能。典签职权的强化与皇权加强密切相关。萧子响出镇荆州期间与典签矛盾激化,最终被逼反叛,不久兵败而亡。细绎发现,萧子响之死与文惠太子萧长懋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反映了南齐宗室内部矛盾的激化。萧子响被害之后,萧嶷与萧长懋相继病陨,高武嫡系宗室力量逐渐式微,旁支宗室崛起,并取而代之,随之而来的是皇权更迭,萧齐宗室内部权力争夺愈演愈烈。
[1] 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考论[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3] 鲁力.魏晋南朝宗王问题研究[M].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4] 赵翼.廿二史剳记校证(订补本)[M].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2.
[5]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唐春生.萧嶷与齐武帝之“夙嫌”析:兼及与文惠太子之关系[J].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73-78.
[7] 李猛.豫章王嶷与南齐建元政局考论[J].学术月刊,2016(8):131-140.
[8] 张金龙.南朝卫尉及其职掌考述[J].历史研究,2004(4):38-42.
[9] 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卢 蕊〕
AnalysisonthedeathofGovernorXiaoZixiang
YUAN Qi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2, China)
In order to further control the king of the emperor, Emperor Wu of Qi was able to strengthen the Dianqian function. As emperor’s ears and eyes, Dianqian caus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king of the emperor and the emperor. Xiao was the fourth son of Emperor QiWu, who was forced to rebel at the end of the town of jingzhou and eventually died becaure of the failure of the rebel. In addition, the death of Xiao and the civil war in the clan also had a certain relation, which could be glimpsed to the explosion of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royal family.
Emperor Qi Wu; Dianqian; Xiao Zixiang; imperial clan infighting
K239.1
C
1008-8148(2017)04-0109-03
2017-06-10
袁 庆(1990—),男,江苏灌云人,硕士生,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