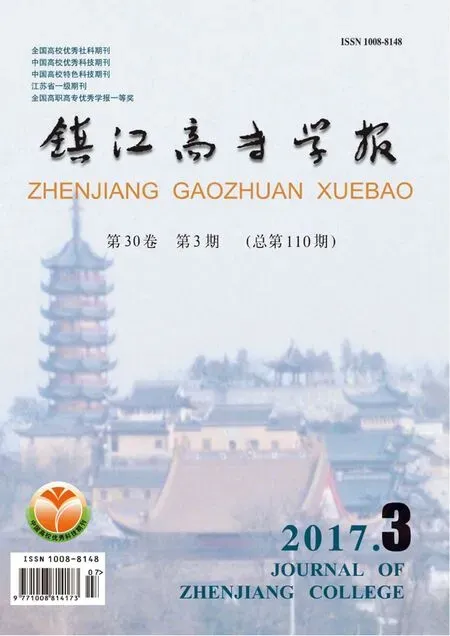流浪与回归:“群体社会”的个体生存困境
——论李锐《人间:重述白蛇传》的悲剧意蕴
胡 育,梁爱民
(1.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镇江分院 机电系 , 江苏 镇江 212016;2. 江苏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流浪与回归:“群体社会”的个体生存困境
——论李锐《人间:重述白蛇传》的悲剧意蕴
胡 育1,梁爱民2
(1.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镇江分院 机电系 , 江苏 镇江 212016;2. 江苏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人间:重述白蛇传》以多重叠合的叙述视角,在佛、妖和人的三界切换中,演绎主人公痛苦而悲壮的命运历程。对无意识“群体社会”的抗争和突围,不仅体现了个体生命价值的意义,也折射出现实世界中无法不让人对其保持一份警惕的“文明”之罪。小说借重述神话的方式再次承担了小说“勘探”世界的使命。
《人间:重述白蛇传》; 群体社会; 文化个体
《人间:重述白蛇传》(以下简称《人间》)是李锐继苏童的《碧奴》与叶兆言的《后羿》之后“重述神话”的又一力作。作为神话的讲述者,他让神话的主人公在人、佛、妖三界孤独流浪,他听见主人公愤懑而无奈的叹息,亲见袈裟沾染了鲜血。他的笔下,白素贞、粉孩儿、法海的身影站立在幽暗的最深处,那里是黑暗与光明的交汇点,也是历史、神话和现实的结合处。《人间》借重述神话的方式再次承担了小说“勘探”世界的使命。
1 白蛇:“跨界者”的焦虑和牺牲
“这白蛇不是那白蛇”[1]18《人间》在开始讲述白蛇故事前就如是做了交代。因为这白蛇不是田汉《白蛇传》里为了领略温山软水而来到人间的白蛇,也不是方成培《雷峰塔》中为了寻觅“有缘人”而转到尘世的白蛇,这白蛇来到人间只是为了“做一个人”。正是为了做一个人,注定了她要历经人间诸多的苦难和折磨,经受人世间数千年人伦法则的拷问。白蛇苦修两千九百九十九年,最终却不顾“两耳不闻洞外事”的教诲,挺身救人于危难之中致使修炼功亏一篑。
邂逅许宣,遭遇法海,藏身“碧桃村”,白蛇始终摆脱不了包括法海在内所有人的窥视。先是她最爱的许宣对她的怀疑和抛弃,许宣“反认他乡是故乡”,将金山寺当做避难所,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着白蛇。再就是法海秉持所谓的“道义”,如影随形、穷追不舍地“除妖”。然而,许宣的负心,只是让白蛇伤心失望而已,法海的穷追对于她而言,也不过是道术上的较量,说到底,这些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与人的“较量”,白蛇所要争取的,是获得一个名正言顺、光明正大的“人”的身份,“二千九百九十九年的苦修埋葬了她作为一条蛇的前生前世,她用二千九百九十九年的时间换得了一个平凡的肉身凡胎的今生。她不要呼风唤雨,不要奇迹,不要长生不老,她只要这几十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人生。她用二千九百九十九年投生再造迎来的今世,是光明磊落理直气壮的”[1]104。无论是法海还是被法海所利用的许宣,都没有对白蛇在人间的“妖”的身份构成真正的威胁,也没有动摇她做一个真正的人的信念。
真正的斗争是在白蛇的内心,“人”“妖”对立又离奇的结合让白蛇处于非常态的焦虑和不安中:面对许宣的背弃,她恶作剧地在人间撒欢,这正是她内心巨大压力和矛盾的发泄;梦中醒来,担心腹中胎儿是“人”还是“妖”,透露了她对身份无法认同的无以隐遁的焦虑;而“千年一日,一日千年”的感概,更让她饱尝了时空分离的失落感。做妖容易做人难,而做一个亦人亦妖的人间流浪者、一个分离了时空界限和身份限定的“跨界”者,让白蛇身心俱疲,这种人世间的“失重感”,穿越了厚重的历史,突破了神话与现实想象的界限,具备了某种“当下性”的特征。叙述者正是通过对前世、今生的跨越式的讲述,追问一切试图突破时空、历史和文化束缚的“跨界”者必将经受怎样的历练。
焦虑还只是过程,残酷的结局在一个叫“碧桃村”的小地方等待着白蛇。“碧桃村”,一个小小的村落,一个似乎是远离尘世喧嚣的山村,曾经给了白蛇一家“快乐的日子”。但是碧桃村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虽然只有十多户人家,却都是堕民(罪人)的后代,他们在“回春散”事件后保持着对白蛇身份怀疑的高度一致。他们委实是一群无知、盲从的群体,他们毫无节制地捕食山蛇,导致了一场惨绝人寰的“人蛇大战”,却把这一切灾变的起因推到一个随竹笛之音而起舞的小孩身上,他们在白蛇用自己的鲜血挽救他们的性命之后却忘恩负义地群起而攻之。在白蛇看来,这群无畏却显然是无知的群体才是她在人间最大的劫难,是她前世苦修未成而注定难以逃脱的宿命。那个被火把照亮了的杀气腾腾的夜晚,成了白蛇在人间最恐怖的梦靥,却也是让白蛇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辉煌时刻。
“碧桃村”不过是人间的一个缩影,胡爹不过是碧桃村群体世界中的“这一个”。胡爹复制了“回春散”的配方,牟取了丰厚的财富,并以他的狡诈觉察到“回春散”背后“蹊跷”的故事,产生了对白蛇身份固执的怀疑——人类对于“异己”“异类”的怀疑和反击的本能。当流言四起,当以高僧自居的法海“确认”了他们的怀疑,碧桃村的这一群体便成了“无意识”和“非理性”的人类。“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2]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倏忽之间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个面目狰狞的“人类”,当自觉的个性消失,感情和思想转向一个与此前不同的方向,人类社会就面临着变成组织化群体的人,这个时代也就是勒庞所说的“群体时代”。
《人间》以今生、前世为因果叙事,让白蛇徘徊于“人”“妖”两界,感受着因缘难解、善恶倒置的尴尬,它让我们发现,超越了前世今生因果的,是难以逾越的某种历史铁律。《人间》是对历史铁蹄下个体生命痛楚的关注,是对穿越了历史时空的人性的拷问。白蛇因为救村民而牺牲,而那些以人自居的“群体”却似乎成了青面獠牙的“异类”。白蛇生命的悲剧不仅成就了她自己的“人”的价值,也必将激奋所有在无意识的“群体”面前保有自己、保全个性的每个人,为了“人的价值”这一理想而勇敢前行。
2 粉孩儿:“边缘人”的宿命和流浪
粉孩儿,一个“蛇人”,与“亦人亦妖”的身份不同,粉孩儿比起他的母亲白蛇更多了一些“人”的因素。“真真正正,一个小娃娃,什么都有,小手、小脚、小指甲壳……”。“姐姐呀,你好了不起,你生下了一个人!”小青的一声赞叹本是所谓“异类”对于成“人”自豪的宣言,但正如《人间》结尾借叙述者所言,在这少年身上,“或许携带着人类所不能了解的灵异与古老的基因密码,他是造物的意外”。一天天长大的粉孩儿果然日渐露出了他不同于常人的“异类性”:
他盘在树上,双腿倒钩树干,让自己隐藏在浓密的树叶中。一只呆头呆脑的不设防的小麻雀,飞过来,发出心无城府的欢叫。正午的阳光,明亮到令人目眩——那是一个静谧安详的正午。突然他身子如箭镞般“嗖——”一声飞出,只一闪,再弹回,那只无辜的小麻雀就落在了他的齿间。它挣扎,用翅膀拼命拍他的脸,一股腥甜的鲜血,慢慢溢满他的口腔[1]9。
粉孩儿的这种嬉戏完全出自天性。与白蛇一样,粉孩儿也竭力隐藏自己的“蛇性”,但与白蛇在焦虑中寻求人类社会的认同不一样,粉孩儿拒绝与其他一般人有更多的交流,只是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一个人跑到他心驰神往的草地——他的乐园。
与香柳娘的约定,让粉孩儿成为 “言仕麟”又成为后来的“许仕麟”,让他逐渐找到了真正的自己,让他有了承受人生风险的信心和勇气。粉孩儿在状元及第之后不足一个月,得到母亲故世的消息后,毅然选择了归隐。这是一次在污浊、庸俗的群体社会中实现自我拯救的精神突围。京城这样的大都市,“到处是人,到处是人的眼睛,到处是朱楼广宇”,却没有一个他能真正藏身的所在。这次突围,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恰恰是个体对群体的胜利,是自觉的个性对无意识的乌合之众的绝妙讽刺。
然而,这只是粉孩儿寻求自我认同的第一次却也是最后一次胜利。“在某种意义上,个体并不存在于传统文化中,而个体性也不被赞赏。只有随着现代社会的出现或更具体地说,随着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分化,分离的个体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3]个体对群体的突围注定要付出倍于常人的勇气和代价。虽然,粉孩儿有足够的勇气来承受或改变这一切,虽然,他最终没有走出神话的宿命,由一个万人仰慕的天之骄子成为一个混迹江湖的浪人,这种宿命类似于俄狄浦斯无法逃避的神喻,但是,粉孩儿却没有混同于庸众,他的命运一半是上天安排,一半却是自己的选择,他的特立独行注定了他最后的归宿。也许“流浪”就是他的名字,他也情愿与自己的灵魂一起漂泊,伴随着“做一个真正的自我”的信念,即使有再大的苦痛,也都能因这种信念的支撑获得无穷的动力。
可以这样认为,粉孩儿与庸众的矛盾乃是觉醒的生命意识与蒙昧的群体意识之间的矛盾。自觉的生命意识既领悟到个体与普遍原则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又懂得如何直面这样的冲突。他不可能指望形而上的普遍律令的改变,而只能选择高扬自己生命的旗帜,并与这样的律令背道而驰。哲学家齐美尔(G·Simmel)说:“生命的本质就是产生引导、拯救、对抗、胜利和牺牲。它似乎是通过间接的路线,通过它自己的产物来维持和提高自己的。生命的产物独立地和生命相对抗,代表了生命的成就,表现了生命的独特风格。这种内在的对抗是生命作为精神的悲剧性的冲突。”而且,“生命越是成为自我意识”,精神性的悲剧冲突就越是显著[4]。粉孩儿的悲剧,不是其肉体的损伤甚或灭亡,而是其精神的折磨和苦痛。他的生命给予了他意识,给予了选择的自由,但是,“妖性”与“人性”的内在抵触,让这种自由成为一种煎熬,精神在此时成为一头困兽,要么,躲躲藏藏地做一个“人”,要么光明磊落地做一个“妖”,尽情展示他的生命活力。在蒙昧群体的审视和怀疑中,他的精神在寻求一个豁然的突破口,并最终实现了这一突破,他付出了被所谓文明和文化所抛弃的代价,堕入了社会的底层,然而,这里却蕴含着一个伟大而高贵的生命憧憬:“在朝向真理的运动中忍受暧昧并使之明白显现出来,在不确定中保持坚毅,证明他能够拥有一无止境的爱心和希望。”[5]粉孩儿失去的只是他作为文明人的“身份”和地位,获得却是关于生命意义的真理;他放下的只是对普遍律令里的抽象法则,扬起的却是饱满的生命风帆;他放弃的只是行尸走肉般的虚幻世俗,而他坚持的却是他自己的真实存在。正如乌纳穆诺所说:“所有深受苦难的人,虽然深受苦难,他们还是宁愿是他们自己,而不愿意成为没有经受苦难的其他人。因为不幸的人,当他们不幸时,他们仍然能够保持他们的正常状态。当他们努力坚持他们的存在的时候,他们宁可选择不幸,也不愿意选择不存在。”[6]粉孩儿的命运及其悲剧不仅仅是个神话,当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将地球联结成一个小小的村落,人类也都成了坐在电脑前的“邻居”。我们之间并没有“人”与“蛇”的区别,但是我们携着不同的文化血缘,在人类文化狂欢的盛宴即将开始的时刻,我们以不同的语言寻找自己的“同类”,在都市霓虹灯的映照下寻找“远方的家”,在茫茫人海中,在无意识的机器面前,我们恍若迷失的孩童。粉孩儿的命运直接指向了我们身后更加深邃的历史背景,还有无限延展的文化,倘若我们不能对这种更加广袤的历史和文化了然于心,不能彻悟自己的心灵选择,那么,粉孩儿的命运所展示的,只是人类的苦难,而非真正的悲剧。
3 法海:“云游者”的反思和挣扎
作为重述的《白蛇传》,法海不可或缺。但是《人间》中建构了一个具有颠覆意义的法海形象。这种颠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法海不再是一个以道义名义夺人幸福却执迷不悔的人物;其二,法海由一个得道高僧成为一个凡人,只不过拥有降妖除魔的利器而已;其三,法海不再是寺庙苦修的僧人,而是成为一个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流浪者”。在《人间》繁复的叙事结构中,法海形象,尤其是其内心世界的深邃和扰动,大部分是通过《法海手札》来讲述的。《法海手札》放弃了对白蛇、粉孩儿等故事全知全能的视角,转而以第一人称叙事手法,直面法海的内心,逼真呈现了法海心灵深处挣扎的痛苦,以及“除妖人”和普通人身份之间的犹疑与困惑。
《法海手札》增强了叙事真实性。这本《法海手札》是在叙事者生存的当下时空挖掘出的“文物”,叙事者是其见证者,尽管后来叙事者放弃了对《法海手札》的转述,但是,真实的历史时空无疑削弱了这本《法海手札》的“神性”色彩,为法海回归“人性”形象提供了叙事学依据。而文本更真实的一面主要还是来自于其内心“独白式”的叙事。
《法海手札》以自传的方式告诉人们,法海肩负着“除妖”的神圣使命来到这个世界,尽管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承受了太多的坎坷和艰难,但是,他从头至尾都没有放弃“除妖”的信念。事实上,法海只是个“平常人”:他有所恨也有所爱——只有凡夫俗子才会有爱恨情愁。他 “慧眼”未开,不能识别真正的“妖”,因此“郁郁不乐”。师傅与狐妖的惨烈搏斗让他体验到了作为一个“除妖人”必须具备的“坚定”甚或“残忍”,做一个铁面无私的“除妖人”,切不可“因小善而忘大义”。何为“大义”?那便是“除妖”。可是,法海只是肉眼凡胎,对于无处不在的人间罪恶他无能为力,他因此失落、寂寞。这是法海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第一次困惑。
法海第二次深刻的困惑来自于白蛇所说的一句话:“佛家最讲慈悲,众生皆有佛性,何谓人?何谓妖?”这个问题令他至死而不得其解。因为他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他相信了他的同类——许宣,而错失除妖的良机。但在他身染重病、奄奄一息之际,救他的,居然是他的仇敌——白蛇。一个是抽象的佛家道义,一个是真切的人间感情,法海虽踌躇满志于“除妖”伟业,却踟蹰不前于 “人”“妖”的两难命题。他深知,能否甑别“人性”和“妖性”乃是“慧眼”开启与否的标志,但对此,他没有信心。
困惑,正是作为精神流浪者法海的生存状态。正是这两次“困惑”让法海对“人性”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当胡爹前来禀报灾情并表达了对白蛇一家的怀疑时,法海聚气凝神,若有所得:
人心真是黑暗,举目可见忘恩负义之人,行忘恩负义之事。我奇怪为何这志同道合的来访者让我郁闷。他的话,句句都像是出自我口,倒让我对自己又一次生疑。这是个不光明的人,不光明的人口中为何句句都是我所持的真理[1]145?
法海看到一个卑微、龌龊的自己,他似乎已经悟到,他不过是个打着“除妖”旗号的忘恩负义的、“不光明”的小人。他终于悟到,他所苦苦追寻的所谓道义和真理、一切的大善和大慈悲,其实并不存在于这个充满了怀疑、杀戮的人间,而是在耳目所历的现实时光之外。
彻悟的法海形象就这样在一个自传性的独白叙述中凸显,接下来故事进入了“全能叙事”的视角,如同一个超越于时光之外的“慧眼”打量着人间所发生的一切,体察着觉悟后的法海如何用行动弥合灵魂的裂痕。他明示许宣带着儿子从后门逃生,并给了死后的白蛇一个干净的肉身,而自己却再也没有入寺修道,他成了一个还俗的和尚。还俗,是社会身份的改变,对于法海,他终于停止了流浪,重新找回了自己。“人归于人,水归于水”,不仅是玄学的参悟,更是生命的信仰,有了对人世间的深刻体察和彻悟,才有对自身存在的正确判断,也才能有与生活之“真实”邂逅的审美境界。如果说,俄狄浦斯的流浪是始于对命运的无知,而法海的流浪则是始于对命运和人性的反思,唯有这样的反思和彻悟才使得他最终回归了自身,回归了真实的存在。海德格尔说:“只有当世界这样的东西由于这个存在者的在此已经对它揭示开来了,这个存在者才可能接触现成存在世界之内的东西。”[7]这样的境界才是我们与“物”的“照面”,我们看见的将不再仅仅是自己,而是万物的真相,然而,这万物的真相之中就包含了我们自身,“无我”却可以随时、随处“有我”。
法海的“回到自身”,是他经过了人世的血腥、残暴之后的理性选择,这种选择充满了悲怆与无奈。这个以“万物之灵长”自居的人类社会,应该如何对待养育了自己的自然万物,又应该如何正确认识我们自己在自然中的真实存在?《法海手札》的叙述方式也许正是人类持续对自我进行反思和质问的形象注脚,而法海的精神悲剧历程似乎也提出了这样的警示:我们注定要以毫无退缩的勇气直面有限的存在,即使经历再多的苦难和折磨,也要让精神得以飞升,得到永恒。
4 结束语
昆德拉在谈及小说艺术的时候这样认为:“小说不是作者的忏悔,而是在世界变成的陷阱中对人类生活的勘探。”[8]“现代性”为人类精心编织了一个神话般的生存网络,借助几乎无所不能的科技,时空在这个网络中神奇交错,日趋发达的“群体社会”唱着“全球化”的赞歌,而无视文化个性的生存窘境。可以这样认为,《人间》乃是对正在变成“陷阱”的“人间”的一次大胆勘探。白蛇因“跨界”而焦虑,粉孩儿因“身份”而孤独,法海因“道义”的使命而痛苦,他们的悲剧结局皆是因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必然地与“群体社会”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所致。对无意识的“群体社会”抗争和突围,不仅体现了个体生命价值的意义,也折射出现实世界中无法不让人对其保持一份警惕的“文明”之罪。面对偌大一个“人间”陷阱,《人间》不仅借重述神话的方式再次承担了小说“勘探”世界的使命,更是以直面人世之复杂、人性之卑劣、人生之悲苦的精神,让我们对当下的世界、对人性的历史和历史的人性保有一份清醒的怀疑,对“回归自身”的生存命题有一份更清醒的认识。这也许正是《人间》的悲剧价值所在。
[1] 李锐.人间:重述白蛇传[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7.
[2]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18.
[3]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85.
[4] 刘小枫.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253.
[5] 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115.
[6] 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13.
[7]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65.
[8]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24.
〔责任编辑: 刘 蓓〕
Vagrancyandregression:Individualsurvivaldilemmaamongthegroupsociety—TragicimplicationinLiRui’sTheWorld:RestatementoftheWhiteSnake
HU Yu1, LIANG Aiming2
(1. Electromechanical Department, Zhenjiang Branch of Jiangsu Joint Vocational and Techrical College, Zhenjiang 212016, China; 2. Teachers’ Edurcation School, Jiangsu Uriversity,Zhenjiang 212013,China)
The world: Restatement of the White Snake interpreted characters’ bitter and tragic fates among Buddha, demon and man with multiple overlapping narrative perspectives. The struggle and breakthrough against the unconscious “group society” not only reflected the value of individual life, but also refracted the crime of “civilization”,which we should guard against in real world. This novel undertook the mission of “exploration” into the world by the way of restatement of myths once more.
The world: Restatement of the White Snake; group society; cultural individual
2017-04-22
胡 育(1978—),女,江苏镇江人,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梁爱民(1970—),男,江苏泰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文学评论研究。
I207.73
: A
:1008-8148(2017)03-0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