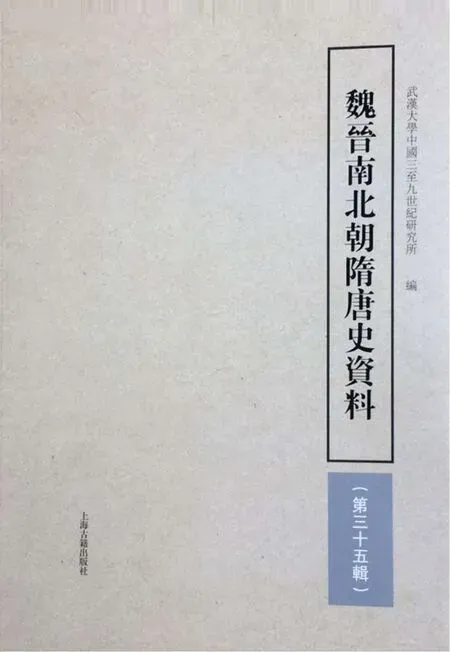試論都督制之淵源及早期發展
雷家驥
試論都督制之淵源及早期發展
雷家驥
一、 前 言
論軍需先論制。本文*本文於2016年10月先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之“嚴耕望先生百齡紀念學術研討會”宣讀,事後修改爲本文定稿。所論之都督制,於魏晉而言實爲新興的軍制,與秦漢以來之將軍制及監軍制關係密切。换言之,魏晉都督制之淵源,決不會憑空而産生,實與監軍監督將軍及其所屬軍隊有關,是以本文專從軍隊之統率、監督角度,進論都督制與此制的關係淵源,並溯及其早期的發展演變。*《漢書·百官公卿表》另述中央自郎中令、衞尉、中尉……以至地方之郡尉等官,與統兵征伐作戰之體系關係不大,故本文暫不討論。本文所引正史,俱據臺北: 鼎文書局新校標點本。
按: 中國正史向爲文人所撰,故對軍制論述不多,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載,其敍述秦漢之最高軍事機關以及將軍制即甚簡,僅云:
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長史,秩千石。
《續漢書·百官志》所載雖較詳,但仍感失之在略。兹省略太尉,而逕引將軍之官及其統率指揮系統,以概見其制度。該志載云:
將軍,不常置。本注曰: 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 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蔡質《漢儀》曰:“漢興,置大將軍、驃騎,位次丞相,車騎、衛將軍、左、右、前、後,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世祖中興……前、後、左、右雜號將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
其領軍皆有部曲: 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爲副貳。
其别營領屬爲别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
其餘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司馬彪《續漢書》諸志今已補入范曄《後漢書》而爲志,爲尊重原作者,今仍稱《續漢書》。按: 本段標點頗爲筆者所改。
是知秦漢將軍之官,位階甚高,平時“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戰時掌征討作戰,屬於軍令系統。然因將軍對所屬軍隊握有全盤統率指揮權,故君主爲策安全起見,對將軍平時所領之屯駐軍派有監督,而對其戰時所統之征討軍亦派有監督,此即監督系統,與將軍之軍令系統固不全同一系也。將軍統領直屬部隊,轄下之戰鬥單位分部、曲、屯,各級主官依次爲校尉(司馬)、軍候、屯長;有時視需要而另配以他部,配屬部隊的兵力雖不一定,但建制則與直屬部隊相同。至於其他將軍亦置以征討,統率系統之建制也同於大將軍。可見秦漢軍制原無所謂都督、督將之制,都督制與將軍制實爲不同歷史分期的一代大制。然雖如此,不過兩者之間卻不能謂全無關係,蓋都督制導源於將軍之監督制也。
本問題之緣起,與晉、宋、南齊官志敍述都督制起源及演變其間差异頗大之事有關。據《宋書·百官志》載都督制的淵源及其早期發展云:
持節都督,無定員。
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帝爲相,始遣大將軍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
魏文帝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則總統外内諸軍矣……
晉世則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晉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居之。宋氏人臣則無也。江夏王義恭假黄鉞。假黄鉞,則專戮節將,非人臣常器矣。
所載與唐初修成之《晉書·職官志》大抵相同,唯晉官志在載述此制之前,稱此制爲“常都督制”,並謂是“黄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此略异耳。是則常都督制即是州都督制,完成於晉世,當時已成方面大員之職,兩志所載出入不大;然而,“常都督制”之外是否尚有“非常都督制”?斯則兩志所未嘗言。至於其未成爲方面大員以前之演變如何,如何發展成魏晉之制,爲何最後發展成有都督、監、督,以及使持節、持節、假節三等級之别?此則亦爲兩志所未嘗言。
其後,南齊王室蕭子顯所撰之《南齊書》,於《百官志·州牧刺史》條所述又與二書頗不同,謂:
魏晉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督,起漢從帝(按: 即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揚、徐二州軍事,而何、徐《宋志》*所謂何、徐《宋志》,蓋即何承天、徐爰二人所撰之《宋書·官志》。《宋書·徐爰列傳》謂“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卷九四,第2308—2309頁。云起魏武遣諸州將督軍,王珪之《職儀》云起光武,並非也。
宋以下所纂類書多據此三書而抄之,且又頗常抄錯,是則都督制果起於何時,淵源爲何,早期演變如何,何書所載爲是等等問題,誠值得再研究。
上述諸問題近今中外學者對之多乏系統而完整的解釋,即使研究都督制最著名的嚴師歸田與小尾孟夫亦然,步其塵轍諸後學更無論矣。小尾孟夫論州都督(本文或稱爲軍區都督)之制自曹魏始,論征討都督(本文或稱爲野戰都督)之制自西晉始,上限如此,其不論及此制的淵源及早期演變,固可無待論焉。*參小尾孟夫: 《六朝都督制研究》,廣島: 溪水社,2001年。然而,研究都督制最爲權威之嚴先生,所論亦仍有問題待究或論述不足,如其大著僅略考都督制始於東漢馮緄,而對此前是否並無此制,以及此制淵源爲何,爲何發展爲都督制,到底先有軍區都督抑或先有征討都督,兩者關係爲何等等,皆因惜墨而無所論及。*嚴先生名著《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四十五B,民國79年三版)有多章論述都督制及其相關問題,請逕參考,不贅。
筆者曾發表《從督軍制、都督制的發展論西魏北周之統帥權》一文,内中曾參考廖伯源相關之論文,*如廖伯源: 《漢代監軍制度試釋》,《大陸雜誌》70-3。該文後來收入其所著《歷史與制度——漢代政治制度試釋》一書,臺北: 臺灣商務,1998年。拙著《從督軍制、都督制的發展論西魏北周之統帥權》一文,見《中國中古史研究》8,2008年。概略論及督軍制之起源云:
督軍之制起於監軍,監軍之制起於秦漢,但秦與西漢之監軍置有專官曰護軍;降至東漢,朝廷臨時派遣使者擁節監軍,而以派遣御史官爲多,故有“督軍御史”之稱。督軍使者所掌之職,也就是其軍事任務,有三種: 一、 監察諸軍征討,二、 監督屯營駐軍,三、 督州郡諸軍討捕叛亂。使者擁節監軍,所奉者即是天子之命,以故直屬於天子,遂逐漸侵奪諸將的統率權,終成魏晉以降的都督諸軍事,爲軍事方面之大員……由此觀之,督軍制之初起原屬軍事授權,是臨時軍事差遣之職,未爲官銜;朝廷之所以常遣侍御史或御史中丞出外臨督者,蓋因其屬本爲内廷官,具有法定之監察權,更有利於直承天子以監督諸軍執行任務耳。
其實監軍、督軍、護軍皆與軍隊監督制度有關,只是職權地位頗有差异,其中監軍、督軍的職權較爲接近,是較純粹的監軍制;而護軍早時本爲軍隊之督察長,其後與軍隊監督制度亦頗有關係。由於上述拙文的主旨僅欲從督軍制至都督制的發展論西魏北周之統帥權,並未以都督制本身的淵源及其早期發展爲主以作詳論,故所論難免疏略,偶有解釋亦尚未清晰完整,容易令人忽略而不易明了。職是之故,忝爲嚴先生門生,不免斗膽思爲先生作後續的補充解釋,並略申拙見以補前衍,用懷先生百年之紀念也。
都督制之淵源殆有遠源與近源兩種,遠源又可分爲廣義軍隊監督——護軍制,以及狹義軍隊監督——監(含督)軍制兩種制度;近源則爲東漢末始出現並發展之“都督”制。另外,魏晉都督制雖是一種制度,但卻有兩種亞型: 第一種是非常都督制,即是征討都督制;第二種纔是常都督制,即爲軍區都督制。下列分以甲、乙型表示其核心基本銜,或可一目了然。
甲型: 擁節+都督(或大都督)征討諸軍事+本官→出征
乙型: 擁節+都督(或監或督)某州郡諸軍事+本官+領州郡→駐防
兩型核心基本職銜皆爲“都督諸軍事”,而甲型通常不領州郡。本篇兹將此兩型都督制融入淵源及其早期發展中依次論述。至於吴、蜀方面,因此制發展較慢,非居主流變化地位,復多模仿曹魏之制,故請容日後另行發表。
二、 都督制之廣義淵源: 護軍制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
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哀帝元壽元年更名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
此表但言護軍都尉是秦官,未載職掌。據《通典·職官·勛官·護軍都尉》條,先述陳平於秦漢之間爲護軍中尉,至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復稱爲護軍都尉,接着同於《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述之内容,並尋而再述此制由東漢至魏晉之變化云:
漢東京省。班固爲大將軍中護軍,隸將軍幕府,非漢朝列職。魏武帝爲丞相,以韓浩爲護軍,史奂爲領軍,亦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爲中護軍,領軍爲中領軍。魏初,因置護軍將軍,主武官選,隸領軍;晉世則不隸矣。*參《通典》卷三四,第195—196頁。按: 護軍都尉本爲官,護軍等則蓋爲將軍出征時之戰時編制職,《通典·職官典》將之列爲勛官蓋誤,原因應是護軍在唐朝列屬勛官系統,以故杜佑沿之。至於曹操所置魏國之護軍、領軍,乃至魏朝建立後所改之中護軍、中領軍等,皆爲禁衛軍主帥之官,晉官志有載述,而杜佑則未予説明。
《通典》於此條小注云:“歷代史籍皆云護軍將軍主武官選。……今按: 漢高帝初以陳平爲護軍中尉,已令主武官選矣,故平有受金之讒。又《魏略》云: 護軍之官總統諸將,主武官選,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賄。……此則護軍主選明矣。”按: 小注所引之“歷代史籍”不詳,而明示書名者則有魚豢《魏略》、王隱《晉書》、《晉起居注》、《宋志》。至於《太平御覽·職官部·雜號將軍下·中護軍》條蓋本於《通典》,而所示歷代史籍除了《晉起居注》外,尚有郭頒《世語》與王羲之的《臨護軍教》,殆皆魏晉以降之文獻,或許護軍主武官選蓋是魏晉以降重要職權之一,故特别强調之。筆者竊疑,護軍都尉由秦官變爲東漢之幕府軍職,再變爲魏國的國官,然後隨着曹丕篡漢復變成魏晉以降之常制禁衛軍官,其間職權或應有所轉變,而《通典》等書對此卻無詳述。
筆者按: 秦漢間今見最早有關護軍的記載蓋爲陳平之事。《史記·陳丞相世家》載平由項羽改投劉邦時云:
是日乃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説,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高帝)與功臣剖符定封。……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祕,世莫能聞也。
此記載《漢書·陳平傳》與之相同,文句較异者乃是將陳平典護軍“反使監護軍長者”改爲“使監護長者”。無論如何,現今的問題乃在漢王拜素昧平生的陳平爲都尉,使之“參乘”而又“典護軍”,爲何使諸資深將領爲之鼓譟?深入究其原因,應是“參乘”與人主太近密,而陳平於軍中向無資歷反而禮遇超越諸將;禮遇既已超越矣而又使之典護軍,其權責在“監護軍長者”——監護諸軍資深將領,以故遂引起諸將之不滿而鼓譟也。是知護軍之職掌爲監護諸將。
“監護”一詞,似乎與杜佑所謂“主武官選”相關不大。按: 漢代許慎《説文解字》云:“護,救視也。”即其爲字有挽救視察之義。是則“護軍”之監護諸將,其作用就是監視督察諸將以保護軍中的安全,其職掌類似近今之軍隊督察,而護軍都尉無异即是督察長,在統帥之下對諸將擁有廣義的監督權。由於劉邦經常親征而爲最高統帥,爲了表示對陳平的信任,以塞諸將之噪音,是以乾脆提升陳平爲位當九卿之護軍中尉。護軍都尉與中尉之所以能影響諸將的部署甚或獎懲升黜,原因在此,於是諸將不得不巴結之,遂有“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的事情發生。
及至元狩四年,漢武帝命衛青、霍去病分軍出擊匈奴,大捷,封狼居胥,禪姑衍。尋乃創置大司馬位,以青爲大司馬、大將軍,去病爲大司馬、驃騎將軍,並且將護軍都尉一官移隸於大司馬。降至成帝綏和元年(前8)置三公官,大司馬去所帶將軍官,而護軍都尉之職權明確定位於“居大司馬府比司直,哀帝元壽元年(前2)更名司寇”,最後在平帝朝定名爲護軍。衆所周知,司寇向掌刑罰,至於司直則隸丞相府,“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司直參見《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條(第725頁)。司寇於元壽二年五月正三公官分職時置,故同書《哀帝紀》該年月條謂:“正三公官分職……正司直、司隸,造司寇職,事未定。”注引師古曰:“司直、司隸,漢舊有之,但改正其職掌。而司寇舊無,今特創置,故云造也。”(卷一一,第344頁)不知《百官公卿表》爲何謂護軍都尉早就在“元壽元年更名司寇”;要之,護軍都尉雖更名司寇,仍隸屬於大司馬府。顯示護軍都尉以軍中武官之督察監護權爲本職,及至移隸最高軍事機關後,其職乃兼及軍事檢察權,蓋由協助統帥督察武官之原來職權,擴大爲察知軍中犯罪即可主動佐府主舉不法也。由是,司直佐丞相舉不法,護軍佐大司馬舉不法,一文一武,雖非官僚體系中狹義的監察官,但卻成爲分掌監視督察文武百官之要任。由於是外朝官,所以護軍通常不擁節,護外國及蠻夷則例外。
由於護軍本職有監視督察軍旅之權責,故雖盟軍,漢廷亦得派遣護軍充使以監護之,如《漢書·常惠傳》載宣帝時,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烏孫求救,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由五將軍統領分道出征,而常惠别護烏孫國軍,傳云:
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烏孫國主)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驘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爲長羅侯。
常惠既然帶印、綬、節“持節護烏孫兵”,故是奉使監護盟國軍隊,不屬五道漢軍軍中編制之職,也非總監。此差遣任命的方式,是最接近“持節監”或“持節督”某某軍的任命方式。由於監(含督)軍約與主帥平等,雖主帥也在被監之列,與護軍之位下於主帥不同,故“監軍”位號重於“護軍”;*《史記·衞將軍驃騎列傳》載“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户封敖爲合騎侯。”(見卷一一一,第2926頁;又見同書《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合騎》條卷二,第1033頁),可見同是以征匈奴而立功封侯,但護軍都尉公孫敖則是在主帥之下屢從征,與常惠之“持節護烏孫兵”不同。也或許正因常惠所監護的對象爲外國元首及其國軍,因此不便以“持節監”爲名,使之與外國盟軍統帥平等也。要之監、護性質相近,而位號則前者重於後者,此可爲證。當五道皆無功而獨常惠所護之盟軍有功時,常惠遂因“奉使克獲”之功而封侯。*《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常惠條:“以校尉光禄大夫持節將烏孫兵擊匈奴,獲名王,首虜三萬九千級,侯,二千八百五十户。”(卷一七,第669頁)至於五將,同書《五行志中之上》注引師古曰:“本始三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爲武牙將軍,及渡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是爲二十萬衆也。”(卷二七,第1393頁)由於頗常有此類事例,故後來漢魏以降,因監護西域諸國而置西域都護,因監護匈奴而置護匈奴中郎將,因監護氐、羌、蠻等而置護氐、羌、蠻校尉,甚至直以護軍爲名用以護雜胡——非單一之少數民族,其淵源皆本於此;*護軍本以監護本國軍隊爲主,漢魏以來漸漸兼以監護西域、匈奴以至其他少數民族,是其職權推廣擴張,不過此趨勢之發展卻是由西域都護、護匈奴中郎將、護蠻夷校尉以至蠻夷護軍,位秩陸續降低,或許與所護國内外的民族地位高下或人數多少有關。要之這些官職之所以以護軍爲名,即取其具有監護之作用,甚至可能是對之軍管。嚴先生曾從地方行政制度角度專章論述諸部護軍,參前揭書第十三章;馬長壽《前秦〈鄧太尉祠碑〉和〈廣武將軍□産碑〉所見的關中部族》(收入其《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北京: 中華書局,1985年)則是以個案分析部族護軍管治雜胡的情況;拙著《從漢匈關係的演變略論劉淵屠各集團復國的問題——兼論其一國兩制的構想》(《東吴文史學報》第八期,1990年,第47—91頁)及《氐羌種姓文化及其與秦漢魏晉的關係》(《國立中正大學學報》第六卷第一期,1995年,第159—209頁),則對南匈奴與氐羌在漢魏時被中國監護並軍管頗有論述。而且因是奉使監護外國或少數民族君長,因此也以授節爲常,*《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六年是歲條引《漢官儀》云:“使匈奴中郎將,擁節,秩比二千石。”(卷一下,第51頁)按: 使匈奴中郎將後改稱護匈奴中郎將,因是奉使往護匈奴,故擁節,此是西漢以來之制度。匈奴也學有此漢制,故其單于臣服西域諸國時,所遣監護之使亦持節。如《後漢書·班超列傳·子勇附傳》載班勇於東漢初經略西域諸國,在擊車師後部時,“捕得(其王)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可以爲證,見卷四七,第1589—1590頁。只是史家偶爾省文而已。
護軍職典監護諸將,維護軍紀軍風,責任重要,即使東漢以降省罷護軍之官,然而卻未省卻其職,軍隊出征時仍然常於將軍幕府之内編置護軍之職,乃至在護軍專名之外,另分有中、左、右等護軍職名,*《續漢書·百官一·將軍》注引《東觀書》曰:“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可爲例,見《後漢書》卷二三,第3564頁。而皆事竟乃罷。例如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故班固有大將軍中護軍之稱。*參《後漢書》卷二三《竇融列傳·憲附傳》及卷四下《班彪列傳·固附傳》。護軍對軍隊如此重要,以故漢末魏晉戰亂頻繁之時,漸漸恢復護軍爲武官,且必要時直接領兵執行軍事行動,*例如史載曹操西征馬超之亂,因有後顧之憂,乃“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爲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爲左護軍,留統諸軍”。(見《三國志·徐宣傳》,卷二二,第645頁)又如,李嚴爲劉璋成都令,“建安十八年,署嚴爲護軍,拒先主於緜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 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郪,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嶲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即魏文帝黄初三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宫, 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内外軍事,留鎮永安。”(見《三國志》本傳,卷四,第998—999頁)可見漢魏間戰亂之時,諸集團皆以護軍統兵執行軍事行動,或作戰或屯守矣。稍後又由掌領禁衛軍的中護軍或護軍將軍(按: 中護軍之資深者爲護軍將軍)主武官選。蓋由於護軍行使廣義的監軍權,職權應會涉及武官風紀的考核,也就是涉及軍事人事行政,以故能影響諸將的獎懲升黜,陳“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之另一原因亦應在此。因此,或許在漢武帝將護軍都尉移屬大司馬府之後,護軍亦逐漸在制度上兼涉軍事人事行政,以故降至魏晉遂正式“主武官選”歟。
護軍除了上述職權外,蓋亦有參預軍機、獻策計謀之權便。護軍中尉陳平屢出奇計而使漢王戰勝剋敵,班固爲大將軍中護軍參議遠征軍軍機,已見前述。第二個見於史册的護軍中尉是隨何。隨何以謁者向漢王劉邦獻策,並主動請纓,奉使前往説降黥布,使黥布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項羽於垓下。天下已定,漢高帝論功行賞,“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參《史記》卷九一《黥布列傳》,第2603頁。除此之外,兩漢至魏晉以護軍之名參與征討、領兵作戰或監護軍隊而立功之例尚多,因與本文此處論廣義監軍權的關係不大,以故不贅。或許有人要問,陳平由護軍都尉遷護軍中尉有何特殊的意義?鄙意恐怕主要是官位的提高。*據《漢書·百官公卿表》,都尉秩一般是比二千石,護軍都尉既比司直,司直之秩即爲比二千石,可以概見。至於中尉則位九卿,屬中二千石;而帶有某些名目之中尉,如主爵中尉,則位爲二千石,故護軍中尉恐秩二千石至中二千石之間。《漢書》卷六九《趙充國傳》謂武都氐人反,車騎將軍長史趙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按: 車騎將軍長史秩千石,中郎將秩比二千石,水衡都尉秩二千石,可以參考。又按: 《續漢書·輿服下·青紺綸》注引《東觀書》謂“建武元年……校尉、中郎將……中護軍、司直秩皆二千石”。(見《後漢書》卷三,第3675—3676頁)或許是比二千石之誤,見《後漢書》卷二三,第3675頁。至於陳平拜護軍中尉而“盡護諸將”,蓋或有總監護的性質,恐怕是漢王針對絳、灌諸將之不滿而故意對陳平加重授權。其後隨何之爲護軍中尉,則未見有此殊遇矣。
至於大軍征行作戰,漢時也偶會編置具有總監而又頗帶統帥性質之護軍將軍,如《漢書》卷五二《韓安國傳》載漢武帝元光二年漢、匈破交大戰之首役——馬邑事變——時云:
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衞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
其因恐與各道統兵會戰諸將,盡多秩爲比二千石以至中二千石,乃至位爲九卿之大官有關,以故需命上卿級的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提高其至將軍名義,使“諸將皆屬”而盡護諸軍,故同書《匈奴傳》謂是“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云。又如東漢末之夏侯淵亦是其例。《三國志·諸夏侯曹傳》載云:
(建安)十四年,以淵爲行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渭南。又督朱靈平隃糜、汧氐。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
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圍遂、(馬)超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
夏侯淵分以行征西護軍、行護軍將軍先後督軍作戰,不啻握有監護權以督軍作戰,其性質實已是該支軍隊的統帥,只因非由漢朝正拜而僅由霸府任命,以故未持節而以“行”的名義任之耳。
作爲軍中督察主管,在涉及某些監督檢察相關的權力時,護軍殆無直接行使軍事司法之權,從《漢書·胡建傳》可見其例:
胡建……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巿,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漢書·胡建傳》本段文字的解讀頗爲艱澀,請自參卷六七、第2910—2911頁之顔師古注。按: 正文標點原爲“護軍諸校”,今改爲“護軍、諸校”,蓋護軍雖有直屬部屬,但此處之“護軍諸校”,應是指點選士馬之日,群坐堂上的護軍以及校尉也,故改。又按: 《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廷尉職掌刑辟,其屬有正,秩千石。據前注所揭《續漢書·輿服下》注引《東觀書》,謂“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則軍正丞可參考。至於校尉、司直、中護軍之秩皆是比二千石,而監御史原爲掌監郡之秦官,秩不載,至武帝元封五年置刺史後,官名職權遂爲秩六百石的刺史所取代。要之,此爲軍正丞以低秩官逕行法以斬監軍御史,而比二千石之護軍不敢制止之例。
由此傳可知,軍法與一般法律各自爲體系,軍法由軍正等軍事司法系統獨立執行,不屬於作爲主帥的將軍,所以謂“正亡屬將軍”也。除了將軍有罪必須奏聞之外,至於對其他軍中校尉等比二千石之屬,皆可得逕行執法。此次是監軍御史在軍穿垣做生意,以故軍正丞胡建於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之時,率兵執斬監軍御史,而令護軍與諸校皆愕驚而不知所以。可見軍事督察與軍事司法之職權在軍中蓋爲分開的二系統,護軍系與主帥之軍令系統關係較近密,而軍正系則相對較爲獨立,是以護軍不能直接行使軍事司法權,用以制止秩位較低的軍正丞逕行執法斬殺監軍御史也。
軍隊歷來具有封閉性之特質,所以“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各級軍人只聽其上一級長官的軍令。爲了使軍令貫徹、軍紀落實,是以設置作爲軍事督察之護軍,使握有廣義的監軍權,協助統帥護衛軍中安全。是則其與握有狹義監軍權之監軍,究竟有何重要的差别?按: 監軍是專掌監察軍隊之職,與護軍所握之權除了行使時有範圍廣、狹的不同外,二者最明顯的差异,厥是監軍乃奉使赴軍之差遣職,不屬於統帥,反而統帥也在其監察之列,而護軍則爲軍中編制的督察職,隸屬於主帥;另外,監軍與較其後起的督軍,可得授予擁節之特權,而秦漢之護軍則無——監護外國或蠻夷則例外。其詳請見下節。
三、 都督制之狹義淵源: 監軍與督軍
雖然將由君命,但是軍中既然“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一切均聽令於主帥,是則人君豈能放心?由是遂有監軍之制産生。軍隊監督者由君主所遣,以奉使之性質代表君主赴軍,故爲差遣使職,兩漢或多稱監軍爲監軍使或監軍使者,後起之督軍則較多稱爲督軍使者,至於直稱監某軍、督某軍,或加稱本官名,如監軍御史、督軍中郎將等,東漢亦頗常見。不過,監軍之制起源甚早,也不一定以御史充使。兹以司馬穰苴之監軍爲例,此也是載述監軍制諸書所常見之首例。《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載云:
司馬穰苴者,……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己之軍而己爲監,不甚急……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
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馳三軍法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歸。……景公……尊爲大司馬。
按: 莊賈是以君之寵臣、國之所尊而監穰苴軍,當時監軍持節之制似未成慣例,以故因犯軍法,在穰苴詢問過軍正後被斬。此與上述之監軍使犯軍法,而被軍正丞胡建所斬之事例略同,顯示先秦時監軍的權勢尚未陵越將軍。此外,穰苴不殺亦犯軍法而當斬的齊景公來使,僅斬其僕等作替代,顯示軍中似有“君之使不可殺”之例。然則監軍與使者皆爲奉使,爲何一者可殺一者不可?筆者以爲,恐怕此與奉使者當時有否持節,應有相當大的關係。持節者明顯代表人君,明顯爲“君之使”,以故若非人君下令則不可殺,而監軍則是差遣至軍中之職。上述二監軍之例皆未提及持節與否,又犯軍法,以故可得而斬歟?若是,則漢魏監軍、督軍有時書持節有時不書,則殆非全是史官之漏記或省文,而是自先秦以來即有監軍不持節的事例也。
秦時另有一例,可以窺見人君始能下令殺監軍,而監軍權位約與主帥平等。《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條載坑儒之事發生,“始皇長子扶蘇諫……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即是要扶蘇奉使出監蒙恬軍。兩年之後,同紀復載云:
上病益甚,乃爲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李)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賜死。
史公於卷八七《李斯列傳》對此事有詳載,其中述及:
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趙高等)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
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内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
及至二世立後,遣使者至陽周,責其罪,蒙恬乃吞藥自殺。*詳《史記·蒙恬列傳》,卷八八,第2567—2570頁。按: 扶蘇以君之長子監軍,與莊賈以君之寵臣監軍,身份不同,但似皆未擁節;然而,始皇死前詔令扶蘇會葬咸陽,“以兵屬蒙恬”,應即表示監軍不論持節與否,實際職掌皆是與主帥共同掌控所屬軍隊,也就無异分享統帥權,只是一者掌監督,一者掌統率而已,兩者即使本官高低不同,然而權位則約相當也,除非一方犯法。
監軍之例先漢已有,上述司馬穰苴率軍出征而置監軍,蒙恬領兵屯駐亦置監軍,而爲監者皆非御史。其後西漢沿用秦制,雖《史》、《漢》所載事例不多,但亦有之,如武帝征和二年江充以水衡都尉奉使治蠱禍,連及皇后、太子之事即可爲例。由於太子懼,不能自明,故收充斬之,《漢書·劉屈氂傳》載此事云:
戾太子爲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左丞相)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宫,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宫,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撟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丞相附兵浸多,太子軍敗,南犇覆盎城門,得出。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漢書》此傳原標點爲“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不甚可解。按: 任安與司馬遷是朋友,同時被腰斬的司直田仁亦與司馬遷善,故遷爲田仁之父田叔作傳,論及仁而未論及安,更未爲安作傳。今據褚先生所補《史記·田叔列傳》云:“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詳邪,不傅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按《索隱》:“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書上聞,武帝曰:‘……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見卷一四,第2779—2783頁)因此筆者改原標點爲“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
據褚少孫所補《史記·田叔列傳》,謂任安、田仁俱爲衛青舍人,爲武帝所賞識,“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按: 西漢首都長安有南、北二軍,北軍掌保衛京城,南軍掌保衛宫城,任安時爲“監北軍使者”,然褚少孫之所補,先謂任安“護北軍”,中轉爲益州刺史,後稱“北軍使者護軍”。按: 時無“北軍使者護軍”之職,筆者以爲應謂任安充“北軍使者”,而以此職監護北軍,未必遽謂其爲“北軍使者護軍”或“北軍護軍”也。班彪父子以補續《史記》的好事者“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因而“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另起爐灶撰《史記後傳》及《漢書》,*見《後漢書·班彪列傳》,卷四上,第1325頁。所言當較褚少孫之續書可信,因此以任安時爲“監北軍使者”爲是,亦即是北軍之監軍使者也。*《資治通鑑》(臺北: 宏業書局,1962年再版)亦稱任安爲“護北軍使者”(見漢武帝征和二年七月條,卷二二,第731頁),蓋據褚少孫所補之《史記·田叔列傳》歟?按: 奉使護外國之軍殆可稱爲使者,護本國之軍稱使者則少見。褚少孫既先謂任安“護北軍”,中爲益州刺史,後稱“北軍使者護軍”,則“護北軍”與“北軍使者護軍”(或“北軍使者”)是不同的先後二職,中間隔以益州刺史之官。司馬光似將“護北軍”與“北軍使者護軍”混爲一事矣。又,“北軍使者護軍”似應標點爲“北軍使者,護軍”,即以北軍使者監護本軍。蓋刺史爲正式之監察官,監北軍使者則爲正式之監察職,與護軍仍頗有不同,故任安由護軍遷監郡刺史,復遷爲北軍監軍使,以北軍使者監護此軍,固其宜也。不過,仍值注意的是,任安奉詔爲“監北軍使者”,但似未持節,與穰苴及蒙恬之監軍頗同,蓋爲秦漢間之慣例或是史家之省文歟?
《漢書》載監軍事例較少而《後漢書》較多,殆因東漢初及末皆戰事頻繁之故。據所見事例,前引《宋書·百官志》謂“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討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之説或有商榷餘地。蓋“前漢遣使,始有持節”,事例多見,不必贅。然而由於後漢初對内對外之戰争,常爲規模較大的征討野戰,與監州郡兵以事較小規模的地方平亂頗不同,爲因應事勢需要,故光武頗以差遣武官赴軍監戰爲常,差遣御史則罕見。
例如建武初,軍旅草創後,光武將自征隗囂,尋還宫,中郎將來歙等仍留關中。九年(33)隗囂死,“詔使(來歙)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並“拜(馬)援爲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參《後漢書·來歙列傳》(卷一五,第587頁)及《馬援列傳》(卷二四,第835—836頁)。按: 馬援原爲隗囂之綏德將軍,是武官,此時投奔光武帝,拜秩比千石的太中大夫。是則來歙之監護諸將,實則是監察諸將的另一種説法,與護軍監護諸將之説法頗有同有不同。姑無論來歙如何監護諸將,要之馬援既然“副來歙監諸將”,則來歙必就是正監軍。稍後,《後漢書·光武帝紀》載建武九年“八月,遣中郎將來歙監征西大將軍馮异等五將軍討隗純(隗囂子)於天水”,來歙於此役自稱“使者”,正顯示其的確是監軍使者,馬援爲監軍副使。同書《來歙列傳》載歙於此役被刺前後云:
詔歙率征西大將軍馮异、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弇、趙匡。……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辨,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强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投筆抽刃而絶。
按: 本傳又載來歙早在建武五年已以太中大夫持節奉璽書於隗囂,而此時卻是要監戰,故以比二千石的中郎將充監軍使者,“悉監護諸將”,雖不言持節與否,但因先前已持節,諸將又多爲二千石卿級將軍或上卿級大將軍,因此來歙是以低秩監高秩、以鄙官監高官也。此次正式作戰,來歙由留屯監軍改派爲征討監軍,史稱歙是“率”諸將以行,用辭遣句頗有以上臨下之意。而其被刺後,竟以監軍使者身份“召”虎牙大將軍蓋延至,“欲相屬以軍事”,又“叱”之,且言“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則的確有以上臨下之權勢也,可以無疑。監軍中郎將何以有如此大的權勢?或許可先從漢代許慎之解字先行窺悉。《説文解字》云:“監,臨下也。”段玉裁注則謂視也,臨下也。是知監軍秩位雖較將軍低,實則對所監者具有監視臨下之意,以故有此權勢。再者,同書《馬武列傳》載:“顯宗(明帝)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遂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詳該傳卷二二,第786頁。此次作戰,由馬武以捕虜將軍掛帥,故本傳所書以其爲首,固當也;然而《顯宗紀》中元二年(57)十一月條則記此次征行,謂“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討燒當羌”,顯示較正式的官方記載是以監軍——即監軍使者——竇固爲先。蓋竇固雖爲中郎將,但隸於郎中令體系,具有内廷禁衛軍官性質,是以天子命之奉使監軍,遂有臨下之勢。來歙亦同此例。
監軍既對主帥及諸將有臨下之勢,因此也大有與主帥共同統率軍隊之權,如秦始皇死前詔令扶蘇“以兵屬蒙恬”,來歙“率”及“叱”所監將軍等行爲表現,皆足以説明監軍的確有此權勢。《後漢書·馬援列傳》載其征討五溪蠻,亦見有此類事例:
(建武)二十四年(48),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没,援因復請行……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四萬餘人征五溪……明年……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曰:“……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
同書《宋均列傳》則載云:
後爲謁者。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没。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阸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温溼疾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吕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筆者按: 武威將軍劉尚擊五溪蠻,因輕敵而全軍覆没,以故光武遣伏波將軍馬援率中郎將馬武等往征。因援軍遲滯,是以光武遣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來責問,大概當馬援病危時“因代監軍”。此之所謂“因代監軍”,恐怕是指臨時代行統帥以監統其軍之意,蓋因馬援率軍至時,光武已詔“令(宋)均監軍,與諸將俱進”,故不可能一軍中有兩監軍也。因此,不論梁松是代監軍也好,代統帥也好,皆應指代馬援行使統率權而監統其軍。宋均本官雖是掌理賓讚受事的六百石謁者,然於統帥死後,仍以正式監軍的身份,召集諸將商議軍事,行使監軍權,而致“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其權勢可見一斑。*《資治通鑑》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三月條有載此事(見卷四四,第1408—1413頁),但對梁松“因代監軍”,宋均“監援軍”之事無考。又,虎賁中郎將領期門兵,秩比二千石,謁者掌賓讚受事,六百石,皆郎中令(即光禄勛)之屬官,見《漢書·百官公卿表》,卷一九上,第727頁。由此言之,監軍與護軍性質雖相類似,但後者決無前者之地位權勢,可以知矣。
至於督軍,漢常制無此官,其初起時蓋是戰時之編制。
《宋書·百官志》追溯其淵源,謂“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可謂説對了一半,因爲督軍既是戰時編制,故當然“事竟罷”也;然筆者前面之所以言其説尚值商榷者,蓋因揆諸史書,似未見建武初即有征討四方時始權置督軍御史之例也。而《南齊書·百官志》謂刺史爲使持節都督或持節督,“起漢從帝(即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揚、徐二州軍事”云云,嚴耕望先生亦以《南齊書》所載爲是,並謂馮赦即馮緄,*詳嚴先生前揭書上册,第87—88頁。其説頗有疑處,以故竊謂可再商榷。
按: 《後漢書·馮緄列傳》云:
初舉孝廉,七遷爲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群賊,遷隴西太守。
而同書《順帝紀》建康元年(144)八月條則云:
楊、徐盜賊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遣御史中丞馮赦督州郡兵討之。
是則馮赦即馮緄,嚴説殆無可疑,所謂“督州郡兵”即是“督揚州諸郡軍事”,恐怕《南齊書·百官志》所謂“督揚、徐二州軍事”有誤。又,馮緄獲督軍討賊之授權,而一書之中或載其持節或否,正可作爲省文之例。又據同書《法雄列傳》載此類事情更詳細,謂:
(安帝)永初三年(110),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111),伯路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轉入高唐,燒官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乃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乃徵(宛陵令法)雄爲青州刺史,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會赦詔到,賊猶以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爲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必……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埶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
此是地方性動亂,事情發生較馮緄之事更早,《安帝紀》載於永初三年七月,謂“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是則龐雄先以侍御史督州郡兵討破張伯路,只是翌年伯路復叛,聲勢更大,於是乃有命王宗以御史中丞“持節”發幽、冀諸郡兵數萬人,與青州刺史法雄并力進討之後續行動。然而,《安帝紀》永初四年正月條,又謂“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討破之”,則省去“持節”而用“督”字。是則此次平亂,行使督戰權的先是督軍御史龐雄,後爲持節督軍御史中丞王宗,其名義皆是以督州郡兵作戰,與馮緄之督州郡軍作戰正同。是則督州郡兵即是督州郡軍,也就是督軍,若是,則不論持節督也好或不持節督也好,其制皆不起於順帝時之馮緄,甚至也可能不起於安帝時之王宗。兹試論之。
由於地方動亂常有流寇性質,動輒連及數郡乃至數州,以故所謂督州郡軍事或督州郡兵之“事竟罷”戰時編制因而肇興,以免督軍由督戰進而占據地盤,造成尾大不掉之局。按“督”之爲義,《説文解字》云:“督,察視也。”前引段玉裁注釋“監”字,亦謂視也;但監有臨下之意,而督字無此意。是則“督”字用於軍事派遣,蓋具有視察督促之意較多,然視察督促行之既久,則毋寧就如同監軍之監督也。督軍之起始雖不及監軍、護軍之早,但西漢即已有之,如《漢書·酷吏傳》載漢武帝時:
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小群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
此爲差使前往州郡督軍討捕盜賊或持節發州郡兵討捕盜賊之例。《漢書·成帝紀》永始三年(前14)十二月條載督軍使之職責更清楚云:
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逐捕,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
顔師古注曰:“趣讀曰促。”*此條及注見該紀卷十,第323—324頁。此更明顯是盜賊流動爲禍,竟至經歷十九個郡國之多,天子於是分遣使者前往督促州郡逐捕之,而且皆是持節前赴。此事與上條引文之事皆發生於西漢,而早於馮緄之例甚多。
及至兩漢之間,群雄與盜賊林立,*此情況可概見於《後漢書·光武帝紀》更始二年正月條,卷一上,第12—18頁。由是戰争頻仍。於是遂因用兵需要,光武即位後,與監軍一般,乃起用武官督軍作戰,如建武四年(28)拜將軍馬成督軍征討,《後漢書·馬成列傳》云:
拜(成)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進圍憲於舒……至六年春……盡平江淮地。
其後又派將軍馬援督軍遠征,《馬援列傳》載此事云:
(建武)十七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璽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官中郎將)劉隆爲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
交阯之役亦見於《光武帝紀》建武十八年四月條,謂“遣伏波將軍馬援率樓船將軍段志等擊交阯”云云,是則將軍“督”將軍、諸校作戰之爲義,實乃等同於“率”,因而督率也就頗有統率之意,即使督軍非武官充任亦然。因此,同書《張宗列傳》謂:
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潁川桑中盜賊復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
是則張宗先以太中大夫將兵討賊,後以謁者督郡兵討賊,與後來王宗之以御史中丞督郡兵討賊般,皆是以非武官身份充使視察督促軍隊,而實際上行使作戰指揮權。上述史書所載諸“督”例,均有領兵作戰的軍事作爲,只是兩漢群雄之間,戰争較正式而大型,故頗以武官充督或監罷了。蓋將軍知兵,原本在制度上即爲法定統兵作戰之官;至於地方動亂,非是正式征伐野戰,以故仍沿西漢慣例而多以文臣充使。其實光武以來如此諸例,不論是以武官督軍征戰也好抑或是以文臣督兵討捕也好,性質皆與監軍使之監軍殆無大异。由於督軍原掌視察督促軍隊作戰,初對主帥諸將殆無臨下之意,至光武時以將軍任之始如同主帥,故由此可知,爲何督軍之權位高於護軍,而監軍又高於督軍,以至晉世定制,遂成爲“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之等級矣。
又,據《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三年(160)九月條載:“太山、琅邪賊勞丙等復叛,寇掠百姓,遣御史中丞趙某持節督州郡討之。”而同書《趙彦列傳》則載云:
趙彦者,琅邪人也……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没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爲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彦爲陳孤虚之法……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見《後漢書·方術列傳·趙彦傳》,卷八二下,第2732頁。
是則此御史中丞趙某即是趙彦,而此役不僅是趙彦持節督州郡討賊,而且宗資也以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據此而論,蓋趙彦先以文臣持節督州郡討賊,似因戰事不理想,是以再命武官宗資杖鉞將兵督州郡實行合討。在軍中,趙彦既爲宗資陳策,因此統帥應即是宗資。另外,“節”是帝王之大器,“持節”是代表天子臨軍,殆有加重持節者威權的作用。*《續漢書·輿服上·大使車》條謂“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見《後漢書》志二九,第3650頁)同書《郡國五·交州》條注引王範《交廣春秋》,載“詔書以州邊遠,使持節,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鎮”(《後漢書》志二三,第3533頁)。因此鄭興勸隗囂,謂“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後漢書》興傳,卷三六,第1219頁),而《續漢書·百官四》載武帝初置比二千石的司隸校尉時,使“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注引蔡質《漢儀》謂“職在典京師,外部諸郡,無所不糾。……入宫,開中道稱使者。每會,後到先去”(志二七,第3613頁),亦是爲了加重司隸校尉的威權。此皆可見擁節有加重威權的作用。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宗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寇盜之“鉞”,即是大斧,亦是帝王之大器,授予領兵出征的統帥,殆有授予專征討以行大刑的全權之意,*《續漢書·輿服上·法駕》注引“《説文》曰:‘鉞,大斧也。’《司馬法》曰:‘夏執玄鉞,殷執白鉞,周杖黄鉞。’”(見《後漢書》,卷三,第3649頁)《後漢書·公孫述列傳》注引《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黄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卷一三,第539頁)可見統帥杖鉞,是代表帝王用兵之大器,而用兵即是行大刑也。宗資在此役之所以作爲統帥,權力在持節督軍御史趙彦之上,即與此授權有關。又,史載“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麗嗣子伯固並畔,爲寇鈔,四府舉(橋)玄爲度遼將軍,假黄鉞。玄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見《後漢書·橋玄列傳》,卷五一,第1696頁。是則或因此戰具有大型國際戰争的性質,於是天子不僅假“鉞”於征討軍統帥,而且是假以“黄鉞”。在後來的魏晉都督制中,“假黄鉞則專戮節將”,*《宋書·百官志》謂“假黄鉞,則總統外内諸軍矣”;又謂“假黄鉞,則專戮節將,非人臣常器矣”,見卷三九,第1225頁。其先例概已見於此時。
綜觀《後漢書》所載,名稱不論是督、督軍或督軍使者,其實就是督州郡兵(軍)、督某將軍軍之稱謂,前者多持節,是較名正言順的使,後者少持節,常爲派遣武官督戰時所任。當其派出時,史文常書爲遣使者督,或謂遣謁者督、遣侍御史督、遣御史中丞督、遣中郎將督、遣校尉督以至遣都尉督等,不一而定;而亦常與本官合銜而連稱,如督軍御史、督軍中郎將、督軍校尉等。要之督軍位秩一般皆高不過領兵之將軍或州郡二千石長官,而且也不一定是武官,因漸以具有法定監察權的御史系統官員充使爲多,以故“督軍御史”較常見。除正式作戰之時,朝廷常命法定統兵武官擔任督軍,而不常書其爲持節使者之外,平時督軍使者執行之任務,或是監督軍隊的屯駐,或是平定地方——含少數民族——之動亂,戰事都不算太大或太持久,所以常由文臣充使,並常是就近督發州郡兵執行任務,當然兵力規模也就不致太大。
史載建安十七年曹操南征孫權,表請荀彧勞軍於譙,因表留彧曰:“臣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臣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王命……臣輒留彧,依以爲重。”遂以彧爲侍中、光禄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見《三國志·荀彧傳》,卷七,第2290頁。按: 荀彧自獻帝都許以來,一直以侍中、守尚書令參與籌劃軍國之事,表上後改爲持節、侍中、光禄大夫,參丞相軍事,職稱非監軍使或督軍使,但據曹操所言,則實際有監督之重。既然曹操已挾持天子,則其强逼獻帝命内臣持節,用參軍事之名義監督己軍,誠是絶對可能之事。然而既謂“古之遣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是則副二之將居於監督之下固可無論矣,不過主將、監與督三者在軍,權位差别如何?
前謂監督軍旅之使,位秩殆皆高不過領兵之將軍,但是威權則不然。或許由馮緄督軍平揚州動亂後之事例可作考察。據《後漢書·馮緄列傳》所載:
馮緄……少學春秋、司馬兵法……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群賊,遷隴西太守。後……遷廷尉、太常。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桓帝,162),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閑,荆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南,皆没。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各焚都城,蹈籍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内御……將軍其勉之!”
時天下飢饉,帑藏虚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爲所中,乃上疏曰:“……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荆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傅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以軍還盜賊復發,策免。
按: 馮緄曾有持節充督軍使之經歷,及至拜爲朝廷第三號的車騎將軍,將兵十萬而爲統帥,雖説天子已特别聲言委以指戰全權,但卻仍自請於監軍使者之外,另置宦官以監軍財費,可謂畏慎已極。然而戰勝而還,作爲大軍統帥的他,最後仍因監軍使者之奏劾而受審。可見面對天子所派、具有臨下權勢的軍隊監使,連大軍統帥如馮緄者也不免爲之畏懼,是則何來事權一之、不復内御的全權委任?至於下文所述小黄門蹇碩之例,以上軍校尉充“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以及大將軍所領屬,可見統帥在軍,威權不在監軍使及督軍使之上,反而像曹操所言,監督之重在將之上也。或曰此爲漢末情況,且涉及宦官,不過觀東漢初中郎將來歙監征西大將軍馮异等五將軍軍時之威勢,是知統帥之“上設監督之重”,的確是由來有自也。
又,《後漢書·皇甫規列傳》載桓帝延熹四年,命中郎將皇甫規持節監關西兵出討叛羌云:
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别種寇鈔關中……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
皇甫規持節監關西兵出討諸羌,使涼州復通。及至來到州界,悉條奏督軍御史張稟、涼州刺史郭閎等官員之罪,使之或免或誅。此例顯示即使並在軍中,不但統帥之“上設監督之重”,而且監使之威權又重於督使也。這正是魏晉都督制監州諸軍事權位在督州諸軍事之上的淵源。
四、 靈、獻之際軍隊監督制度的變化與督軍及督將
東漢順帝差遣馮緄督軍之後,督軍制之變化尚有若干事例值得注意。
桓帝之後是靈帝,諸葛亮《出師表》所謂“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親小人遠賢臣而導致後漢傾頽,從靈帝晚年黄巾大起後,而竟任命宦官督軍之事例,可以窺見一斑。按: 中平元年(184)二月張角起事,約三十餘萬人,十餘年閑,自青、徐、幽、冀、荆、楊、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顯然與以前州郡動亂之規模大不相同。*詳《後漢書·孝靈帝紀》中平元年二月條并注及同書卷七一《皇甫嵩列傳》。當時,靈帝以外戚何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以鎮京師。復起大壇,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此事《靈紀》繫於中平五年(188)十月甲子,軍事部署與天子閲兵則詳於《後漢書·何進列傳》,卷六九,第2246—2247頁。時勢可謂緊張之極;不過《後漢書·何進列傳》卻載云:
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黄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爲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西園八校是禁軍,司隸校尉所屬是首都治安部隊,大將軍當時統有部分禁軍以及首都衛戍部隊,由此可見,此時中央一切軍隊,均隸屬於擁有督軍權之上軍校尉小黄門蹇碩,以故受命充“督”之宦官蹇碩,即是以督軍校尉成爲首都諸軍的“元帥”——在魏晉軍事體制上,禁軍是中(内)軍,衛軍是外軍,魏晉以降中央置有“都督中外諸軍事”一職,*中、外軍之分别有多説,筆者從軍制學觀察,認爲以禁、衛二軍作解釋爲宜,請詳前揭《從督軍制、都督制的發展論西魏北周之統帥權》拙文。有關中央都督制之討論,較著者爲何兹全的《魏晉的中軍》(《史語所集刊》17,民國37年),與祝總斌的《都督中外諸軍事及其性質、作用》(收入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主要討論中軍組成、功能,以及中、外軍之别等問題。後者更稱西晉以降都督中外諸軍事虚銜化、榮譽銜化,以致至隋消失云云,所論非從軍制學觀察,且有過推之嫌,筆者不能苟同。此則爲其濫觴。爲此,稍後大將軍何進不得不召董卓兵團入京,欲以兵變方式盡誅宦官,卻遭實際掌握統帥權之督軍宦官反兵變,導致董卓廢立天子,使後漢爲之傾頽。據此可知,督軍以文臣充使討賊,原是沿襲西漢以來的慣例;但在征討作戰時,則頗改以將軍或中郎將任之,因此之故,當漢末國家已進入緊急狀態之時,靈帝竟以秩比四百石之小黄門蹇碩督軍爲元帥,是則實爲异數矣。
不但中央兒戲如此,當此之時,史載官爲太常的宗室劉焉,見“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爲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爲交阯,以避時難”。於是“出焉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太僕黄琬爲豫州牧,宗正劉虞爲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及至獻帝興平元年(194),劉焉病卒,州吏立其子劉璋爲刺史,詔書因而以璋繼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引文見《後漢書·劉焉列傳》,卷七五,第2432—2433頁。《三國志·劉二牧傳》略同,見卷三一,第865頁。此處宜注意的是,假如董卓兵團之崛起代表了漢朝軍隊的私人部曲化,則劉焉父子類似世襲的相繼以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使監軍權與地方行政權合一,則是代表了全權掌控地方的制度已開始興起。稍後,建安二年(197),獻帝遣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冀州牧袁紹爲“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使管治四州之地、數十萬衆。*見《後漢書·袁紹列傳》,卷七四上,第2389—2390頁。抑且代表了原本已擁有監軍權而逐漸干預統率權的監使督使,至此又與地方行政長官相兼,並且是以天子名義任命之,是則朝廷自中央至地方名實俱失,斯則後漢傾頽之勢已不可扶救。難怪建安十五年丞相曹操下《求賢令》,大言“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矣!*見《三國志·武帝紀》是年注引《魏武故事》所載十二月己亥令,卷一,第33頁。
由上所論可知,魏晉都督制中之戰時征討都督制——濫觴於西漢之遣使督州郡兵討賊,其以督某將軍軍之名義督軍征伐者,則至遲在兩漢之間已見萌起,而固定督某州諸軍事之軍區督軍制,則約在靈、獻二帝之間乃見雛型。總而言之,征討都督制濫觴於西漢,軍區都督制則約成於東漢靈、獻之間,均非如《南齊書·百官志》所説般“起漢從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揚、徐二州軍事”也,*順帝建康元年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之馮緄應只是事畢則撤的征討統帥,助其平亂的中郎將滕撫,於翌年(冲帝永嘉元年,145)又以九江都尉“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群賊,尋於遷拜“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後,復又進擊張嬰,悉平東南而還,遷爲左馮翊。按: 馮緄此時不知是否已改調去職,但其所帶是持節督軍職銜甚明,而滕撫則是以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繼續進討餘寇,似仍是征討之督而非軍區督,由於緄、撫二傳均記述不詳,故暫不視其二人爲魏晉軍區都督制之先例。只是充任督軍者均未以“都督”一名作爲大號而已。至於以“監”爲名之征討監軍與軍區監軍,其制的發展情況約略相同,只是征討監軍較常見耳。
再者,獻帝遣使拜袁紹爲大將軍兼督四州,是當時割據群雄之最强大者。實則袁紹崛起之初領冀州牧時,即已引沮授爲别駕,尋“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按: 袁紹軍中另置有護軍,以故此之所謂“監護諸將”,即是監軍,故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戰前,沮授與袁紹軍府僚屬争議應采之戰略時,郭圖等批評沮授之策保守,謂“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並且,史載“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内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内。’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云。*參《後漢書·袁紹列傳》,卷七四上,第2378—2379、2390—2391頁。《三國志·袁紹傳》略同。就此而論,軍閥割據之時代,軍權被作爲統帥的軍閥所牢牢掌握,監軍、督軍僅是爲其監統軍隊而已,幾乎皆非天子所正授,以故多不擁節;然其威權地位以及在軍中之事任,則殆與兩漢以來的情況相比變化不大,故郭圖等謂監軍沮授監護諸將,監統内外,御衆於外,威震三軍是也,而督軍之權勢則僅略遜耳。至於袁軍此時所置之三都督,究其實質殆爲督軍之另名,與始見於董卓軍系作爲戰鬥單位主官的都督不同。由於此職名關係漢晉之間都督大帥化的變化發展,故宜先考其初起時之地位職掌。
按:“督”之爲義有察視之意,用於軍旅意即差遣至軍視察軍隊並督之作戰,因而其基本職權就是視察督戰權。東漢差遣督軍使較西漢常見,且由視察部隊而漸干預指揮權,即使非武官任之亦頗然,此蓋因監督之重在於主將之上故也。及至靈、獻之際,督軍之身份職權遂因上述的演變,而發生兩種分化趨勢: 即軍區大帥化以及戰鬥職稱化。前者指變爲大帥級——督某州諸軍事或都督某州諸軍事——軍區司令,後者則主要是指分化爲軍隊基層單位的各種督將。
先論後者,據《三國志·武帝紀》建安五年十月曹操襲擊袁紹軍糧所在之烏巢時,裴注引《曹瞞傳》,謂“大破之,盡燔其粮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等,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云。*《後漢書·袁紹列傳》注亦引此書,但不及《武帝紀》注所引詳,見卷七四上,第2401頁。所謂“將軍淳于仲簡”,即是前西園八校之一、後爲袁紹三都督之一的淳于瓊,可見袁軍野戰體系之中,督將與都督不同,而督將地位遜於都督。曹軍與此略不同,如龐悳拜立義將軍,率所領與曹仁戰關羽於樊,會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羽乘船攻之,悳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因船覆水中而爲關羽所得。是役曹仁以假節、征南將軍爲統帥,*龐悳事參《三國志·龐悳傳》,卷一八,第546頁。曹仁官職則見同書本傳。其實此役關羽所部亦見有都督,見《三國志·吴主權傳》建安二十四年條,卷四七,第1121頁;及同書《潘璋傳》,卷五五,第1299頁。顯示立義將軍龐悳應是其所部,即是其手下督軍之一,而悳之手下則置有地位更低的戰鬥督將。可見袁紹的戰時野戰編制爲主帥—都督—督將—戰兵;而曹軍則爲主帥—督軍—督將—戰兵。都督在野戰編制中,身份地位至此尚未有一致的規劃;但都督一職決非大帥之職則可知。尤其“督將”一名之漸見,代表了基層野戰軍官分化爲督將、騎督、都督等等軍職之發展趨勢。
靈、獻以後,“督將”爲上述基層野戰軍官分化後的統稱,而其中之“都督”則殆爲督將中之專稱,董卓軍系載之最清楚,反而最早載於史書的公孫瓚恐不可靠。
按:“都督”一名表面上似始見於公孫瓚,但深究其實則不然。既事涉魏晉都督制的初始,以故宜略爲考證。《三國志·公孫瓚傳》載云:
公孫瓚……以孝廉爲郎,除遼東屬國長史……遷爲涿令。光和(靈帝,178—183)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
然而《後漢書·公孫瓚列傳》所載參戰事頗與《三國志·公孫瓚傳》不同,而謂:
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中平(靈帝,184—189)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温討涼州賊。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
根據《後漢書·公孫瓚列傳》校勘記,則謂“‘突騎’下疑有奪字,或是‘從’字,或是‘屬’字”云。姑無論奪去何字,要之此傳與《三國志·公孫瓚傳》所記時間以及隨誰作戰等,均互有出入。
據《後漢書·靈帝紀》載,張温爲車騎將軍事在中平二年八月,翌年二月即去任而爲太尉,是則公孫瓚率突騎三千人隸張温往討涼州賊,只能判定發生於此時段,故同書《張霸列傳·玄附傳》謂“中平二年,温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是也。*見《後漢書》,卷三六,第1244頁。
又據《靈帝紀》,涼州賊邊章於中平元年十一月從湟中義從胡北宫伯玉與先零羌叛,*《後漢書·蓋勛列傳》亦載謂“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寇亂隴右”,見卷五八,第1880頁。是則翌年遂命車騎將軍張温前往討之,而公孫瓚率突騎三千人屬之,則所率之幽州突騎也就應就是烏桓突騎。*《三國志·公孫瓚傳》失載瓚督騎從張温西征之事。又,兩漢之間幽州烏桓突騎即相當有名,爲光武所用(詳《後漢書》卷八《吴漢列傳》)。烏桓突騎或作烏丸突騎,魏晉世一直爲善戰之名騎,屢爲北方割據者所用,如《三國志·牽招傳》載謂“冀州牧袁紹辟(招)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卷二六,第730頁)。而《後漢書·應奉列傳·劭附傳》載“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爲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卷四八,第1609頁),可以參考。筆者按: 據《靈帝紀》,中平二年三月先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西征,不尅,同年八月乃以司空張温爲車騎將軍往討。因此,瓚督烏桓突騎隸屬張温往討,殆在中平二年八月以後。其後瓚與袁紹交戰,烏桓助紹擊瓚,破滅之;赤壁之戰後曹操平河北,破烏桓,“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爲天下名騎”云(見《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卷三,第835頁)。
由於《三國志·公孫瓚傳》將涼州賊起事提前繫於光和中,時間上不合,又失載瓚督騎從張温往征之事,且謂“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一句不僅職稱不明,且語意欠通,*鄙意應將“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標點爲“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爲宜。因爲若從字面作解釋,本句蓋指朝廷征發三千突騎,而假公孫瓚以都督,使行督率之事,傳使將之也。而陳壽頗有將魏晉後來既定職稱與漢末尚在變化時之職稱相混淆之例,是以陳壽此處所述可信度較低;相對揆諸史書,中平二年以前尚未見有“都督”之名,而派督軍指揮作戰則是東漢常見之事,且其職位通常低於太守,以故《後漢書·公孫瓚列傳》所載較符慣例,較爲可信。因此,靈帝末年征討軍系統已置有都督之職可以置疑,而最早之例約見於靈帝崩後董卓的軍中則爲可能。
靈帝崩(中平六年,189)後,董卓廢弒少帝,立獻帝,引起“山東義師”群起討伐,卓乃挾帝西遷長安(初平元年,190),全國自此陷入群雄割據戰争之中。戰争既頻,於是戰鬥單位“督將”之名遂在軍中漸漸普及,而“都督”一名亦連帶出現。兹試論之。
董卓挾帝西遷,當時長沙太守孫堅率郡兵進屯陽人。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爲大督,吕布爲騎督”前戰。*事詳《後漢書·董卓列傳》注所引《九州春秋》卷七二,第2328—2329頁。嗣因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堅追擊之,軫、布敗走。《三國志·孫破虜討逆傳》注引《英雄記》對此役載謂:
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吕布爲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軫……性急,預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欲賊敗其事……軍衆擾亂奔走……軫等不能攻而還。*見《三國志·孫破虜討逆傳》注,卷四六,第1098頁。按: 胡軫爲大督護殆非,理見正文。又,孫軍知董軍有大督之編制,故其後亦有此編制,如吕蒙爲大督督軍襲關羽而取荆州即是其顯例;後來劉備也仿之,親征報仇時,任馮習爲大督。有關此事容另文發表,於此不贅。
大督護之職前所未見,三國亦無有,故筆者以爲,胡軫是以太守而爲“大督”,*《通鑑》漢獻帝初平二年(191)二月條僅謂“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吕布爲騎督”,見卷六,第1919頁。按: 應以前注所引《九州春秋》爲是。吕布爲“騎督”,是此二名的初見。所以稱“大督”者,恐因此役“吕布爲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而以“大督”作爲主帥之故也。“大督”所統既多督將,以故稱大——亦即卓軍此役的野戰編制爲“大督—督將(都督)—戰兵”是也。據《後漢書》與《三國志》卓傳,卓軍中盡多中郎將及校尉,吕布即是其中郎將之一,皆爲漢制之正式官名,是則此之“大督”、“騎督”以至“都督”,皆應是由董卓臨時指令麾下此類將校充任之,用以各率所部赴戰的戰時編制,可以明矣。“大督”既由二千石太守充任,則其下諸督及都督,位秩恐皆不能超過之。位秩既輕則容易除授,是以步騎將校充任都督者甚衆,可以想知也。陽人之役,孫堅“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見《三國志》卓傳,第1096頁。顯示卓軍胡軫部的確都督甚衆,然而只是野戰系統戰鬥單位將校之任,而非大帥級主將。
不僅權臣如董卓之自行指派都督或督,即使討卓的山東群雄,多無盟主袁紹般之位秩與聲勢,己身充其量不過只是將軍刺守而已,不便也很難動輒向已被董卓挾持的獻帝表請其屬下爲將充使,因而率多從權,擅自命將,所在有例。除了袁紹軍隊前已略敍之外,例如吕布叛殺董卓之後,被遷爲“奮武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尋爲卓部反攻所敗,逃至關東,依違於群雄勢力之間,爲平東將軍,兵力僅數千人;然而布軍有一支勁旅,屢敗群雄。《三國志·吕布傳》注引《英雄記》載云:
建安元年(196)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内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閤外,同聲大呼攻閤,閤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内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即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衆……順斫萌首……送詣布。*見該傳裴注,卷七,第223—224頁。
按: 都督高順營即布軍之“陷陣營”,同傳裴注復引《英雄記》曰:
順……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鬭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陳營。順每諫布……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外内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見該傳裴注,第227頁。《後漢書·吕布列傳》注引《英雄記》同而略簡,見卷七五,第2450頁。
是則作爲平東將軍的吕布,兵力也不過數千人罷了,因此麾下之都督所督僅七百餘兵。“都督”高順,《後漢書》布傳稱之爲“督將”,是爲“都督”即“督將”專門職稱之一證,且已有正式職稱化的傾向。要之,觀高順所爲所事,知布軍“陷陣營”的戰鬥單位主官職稱爲都督,所將僅七百餘兵,其事甚明。
吕布軍系出董卓軍,故其軍中編有都督等督將不足奇,至於作爲山東群雄之一而相繼統部的孫堅、孫策父子,所部亦有都督乃至大都督之編制。
如《三國志·吕範傳》謂孫策“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楊賊,還吴,遷都督”,孫策稱之爲“小職”。*見《三國志·吕範傳》及注引《江表傳》,卷五六,第1309—1310頁。策死於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戰時,弟權嗣位,所部即有大都督之編制。如史載權弟孫翊爲丹楊太守,禮致故孝廉嬀覽與戴員,以“覽爲大都督督兵”,*見《三國志·吕範傳》及注引《吴歷》,卷五一,第1214—1215頁。皆是其例。要之孫軍早期的大都督地位尚處於太守之下,都督則約高於縣令而已,是否仿自董卓軍系之編制則不得而知。至於約略同時之袁軍編有基層戰鬥單位督將,曹軍頗亦如是,顯示此類“督將”在群雄軍中已漸普置,只是因其位階低而戰功不著,群雄存活又多不長久,又或群雄初起時因兵力薄弱而不置,以故其基層戰鬥單位督將遂名不見於史傳耳。
至此,似應回過頭來看公孫瓚率突騎三千人之事,以探究如此類事例者竟是何體制何地位。
據兩書瓚傳,公孫瓚之率突騎三千人隸車騎將軍張温軍出征涼州賊,有幾個要點應注意: 第一,公孫瓚不是征討軍統帥,而是統帥轄下一支軍隊之主帥;第二,似不是督軍使,以故未持節;第三,似不是僅領數百乃至上千部隊的戰鬥督將;第四,是以位於太守之下的遼東屬國長史,臨時配屬統帥張温以赴戰之領軍主帥。按: 東漢以來,持節督諸將軍軍或持節督州郡兵者一般位階多在將軍、太守之下,雖然公孫瓚上述之第四點頗符位在將軍、太守之下——監察者位於被監察者之下——的原則,但其餘諸點皆不盡然,因此顯示公孫瓚應是統帥麾下督軍之一,但非持節之督軍使;此種領數千人作戰的督軍,如果獨立作戰則就是戰役主帥,即使降至建安中後期亦然。揆諸《三國志》卷一七所敍于禁、張遼、徐晃諸將,其實皆與瓚例頗爲相同,只是彼等督軍時已因戰功遷爲雜號將軍而已。如該卷敍于禁,曹操拜禁爲虎威將軍,嗣因常恨朱靈,以禁有威重,遣禁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乃以靈爲禁部下督,其後于禁及其所督七軍於樊因被水所淹而降於關羽,已是衆所周知之事。此是于禁爲督軍主帥,手下置有督將之例。另一例如張遼,逍遥津之捷後拜征東將軍,曹操巡行其戰處,歎息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其後魏文帝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詣遼屯合肥,並敕遼母至,導從出迎,遼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云。復如徐晃,從征張魯,遷平寇將軍,留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後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晃所將多新卒,難與羽争鋒,曹操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亦即是皆配屬於晃之督部也。此諸將皆未見有領太守之記載,不如夏侯惇、夏侯淵、曹仁諸將般領太守,或許表示其雜號將軍尚未高到可以領郡之任,或是曹操僅欲單純委之以督軍屯守作戰之任而已;不過,他們殆皆是督軍,並皆可以獨立作戰而爲主帥,轄下置有若干督將。由此足以反映漢末喪亂之時,諸軍閥在無天子以遣使持節名義之授權下,各命手下將校出督軍隊,以實行征討野戰的戰時體制也。
此征討野戰體制之督軍,若移用於任之以方面、責之以守土——亦即負責區域防禦,即爲軍區都督制之濫觴。以下舉袁軍之變化以概此制早期的主流發展。
群雄之中,最早發展出魏晉都督常制形式的厥爲袁紹軍隊。蓋獻帝初平元年(190)山東義師起,群雄推袁紹爲盟主,翌年袁紹爲冀州牧後,乃表别駕沮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因是袁紹“表請”,以故沮授並非持節監軍使,只是軍閥之監軍而已。及至初平四年,行奮武將軍、領兗州牧的曹操爲報父仇而攻徐州牧陶謙,史載:
初,清河朱靈爲袁紹將。太祖(曹操)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此事附見於《三國志·徐晃傳》,卷一七,第530頁。
是則朱靈所督諸營野戰軍,除本營之外,所督别營並不隨靈留下。假如將之與此時吕布所屬的陷陣營比較,陷陣營主官是都督——也就是督將——高順,則朱靈所督三營每營殆皆編有督將,而朱靈本人則是袁軍之督軍,只是因非天子所遣,以故也非持節督使,而只是軍閥之督軍。此類由漢末軍閥派出之不擁節“監軍”、“督軍”,《三國志》紀傳所在多見,至於曹操集團稍後頗有擁節者,則是因其已挾天子之故。
降至獻帝拜袁紹爲大將軍兼督四州之地,有衆數十萬,統督如此龐大的軍隊以及如此廣大的地盤,正是袁紹可以實行整編其組織的本錢,故降至建安五年(200),袁紹選擇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曹操,乃分監軍沮授所統爲三都督,命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由是言之,儘管三都督未必是平均分配沮授的兵力,又容或另有其他將領如顔良、文醜、張郃、高覽等亦受分配,要之每一都督所統兵力亦應不少,殆皆在萬人以上纔是。是則此時袁軍之中,三都督各典一軍無疑就是三個戰役單位的督軍,與董卓、吕布、孫策等軍將之作爲戰鬥單位督將不同,以故乃有“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遂發生都督淳于瓊及其所督諸督將、騎督均被曹操襲殺之事。*見《三國志·武帝紀》建安五年十月條及注引《曹瞞傳》卷一,第21頁。按: 《三國志·張郃傳》載:“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卷一七,第525頁)此處之“督”字應作動詞用,因淳于瓊已爲都督故也。由此可以判斷,此時袁軍之都督,在軍制意義上已出現大帥化之傾向。從喪亂之世户口大損的情況看,統兵萬人實在已算是大軍,於其下再編置若干戰鬥督將與騎督殆爲可能之事,是則在袁軍野戰系統“都督—督將—戰兵”之編制下,都督顯然權位並不低,至少比董軍、吕軍以及孫軍中都督之權位高許多,難怪去年袁紹任長子譚出爲青州都督。《三國志·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載其事云:*見《三國志·袁紹傳》及注,卷六,第195—196頁。按: 此事發生在建安四年紹破公孫瓚之後,故筆者曰去年,翌年始有分監軍爲三都督,使授等各典一軍之事。
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譚始至青州,爲都督,未爲刺史,後太祖(曹操)拜爲刺史。
袁紹出袁譚任職都督,正顯示都督權位不低,已頗有大帥化之傾向;不僅此也,抑且兼有軍區化之趨勢,只不過低於紹之“督冀、青、幽、并四州”,並不兼治部民而已。袁譚此例,蓋爲魏晉軍區都督制都督掌兵、刺史治民,偶例之外常不相兼之先河,*自晉惠帝末以後,都督必領治所之刺史。詳參嚴先生前揭書,第88—89頁。而也是都督若干州管下置有一州督或一州都督的制度張本。
總之,官渡之戰前,袁軍軍區系統已出現都督一職,與野戰系統都督一般,均有大帥化之傾向。而且,袁軍“都督—督將”之編制,頗暗合“戰役—戰鬥”以及“戰略—戰術”軍事體系建立的原理,*若單就袁軍都督統兵萬人以上而言,漢魏間固已是大將之任,即使至建安末曹軍名將如于禁、張遼等,所統兵力亦不過數千人而已。作爲野戰大軍統帥,或許無權參與軍事戰略、國家戰略乃至大戰略層次的策劃,但對野戰(戰場)戰略以及主持戰役,肯定有決定支配之權力。蓋爲前所未有的編制,是東漢督軍制過渡至魏晉都督制之一變。袁紹野戰軍的“都督—督將”編制承自董軍的“大督—督將”編制,而其以督或都督作爲軍區主帥之職名則應與曹軍的發展有關,故需論曹軍之崛起與再發展。
五、 建安、黄初間曹軍體制變化: 大帥級都督制之成立
何進等謀誅董卓失敗後,曹操間行東歸,散家財合義兵,有衆五千人。*見《三國志·武帝紀》及注引《世語》,卷一,第5—6頁。及至初平三年(192)領兗州牧,追破黄巾,受降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鋭者號爲青州兵,兵力始大。建安元年(196),曹操迎天子都許,拜司空、行車騎將軍,勢力漸固,然後乃有建安五年敗袁紹於官渡之事。
從曹操崛起之初以至其終,部下均置有督將,或因位低權微,以故史傳記之者甚少。如興平元年(194)曹操率軍攻徐州牧陶謙時,會張邈、陳宫以兗州反,潛迎吕布,操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宫通謀”云云。*“督將大吏多與邈、宫通謀”見《三國志·荀彧傳》,卷十,第308頁。又如前述建安二十四年(219),立義將軍龐悳與關羽作戰時手下有督將成何,皆是其例。至於兵種兵科如袁軍之騎督、督糧等類督將,乃至較高級之督軍,曹軍亦有編制。如征陶謙時,“(曹)仁常督騎,爲軍前鋒”;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三國志·曹仁傳》,卷九,第274頁。此爲曹軍見有騎督之始。其後的“虎豹騎”,初由曹純所督,史謂“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鋭,或從百人將補之,太祖難其帥。純以選爲督,撫循甚得人心”云。*史載曹仁之弟純,“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見《三國志·曹仁傳》及注,卷九,第276—277頁。按: 同書《太祖紀》載曹操圍南皮之役發生於建安九年九月,顯示此前已有此兵種。由是觀之,此時的督騎與督虎豹騎所領兵力均應不太多,其所督也應是戰鬥單位,故爲戰鬥單位的督將而已。但是,虎豹騎除了從征之外,尚兼負宿衛責任,*見《三國志·曹休傳》,卷九,第279頁。又因曹操經常親征,平時如戰時,故常置督以督之,並使之具有野戰兵與宿衛兵的雙重性質,是以爲曹軍特别建制的兵種。至於建安元年曹操已挾天子而爲司空後,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曹操乃“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官渡之戰時,夏侯淵以潁川太守“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兗、豫、徐州軍糧”;其後曹操西討馬超,護羌都尉楊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等等事例,*扈質事見《三國志·徐宣傳》(卷二二,第645頁),夏侯淵事見《三國志》本傳(卷九,第270頁),楊沛事見《三國志·賈逵傳》注引《魏略》(卷五,第485頁)。顯示曹軍不僅置有名爲督軍、督、督將以及都督等作戰系統軍職,抑且視需要而專置督軍糧以及都督津渡等非一綫作戰系統的軍職。
及至破袁紹之後,曹操三分天下漸有其二,而較高級之督遂漸興,或許趙儼之例可顯示出此重要關鍵。《三國志·趙儼傳》載云:
入爲司空掾屬主簿。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荆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引文見《三國志·趙儼傳》,卷五四,第1273頁。按: 曹操於建安元年(196)爲司空,趙儼既入爲司空掾屬主簿,則應在此年以後,但明確時間不詳。至於儼徙都督、護軍,事在曹操征荆州——建安十三年九月——之時,《通鑑》即繫其事於此年。
按: 前述建安十七年曹操南征孫權時,表留荀彧“參丞相軍事”,聲言藉此以示“上設監督之重”;又因荀彧是以“侍中、光禄大夫”之漢天子内臣之名義持節奉使留軍,是則此職無疑應是當時曹軍之監軍使。同理,趙儼之參于禁、樂進、張遼三軍亦然。至於其“都督護軍”宜作“都督、護軍”,蓋同時兼任此二職也。都督爲野戰系統小職,護軍於監督系統地位亦在督軍之下,趙儼合此二職以護于禁等七軍,恐怕是因儼以霸府主簿領太守而徙任,身份較特殊,因此乃以“都督、護軍”名義擔任之;*嚴先生前揭書舉杜恕之遷“淮北都督護軍”與趙儼之徙“都督護軍”兩例,解釋爲“是魏都督諸州軍事有護軍也”(第102頁)。筆者以爲此説恐有問題。因爲東漢只有將軍始置護軍,都督小職,其下並無護軍之置,趙儼任此職是在漢世,此時並無淮北都督一職,以故暫不從其説。雖因儼非天子使者而不擁節,但此舉對“都督”一職的提升,可謂作用甚大。因爲趙儼所護七將之中,揆諸《三國志》諸紀傳,除了朱靈、路招、馮楷三將失載或官職不考外,當時于禁爲虎威將軍,張遼爲蕩寇將軍,張郃爲平狄將軍,李典爲捕虜將軍。而在此之前,于禁曾在官渡之戰時,以裨將軍“督守土山”;拜虎威將軍後,曾奉曹操之令詣朱靈營奪其軍,而以靈爲其部下督。又,陳蘭、梅成叛亂時,曹操令蕩寇將軍張“遼督(平狄將軍)張郃、牛蓋等討蘭”。*《通鑑》繫此役於漢獻帝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卷六六,第2098頁。又,于禁等將均見《三國志》卷一七,不贅。據此以推,諸將在官渡之戰以前殆皆是較低階的將校,約至建安十四年左右,已升至介乎戰鬥與戰役之間的督軍,其間大概以張遼此蕩寇將軍督平狄將軍張郃討陳蘭最爲著目,頗有戰役大督的架勢。因此,或許可以换一個角度作觀察: 于禁等七將皆是雜號將軍級督軍,依東漢例征討將軍常置護軍於其下以佐之,西漢更會偶置具有總監而又頗帶主帥性質之護軍將軍以領軍,今趙儼以二千石太守級之官徙爲“都督、護軍”,職掌恐是此七軍共同之監督指揮官。曹軍先前未曾出現過如此情況,是則趙儼起碼已可視爲是亞於大帥級之軍隊總監。“都督、護軍”之職其後於魏晉亦僅兩見,職掌亦與諸軍的監督指揮有關。*此職兩見均在趙儼之後。杜恕於魏明帝時“爲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恕附見其父《杜畿傳》,《三國志》卷一六,第505頁),霍弋則見於蜀亡之時。在蜀亡混亂之中,吴將吕興驅逐交阯太守,遣使“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自陳”(見《三國志·三少帝紀·陳留王奂》咸熙元年春正月條,卷四,第151頁)。按: 漢末都督不置護軍已見前説,杜恕之任淮北都督、護軍情況不詳,至於霍弋,史載蜀後主時“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即以監軍、翊軍將軍監統益州南部南中諸郡軍事也。獨當一面之霍弋,在蜀亡時不肯投降,及至知悉後主已東遷,“始率六郡將守上表”向晉王司馬昭投降。《漢晉春秋》謂司馬昭嘉之,“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云(參《三國志·霍峻傳·子弋附傳》並注引《漢晉春秋》,卷四一,第1008頁)。筆者以爲,蜀漢原無“南中都督”之職,因其地新定,政情未穩,故司馬昭用霍弋爲“南中都督、護軍”,蓋權宜而置,用以作爲監統原來南中六郡諸軍的總帥也。由於霍弋是降將,故從原職的監軍降級爲護軍,此爲處置亡國降臣向來之慣例。同理,蓋因淮北是戰略重地,諸軍衆多,時有戰事,故明帝用杜恕爲“淮北都督、護軍”,以作爲此區諸軍之監督指揮也。
護軍於兩漢本爲軍中督察之職,但漢末有時也兼掌統率指揮的職權,從趙儼後來出任關中護軍的表現略可窺知。按: 趙儼任關中護軍,其職責在“盡統諸軍”,而此諸軍則是平難將軍殷署等所分督的韓遂、馬超舊部五千餘人。《三國志·趙儼傳》復載其後之事態發展云:
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殷)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别,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
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爲“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爲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
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温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内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别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
此事發生於所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之時,《通鑑》繫於建安二十年十一月張魯降操之後,而陳壽則載於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樊之前。蓋關中護軍趙儼奉曹操大營軍書,差調千二百兵前往新得之漢中助守,由平難將軍殷署督送之。中途兵變,事連作爲元帥的趙儼本營。儼遂以詐慰撫叛兵,待大營援兵至,再用脅喻方式盡徙之至大營。是則所謂“以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也者,既是任以維護軍中安全的督察職任,而同時也付予作爲元帥之統率權。建安中期以後,護軍常如督軍及監軍般領兵作戰,孫、劉集團皆然,良有以也。
由此可知,建安中期以降,護軍既已漸從軍隊之督察而兼帶統率之任,則原則上軍中地位較高的督軍及監軍當更如是矣,如此之變化,是由單純的軍隊監督制往大帥級監督制——魏晉都督制——的方向發展也。相對而言,“都督、護軍”無异是護軍級的都督,對於原爲野戰小職的“都督”之所以能升爲大帥,亦無异具有發展關鍵的意義,只是此時尚未定制耳。曹操後來置有護軍將軍及都護將軍諸職,如《三國志·夏侯淵傳》載,假節、行護軍將軍夏侯淵在漢中平後,曹操於建安二十一年再“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見《三國志》卷九,第272頁。是則夏侯淵之軍號不論是護軍或都護,皆有監統督護總監諸軍之意,其職庶幾近於“都督、護軍”。*按: 光武帝未即位時亦有“都護將軍”一例,即“以(賈)復爲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是也(《後漢書·賈復列傳》,卷一七,第665頁),顯示此官當時權位並不高。至於《漢書》亦一見“都護將軍”之句,但實爲甘延壽與陳湯發西域兵往襲郅支單于,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時,而應謂“天子哀閔單于弃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之詞(《漢書·陳湯傳》,卷七,第3011—3012頁),是則此答詞蓋謂天子使西域都護率軍來迎單于,非將軍之官名也。要之,都護有護軍之意,前文已論之。或許此時“都督、護軍”的簡稱即爲“都護”歟?按: 張郃、徐晃當時已有大將之姿,*《三國志·張郃傳》載郃於建安二十年從征漢中張魯,“督步卒五千”爲先鋒,魯降,操留淵與郃等屯駐,“郃别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淵尋戰死,諸軍“新失元帥”,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曹操遣使假郃節(卷一七,第525—526頁)。同卷《徐晃傳》載晃亦從征張魯,魯降,亦留屯駐,約在此前後爲假節、平寇將軍(卷一七,第528—529頁)。可見當時二將均有大將之姿。是則夏侯淵之以“行都護將軍”督此二將,固是水漲船高而爲大帥矣,所以尋即正拜爲征西將軍。*魏晉方面大將征、鎮、安、平諸將軍皆配以方位爲號,如駐防東方揚州的將軍,通常視其資歷而拜爲征(或鎮、安、平)東將軍,南、西、北亦如此類推。其詳可參小尾孟夫前揭書第一部之第一、二章,不贅。由此可信,當年趙儼之“都督、護軍”職銜,殆爲曹軍征討野戰軍軍制往大帥級别都督制發展之過渡,也是大帥以“都督”入銜的關鍵,*高敏前揭書特有一小段論述“都督護軍”,僅舉趙儼爲例,大意謂此職是針對大量私兵將領的存在而設,並謂此職可簡稱爲護軍,故趙儼後稱“關中護軍”云。按: 高敏蓋將“都督護軍”與“關中護軍”二職及其任務混而爲一矣,故竟謂趙儼除了統于禁等七軍之外,還可統韓遂等舊部,“儼然是都督關中諸軍事的職務”云云(第101—103頁)。鄙意對此説不敢苟同,此説既乏深入分析比較,又不從長時段軍制發展作考察,連于禁等不屯於關中亦略不查證,故難成立;然而,筆者並不否定“護軍”之權,也是“都督、護軍”所行使的職權之一。不待遲至建安二十二年夏侯惇之都督二十六軍也。
建安二十二年時,“都督”一名於曹軍征討野戰系統中,已成爲大帥之職銜,非僅作爲監護大員而已。其發展的真相及實際情況與曹操的戰後部署有關,兹略贅之。《三國志·夏侯惇傳》載云:
夏侯惇……太祖初起,惇常爲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爲司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自徐州還……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
可見夏侯惇由裨將而至爲校尉、將軍,由領太守而至領京尹,最後在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孫權,翌年操還,遂都督二十六軍留屯居巢。
不過,前言所引《晉》、《宋》二官志皆作建安二十一年“督二十六軍”;而《通鑑》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三月條則謂“操引軍還,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何者爲是?
按: 據《武帝紀》曹操建安二十一年五月進位魏王,十月遂征孫權。二十二年正月,曹軍在居巢,進逼濡須口,孫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是則一書出征之時,一書還師之時也。既謂軍還始任之,則應以二十二年爲確。另據《吴主權傳》,曹操攻至濡須口,因孫權請降並和親,故乃引軍還。然而,因孫權退走時仍留周泰統朱然、徐盛等部而爲濡須督,是以乃有曹操留夏侯惇等軍屯居巢之事。關於此時夏侯惇的職銜是用“都督”抑或“督”之名,似需分析曹仁等官職始能確定之。《三國志·曹仁傳》載云:
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通鑑》繫於建安十七、十八年)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荆州。侯音(《通鑑》繫於建安二十三年十月)以宛叛……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即拜征南將軍。
曹仁以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是此役征討野戰軍統帥之職名,而非戰鬥單位之督將。此爲曹軍征討野戰系統以“都督”爲統帥職名的始見,較夏侯惇之“都督二十六軍”更早,而較曹軍之軍區都督出現晚,統帥本官位階亦不算太高。其後曹仁又遷爲更高級的假節、行征南將軍,但是否仍“都督七軍”則不詳。本傳雖不載仁由樊從征孫權一事,不過此時位階更高、曾爲“都督”則是事實。至於《張遼傳》云:
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
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
是則曾以蕩寇將軍“督張郃、牛蓋等討(陳)蘭”有功、而被授予假節的張遼,此時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爲護軍薛悌所護。當建安十九年孫權來攻時,遵曹操教令出戰,有逍遥津之捷,使權無功而退,因而進拜征東將軍。也就是説,張遼因屯駐合肥而被護軍所護,不是可得有權策劃戰場戰役的諸將之一,戰後進拜爲假節、征東將軍,卻儼然已成爲方面大將,所以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復征孫權後“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據本傳所載,魏“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顯見張遼先後以征東將軍、前將軍之職一直屯於合肥,是此著名要塞之督軍,只是一度以假節、征東將軍隸屬夏侯惇而已。
又,曾側翼掩護張遼進攻陳蘭的威虜將軍、徐州刺史臧霸,於此役也“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見《三國志·臧霸傳》,卷一八,第538頁。
由是觀之,建安二十二年曹操退兵前,鑒於此地區原屯兵力太少,以致孫權來攻,因此遂增强假節、征東將軍張遼所部兵力,並留假節、行征南將軍曹仁、假節、揚威將軍、徐州刺史臧霸等部凡二十六軍屯於居巢。然而,夏侯惇於二十四年始拜前將軍,此時伏波之號未必高於征南、征東,河南尹亦未必强於徐州刺史,以故乾脆以漸大帥化之“都督”職銜,作爲二十六軍統帥的大號,俾夏侯惇能用爲統一指揮二十六軍以執行戰區防禦的任務也。*據《武帝紀》建安二十二年三月曹操留夏侯惇屯居巢,翌年秋即軍臨長安親征劉備,顯示曹操思有事於西,故留夏侯惇都督重兵駐防於東也。
據上所述,建安十七、八年間曹仁以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攻敵於前,二十二年夏侯惇以伏波將軍都督二十六軍駐防於後,此二將軍號皆爲雜號而非重號,故《宋書·百官志上》所謂“魏武帝爲相,始遣大將軍督軍”殆誤,但“都督”在野戰軍系統之中,至此已成大帥之職,既可執行攻勢的征討野戰,亦可執行守勢的戰區防禦,其事則確然也。由於此故,《通鑑》所謂“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實應標點爲“留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始爲正確。
又,前文謂漢中平定後,曹操以夏侯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當時張郃、徐晃已有大將之姿。稍後曹操拜淵爲征西將軍,淵卻於建安二十四年初被劉備攻殺。《三國志·張郃傳》謂“當是時,新失元帥……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諸將皆受郃節度。”而裴注引《魏略》曰:“淵雖爲都督,劉備憚郃而易淵。”不管劉備是怕張郃抑或是怕夏侯淵,要之《魏略》用“都督”二字以況大軍元帥或軍主,則“都督”一職於建安十八年至二十四年之間,殆已是征討野戰大軍統帥的位號矣。
由此可知,單從征討野戰系統“都督”此一職名而言,“都督”起於漢獻帝初期或靈、獻之間,始見於董卓軍中,初爲戰鬥單位的主官;其後在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前後,趙儼以“都督、護軍”護于禁等七軍時,“都督”一名於曹軍的征討野戰系統中已有大號化之傾向;降至建安十八年左右,曹仁以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破田銀等,“都督”一名即已成爲戰役統帥的職名。又降至曹操死前的建安二十二至二十四年之間,“都督”一名已可確定成爲征討大軍統帥之位號。至此,曹軍之中,以大號化之都督下督衆督軍,衆督軍下督衆督將,衆督將下督戰鬥兵的野戰體系已形成。亦即原爲董卓所草創的“大督—督將—戰兵”野戰軍新編制,已被曹操所擷取發揮,依“戰略—戰役—戰鬥”之軍事原理,因應戰争規模大小之需要,而建成“都督—督將—戰兵”或“都督—督軍—督將—戰兵”的新軍事體制,並漸從兩漢制向魏晉制演變。此演變漸漸而成,非成於一朝一夕。從遠因看,固非如《南齊書·百官志》所言,是源於東漢順帝時之御史中丞馮赦督揚、徐二州軍事;從近因看,亦非如《晉》、《宋》二官志所言般,明確成立於建安二十一年之夏侯惇督二十六軍也。
不特此也,隨着上述軍制的轉變過程中,同時另有一種演變也正在進行,即原本較常以督軍進攻爲主的東漢督軍制,同時也衍生出以區域防禦爲主的魏晉常都督制。約在建安二十年間,曹操親征韓遂、馬超後令趙儼以關中護軍督護韓、馬舊部諸軍,並令部分移防漢中;另外在二十二年,自己又親征孫權後,留夏侯惇都督大軍執行戰區防禦任務,由此均可看到此“攻勢→防禦”之戰略體制演變。此種監統軍隊執行防禦戰略的督軍制轉變,其發展尚頗有可述者。
上節述及監某州諸軍事及督某州諸軍事之魏晉常都督制,起碼在靈、獻間已見雛型,但僅止於見雛型而已。例如該節提及順帝建康元年(144),以御史中丞馮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討賊,助其討賊之滕撫,於翌年(冲帝永嘉元年,145)又以九江都尉助馮緄合州郡兵討賊,尋遷拜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就此例而論,馮緄的確是名符其實奉使督州郡兵之督軍使,而滕撫則先是以武將來助之,其後始遷督揚、徐二州事而爲督軍。據此而言,滕撫蓋亦是朝廷派遣的督軍使,二者之差别,似在於有否持節或是否武官而已,至於其執行督州軍以攻擊盜賊之任務則無大差别。觀此二人之例,固可視爲是東漢初以來奉使征討之督軍,但因先後連續督此區的時間不短,故也頗有州督(軍區督)的色彩,是以《南齊書·百官志》將馮緄定爲魏晉持節州都督制之始起,良有以也。其實持節督州郡兵討賊,馮緄之前已有其例,竊已敍述,只是魏晉州都督制之所以作爲常都督制,是因此督劃有固定之督區,並於督區内執行區域防禦任務時間頗久之故。上述兩督指定統督揚、徐州郡兵執行攻勢之作爲,是否僅執行兩年而事畢即撤,史載不詳,故筆者不敢遽謂是魏晉常都督制之始。要之,兩督既然先後來此區督軍討賊,則亂事及其善後時間恐不致太短,是以殆爲常都督制發展關鍵之一,是則不宜驟予否定。
及至山東討董兵起之時,大司馬、幽州牧劉虞與部下公孫瓚不睦相仇,獻帝初平四年(193),虞與瓚相攻。《後漢書·劉虞列傳》載云:
虞遂大敗……瓚追攻之……遂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司)〔青〕、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
按: 劉虞所“督六州事”僅見於此傳,不知是哪六州?揆其雖爲大司馬、幽州牧,但實力並非最强,在當時群雄各割地盤之情況下,似也不至於督六州之多。至於拜公孫瓚“假節督幽、并、青、冀”之事,亦僅見於此傳,恐怕一個劉虞手下之督軍,儘管拜爲前將軍,當時也不至於做到“假節督幽、并、青、冀”。《後漢書·劉虞列傳》書此事蓋誤也。反倒是《後漢書·公孫瓚列傳》另載劉虞從事鮮于輔等,於虞破亡之後,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而《三國志·公孫瓚傳》則謂:“鮮于輔將其衆奉王命。以輔爲建忠將軍,督幽州六郡。”*見《三國志·公孫瓚傳》,卷八,第247頁。是則《後漢書·劉虞列傳》所謂瓚“假節督幽、并、青、冀”也者,殆爲鮮于輔以建忠將軍“督幽州六郡”之誤也。然而幽州所部有十一郡、國,輔所督仍不悉是哪六郡。假如鮮于輔“督幽州六郡”的記載爲真,則此事發生於初平四年(193)以後,而鮮于輔僅是以將軍督一州中之若干郡而已;但無論如何卻是魏晉常都督制以及督軍僅督郡之最早明確記載。又稍降至建安二年(197),獻帝拜冀州牧袁紹爲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其後袁紹另以袁譚都督四州中之青州,而曹軍亦出現州都督之制,是則爲多州督與一州都督兩職的始見。由此可知,自漢獻帝以來,督軍或稱督或稱都督,有僅督郡者,有督一州者,有督多州者,軍區都督制已漸被推廣,只是尚未普遍爲定制而已。因此,若必執軍區常都督之始創而論,則非始於魏文帝的黄初二、三年(221—222)間,可以無疑。
前謂曹操承此發展趨勢,於東歸招兵五千人後,勉强可於軍中編置督將,事實上也如此做矣。及至初平三年(192),曹操領兗州,收得青州兵,實力始壯。又至迎天子都許,改元建安,實行挾天子以令諸侯。稍後於建安三年(198),曹操因吕布叛後的兗州尚未安集,遂以謀士尚書程昱爲“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參《三國志·程昱傳》,卷一四,第428頁。此爲曹軍置有州都督之始見。
按: 東中郎將爲漢末所置四中郎將之一,“皆帥師征伐”,*參《續漢書·百官志·光禄勛》羽林中郎將條注,見《後漢書》志卷二五,第3576頁。故理論上程昱以東中郎將都督兗州事,是要執行曹操所交付的征討任務;不過曹軍全軍掌握在喜好親征的兗州牧曹操手中,是以征討之事自不假手於州都督程昱。觀程昱需以此官領兗州屬郡之一的濟陰,始能管及兗州的部分政事,顯示曹操因欲親征四方而需委腹心以政軍重任,坐鎮根本之地,防止吕布之事重演,而卻又不放心授予一州之政軍全權也。是則素性猜忌的曹操,始置州都督之時,是僅以中級武官爲本官,使之兼領其中一屬郡,而統督該州一州的軍事,以防尾大不掉之事重演。總之,曹軍初置時的軍區都督比同時期的野戰都督位階高,則是不争之事實。
建安七年五月,官渡戰敗後的袁紹病死,諸子内鬥。曹操乘機伐之,九年七月拔鄴,操遂自領冀州牧,稍後並欲親征冀、幽二州其餘之地時,乃任荀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是爲曹操第三個見於史傳的軍區都督。荀衍一度曾破獲紹甥并州刺史高幹襲鄴之陰謀,*荀衍爲荀彧之兄,事詳《三國志·荀彧傳》,卷十,第315—316頁。可見其以監軍之職爲軍區都督,又不領郡,任務確是爲了防守。
荀衍“都督河北事”,既爲曹操第三個見於史傳的軍區都督,而第二個即爲鍾繇。繇於官渡之戰前,以官職更重要且與曹操近密度更大的侍中、尚書僕射之職出督關中諸軍,《三國志·鍾繇傳》載此事云:
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争。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
是則鍾繇以守司隸校尉掌關中之政並持節督關中諸軍,可得便宜行事,全權兼管政軍。觀鍾繇之以本官持節督,與中郎將程昱、校尉荀衍之無節都督相較,則固已是方面大員矣,於是同傳所載下述事件遂可得而理解。
同傳謂官渡之戰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袁紹甥并州刺史高幹等並爲寇,繇率諸將討破之。所謂衛固作亂,《魏略》謂是詔徵河東太守王邑而换杜畿爲太守。王邑心不願徵,吏民亦戀邑,於是郡掾衞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留邑。鍾繇鑒於杜畿已入界,不聽,促令王邑交符;然而王邑卻佩印綬,逕從河北詣許自歸,不理會鍾繇之促令。因此,鍾繇遂“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其文云:*自劾文請詳《三國志·鍾繇傳》注引《魏略》,卷一三,第393頁。
臣前上言: ……謹案文書,臣以空虚,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衞固誑迫吏民……漸失其禮,不虔王命。……咎皆由繇威刑不攝。臣……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至乃使邑遠詣闕廷。隳忝使命,挫傷爪牙。……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爲。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爲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免冠徒跣,伏須罪誅。
按: 鍾繇自署其銜爲“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不提“持節督關中諸軍”,是則後者是職不是官,當時可以不入銜。不過,自劾書中之所謂“近侍”是指侍中也,“機衡”殆指尚書僕射,至於“總統偏方”則應指以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而言,以故自謂爲“大臣”。如此觀之,“持節、督關中諸軍”即是繇所言之“督使”;既是“銜命督使”,故是身負“使命”;既銜命以督使處理事務,是以稱其機構爲“督司”;*《三國志·劉廙傳》注引《廙别傳》載廙表論治道曰:“……亂弊之後,百姓凋盡……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卷二一,第616頁)按: 劉廙卒於魏黄初二年,所著書數十篇均應在建安之時,可見督司不論本官高下已是重任。又,《三國志》或注引諸書載漢末以來有督軍從事、都督從事之類職稱,蓋是督司之僚屬歟?因史料既少而又失詳,兹不贅論。“督司”依法而立,是以東漢擁節督軍應有“督司之法”以爲組織及施行的依據,只是裴松之批評陳壽失之簡略,而自己亦注疏不全,以致世知魏晉有都督之制而漢代“督司之法”則闕如也。
文中鍾繇自謂“威刑闇弱……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爲”,蓋因河東乃司隸部屬郡,而太守王邑竟不理會鍾繇的督促交符,逕佩印綬而去,且吏民亦“各詣繇求乞邑”,致令作爲直屬上級行政長官的鍾繇感覺不能威制屬郡官民,以故自認非大臣當所宜爲。至於所謂“威禁失督司之法”,蓋指河東吏民“作亂”,且連及袁紹外甥并州刺史高幹,雖已爲繇督率諸將所破,但繇本人既身爲督司,“隳忝使命,挫傷爪牙”,失鎮懾威禁之效如此,確爲兹事體大。
此次“作亂”事件中,史謂杜畿入爲太守後,爲安撫郡掾衞固及中郎將范先,乃“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此措置是令范先爲實際領兵之督軍,而以衞固在名義上爲之都督。都督兵權分化被奪,故其後遂被杜畿輕易所殺。*詳《三國志·杜畿傳》,卷一六,第495頁。將衞固與“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的程昱,以及“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的荀衍相比,三人雖同稱爲都督,但衞固屬於野戰系統之郡級都督,位於太守之下,身分與太守如同君臣;*建安前期郡有郡督軍、郡都督,乃至大都督編制,地位殆在太守之下,前引董卓、吕布、孫策軍中已見其例。諸職之身份與太守甚至有如同君臣者,如《三國志·高堂隆傳》載隆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争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曰:‘……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見卷二五,第708頁。而程昱卻是軍區系統之州都督,荀衍則是同系統之地區都督,二人殆爲區域戰略級的都督,固非野戰小職之郡級都督可比。或許建安前期,曹操對重要地區視需要而置都督等督將,其級别則各有等差歟?
情勢吃緊的地區除了鍾繇持節所督之關中外,其後新平的漢中情勢亦然。蓋韓遂、馬超失敗後,降曹舊部正被關中護軍趙儼所整編監統,情勢已較爲穩定;但是降至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張魯,巴、漢皆降後,劉備亦於同年襲取益州,並進據巴中,情勢自是吃緊。於是,曹操乃遣平狄將軍張郃擊備,翌月自還,留行都護將軍夏侯淵屯漢中與之相峙;然至二十四年正月夏侯淵爲備所殺,曹操遂再自長安出臨漢中,而劉備則於陽平因險拒守。相峙間東方發生關羽北攻曹仁之事,曹操乃於五月引軍還長安。據此,漢中攻防戰此時尚未情勢判然,以故曹操遂置督以處理戰地政務。《三國志·杜襲傳》載云:
後(侍中杜)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劉備所没,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時已遷蕩寇將軍)、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爲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遂以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
是則杜襲以“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是建安二十年曹操降張魯而還之後事。此時曹操已令趙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頗有成效;然此後漢中情勢更爲嚴峻,故不得不令趙儼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禦。二人一護關中,一督漢中,論官職履歷,趙儼略低於杜襲,論與丞相關係之近密度,則儼亦與襲有一段差距,因此曹操纔委杜襲爲軍隊監護系統中位階較高、事權較重的督軍,而趙儼則僅爲護軍而已。二人均是從霸府僚屬轉任,以故皆未擁節。甚至其後,曹操委襲以丞相府留府長史,則駐留長安的杜襲,權位更是在趙儼之上矣。
由此可知,自建安初曹操挾天子而令諸侯後,已頗有任命將領或牧守爲州都督之例;但任之者除非另命以領州或領郡,否則其任務殆純以執行區域性戰略防禦爲主,且愈後愈多假之以節,俾其事權加重。至於當此同時,袁紹授袁譚爲青州都督而未使之領刺史,其措置蓋與曹操正同。就此而言,曹操對此軍區新制不僅有推廣之功,抑且也不自拘於例,而運用相當靈活,因此始有“都督、護軍”此類護軍級都督職名的産生。
至此,似乎可以根據群臣對嗣魏王曹丕勸進表——即後來刻石的《上尊號碑》——之署銜,一究都督制在此重要時程所現出的問題,而此了解則需先從曹操死前之情勢展開觀察。
據《武帝紀》并裴注,記載曹操死前内外情勢,謂建安二十二年底劉備遣張飛等進屯下辯;曹操遣曹洪拒之。二十三年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典兵督許中事”之丞相長史王必營,爲王必與典農中郎將嚴匡所討斬。史謂彼等之所以反,是因覩漢祚將移而發憤,計劃殺必後挾天子以攻魏,並南連劉備。此事平定纔大半年,同年七月,曹操西征劉備,十月宛守將侯音等趁機反。曹操使曹仁圍宛,翌年正月屠宛斬音。史謂此反與南陽間苦繇役之事有關,反衆亦與關羽連和。由於劉備因險拒守,所以曹軍無功,又需急還師以救樊襄,幸好還至洛陽時徐晃已破關羽而解圍。關羽尋被孫權所襲殺,於翌年——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其首傳至洛陽。此兩年多一點的時間,曹操内憂外患並發,東西疲於奔命,亦於同月身死於洛陽。遺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遺令“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是曹操臨死仍恐身後再生兵變,以及外患乘機來攻,使局面無以收拾也。事實上當其身死之時,長子次子均不在旁,情勢也的確緊張,如《三國志·賈逵傳》注引《魏略》曰:
時太子在鄴,鄢陵侯(即次子曹彰)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群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逵建議爲不可祕,乃發哀,令内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敍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逵以爲“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
老王身死,嗣王未立,群龍無首,而軍民騷動,青州軍竟擅擊鼓相引去,可謂已進入緊急狀態。偏偏當其“時,(次子)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賈)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宫還鄴。*參《三國志·賈逵傳》並注引《魏略》,卷一五,第481頁。因此,魏王太子曹丕之所以於同一年中,年初急於嗣王位,年尾則急於踐帝祚,群臣也迅速且頻頻交章勸進,良有以也。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魏王丕延康元年、魏文帝丕黄初元年,220)正月曹操死,曹丕嗣魏王位後,群臣聯署上表,請丕踐祚稱尊,事後刻而爲石,此即《上尊號碑》。*《上尊號碑》見王昶《金石萃篇·魏一》,收入嚴耕望先生所編之《石刻史料叢書》甲編之六第十三册(臺北: 藝文書局)。該碑文亦見於《三國志·文帝紀》延康元年十月魏王丕即祚改元黄初時之裴注,但僅列三公之名。群臣所署銜,尤其是署“行都督、督軍”銜者,*前揭拙著《從督軍制、都督制的發展論西魏北周之統帥權》一文,將“行都督督軍”一銜標點爲“行都督、督軍”,蓋此銜是由都督及督軍兩種軍職合成故也;但若問標點爲“行都督督軍”是否可行,則需待更多證據始能確定。因出現於局勢緊急之時,故可用以印證魏晉常都督制完成前夕的過渡情況。
該表由魏相國華歆等三公領銜,其次由諸大將署名,其次是匈奴南單于及九卿,再次爲督軍御史及中領軍、中護軍以下諸禁衛將校,最後則是諸雜號將軍。按: 碑中署“督軍御史、將作大匠、千秋亭侯臣照”即董昭,其所督之軍殆爲中領軍以下諸禁衛軍,與野戰軍無涉;至於最後諸雜號將軍,皆非都督大將,故此處從略,不用作分析比較。
今將排名在督軍御史董昭以前之諸大將及其所署銜開列如下:*因該碑是事後所刻,且殘缺,以致所書名或銜頗有失誤,跋尾對之有所考證,筆者亦曾據之予以再考,可參前揭拙著《從督軍制、都督制的發展論西魏北周之統帥權》。括號内之字爲跋尾所考或筆者所補。
使持節、行都督、督軍、車騎將軍、陳侯臣(曹)仁
輔國將軍、清苑鄉侯臣(劉)若
虎牙將軍、南昌亭侯臣(鮮于)輔
輕車將軍、都亭侯臣(王)忠
冠軍將軍、好畤鄉侯臣(楊)秋
渡遼將軍、都亭侯臣(閻)柔
衛將軍、國明亭侯臣(曹)洪
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本傳作鎮)西將軍、東鄉侯臣(曹)真
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揚州刺史、征東將軍、安陽鄉侯臣(曹)休
使持節、行都督、督軍、征南將軍、平陵亭侯臣(夏侯)尚
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青州刺史、鎮東將軍、武安鄉侯臣(臧)霸
使持節、左將軍、中(本傳作都)鄉侯臣(張)郃
使持節、右將軍、建(本傳作逯)鄉侯臣(徐)晃
使持節、前將軍、都鄉侯臣(張)遼
使持節、後將軍、華鄉侯(本傳作鄃侯)臣(朱)靈
碑刻大抵是根據諸將於曹丕即王位後,甚至是踐祚稱帝後之官銜而刻,因是後刻之文,故與《三國志》相關諸傳之載述遂頗有出入,如諸傳載述漢亡前擁節統兵諸將,殆因不是天子使者而皆授以較低等級的“假節”,幾無“使持節”者,即是其顯例;*吴蜀此時若俾統兵諸將以擁節,則亦皆以“假節”授之,“持節”或“使持節”極爲罕見。又陳壽將“行都督、督軍”之銜一律稱以“都督”,恐是以其當時定制行用之“都督”銜取代之也。復者,自輔國將軍劉若以至渡遼將軍閻柔均是雜號將軍,既非大將也非都督;曹洪雖於曹操生前當過都護將軍,但與曹丕關係甚爲不佳,以故本傳僅謂“文帝即位,爲衞將軍,遷驃騎將軍”,情況均無必要進行分析者,故皆不論。再者,左、右、前、後將軍張郃等,此時固是大將可以無疑,然皆無都督之職,宜待以後再析。
兹據各本傳所載,張郃、徐晃、張遼、朱靈等將,早就應能當都督大帥,或許他們因爲是遺令所禁止的“不得離屯部”之“將兵屯戍”主帥,早已被派出之督軍或護軍所督護,以故不能同時兼爲“都督、督軍”耶?也就是説,當時似有一種不成文規定: 除非情況特殊或是親貴大將,否則既任主帥則不兼監督,既當監督則不兼主帥。若任爲主帥而兼監督,則固是非常之任也。
至此,蓋可進而考慮“行都督、督軍”一職,究竟是否非常之任,果爲何官職矣?
按: 不論職稱爲“行都督督軍”抑或爲“行都督、督軍”,依前述漢末軍事體制的變化,都督於曹軍野戰系統中已漸成統兵大帥之職,而於軍區系統中亦漸成統率一州或一區之主帥職;督軍則仍如東漢以來之慣例,是監督並頗兼指揮軍隊之首長職。是則此二職相兼,理論上當是對所屬諸軍或所管軍區,握有統率監督、全權指揮之統帥職,也就是實質的督軍級都督,遠非當日之野戰小職可比。由於群臣未奉曹操梓宫還鄴之前軍情已相當嚴峻,是則中央諸軍固需親貴重將統領,而四方戰略要地亦必思擇良將以分憂勞。觀授予“行都督、督軍”之五人,三曹一夏侯皆爲曹丕最親重的將領,或許此四將均是以“行都督、督軍”之職,分别統率監督各分地之諸軍,俾收軍令統一以及鎮懾良效。只是其中之一的曹休當時已明確確定兼領揚州刺史,目的蓋在防吴,而其餘二曹一夏侯則在署銜時尚未明確派定任務區而已。至於另一正除青州刺史之臧霸,顯然是爲了針對不受禁止而“擅擊鼓相引去”的青州軍,蓋可無疑。*據《三國志·臧霸傳》,霸本吕布將,布敗亡後歸操。操一直委之以青、徐二州,因功遷徐州刺史。後從曹操征孫權,拜揚威將軍,假節;操軍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此次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應與之無關,而曹丕則是欲借重其經略青、徐二州甚久之聲名,故由刺徐州改刺青州,蓋用以鎮撫青州軍也,是以本傳直稱其爲“都督青州諸軍事”。由於曹操生前,南面的荆州軍事本就由曹仁負責,西面的關中則曹洪此時恐仍留駐,是則曹魏最重要的揚、荆、雍三邊已概略無虞,然内部嚴峻卻尚未全消,是以曹丕遂快速篡漢,促使生米已煮爲熟飯之局面形成。復因此措置是緊急時期之臨時緊急處分,故采先前“行征南將軍”、“行都護將軍”等慣例,於“都督督軍”之前冠以“行”字,用以表示並非正常除拜之職稱,而是臨時緊急權行者也。據此可知,不論其銜是“行都督、督軍”抑或“行都督督軍”,皆實爲臨時統帥而兼監軍之職,確是非常之任。
然則統監大軍的統帥,爲何以“都督、督軍”爲名,有何作用與意義?
按: 兩漢以來僅有將軍麾下設置護軍,前論赤壁之戰前,趙儼徙“都督、護軍”,護張遼、張郃等七軍,無异即是此七軍的總監。“都督、督軍”亦同此理。蓋“都督”之職,在獻帝早期本爲基層戰鬥單位之軍職,袁紹、曹操使之變爲統率一州或一區諸軍之中高級軍職,至建安末曹操更使之大帥化,權位已步步提升矣。至於“督軍”,東漢以來本爲狹義之監軍職,軍中地位較“監軍”低、較“護軍”高,但任命則較“監軍”更爲常見。因此,以常見之“督軍”與新近大帥化之“都督”相兼任,無异即爲督軍級都督,更能令人顧名思義,知帶此職銜者亦是諸軍之統帥兼總監,較“都督、護軍”權位明顯更高,使其對諸軍的控制支配力大大增强也。由此可知,由“都督、護軍”而變爲“都督、督軍”,是因不同之人,不同位階之人,於不同之非常情勢,而權宜設置之軍職。至於“都督、督軍”自魏文帝踐祚後不久之所以消失不見也者,蓋是被擁節統率監督而已完全大帥化的“都督”一名所直接取代故也。“都督”職稱及權力於此漢魏篡代之際逕行取代臨時的“都督、督軍”,實爲魏晉都督制轉型的重要關鍵所在,可以無疑。此名自後可以用作征討野戰體系之統帥職稱,也可以用作軍區防禦體系之統帥職稱,甚至仍可用作基層單位軍事主管之職稱,靈活方便,終成一代大制。於是,擁節都督、擁節監以及擁節督的魏晉三等都督制,最晚遲至魏文帝黄初二年漸告形成。至於擁節之等級——使持節、持節、假節——只是代表授予不同程度之軍事專殺權,加重大帥對軍中以及管内官吏軍民之指揮監督威權,俾使其執行相關事務更順利有效而已;此三級擁節劃分法,亦無异已將兩漢以來的軍隊監督權,吸收入了魏晉三等都督制之中。
試據各本傳考察上述五員“行都督、督軍”在黄初初稍後的後續發展,以觀察其變爲都督制的某些變化。
曹仁於曹丕“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而《上尊號碑》卻未提及此銜,蓋是署於未正拜之時也。按: 上述五員“行都督、督軍”中以曹仁資歷最高,以故大概於署名後,尋即出爲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總督前綫三方之任。雖然因劉備已據有益州,故其都督益州是遥領之虚銜,但是“行都督、督軍”此時已被“都督”之銜所取代則爲真。另據《文帝紀》,由於黄初二年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故翌月遂遷車騎將軍曹仁爲大將軍,最後仁於四年三月薨於大司馬任上。據此可推,“行都督、督軍”因是權宜所任,故稱爲“行”,並可能於黄初二年左右完全爲“都督”銜所取代。
原官中堅將軍的曹真,在夏侯淵戰殁後,曹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真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録前後功,進封東鄉侯……黄初三年還京都”。是則曹真先在曹丕即王位後爲鎮西將軍,行都督督軍,稍後始確定爲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此事不晚至黄初三年,蓋在黄初二年間發生。其“行都督、督軍”之銜亦同時被“都督”所取代。
夏侯尚本傳載其原官魏國黄門侍郎,“太祖崩於洛陽,尚持節奉梓宫還鄴。并録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荆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黄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是則其遷征南將軍領荆州,假節、都督,爲曹丕踐阼稱帝之後、黄初三年以前所發生,其“行都督、督軍”之職亦被“都督”所取代。
曹休在曹操拔漢中還長安後拜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爲領軍將軍,録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按: 夏侯惇督軍於外,至延康(即黄初)元年三月晉爲大將軍,同年四月庚午薨。是則曹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應在魏王丕延康元年四月以後、魏文帝黄初三年十月以前,其“行都督、督軍”亦被“都督諸軍事”所取代。
臧霸本傳更直謂“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是則其任青州都督之事,竟是延康元年之事矣。
碑文與史傳相差若此,真相已不可完全確考。總之,五員大將之任“行都督、督軍”均是魏王曹丕延康(即黄初)元年時之緊急權宜職,是年或最遲至黄初三年已正名爲“都督”,卸下了“督軍”之兼職,而其中有領州或不領州者,要之都督皆非由州牧刺史以本官所充任。蓋軍事緊急之際,起用武官以本官任之實較文官爲宜也。若僅就此事而言,《宋書·百官志》所謂“魏文帝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之説,殆較《晉書·職官志》所載之黄初三年爲正確;然而,由於曹休與臧霸均有可能在延康(即黄初)元年已從“行都督、督軍”改爲“都督”,以故《宋書·百官志》所載仍可有保留之餘地。若换一角度純從軍區都督制本身之發展而論,則漢獻帝初時已出現僅督郡之軍區都督,稍後又出現多州督以及一州都督,曹操因勢利導推而廣之,並漸漸授都督以假節,是則常都督之制固非始創於黄初二、三年之間也。由是言之,則《晉》、《宋》、《齊》三書皆誤矣。
六、 結 論
軍隊自來是一個封閉的團體,所謂“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一切聽令於主帥。秦漢時期將軍之作爲主帥,對軍隊行使統率權,平時典屯衛,戰時掌征討,位高權重,人君豈能放心,由是遂有軍隊監督制度之産生,以故可以説秦漢監軍制是專爲將軍制而設的制度。
軍隊監督制度既施於監督平時駐軍,更施於監督戰時之征討——包括出師征伐與州郡討捕。只因平時駐軍相對較静態,以故監督者活動記載較少,相對而言,戰時征討常事關社會安定乃至國家安全,皆爲當時重要而著目之事,是以監督者之活動記載遂多。因此,論述軍隊監督制度之淵源以及早期發展,主要是靠後者的相關載述。
軍隊監督制度蓋有兩種: 監軍(含督軍,下同)制與護軍制。兩者俱爲魏晉都督制之淵源,且均出現甚早。“監軍”是先秦之職,是典型的或是狹義的監督制,與其性質功能相當之“督軍”則起於西漢;而“護軍”則是秦官,本掌軍隊督察,爲廣義的監督制。或許可以説,魏晉都督制之制度主源在前者,後者是支源,但兩者俱是魏晉都督制形成之遠因,近因則與“都督”一職在東漢末出現以及其職權變化有關。“都督”一職出現時職掌戰鬥,是野戰系統戰鬥單位之指揮官,本與監督系統無關;至於其所以與軍隊監督制度有關,則是與監軍制在建安年間互爲結合之結果。兹分别總結此諸官職的發展,略述之如下:
大體而論,護軍制之護軍,是協助軍事機關長官或征討軍統帥監視督察所屬軍隊、以保護軍中安全的督察長,秦漢之間正式官名爲護軍都尉。及至漢武帝時其官移屬最高軍事機關大司馬府後,兼典軍事檢察權,與丞相府佐丞相舉不法之屬官司直,一武一文分掌監視督察文武百官,職任相當重要,而於平帝朝直接定名爲護軍。護軍因是外朝官,所以不擁節,在軍中權位遜於連統帥也在監察之列的監軍使;但若派護外國及蠻夷則例外,此時其“持節護”之銜即與監軍使類同。東漢以降省罷護軍之官,然於軍隊出征時仍常在將軍幕府之内編置其職,甚至會有中、左、右等護軍分化的職名,而隨征討事竟而罷。
護軍對軍隊如此重要,以故漢末魏初戰亂頻繁之時,漸漸恢復護軍作爲武官,必要時且領兵作戰。降至建安中後期,曹操又不時編置“都督、護軍”、護軍將軍以及都護將軍等官職,使之朝總監化以及大帥化的方向發展,但是終未完全并入都督制。及至魏晉以降,中護軍(資深者稱護軍將軍)乃成爲中央禁衛軍第二號監統主帥,*視作戰序列編制的需要,護軍在東漢有前後左右中之分,而中護軍於戰時通常直隸統帥以作爲中軍之護軍。曹操經常親征,自官渡之戰後實際上就是漢朝的最高統帥,及至封爲魏公而建魏國,乃置中護軍作爲魏國禁衛軍之主帥。此禁衛軍之中護軍與野戰軍之中護軍系統不同,而晉制承魏仍爲禁衛軍主帥。筆者此説因漢末三國史料零散,不易完整參見,或可參蜀漢之制以爲旁證。按: 劉備也常親征,死前於永安以李嚴爲“中都護,統内外軍事”,權位僅次於諸葛亮。備死之後,諸葛亮以丞相爲最高統帥亦略如曹操,其北伐時即置有前後左右中護軍,具體部署之例見《三國志》卷四《李嚴傳》並注引《諸葛亮與平子豐教》,不贅。並主武官選。
至於監軍,首宜注意的是,握有廣義監軍權之護軍,與握有狹義監軍權之監軍,最明顯的差别在: 監軍是奉使赴軍以掌監察之差遣職,頗常用内朝官,在軍不屬於主帥,反而主帥也在其監察之列;而護軍則爲軍中編制的督察官,屬於外朝官,配隸於主帥帳下。另外,監軍及其較後起的督軍,可得有授予擁節——兩漢天子之使者通常是持節,漢末曹操對其屬下武將之督軍者則通常授以假節——之特權;而護軍則通常無此特權。
其次,監軍自春秋後期已見設置,督軍則起於西漢,二者皆常以具體之監或督某州郡兵,或者監或督某將軍軍爲稱。監或督某州郡兵者之任務常是爲了討捕盜賊,多以文臣充任,而監或督某將軍軍之任務則是爲了征伐致討,故兼用武官。由於兩者不是官而是使職,以故並不入銜,且幾乎可以差遣任何中級以上官吏充任之,所以軍隊監督者位階常在被監督者之下,此與漢制派遣六百石刺史監二千石郡太守的原理相同。充任監督者有時在職任上加上本官官名以爲稱,如監軍御史、督軍御史、督軍校尉等,此類例子以東漢較常見。二職在兩漢時,或書持節或不書,殆非史官漏記或省文,而是當時確有不持節之事例,尤以外朝官充任時較常見。
建安中曹操表留荀彧爲其監軍時,謂“古之遣將,上設監督之重”,其説蓋是實情。從本文所舉諸例,可以看到監軍或督軍位階即使較作爲主帥之將軍刺守爲低,但是對其所監臨之對象,則幾乎皆有以上臨下的權勢。退而言之,此二職之位階不管在軍是否與統帥平等,要之統帥似乎極難對其發令——建安間非常時期實際掌握兵權之軍閥除外,頂多是一者掌統率,一者掌監督而已,謂是分享統帥權也不爲過。蓋統帥權是統帥對所部實行統率指揮監督管制之權,若旁置平行或幾乎平行的監軍系統,分行監督管制之事,即是將統帥權分裂也。由此也可以知道,爲何將軍制必須轉型爲都督制,始克使統帥能應付長期分裂戰亂之局矣。
“監督之重”既然設在將軍之上,對將軍刺守擁有以上臨下之權勢,其軍制轉變的重要關鍵時段殆在東漢中期以至建安年間,至建安後期轉變得更爲劇烈明顯。此蓋基於戰争頻繁、戰事拖延,遂使監軍與督軍既握有監軍權而又漸漸干預統率權的事態得以發展,以致令爲政者必須思考是否應將二權合而爲一。其演變結果乃是讓監督系統之監軍、督軍實際兼掌統率權,反之亦提高野戰系統都督之指揮職權而使之切實兼掌監軍權,兩系互爲結合,以利轉變爲新型統帥制度——都督制,冀能收到諸軍統一指揮監督管制之效。爲了促使新統帥之等級權責清楚分明,使此新制能切實産生所期望的效果,魏晉朝廷於是將晚近已大帥化的都督列爲統帥之最高等級,原來監軍在督軍之上的慣例則予以保留,遂乃建成《晉》、《宋》二官志所敍之“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的三等統帥職;復又爲了讓其能有充分執行統一指揮監督管制的能力,於是建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的三級軍事專殺權,以便統帥用以合法對付早已被其監臨的文武官吏。至於秦漢原來作爲統帥的將軍職權,既已漸爲都督等職所取代,於是將軍號遂逐漸退爲階官,而將軍領營兵制乃漸變爲都督領府兵制,並下開魏周隋唐新府兵制之先河。*秦漢將軍領營兵,著者如渡遼營,小者如本文提到之陷陣營等,均是其例。及至漢末以至魏晉,因戰事頻繁而將軍變多,將軍府所領之兵即以其軍號爲名,號曰某某府兵(參唐長孺先生《魏晉府兵制度辯疑》,收入其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 三聯出版社,1955年)。其實某某府兵不過只是隨府主軍號之更易而改變的營兵轉稱罷了,但在軍制上卻代表了一定的轉型意義。其後經北魏六鎮之亂而喪亂益甚,西魏北周改革軍制,以各級將軍充任各種都督以實際統領府兵,或謂是特殊之兵制(陳寅恪先生所論,已衆所周知,不贅)。此制後至隋朝唐初雖一再予以修改,但府兵最基層之三級軍官到最後仍以都督——即大都督、帥都督與都督——爲稱,情況猶如漢末都督制初起時之重演,然仍不失爲都督領府兵之遺意。除了前揭拙文外,筆者尚有若干論文論及此發展,如《從政局與戰略論唐初十二軍之興廢》(《中國中古史研究》2,2003年)、《試論唐初十二軍之建軍構想及其與十二衛的關係》(《中國中古史研究》10,2010年)、《試論西魏大統軍制的胡漢淵源》(《中國中古史研究》12,2015年)等,讀者請自便參考。
魏晉都督制之主、支源流既如上述,是則竊以爲不論監軍也好督軍也好,不論監督征伐將軍也好抑或監督州郡討捕也好,皆可認爲是魏晉都督制中征討都督——筆者歸之爲都督制甲型——之淵源,即“擁節+都督(或大都督)征討諸軍事+本官→出征”之濫觴,而爲乙型——“擁節+都督(或監或督)某州諸軍事+本官+領州郡→駐防”——之所從出。由於甲型的特點在無專屬固定之管治區,也常不領州郡,因此儘管起源得早,發展得久,但數百年間仍不能轉變爲乙型的軍區都督。其原因是: 要轉變爲乙型軍區都督,充分條件是要因應戰争與國防的需要,長期駐防並有固定防區,而不能戰事過後即予撤消。太平時期姑無論矣,即使東漢光武經“中興”戰争後,因立刻進入求治的時代,故也不能提供如此局面與條件,俾能發展出乙型都督制;而漢末則不然,是經歷大喪亂後復又面臨長期分裂戰争,正好爲乙型都督制之發展提供了温床,故能使其得以長足的發展。
至於乙型軍區都督制發展的關鍵契機,可謂造端於靈帝之遣出劉焉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使監軍權與地方行政權得以合一,俾主事者能全權監領地方政軍,具有軍事割據史的重要意義。稍後至獻帝初,建忠將軍鮮于輔督幽州六郡,則是作爲統兵主帥之將軍督州郡之始。及至建安二年獻帝遣使拜冀州牧袁紹爲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以朝命使其統合地方行政權、軍隊統率權以及監軍權於一,無异正式承認其割據,更爲軍區都督制以及軍事割據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化。喪亂之下,由軍制突變開始以至整個統治體制快速瓦解,遂使具有地方割據意義之乙型都督制得以迅速完成其基本形式。
當此之時,已挾天子而令諸侯的曹操,乘勢將此用於征討野戰的新軍制,改變爲區域防禦的戰略體制,以實行長期地方占領,因此天下三分漸有其二,使甲、乙兩型都督制亦隨此發展而獲得試驗、推廣與施行之良機。是則雖然曹操行之不久即死,生前尚未建立都督三等、授節三級之制,更來不及使之及身完備;不過若微曹操之如此運用並推廣,則其後尚安有所謂魏晉都督制哉。
於此必須再予强調的是,“都督”一職始見於靈、獻之際,初爲野戰系統指揮戰鬥之小職,董卓似是創始人,而山東群雄後亦多置此職。及至建安初期袁紹坐大,都督不論在野戰系統或軍區系統,位階皆提高至中階職級,依“戰略—戰役—戰鬥”原理編建的“主帥—都督—督將”新軍事體系乃告出現,曹軍更將之沿用而變化。降至建安中後期,曹操命太守趙儼爲“都督、護軍”以護于禁等七軍,命曹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田銀,命伏波將軍夏侯惇“都督”二十六軍屯居巢,而曹丕於甫即王位後尋即任命重號車騎將軍曹仁等爲“行都督、督軍”,在在顯示出都督一職在曹軍軍事體系中事權位階已漸次提升加重,終成執行征討攻勢以及區域防禦——即日後甲、乙兩型都督制——之大軍統帥位號。對此發展,《晉》、《宋》官志所述付諸闕如,而所言曹操“始遣大將軍督軍”以及“夏侯惇督二十六軍”亦有所訛誤也。
再者,趙儼之“都督、護軍”與曹仁等將之“行都督、督軍”,任命方式如出一轍,均具有臨時緊急任命的性質,不僅可清楚表示此職是結合統率權與監軍權而成的職稱,抑且可用以作爲證明原本單純負責野戰的都督,經護軍級都督—督軍級都督之發展過程,憑何制度性關鍵,轉變爲握有統兵全權的大帥也。“都督、護軍”一職事竟即撤,而“行都督、督軍”則約在黄初元年至黄初三年之間——尤以曹丕稱帝、劉備征吴而魏局略穩之黄初二年最爲可能——逕由“都督”之職稱所取代。執此而論,《宋書·百官志》所言“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差是;只是其觀察此制的變化發展時段不够長,又未明辨征討都督與軍區都督的差别而雜述之,復未解釋都督制三級授節等等問題,頗爲可惜而已。
總之,先秦秦漢軍隊監督系統係因將軍領兵作戰之制度而産生,而魏晉都督制則是承其變化發展而形成之新體制。都督制若從源起而論,其遠因蓋濫觴於先秦以來軍隊監督系統監軍制的設置與發展,近因則與東漢末作戰系統新出現的都督職權變化有關,最後是兩系統在漢、魏之間相結合,致成統、監合一的都督新體制,但統帥之職權尚未嚴格分爲都督、監、督三等,授節也未分成使持節、持節、假節三級。至於軍區都督,則在發展最後階段由非常制的征討都督分衍而出,成爲魏晉南北朝普遍施行之常都督制。因此可以説,甲型的非常都督制淵源長遠而多元,而乙型的常都督制則要遲至靈、獻之際始分衍萌起,漢丞相曹操推而廣之,魏文帝曹丕承而用之,故嚴格而言,魏晉常都督制既非起於漢順帝之時,也非始於魏文帝之黄初二年。發展過程自萌起至定制,其間曹操對此制之推廣施行貢獻極大,常都督制可謂創於其手,至於魏文帝而沿用變化之,及至西晉乃成定制,沿革相因相仍,錯綜複雜,然若深入研究,則雖百世而猶可被知也。
——兼论北周府兵军职都督的勋官化问题
——《影》的标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