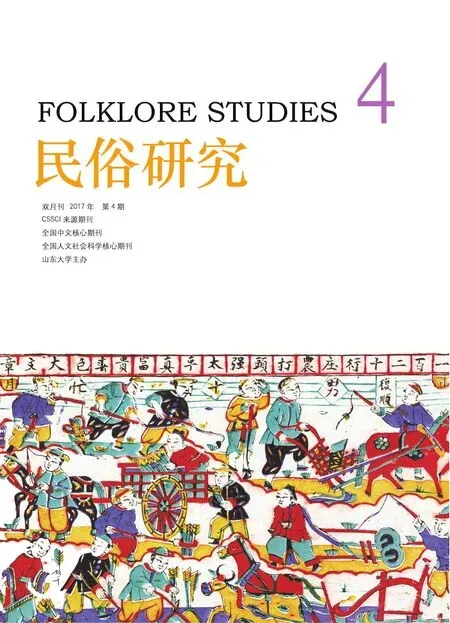物质关系和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
孟凡行
物质关系和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
孟凡行
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或强调物质文化的本体形态、结构和功能,或强调物质文化背后的“语法规则”,或强调物质文化的传承……各有自己的学科追求和研究旨趣,各自展开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发展出了以马塞尔·莫斯为代表的“总体呈现”理论,民俗学发展出了以迈克尔·欧文·琼斯为代表的“物质行为”理论。前者强调物的社会性,后者强调物的文化性、传承性和对人的关注。“物质关系”借鉴两理论的优长,视物为人类实践的中心环节,并将其置于由自然生态、物、人、社会所构成的有机系统中讨论,以此展开人和文化的整体研究。而“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则是在“物质关系”理念下,提出的作为物或物学研究之基础——物质文化民族(俗)志考察和撰写的基本框架。
物、物质文化、物质行为、物质关系、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物学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一件器物,比如一架曲辕犁,或许会为它历经沧桑而动容,或许会为它柔美的曲线设计所欣喜,或许会为它千百年来保持不变的基本结构而惊奇。但这就够了吗?做到这些就算认识它了吗?我们在大街上遇到一个陌生人,除了通过外貌知道他(她)的性别、大概年龄甚至职业之外,还能知道些什么呢?难道这些就能证明我们认识这个人吗。每个人或多或少知道一些器物,但基本上也就限于名称、基本功能等等。这跟在大街上知道陌生人的性别、年龄差不多。“以器物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常常被判定为文化之中最易明白、最易捉摸的部分,其实却需要基于更为深入的理论追寻和反思,才能够对此有新的认识和理解。”*王建民:《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器”与“道”》,《思想战线》2014年第5期。那么怎么才算是对物质文化有新的认识和理解呢?如果要对其展开研究需要关注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都有哪些可使用、借鉴的理论工具和视角?本文借助人类学、民俗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探讨物质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理论和视角,并思考多学科综合的物质文化研究进路。
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包括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一些国家的考古学和博物馆专业设在人类学系,典型者如美国。博物馆因为其公共服务性质,除了大学和研究所外,又有独立成体系的文博系统。)、艺术史*广义理解,艺术史属于历史学,但在现实操作中,艺术史往往被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等大历史排除在外,比如多数国家的艺术史学科隶属艺术学学科,而非历史学。但也因为此,艺术史研究获得了相当大的独立性,自成体系。可能是物质文化研究的传统领域。历史学主要关注文物,自成体系,与有“考现学”性质的现代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理念相异。艺术史主要关注“艺术品”,与本文探讨的主题也有差别,应于另文论述。本文主要考察人类学、民俗学以及与其价值取向相近的社会史、文化史等学科*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用的学科划分并非绝对,同时在多个学科做研究,并取得公认成果的学者并不少见。的物质文化研究理论和视角。
一、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的主题、理论和视角*本文主要从跨学科的视角探讨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进路,并非学术综述文章,比较详细的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综述可参考马佳:《人类学视域中的物质文化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受进化论和唯物主义的影响,物一直是早期人类学学者青睐的主题。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提出“遗留物”学说,认为现世文化是远古蒙昧人的“遗留物”,人类现在的文化是由远古文化进化而来的,通过对这些“遗留物”的研究可以探究人类社会的进化,给人类社会划分进化阶段。*[英]爱德华·泰勒:《人类学:人及其文化研究》,连树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继起的传播论学派不同意进化论学派认为文化是进化的结果,而认为人类文化是由最初的几个甚至一个中心(古埃及)传播开来的结果。*[日]绫部恒雄编:《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23-26页。稍后兴起的美国历史特殊论学派一改进化论和传播论对世界文化史宏观构拟的追求,而是认为每个地区、每个民族的文化自有其价值,进而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究物质文化对本民族的价值和意义。比如在博厄斯对原始艺术的研究中,他通过对印第安人陶器、木雕、服装等物品的造型和纹饰论证人类心智水平的一致性,以及肯定地域文化对当地人的巨大价值。*[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博厄斯及其弟子以此理念为基础提出的“文化相对论”成为当时反对种族主义的强有力理论,并成为世界人类学的基本认识论之一。
上述学派的物质文化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有缺憾。就文化研究而言,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物与人的关系。物与人之间的鸿沟在莫斯*又译作毛斯。的人类学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的弥合。他通过对礼物交换的系统性比较研究,揭示了这一社会交往形式在维系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并认为在人类早期群体之间的物的交换是更大范围内的非经济交换的一部分,这就是他著名的“总体呈现”(prestation totale)理论。莫斯在其对礼物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在后进的社会中或古代社会中,是什么样的权力与利益规则,导致接受了馈赠就有义务回报?礼物中究竟有什么力量使得受赠者必须回礼?”*[法]马塞尔·莫斯:《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5页。他的答案是“礼物之灵”,就是礼物所具有的总想回到原主人那里去的“灵”使现主人不得不回礼。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则批判性地提出了“互惠原则”的答案。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等人针对“礼物之灵”提出了批评性意见。这些基本上都是在“互惠原则”的理论框架之内展开的。总之,与进化论学派相比,人类学对礼物的研究为物质文化走向人类学的整体研究推进了一步。但我们看到,人类学的礼物研究强调的不是礼物本身,而是礼物背后的交换,他们通过交换来探讨社会构成和运行机制,而对物本身的关注相对不够。
马林诺夫斯基在批判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学研究的整体论。整体论在功能学派的倡导下成为人类学的传统之一。整体论视角下的物质文化研究强调将物与其附着的文化整合起来研究,两者可有重点,但不可偏废。马林诺夫斯基写道:“人因为要生活,永远地在改变他的四周。在所有和外界重要接触的交点上,他创造器具,构成一个人工的环境。他建筑房屋或构造帐幕;他用了武器和工具去获取食料,不论繁简,还要加以烹饪;他开辟道路,并且应用交通工具。若是人只靠了他的肉体,一切很快地会因冻饿而死亡了。御敌、充饥、运动及其他一切生理上的、精神上的需要,即在人类生活最原始的方式中,都是靠了工具间接地去满足的。”*[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页。在这里,马林诺夫斯基将物质文化(工具)置于人与自然之间,将物质文化本身放大到连接人与自然中介的高度,强调了物质文化对人的生存的意义。但是我们不应该就此认为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的物质文化研究是一种旧式博物馆式的就物质论物质的“唯物主义”。他认为如果没有与物质配套的精神、经济、语言等各方面的种种知识,“物质设备是死的没有用的。”*[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页。他还认为“只有在人类的精神改变了物质,使人们依他们的理智及道德的见解去应用时,物质才有用处。”*[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页。总之,“器物和习惯形成了文化的两大方面——物质的和精神的。器物和习惯是不能缺一,它们是互相形成及相互决定的。”*[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6页。
在器物本体研究领域,马林诺夫斯基所提出的器物的功能决定其形式的观点值得重视。他对浮海船只的形式和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物的形式决定于其基本及衍生的性质”的观点,并认为在一定的限度内“一个器物的主要性质是维持不变的,而它的细节则尽可能变异。但有意思的是在任何文化中,在这限度内的变迁也不是毫无一定的而有固定的形式可见,似乎是一旦选择定了后就永远得照例遵守了。”*[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费孝通译文集》(上册),群言出版社,2002年,第218页。器物的主要性质决定了器物的形式,而器物的主要性质具有很强的稳定性,照此推论,器物的主要形式也就有相当的稳定性了。将这一观点做一个反推论,可以得出器物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器物的功能,这一认识对于利用历史图像资料研究物质文化与人们生活的关系、物质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方法论意义。
此外,马林诺夫斯通过对物质文化与其精神层面的关系的探讨,提出了“物质文化是模塑或控制下一代人的生活习惯的历程中所不能缺少的工具”的观点。他说:“人工的环境或文化的物质设备,是机体在幼年时代养成反射作用、冲动及情感倾向的试验室。四肢五官在应用工具时养成了文化中所需的技术。神经系统亦因之养成了一切构成社会中通行的科学、宗教及道德的概念、情感及情操。这些心理历程尚有一重要的相配部分,就是喉舌养成了那些概念及价值所关联的一定的声音。”马林诺夫斯基的这段话概括地讲了物质文化在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情感、技术、认知、表达,几乎涵盖了人发展的所有方面。可见,在马林诺夫斯基眼里,通过物质文化的研究可以探讨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大部分问题。
结构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引导人们关注物质文化的符号和象征价值和社会意义。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著名的二元对立系统(如物质—精神、男—女、生—熟等)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有较大推进。在具体研究方面,布迪厄使用“整面墙—背阴墙”、“居高部分—低洼部分”、“男性生活区—女性生活区”、“人宅—畜宅”等的对立关系,对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Berbers)的住宅空间进行了描写和分析,揭示了住宅结构、空间及住宅内的物品的象征意义,并据此讨论了柏柏尔人男女世界和他们的心智结构。*[法]皮埃尔·布迪厄:《住宅或颠倒的世界》,《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425-443页。人类学家除了研究建筑空间的功能,还研究空间的文化属性。“杰姆逊对于波拿宛切酒店建筑的分析表明,功能性的使用空间正在被所谓文化性的建筑空间所替代。人们所使用的就是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物质的酒店空间本身就是由文化构成的。”*Frederich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of Late Capitalism,Durhar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转引自孟悦:《什么是“物”及其文化?——关于物质文化的断想》,孟悦、罗刚主编《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前言”第4页。还有的人类学家通过房屋的建筑格局研究家庭和个人的隐私权、公私关系、人际关系等问题,也是很有启发的视角。*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27~155页。苏珊·皮尔斯(Susan Pearce)通过解读服装的社会意义对社会分层进行研究。*Susan Pearce, ‘Interpreting Museum Objects: An Outline of Theory ’,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nthropology and the Museum, Ed. by Tsong yuan Lin,Taiwan Museum, 1995, pp.298-300。转引自潘守永:《物质文化研究: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年第2期,第130页。
最近活跃在中国的世界知名人类学家罗伯特·莱顿早年出版有《艺术人类学》一书,该著介绍了“小型社会”多种形式的艺术,并将艺术品与仪式、神话、权力联系起来考察,在此基础上探讨艺术的本质,并讨论了当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艺术观。文中关于艺术品沟通社会上下层的观点值得重视,他指出:“艺术品在(上下层社会的)互动模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互动模式使得政治体制进入了生活。更进一步的意义是,通过艺术品获得了可见形式的种种观念似乎不只是对政治体制的消极反应,而且更是对政治权威的本质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的哲学反应。”*[美]罗伯特·莱顿:《艺术人类学》,靳大成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第100页。
台湾学者黄应贵主编的《物与物质文化》论文集是中国学者对物有较大影响的著作,该著的八位作者基于相比人观、时间和空间等文化类别,“物更能凸显人类学创新与再创造的行为,而为文化传统再创造之所以可能的重要基础”*黄应贵主编:《物与物质文化》序,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4年。的学术理念,以艾灸、服饰、祖灵屋、食物(两篇)、人体图绘、神像、新农作物为田野考察对象,展开对物自身、交换与社会文化性质、物的象征及物与其他文化事项的关系、社会生活方式与心性等问题路径的广泛探讨,“在有关不同的探讨路径所再现的不同物性,以及如何通过象征性沟通系统性质的探讨来连结物性与历史及社会经济条件等,更涉及物与其他分类范畴连结之所以可能的物质与心理基础,最后更强调由物切入所做的研究,对于被研究社会文化的理解上,所提供的新观点,以凸显物与物质文化研究在人类学知识理论发展上的独特贡献。”*黄应贵主编:《物与物质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4年,第1页。
近年由孟悦、罗钢主编的《物质文化读本》一书收录国内外学者论文23篇,主要探讨了人类学界对礼物和交换、物与情感、财产与消费、物质文化与文化身份、物与意识形态、物与词语表达等内容,*孟悦、罗钢主编《物质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可以看出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涉及了多种领域,研究范围日益扩大。
二、民俗学器物研究的主题、理论和视角
(一)物质民俗研究
民俗学者虽然也使用物质文化的概念,但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内涵稍小的物质民俗概念强调自己的学科归属。中国民俗学的创始人钟敬文在《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给出了物质文化*“物质文化”和“物质民俗”内涵有重叠,但也存在区别,最明显的是两者的研究范围不同:“物质民俗”的研究范围是“中下层”文化,而“物质文化”研究也包括上层文化。但是钟敬文此处所使用的“物质文化”一词实等同于“物质民俗”。因为作者是将这个概念放置在民俗文化的范围内看待的。且看此引文的前段:“民俗文化的范围,大体上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和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尚事物。”(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第9页)的定义:“物质文化,一般包括它的各种品类及其生产活动两个方面。它是由人类的衣、食、住、行和工艺制作等物化形式,以及主体在物化过程中的文化传承活动所构成的。像传统的民居形式、服饰传统和农耕方式等,都是物质文化的内容。”*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1996年,第9页。该定义强调了几个重要方面:一是物质文化的物质本体——“人类的衣、食、住、行和工艺制作的物化形式”;二是物质文化的分类学——“它的各种品类”;三是强调了物质文化的生产——“生产活动”;四是物质文化的传承——“主体在物化过程中的文化传承活动”。既强调了物质文化的结构(物质本体和分类学),也关注到了物质文化的历史学(传承),又关照到了物质文化创造主体的行为和实践(生产活动和传承活动),打破了英国早期民俗学家班恩(C.S.Burne)对物质文化的狭隘认识,基本上完成了对物质文化整体论意义上的概括。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定义虽然关注到了物质文化的主体也关注到了物质文化的本体,但是对物质文化的客体则缺少讨论。如定义中的文化传承活动被限定在了“物化过程中”,但就物质文化研究来看,其内涵到“物化”远未结束,如工具制造的过程是工具“物化”的过程,但人们对工具的使用,以及使用过程中的行为和活动也是物质民俗的重要内容。
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为《物质生产民俗》和《物质生活民俗》。从这两章所占全书的篇幅来看,物质民俗研究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给了物质民俗研究在民俗学中应有的位置。该书第二章给出了物质生产民俗的定义:“物质生产民俗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特定地区、社会群体中的大众,在一定生态环境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文化事象。它包括:农业民俗;狩猎、游牧和渔业民俗;工匠民俗;商业和交通民俗等,它贯穿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全过程。“*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0页。而在第三章中,该书没有给出物质生活民俗的定义,只描述了物质生活民俗的大体内容:“物质生活民俗包括饮食、服饰、居住、建筑及器用等方面的民俗。”但就该书给出的物质生产民俗的定义、内容以及物质生活民俗的内容也可以看到许多值得强调的地方:首先,物质生产民俗的定义强调了物质民俗的区域性——“一个国家、民族的特定地区”;其次,该定义明确指出了物质民俗的主体——“社会群体中的大众”;第三,强调了生态环境对物质民俗的生成和制约——“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
钟敬文在《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和《民俗学概论》中对物质民俗的定义和论述在中国民俗学界有权威范式意义。从整体论的角度来看,他告诫我们要注重从物质民俗的本体、主体、客体三方面对其进行考察,重视物质民俗与生态环境的互动,重视物质民俗的主体对物质民俗的传承及创造,重视物质民俗分类学,从文化研究的意义上把握物质民俗的含义。
由钟敬文先生指导的博士生郑然鹤较早地对其物质民俗研究思想进行实践,所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与韩国犁的比较研究——以中国华北、东北地区为中心》,通过田野调查和借助文献研究及出土遗物,比较研究中国华北、东北地区的犁与韩国犁,剖析了两国犁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联系和不同,并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两国与犁有关的风俗和观念。通过比较,论文认为韩国犁起源于中国,但韩国人对其进行了改良,以适应韩国当地的地形、气候、土壤和民俗习惯。*[韩]郑然鹤:《中国与韩国犁的比较研究——以中国华北、东北地区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5月。该文是由中国民俗学家指导完成的以一种具体的器物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进行中韩文化比较的物质民俗研究论文,具有较高的学科文献和理论价值。
由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学者共同完成的中法国际合作项目《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已由中华书局2003年出版“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四册:白尔恒、[法]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魏丕信(Pierre-Étienne Will)编著《沟洫佚闻杂录》、秦建明、[法]吕敏(Marianne Bujard)编著《尧山圣母庙与神社》、黄竹三、冯俊杰等编著《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董晓萍、[法]蓝克利《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深入探讨了水资源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取得了广泛的学术成果。该项目“通过华北民众有能力管理像水这样重要的物质资源的视角,观察其民间组织的活动形态,分析华北基层社会群体怎样被迫做出生存选择,怎样去维护自身利益,建立社会等级,传承思想等级和行为的准则,并在这一层次上,建立他们的社会结构。”*[法]蓝克利、董晓萍、[法]吕敏:《陕山地区水资源与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总序》,载董晓萍、[法]蓝克利:《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总序,中华书局,2003年,第5页。
项目成果之一《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一书综合利用村社碑刻、水册、村民日记以及田野访谈资料,描述了山西霍山脚下十五个极端缺水的村庄所建构的“不灌溉水利系统”和地域社会,并重点探讨了维持“不灌溉水利”所形成的“四社五村”村社组织和用水规范。该书从社会史的视角拓展了物质民俗的研究范围和领域,提出了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该书还指出了“地方代言人”在促进国家与地方社会一致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但对“地方代言人”运用地方民俗传统和个人智慧化解甚至抵抗国家意志,在保护地方社会的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具体过程缺少关注。
最近两部由本土学者出版的著作,持续刷新人们对物和物质文化的认知。其中张柠的《土地的黄昏:中国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用较大的篇幅描写和分析乡村器物。该著将乡村器物提高到乡土价值载体的高度,作为与时间、空间、社会等级、农民的身体形态和形象并举的重要论域,且用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分四章描述和分析乡村的家具、农具、食物和玩具。认为乡村器物“是了解乡村秩序中的农民农耕生产和日常生活行动的直接入口……器物既是农民的帮手,也是农民的限制。这些器物的生产和使用,直接联系着乡土文化的各种价值观念。改变器物的结构和器物的功能,也就是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行为目的乃至价值的行为准则……农民与器物的关系的变化,也就是乡土价值的变化。”*张柠:《土地的黄昏:中国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页。该著无论是对研究对象的把握、谋篇布局还是观点均有相当新意,对物质民俗研究领域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与张柠的关注点和出发点不同,汪民安《论家用电器》完全基于自己对机器的感觉和经验,思考家用电器所塑造成的家庭空间,并以此重新检讨家用电器的文化功能及与人的关系。该著作以我们司空见惯、习焉不察的洗衣机、冰箱、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为研究对象,考察机器对人的解放和控制、对人群的分层、对人心态的影响等问题,探讨现代家庭作为休息空间和生产空间的角色,以及家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对物作为叙述对象的价值方面,汪民安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观念和行动可以改变历史,但是,物和机器同样可以改变历史。既然如此,为什么学院讨论总是限定在人的领域,观念和思想的领域,而放弃物质的领域?”*汪民安:《论家用电器》,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7页。他认为:“正如任何观念都有自己的命运一样,物也有自身的特定命运。这些以电为基础的物体,它们也在快速脱离人的意志而自主地进化,它们也有自己奇妙的生命历程。”因此,要清楚的认清人自身,“或许我们需要新的传记,不是观念的传记,而是物的传记,物的生和死的传记。”*汪民安:《论家用电器》,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8页。为物做传记,这与记录民俗学对物质民俗的研究理念是一致的。
以上两位作者严格来说虽不是民俗学学者,其著作对器物的研究有些地方也缺乏实证性考量,但处处散发卓越的洞见,对物的认知领域有强大的冲击力,甚至有可能就此建构物质民俗研究的一种新方式。
(二)民具学研究
在物质民俗研究领域,民具学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且自成体系。其中以日本民俗学界的民具研究开展时间最长、取得的成就最大。近年,国内民俗学、人类学界的少数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开拓性工作。
日本的民具研究
日本的民具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期,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民具一词就来自日本。日本的民具研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民具学”。1968年,日本的民具学者创办了专门研究民具的学术杂志“民具月刊”。1975年,日本民具学者正式成立了“日本民具学会”。在此基础上,日本民具学者出版了大量民具志和民具研究理论著作。*周星:《日本民具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载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76-325页。
民具一词是由日本民具学者涩泽敬三首先创用的。在此之前,日本学界曾用过“民俗品”、“土俗品”之类的词汇。涩泽敬三的定义见于1936年由日本“阁楼博物馆”编辑的《民具搜集调查要目》之中:“民具乃是‘我国同胞基于日常生活的需要,采用某些技术而制作出来的身边寻常的道具’,‘它涉及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一切基于人们生活的需要而制作和使用的传承性的器具和造型物。’”*阁楼博物馆编:《民具搜集调查要目》,阁楼博物馆刊行,1936年;三一书房,1972,转引自周星:《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77页。这个定义对后来的民具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宫本馨太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民具定义:“民具乃是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因需要而制作和使用的传承性的器具,民具包括一切可能的造型物,它对于理解和揭示国民文化或民族文化的本质及变迁过程具有不可欠缺的意义。”*宫本馨太郎:《民具入门》,庆友社,1990,第9-15页(最早发表于1969年),转引自周星:《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77页;又见天野武:《庶民生活的见证——民具》,原载王汝澜等编译:《域外民俗学鉴要》,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2页。
民具学家宫本常一对民具的理解是:民具乃是有形民俗资料的一部分;民具是人们手工或使用道具制作的,而不是由动力机械制作的;民具是由民众基于其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制作出来的,其使用者也限于民众;而那些由专职的匠人以很高的技术制作的器物通常被叫做工艺品或美术品,很多也是被贵族和统治阶级的人们所使用的,这是应该和民具区别开来的;民具的制作不需要很多程序,与其说它们是由专职的匠人制作的,不如说是由普通人在从事农、渔业的同时制作的;民具多由人手驱动;民具的素材主要有草木、动物、石头、金属、陶土等,原则上不包括化学制品;民具大都是一次加工而成,当包含复杂加工的情形时,也有由“能人”制作的。*宫本常一:《提倡民具学》,未来社,1979年,第75-77页,转引自周星:《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77-278页。
日本民具学会的前会长岩井宏实认为:“民具乃是身边寻常普通的道具,它‘涉及生活文化的所有领域,并能明确地显示出基础性的传统文化特质,是对于理解日本的民族文化及其历史变迁所不可欠缺的具体资料’。”*岩井宏实:《民具的博物志》,河出书房新社,1990年,第189-194页,转引自周星:《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77-278页。
以上四位学者的看法,基本代表了日本民具学界对民具的理解。这四种看法都在一国民俗学的框架下之内,都强调了民具的传承性和寻常性。我们从此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民具学家对民具认识的逐步细化和深化的轨迹。涩泽敬三民具定义中的民具的所有者比较模糊,他用的“我国同胞”显然不是民俗学的学术术语,我们从这个定义上看不出民具指的是中下层文化还是也包括上层文化。宫本馨太郎的定义已经有了民俗学框架下的民具主体——“一般民众”,这表明民具是中下层文化,不包括上层文化的器具,如宫廷用器和王公贵族用器。这个定义还强调了民具在揭示民族文化变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与当时日本社会所经历的急剧变迁有关。民具在文化变迁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的学说对后人启发颇大。但宫本馨太郎的定义中民具的限定词“日常生活”,似乎将民众的非日常用具排斥在外了。宫本常一强调了民具的中下层文化本质,而且进一步明确指出民具的范围是“生产”和“生活”而不是模糊的“生活”领域。他还认为民具不包括由动力机械制作的器具。相比前两者,宫本常一的定义中没有“造型物”一词。“造型物”可以是器具,也可以是建筑或设施。我们知道,在民具的研究中很少会涉及到建筑,建筑民俗是一个和民具民俗并列的学术领域。宫本常一的定义使民具的范围更加明确了。相比于前三者对民具的定义,岩井宏实则更强调民具传承的精神性和民具的民俗学资料价值。他认为民具的实用性可能消失,但是民具中所蕴含的民众智慧却不会轻易消失。
日本学者基于自己对民具的基本理解就“民具的属性与功能问题,民具的形态、形制与样式问题,民具的实用性、艺术性和象征问题,民具的地域性、时代性和传承性问题,民具与生活的关系及其在生活中的意义,民具的‘生命史’”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谈论。”*周星:《日本民具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载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25页。
(三)我国的民具研究
相对于日本学界而言,我国的民具研究尚显薄弱,民具一词很少见诸书面,明确提出自己民具观的学者就更少了。张紫晨对民具所下的定义较有代表性:“劳动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各类工具、器皿等用品。作为民俗学研究对象的民具,主要是指传统的,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一切造型物。民俗学上往往把民具划分为基本民具、准民具、指标民具等几种类型。根据民具的用途、机能、形态、制作要素来进行不同的分类。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对民具大致可以分为传统民具和流行民具,或新民具和旧民具两大类。”*张紫晨主编:《中外民俗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3-174页。这个定义受到了日本民具学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如将民具的所有群体解释为“劳动人民”,具有鲜明的中国时代特征。这个定义强调了民具的传统性和传承性。但如同宫本馨太郎的定义一样,“日常生活”一词的使用,遗漏了一些重要民具。
许平认为:“它(民具)一般指除建筑形式之外的各种实用生活器具和设施,其中又以包含了日用器具在内的广义的生活与劳动‘工具’的研究为核心。”*许平:《〈中国民具研究〉导论》,《浙江工艺美术》2003年第1期,第1页。这一认识与宫本常一相近,突出特点是明确提出建筑不属民具范畴。但“实用”一词使用得颇为模糊,那些用于观赏的民间器具(如花灯)也应该是民具。
其他与民具相近的概念有民俗文物、民族文物、物质民俗等。“民俗文物,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间生活文化中的物质文化遗存和精神文化的物化遗存……既是民间的生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反映着民间风俗、习惯等民俗现象的遗迹和遗物;既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的基础之所在。”*徐艺乙:《关于民俗文物》,《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民具和民俗文物有颇多重合之处,如都是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都强调传承性等等。与民具相比,民俗文物突出强调了精神性和基础性,认为民俗文物是“精神文化的物化遗存……反映着民间风俗、习惯等民俗现象的遗迹和遗物……是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的基础之所在。”虽然民俗文物是在文博学科的框架下展开讨论的,但是它具有强烈的民俗学意味。当然这个定义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生活文化”一词就用得比较模糊。相比之下,民族文物的定义则更加强调文物的民族性和物质性:“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某一民族的文化遗存。它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该民族在具有多民族共性的大家庭中保存了本民族的生产、生活、文化、艺术、宗教、服饰、习俗等特色的实物资料。如民族建筑、民族服饰、民族文化用品、民族乐器等。”*吴诗池编著:《文物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9页。民族文物的定义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注意到了民族文物存在于“多民族共性”的大背景之下,也就是注意到了各民族之间的民族文物影响和交流。二是对民族文物的范围作了较明确的学术划定。认为民族文物存在于“生产、生活、文化、艺术、宗教、服饰、习俗”等方面。但是该定义亦有不足之处,如对文物的精神性强调得不够,“民族特色”一词将多数普通文物拒之门外,此定义距离民具的意涵更远一些。
国内民俗学和相邻学科对民具的实地调查研究成果不多,其中由尹绍亭主编的《云南物质文化》*尹绍亭:《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罗钰:《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唐立:《云南物质文化》(生活技术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罗钰、仲秋:《云南物质文化》(纺织卷),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丛书值得一提。该丛书对云南山区多个民族的民具进行了精心的测量、绘图、描述,并对民具的使用方法和功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说。该书除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之外,还有较强的方法论意义:第一,“点面结合”(既对一个村落中民具比较齐全的一两户居民的民具做全数调查*“全数调查”是日本民具学者提出的民具调查方法,即对一个民具较齐全的家庭或村庄等单位中的民具做全部调查。,再对其他农户的民具做补充调查)和“动静结合”(既对民具做静态的结构考察,也在实际的使用场景中对民具的使用方法、功能等做动态观察)的研究方法。第二,民具使用体验法。对民具亲身操作,获得实践认识。
当然该丛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正如周星所指出的:“尹教授在采集资料时已注意到‘点面结合’,并努力展示了一些‘点’上资料的完整性,可不同器具间的‘器物组合’似乎较少引起重视。除了‘地域’、,还应有‘社区’概念,在社区基础上建立‘器物组合’,甚至必要的统计分析,应该是可能和有价值的……尹著和罗著在‘器物’研究上都很突出,在‘技术’研究方面,比较注意器物使用的技术,而程度不等地对器物的生产制作技术、交易流通(不等于文化理论里的‘传播’)及占有关系等有所忽略。”*周星:《物以载道:我心中的学术精品》,《中国图书评论》1999年第4期。
孟凡行新近出版的《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孟凡行:《器具:技艺与日常生活》,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一书广泛吸收国内外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日本民具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对贵州六枝特区梭戛乡长角苗族群的民具进行了三个多月的深度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该书主体部分通过丰富完善使用民具群、民具组合等概念对该族群的民具进行了详细描述性分类研究。然后从该族群所处的环境出发,通过对民具的结构和形制,制作工艺和使用,民具的流通、储存、生命史等内容的考查和分析,研究民具和人以及自然社会环境的互动,探讨围绕民具所形成的文化,最后讨论民具文化的传承和变迁。认为民具的特质与其说是基于地域文化特点的形制和功能,不如说当地人对器物的使用方式及其认识。这些只有将器物放在民具、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多边互动关系之中才能得到比较确切的理解。
三、其他相关学科物质文化研究关注的问题、理论和视角
近年来历史学和人类学、社会学相互影响,激发了文化史对一些过去较少关注的问题的研究,也推进了历史人类学、社会历史学等学科的发展。这些学科采取的视角和关注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从研究对象来看,文化史特别强调对食品、服饰、住宅的研究;从研究的面向上来看,文化史重视对物质文化消费的探讨;从理论趋向上来看,文化史则注重揭示和运用物质文化的符号意义。诸如锡德尼·W·明茨(Sidney Wilfred Mintz)对糖的研究、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对服饰的研究、奥尔瓦尔·勒夫格伦(Orvar Löfgren)和乔纳斯·弗莱克曼(Jonas Frykman)对住宅的研究等等。明茨的《甜与权:食糖在现代史中的地位》*Sidney Wilfred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Penguin Books Ltd,1986.一方面关注了消费者和食糖之间的关系,探讨了食糖从富人的奢侈品到民众日常必需品的演变过程。另一方面他又关注了食糖的符号学意义,食糖是富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它因此有了社会分层意义。而当食糖从奢侈品向生活必需品转变的过程中,原有的符号意义逐渐消解,从而获得了新的意义。罗什的《服饰文化》*Daniel Roche,The culture of clothing :dress and fashion in the ‘ancien régime’,translated by Jean Birrell,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是一本有关法国十八世纪服装和时尚的历史。这部著作透过人们着装的历史表象,探究背后人们的思维、情感结构和价值观。勒夫格伦和弗莱克曼的《文化建设者》*Orvar Löfgren,Jonas Frykman. Culture Builder,translated by Alan Crozier,London: Rutgers,1987.叙写了19世纪瑞典布尔乔亚住宅的历史。书中提出,19世纪后期的瑞典“发生了从‘节俭’向‘富足’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发生的原因是住宅‘变成了一个家庭炫耀其财富和展示其社会地位的舞台’。室内的家具和装潢,尤其是客厅,有助于家庭向来访的客人炫耀自我。”*[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1页。此外,作者也对居所中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进行了讨论,*[英]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些都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和视角。
历史学理论对物质文化研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是对“留下痕迹”和“阅读痕迹”的双重强调。第二是在田野里解读文献的观点。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反对传统历史学家“史学从文本出发”的论调,认为这把历史学紧紧地绑在了文字上。相反,他强调对物质事实的关注:“一把钢斧、一个未经烧制或经过烧制的陶罐、一个天平或其若干砝码,总之都是一些可以触摸和可以攥在手里的东西。人们可以检验它们的阻抗力,而且可以从它们的形状当中得出涉及当时人们和社会的生活的无数具体提示。”*Lucien Febvre, Ein Historiker Prüft sein Gewissen,in:ders.,Das Gewissen des Historiker,S.13.转引自[瑞士]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8页。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认为史料是多样化的,历史学研究凭借的不仅仅是文本所记载的史料。他说:“历史证据的多样性几乎是无限的。”*Marc Bloch,Apologi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oder Der Beruf des Historikers,hg.von Peter Schöttler,s.75.转引自[瑞士]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0页。他还将史料的多样性进行了举例式的明确陈述:“凡是人说过的话、写出来的东西、制造出来的或者哪怕只是接触过的物件,都能够而且必定会向我们提供关于他的信息。”*Marc Bloch,Apologi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oder Der Beruf des Historikers,hg.von Peter Schöttler,s.75.转引自[瑞士]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白锡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0页。历史学家重视“留下痕迹”不代表他们轻视文本,文本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无需多言。历史人类学家对“留下痕迹”和“阅读痕迹”的双重强调,正是这门学科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在中国,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以华南和港台地区为盛,这些学者*如大陆的陈春生、刘志伟等,香港的蔡志祥、张兆和、廖迪生,英国的科大卫(David Faure)等。取得了一些理论上的共识。其中的一个理念是在具体的田野环境中解读文献。诚如张应强所说:“我们拿到的文献,不管是官修的文献还是民间的文献,这些文献只有在田野里进行解读;换句话说,他们觉得,我们应该是在田野里读通这些‘古籍’。”*徐杰舜、张应强:《历史人类学与“文化中国”的构建》,《广西民族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联系到博物馆式的物质文化研究,在田野里解读文献的观点,对物质文化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物质文化也只有在田野中,并且是在其存在的原生文化场域中才能得到最有效的解读。
社会学“远距离联系”的概念也值得物质文化研究者思考。热拉尔·努瓦利耶认为:“当我使用一个物品,我并没有自觉意识到它是被其他人制造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社会事实。然而,这个物品将我与他人联系起来。”*[法]热拉尔·努瓦利耶:《社会历史学导论》,王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远距离联系”的概念为我们以物质文化为媒介探究远距离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影响,进而编织社会结构的网络提供了武器。
从以上几个学科方面的梳理可以看出,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以上所见主要是学界在共时向度对两者关系的理解。历时向度也就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向度的研究也值得我们思考。这方面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W.F.Ogburn)和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的理论可能是提出新问题的出发点。前者提出的“文化堕距”认为:社会变迁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在发生变迁的时候,各部分的速度并不一致。一般来说,物质文化首先变迁,其次是制度文化,再次是风俗、道德文化,最后是价值观念。这种理论还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精神理念、道德观念与我们物质文化、技术发展不相适应而引起的。*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8、363页。萨林斯通过对北美爱斯基摩人的研究,得出了一个民族的物质文化的变迁不足以引起这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等核心文化的改变,而往往是人们利用外来的先进工具等物质设备为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服务的理论。*[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胡宗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18-21页。“文化堕距”理论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我们在承认“世界是平的”的时候,也不能忘记在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地方性知识”的启迪下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萨林斯的观点给学界带来了颠覆性的认识,极富启发性。
四、结语:多学科视野下物质文化的综合研究进路
通过上文的简要梳理,我们看到在物和物质文化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和民俗学做出的贡献最为突出。实际上,就物和物质文化研究领域来看,人类学和民俗学在创始之初很相近,最明显的一点是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泰勒提出的“文化遗留物”观点,也曾为民俗学所借鉴,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早期民俗学的发展。后来,因为人类学的异文化和小型、无文字社区研究取向,民俗学的本文化、历史悠久社区研究取向的差异,人类学发展出了前文所述的更重视社会性的“总体呈现”命题,而民俗学则发展出了更重视文化性和传承性的“物质行为”命题。
(一)物质行为:一种物质文化综合研究视角
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虽然不同学科有自己的学科追求和研究旨趣,但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类文化、历史和社会结构,以及瞬息万变、难以捉摸的群体、个人实践,任何基于单一学科理念的视角、方法都有将“复杂社会进行简单治理”的嫌疑。只有以研究内容和问题为导向,加强学科间对话,并广泛吸收各学科有价值的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进行多学科视角下的综合研究,并不断开发新的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才有可能将该项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近些年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影响颇大的思想家级别的学者,不管是抛出场域、惯习、文化再生产等概念武器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还是整合话语意识、理性实践、动机和认知无意识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都是以行动者为工具,超越传统理论的二元分裂,从而有效在结构和建构(布迪厄)或结构和行动(吉登斯)二者之间调和的综合集成创新研究。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李强在2015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总结发言中也指出,面对复杂的社会,最好的研究方法就是综合研究。
迈克尔·欧文·琼斯是物质民俗领域倡导综合研究的代表学者,他指出民俗学对物质文化及其制作技术的研究主要有四种视角,分别认为物质传统是历史手工艺品、可描述可传承的实体、文化的实体,以及将制作和使用物品看作是人类行为。第一种视角认为手工艺品根植于传统并流传至今;第二种视角强调研究物质实体的样式,以此展开物质民俗的类型学研究;第三种视角认为物质民俗能够体现出研究群体的文化要素,并主要关注“物质文化怎样符合(一般并不一致)并体现出一个群体的设想、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第四种视角将对物品的制作和使用当作人类行为来研究。*迈克尔·欧文·琼斯:《手工艺·历史·文化·行为:我们应该怎样研究民间艺术和技术》,游自荧译,《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5期。琼斯认为对于物质民俗和技术的研究而言,这四种视角都是不可或缺的,并倡导混同四种视角的综合研究。为了倡导这种综合的研究方式,他提出了物质行为的概念。认为:“物质行为不仅包括个人创造的物品,而且包括制作者构思、制造、使用或提供给他人使用的过程。它包括创造东西的动机(感观的、实用的、观念的、治病的),制造过程中的感情和身体活动以及对物品和制作的反应。物质行为既包含着个性特征、心理状态、心理过程以及关于手工艺品的社会的相互影响,也包含着个人在物品中融入的思想、人们赋予物品的涵义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象征性和实际地使用物品的方式。”*迈克尔·欧文·琼斯:《手工艺·历史·文化·行为:我们应该怎样研究民间艺术和技术》,游自荧译,《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5期。
琼斯还强调“物质行为研究不是将研究对象作为孤立的现象,而是将其作为活动的产品,体现出无形的过程以及引发反应的可触知的刺激。”*迈克尔·欧文·琼斯:《手工艺·历史·文化·行为:我们应该怎样研究民间艺术和技术》,游自荧译,《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5期。民俗学对物质民俗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物质本身,而是应该关注物品背后的人,重视对物品的构思、制作、使用过程的研究,重视透过物品观察人的观念、情感、需要和愿望。*迈克尔·欧文·琼斯:《手工艺·历史·文化·行为:我们应该怎样研究民间艺术和技术》,游自荧译,《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5期。琼斯的物质行为研究视角将物质民俗和技术民俗整合起来,注重民俗过程的探讨,并深入到人的情感和观念层面,是一种综合研究策略。
(2)“物质/器物关系”和“物质/器物文化的四层结构”
器物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对人和文化的整体研究,其主要路径是各种互动“关系”。大体相当于在中国历史上引起长久争论的“器”、“道”关系。*王建民《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器”与“道”》(《思想战线》2014年第5期)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器”和“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极富洞见的阐发。概括起来如器物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材料、对自然的改造、废弃器物处理等)、器物本身的结构关系(形制、制作工艺及历史、审美)、器物和人及社会的关系(人口,物理和社会功能,器物对人身体和精神的塑造和控制、人工智能、器物对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信仰和祭祀、情感、礼仪和仪礼,器物和技术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面子和人际关系,资源争夺和权力分配,消费、流通)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系都是双向的互动关系,人制作、使用器物,但同时人在一定程度也被物化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从诞生之日起,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是同时进行的。正因为此,我们可以说物质文化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门通过器物研究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学问。为增强对整体文化的理解以及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而进行的区域间物质文化比较,除了要关注不同区域中器物、技术本体的异同外,更重要的是探究“物质/器物关系”的差异。研究“物质/器物关系”,撰写物质文化民族(俗)志,从结构的角度切入有一定的实操性。
器物有其自身的文化结构,笔者认为器物至少存在四层结构:一是单个器物的结构,也就是单个器物的材料、形制、构成和制作工艺;二是器物组合的结构,也就是器物和器物的组合关系,器物组合是以一项完整的实践活动所使用的全部器物来界定的,比如完成犁地劳动的犁、耙、耱、牛马挽具等组成犁地农具组合,而一场音乐会需要的乐器则组成特定的乐器组合。器物组合有一定稳定性,但因为实践活动的多向性,所以器物组合并不是完全固定的。小的器物组合还会组成更大的器物组合,比如耕种农具组合就包括了犁地、播种、灌溉等器物组合。因此我们可以将器物组合分级,如一级器物组合、二级器物组合等等,一级器物组合是器物组合的最高级,比如所有生产性的器具组合组成一级生产器具组合,所有生活性器具组合组成一级生活器具组合等;三是器物群的结构,也就是一级器物组合之间的结构关系;四是器物和其他文化事象(如生态环境以及上文提到的器物、人及社会的互动关系)之间的结构关系。器物文化的四层结构不仅注重器物(特别是基本器物和标志性器物)本体的研究,而且强调将器物放在一定地域的社会历史及自然生态大环境中,作以器物组合和器物群为基础的整体研究。在此过程中器物的制作和使用技术(手工艺)、人们对器物的认识(心态)等贯穿始终。
(三)“物质关系”与“总体呈现”、“物质行为”经典命题的区别及其价值
如前文所述,在物和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人类学发展出了以莫斯为代表的“总体呈现”命题,民俗学则有琼斯的“物质行为”命题。那么本文所提出的“物质关系”命题与上述经典命题有和区别?其有什么样的独特学术价值?
“总体呈现”命题是莫斯在考察初始民族的礼物交换的过程中提出的,他认为部落之间的礼物交换是更大范围的非经济交换的一部分,初始社会正是依靠这些循环不断的物品交换建构、维系和再生产自己的社会的。因此,物的交换是初民社会维系其社会结构的基本机制。由此,可以看出“总体呈现”理论的提出者莫斯延续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社会事实研究的基本学术理念,集中于对社会的关照,而对物本身和人缺乏关注。
与莫斯的学术取向不同,琼斯“物质行为”理论的探讨对象是物质民俗的研究视角。“物质行为”将物本身、物所体现的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制作物的技术、制作和使用物的人、人在制作和使用物过程中的心态等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较好地体现了对物的传承性、文化性等民俗学传统论题的关注。“物质行为”理论对器物本身和器物背后的人的双重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拟补了“总体呈现”理论对物本身,尤其是人的忽视,但我们同时看到,可能囿于学科兴趣,“物质关系”理论则缺乏对社会维度的关照。最后,两命题都缺乏对自然和生态这一终极维度的关照,而这对当今世界尤其是饱受环境问题困扰的中国尤其重要。
“物质关系”在“总体呈现”和“物质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但不同于两者或以物看社会,或以物看文化和人,而是将物看作是人类文化实践的中间环节。其上连接的是制作器物的人和社会、与器物的原材料有关的自然生态,其下是人在一定的社会中执器物完成的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自热生态的影响。而贯穿这一过程的是人们对器物的使用方式和使用方法,即技术,而人们对器物和技术的认识则是一部人的心态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自然生态、物、人、社会以平等的姿态放在一个系统内讨论,尽力避免偏执“拜物”、“唯社会”、“人类中心论”、“生态决定论”之一端,实现对物的研究的整体关照。
至于“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则是在“物质关系”命题下,从事物或(大胆)曰物学研究,特别是其基础性工作——物质文化民族(俗)志考察和撰写的基本思考框架。
综上,“物质关系”借鉴人类学和民俗学对器物研究的主要成果,将物放在自然生态、物、人、社会的有机系统中讨论,不仅探讨四大因素本身,尤其关注四者之间的关系,实践整体研究理念,力图搭建跨学科的物或物学研究。而作为此研究的基础应是物质文化民族(俗)志,针对中国物质文化民族(俗)志缺少的现状,本文延伸提出“物质文化的四层结构”的物质文化考察和撰写框架,供学界参考和批评。
孟凡行,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 210096)。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器物、手工艺遗产与关中文化研究”(14CG12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