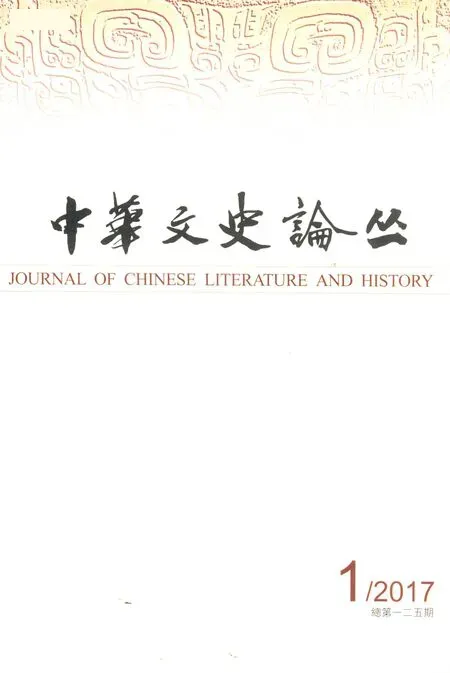唐代玄奘的聖化
劉淑芬
唐代玄奘的聖化
劉淑芬
在中國歷史上,玄奘(600—664)被視爲譯經求法的高僧。然而,日本自鎌倉時代(1185—1333)以降,玄奘則被聖化爲護法神祇,其聖化呈現階段性的進展,内容大多來自中國,包括唐宋時期的文字和圖像文本。本文主要討論唐代玄奘傳記《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有關其西行求法、圓寂前後的聖化敍述,中宗、玄宗朝對玄奘的追念及影響,中晚唐時期新出現的玄奘傳奇(如與其西行事迹相關的深沙神信仰),以及藉他之名宣揚的經典和齋儀,探討其聖化的軌迹。入宋以後聖化玄奘的宗教文物,以及鎌倉時代玄奘的聖化過程,將以另文討論。
關鍵詞:玄奘聖化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深沙神齋儀
一 前言
在中國歷史上,玄奘被視爲譯經求法的高僧。然而,日本從鎌倉時代(1185—1333)開始,在“大般若會”使用的儀式繪畫“釋迦十六善神圖”中,玄奘業已聖化(sanctification)爲護法神祇;今日奈良藥師寺玄奘三藏院供有他的塑像,供桌上立有一個牌位,上面寫着“南無大遍覺玄奘三藏菩薩”,受僧俗禮拜供養。反觀中國,玄奘僅在明代小説《西遊記》裏被稱爲“聖僧”,在世俗或佛教界中僅將他界定爲高僧;如宋志磐撰、明袾宏重訂《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中,將他視爲“求法”的高僧。①《法界聖凡水陸勝會修齋儀軌》卷二,奉請“譯經摩騰竺法蘭、求法奘三藏等諸法師”,《卍新纂續藏經》(74),頁791上。事實上,日本玄奘聖化的内容大多淵源自中國,包括玄奘傳記中聖化的敍述,九世紀深沙神信仰的傳説、玄奘聖化的圖像等。
筆者《玄奘的最後十年》一文指出:高宗永徽中,玄奘無端被捲入政爭風暴,使他的晚年備極艱辛,更成爲政治上的禁忌。②《玄奘的最後十年(655—664)——兼論總章二年(669)改葬事》,《中華文史論叢》2009年第3期,頁1—97。然而,玄奘個人德行高超和佛教的精深修習,使得他在西行萬里求法的歷程中,從西域、中亞到印度,都贏得國主尊敬護持,普爲僧衆所崇仰。他帶着大量的經典、佛像、舍利歸國時,人們對他尊崇已極,視之如彌勒下生。起初他得到唐太宗全力的贊助,潛心於經典的翻譯;儘管永徽六年(655)以後政治上波濤洶湧,他未能幸免波及,但無損於其時僧團信衆對他的崇拜景仰。因此,他在世之時、圓寂前後都有聖化之迹,如戒賢夢見文殊囑咐傳法玄奘、天人送香等。有關玄奘聖化都記載在其傳記中,包括:道宣(596—667)《續高僧傳》的《玄奘傳》、冥詳《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下簡稱《行狀》)、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下簡稱《慈恩傳》),三者互有參考和補充之處。其中,在垂拱四年(688)成書的十卷本《慈恩傳》是最晚完成的,記敍玄奘的聖化也最爲詳盡。不過,由於在玄宗以前,上述傳記未能入藏流佈,使得玄奘的聖化記述晦而不顯。至玄宗朝,此書得以編入藏經,《開元釋教録·玄奘傳》有中宗追念玄奘的紀事,成爲肅宗在玄奘墓塔建興教寺的先聲。然而,一直到九世紀初年,對玄奘聖化的敍事和流佈仍然極爲有限。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大安國寺僧義林以神迹爲由,請修建傾圮的玄奘舊塔並得到許可,其後並建立塔銘。由於《玄奘塔銘》包含了他聖化的敍述,它的意義就不僅止玄奘在圓寂後一百七十五年終於得建塔銘紀念而已。中晚唐時期,也出現以玄奘之名宣揚的中國撰述經典(疑僞經典)如《大辯邪正經》、齋儀如十齋日、禮拜法如《十二月禮佛文》,以及和玄奘相關的深沙神信仰的流行,皆可反映玄奘聖化至此方浮顯於世。入宋以後,更出現一些聖化玄奘的宗教文物,如經藏院中供奉玄奘像、玄奘右手作“屈二指”的聖化圖像等。
本文主要探索唐代玄奘的聖化,包括唐代前期成書玄奘傳記中的聖化敍述,中宗、玄宗朝對玄奘的追念及其影響,中晚唐時期新出現的傳奇,以及藉玄奘之名宣揚的經典和齋儀,以追蹤其聖化之迹。
二 玄奘傳記的聖化敍述
玄奘西行三萬公里、去國十七年,取回大量的梵本經書、佛像舍利等文物。①2011年在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的玄奘展覽,名爲“天竺へ:三藏法師3万キロの旅”。當時人們崇仰他如神祇,他返回長安時,僧俗貴胄平民數十萬人皆爭睹這位傳奇人物“如值下生”。在玄奘圓寂前一年,李儼稱贊其“德鄰將聖”;在他遷化以後成書的傳記中亦有不少神格化記敍。玄奘傳記中聖化的敍述有下列幾項主要内容:印度戒賢論師夢見菩薩囑咐傳法玄奘、玄奘圓寂前後的各種徵應和異象,以及玄奘圓寂後,韋陀天現身告知玄奘已生至彌勒内院。前二者是各玄奘傳記都有的内容,只有詳略不同,至於最後一項則僅見於《慈恩傳》,這些記敍提供了其後中國和日本聖化玄奘的底本。
(一)玄奘在世時“聖”的形象
在玄奘有生之年,人們對他極爲崇仰,視他爲超凡的聖人,當他從印度求法取經返回長安時,前來迎接經像並瞻仰這位傳奇高僧的羣衆有數十萬人之多,對他仰之如佛。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玄奘圓寂,四月十五日葬於滻水之東白鹿原,長安僧俗爲他準備的葬具儀仗則是仿效佛涅槃的規格。
貞觀三年(629)四月,玄奘私自出訪印度;十七年之後,他在返程中抵達于闐時先行上表,行至沙州時再度上表太宗。當時太宗在洛陽,即命西京留守左僕射房玄齡安排迎接事宜。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抵達長安城西郊時,數十萬僧俗相趨前往申展禮敬,宛如迎接彌勒降生一般,可能見過這個場面的道宣有如下的記載:“道俗相趨,屯赴闐卲數十萬衆,如值下生。”右武候大將軍侯莫陳寔、雍州司馬李叔眘、長安縣令李乾祐等人前往迎接,由漕運進入宫城南面之西的都亭驛(在朱雀門外西街)。①《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119。《資治通鑑》卷二六〇唐昭宗乾寧二年五月胡三省注:“都亭驛,在朱雀門外西街,含光門北來第二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8470。二十七日,下令長安城各寺院安排帳輿、華幡等莊嚴儀具,翌日清晨在朱雀大街集合,以備載送經像到修德坊(在宫城之西第一坊)的弘福寺。何以有如此大規模的儀仗?係因玄奘帶回來的經典文物數量極爲可觀,有多達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的梵文經典,須用二十匹馬承載;此外,更有一百五十粒佛肉舍利和七尊高大珍貴的佛像等文物:
是日有司頒諸寺,具帳輿、花旙等,擬送經、像於弘福寺,人皆欣踊,各競莊嚴。翌日大會於朱雀街之南,凡數百件,部伍陳列。即以安置法師於西域所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留影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婆羅痆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宫下降寶階像,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陀國鷲峯山説《法華》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刻檀像等。又安置法師於西域所得大乘經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論一百九十二部,……凡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以二十疋馬負而至。
長安各寺院之所以準備“各競莊嚴,窮諸麗好,旙帳、幢蓋、寶案、寶轝”,①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26—127。爲的是莊嚴和供養佛寶的舍利和佛像、法寶的梵夾經典。
這支將經像從都亭驛運送至弘福寺的隊伍,既隆重又莊嚴。它包含數百件各色儀仗,以梵唄作爲前導,僧尼隨行護送,百官、士人、百姓都列在道旁,瞻仰禮拜佛舍利和莊嚴的佛像,燒香、散花供養,香霧繚繞,梵樂偈讚不絶。當時祥雲現天,宛若護送經像入寺:“其日衆人同見天有五色綺雲現於日北,宛轉當經、像之上,紛紛郁郁,周圓數里,若迎若送,至寺而微。”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頁128。當此之時,玄奘的聲望地位達到高峯,道宣形容時人對玄奘的崇仰是前所未見的:“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廢業,七衆歸承。當此一期,傾仰之高,終古罕類也。”①《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頁119。玄奘至洛陽謁見太宗,太宗本擬玄奘還俗以襄助國事,但玄奘堅決懇辭。其後,在太宗的支持下,玄奘傾全力投注在梵典的漢譯上。貞觀十九年(645)至二十二年,玄奘主持弘福寺譯場;貞觀二十二年十二月至高宗顯慶元年(656),玄奘入住新建大慈恩寺翻經院譯經。從永徽二年(651)開始,高宗擬從輔政舊臣一系奪回朝政主導權,在此政治風暴中,因玄奘是先朝國師,原先和太宗舊臣親近,因此處境日益艱困。顯慶二年至三年期間,高宗、武后駕幸洛陽,也帶着玄奘同行;顯慶三年回到長安,敕住西明寺,他離開了慈恩寺譯場,又無親近的弟子和譯經僧相隨,處境艱困,譯經工作近乎停頓。至顯慶四年,隨着高宗肅清輔政舊臣的行動接近尾聲,他所熟悉的舊臣或死或貶,幾無遺餘,玄奘爲了自保而請求去長安西北玉華寺譯經。他在偏遠僻靜的廢宫佛寺完成自己最重要的譯作《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道宣高度推崇此經的翻譯:“以顯慶五年正月元日,創翻大本,至龍朔三年十月末了,凡四處十六會説,總六百卷。般若空宗,此焉周盡。”②《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頁129。字下點爲筆者所加,下同。
玄奘在世之時,受到時人高度的景仰尊崇,在他去世的前一年——龍朔三年(663),李儼撰寫《道因法師碑》,便稱玄奘“德鄰將聖”。道因法師(587—658)曾參與玄奘的譯場,貞觀十九年六月,太宗自各地徵召名僧大德十二人至長安,益州多寶寺道因法師即爲其中之一。其後,道因應慧日寺主楷法師之請,在該寺講經,於顯慶三年圓寂,歸窆於成都彭門光化寺。至龍朔三年,慧日寺弟子玄凝等人建碑於寺,以表追思仰望之情,請中臺司藩大夫李儼撰文、歐陽通(歐陽詢之子)書碑。此碑敍及道因參與玄奘譯場,同時贊嘆玄奘的求法譯經功業:
奘法師道軼通賢,德鄰將聖。朅遊天竺,集梵文而爰止;旋謁皇京,奉綸言而再譯。以法師夙望,特所欽重,瑣義片詞,咸取刊證,斯文弗墜,我有其緣。①《金石萃編》卷五四《道因法師碑》,《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2),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1977年,頁913下。
李儼篤信釋教,親近名僧道世,先後爲他所撰述的《般若集注》、《法苑珠林》撰序。②李儼《金剛般若經集注序》,《廣弘明集》卷二二,《大正新修大藏經》(52),頁259下—260上;《法苑珠林序》,周叔迦、蘇晉仁《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1—2。他身處朝中,又曾爲和玄奘同年辭世的清河長公主(太宗之女)撰寫碑銘,對於高宗永徽之後玄奘的處境必定瞭然於胸。然而,他仍藉撰此碑標舉玄奘的功績兼頌其德,由此可知李儼對此一代高僧的崇仰欽敬。又,從道因法師碑的建立,也可反映玄奘晚年所受的抑制困頓,以及身後的寂寥。曾在玄奘譯場的道因歸葬西川,五年後弟子仍得以在長安慧日寺建碑紀念;於次年圓寂的玄奘則在一百七十五年後方有塔銘。
麟德元年(664)玄奘遷化,高宗對玄奘的葬事極其冷漠,且未有任何官員參加其葬禮,僅下令“玉華寺故大德玄奘法師葬日,宜聽京城僧尼造幢蓋送至墓所”。③《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〇,頁225。然而其時長安城的僧俗對於玄奘極爲尊崇景仰,比照佛涅槃之儀來準備葬送之具:
以四月十四日將葬滻東,都内僧尼及諸士庶共造殯送之儀,素蓋、旛幢、泥洹、帳轝、金棺、銀槨、娑羅樹等五百餘事,布之街衢,連雲接漢,悲笳悽挽,響帀穹宇,而京邑及諸州五百里内送者百萬餘人。雖復喪事華整,而法師神柩仍在籧篨本轝。東市絹行用繒綵三千疋結作涅槃轝,兼以華珮莊嚴,極爲殊妙,請安法師神柩。門徒等恐虧師素志,因止之。乃以法師三衣及國家所施百金之衲置以前行,籧篨轝次其後,觀者莫不流淚哽塞。是日,緇素宿於墓所者三萬餘人。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〇,頁226。
按:涅槃轝、金棺、銀槨、娑羅樹,都和釋迦牟尼佛涅槃葬儀有關。佛涅槃於娑羅樹下,而金棺、銀槨的葬具都是佛的葬儀規格,《大般涅槃經》敍述佛涅槃後,“諸力士以新淨綿及以細嗴纏如來身,然後内以金棺之中,其金棺内散以牛頭栴檀、香屑及諸妙華,即以金棺内銀棺中,又以銀棺内銅棺中,又以銅棺内鐵棺中,又以鐵棺置寶輿上”。②《大般涅槃經》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經》(1),頁206上。佛身置於金棺、銀槨,外覆銅、鐵棺,再放在寶輿上。
雖然東市絹行用繒綵三千疋做成“泥洹輿”,並且以鮮花和珠寶裝飾,請將玄奘靈柩安置於此輿送往葬所。然而,因玄奘生前囑咐後事務從儉約:“若無常後,汝等遣我宜從儉省,可以蘧蒢裹送,仍擇山澗僻處安置,勿近宫寺。不淨之身宜須屏遠。”③《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〇,頁218中。因此弟子遵從他的遺言,玄奘神柩僅安置於籧篨做成的車子。南宋佛教史家不查,仍記載玄奘以金棺銀槨入葬。④釋道法《佛祖統紀校注》卷三〇《慈恩宗教》:“用佛故事,以金棺銀槨葬於滻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659;《隆興編年通論》卷一三也有相同的記敍,《卍新纂續藏經》(75),頁175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葬送的行列中,以玄奘法師的三衣作爲前導,次則是太宗皇帝所賜的“百金之衲”,其後纔是置有玄奘遺體的籧篨車。因爲三衣袈裟是菩提上首,《悲華經》稱:“出家著袈裟者,皆得授記不退三乘”,⑤《大正新修大藏經》(3),頁219下。而百金之衲是玄奘葬事中惟一來自皇帝的供養,顯示出太宗對玄奘譯經事業的護持之功。貞觀二十二年,太宗曾經賜給玄奘一件花了數年製作、價值百金的袈裟,當時在場的另外一名僧人道恭作詩詠此袈裟云:“福田資像德,聖種理幽薰。不持金作縷,還用綵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綺相氛氳。獨有離離葉,恒向稻畦分。”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頁151。可見此衣多彩,朱青交錯。袈裟上面的條紋有若田疇,可生功德,爲世間的福田,故又名“福田衣”。十四世紀日本的繪卷“玄奘三藏繪”中,玄奘即使在西行求法的過程中,都不作行腳僧裝扮,而是身穿着紅色的袈裟,②塜本善隆《玄奘三藏繪》,野村卓美《解脱房貞慶と『玄奘三蔵絵』——貞慶作『中宗報恩講式』をめぐって》,《文藝論叢》第73號(2009),頁6—9。其實是有淵源的。
(二)戒賢之夢——菩薩的聖授傳法
玄奘遠訪天竺主要的目的是研究《瑜伽師地論》以解決衆疑,爲此他至摩揭陀國那爛陀寺的求教於尸羅跋陀羅(漢譯“戒賢”)論師,時人尊稱爲“正法藏”。玄奘傳記都稱:在他到訪的三年前,戒賢在夢中得到文殊菩薩指示,囑咐他傳授《瑜伽論》予支那國僧人,玄奘的到訪,證實了菩薩的授記。此一傳奇聖化了玄奘,使得他在佛教界的地位大爲提升。
關於戒賢的夢,玄奘各傳記敍詳略不一,而以《慈恩傳》最爲詳細,略述如下:玄奘至印度王舍城那爛陀寺參訪高齡一百零六歲的戒賢論師,③玄奘初訪戒賢論師的時間不詳。請求向他學習《瑜伽論》時,戒賢激動地落淚,命其侄兒覺賢告訴玄奘緣由。原來,戒賢先前曾爲疾病所苦長達二十年,三年前,他因病苦不欲生,意圖絶食求死。當晚,夢見黄金色、琉璃色和白銀色的三位天人,分别是文殊菩薩、觀世音菩薩、彌勒菩薩。彌勒菩薩告以若能廣傳正法,將來得以生至兜率天。文殊菩薩指出:由於戒賢前世爲國王身時,做了很多惱害百姓的事,所以有此病苦的報應。教示戒賢至誠懺悔,宣揚經論,自然得以消除病苦,並且囑他傳法予將來到訪的玄奘:“當依我語,顯揚正法《瑜伽論》等,遍及未聞,汝身即漸安隱,勿憂不差。有支那國僧樂通大法,欲就汝學,汝可待教之。”戒賢恭敬地答應了,自此之後,他的病竟然痊癒了。三年之後,終於等到玄奘到來。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頁67。《續高僧傳·玄奘傳》和《行狀》都僅提及金色天人的文殊菩薩,《續高僧傳》最爲簡約:“有支那僧來此學問,已在道中,三年應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吾是曼殊室利,故來相勸。”玄奘聽了覺賢的敍述“悲喜交集,禮謝訖”。《行狀》則和此内容相近,惟略爲詳細。②《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頁111;《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大正新修大藏經》(50),頁216上—中。
《行狀》、《慈恩傳》都認爲此是文殊菩薩的傳法印記,《行狀》在此段文字之後稱“法師親承斯記,悲喜不能自勝,更起禮謝”。③《大正新修大藏經》(50),頁216中。《慈恩傳》則説得更明白:
法師得親承斯記,悲喜不能自勝,更禮謝曰:“若如所説,玄奘當盡力聽習,願尊慈悲攝受教誨。”法藏又問曰:“法師汝在路幾年?”答:“三年。”既與昔夢符同,種種誨喻令法師歡喜,以申師弟之情。④《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頁68。
道宣在《玄奘傳》之末,稱贊玄奘的德業功績亦云:“若非天挺英靈,生知聖授,何能振斯鴻緒,導達遺蹤。”⑤《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頁131。此一“生知聖授”即指上述戒賢夢中菩薩囑咐的傳法授記。
鐫刻於唐文宗開成四年(839)的劉軻撰《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并序》中,將上述三菩薩囑咐戒賢傳法玄奘的傳奇簡化如下:
惟至中印度那爛陀寺,寺遣下座廿人明詳儀注者,引參“正法藏”,即戒賢法師也。既入謁,肘膝著地,足已,然後起。法藏訊所從來,曰:“自支那,欲依師學《瑜伽論》。”法藏聞則涕泗曰:“解我三年前夢金人之説,佇爾久矣。”①《全唐文》卷七四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7年,頁7682下;《金石萃編》卷一一三《玄奘塔銘》,頁2033上。
敦煌文獻S.6631中有署名“釋利濟”的僧人撰寫《唐三藏讚》,也提到了此一傳奇。此文用極簡的文字敍述玄奘的出身、出家、西行求法、戒賢受菩薩囑咐傳法,在印度弘法辯論無所匹敵,歸國譯經,乃至圓寂後上生彌勒淨土:
嵩山秀氣,河水英靈。捷特瑰傳,脱履塵榮。鄉園東望,竺國西傾。
心存寶偈,志切金經。戒賢忍死,邪賊逃形。彌勒期契,觀音願成。
辯論无當,慈悲有情。一生激節,万代流名。②黄永武編《敦煌寶藏》(49),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1—1986年,頁512上—下。
此讚用“戒賢忍死”以待玄奘之到來,概括戒賢傳法聖授的傳奇。這種描述也爲其後佛教界沿用,《佛祖統紀》中的《慈恩宗教》亦用此語:“遂學法相於戒賢,傳唯識宗。賢時年一百三歲,蒙文殊付托,忍死以遲奘。”③《佛祖統紀校記》卷三〇,頁660。
遼代僧人非濁所撰《三寶感應要略録》一書,則在敍述戒賢之夢的傳奇之餘,進一步宣告玄奘授記成聖。此書約在宋仁宗嘉祐八年即遼道宗清寧九年(1063)成書,④據推測《三寶感應要略録》的成書年代應在1 0 6 3年前。近年來,有學者從此書的文字等原因考察,推測它可能是平安時期中期在日本的撰述,見金偉、吴彦《『三寶感應要略録』の撰者について》,《文藝論叢》(京都,大谷大學文藝學會)第7 5號,頁1 8—3 3。由於還未有更實際的證據,本文仍維持此書爲非濁所撰。邵穎濤認爲此書成書約在清寧七年或八年間,見《遼僧非濁〈三寶感應要略録〉研究》,收入怡學主编,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编《遼金佛教研究》,北京,金城出版社,2 0 1 2年,頁1 8 1。卷中《戒賢論師蒙三菩薩誨示感應》一則,即敍述戒賢夢中三天人的傳法印記,原先在《慈恩傳》以“僧衆聞者,莫不稱嘆希有”作爲此段敍事的結語。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三,頁67。《三寶感應要略録》另加上一句:“僧衆聞者,莫不稱嘆希有,玄奘可聖記矣。”②《三寶感應要略録》,《大正新修大藏經》(51),頁851中—下。“聖記”是指玄奘已受佛授記成聖。③吉藏撰《法華義疏》卷八《授記品》:“今云:修佛因得佛果,即是有果可記,故名爲記。聖記示人,稱爲授記也。”《大正新修大藏經》(34),頁565下。其後,此書東傳日本,對約在1120—1140年間成書的《今昔物語》有很大的影響;④李銘敬《日本『三寶感應要略録』受容》,《中國古典研究》第50號,頁11,13。如《今昔物語》有“玄奘三藏赴天竺傳法歸來”一則,稱:“前此中國唐王朝第三代時,有位叫做玄奘的聖人,在前往天竺途中……”⑤山田孝雄、山田忠雄、山田英雄、山田俊雄校注《今昔物語集》二,卷六,東京,岩波書店,1960年,頁430。鎌倉時代法相宗僧人主導了玄奘的聖化,而《今昔物語》的編者正是法相宗近旁的人,⑥原田信之《今昔物語集南都成立の唯識學》,東京都,勉誠出版,2005年,頁106。因此,可知此書在日本玄奘聖化的歷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
關於戒賢之夢的傳奇,也出現在其他鎌倉時代的文本中,將另文討論。
(三)圓寂前後的徵應和異象
高僧臨終前後的敍述是僧傳敍述的重點之一,如《高僧傳》本傳二百五十七人中,九十人有相關的記述;《續高僧傳》正傳四百八十五人中,有二百七十人敍及此事,包括預知死期(如和門人寺僧辭别、交代葬法、分配財物)、辭世後遺體的變化、得道的感應瑞徵。①岡本天晴《僧伝にみえる臨終の前後》,《日本佛教學會年報》第46號,頁443—455。玄奘傳記幾乎包含了以上所有臨終敍事的項目,而圓寂前後的徵應和異象,更遠較其他高僧爲多,此處僅敍爲後人徵引較多的四項:玄奘自稱得生彌勒淨域、慈恩寺僧明慧見到如佛涅槃時的光虹、玄奘去世後天人獻香、韋陀天告知玄奘生至覩史多天内院。
1.玄奘自言得生彌勒淨域
有些高僧在臨終前會告知弟子其所得的果位,如隋代智顗(538—597)稱他得到“五品内位”(即天台圓行八個行位中的第五品),②灌頂《隋天台智者大師别傳》,《大正新修大藏經》(50),頁196中。玄奘則自稱得以生至彌勒内院。
玄奘所修行的唯識學瑜伽學派的祖師是彌勒菩薩,玄奘至印度師事戒賢也是祈求往生彌勒淨域,因此玄奘畢生修習的目標,即是求往生彌勒菩薩所居的兜率天。吉村誠指出:玄奘一生所造的佛像都和彌勒信仰有關,如他“造俱胝畫像、彌勒像各一千幀”,以及在臨終前數日命塑工宋法智於嘉壽殿造菩提像,菩提像是釋迦牟尼成道時降魔之像,而彌勒菩薩是最早造此像者。③吉村誠《玄奘の彌勒信仰について》,《日本佛教學會年報》第70號,頁51—53。又,麟德元年(664)正月二十三日,臥疾的玄奘自作偈言:“南無彌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顔,南無彌勒如來所居内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並且教身旁弟子念誦,以求生兜率内院。二月五日,陪侍身旁的弟子普光即大乘光(627—683)等人問玄奘“和尚決定得生彌勒内院不?”玄奘回答:“得生。”④《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〇,頁221,222;《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頁219下;《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頁130。從此時起,氣息漸微弱以至入於寂滅。彌勒菩薩蒙釋迦牟尼佛授記爲未來佛,現在居於兜率天(又作“覩史多天”),此天分内院和外院,内院爲補處菩薩的住處,彌勒菩薩在此説法,在此修行圓滿,便可成佛。外院則有諸多享樂,會耽誤或妨害往生者至内院修習。因此,玄奘偈言稱捨命之後必生“南無彌勒如來所居内衆”。
2.慈恩寺的虹光
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玄奘於玉華寺圓寂之際,在長安慈恩寺的僧人明慧夜半經行念誦,仰頭看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到南,直至慈恩塔院。坊川玉華寺(今陝西銅川市北四十二公里)在長安以北約百餘公里處;又,慈恩寺塔對玄奘而言有特殊意義,永徽二年(651)玄奘啓請建立浮屠“雁塔”以收藏從印度帶回來梵本經典。因此,明慧直覺地認爲此一天象恐是玄奘圓寂的徵應:“往昔如來滅度,有白虹十二道從西方直貫太微,於是大聖遷化。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無常事耶?”至九日,玄奘去世的消息就傳到長安了。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〇,頁223。按:唐代佛教文獻中引《周書異記》,稱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五色虹光入貫太微,是西方聖人釋迦牟尼出生的瑞應:“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水溢出,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太史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一千年外聲教及此。’昭王即敕鐫石記之,埋於南郊天祠前。此即佛生之時也。”②道宣《釋迦方誌》卷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01;《廣弘明集》卷一一,《大正新修大藏經》(52),頁163上。慈恩寺僧明慧則將虹貫太微解釋爲是釋迦入滅的徵兆,猜測在北方玉華寺譯經的玄奘恐有不測。雖然此種記述不合常理,但它無疑是作爲聖化玄奘的一個傳奇,後代佛家史家也未有所質疑。
贊寧(919—1001)在《宋高僧傳·明慧傳》中,收録此一傳奇,認爲是明慧讀誦的感應,故在卷二五《讀誦篇》的論贊中有“明慧行道,占虹氣之貫天”之語。①《宋高僧傳》卷二四《唐京兆大慈恩寺明慧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611;卷二五《讀誦篇》論曰,頁648。此則傳奇將以虹光的天象,將玄奘的圓寂比擬佛陀的涅槃,以此聖化了玄奘。
3.天人獻香
《慈恩傳》敍述玄奘圓寂後一個多月,有人送來栴檀末香,請依印度之法,將它塗在玄奘身上,弟子不許。此人自稱奉有聖旨“别奉進止”,弟子不得已乃開棺,發現玄奘面目如生,而且散發如蓮花般的特殊香氣。待塗香重新入斂之後,送香來者突然失去蹤影,衆人猜想送香者可能是位天人。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〇,頁232。《開元釋教録》、《貞元新定釋教録》也都記敍此一天人送香的故事。③《開元釋教録》卷八,《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561中;《貞元新定釋教目録》卷一二,《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861中—下。《隆興編年通論》認爲此人應是來自兜率内院的聖者:“識者以爲兜率内院人也。”④《隆興編年通論》卷一三,頁175上。
4.經久面貌如生
不少的高僧辭世之後,面色遺體均没有變化,甚至不會敗壞,玄奘的傳記也都有此類的記述。《行狀》稱他去世六十天之後,顔色如生,還散發香氣,甚至長出新髮:“時經六十日,頭髮漸生,顔色如常,赤白不異。又有香,了無餘氣。”《續高僧傳》係根據《行狀》記載:“迄今兩月,色貌如常,又有冥應,略故不述。”總章二年(669),高宗敕令將玄奘改葬少陵原,再起出玄奘棺木遺體“經久埋瘞,色相如初,自非願力所持,焉能致此?”《慈恩傳》則稱“過七日竟無改變,亦無異氣。自非定慧莊嚴,戒香資被,孰能致此?”①《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頁219下;《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頁130;《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〇,頁222。以上關於玄奘遺體没有變化的描述,也被視爲其修行證果的表徵之一。
(四)韋陀天示知玄奘生至彌勒淨土
在玄奘的傳記中,僅有《慈恩傳》記述韋陀天告知玄奘生至彌勒内院之事,這是玄奘聖化傳奇中最强而有力的宣言。
西明寺上座道宣律師有感通能力,乾封年間,有位自稱“韋將軍諸天之子”(韋陀天)的神人現身,指正道宣制定、決疑戒律若干謬誤偏差之處。道宣便趁此機緣詢問古來傳法高僧德位高下,神人回答如下:
神答云:“自古諸師解行互有短長而不一準,且如奘師一人,九生已來,備修福慧,生生之中,多聞博洽,聰慧辯才,於贍部洲支那國常爲第一,福德亦然。其所翻譯,文質相兼,無違梵本。由善業力,今見生覩史多天慈氏内衆,聞法悟解,更不來人間受生。”神授語訖,辭别而還。宣因録入别記,見在西明寺藏矣。據此而言,自非法師高才懿德,乃神明知之,豈凡情所測度。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〇,頁224。
韋陀天的話語中,對玄奘推崇備至,稱他累世多聞博學、解行相儔,兼以福慧兼修,更重要的是肯定玄奘的佛典漢譯,傳達了玄奘證果成聖的訊息。“覩史多天”即彌勒所居的兜率天,玄奘生至彌勒菩薩説法的内院,得以“聞法信解,更不來人間。既從彌勒問法,悟解得聖”。上文稱道宣將此事記載下來,藏在西明寺。道宣性好感通事迹,撰述三本感通的著作:《道宣律師感通録》和《集神州三寶感通録》二書於麟德元年(664)完成,《律相感通傳》作於乾封二年(667),都係他終南山修習時所作。其中,僅《律相感通傳》提及韋將軍(即韋陀天)現身之事,①道宣《律相感通傳》,《大正新修大藏經》(45),頁881下—882上。道宣另有《道宣律師感通録》,題爲“麟德元年終南山釋道宣撰”,内容和《律相感通傳》相近。《大正新修大藏經》(52),頁435上。但未有上述韋陀天告知玄奘生覩史多天的記載。
以上玄奘聖化的諸種傳奇之中,戒賢的夢中菩薩傳法印記、韋陀天宣告玄奘生至彌勒淨土二事,普遍爲日本鎌倉時代聖化玄奘的各種文本所采用。至於中國則僅傳述戒賢之夢,而不談韋陀天的證辭。
三 開元以後對玄奘的追念
高宗朝以後,玄奘似是不能明言的禁忌,至玄宗時方予以解禁。玄宗初年建《西明寺塔碑》,首露解禁的端倪,至智昇編《開元釋教録》時更將《慈恩傳》入藏流通。又,此經録《玄奘傳》揭露中宗曾爲玄奘弟子,以及追謚紀念之事,實爲肅宗朝在玄奘墓塔建“興教寺”之先聲。
最终纳入研究的对照组40例患儿年龄为1.5-11.0岁,平均年龄为(3.21±0.52)岁,其病程为1个月-3个月,平均病程为(2.35±0.31)个月,患儿中男女分别为18例和22例。观察组40例患儿年龄为1.5-12.0岁,平均年龄为(3.43±0.51)岁,其病程为1个月-4个月,平均病程为(2.42±0.33)个月,患儿中男女分别为19例和21例。两组患儿的基本情况比较均无显著差异(P>0.05),故组间可实施对比。
(一)玄宗與《西明寺塔碑》
開元四年(716)建立《西明寺塔碑》,可視爲玄宗對玄奘解禁之始。西明寺係顯慶元年(656)高宗因太子李弘病癒、爲報佛恩而建造的,由玄奘度地規畫,於顯慶三年六月完工,但未建寺碑。玄宗何以在西明寺落成近六十年之後始建立寺碑?一則是玄宗係李弘(652—675)的繼祧嗣子有關,二則是擬突顯西明寺的建立和玄奘的關係,並以此尊崇玄奘,此二者皆和高宗朝以後的政局有關。
以下略述此一時期政局的變化,方得以顯示此碑建立的時間和意義。玄奘在永徽六年(655)以後被政治風暴所波及,此乃因年輕的高宗欲從輔政大臣一系中奪回政治上的主導權,而當時武后是他重要的輔佐。在此之後唐室政治的發展是武氏掌權,其後更稱帝建立武周政權,因李唐皇室、朝廷大臣未附從,故以酷吏剪除皇室子弟,以及誣陷大臣。神龍元年(705),張柬之、崔玄暐聯合羽林將軍桓彦範、李多祚等人逼武則天退位,擁中宗李顯登基。中宗曾下令安葬那些爲武后及其酷吏所枉殺寃屈者,並且恢復其官爵。然而,中宗時仍受掣於武三思、上官婉兒,未能畢竟其功。其時,朝政爲韋后、安樂公主、武三思和安樂公主之婿武崇訓所把持,神龍三年太子李重俊不堪侵侮,與兵部尚書魏元忠、成王李千里(太宗之孫)、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合謀,斬殺武三思、武崇訓,未及誅除韋后和安樂公主。因中宗對羽林軍喊話,羽林軍倒戈,政變失敗,李重俊、成王千里皆死於此役,習稱“重俊之變”。景龍四年(710)中宗駕崩,韋后立李重茂爲帝(少帝),改元唐隆,自己臨朝聽政,以韋氏家族掌南北衙軍,擬自居帝位。臨淄王李隆基(李旦之子)與太平公主以禁軍攻入宫城,殺韋太后、安樂公主、上官婉兒及諸韋子弟。少帝退位,擁立相王李旦爲帝,是爲睿宗,此役稱爲“唐隆之變”。睿宗以李隆基爲太子。景雲二年(711),睿宗命太子監國,次年退位,太子即位,是爲玄宗,改元先天。先天二年(713),據稱在“唐隆之變”有功的太平公主,謀起兵奪權,玄宗先發制人遣兵擒獲太平公主,賜死於家,是爲“先天之變”。此年改元開元,至此玄宗方得以無所掣肘,下啓開元治世。
如上所述,中宗未能成功地爲武后稱帝以來受酷吏之害者昭雪,至玄宗之世方能畢其功。中宗神龍元年,下令追奪垂拱以降枉濫殺人的丘神勣、來俊臣、來子珣、周興等二十三人的官爵;玄宗開元二年二月五日,更進一步敕令上述二十三人“殘害宗枝、毒害良善”,其子孫不許仕宦;至於陳嘉言、魚承曄、皇甫文備、傅遊藝四人情狀較輕者,子孫不許近任。①《舊唐書》卷五〇《刑法志》:“中宗神龍元年,制以故司僕少卿徐有功,執法平恕,追贈越州都督,特授一子官。又以丘神勣、來子珣、萬國俊、周興、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嘉言、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二十三人,自垂拱已來,並枉濫殺人,所有官爵,並令追奪。”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2149;卷七《中宗紀》,頁137;卷八《玄宗紀上》,頁187;卷一八六上《酷吏傳上·來俊臣》,頁4841。同樣地,對於其時遇難的皇室宗族和大臣加以改葬、復姓、恢復官爵之舉,也經歷過中宗、玄宗朝兩個階段。以太宗第八子越王李貞(627—688)爲例,武則天稱帝,垂拱四年(688),李貞和宗室多人擬起兵勤王,但最後付諸行動的僅有李貞及其子琅邪王李沖、女婿黄守德,事敗皆死。此外,因此事件者被誅或迫脅自殺、貶死的皇室成員包括:常樂公主(高祖十九女)、韓王元嘉(618—688,高祖十一子)、魯王靈夔(?—688,高祖十九子)、霍王元軌(622—688,高祖十四子)等。②《舊唐書》卷六四《霍王元軌傳》,頁2430。神龍元年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請恢復李貞和李沖的官爵,但武三思令昭容上官氏代中宗手詔不許,僅恢復其族姓。至開元四年(715),玄宗備禮改葬二人,復其爵土。開元五年,玄宗想起越王貞死非其罪,以許王子李琳爲其繼嗣,將其神主祔於太廟。③《舊唐書》卷七六《越王貞傳》,頁2664。雖然垂拱以後的制敕已不傳,無由得知玄奘是以何種形式被禁錮,然以上例爲對照,當可推知:對玄奘的解禁亦復先經過中宗朝的私下的追謚和紀念,至玄宗朝纔漸次解其禁。
高宗和武則天的四個兒子依次爲“孝敬皇帝”李弘(652—675)、“章懷太子”李賢(654—684)、中宗李顯(656—710)、睿宗李旦(662—716);太子李弘早逝,武后令李旦之三子李隆基爲其嗣子。關於李弘的死因,《新唐書》、《資治通鑑》和宋人的記載,皆稱他因觸怒武后,高宗上元二年(675)從幸合璧宫遇酖而死。然自司馬光《通鑑考異》以下頗有疑此説者,難以斷言。①《新唐書》卷七六《后妃傳上·高宗則天武皇后》,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3477;卷八一《高宗諸子傳·孝敬皇帝弘》,頁3589;《資治通鑑》卷二〇二唐高宗上元二年四月,頁6377。不尋常的是,在他去世後十餘年,武后方命李旦之子李隆基繼其嗣。②武后命李隆基爲李弘的嗣子的時間有二説,《舊唐書》稱係武后長壽中(692—694),《新唐書》記載則在武后永昌初(689)。見《舊唐書》卷八六《高宗中宗諸子傳·孝敬皇帝弘》,頁2830;《新唐書》卷八一《高宗諸子傳·孝敬皇帝弘》,頁3590。又,若比較其弟中宗、睿宗和其嗣子玄宗對李弘和李賢的祭祀追謚,顯見他們對李弘未能登帝位有更深的惋惜和遺憾。按李賢是政治受難者,高宗調露二年(680),因武后信賴的術士明崇儼爲强盜所殺,懷疑是太子賢所爲,先是將他貶爲庶人。開耀元年(681),復貶到巴州。光宅元年(684)武后稱帝後,派左金吾將軍丘神勣到巴州去監看,丘卻逼他自殺,武則天追封爲雍王,貶丘神勣爲疊州刺史。中宗即位後,迎回李賢的靈柩,陪葬於乾陵。睿宗登基後,追贈李賢爲太子,謚“章懷”。③《舊唐書》卷八六《高宗中宗諸子傳·章懷太子賢》,頁2832;《新唐書》卷八一《高宗諸子傳·章懷太子賢》,頁3591。關於李弘的祭祀,中宗先是將他祔於太廟,號爲“義宗”;因姚崇、宋璟上言李弘未曾即帝位,不宜與先帝同列太廟。睿宗景雲元年(710),另在東都從善里立廟祭祀。開元四年,玄宗在東都來庭縣廨另建義宗廟,《西明寺塔碑》也正是在這一年樹立的。其後,因韋湊(659—724)上言“義宗”之號不合祀典,故改爲其本謚“孝敬皇帝”。④《舊唐書》卷七《中宗紀》,頁140;卷七《睿宗紀》,頁156;卷八《玄宗紀上》,頁180;卷二五《禮儀志五》,頁948—949,951。也就是“義宗”的廟號從中宗時期一直持續到玄宗初年。比較中宗、睿宗對李弘的祭祀追謚,似較李賢更爲隆重,是否在憐其早逝之餘,更同情他遭遇非常之死?
西明寺係爲李弘病癒祈福所建的寺院,它創建之初係由玄奘度地規畫,又顯慶三年(658)七月至顯慶四年十月,玄奘曾居於此寺,但在此期間他未有寺職,且無親近弟子隨侍陪同,亦無法在此寺譯經,拙文曾以“無形的牢籠”形容他的處境。玄宗李隆基即位後四年,在西明寺立碑以申對其伯父的追思紀念之意,然就碑文的内容,則顯示對玄奘的敬意尊崇,並且隱含對他的同情。
《西明寺塔碑》可以説是西明寺最重要的資料,也是非正式的玄奘的紀念碑。其内容主要是敍述此寺建造的原委、規建者、營建者,以及落成時入住的僧人的名字,反而少敍及開元時期此寺的情況,可見它要凸顯的是西明寺的建立和玄奘的關係,在此碑中並且稱玄奘爲證果的羅漢。
此碑由蘇頲(670—727)撰文,他是中宗以來唐室最倚重的文翰,在玄宗朝曾爲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①柯卓英、岳連建《蘇頲生平事迹考論》,《唐都學刊》1998年第3期,頁36。《資治通鑑》卷二一一唐玄宗開元五年十月,頁6730。又爲開元年間去世的兩位公主撰寫碑銘——《高安長公主碑》和《唐涼國長公主碑》,後者並且由玄宗親自書寫上石,②陳思纂輯《寶刻叢編》卷八《唐高安長公主碑》,《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24),頁18240下;《金石録》卷二六《唐涼國長公主碑》,《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12),頁8953上—下。按:開元二年(714),唐高宗李治的次女高安長公主(649—714)逝世;開元十二年,睿宗女高涼國長公主(687—724)辭世。凡此皆足以顯示皇帝對他的倚重。蘇氏辭采駢美,爲當世所重,兼長於佛理,中宗景龍年間被任命爲義淨譯場的“翻經學士”,亦常爲高僧名寺撰寫碑銘,如《龍門天竺寺碑》。③義淨譯《根本説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經》(24),頁419中;蘇頲《唐河南龍門天竺寺碑》,《全唐文》卷二五七,頁2600下—2602上。《西明寺碑》應是玄宗命他撰寫的。此碑首先敍述佛教之旨,次則説明西明寺建造的緣起,係爲李弘病癒而造者。三則説明此寺規畫者爲玄奘,由將作少監沈謙之興造,並且描繪頌揚此寺莊嚴廣大,裝飾弘麗。四則敍述落成之時寺院的供給、首批進駐西明寺僧人的姓名,以及三綱的名銜法號:
遂賜田園百頃,淨人百房,車五十兩,絹布二千疋。徵海内大德高僧,有毗羅、靜念、滿顥、廣説、鵬耆、辯了、鶖子、知會,凡五十人。廣京師行業童子,有空淨聞道、善思喜法、須迦分施、撰擇不染者,凡一百五十人。導天衢,指天寺,上御安福觀以遣之。……若普聞名稱,時立威儀,行則上首,舉爲左臂者,上座道宣、寺主神察(泰)、都維那智衍、子立、傳學、元則、棲禪、靜定、持律、道成、懷素等人。法師舍衛是求,須彌不動,以等空知,行如海法,如陶器必盡,而寫瓶共縛。今大律師崇業,約身利物,……上座大德神岳法師,開方便品,……①蘇頲《唐長安西明寺塔碑》,《全唐文》卷二五七,頁2597下—2598上。
此寺畢工之時,徵召海内大德高僧五十人;從京師之内簡擇行業童子一百五十人入住,上文列舉了八名高僧的名號,皆不見佛教史傳的記載。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〇僅記“大德五十人、侍者各一人,後更令詮試業行童子一百五十人”,無任何僧人的姓名。頁215。又列西明寺最初的三綱和重要僧人之名“上座道宣、寺主神泰、都維那智衍、子立、傳學、元則、棲禪、靜定、持律、道成、懷素等人”,除了上座道宣、寺主神泰之外,③《佛祖統紀校注》卷四〇:“顯慶二年,敕建西明寺,大殿十三所,樓臺廊廡四千區。詔道宣律師爲上座,神泰法師爲寺主,懷素爲維那。”頁921—922。皆不見於他處記載,可以補充史傳之不足,彌足珍貴。但此寺落成時,其規畫者玄奘卻受到冷落,《慈恩傳》稱高宗“敕遣西明寺給法師上房一口,新度沙彌十人充弟子”。④《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〇,頁215;並見拙文《玄奘的最後十年》,頁53—56。此碑也暗示此時玄奘未有任何寺職,專意於佛法修持的情況:“法師舍衛是求,須彌不動,以等空知,行如海法,如陶器必盡,而寫瓶共縛。”
在敍述西明寺落成時寺院僧人的情況之後,略過從顯慶三年至開元四年之間的歷史,直述開元初年時寺主和上座二人“今大律師崇業,約身利物,……上座大德神岳法師,……”。相較於前面詳述此寺落成之時的寺職、大德的名字,由此可見,此碑主要的目的在於紀述西明寺落成之事。又,此碑另一用意是在標舉褒揚玄奘,稱他是證果的羅漢:“先是,三藏法師玄奘惟應真乎,迺成果者。首命視延袤,財廣輪。往以繩度,還而墨順。”另外,在文末頌詞中也將玄奘比擬爲迦葉,將太子李弘喻爲佛典中精勤修習佛法的德光太子:“惟聖皇之經始兮,惟調御之依止。封迦葉之上人兮,延德光之太子。香爲土兮金爲界,樹低枝兮蓮出水。”①蘇頲《唐長安西明寺塔碑》,頁2597下,2598下。此寺乃因李弘病癒祈福而造,李弘良善有德,仿若佛經中統治閻浮利天下的頞真無國王太子德光,修行不放逸。②竺法護譯《佛説德光太子經》,《大正新修大藏經》(52),頁414上—418下。可見作爲李弘的嗣子的玄宗也有藉此紀念李弘之意。
《西明寺碑》可以視爲對玄奘解禁之始,此碑的内容公開記述經始西明寺、乃至於寺院落成後,他並無寺職的狀況,也無昔日弟子追隨近侍被架空之事,似有意突顯高宗時期西明寺創建的歷史,同時尊崇並且聖化了玄奘。
(二)《開元釋教録·玄奘傳》的新内容
開元十八年(730)成書的《開元釋教録》,正式將《慈恩傳》納入藏經流通。又,此録中《玄奘傳》增加了先前未有的新内容:中宗爲玄奘弟子號“佛光王”,以及中宗私下追念玄奘的三件事,這是今見最早的記載,可以視爲繼《西明寺塔碑》後更進一步對玄奘的解禁。中宗追念玄奘之事分别是:在長安和洛陽各建一所佛光寺,將宫中所藏的玄奘畫像送到慈恩寺翻經堂中,追謚玄奘“大遍覺”。
1.《慈恩傳》的入藏
《慈恩傳》係以弘化釋教和護持佛法的名義,被編入《開元釋教録》的;卷一三將《慈恩傳》歸入“此方撰述集”的條目,與梁釋僧祐《釋迦譜》、唐道宣《釋迦氏略譜》等四十部書並列,其後説明諸書皆是有助釋氏教化和護法之作:
《釋迦譜》下四十部,合三百六十八卷,並是此方賢德撰集。然於大法裨助光揚,季代維持,寔爲綱要,故編此録,繕佈流行。若寫藏經,隨情取捨,諸餘傳記,雖涉釋宗,非護法者此中不録。①《開元釋教録》卷八,頁624上—625中。
上文中特别强調這些書是護法之作,在此後又列《漢法本内傳》五卷、《沙門法琳傳》(又稱《法琳别傳》)三卷,稱“右二部傳,明敕禁斷,不許流行,故不編載”。②《開元釋教録》卷八,頁625中;《開元釋教録略出》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746中。由此可知《慈恩傳》的入藏顯然也是得到許可的。至於《沙門法琳傳》,據貞元十六年(800)成書的《貞元新定釋教目録》,方得以入藏;在此録中對於《沙門法琳傳》的入藏的原委,留下了記録,卷二三稱此書“明敕禁斷,不許流行,故不編載。今詳此意,蓋在一時,然不入格文,望許編入《貞元目録》”。③《貞元新定釋教目録》卷二三,《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959中。此當係智昇在編寫的過程中的期許,其後透過左右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馬承倩上奏,請准將《大佛名經》、《法琳别傳》、《續開元釋教録》編入附録,而得到許可。此書卷首稱特承恩旨入録者有三:“古新譯《華嚴經》一、三朝翻譯經律論二、《大佛名經》一部等三,斯皆特降絲綸,許編目録。”亦附有貞元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牒功德使敕許之文。①《貞元新定釋教目録》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771中,774上。
2.唐史上的“佛光王”與大内“佛光寺”
《開元釋教録·玄奘傳》記載了中宗李顯出生滿月時即從玄奘剃髮出家,爲“佛光王”。此事僅見於《慈恩傳》,《續高僧傳》、《行狀》未有記録。《開元録》不僅記此事,且稱“其‘佛光王’即中宗孝和皇帝初生之瑞號也”:
其“佛光王”即中宗孝和皇帝初生之瑞號也。創登皇極,敕爲法師於兩京各置一佛光寺,並度人居之,其東都佛光寺即法師之故宅也。復内出畫影,裝之寶輿,送慈恩寺翻譯堂中,追謚法師稱“大遍覺”。②《開元釋教録》卷八,頁560中。
中宗登基以後,在長安、洛陽的宫城内各設一所佛光寺,東都洛陽的佛光寺就是顯慶二年(657)玄奘隨高宗武后至東都時居住的積翠宫,③拙文《玄奘的最後十年》,頁46。《新唐書》卷三四《五行志一》:開元十八年“十月乙丑,東都宫佛光寺火”。頁885;《舊唐書》卷九《玄宗紀下》則作:開元二十八年十月乙酉“東都新殿後佛光寺災”。頁213。長安的佛光寺在西内神龍殿之西,又稱“佛光殿”。④宋敏求《長安志》卷六《宫室四》:“西内南面有六門,右曰安仁門,内有安仁殿,在甘露殿西。乾化門内佛光寺,在神龍殿西。”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02。《開元釋教録》皆云“大内佛光殿”。以“佛光”爲名應是紀念其師玄奘,並且彰顯和他的關聯。雖然在長安、洛陽皆有紀念玄奘的佛光寺,但皆位於宫城之内,多少意味着其時中宗紀念玄奘也不能公然昭示天下。自此之後,宫内的佛光寺(佛光殿)成爲皇帝的内道場,如長安慈悲寺義紭法師曾奉詔“於内道場佛光殿轉經行道”。⑤蔡景《述二大德道行記》,《全唐文》卷三九八,頁4066下。
中宗並且在長安宫内的佛光寺開譯《大寶積經》,完成他未竟之功,以紀念玄奘。龍朔三年(663)十月,玄奘譯畢六百卷的《大般若經》;次年麟德元年(664)正月,譯經僧和玉華寺僧人請他翻譯《大寶積經》。由於此經部帙龐大,他想到有“寶積之功不謝於般若”,有生之年可能無法畢功,僅譯了四行就停筆了。神龍二年(706),中宗命菩提流志翻譯《大寶積經》,以“續奘餘功”,圓滿其師譯事。中宗選在長安宫城的佛光寺(殿)開譯此經,親自筆授經旨,百官后妃一同觀禮:“創發題日於大内佛光殿,和帝親御法筵,筆受經旨,百僚侍坐,妃后同觀。”①《續古今譯經圖紀》,《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371中;《開元釋教録》卷九,頁570中。《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至麟德元年正月一日,玉花寺衆及僧等請翻《大寶積經》,法師辭曰:‘知此經於漢土未有緣,縱翻亦不了。’固請不免,法師曰:‘翻必不滿五行。’遂譯四行,止。”頁219上。由於《大寶積經》卷帙較多,歷時八年纔完成,其間唐室也經歷劇烈的變化。景龍四年(710),韋后和安樂公主毒殺中宗,立少帝(李重茂),不久,睿宗之子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發起宫廷政變,殺韋后,擁立睿宗(李旦,高宗八子)。睿宗哀愍中宗遭遇横禍,繼續支持此經的翻譯,②《大寶積經》卷一:“俄屬靈祐虧微,綿區集禍,喬岳之仙長往,茂陵之駕不還。朕以庸虚,謬膺不構,敬遵前旨,勗就斯編。”《大正新修大藏經》(11),頁1中。也在宫苑之中親自擔任“筆受”的工作。延和元年(712),睿宗傳位玄宗李隆基,被尊爲“太上皇”,儘管政治上有所變動,《大寶積經》的翻譯工作仍持續進行,至玄宗先天二年(713)全部譯畢。菩提流志共譯出二十六會,並且整理勘定先前各代僧人已譯出的二十三會,共計一百二十卷。③《開元釋教録》卷九,頁570上,中。此經先進奉太上皇的睿宗,其後再呈玄宗,睿宗並且親撰《大寶積經序》。
3.“大遍覺”之謚與興教寺的建立
中宗追謚玄奘爲“大遍覺”是有深意的,意即“大菩薩”。①留支三藏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須菩提!若菩薩信見諸法無我、諸法無我,如來應供正遍覺説:‘是名菩薩,是名菩薩。’”《大正新修大藏經》(8),頁760中;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九三:“若於諸行有遍覺者,當知彼類可名菩薩。”《大正新修大藏經》(7),頁1071上;卷五六七《顯相品》:“諸菩薩摩訶薩成佛之所名爲覺處,能自覺故名爲正覺,能覺有情名正遍覺。”頁928上。這和《慈恩傳》彦悰箋:“余考三藏夙心,稽其近迹,自非摩訶薩埵其孰若之乎?”是可以相呼應的。“摩訶薩埵”是梵語,意即“大菩薩”。②《翻梵語》卷二:“菩薩(應云菩提薩埵……)……摩訶薩(應云摩訶薩埵。譯曰:摩訶者大,薩埵者,如上説)。”《大正新修大藏經》(54),頁991中。由此看來,中宗也有可能讀過《慈恩傳》的記載。迄今所見唐代的文獻中,一直到不空(705—774)纔在其表文中以此謚代替玄奘之名,此一表文可能也影響及興教寺的建立。
乾元元年(758)三月十二日,大興善寺僧人不空上表請將收藏在長安、洛陽寺院以及各州縣村落所藏的梵夾修補,並請准許翻譯部分經典,其中即包含慈恩寺玄奘從印度帶回來的梵典:
中京慈恩、薦福等寺,及東京聖善、長壽、福先等寺,并諸州縣舍寺村坊,有舊大遍覺、義淨、善無畏、流支、寶勝等三藏所將梵夾。
右大興善寺三藏沙門不空奏,前件梵夾等,承前三藏多有未翻,年月已深,縚索多斷,湮沈零落,實可哀傷。若不修補,恐違聖教。近奉恩命,許令翻譯,事資探討,證會微言。望許所在檢閲收訪,其中有破壞缺漏,隨事補葺。有堪弘闡助國揚化者,續譯奏聞,福資聖躬,最爲殊勝。天恩允許,請宣付所司。③《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一《制許搜訪梵夾祠部告牒一首》,《大正新修大藏經》(52),頁828上—中。不空何以首列慈恩寺“大遍覺”玄奘帶回的梵夾?一則因玄奘帶回大量的佛典梵夾——“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續高僧傳》稱迄玄奘圓寂時,其中一半以上仍未漢譯。①《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恨其經部不翻,猶涉過半。”頁131。玄奘於二月五日辭世,三月六日高宗即下令將他帶去玉華寺未翻的經典交付慈恩寺掌管,追隨他前往玉華寺譯經的僧人也各遣返原來的寺院。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〇:“至三月六日,又敕曰:‘玉華寺奘法師既亡,其翻經之事且停。已翻成者,準舊例官爲抄寫;自餘未翻者,總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損失。其奘師弟子及同翻經先非玉華寺僧者,宜放還本寺。’”頁225。慈恩寺譯場自此封閉,這些梵夾也封存在此寺之中。二則玄奘攜回的梵典中,有一部分是密教的經典。幾乎没有人注意到玄奘和密教亦頗有關涉,他譯出的經典之中有九部是密教陀羅尼咒:
《不空罥索神咒心經》、《十一面神咒心經》、《咒五首》、《勝幢臂印陀羅尼經》、《諸佛心陀羅尼經》、《拔濟苦難陀羅尼經》、《八名普密陀羅尼經》、《持世陀羅尼經》、《六門陀羅尼經》。③《開元釋教録》卷八,頁556上。
貞觀十九年(645)玄奘翻譯《六門陀羅尼經》,可能和太宗對陀羅尼經典感興趣有關。據《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的序,高祖之世,中天竺婆羅門僧瞿多提婆帶着密教經典文物“於細嗴上圖畫形質,及結壇手印經本”來華,但高祖不感興趣,瞿多提婆遂悻悻然歸國。至貞觀年間,北天竺僧伽梵達摩(唐言“尊法”)攜帶此經梵本來華,太宗下令訪求天下學解僧能與梵僧對譯者,長安大總持寺智通獲選入翻經館,共同譯出此經。④《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大正新修大藏經》(20),頁83中;《開元釋教録》卷八,頁562中—下。當時玄奘在弘福寺譯場主持譯事,智通亦在其統籌之下,並且從他學習。①《大正新修大藏經》(20),頁83中;《宋高僧傳》卷三《唐京師總持寺智通傳》,頁41。當玄奘往訪印度,正逢當地大乘佛教大舉密教化之時,他在彼處亦當接觸到不少密教印咒。在智通所譯的陀羅尼經典中,自注從玄奘學習密印,《觀自在菩薩怛嚩多唎隨心陀羅尼經》,總攝印第四十八後自注:“此總攝印明悉能總攝一切印法(此是智通於玄奘三藏處受得此印)。”②《大正新修大藏經》(20),頁467上。另本有更詳細的敍述:
此咒隨心用攝鬼,此一印通於師三藏玄奘法師邊親受。三藏知此印闕,故授與智通。師中天竺國長年跋吒那羅延、與罽賓國沙門喝囉那僧伽同三曼茶羅會,受持此法。後因敕召入京。遂有大總持寺僧智通,聞解翻譯,與數十大德求及此印法,遂流傳翻譯。通依作壇,經七七日,如法受持,願皆滿足。威力既異於常,亦不敢流傳於世。亦有數百誦咒,師僧於通邊求及此法,畢竟不行。縱得者印法,不過三。通作此法,觀世音菩薩親自現身。自外不能具述。③《觀自在菩薩隨心咒經》,《大正新修大藏經》(20),頁463上。
從智通所記,可知玄奘不僅習得密印,並且在返國之後傳授予譯經僧。在他所帶回來的梵本經典中,多少也包含一些密教的經典。
在玄奘去世九十四年之後,不空上表請修補將玄奘等人從印度帶回來的經典梵夾,並請允許翻譯。不空後來所譯的密教經典中,有多少係來自大慈恩寺翻經堂玄奘所帶回的梵本,不得而知,但不空的奏文或可能和興教寺的建立有關。就在不空上奏這一年的八月二日,肅宗敕令在玄奘墓塔處建塔院,以表彰他的譯經傳法之功: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有敕,於塔塋所置大唐興教寺,以旌傳譯之功,垂芳不朽(時至德三載歲在戊戌,二月五日改爲乾元元年;八月二日敕内出寺額,度僧七人。至十二月日,白黑奉迎“大唐興教寺”額,至於鬱川寺所安置耳)。①《貞元新定釋教目録》卷一二,《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862上。
由皇帝頒給寺額,名爲“大唐興教寺”,度僧七名居於此寺。因玄奘墓塔在鬱川少陵原,至十二月寺成,僧俗信徒迎寺額至鬱川興教寺。
中晚唐的佛教文本中,有以“大遍覺”代替玄奘之名者,如長安西明寺沙門曇曠所撰《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云:“傳譯緣者,大唐貞觀有大三藏遍覺大師,厥號玄奘,俗姓陳氏,洛邑人也。”②《大正新修大藏經》(85),頁1046下。此經敦煌遺書中至少有四十六號寫本。西明寺曇曠不知何時人,但他撰《大乘起信論廣釋》上有“大曆八年六月十七日齊奉道寫”,③《大正新修大藏經》(85),頁1174上。可知他約活躍在公元八世紀中葉前後。又,圓照撰《貞元新定釋教目録》(成書於貞元十五年,799)在玄奘名字之前加上“大遍覺”,以示尊崇:“大佛名經十六卷:又舊録云:如第九卷云南無富樓那(唐言具滿)、南無彌多羅(唐言慈尼者子),大唐大遍覺三藏玄奘譯云滿慈子。”④《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837中。敦煌遺書S.5537《唯識三十論要釋》也提到此謚:“我唐貞觀有大三藏遍覺大師,厥名玄奘。”⑤《敦煌寶藏》(43),頁296上;《大正新修大藏經》(85),頁963上—中。
入宋以後,幾乎没有以“大遍覺”稱呼玄奘之例,但在日本則沿用至今。
4.慈恩寺“翻經堂”的玄奘像
高僧圓寂之後,有在其所居之院堂設置“影堂”者,内置畫像或塑像,以兹追思紀念,如長安光明寺有善導(613—681)影堂。晚於玄奘三年辭世的道宣在西明寺亦有影堂。①《佛祖統紀校注》卷二七《蓮社七祖·法師少康》,頁564。《宋高僧傳》卷一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傳》,頁329。玄奘遷化後,既無塔銘,也無影堂。不過,玄奘的弟子和追隨者透過不同的形式來爲他建立非典型的影堂。追隨玄奘至玉華寺譯經靖邁在慈恩寺翻經院的“翻經堂”中,圖繪古來譯經僧俗之像。及中宗即位後,則將宫中玄奘畫像送至翻經堂,並作像贊,在玄奘最重要的譯場終於有類似紀念性的影堂了。
對於玄奘來説,慈恩寺具有特殊的意義。玄奘歸國之後,以譯經爲此生志業,弘福寺翻經院、慈恩寺翻經院和玉華寺是其三大譯場,其中大慈恩寺翻經院是玄奘最重要的譯經場所。他在貞觀二十二年(648)十二月入住太子李治爲長孫后所建的慈恩寺翻經院,至顯慶二年(657)二月他率領其譯經團在此譯經。總計其一生共譯出七十五部經典,其中四十一部係在慈恩寺譯畢的。②《開元釋教録》卷八,頁555中—557中。玄奘一生共撰譯七十六部經典,因《大唐西域記》屬撰述性質,故共七十五部,其中四十一部是在大慈恩寺翻經堂譯出的。十五部在玉華寺,兩部在終南翠微宫,十五部在弘福寺(包括《大唐西域記》)完成,西京北闕内紫微殿右弘法院兩部,東都大内麗日殿一部。又,永徽二年(651)他啓請建立浮屠“雁塔”以收藏從印度帶回來的梵本經典。雖然他晚年在玉華寺譯經,但麟德元年(664)二月五日圓寂後,遺體即送回長安大慈恩寺翻經堂。因此之故,時人如圓測(613—696)、法藏(643—712)、道世(?—683)、良賁(717—777)的著作中,仍然稱他爲“慈恩寺玄奘法師”、“慈恩三藏”,③《法苑珠林校注》卷一〇〇,頁2886;圓測《仁王經疏》卷上,《大正新修大藏經》(33),頁370下—371上;良賁《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上,《大正新修大藏經》(33),頁432上;法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教迹義記》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經》(39),頁1039上;法藏《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卷上,《大正新修大藏經》(42),頁219中。其傳記也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爲名。
在玄奘辭世後,他的譯經團成員者被遣回原來的寺院,追隨玄奘達二十年之久的靖邁也返回長安慈恩寺。因在慈恩寺翻經堂圖繪有古來譯經緇素羣像,靖邁爲在上述圖像之旁題記,故撰《古今譯經圖紀》。筆者認爲:此羣像和《古今譯經圖紀》都是爲玄奘留下圖像和翻經目録而作。翻經堂古來譯經僧俗畫像究竟是何時所繪?不得而知,可能是靖邁和其他譯經僧所規畫的。《開元釋教録》卷八《古今譯經圖紀》條云:
沙門釋靖邁,簡州人也。以博學馳譽,大唐三藏翻譯衆經,召充綴文大德。後大慈恩寺翻經堂中,壁畫古來傳譯緇素,靖邁於是緝維其事,成圖紀題之於壁。①《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562中。
靖邁撰《古今譯經圖紀》四卷,共記一百一十二人事迹,可知翻經院壁上所繪應是一百一十二人。此一百一十二人中,隋代有三人,唐代僅有中印度僧人波羅頗迦羅和玄奘二人,而玄奘是此羣像最後一人。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指出:“首自迦葉摩騰,終於大唐三藏。”②《續古今譯經圖紀》,《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367下。
《古今譯經圖紀》卷四所列玄奘翻譯的經典,可能來自玄奘臨終前命譯經僧整理的目録。麟德元年(664)正月九日,玄奘在水溝邊跌倒傷足,自此臥病,他自知不久人世,故命譯經僧嘉尚將他所翻譯經典和所造的功德做完整的記録和統計:
法師又云:……遂命嘉尚法師具録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三十八卷。又録造俱胝畫像、彌勒像各一千杘,又造素像十俱胝,又寫《能斷般若》、《藥師》、《六門陀羅尼》等經各一千部,供養悲、敬二田各萬餘人,燒百千燈,贖數
萬生。録訖,令嘉尚宣讀,聞已合掌喜慶。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〇,頁220。
《開元釋教録》中玄奘譯經有十一部取材自《古今譯經圖紀》。②《開元釋教録》卷八,頁555中—557中。在此録中,智昇將《古今譯經圖紀》簡稱爲《翻經圖》。
靖邁和玄奘的淵源很深,他原爲簡州(今四川簡陽西北)福衆寺僧人,貞觀十九年(645)被徵召入弘福寺譯場之後,其後更追隨玄奘至大慈恩寺、玉華寺譯經。除了玄奘入住西明寺時期之外,他陪侍在玄奘身邊幾近二十年之久。靖邁的名字也見於下列玄奘所譯五部經典:貞觀二十年迄二十二年翻譯《瑜伽師地論》、永徽元年(650)譯畢的《本事經》、顯慶四年(659)譯出的《成唯識論》,擔任證文;顯慶四年譯出的《阿毘達磨法藴足論》擔任飾文之任,顯慶元年譯出的《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擔負綴文。③《瑜伽師地論》卷一〇〇,《大正新修大藏經》(30),頁881下;《開元釋教録》卷八,557上;《成唯識論》卷一〇沈玄明《成唯識論後序》,《大正新修大藏經》(31),頁59下;《阿毘達磨法藴足論》卷一二靖邁《法藴足論後序》,《大正新修大藏經》(26),頁514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一之末“大慈恩寺沙門靜邁綴文”,《大正新修大藏經》(27),頁4下—5上。玄奘圓寂之後,他和其他跟從玄奘的譯經僧都回到長安大慈恩寺,《開元釋教録》卷一〇記載《古今譯經圖記》的作者爲“大慈恩寺翻經沙門靖邁”。④《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578下。《宋高僧傳》卷四靖邁傳作《唐簡州福聚寺靖邁傳》,似爲不妥。頁70。
《古今譯經圖紀》的《玄奘傳》,敍述顯慶元年高宗敕命六臣監共譯經之後,直接跳到玄奘譯出佛經的名單,首列六百卷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⑤《古今譯經圖紀》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367中。此經於龍朔三年(663)譯完,是玄奘最後的譯作。由此可知,《古今譯經圖紀》成書於玄奘圓寂之後,似寓有玄奘晚年不能明説的苦處:也就是説,此傳不提顯慶元年(656)到龍朔三年(663)之事,亦未提及玄奘赴玉華寺譯經之緣由。道宣在《大唐内典録》玄奘小傳中稱:“奘還京寺,如常傳譯,後以緣故,徙住玉華宫。”①《大唐内典録》卷五,《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283中。很委婉地道出玄奘前往玉華寺譯經的曲折。翻經堂譯經僧俗羣像和靖邁的紀文,可以説是將玄奘作爲譯經羣像之一,爲他在翻經院作“非正式”的影堂。
靖邁撰《古今譯經圖記》不僅有紀念玄奘的意圖,同時也是他從玉華寺返回長安之後修習的轉向。靖邁和玄奘最親近的弟子普光(627—683)、窺基(632—682)等人皆追隨玄奘至玉華寺譯經,是他譯經團中最重要的成員和助手,但麟德元年(664)玄奘圓寂後,他們都被遣返原來的寺院,也不再參入其他的譯場(如義淨譯場)。普光是玄奘譯經最得力的助手,玄奘譯出七十五部經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十分七八是光筆受”。②《宋高僧傳》卷四《唐京兆大慈恩寺普光傳》,頁68。玄奘辭世時,普光年方三十八歲,此後他就再也没有參加任何經典的翻譯工作。又,窺基當時也剛三十二歲,從此至永淳元年(682)辭世之間,僅在永隆元年(680)參與天竺僧人地婆訶羅譯《大方廣佛花嚴經·續入法界品》一卷的翻譯。③《續古今譯經圖紀》,《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368中—下;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三《世主妙嚴品》:“二大唐永隆元年中,天竺三藏地婆訶羅,此云日照,於西京大原寺,譯出《入法界品》内兩處脱文,……十五行經。大德道成律師、薄塵法師、大乘基法師等同譯,復禮法師潤文,依六十卷本爲定。”《大正新修大藏經》(35),頁523下—524上。普光和窺基都將其心力轉向經典的注疏,窺基以注解經典聞名,爲《金剛般若》、《法華》、《彌陀》、《彌勒》、《勝鬘》等經作注疏,而被冠以“百本疏主”之號;而普光則以《俱舍論記》聞名。也就是説,在玄奘圓寂之後,長期佐翼玄奘譯經的核心成員如普光、窺基、靖邁等人,幾乎絶迹於其他譯場,隱身投入經録和經典的注疏工作,爾後即寂爾無聞。至於其他非“嫡系”弟子如法寶、德感等人則投入皇帝所支持僧人如義淨(635—713)、寶思惟、提雲般若、菩提流志(?—727)等人的譯場,而得以揚名佛教界,或在政治上發揮影響力。①如僧人德感,見孫英剛《從五臺山到七寶臺:高僧德感與武周時期的政治宣傳》,《唐研究》(21),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49—176。至於和普光、法寶修爲在伯仲之間的弟子利涉,則隱没至中宗即位後,因中宗敬重親近玄奘弟子之故,受到皇帝的欽仰重視,也爲朝臣所親近,直到玄宗開元年間,猶受朝野敬重尊崇:“奘門賢哲輻湊,涉季孟於光、寶之間,其爲人也猶帛高座之放曠。中宗最加欽重,朝廷卿相感義與遊。開元中,於安國寺講《華嚴經》,四衆赴堂,遲則無容膝之位矣。”②《宋高僧傳》卷一七《唐京兆大安國寺利涉傳》,頁420。
又,中宗即位後,將宫中所藏的玄奘像送到慈恩寺翻經堂,即有爲玄奘建立影堂的意涵。此一玄奘畫像應來自宫城中的鶴林寺,此寺係高宗爲了高祖薛婕妤出家(法名寶乘)所建的寺院。顯慶元年二月十日,寶乘受具足戒時,高宗特地延請玄奘和九位大德至宫中,以玄奘爲闍黎(親教師),爲寶乘和另外五十餘比丘尼受戒。在此儀式之後,命當世名畫家吴智敏圖畫此十僧之像,留在寺中供養。③《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八,頁180。此外,中宗還爲此畫像作讚文,開成四年(839)劉軻撰寫《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并序》,即敍及中宗親筆撰述的“影讚”:“中宗製影讚,謚‘大遍覺’。”④《金石萃編》卷一一三《玄奘塔銘》,頁2032上。中宗所撰的像讚隨着畫像送到慈恩寺譯經堂供養,後來似乎廣爲人所模寫,九世紀時來華的日本僧人圓珍攜回去的經典圖像中,就有“大遍覺法師畫贊一卷(御製)”。⑤《日本比丘圓珍入唐求法目録》,《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1101中—下。《智證大師請來目録》:“大遍覺法師畫贊一卷(御製)。”《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1107上。
長安大薦福寺翻經院有義淨影堂,此堂壁上圖繪玄奘西行“摩頂松”的傳奇,也可視爲紀念玄奘的圖像。神龍二年(706),中宗在大薦福寺置翻經院以安置義淨,①《開元釋教録》卷九《總括羣經録上之九》,頁568下。前此義淨因仰慕玄奘,展開他“經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往訪印度求法的旅程,②《宋高僧傳》卷一《唐京兆大薦福寺義淨傳》,頁1。故在此翻經院圖繪玄奘西行“摩頂松”的傳奇,是可以理解的。會昌元年(841)二月八日,日僧圓仁(794—864)在大薦福寺翻經院“見義淨三藏影,壁上畫三藏摩頂松樹”。劉肅《大唐新語》中記載此一傳説:
玄奘法師往西域取經,手摩靈巖寺松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吾歸,即向東。”既去,其枝年年西指,一夕忽東方,弟子曰:“教主歸矣。”果還,至今謂之“摩頂松”。③劉肅《大唐新語》之《輯佚·玄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206;《太平廣記》卷九二《玄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606。
上則紀事未見於前述玄奘的諸傳記,不知起於何時。值得注意的是:圓仁記載僅稱“三藏摩頂松”,而未提玄奘之名。玄奘“摩頂松”的傳奇成爲送僧人遠行詩作的典故,如李洞《送雲卿上人遊安南》(一作《送僧遊南海》)、戴叔倫(732—789)《贈行腳僧》詩中皆用此典。④磯部彰《『西遊記』形成史の研究》第一章《唐前半期における唐三藏傳説の發生と擴散》,東京,創文社,1993年,頁57—59。《全唐詩》卷七二一,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8271;卷八二四,頁9287。今本《西遊記》最末回亦有此説,改爲洪福寺松,可見頗爲後人所熟知。
(三)《大遍覺法師塔銘》與玄奘的聖化
代宗大曆年間,“大遍覺”之謚已被用來取代玄奘之稱,但直至九世紀中葉,法相教法的傳人方在興教寺建立《大遍覺法師塔銘》,此塔銘有玄奘聖化的敍述,和中晚唐出現以玄奘之名推廣的經典和宗教儀規頗有互相映照之處。
文宗大和二年(828),大安國寺僧人令撿上奏請修建玄奘塔和窺基塔,次年竣工,但兩人的塔銘卻在十年之後纔鐫刻,實值得細細推敲。首先,關於修塔的原因,此二塔銘所説就不一致。《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下簡稱《玄奘塔銘》)稱大安國寺僧人義林在玄奘忌日,於寺内修齋,看見玄奘塔上有光,以此神迹上奏文宗,請准修玄奘塔。①《金石萃編》卷一一三《玄奘塔銘》,頁2032上。安國寺位於長安最北城坊之一“長樂坊”内,玄奘塔位於終南山下的少陵原,距離今日西安市約二十公里。就常理推之,從長安城北的安國寺如何看得見玄奘塔上的圓光呢?此事是否意味着即使到了文宗時代,談論玄奘仍然是一個禁忌,因此必須以上述神迹請皇帝同意修建其塔?至於《大慈恩寺大法師基公塔銘》(下簡稱《基公塔銘》),則稱係因舊塔傾,乃修建新塔:“大和二年二月五日,異時門人安國寺三教大德賜紫法師義林,見先師舊塔摧圮,遂唱其首,率東西街僧之右者,奏發舊塔、起新塔。”②《金石萃編》卷一一三《基公塔銘》,頁2036下。
再則,在修塔之初,義林即特别留心要爲玄奘建立塔銘:“乃與兩街三學人共修身塔,兼礱一石於塔。”即預備書寫塔銘之用。這是因爲原來陪葬在玄奘塔兩側的窺基塔和普光塔,在埋藏之時就各建有碑銘,僅有玄奘始終未有塔銘。按:永淳元年(682)窺基辭世,有吏部侍郎李乂(647—714)撰文的碑碣;次年普光遷化,亦建有《唐大慈恩寺故大德大乘光法師墓誌》。③《金石萃編》卷一一三《玄奘塔銘》,頁2032上;杜文玉《唐慈恩寺普光法師墓誌考釋》,《唐研究》(5),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466—467。惟獨玄奘爲高宗朝政治風暴波及之故,始終未立塔銘。不過,此時普光塔已經傾圮不復存了。然而,二塔修造尚未完成時,義林即告遷化,臨終前囑咐門人令撿必須爲玄奘建立塔銘,“尔必求文士銘之”。
再則,大和三年二塔完工,次年大和四年窺基塔銘之文已先行撰就,因等候玄奘塔銘之文,故至開成四年(839)一并鐫刻上石。此二塔修就第二年十月,令撿即帶着窺基的行狀,請金州刺史李宏慶撰寫塔銘。①《金石萃編》卷一一三《基公塔銘》,頁2036下。然而,他卻遲至開成二年纔帶着絲囊包裹着玄奘傳記,從長安到洛陽修行里洛州刺史劉軻的宅第,請求他撰寫玄奘塔銘。是否至此時佛教界對於爲玄奘建立塔銘仍有疑慮?令撿請劉軻撰塔銘時稱:“聞夫子斧藻羣言舊矣,詎直專聲於班馬,能不爲釋氏董狐耶?抑豈不聞貞觀初慈恩三藏之事乎?”②《金石萃編》卷一一三《玄奘塔銘》,頁2032上。由此似可推測佛教界深知玄奘受到壓抑不能伸張,因此令撿企望劉軻能爲“釋氏董狐”,此與《宋高僧傳》形容《慈恩傳》的作者慧立“性氣炰烋,以護法爲己任,著《傳》五卷”,③《宋高僧傳》卷四《唐京兆大慈恩寺彦悰傳》,頁74;並參拙文《玄奘的最後十年》,頁8—9。實可相互參照。此外,彦悰的《唐護法沙門法琳别傳》因傳主法琳爲護持佛教,忤逆觸怒太宗,自唐初即遭“明敕禁斷”長達百餘年,一直到德宗貞元十五年(799)纔宣告解禁;④《貞元新定釋教目録》卷二三,《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959中。並參拙文《玄奘的最後十年》,頁7—8。此事或許可以提供玄奘塔修畢的八年之後,令撿纔請劉軻撰寫塔銘相互參照。劉軻以史才聞名,並且“素明玄理”,⑤《舊唐書》卷一七三《吴汝納傳》稱:“與劉軻並以史才直史館。”頁4500。先後爲多位名僧撰寫碑銘,如大德智滿律師塔銘、棲霞寺故大德玭律師碑、廬山東林寺故臨壇大德塔銘、唐棲霞寺故大德玭律師碑,⑥《宋高僧傳》卷一一《唐南陽丹霞山天然傳》,頁251;同卷《唐池州南泉院普願傳》,頁256;《廬山記》卷五《廬山東林寺故臨壇大德塔銘并序》、《唐棲霞寺故大德玭律師碑并序》、《唐廬山東林寺故寶稱大律師塔碑》,《大正新修大藏經》(5 1),頁10 48下—1 04 9上。實是撰寫玄奘塔銘的不二人選。至開成四年(839)五月十六日,《玄奘塔銘》、《基公塔銘》皆由大安國寺内供奉、講論大德建初書寫刻石,在玄奘圓寂後一百七十五年,終於有了塔銘。由上述修塔建銘的曲折,亦可知即使玄奘辭世百餘年後仍然受到無形的禁錮。
玄奘和窺基二塔銘是成組的,須相互參照;以玄奘塔銘爲主,以窺基塔銘爲輔而作解讀。從碑文的篇幅和内容,都顯示此次修塔主要是爲玄奘樹立塔銘。一則《玄奘塔銘》敍述頗爲詳盡,可説是極簡版的《慈恩傳》,《基公塔銘》則顯得簡略。《玄奘塔銘》的篇幅是《基公塔銘》五倍,前者碑石高三尺四寸五分,廣六尺八寸四分;其上的題刻共七十六行,每行四十二字,共二千九百八十三字。後者石高二尺二寸五分,廣三尺四寸五分;塔銘文字部分共四十一行,每行二十三字,共九百四十三字,不計造塔者題名僅有六百二十九字。①二則修塔者題名置於《基公塔銘》之末:
左街僧録勝業寺沙門體虚、前安國上座沙門智峯、右街僧録法海寺賜紫雲端,安國寺上座内供奉内外臨壇大德方璘、寺主内供奉灌頂、都維那内供奉懷津、院主曇景,同勾當僧懷真、德循、惠臯、惠章,興教寺上座惠温、寺主超願、都維那全契,僧道榮、僧道恩、僧瓊播、義方、巡官宋元義。
開成四年五月十六日講論沙門令撿修建。②《金石萃編》卷一一三《基公塔銘》,頁2037下。
由以上的題名可知:此次修塔係由安國寺義林倡首,而得到“兩街僧之右者”長安大德高僧的支持,因此有左、右街僧録的題名。由於鐫刻塔銘距最初起造已有十一年之久,倡議者義林早已辭世,故題名中未見其名,但在二塔的銘文中都提及義林。《玄奘塔銘》云“修塔者誰,林公是營。門人令撿,實尸其事。銘勒塔旁,撿真法子”。又,《基公塔銘》云“義林高足兮曰令撿,親承師言兮精誠感”。①《金石萃編》卷一一三《玄奘塔銘》,頁2035下;《基公塔銘》,頁2037上。至於建塔的經費則是由義林和其弟子出資的:“功未半而疾作,會其徒千人,盡出常所服玩,洎向來箕斂金帛,命高足僧令撿俾卒其事。”②《金石萃編》卷一一三《基公塔銘》,頁2036下。在此十年之間,前後任安國寺三綱都大力支持此事,故有“前安國上座沙門智峯”,以及現任三綱“安國寺上座内供奉内外臨壇大德方璘、寺主内供奉灌頂、都維那内供奉懷津”的題名。又因興教寺爲二塔所在地,故有該寺三綱之名。
修建玄奘塔的大安國寺僧義林及其弟子令撿,都是法相教學的傳人,從義林在玄奘忌日修齋,即可窺知一二。又如《基公塔銘》稱“異時門人安國寺三教大德賜紫法師義林,見先
獉師獉舊塔摧圮,遂唱其首”,以及令撿泣奉義林遺命,劉軻在《玄奘塔銘》云“非法廟諱之冢嫡,誰何至此乎”,③《金石萃編》卷一一三《基公塔銘》,頁2036下;《玄奘塔銘》,頁2032上。廟諱指“胤”字。此法胤係指唯識法相之傳承,從唐初迄於晚唐不絶如縷。九世紀入唐僧中有“法相請益”的名目,文宗開成三年(838)隨遣唐使船到中國的日僧中,有常曉(三論留學)、義澄、戒明(法相請益)、圓行(真言請益)。④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12,15,42;卷二,頁62。至宋、元時期法相教學傳習不絶,⑤竺沙雅章《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第二章《宋元時代杭州寺院慈恩宗》,東京,汲古書院,2000年,頁27—57。惟傳承不見於記載。
值得注意的是:《玄奘塔銘》中有聖化的敍述,《基公塔銘》則無。《玄奘塔銘》包含《慈恩傳》四段聖化的敍述:(1)戒賢夢中有關玄奘的傳法印記:“法藏訊所從來,曰‘自支那,欲依師學瑜伽論’。法藏聞則涕泗,曰‘解我三年前夢金人之説’。佇爾久矣。”(2)玄奘自言得生彌勒内院:“至二月五日夜,弟子光等問云‘和尚決定得生彌勒内衆否’?頷云‘得生’,俄而去。”(3)玄奘圓寂前後靈應神異的敍述:“自示疾至於昇神,奇應不可殫紀,蓋莫詳位次,非上地其孰能如此乎!”按:菩薩的修行證果有十個次第,從初地至十地,可分爲初地至六地、六地至八地、八地至十地這三個階段,第八地爲“不動地”,煩惱斷盡,不爲煩惱所動,故八地至十地是上地菩薩,接近成佛的階段。(4)在銘文中以“三藏之生,本乘願來。……脱屣玉華,昇神睹史”約括韋陀天宣告玄奘上生到彌勒淨土。①《金石萃編》卷一一三《玄奘塔銘》,頁2033上,2034下,2035上,下。此外,《基公塔銘》中更將玄奘比附爲阿難:“師姓尉遲,諱基,字廟諱道。……三藏法師廟諱奘者,多聞第一,見道頗加竦敬,曰‘若得斯人傳授,釋教則流行不竭矣’。”②《金石萃編》卷一一三《基公塔銘》,頁2036下,2037上。佛典中稱釋迦弟子阿難尊者“多聞第一”,③最早的佛典阿含部中就提及阿難是“多聞第一”,如《雜阿含經》卷二三,《大正新修大藏經》(2),頁168中;《增壹阿含經》卷四九,《大正新修大藏經》(2),頁820中—下。此處稱玄奘多聞第一,實將他比附爲阿難,這種論述也影響及鎌倉時代的宗教文物,將玄奘和阿難相對應的安排。④拙文《鎌倉時代玄奘的聖化》,待刊。
由上可知,此次修建玄奘、窺基新塔,終於達成爲玄奘建立塔銘的目的;至於窺基原來立有李乂撰寫的墓碣,此時則移入興教寺内:“佳城之南兮面南山,廟諱奘法師兮葬其間。基公既殁兮陪其後,甲子一百兮四十九。碣文移入兮本寺中,曇景取信兮田舍翁。”⑤《金石萃編》卷一一三《基公塔銘》,頁2037上。
三 從中晚唐的經典儀規、信仰看玄奘的聖化
中晚唐時期,有以玄奘之名宣揚的佛典、儀規,也有和玄奘相關的深沙神信仰,凡此都可視爲玄奘聖化的表徵。
(一)藉玄奘之名宣揚的經典
敦煌遺書中有不見於藏經的中國撰述經典(疑僞經典)或注疏,藉玄奘之名以兹宣揚,如《梵語心經》、《大辯邪正經》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還源述》。
1.《梵語心經》
敦煌遺書中有六號(S.2464、S.3178、S.5627、S.5648、S.2322、北大D.118)漢文音譯梵文《般若心經》(下簡稱《梵語心經》),迄今學界集中在此經的來源和譯者的討論。①萬金川《敦煌石室〈心經〉音寫抄本校釋序説》,《中華佛學學報》第17期,頁95—121;方廣錩《〈般若心經〉——佛教發展中的文化匯流之又一例證》,《深圳大學學報》(人社版)2013年第4期,頁6—25。筆者學淺,無置喙餘地,此處僅從佛教信仰宣揚的角度而言。此六號文獻中,S.2464號《唐梵飜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共有三個部分,首先是署名“西京大興善寺石璧上録出慈恩和尚奉詔述序”的序文(下簡稱《梵語心經序》),第二部分是《蓮花部普讚嘆三寶》,第三部分爲《梵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關於《梵語心經序》,前此學者或以爲係變相的冥報傳,或是佛經的靈驗記;②陳寅恪《敦煌本〈唐梵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跋》,收入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176;張石川《敦煌音寫本〈心經序〉與玄奘取經故事的演化》,《文史哲》2000年第4期,頁120—121。本文則認爲它是在九世紀陀羅尼盛行的風氣中,藉着《慈恩傳》的敍事進一步衍化的傳奇,用以推廣《梵語心經》的宣傳品。
《梵語心經序》脱胎於《慈恩傳》中一段敍事,稱玄奘在蜀地見到一位滿身臭穢的病人,將他帶到寺院供給衣服飲食;病人感念其恩德,故授與玄奘此經。及玄奘西行時,逢諸惡鬼,即使念誦觀音名號都無效時,念此經即能安然渡過難關:
從此已去,即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顧影惟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愍將向寺,施與衣服、飲食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遶人前後,雖念觀音不得全去,即誦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憑焉。①《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頁16。
其後上述傳奇繼有衍化。《太平廣記》記述玄奘前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有一病僧授以《多心經》,持誦此經使他在西行的路途中皆得以逢凶化吉:“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迹。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②《太平廣記》卷九二《玄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606。張石川指出此一紀事出自李冗《獨異記》,它係成書於會昌六年(846)以後。③張石川因此認爲《獨異志》的故事最晚出,見《敦煌音寫本〈心經序〉與玄奘取經故事的演化》,《文史哲》2000年第4期,頁120—121。又,拙文研究中古聖僧信仰,發現從北朝以迄於五代,僧人所救濟病人或是病僧常是聖僧的化身,他們或請僧人至神山聖寺,或者以不同的方式回報,幾乎成爲聖寺神僧故事的典型。④拙文《中國的聖僧信仰和儀式(四—十三世紀)》,收入康豹、劉淑芬主編《第四届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信仰、實踐與文化調適》(臺北,2013年10月),上册,頁164—167。
《梵語心經序》則更加上神化的鋪敍,記述玄奘往西天途中,路經益州空惠寺,①約在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至五年間,玄奘與其兄長捷法師居於“益南空慧寺”,但玄奘往訪印度的路途不經益州。遇一病僧,授他“三世諸佛心要法門”,即《梵語心經》,以保他路途平安。玄奘在路上遇到危難或糧食缺乏時,持念此經,都得以度過難關。及他抵達那爛陀寺,竟然見到那位病僧,自稱是觀音菩薩,告以能平安到達此地,係仰賴昔日傳授的法門:
西京大興善寺石璧(壁)上録出慈恩和尚奉詔述序
梵本般若多心經者,大唐三藏之所譯也。三藏志遊天竺,路次益州,宿空惠寺道場内。遇一僧有疾,詢問行止。因話所之,乃難嘆法師曰:“爲法忘體,甚爲希有。然則五天迢遞十萬餘逞,……逞途多難,去也如何。我有三世諸佛心要法門,師若受持,可保來往。”遂乃口受與法師訖。至曉,失其僧焉。三藏結束囊裝,漸離唐境。或途經厄難,或時有闕齋饈,憶而念之四十九遍,失路即化人指引,思食則輒現珍蔬。但有誠祈,皆獲戩祐。至中天竺磨竭陀國那爛陀寺,旋遶經藏次,忽見前僧而相謂曰:“逮涉艱嶮,喜達此方,賴我昔在支那國所傳三世諸佛心要法門。由斯經歷,保爾行途。取經早逯,滿爾心願。我是觀音菩薩。”言訖沖(衝)空。既顯奇祥,爲斯經之至驗。信爲般若,堅爲聖樞。如説而行,必超覺際。究如來旨,巨曆(歷)三祇;諷如來經,能銷三障。若人虔誠受持者,體理斯而懃焉。②S.2464《唐梵飜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并序》,《敦煌寶藏》(19),頁688下—689上;今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8),頁851上—中。“早逯”之“逯”爲“遁”的古字,《大正藏》本作“縟”。
此序首先强調此梵本心經係玄奘所譯,二則將此經塑造爲觀世音菩薩護佑玄奘西行而傳授者。三則此經可以逢難化安,消除種種困厄。四則稱玄奘誦持之法,遇困頓之時,即念此經四十九遍,都能及時獲得救護福佑。最後稱此是般若的中心,依此而行,不需經三大阿僧祇劫,即能超脱證果。
另一敦煌文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還源述》和《梵本心經序》也有類似之處,此係《心經》注疏,失撰者名,敦煌有S.3019、S.7519文獻,後者是殘本。S.3019號今收於《大正藏》(85),在結尾的偈頌之後,另有五行文字:
此經元於《大般若》中疏出,如《法華經·普門品》别行之類是也。三藏法師玄奘每受持而有靈應,是故别譯以流通。若人清心澡浴,著鮮潔衣,端身正坐,一誦五百遍者,除九十五種邪道,善願從心,度一切苦厄。①《大正新修大藏經》(85),頁169上。S.3019《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還源述一卷》,《敦煌寶藏》(25),頁281下。
梵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與三藏法師玄奘親教授梵本不潤色。②S.2464《唐梵飜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敦煌寶藏》(19),頁689上。
敦煌文獻《梵語心經》有“潤色”一詞共五個本子,僅S.3648作“不空閏色”,其餘四本(S.2464、S.3178、S.5627、北大D.118)皆作“不潤(閏)色”,③方廣錩《〈般若心經〉——佛教發展中的文化匯流之又一例證》,頁10,將敦煌遺書六號《梵語心經》—S.2464、S.3178、S.5627、S.5648、S.2322、北大D.118,加上大谷大學學本的内容、首題、著譯者作成一表。因此,應以“不潤色”爲準,④方廣錩《〈般若心經〉——佛教發展中的文化匯流之又一例證》,頁13,注12:“不潤色”文意滯碍,而聯繫前文不空譯《蓮花部普讚嘆三寶》,則以“不空潤色”文意爲長。它意在强調觀自在
上文也强調玄奘持誦而有應徵,次則教人持誦之儀,並且述説其功德。
S.2464號第三部分即是《梵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在漢文音譯梵文的經文之前有一行字:菩薩親自教授玄奘梵本,未加更改“不潤色”。以北大D.118而言:
大唐三藏傳梵語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與三藏法師親教授梵本,不閏色。①北大D.118《梵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敦煌文獻》(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88上。
上文“三藏”、“梵”字兩見,先稱三藏傳梵語心經,再述觀自在菩薩親教授三藏梵本,最後强調它是未經修飾的文本。因此,本文以爲此號文書是藉玄奘以宣揚《梵語心經》。
從初唐以降,玄奘所譯漢文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廣爲流傳持誦,刻於石窟、石碑或經幢者甚多,如洛陽龍門石窟有神龍二年(706)王才賓爲亡母造浮圖暨《心經》;又如河北正定開元寺三門樓創建於武后時期,其上所刻佛像經文皆非一時之刻,總計有十二部《心經》。另外唐代一些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上亦有兼刻此經者。②《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三二《王才賓浮圖頌并心經》,《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6),頁4512下;卷四一至四三《開元寺三門樓題刻二十二段》;頁4656上—4706上;卷四六《本願寺僧知愻等尊勝幢記》,頁4738上。又如玄宗之妹婿秘書少監鄭萬鈞刻將此經刻在石碑上,置於聖善寺供養等。③張説《石刻般若心經序》,《全唐文》卷二二五,頁2271上。由上可見其普傳流行,因此毋庸再宣揚此漢文經本。以此觀之,則《梵本心經序》可能是九世紀陀羅尼流行的背景下,特爲宣揚梵本音譯的《心經》所作。以下列兩事可顯示九世紀密教陀羅尼的流行,一是房山石經刻有唐昭宗乾寧五年(898),安國寺傳密教沙門超悟大師行琳撰《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二是其時出現了多種陀羅尼並刻一石之碑。④行琳《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序》,收入林光明《房山明咒集》(1),臺北,嘉豐出版社,2008年,頁1—7。拙文《咒石與經幢——九世紀碑刻所見佛教僧俗持念的陀羅尼》,《石經研究》創刊號。
由於《梵語心經序》中,將《梵語心經》和觀音菩薩親授作連結,故在敦煌遺書六號《梵語心經》中,有四號(S.2464、S.3178、S.5648、北大D.118)包括不空所譯的《蓮華部普贊嘆三寶》,這是因爲密教“蓮花部”又稱“觀音部”之故。S.2464第二部分是署名“特進鴻臚卿開府議同三司封肅國公贈司空官食邑三千戶敕謚大辦正廣不空奉詔譯”的《蓮花部等普讚嘆三寶》,S.5648有“敕謚大辨正廣不空奉詔譯”的《蓮花部普贊嘆三寶》。按:大曆九年(774)七月五日,代宗追贈不空“大辨正”的謚號,由於不空係在天寶十五載(756)入住大興善寺,又因S.5648中有“癸酉”年的紀年,若以吐番支配時期推算,相當於793年,故此序的上限當在公元756年至793年之間。①福井文雅《般若心經の総合的研究:歷史·社会·資料》第四章《慈恩和堂述“梵本若多心經序”考》,東京都,春秋社,2000年,頁88—90。《梵語心經》的宣揚和不空、密教都有相當的關連,S.2464《梵語心經序》署名“西京大興善寺石壁上録出慈恩和尚奉詔述序”,不論是序是否爲窺基所撰,抑或此序是否曾經被刊刻在大興善寺的石壁上?都不得而知。不過,從天寶十五載迄代宗大曆九年(774)間,不空確是住長安大興善寺,梅维恒(Victor H.Mair)甚至懷疑不空直接或間接促成此文的寫作。②梅維恒《〈心經〉與〈西遊記〉的關係》,《唐研究》(10),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47。作者認爲此文署名“慈恩和尚”的動機是表達對玄奘的敬仰。不過,從唐以降“慈恩和尚”係指窺基,而非玄奘,這一點不可不辨明。
晚唐《梵語心經》似有一定程度的流行,九世紀入唐僧最澄(767—822)請回《般若心經梵本漢字》一卷、圓仁攜回《梵漢兩字般若心經》一卷,③最澄《傳教大師將來越州録》,《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1058中;圓仁《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録》,《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1074中;安然《諸阿闍梨真言密教部類總録》稱上述二本爲:“梵唐對譯般若心經一卷(澄、仁)。”《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1120中。二者疑即是上述《梵語心經》(唐梵飜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敦煌遺書P.2704V《贊〈梵本多心經〉》中有“般若題名觀自在,聖力威神无比對。危難之心諷念時,龍鬼妖精尋自退”。又,“當時三藏憑經力,取得如來聖教歸”。都有《梵語心經序》之迹。①方廣錩《〈般若心經〉——佛教發展中的文化匯流之又一例證》,頁12—13,附録二。法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317上。晚唐李洞(?—893?)送朗公歸西域詩《送三藏歸西天國》云:“十萬里程多少磧,沙中彈舌授降龍。”應是用玄奘念《梵語心經》之典。明彭大翼(1552—1643)《山堂肆考》一書中,有《虎豹潛迹》條,記玄奘往西天取經路經罽賓,有老僧授《心經》一卷,復稱:“又玄奘彈舌念梵語《心經》,以授流沙之龍。”清高士奇輯注《三體唐詩》,即引其説,注云:“奘公彈舌念《梵語心經》,以授流沙之龍。”②《全唐詩》(21)卷七二三,頁8300;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四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977册,頁39上;周弼編,高士奇輯注《三體唐詩》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358册,頁13。
《梵語心經序》稱觀音菩薩親授玄奘《梵語心經》,其説廣傳綿延。明清時期雲南阿吒力僧常用之科儀《楞嚴解寃釋結道場儀》中,即包含《梵語心經》,它的偈頌則提到了觀音親授此經:
仰啓真空無相教,梵音不譯頗難思。昔因三藏往西天,遂感觀音親授記。誦念除厄並滅罪,聽聞獲福與延齡。咸期不退菩提心,一切善根悉圓滿。③趙文煥、侯沖整理《楞嚴解寃釋結道場儀》卷五《楞嚴解寃釋結道場儀提綱》,收入《藏外佛教文獻》第六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年,頁162。
由此可知,觀音親教授玄奘《梵語心經》的傳奇,確實有深遠的影響。
2.《大辯邪正經》
敦煌遺書有三件未入藏的《佛説大辯邪正經》的寫本:P.2263、北8297、P.3137,其中P.2263收入《大正藏》(85)。此三件在卷末有兩行字:
玄奘及長年師及邪奢等,於如來七寶窟中,得此如來《大辯邪正甚深密藏經》一卷。①《大正新修大藏經》(85),頁1413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239下。
稱此經爲玄奘和印度的長年師等人,共同在佛典中常提及的七寶窟中取得的珍貴經書,當係爲增加信衆對此經的珍視,以達到宣揚之效。
除了上述二經之外,另有《壽生經》一卷。經文之首稱:“貞觀十三年,有唐三藏法師往西天求教,因檢大藏經,見《壽生經》一卷。”②《卍新纂續藏經》(1),頁414下—415中。迄今所知,此經最早見於明代的記載。袾宏(1523—1615)《諸經日誦集要》卷中收録此經,③《諸經日誦集要》卷中,《嘉興大藏經》(19),頁164下—165中。袁枚(1716—1797)所撰的小説《子不語》中,敍述直隸蓮池禪寺僧“誦《壽生經》作佛事”。④袁枚《子不語》卷一二《銀隔世走歸原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86。此經流傳甚廣,以迄於今,近年臺灣猶印行流傳。
(二)深沙神信仰
九世紀唐土流行的深沙神信仰,也是藉着玄奘西行傳奇而興起的。唐文宗開成三年(838)至四年訪華的日僧常曉(?—866),將“深沙神王像一軀”,以及《深沙神記并念誦法一卷》帶回東瀛。常曉根據他在唐帝國的見聞,有以下的敍述:
深沙神王像一軀
右唐代玄奘三藏遠涉五天感得此神,此是北方多聞天王化身也。今唐國人總重此神救災成益,其驗現前,無有一人不依行者,寺裏、人家皆在此神,自(目)見靈驗,實不思議。具
事如記文。請來如件。①《常曉和尚請來目録》,《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1070下—1071上。
他觀察到寺院、民家都供奉深沙神,並且記述人們對他的認知:玄奘西行取經途中,得到毗沙門天王化身的深沙神的協助,故稱“救災成益,其驗現前”。此説應是在《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之後發展而成的。根據磯部彰的研究,深沙神原來是鬼,在前兩世中都將阻礙玄奘取經,至第三世時,由於毘沙門天王的護持,終於破解深沙神的阻撓。自此之後,深沙神不但歸信,並且幫助玄奘通過沙漠。玄奘返唐之後,向太宗祈請在寺院中做法事追薦深沙神,太宗下令“可付於七身佛前護殿”,也就是將深沙供奉在七佛殿前做護法神。②磯部彰《「西遊記」形成史に現われた密教文化の諸相—チベット密教との関係を中心に》,《密教圖像》,第5號(1987),頁17;《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卷一七《到陝西王長者妻殺兒處》,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4年,頁40。因《取經詩話》卷三有北方毗沙門天王在天上水晶宫設齋,孫行者還帶玄奘去參與此會,故小川貫弌很早就指出:此書係建立在毗沙門信仰下。③小川貫弌《大唐三藏取經詩話の形成》,《龍谷大学論集》362號,頁75。中國毗沙門信仰起源很早,④党燕妮《毗沙門天王信仰在敦煌的流傳》,《敦煌研究》2005年第3期,頁99—100。筆者以爲深沙神信仰係建立在毗沙門信仰之外,又藉着玄奘取經感化深沙神的傳説而發展傳佈的。
在常曉之後,大中十一年(857)圓珍(814—891)在温州永嘉郡也取得《深沙神王記一卷》。⑤圓珍《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録》:“深沙神王記一卷(新寫)……已上於温州永嘉郡求得。”《大正新修大藏經》(55),頁1094上。常曉、圓珍帶回深沙神的圖像和儀軌,日本遂有深沙的信仰。⑥中野玄三《“玄奘三藏繪”概説》第一章“玄奘三藏繪”の成立背景,三、玄奘と深沙大將,頁124—128。日本玄奘聖化的内容之一,是和深沙神連在一起的,鎌倉時代在“大般若會”所懸挂的“釋迦十六善神圖”中,深沙神和玄奘成組出現,成爲護佑《大般若經》的神祇。①中野玄三《“玄奘三藏繪”概説》第一章“玄奘三藏繪”の成立背景,四、初期釋迦(般若)十六善神像,頁128。
(三)與玄奘相關的禮拜法和齋儀
敦煌遺書中,也有以玄奘爲名闡揚的禮拜法和齋儀,一是《十二月禮佛文》,一是十齋日。
敦煌遺書有十四件《十二月禮佛文》,都是晚唐五代時期的寫本,方廣錩先生對此有全面性的研究。②關於《劉師禮文》,方廣錩先後有三篇文章:(一)《試論佛教的發展與文化的匯流——從〈劉師禮文〉起》,《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年第1期,頁38—40;(二)《試論佛教的發展與文化的匯流——從〈劉師禮文〉起》,《法音》2007年第6期;(三)《談〈劉師禮文〉的後代變種》,《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16年第1期。他指出這些文書都係S.4494《劉師禮文》的後代變種。這件文獻原係西魏大統十一年(545)由僧人道養所抄寫的,“劉師”即東晉僧人劉薩訶(345—436),禮文係他所倡導的一種禮拜修持之法,即在每年十二個月在某個特定日子的特定時辰,向某個方向禮拜特定的次數,可以滅罪得福。③方廣錩《試論佛教的發展與文化的匯流——從〈劉師禮文〉起》,頁38—40。此種禮拜法在北涼玄始年間(412—427)流佈,幾經傳抄流行,到唐中晚期時,遂演變爲玄奘從佛典中略出的禮佛儀規。這些寫本之中,有將玄奘誤作玄藏,也出現玄奘未駐錫過的寺院龍興寺、崇福寺之名。④方廣錩《談〈劉師禮文〉的後代變種》,頁26。
這十四件《十二月禮佛文》之中,有十一件都提到玄奘,也就是以玄奘之名推廣、宣傳此一禮拜法。方廣錩整理十四件文書,將之歸納爲在流傳抄寫中衍生出八種異本,⑤方廣錩《談〈劉師禮文〉的後代變種》,頁21—29。以下將依此這些異本的内容,探討此種文本的演化過程(以下所引諸異本皆出自方先生録文)。唐代衍生出來的諸異本顯示:這些異本不僅以玄奘之名,取代創造此禮拜法的劉師(劉薩訶),而且對玄奘和此禮拜法關係的鋪敍由約而繁,最後串連成一個完整的宣傳品。如P.3795(異本三),僅單純説此禮拜法係玄奘自十二經中略出:
右上件齋月日,是玄奘法師在十二部經略出,若有人能滿三年,依時持齋禮拜,所求如願。抄本流傳,除罪十方六千六百劫。①方廣錩《談〈劉師禮文〉的後代變種》,頁24;P.3795《大乘四齋日等》,《法藏敦煌西域文獻》(28),頁79。
至上圖141號(異本五),則增加玄奘西行,取經回長安崇福寺披尋,方知有十齋日和每月禮佛日:
敬白善男子等,玄藏法師從西方將經至崇福寺披尋,始知每月有十有齋日,及每月禮拜佛之,並是諸天賢聖集會之日,若能依此時齋及以禮拜,五百生常得安樂。寫一本在家,得善神助護。若寫一本轉施諸人,亦得福无量。②方廣錩《談〈劉師禮文〉的後代變種》,頁26;上圖141《玄藏法師十二月禮佛除罪文》,上海圖書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340下。
底本:S.2565,甲本:P.3809(異本四)則兩度强調玄奘西行返唐,從一千卷經典中略出《十二月禮佛日》:
西京龍興寺玄奘法師於西國來大唐國,有十二月禮佛日,每月只在一日。
正月一日(下略)玄奘法師於西國取經一千卷内,掠出此禮佛月日。若能有人受持讀誦者,獲福无量。用力最上,功德甚多。福高遷如須彌山王,深如巨海,无如天地,廣積无邊功德。歡(勸)諸善男子、善女人虔心重意,普願合掌珍重,合家
禮敬經文讀嘆,罪滅福生,信心奉行。①方廣錩《談〈劉師禮文〉的後代變種》,頁24—25;S.2565V《金剛經纂一卷》,《敦煌寶藏》(21),頁137上;P.3809《十二月禮佛文》,《法藏敦煌西域文獻》(28),頁131下—132上。
異本六和異本七則加上玄奘將此禮佛文上呈唐太宗的敍述,P.3588(異本六)僅簡單敍及“上都弘福寺玄奘大師從西天來,進上太宗皇帝《十二月禮佛文》”。異本七和異本八則更加上太宗敕抄此文頒下諸州,S.2143、大正2829(異本八)僅見“爾時玄藏法/敕抄此佛名,頒下諸州”。至於上博48、S.5541、P.2566V、P.2575、P.2575V(異本七)則更演繹成一則豐富完整的故事,加上了玄奘略出此禮佛文之後,和弘福寺的樹木相禪師共讀,因感到它極其重要,遂一起晉見上呈太宗。太宗爲此齋儀感動,賞賜極多,並且將此《禮佛名》頒下諸州:
尒時玄藏法師將此禮佛名向京師城内,入弘福寺。樹木相禪師共讀此《禮佛名》。出家之輩,多有犯罪,極要!極要!木禪師及玄藏法師將《禮佛名》皇帝如聞。尒時聖主解讀其文,舉手彈指,悲啼啼哭,五體投地,敬謝禪師:“朕當受持此禮,憶念供养,不令忘失。”敕賜禪師金銀千斤,亂綵無數,抄此一本,頒下諸州。……正月一日,……尒時玄藏法師向西國翻經十二部尊經要略,略出《禮佛名》,恐畏閻浮衆生多造罪業,五濁惡世受罪衆生,王官逼迫,無有的容。積罪極重,死墮地獄、餓鬼、畜生,受大苦惱,無有閑客。入道場懺悔,禮拜亦不及。六時禮拜,供養諸佛。遂略出《十二月禮佛名》,取月月時節,不唱禮佛名。②方廣錩《談〈劉師禮文〉的後代變種》,頁27—28;上博48《十二月禮佛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博物館編《上海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41上,42下。前述異本四稱禮佛文係玄奘從一千卷略出,至此更稱從部帙龐大的十二部尊經節略所得。由上可知,經過不斷的層疊增添,至此演繹成一個完整、有力的宣傳文本。
以上十四件晚唐五代寫本中,P.3588的時間當在九世紀下半葉以後。此件包含《澄照大師於臺山金閣院金字藏中檢得七佛名號》、《上都弘福寺玄奘大師進太宗皇帝十二月禮佛文》兩個文本。①《法藏敦煌西域文獻》(26),頁5下。按:澄照大師爲道宣的謚號,懿宗咸通十年(869)“敕追謚南山道宣律師曰澄照”,②《佛祖統紀校注》卷四三,頁998。故知此件文書的年代當在咸通十年以後。此外,S.2565V,有尾題“金剛經纂一卷”,方廣錩發現敦煌文獻P.3024V有首題“佛説金剛經纂”,後半爲英國大英圖書館藏S.2565V,有尾題“金剛經纂一卷”,此係一件文書被撕爲兩號。有“天曆元年,北山縣有一劉氏女子,年十九歲身亡,到冥司,……”的記載,方先生以爲:歷代行政區畫均無“北山縣”,故懷疑“天曆元年”是否爲真實的歷史年號。③方廣錩《佛説金剛經纂》,《藏外佛教文獻》第一輯,頁354—355。按:北魏長安附近有山北縣,但在傳抄轉寫之際有時訛爲“北山縣”。北魏熙平元年(516)王文愛墓誌側面有“雍州京兆郡山北縣民”的銘記,④《王文愛銘記》,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84。北魏孝莊帝永安年間(528—530),韋孝寬因有戰功,賜爵“山北縣男”。⑤《魏書》卷一三《宣武靈皇后胡氏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337;《周書》卷三一《韋孝寬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頁535。但“山北縣”有時被誤植爲“北山縣”,例如北魏宣武帝胡后出生之日,赤光四照,胡后之父胡國珍曾問卜於善相者,《太平御覽》便作“京兆北山縣有趙胡者善於卜”,武英殿本《通志》也將韋孝寬“賜爵北山縣男”。⑥《太平御覽》,卷一四〇《皇親部六·宣武胡皇后》,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3年,頁681下;《通志》,卷一五七《後周韋孝寬傳》,萬有文庫十通本,頁2539上。因此,《佛説金剛經纂》之十二月禮佛文中“北山縣”或有可能即爲前述的“山北縣”之誤。而“天曆元年”或有可能是唐大曆元年(766)之誤。
此外,這十四寫本之中,有三號也將玄奘塑造爲十齋日創建者,如S.2565、P.3809在十二月禮佛文之前,有“玄奘法師禮拜,逐月有十齋日”。①張總《地藏菩薩十齋日》,《藏外佛教文獻》第七輯,頁364。尹富《十齋日補説》,《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頁31。又,前述上圖141號(異本五)的勸請功文中稱“玄藏法師從西方將經崇福寺披尋,始知每月有十齋日及每月禮拜佛之”,也認爲十齋日是玄奘引進的。②方廣錩《試論佛教的發展與文化的匯流——從〈劉師禮文〉起》,頁26。
此一冠以玄奘之名宣揚的禮拜法,也流傳至東南沿海地區。唐宣宗大中八年(815),日僧圓珍在福州、温州、台州一帶,蒐得《玄奘三藏從西天取來禮拜文一卷》。③《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經律論疏記外書等目録》,頁1094c。西魏《劉師禮文》先是被改成玄奘從佛典中節略的《十二月禮佛文》,至此時更被直接冠以“玄奘從西天取來”之名,反映了此禮拜法藉由玄奘抄略之説,以期收到宣揚廣傳之效。此一以玄奘之名宣傳的禮拜法持續轉述廣傳,以迄於今,方廣錩文中提及2004年在香港印刷的《人生寶鑒》第七卷有“《救劫回生經》中録唐京都宏福寺元焚(玄奘)法師自西藏回,上表太宗皇帝,十二月禮懺悔發願日期。……”④方廣錩《談〈劉師禮文〉的後代變種》,頁29—30。事實上,近數十年來,臺灣民間宗教也持續印行此書。
五 結語
本文主要探索唐代隱晦不顯的玄奘聖化之迹,玄奘傳記已包含一些聖化的敍述,然而,由於他無端被捲入政治風暴中,其傳記《慈恩傳》完成之後長達四十年的時間不能流通,使得其聖化的論述潛藏隱沉,至唐玄宗時其禁稍解。儘管唐人好爲詩文,但幾乎没有專篇陳述或讚詠這位高僧和事迹。蒐盡《全唐詩》,也僅有兩首詩提及玄奘,即僧人慧宣、道恭詠嘆唐太宗賜玄奘衲袈裟詩二首。①慧宣《詠賜玄奘衲袈裟》,《全唐詩》(23)卷八〇八,頁9112;道恭《出賜玄奘衲袈裟衣應制》,同上書,頁9116。一直到晚唐時,這種情況纔有所轉變,包括《玄奘塔銘》的建立,和佛教界以玄奘之名推廣的經典和齋儀,顯示其聖化受到尊崇和重視。
唐代玄奘聖化的敍述包括:印度戒賢論師夢中文殊菩薩的傳法印記、玄奘自言得生至彌勒内院、圓寂前後諸種瑞應,以及韋陀天現身告知道宣,玄奘已經成聖。其中,文殊菩薩的傳法印記、玄奘自稱得生淨土二者最爲廣傳,它普遍出現在唐宋時期玄奘傳記和佛教文獻,韋陀天的證詞則僅見於《慈恩傳》,此後遂寂爾無聞。可能因這則記載包含韋陀天指正道宣“所出律抄及輕重儀僻謬之處”的敍述,而道宣在律學和中國佛教史上始終有崇高的地位,是以後人有意忽略。日本玄奘的聖化中,則兼采戒賢夢中菩薩的傳法授記和韋陀天的證詞,由此也可反映中、日佛教不同的環境和氛圍。迄於宋代,有關玄奘聖化的敍事極少,僅見戒賢夢中菩薩的傳法印記和少許玄奘圓寂前後瑞應的敍述。玄奘的聖化另以聖化的圖像、在經藏院設像供養等方式呈現,和晚唐五代以玄奘之名宣揚的經典、齋儀和禮拜法,頗有相似之處。也就是説,從聖化的文字敍述轉化爲實質上的宗教實踐。
入宋以後,玄奘聖化的潛流得以浮出地表,出現一些聖化玄奘的宗教文物,和舍利及遺迹崇拜。其中,最能顯示其聖化的是“大德寺五百羅漢圖”中,玄奘成爲其中的一員。上述玄奘聖化的敍述、文物和圖像,隨着入唐僧、入宋僧傳入日本,其後在鎌倉時代新、舊佛教競爭的環境之下,經法相宗僧人的規畫,有更進一步的闡發,透過不同文本的宣揚,使玄奘晉身爲護法神祇、菩薩,完成了玄奘的聖化。如在九世紀中國深沙神仰信初興時,係藉着玄奘將深沙神轉化爲護法神祇;到了鎌倉時代,深沙神信仰已經形成風潮,甚至進一步以玄奘和深沙神的組合,繪入十六善神圖中,將玄奘聖化爲護法的神祇。何以在中國玄奘的聖化未能畢竟其功、成爲神祇?以及宋代聖化玄奘的宗教文物,乃至於日本鎌倉時代玄奘的聖化等問題,將以另文討論。
(本文作者係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