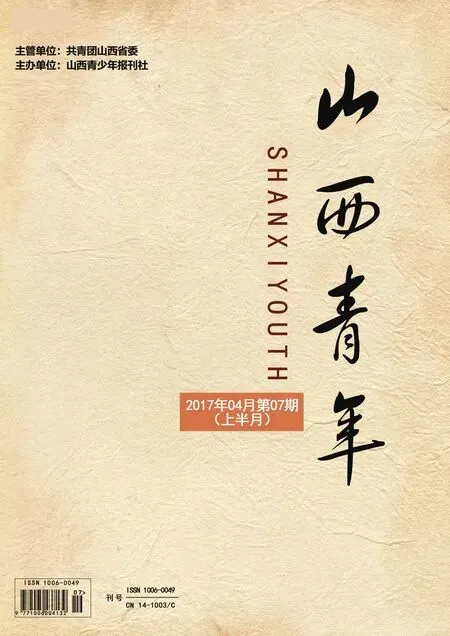镜中水晶*
——传统乌托邦文本的叙事模式
曲 宁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镜中水晶*
——传统乌托邦文本的叙事模式
曲 宁*
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西方有一个可观的乌托邦书写传统,这些文本有着大体相当的文体特征。本文试图引入叙事学视角对这些产生于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乌托邦文本的叙事结构做进一步的总结,解剖它们构筑社会理想的叙事过程中通用的机制。通过这些分析,本文也将重新审视乌托邦图景之理想维度说,在乌托邦理想作为现实之否定性反面的既定身份之下,寻找它们的现实构建身份。
乌托邦;叙事;镜像;有机整体
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思潮是在托马斯·莫尔爵士的《乌托邦》(1516)一书出版后渐渐形成的。一百年间,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01)、约翰·凡·安德里亚的《基督城》(1623)、培根的《新大西岛》(1626)、詹姆士·哈林顿的《大洋国》(1656)、傅立叶笔下的“法郎吉”纷纷出炉,更有乌托邦爱好者不仅仅满足于乌托邦构想,甚至力图将乌托邦文本中的种种社会构建方案化为现实,更是将乌托邦热潮推到一个高度。
这些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实践并未成功,其原因往往被归结到社会方案的幼稚天真、缺乏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与驾驭上面。但是如果后退一步对乌托邦传统做远距离审视,就会发现,乌托邦与现实间的关系无需在其内容中寻找,只需在其写作形式中即可找到表征。
一、乌托邦的镜像叙事框架
自莫尔以来,乌托邦写作已经形成了一种既定的文体,它的文体范式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直到今天,在处理同类题材时,大多数作家也都沿用着其中的特定形式。如果对16-17世纪最经典的乌托邦文体形式进行概括,一般来说它们都假设书中内容出自某位从海外归来的航海家同国内人士间的对话,一面批判当地的社会现实,一面讲出在乌托邦国度的见闻。乌托邦文本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包含了两个层面——一个是弊病百出的现实,一个是有千般好处的理想。原始范本《乌托邦》本身的篇章比例恰到好处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第二部对乌托邦本身的书写可以独立成章,事实上这一部分在实际的写作中也是先完成的,但是莫尔在出版该书之前还是增补了批判英国社会现状的第一部分,并使二者篇幅相当。于是一二两部就构成了一面镜子的内外两个图景:一面腐败横流,利欲熏天,充斥着各种不公混乱、乃至于羊吃人的怪状;一面不受钱物所扰,淡泊祥和,井然有序,人人勤勉节制,彼此尊重。莫尔的乌托邦之所以透露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形成了有效的精神感召力,就是因为在整个文本构成的语境中第二部分对第一部分的针对性。英国现状是乌托邦的反面,只有在前者的映衬之下,后者才格外被凸显为天堂。
这一重镜像作用事实上成为每一个乌托邦文本的基本预设。尽管到后来的文本中再看不到像莫尔一样将现实与理想两部分并举的篇幅设置,《太阳城》将莫尔式的对话与讲述编织在了一起,并将对话部分的评述限制在点到即止,不至于过分打断乌托邦讲述的程度;《基督城》取消国内人士和航海家两个角色,由作者直接出面,向读者讲话,对现状做了10页左右的嘲讽;《新大西岛》和《大洋国》则索性隐掉了对话,直接呈现乌托邦见闻。似乎后面这些文本在一点点弱化自己的乌托邦与现实之间的血脉联系,但是由于这几本书皆受《乌托邦》极大影响,因此不妨把它们在写法上的变换看成是同一文体中晚近文本所采取的叙事省略。那些隐没在背景中的社会现实共同构成了乌托邦镜像的一极,为文本自身的内容提供着合理化的支撑。
二、作为镜面存在的叙事
乌托邦文本的叙事层面将镜像两面的现实与理想连接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乌托邦叙事无论从叙事者的设置还是叙事自身的展开方式上看都努力做到坚实、平滑,波澜不兴,正构成一个完美的镜面。
可靠叙事者形象的塑造。在描摹乌托邦的情状之时,传统乌托邦的叙述人都被确立为一位可靠叙述者。这种可靠性是由乌托邦传统手创者莫尔通过两个步骤完成的。其一,是航海家的郑重引入。文中先有已经在社会上声名确立的莫尔自己出面做航海家的聆听者,并以附言的方式确保所记之事重要可靠,再由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引介,在航海家未出场之前替他做了一番盛赞,保证了其人品、见识、学养的可敬,最后,这位出众人物拉斐尔·希斯拉德才姗姗出场,开始了他的讲述。其二,是谈及乌托邦之前,拉斐尔与莫尔等人侃侃论及英国现状,他对社会各个领域概括力的透彻犀利,成为这个叙述人可信性的第二重保证。有了这些铺垫,在第二部分进行乌托邦的描述之时,读者就可以亦步亦趋地追随拉斐尔的引导,欣赏他呈现出的那无懈可击的完美国度。
架空的航海叙事套路。乌托邦引用和借鉴了一部分从新航路开辟起就方兴未艾的航海小说叙事模式,但是又对该种文体的叙事要素有重要选择性遗漏。如前文所述,为了向读者保证乌托邦描述的可靠性,乌托邦的发现者往往是现实社会中颇具名望的精英,而不单纯是鲁滨孙式的冒险家。在后世更为成熟的漫游小说中,冒险者初到一个陌生世界中,莫不会被大量新奇的感官经验所淹没,惊异、不解、好奇,乃至于恐惧都是应有之意。在对新世界的探索过程中,由于未知、误解和冲突造成的种种危机情况会频频出现,阻碍、延迟对该世界全面了解的完成,这种阻碍和延迟恰恰是此类文体阅读兴趣的重要来源。与正式的漫游小说相比,乌托邦的发现者却总是在来到乌托邦的第一时间就融入了这个全新的环境,很快对乌托邦的全部奥秘了然于胸。因为发现过程的顺畅,就消解了对新世界的发现的戏剧性价值,从而将侧重落实在对新世界构成机制的介绍上。
无情节的叙事。如果说航海或漫游小说人物在发现新世界过程中解决危机的不间断行动是推动情节前进的重要驱动力,那么对于乌托邦的发现者来说,行动已被弱化到极致。也许在所有乌托邦文本中,莫尔的拉斐尔要算是最有行动力的角色了,因为他来到乌托邦之后在了解乌托邦之余还将自己在技艺上的所通之处传授给了乌托邦的住民。其他乌托邦发现者在乌托邦之内仅仅作为学生与记者的身份存在,不曾参与或干涉过该地的任何活动。而乌托邦的居民也相应地仅仅作为没有猜忌心的好客者迎接来访或落难的外邦人,并且坦诚相待,热情地有时甚至是炫耀地忙着把自己的社会肌理组织一层层剥给来客观摩。此外成熟的漫游小说的冒险者在与陌生环境互动时动辄会遭遇生命威胁,所以时常对周围的世界持有某种程度的警觉式的批判。而在乌托邦文本中叙事人被打造成个性极其淡化、毫无个体识别度的抽象符号,被塑造为乌托邦社会“现实”的忠实摄录镜头,他们不必要对此地的人性与风俗持有任何的警戒或者批判,对方展示解说,叙事人忠实记录,没有理解上的疏漏或误会,也没有观念或利益上的戏剧化冲突。于是叙事者这个外来者就成为了乌托邦的可靠再现者、热心赞誉者和忠实传播者。
总之,乌托邦叙事尽管有着与航海小说相近的框架,但是却并无它吸引阅读注意力的那些实质性情节,这使得乌托邦在它的虚假航海小说的外壳之下,只剩下纯粹的宣教功能——宣说的,就是镜面那一端的理想国。
三、水晶状的理想国
乌托邦的描画者们往往在不同程度上是有机整体论者。这种情结当然与乌托邦理想的肇始者柏拉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将自己笔下的理想城邦比喻成一个大写的人,在这个城邦中,管理者、保卫者与生产者像头脑、四肢和躯干一般协调运作,共同支撑起城邦肌体的健康发展。有机体的比喻被后世的乌托邦写作忠诚地继承下来。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说这个城邦中所有人如此完美合作,以至于“就像人体的各部分一样,是紧密相连的”。①莫尔在《乌托邦》中像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一样,劝诫那些无法再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的乌托邦成员自行了断,②这当然也在暗示如此才能以保证国家的给养不至于无端消耗在这些已经无用坏死了的组织上。
然而有趣的是,从乌托邦自身的叙事模式上看,在那些平整光滑的叙事镜面里映现出来的,并不是一个个鲜活灵动的生命体,而像是一个静止不动的无生命晶体。
这一点同样在《乌托邦》上下两部分的叙事对照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一部以莫尔及其朋友和航海家拉斐尔之间的对话形式写成,最开端见多识广的拉斐尔就对莫尔提出这样一个怪现象,即在英国一桩小小的罪行却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于是从这个小小的线头,就牵出了对英国社会上下问题的一系列揭底。因此虽然并没有人物行动意义上的情节可言,但是仅就对话本身而言,这部分的话题展开仍旧很有动感,构成了一条不断延伸的线索,使社会矛盾盘根错节地相互衍生为一团混沌。待到第二部文本则剔除了其他的对话成分,成为可靠叙事人拉斐尔的个人独白。在这一部分中,拉斐尔在读者眼前一一描画出乌托邦的全岛布局、首府亚马乌罗提城的建筑模式、官员及其他职业在著名的公有制下如何各得其所、乌托邦的城际关系和邦交关系、乌托邦的价值观与哲学观等精神内核、其合乎理性的法治手段与战争策略和信仰自由的宗教状况,并得出以下结论:“我已经力求准确地对你叙述了这个国家是怎样组成的,认为这不但是最好的国家,而且是唯一名副其实的国家。”③在第一部中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在这里都已解决,一切解决途径的探索过程都已终结,这个国家仿佛一个彻底完成状态的理想标本。
第二部中对乌托邦状况描述的静态化的处理模式被完美地复制到了此后《太阳城》《新大西岛》《基督城》等文本内部,在这些作品中,乌托邦理想无一不结构整饬,逻辑通透,就像一块块完美的水晶一样被叙事者托在掌心,供读者膜拜。从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乌托邦的叙事者并没有真正在一个活着生命体意义上去对待自己构想出来的理想国度。生命原本就是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应对层出不穷的生存危机而不断成长的产物,混乱、复杂、错误与挣扎都是成长不可能回避的。而乌托邦作家们却希望创造出不再需要任何变化的“完美生物”,这就注定了他们的造物不可能穿越镜面,真正存活在现实之中。
四、镜中世界的距离
每一个乌托邦都是作家的理想结晶。在乌托邦文本中,这种晶体似乎就在镜子另一侧,与现实世界比邻而居,但是实则此类晶体的建构需要一个超验的立场和空间作为支撑,终究要隔绝于令人不满的现实世界。即使是在作者们虚构的笔下,它们也被安置在遥不可及的远方,需要航海家们只身冒死去往世界的尽头才能寻见。
富有反讽意味的是,乌托邦写作假托的航海叙事模式,是这个世界日益走向一个真正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之历程的开端形成的,而这些理想国之所以能够维持其完美结构,也多多少少要倚重于国际化的分工与交流:莫尔的乌托邦积累的大量财富并不来自岛上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而应拜国际贸易所赐;太阳城牢不可摧的城市防御工事也是靠着经常派学者团体到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的技术知识而建成的;同样当傅立叶在现实中着手筹建自己的法郎吉的时候,依赖的恰恰是作为工业生产内在逻辑的社会协作体系。
因此乌托邦的最大悖论在于,每一个乌托邦建构者都试图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理想境界,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脱逃出自己所在的社会现状。正如弗雷德里希·詹姆逊在《论岛屿与壕沟:中立化与乌托邦话语的生产》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乌托邦书写只是把对当下的意识形态的抽象和个体自己的社会幻想整合在一起。④故而乌托邦事实上只是把某种程度上的现实提纯为理想。与此同时,由于他们的镜像叙事模式卓有成效为其理想渲染上了水晶般的完美效果,在这种理想的传播和现实化过程中,又间接将原本处于萌芽状态的现实因素加以壮大和实现,完成了理想成就现实的作用。
在努力避免外界混沌侵害、力保自身独立性的乌托邦实践中,由于失去了与刚刚勃兴的整个工业文明的有机互动,被孤立在玻璃罩中的法郎吉幼苗很快自我耗尽,无以为继。但是在法郎吉中实验过的有机化社会协作机制如今已经衍生为全球性生产与消费链条。这样一来,说乌托邦文学是只能落空的幻想是过分贬低了它的作用。我们也许不能参照它提供的镜中图景建构一个全新世界,但是,现实世界仍旧在乌托邦之镜的映照下逐渐发生着形变。这本身大概就是对书写的力量最好的赞誉。
[ 注 释 ]
①[意]康帕内拉,陈大维,等.太阳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2.
②[英]托马斯·莫尔,戴镏龄.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87.
③[英]托马斯·莫尔,戴镏龄.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15.
④[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王逢振.詹姆逊文集·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0.
*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西方文论史中的有机整体论研究》(吉教科文合字[2014]第639号)阶段性研究成果。
曲宁(1981-),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I
A
1006-0049-(2017)07-002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