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遁逸之途”的独语者
杨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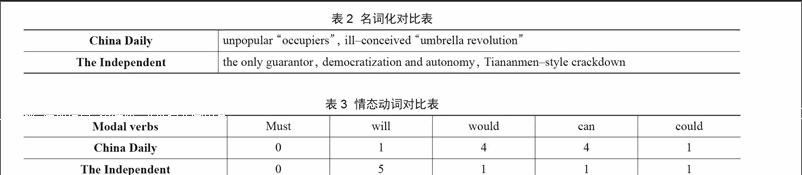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北京沦陷区诗化散文的创作群体,他们自己主办的校园刊物和围绕发表作品的刊物及刊物的创刊宗旨,参与撰稿的作家同人,以此说明他们实际上是一个围绕固定的刊物发表作品,在艺术追求上有着相对接近的倾向和趣味的,有意识地以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作为自己在战时历史条件下的文学选择的写作群体。论文认为可以将他们称为北京沦陷区“诗化散文的校园作家群体”。在创作上他们继承了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段和唯美情调,以类似何其芳《画梦录》所呈现的辞藻的诱惑和声调的沉醉展示了对人生的盲目与虚无的感慨,以及他们在遭遇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时的热情、过敏、幻灭、颓唐。
关键词:北京沦陷区诗化散文;校园刊物;唯美颓废
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仍然是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时期,战争猛烈地打碎了战前的文学格局,知名作家、学者和学术文化机构的南迁,内地许多城镇形成了新的文化中心和文学运动中心,具有二十多年光荣历史的北京新文学活动一时间戛然而止。但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启蒙,非常事件有着命运般的魔力,它毁灭一切,也造就一切。城市的沦陷并未带来文学的沦丧,日占区文学在法西斯肉体和精神的窒息中进行无声而有力的抗争,留京作家在“言与不言”的艰难中仍然保持着思绪的激荡。在北京沦陷区从事文学创作的大多是文学青年,他们在“强权政治的压力下”、在“为文难以维持生计的现实”中为文坛的重建做着孱弱而执拗的努力,这使北京沦陷区文学在一片冻土中曲折地生长起来。
北京文坛的复苏是以散文为突破点的。而文学文坛的复苏,标志之一就是期刊的出现。黄万华在《战时中国文学研究》中有过这样的论述:“北平沦陷后一个多月,《燕京新闻· 文艺副镌》借教会学校的特殊环境创刊,并为进步学生掌握,预示出华北沦陷区文学的生存将从校园文学开始。”1937年9月3日燕京大学新闻系师生创办的《燕京新闻》创刊,由陈继明任编辑。这是北平沦陷后第一份校园纯文学刊物,得到北平广大师生的支持。《燕京新闻》先后辟有四个文艺副刊,至1939年6月出至25期后,改为《文艺》周刊,发表新文学作品及评论。主要撰稿人为燕大的学生,如秦佩珩、毕基初等,辅仁大学的学生林榕、查显琳、毕基初等,以及校外知名作家周作人,徐訏等,此外也刊有教师郭绍虞、阎简弼等人的作品。
1939年4月,由燕京大学学生秦佩珩与辅仁大学学生林榕等人所办的大型文学刊物《文苑》在北京创刊,这是北京校园文学开始活跃的重要标志。《文苑》的创办,“本着在日本军事占领下荒凉的北方文艺界编辑一份‘友谊的纯文艺集刊,为爱好文学的同人开辟一方写作实习和互相批评的园地,为同学们提供一种可读的课外读物,以别于公开推销的庸俗刊物的宗旨”,作者多为青年学生,如南星、李道静、李曼茵、张秀亚、查显琳等,以散文数量最大,内容大多与现实社会联系少,多描写自然风物,回忆故园故友,以及描写身边琐事,抒发一己哀愁。之后,《文苑》由校方接手,成为正式的校刊,名称也改为《辅仁文苑》。《辅仁文苑》被认为是一种“附属学校中的刊物”, “迈着绅士的步伐”,在那个十分恶劣的环境中,作者们不与日伪当局提倡的文艺发生关系,坚持文学纯粹的审美经验,“回到各自的内在,谛听人生谐和的旋律”,“根据独有特殊的感觉,解释各自现实的生命”,从而达到某种内在的真实。在那个鬼魅横行,噤若寒蝉的时代,展示出另外一种美丽,给了我们一丝慰藉。这个团聚了许多青年作家的文艺刊物,成为北京沦陷时期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独语体”散文作家群体驰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阵地。
1939年,纯文艺半月刊《篱树》创刊。该刊只办过两期,由几位燕京大学学生与南星联合,每人凑五元钱创办的小刊物,同人成员有秦佩珩、毕基初、林榕、李道静、吴兴华等,主要发表短小的诗歌与散文。次年5月,燕京大学出版文艺丛刊《燕园集》,刊有诗论,以及秦佩珩、南星、林榕、毕基初等人的散文和诗歌。北京大学文学院还创办过三个文学刊物,但均只出版一期,“以诚实向上的纯文艺月刊为号召”,集结了一批青年作家群体。其中《诗与散文》(1939)分别刊载了周作人、沈启无、张我军、闻国新等知名作家的诗文,以及南星、林榕、秦佩珩、李道静等沦陷后青年作家的作品;《文艺杂志》(1941)则继承了战前北京学界新文艺的传统,与沦陷区的现实政治和通俗文化没有关联,发表作品的作者,如南星、李曼茵、李道静、林榕、闻国新等在华北沦陷区文坛都比较活跃。学生刊物《北大文学》(1943)刊有李道静、黄雨、闻国新等人的小说、诗歌、散文,沈启无、林榕、傅芸子、日本增田涉的论文及钱稻孙、朱芳济的译文。
这样,在沦陷后的短短两三年之间,南星、林榕、秦佩珩、毕基初、麦静等人围绕着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几个校园刊物,发表了为数可观的一大批诗文作品。校园刊物成为他们沉醉在个人艺术世界中尽情驰骋无羁想象与幻想,书写个人幻美、苦闷和忧伤情感的园地,成为继战前三十年代何其芳“独语体”式散文创作之后的又一个诗化散文创作浪潮,构成了沦陷初期冲破北京沦陷区文坛死寂局面的第一股潮流。《辅仁文苑》之后,他们的创作在青年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最终冲出校园,开始在民办刊物(《朔风》、《艺术与生活》)和官办刊物(《中国文艺》、《新民声半月刊》)上发表作品。
南星、林榕等人在综合性民办文艺月刊《朔风》上发表了许多“空灵的抒情文章”,与周作人式的“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有别择”等“趣味而有分量”的小品一起,构成了“一种新中国之文学运动”。《朔风》主编为方纪生,是个“躲在象牙塔里面,不想走出十字街头一步”,不谈政治时事的纯文艺刊物,以向中产阶级提供精神食粮为目的而创刊,它成为死寂的华北文坛开始运作的起点与标志。而以“宣传艺术,提倡高尚娱乐,灌输知识,安慰工余的寂寞”为创刊宗旨的《艺术与生活》,则由个人集资筹办起来,本着“尽量提拔新人佳作”的初衷,培养了一批有影响的青年作家。其中刊出了南星、李曼茵、毕基初等人的诗作专辑,林榕、秦佩珩等人的散文专辑,在异族的殖民统治下,展示了被压榨在生活齿轮下的人们生命的悲凉和思想的寂寞。
从1939年9月出至1943年11月的《中国文艺》是北京乃至华北沦陷区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官办文学期刊,也是南星、林榕、秦佩珩等人的诗化散文创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尤其是《中国文艺》于1941年由林榕接任之后,编辑方针发生了变化,“取消了掌故和影画方面的内容,加强了文学创作”,“力求刊物朴素化,为新作家提供版面”。这一时期,南星、林榕等人的创作也由沦陷初期青年的感伤进入中年的沉郁。林榕更是以“上官蓉”、“林慧文”、“楚天阔”、“慕容慧文”等笔名在“文艺谈”专栏发表了一批分析文坛现象的短论。《中国文艺》最终在华北沦陷区所有有影响的新老作家的努力下有了“新生与活泼的气象”,于官办的性质中为自身的发展争得了独立的文学空间,以纯文学、新文学为正宗,成为华北作家进行文艺创作的文学阵地。
散文在这一时期的流行,除了因为《朔风》、《中国文艺》、《晨报》等刊物的提倡,以及在局势还不明朗的转折期成为作家一种无奈的选择之外,还应该看到,事变后北方文艺界的主潮是散文,散文先于其他文学体裁获得成功,与五四新文学时期存在着某种相似。或者应该这样说,战前作为新文学中心的北京由于战争元气大伤,中国文化中心的南迁和战时中国文学格局的改变,使得其新文学的传统力量被削弱,加上异族统治压抑的文学环境,意外地将这一地区的文学推入一种开放性的格局当中,“回归‘五四成为这一地区文学思潮的重要指向。通俗文学作家、新进作家不同程度地在延续、反思‘五四中调整创作格局,甚至可能使五四时期未来得及充分从容展开的新文学因素得以开掘。”这种“回归”在小说领域表现为一种向五四时期文学回归的现实主义,即借五四时期表现人生的文学观念,在不同层次上开掘异族统治下中国人的心理人生,以及有着复杂心态的知识分子形象、市民形象和劳动者形象;在散文上则表现为对五四时期转向书写内心的创作观念的回归,以个人抒情的真实性和独特性折射出炼狱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尤其是一些新进作家,如南星、林榕、秦佩珩、毕基初、黄肃秋、麦静等人的散文。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上述散文创作的情状,研究者张泉认为:“华北沦陷区的散文被后人不适当地摆在过于显赫的位置上。一方面,由于散文小品是一种‘谁都来得的样式,大批初涉文艺的青年学生往往首先对此作尝试,因而在数量上显得比较大;另一方面,尽管‘华北唯一作家周作人从未有意提倡过,但他的大名及作品在出版物上频频出现这个事实本身便很容易使人造成散文繁荣发达的错觉。实际上,散文的水平和影响在当时都不是很大,只是在华北文坛刚从死寂转入复苏时曾一度较为突出。”我认为情形恰恰相反,在华北沦陷区文坛里,散文较之于小说或其他文体,更易获得写作者的亲睐。相对于其他文体,散文较为清淡简短,形式不拘,灵活性比较大,成文比较容易,初学者往往先从散文开始,即便是成熟的作家也因为散文题材广泛,所写内容涉及宇宙之大,苍蝇之微,以个人的情感和生活为主,容易避开尖锐的社会现实而致力于散文写作。因此,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散文的繁荣是必然的,这一点不容忽视。
估且不论年青作者往往从诗歌与散文的写作上起步。应当说,当战争到来,生命与生存的主题往往最易引发年青人对生存,对人类命运,对生命的意义等问题的痛苦思考。校园刊物成为他们书写文学青年的赤诚和热情的一方净土,“不附庸流俗,也不屈从淫威”。这也是他们于异族统治和伪政权的制度机构限制人的生存空间、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的现实中唯一的选择。他们在暴戾的战争面前继续守持着生命本位,艺术本位的原则,捕捉为生活表象所遮蔽了的生命本质。他们延续着三十年代何其芳式的书写孤独者灵魂的独语和空灵幻想的独语体散文体式,用散文的形式写诗,通过散文的外在形式表现出诗的本质和灵魂。他们疏离人群,无意甚至有意拒绝与人对话,以阴冷的意象和抑郁的氛围一意诉诸自我孤寂的内心。
梦中有斑驳的影像和匆促的形骸……我欲向记忆去摆渡,发现自己的心年久而凋废了,如一个僵硬的空洞的树干,它不会紧紧地怀抱什么,只做了蛇鼠的隐身处,那奇异的地方是黑暗的,永远得不到阳光的访问。有时候一只啄木鸟停在破裂的外皮上,用它的长嘴有节奏地敲击着,正像一个更夫敲击着目坼,而那破裂的外皮已不会再生新芽,只有那夜半后柔和的淡白的月光依旧。
南星的这篇《沉忧》在感伤柔和中把自己对理想的追求与幻灭的感情世界倾注于象征的意象中。我们不妨将这篇作品看作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知识者的一种共同的沉忧。作品中描绘的石桥,街巷,浓雾,夜犬的阴霾氛围可以认为是作者所感受的时代气候的一种象征。而自己是孤独而软弱的梦中人,悠深的黑暗与压抑的环境强化着作者抑郁、迷乱、幻灭的痛苦与惆怅,这也是其个人乃至一代青年内心复杂情绪的象征。
至此,北京沦陷区这一批立足于在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中透露梦境般的独语的青年作家的诗化散文创作,走过了在象牙塔中呓语的校园文学萌芽期,经历了民办刊物与官办刊物的锤炼与洗礼,登上了整个华北沦陷区散文创作的舞台。这样,在苦难深重而阴霾密布的国土上徘徊着一个诗化散文的校园作家群体,他们以象征的朦胧歌声唱出寂寞痛苦的内心世界,以何其芳《画梦录》式的精致玲珑的意象,纤弱狭小的境界,浓丽迷离的色彩,细腻感伤的意绪,丰富了诗化散文创作的内容与形式,成为三十年代唯美而颓废的诗化散文在四十年代华北沦陷区的继承与延续。同时,这批创作,在意象的象征性与情感的暗示性上将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延续下来,并与四十年代西南联大师生、九叶诗人的新诗现代性尝试遥相呼应,使五四新文学的某些艺术传统避免了中断。同时,在这些新进作家的散文中既沉积了古典传统文化的诸多元素,也汲取了多个源头的外国文学营养,呈现着某种开放的形态,这些在战时的历史时期中都有着独特的现实意义。
注释:
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黄万华:《史述与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方纪生:《朔风室札记》,《朔风》第1期,第43页。
周作人《苦竹杂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方纪生:《朔风室札记》,《朔风》第1期,第43页。
徐迺翔, 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页。
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黄万华:《战时中国文学——可以一再被审视的文学空间》,《求索》2005第6期,第150页。
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0页。
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转引自黄万华:《史述与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702页。
参考文献:
[1]耿德华著.张泉译. 中国沦陷区文学史[M].新星出版社,2006.
[2]钱理群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M].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
[3]徐迺翔,黄万华主编.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M].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4]张泉著.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M].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4.
[5]黄万华著. 史述和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6]钱理群著.言”与“不言”之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1).
[7]谢茂松,叶彤,钱理群著.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40 年代沦陷区散文概论[J].北京大学学报,1996(1).
[8]黄万华著.论沦陷区作家的心态及其文学的基本特征[J].华侨大学学报,1995(2).
[9]黄万华著.战时中国文学——可以一再被审视的文学空间[J].求索200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