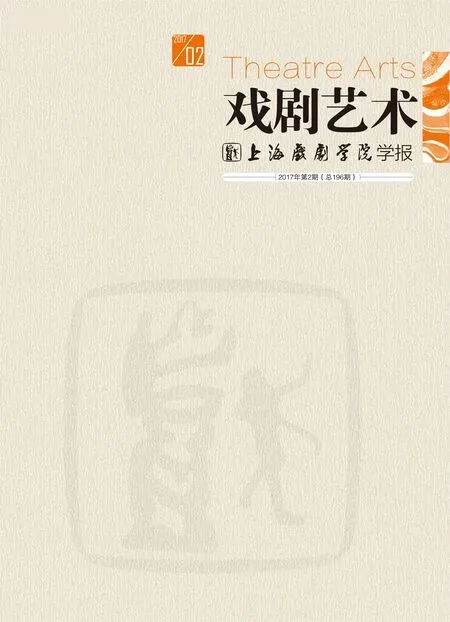他们的下场与上场:在门上装一个把手
[美]阿诺德·阿伦森 著
杨 蕊 译
他们的下场与上场:在门上装一个把手
[美]阿诺德·阿伦森 著
杨 蕊 译
自公元前460年左右,希腊戏剧舞台上最早使用门作为布景开始,便彻底改变了悲剧的节奏,可因门所创造的幻觉使各个场景交切,显示出几个时间和空间同步进行的效果,门的存在可以用于隐藏亦能用作揭秘,其创造出的想像世界意蕴丰富。剧场中的门代表着台上世界与台下世界的通道,演员自门“上场”,他们的身份由普通人得以转化为戏剧角色,电视情景剧中“未上锁的门”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几乎所有的舞台、电影、电视剧的房间都设置了门,然而戏剧舞台上的门却与电视中的门有着千差万别。门打开,信息便涌入;门关上,信息便终止流动。门槛的魔幻色彩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保留了格外郑重的仪式感,没有了门,就没有了宏伟的下场,因此也就没有真正的结尾。
戏剧 舞台布景 门 隐喻
若论及20世纪90年代美国流行文化的重要标志,电视情景喜剧《宋飞正传》不容忽视:杰瑞·宋飞的公寓门被猛然打开,接着那扇门仿佛具有自主意识一般把紧紧抓住门把手的克雷默拖进房内,一股似乎来自于另一个宇宙的狂躁力量就这样强力地刺入杰瑞·宋飞原本平静,甚至略显荒唐的世界。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为我们所熟知的电视情景喜剧的戏剧节奏:20世纪50年代的《蜜月新人》中,与克雷默搞怪程度旗鼓相当的艾德·诺顿,侵入了拉尔夫·卡拉门登冷漠的世界;或是在同时代的《我爱露西》中,看似亲切的埃塞尔·梅尔兹(这个名字或许是暗指库尔特·施维特斯的达达主义分支)忧心忡忡地打开了通向露西那个疯狂世界的大门。
长久以来,门无论是在情景喜剧还是戏剧中都是一个屏障:一个将一切混乱挡在外面的壁垒。然而,它却极易逾越。外面的无序和混乱可以毫不费力地潜入,从而轻易打破虚幻的现实。在每一剧集的结尾,和谐与平衡都会暂时回归,直到下一周来临前,剧中的门都被紧紧关上,门内角色与接下来的故事就停留在了未知状态。
几乎所有的舞台、电影、电视剧的房间都设置了门,剧中角色来来往往,门被打开又再度被关上,然而我们却很少注意到门这一布景,除非特定的情节设置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门上,如演员夸张而滑稽地从门而入、躲藏到门后,或者为了营造恐怖的气氛使一个门吱吱作响。究竟什么是戏剧?戏剧不就是一系列的下场和上场吗?“上场”几乎是即兴喜剧剧本中最常见的语汇,这就使剧本实则成为一个关于“门”的目录。而“退场”这个词正标志着莎士比亚戏剧的节奏,因为即使在莎士比亚时期的舞台上,安提戈涅“被熊追着下场”时也是穿门而过的。“门”代表着起始与终结,标示着人来与人往。
同样地,计算机的基础语言是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数码,用来表示数字通道的连通或阻断。一幕喜剧场景或电视情景剧场景,其实也是一个二进制系统——门打开,信息便涌入;门关上,信息便终止流动。马克斯兄弟主演的电影《歌剧院之夜》中的“大客厅场景”便是一个经典的例子。电影中,格劳乔的船舱像衣柜一样小,但他仍在他的扁平行李箱里发现了三个偷渡者:奇科、哈珀以及影片中爱情故事的男主角艾伦·琼斯。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清洁工、上菜的服务生、修甲师以及水管工等纷纷进入船舱。就这样,这个狭小的空间随着舱门一次次打开逐渐陷入混乱。按照我们的比喻性说法,信息终究会超载,整个系统会崩溃,结果就是:船舱里的人破门而出,蜂拥冲向大厅。
于是,这扇门创建起一个节奏,就像节拍器击打出的一样,不仅动作规整而且建立期待。一旦我们懂得这种架构,我们便开始热切地期冀门在下一次被打开时涌入的信息。但同样重要的是,舱门同时也建立起一个界限,这个界限将船舱的狭小幽闭与整艘船的宽广开阔划分开来,也将有序与混乱、有规则的世界与无逻辑的世界分隔开。穿过那个舱门便是从一种存在状态跨向另一个状态,或是从一个世界跨向另一个世界。
众妙之门
接下来,我将阐述门的三个方面。首先,门在舞台上的引进如何助力悲剧的塑造。其次,为什么情景剧里纽约市的公寓门总是未上锁的?最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门与过去两千五百年里出现在戏剧舞台上的门是否一样?
尽管人们一般并不将门看作一种发明,但我却认为从舞台工艺和布景上来看,门的使用是戏剧史上的一大进步。它是如此显而易见、不可或缺,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没有门的戏剧是什么样子。然而,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希腊悲剧刚刚出现时,舞台上并没有门。当然,门在那个时候已经存在,但对于一个商业和政治活动基本都在户外环境中开展的社会来说,门的作用显然并不突出。也许这样听起来有些奇怪,但的确是到几十年后,才有人想到在舞台上设置一个门。“无门”时代的悲剧与之后“有门”时代的悲剧有着巨大差异。门的引进产生了实际影响,它改变了戏剧的结构与节奏;同时,这一看似简单、无伤大雅的举动也在隐喻、象征以及哲学层面上对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门的引进,划定了两重不同的空间: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已知的与未知的、有形的与暗含的。正如20世纪60年代,大门摇滚乐队主唱吉姆·莫里森所说,“有些事情是已知的,有些事情是未知的,而将它们分隔开的是门”。(这或许援引了奥尔德斯·赫胥黎所著《众妙之门》中的语句,该书是关于幻觉类药物的,书名则源自于威廉·布莱克的诗句)。卡尔·荣格这样描述梦:“在灵魂最深、最隐蔽处隐藏着的一扇小门,它通向宇宙最初期的黑暗,而灵魂早在清醒的自我产生很久之前便已存在了。”[1]
戏剧的作用就在于,它是人类社会一个共同的梦,是一扇通往人类灵魂深处的门。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即使舞台上的门有时看起来只是为一场可爱的闹剧而设,但它的声音都会激荡在人类的灵魂深处,因为门每一次被打开,宇宙的无限可能会立刻彰显出来;而每一次门被关上,所有的可能性立刻消失,我们就会体验一种不同形式的死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门作为在舞台上创造出的界限,却使得剧作家在剧场中的创造性失去了界限,无限可能性都会被释放出来。
戏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场与离场。或许,戏剧最基础的形式之一就是我们与小孩儿玩的“躲猫猫”游戏。我们会躲藏起来,时而偷偷地探出头看看,而他们可以一直欢快地找寻几个小时,在大摇大摆行走的同时,一会儿因害怕找不到而怅然若失,一会儿又因意想不到的发现而愉悦地咯咯傻笑。我们成人实际上也在玩这个游戏,只是我们将它称之为戏剧。剧场中,幕布之后隐藏着一个我们所好奇并期待的世界,所以当大幕拉开时我们通常会鼓掌,甚至激动地屏住呼吸。然而,即使门在当代戏剧中已稍显过时,它仍远比幕布更强大,因为在紧闭的门背后存在着未知的希望或恐惧,而开门同时象征着希望与失去。W.H.奥登《探索集》中的一首诗《门》似乎领略到了门的这种特质。
我们害怕时用一切堵住它,
我们死时则敲击着门格,
由于偶然打开一次,它使得
巨大的爱丽丝看见了奇境,
在阳光下等待着她,而且,
由于自己太小,使她哭得伤心。
有一句流传已久的戏剧谚语,通常适用于易卜生的名剧《海达·高布乐》,即如果有枪在第一幕中出现,那么它一定到最后才会响。如此我不禁推想,如果门在第一幕是紧闭的,那么它一定在最后一幕才打开,反之亦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于一扇锁闭的门,而现代话剧也往往被认为是以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的最后一幕,即娜拉甩上房门为开端的。尽管我们从未真正见过那扇门,但娜拉的出走对角色本身,对戏剧甚至于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意义深远的变革。还有契诃夫的《樱桃园》,一开始是让涅夫斯卡娅夫人和她的随从回到家并穿过门进入房间,而结束时的场景是剧中人物都纷纷离开,关上身后的门,只留下男管家菲尔斯,被独自锁在里面面对死亡。
事实上,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出希腊戏剧舞台上最早用门作布景的时间,即公元前460年左右。我们是根据创作于公元前458年的埃斯库罗斯三部曲《奥瑞斯提亚》判断的。它与之前的戏剧截然不同,很显然一定有什么东西的出现改变了悲剧的形式。那件丰碑式的东西就是门。任何先于《奥瑞斯提亚》的现存戏剧,如《波斯人》、《七将攻忒拜》、《女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都不需要门或是其他类似的舞台构造。例如,《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崎岖的山顶,而《女仆》则是在开阔的户外。因此,从目前收集到的证据来看,《奥瑞斯提亚》之前的大多数戏剧是“没有门的”。
“奥瑞斯提亚”之前
试想一下,在公元前五世纪早期,处于“无门时代”的狄奥尼索斯剧场在城堡的山坡上刚刚建好,观众席的木椅嵌在帕台农神庙的岩质边坡里,人们从那里俯瞰沿斜坡而建的乐池,也就是演员和合唱团表演的地方。除了祭坛,平台上空无一物。管弦乐队的后方是祭拜狄奥尼索斯的庙宇,周围一个开阔的乡村景象清晰可见。在现代的剧场里,观众都是在一个黑暗密闭的空间里比肩而坐,凝视着人工照明的“匣子”,而古希腊的观剧体验与此大为不同,那时候的人们通常都是一边沐浴着地中海明媚的春日晨光,享受着宇宙中心的荣耀,一边观赏着改编后的神话故事。
为了使大家更加清楚地了解“奥瑞斯提亚”之前的戏剧,我们在这里试举一例。例如《波斯人》,这部剧与其他希腊悲剧一样,一开始都是合唱队上场。但舞台没有侧面,舞台上也没有门或者幕布,他们是怎样上场的呢?他们一般是从乐池后穿过很长一段路向观众走来的。这当然需要一些时间,于是观众便可以看着他们逐渐走入视野,就好像慢慢出现在地平线上一样。或许他们在走向舞台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歌唱了,而行军的旋律就是他们抑扬的曲调。他们终于登上舞台,接着便开始唱歌跳舞,在第一首颂歌即将结束时我们会看到一个演员沿着管弦乐队后面的路径慢慢走来,可能是怕我们没有注意到她或不知晓她的身份,这时合唱队就会唱:“但是现在,她来了/一束如同上帝双眼一般辉煌的光/我们国王的母亲,我向您屈膝。”[2]接着继续唱七句歌。
皇后的出场当然需要一个奢华的介绍,但合唱队唱诗的台词长度主要取决于演员行进至舞台的距离。实际上,从演员出现到他登台的这段时间里,合唱队都是在即席演奏。在演员逐一粉墨登场的时候,我们会体味到希望、期待、厄运、恐惧或是乐观。然而我们唯一无法感受到的是惊喜。早期希腊戏剧的上场是列队行进式的,演员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依次登场。当最后一个音符淡出时,演员才开始下场。
然而,舞台布景,尤其是门的引进彻底改变了悲剧的节奏。现在,人物可以突然出现或迅速消失。仅仅因为门的出现,列队行进式的节奏被现在称为的影片节奏的形式所取代。现在,戏剧中如有一系列动作,不需要再在舞台上实时进行,因为门及其创造出的幻觉能够使各个场景交切,显示出几个时间和空间同步进行的效果。所以,如果戏剧家曾因舞台上动作需实时进行而苦恼过,那他们现在再也不用担心这个了。
通往想象世界之门
《奥瑞斯提亚》是现存戏剧中最早要求使用门的。剧中专门参照了一个宫殿的设置,宫殿内外有很多入口与出口,在宫殿“里面”还会发出声响表明内部有动作发生。《奠酒人》和《欧墨尼得斯》这两部剧在表演的过程中几乎恣意地更换场所:《奠酒人》一开始是在阿伽门农的墓前,随后转到克吕泰墨斯特拉和埃癸斯托斯宫殿外部,之后进入宫殿内部,最后再度回到宫殿外。而《欧墨尼得斯》开始是在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外,随后转移到庙宇内部,接着移至雅典的雅典娜神庙,最后结束于元老院的法庭上。
有了门,埃斯库罗斯像是被赐予了一个新玩具,怎么玩也玩不够。门能够使各个场所随意转换,但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创造了戏剧。观众们通过门后传来的阿伽门农撕心裂肺的哭声,便知道了阿伽门农与卡珊德拉被杀的讯息。12句的颂歌追随而至,紧接着最重要的事件发生了。那扇门打开了,我们看到了浴室里阿伽门农的尸体,身上裹着一个紫色袍子,卡珊德拉的尸体横在他的身上,而克吕泰墨斯特拉则耀武扬威地立在一旁。
成就这个场景的便是门。如果没有门,那么遇难者的哭喊声必须从山坡下传来,尸体也要被举着走过遥远的山路才能向观众宣告他们的死亡;不然他们被谋杀的过程就需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观众眼前。尽管在古希腊时期对于舞台上的暴力并没有明文禁止,但暴力却很少出现,这完全是出于实际性考虑:希腊剧作家清楚地明白,谋杀过程无法通过表演在舞台上逼真地重现,即使可以,其效果也远远不如观众无拘无束的想象力。我们可以尽情想象门后发生的事件,那可怕的尖叫声引发的恐惧远比舞台上能呈现出的任何谋杀场景都大得多。
门可以用于隐藏,用于揭秘,也可以用于再度隐藏。在《奥瑞斯提亚》之前的“无门时代”,剧场空旷又开阔,这种情况下“尸体”是怎样处理的呢?两种方案:一是把“尸体”抬下去——这种方案略显尴尬,二是扮演“尸体”的演员唐突地起身,自己走下舞台。而一旦引进了门,这时候只需在揭露凶手后将门关上,在观众脑海中留下屠杀的记忆,之后“尸体”常规地离开即可。
简单的门框和门廊改变了人们对剧场的认知。当然门背后的场景并未有任何改变,还是观众在前一年盛典上看到过的那个雅典乡村,只是那时没有门。但现在,加上门之后,幻觉就开始起作用了。如果《阿伽门农》中的门代表的是阿格斯的宫殿门,那么每一个穿门而上场的人都会被理解为是来自宫殿的。即使观众并不能真正看见宫殿里的场景,他们也会开始想象宫殿内各式各样的房间。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阿格斯而非雅典。
在莎士比亚时期,门创造出的想象世界之意蕴更加丰富。当哈姆雷特第一次通过门上场时,他所处的是埃尔西诺的宫殿。更重要的是,尽管我们明明知道演员是刚从学校赶过来的大学生而非真正的王子,但我们仍坚信如果我们也能穿过那扇门,一定会有一架四轮马车在路边等着,将我们带回威腾伯格。这就是一扇门可以创造的魔力。
门的隐喻意义
戏剧实则就是一种转化。剧场中,一个普通的人会被转化成美狄亚、哈姆雷特、战士的鬼魂或是一只会跳舞的猫。与此同时,一个原本普通的空间也发生了转化。简单的舞台可以突然变为“法国开阔的原野”、底比斯宫殿的前院或是郊区一个房子的客厅。无论舞台的形状、结构如何,都是一个能够转化任何事物的魔法阵。不过,想进入这个魔法阵并非易事。在歌德的《浮士德》中,靡菲斯特一定要被请进浮士德的房间:
浮士德:敲门?进来!谁个又来纠缠?
靡非斯特:是我。
浮士德:进来!
靡非斯特:你应该要说三遍。
浮士德:好,进来! (第四幕,1-5)
上场的过程转化了靡菲斯特,此时他成为了人形,这展现出戏剧的隐喻意义。我们如旧日一般等待着演员进入我们的视线,演员穿过门登上舞台,他们便被转化了。在传统的法国舞台上,这出戏开始时要在舞台的地板上重重地敲三下,表面上这当然是给观众以信号,告诉他们戏剧马上开始,但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召唤地下灵魂的仪式,之后这些灵魂就会在大幕升起时穿门而过,神奇地变成演员。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电视情景剧中的门“永不上锁”。《宋飞正传》中的克雷默和其他角色延续了蒙面即兴喜剧的表演形式。这种蒙面形式极可能是继承了中世纪恶魔小丑的表演(丑角的拼缝服装可能源于中世纪圣诞狂欢主持人反穿打了补丁的夹克衬里),而恶魔小丑表演法可以在民间表演仪式上顽童与骗子的形象中寻到踪迹。
换言之,艾德·诺顿,弗莱德,埃塞尔和埃迪·哈斯凯尔以及其他类似的角色都是恶魔。因此,他们除非受到正式邀请,否则是无法参与舞台上呈现的人类正常生活的。但就像德拉库拉从打开的窗户上场一般,未上锁的门也提供了一种不用敲门便可进入的永久通行证。于是,这些恶魔便可以自由出入了。
但是,他们是从哪里进来的呢?事实上,当然是从无聊甚至有些混乱的后台,一个与观众的舞台幻想几乎毫无关联的地方。然而,舞台强大的象征意义暗示出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看不见,却存在着。当我们看到一个演员穿过门上场时,我们瞬间明白他或她由室外进入室内、由一个房间进入到另一个,抑或是传统的舞台演出说明中经常用到的,来自“森林的另一边”。当然,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并不通过门从森林的一边穿到另一边,但对于舞台上的门,我们并不需要咬文嚼字。在这里它们只是代表一种通道,以此承担着其在剧中的功能,进而开展剧中的生活,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在剧中的作用并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在我们自己家里,门将房间隔开,将室内与室外划分开来;而在剧场中它们则代表着台上世界与台下世界的通道。在莎剧的舞台上,舞台后墙很有可能安装着一两扇门,所有演员都通过这些门上场和下场。有时由于参照了现实世界,这些门的设置十分符合逻辑,如当哈姆雷特进入到格特鲁德的卧室,通过门就会合情合理;当福斯塔夫来到奎克利夫人的酒馆,穿门而入也是理所当然。但是我们看一下《李尔王》的第四幕第四场,“克迪利亚,医生与士兵伴随着鼓声与飘扬的旗帜,进入法国营帐”,或是《麦克白》一开场,“雷闪交加,三个女巫上场”,会发现他们也都是由门而入的。
门的设置是戏剧表演的传统手法。在英格兰复辟时期,剧场的幕前左右两边各建造了两扇门,演员由此上场、下场。这样一来,便使得“上场”“下场”成为了演员的专用词汇。到了18世纪,剧场管理人为了容纳更多观众(赚更多钱),不断地缩小幕前的舞台空间,一开始只是两边各除掉一扇门,最终两扇皆被取缔。对此,演员一直表示强烈的抗议,因为他们需要门。1810年,科芬园的管理层态度有所缓和,因此又重新装上了门,但是很快它们又被拆卸下来,于是戏剧由戏剧化走向了现实化。现在唯一能在舞台上找到的门都存在于舞台布景内,并通常是用来描绘客厅的。如果门是舞台建筑的一部分,我们便处于戏剧性的环境中;但如果是舞台布景的一部分,那我们就处在幻景中。
外与内的辩证法
门是一个临界点,划分了两个互不从属的空间界限。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其著作《空间的诗学》中提出了“外与内的辩证法”这一说法。他这样讲到:“门是一个半开放的宇宙。这至少是半开放宇宙的初步形象,一个梦想的起源本身。这个梦想里积聚着欲望和企图——打开存在心底的企图,征服所有矜持的存在的欲望。”[4]
门槛带有魔幻色彩。孩子们会避免踩到门槛,一些成年人也会暗自这样做,因为长久以来都存在着踩到门槛会招致厄运的迷信。自古埃及时期起,很多文化都保留了背着新娘跨过门槛的习惯。新娘作为一个新嫁到丈夫家的陌生人,这在某种程度上能保护新娘不会触犯到婆家住宅的守护神。
很多文化中都存在着门神这种形象,他会保护主人的进出平安。在某些文化中,护身符或幸运符咒会被埋在门槛下——至今犹太人仍然在门框上挂门柱圣卷来提醒自己,神会依次地保护前来家宅与来访的人。回想起《圣经》诗篇:“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121:8)门因而成为了拯救的象征。《新约全书》“圣约翰的福音”中,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门通向两个空间,两个世界,这也使得门似乎有了些危险意味。这就是为什么鬼神在童话故事中总是住在桥下的原因。《圣经》中有很多罪人或非信徒因跨过一个门槛便死去的故事,恶魔邪恶地等在门外的故事,穿过门就是赎罪仪式的故事以及门槛的保护人、看守人的故事等等。正门通常也是献祭的地方,或者是妥善保管物品的地方。
几乎所有文化都相信天堂、地狱、异世界或者其他这种灵魂与亡灵栖息的空间的存在。几乎所有情况下,现世与冥界只是一门之隔。在埃及,想要通往异世界要通过12扇门;死亡之神奥丁款待英灵的瓦尔哈拉殿堂有540扇门;约翰·韦伯斯特的戏剧《马尔菲公爵夫人》有句台词这样说道,“我知道死亡有万扇门/让人们自己去找寻出口。”(第四幕,第二场)天堂、地狱、伊甸园都拥有各自的门。但丁的《炼狱》第九部专门讲述了炼狱之门,天使坐在坚硬的石头门槛上,给路过的人两把可以使他们通过的钥匙。
因此,登上舞台并不仅仅只是通过一条走廊那么简单了,它的意义更为深远,或者可以说是性命攸关的大事。西方戏剧丢失了上场这件事的仪式感,也削弱了本该带来的恐惧(尽管很多演员会在他们上场前心跳加速,但是怯场和对死亡的恐惧是完全不同的)。台上与台下的象征如此强大,充溢在台本的字里行间。亚洲经典的多样化的戏剧形式仍保留着这种仪式感,特别是日本的能剧。能剧的故事情节总是讲述着神与鬼还有过往的事件。演员并不是进入一个幻想的空间,取而代之的是,演员们会穿过一扇门帘,在倾斜的舞台通道上行进,途经的三棵树代表着天堂、地球和人,最后抵达故事上演的矩形舞台。演员穿过门帘,便化身为剧中人物;当演出结束时,剧中人穿过门帘下场,又回归到演员。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能剧的仪式感就像是以文字形式展现了这个过程。
日本的歌舞伎也使用了相似的手法。作为开场,衣着隆重的主演穿过通往礼堂的门,然后沿着花道(日本歌舞伎舞台右侧通道)走过,在穿过观众的时候途中会停下接受掌声,早期还会接受礼物。在歌舞伎表演中,通过门登场的是戏剧性十足的表演开始,当演员缓缓从门中走来,她们似乎在说:“看着我。”
悲剧与喜剧的节奏
门可以建立起喜剧或是悲剧的节奏。法国的批评家、社会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其评论拉辛喜剧的论文中探讨了门的悲剧意味。他提到,当悲剧中角色离开舞台时,通常意味着他们走向了死亡。巴特将台上台下之间的门描述为“一个悲剧的物体”,“残忍地为我们展示了接触与碰撞,还有捕猎者与猎物的厮杀”。[5]从门中下场意味着死亡这一形式不只限于拉辛的戏剧中——前文提到的阿伽门农、卡珊德拉、克吕泰墨斯特拉和埃癸斯托斯,俄狄浦斯王的妻母伊俄卡斯特,《三姐妹》里的图森巴克伯爵,海达·加布乐——都是从门中下场走向死亡。另一方面,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死亡总是作为反面角色破门而入,在舞台上留下一番浩劫,话虽这样讲,但我们也要缅怀《君臣人子小命呜呼》中可怜的罗森格兰茨和吉尔登斯吞的下场,他们死在了英国。
在闹剧中,门不再是通往死亡的路,而是走向混乱的通道,乔治·费多在《爱情的羁绊》中有一段经典描述:
巴里翁家的客厅。法式的门通往花园,一个拱门通往前门。也有许多门通往各个卧室和其他房间。[6]
情人、配偶、情妇、爱管闲事的讨厌鬼都藏在这些门后。上场与下场时间都被精准地设计,我们哈哈大笑是因为我们知道谁刚刚下场,谁藏在衣柜里,但是被欺骗了的配偶并不知道。荣誉、尊严、婚姻都被门闩适时地拉上而挽救了。
或许没人能比杰出默片丑角巴斯特·基顿更灵活地使用门。如同费多的闹剧,在巴斯特·基顿的很多电影中,所有事情都取决于门的适时使用。在1921年的电影《暗号》中,基顿设计了一个带有很多门的房子(包括独创性的活板门)。电影的高潮发生在基顿饰演的莽夫、他的心上人以及心上人的父亲为了躲避一群杀人犯而在房子里面东躲西藏的片段。门在这部基顿的剧中除恶扬善,戏谑地说,门神在巧妙地施展魔法。仿佛我们再度回到二元世界,即信息要么从门中来,要么就不存在。
契诃夫的室内外理论
虽然门在20世纪的闹剧电影中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且计算机信息技术(doorways)和信息传递者(gatekeepers)在现代互联网的应用中也不可或缺,但是门在现代舞台上的使用的确减少了。20世纪发生了一些悄然的改变。
19世纪末期的象征主义艺术家、诗人要对这些变化负有一些责任,弗洛伊德就是其中的一位。这群人开始质疑外在现实的绝对权威。无论是感知到的真理,还是人内心深处的真理,都不能够被一面墙所承载,也无法通过一扇门而传达。当两个世界逐渐融合之时,内与外的二元对立也开始分崩离析。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另一个“罪人”是契诃夫,他向我们展示了拥有诸多房间与门的房子,但他也试图去打破空间之间的界限,打破可见与不可见。斯特林堡把门锁住,易卜生则甩上了房门,但是契诃夫总是在讲述门外的故事,即使我们还在门里面。
《樱桃园》开场的舞台提示标志着这一变化:“一个作为婴儿房的房间,一扇门通向安雅的寝室。”尽管舞台指示仍在继续,但却鲜有对房间的描述了:“在一个五月的黎明,太阳即将升起。果园里还很寒冷,但樱桃树已经开花了。”[7]在1904年的演出本中,契诃夫只用简单的几句话便将门内与门外的界限打破了。一旦这种做法可行,那门还有什么用呢?安德瑞·瑟班于1977年在林肯中心执导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樱桃园》,舞台设计由桑托·卢卡斯托担任。台上没有墙,因此也便没有门——只是在一个开阔的舞台幕后装饰了几棵飘摇的树。
在二十世纪早期,包括阿庇亚、爱德华·戈登·克雷在内的欧洲舞台设计师彻底地更改了舞台的面貌,使用简单的象征性的设置,如平台、台阶、窗帘及半自动的装置来代替19世纪精细致的舞台设置。舞台不再是幻想当中的故事发生的地点,而仅仅是舞台——一个没有门的舞台。
在创作《樱桃园》的同年——1904年,克雷曾前往柏林担任《威尼斯得免于难》的舞台设计。这部英国王政复辟时代的戏剧是托马斯·奥特韦的作品,由德国名盛一时的导演奥托·布拉姆博士执导。戏核就是一扇门,但是克雷设计了一个没有门的布景。导演与舞台设计的合作虽然告吹,然而门作为舞台设置的宿命也至此休矣。就像19世纪初的演员被剥夺了使用门的权利,他们不知道没有门后该如何上场下场,戏剧在总体上也失去了一定的戏剧性。20世纪最具争议的名剧——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讲述了两个流浪汉一直在路边的树旁等候的故事。因为一些不明确的理由,这两个流浪汉不能离开:他们注定要等待。在剧中戈戈和狄狄几次交换地重复着以下对话:“我们走吧。”/“我们不能。”/“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等待戈多。”最后两句台词及最后一句舞台指示是:
弗拉基米尔:怎么样?我们走吧?
埃斯特拉贡:好,我们走吧。
(他们没有动。)
有很多从隐喻性、哲学性角度分析他们为什么不能离开的文章,但是也有一个很切实的解释:他们不能离开是因为没有门!在《等待戈多》之后,讽刺大师贝克特又创作了《终局》,当然,在《终局》中房间是有门的,然而剧中角色依然被困住而无法离开。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戏剧变得如现代流行音乐,不知该如何结束,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然后逐渐匿声。没有了门,就没有了宏伟的下场,因此也就没有真正的结尾。将门作为重要元素来创造戏剧的社会更趋向于坚固、自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进而衍生了没有门的戏剧。
不稳定的形象
但是没有门的设置,喜剧也将不复存在(要知道,喜剧之父阿里斯多芬是在门被引进之后才崭露头角的)。门奠定了闹剧与家庭戏剧的滑稽的节奏。这把我们引向终极问题——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电视情景剧中的门起到的协调作用和剧院里面实实在在看见的门相同吗?
电视与观众的关系区别于舞台与观众的关系。在剧场表演中,观众和演员同处一个空间,而舞台上的物品设置也通常是固定的。基于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我们与剧场里的一个道具到一面墙所营造出的时空关系都具有动态的真实。即使面对移动的布景,我们大体上都能了解其运转的机制。我们可以观察舞台空间的变化,这使得我们与每一个物体的关系都清晰可见(通过隐喻性的暗示)。无论我们将场景匣子这一强制性的视角,看作是新型演出技术的诗学本质,还是视觉拼凑的后现代布景透视法,我们仍然面对现实世界中有形的可知的空间,它要遵循光、时间、空间的自然法则。如果你愿意这样看待,它是一个如牛顿学说一般严谨的舞台。
很明显,观众与电视的物理关系就不相同。电视只是一个房间内众多物件中的一个罢了,而人物形象就局限在这个小匣子里(在酒吧、休息室、机场里的电视更是如此)。就算配备了家庭影院和等离子电视,现实中的人也还是要比电视上的形象大得多。电视观众和电视形象的大小几乎没有匹配过。况且还有最后一点——影像是孤立的,如同挂在画廊墙上的一幅画,与其所在的环境没有意象的、建筑的或任何必要的关联。
但大多数画廊的布局通常会把画摆在视觉中心,而且挂在墙上最显眼的位置。由于电视本身的技术原因,以及其与观众所处环境的物理关系,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一书中提到的“灵韵”(aura)正在被消弭。距离消失不见。假如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本的意想是要让观看《三姐妹》的观众感同身受地认为:他们就是普罗佐罗一家的客人,那么电视仅仅是把角色带入观众的家里罢了。我们不会把自己投射到最喜爱的电视情景剧中的公寓里;相反地,我们想象他们在我们住所的某个角落。电视并不是一个需要隔着一定距离来观赏的物件,而距离恰恰是营造“灵韵”的关键。当人们观看电视节目的时候,这种距离往往是缺失的(有争议的是,戏剧舞台也创造了一个分离观众的孤立的影像,但分享同一个空间的体验及观看现场表演的意蕴,有助于营造透明感,或是说营造出了“灵韵”)。
电视荧幕内部的距离是以另一种方式消弭的,那就是摄影机不断地移动及视角持续转换(《蜜月新人》处于过渡时期,比起后期的电视节目,这部电视剧在很多层面上更贴近于戏剧,比如说只用一台摄影机采用一个视角拍摄,视角的变动只允许平移与特写。《我爱露西》的创新点在于使用三台摄像机,采用多视角拍摄)。影像的不稳定性不仅消解了“灵韵”,就门的设置而言,也减少了其历史的、符号的、象征的价值与关联。对观众来说,门的大小是可变的量。除此之外,门槛的存在也容易被忽视,因为摄像机能够穿过它移动。我们能透过锁眼凝视,穿过敞开的门,随后跟上一个隔壁走廊和房间的镜头。
“大光学”与“小光学”
埃斯库罗斯是否做到了这一点还需考证。当阿伽门农和卡珊德拉的“尸体”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究竟是在宫殿之内还是之外?埃斯库罗斯使用了门来揭露真相,但也消解了巴什拉的内外二分法。在那一刻,那扇门成为了一个舞台上的门,而不是宫殿的门。参照系统改变了,但是物理布景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变,门所承载的意义也没变。《宋飞正传》的公寓的门也许是克雷默闯入的门口,但对于观众来说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入口。随着演员的步伐,我们可以轻易穿过一个大厅场景中的门,走向另一个房间,或者去闯荡一个更大的城市。
新媒体理论家列夫·曼诺维奇将保罗·维利里奥比作后工业化时期的本杰明。维利里奥创造了“小光学”与“大光学”两个门类,小光学基于几何视角,即基于人类视觉和世俗经验;大光学则基于以光速实时传送的信息。维利里奥认为,大光学正在取代小光学。曼诺维奇解释道:近与远、视野、距离和空间,这些人类视觉与艺术的几何结构的概念正在消解,一个没有任何深度与广度的封闭世界正在诞生。[8]
艺术史学家乔纳森·克拉里是这样描述电子科技带来的影响的:“资本主义将那些扎根于心的东西连根拔起,把那些阻碍流通的东西都扫到一边,让那些以个体存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9]在克拉里聚焦社会经济因素时,他的这番清除阻碍流通的见解也许可以应用于门。门在情景喜剧中可以是一个制造笑料的阻碍物,它同时也能阻碍摄像机的移动。但与剧场观众不同,电视节目或电影的观众希望可以在观看过程中横穿门、窗、墙壁以及日常空间中的一切。电视空间是没有界限的。
在电视节目中,门作为索引的标志是必需的,它让我们相信我们此时坐着观看电视的环境与电视剧中的场景是相似的。自埃斯库罗斯开始,情景剧的滑稽、警匪片中的夸张等等这些舞台的、编剧艺术的节奏就被奠定了。与舞台剧中一直存在的门不同,电视中的门仅仅只是形象上的,它的连续性和几何基础都是暂时的。
在舞台上,门是一个边界的、未知的、潜在的、骇人的、无尽的符号。在银幕上,门只是门。
[1]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寻求灵魂的现代人》,《荣格文集》乔兰德·雅各比编辑,(纽约:Pantheon出版社,1953),第 46 页。
[2]埃斯库罗斯,《波斯人》S.G.伯纳德特译,《埃斯库罗斯第二部》,大卫·格林、理查·蒙德拉蒂摩尔编辑。(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151页。
[3]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浮士德》,贝亚德·泰勒译于1946年。(纽约:阿尔普敦世纪公司,1946年。)
[4]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灯塔出版社,1994年),第222页。
[5]罗兰·巴特,《论拉辛》,理查德·霍华德译(纽约:Hill and Wang出版社,1964年),第 5 页。
[6]乔治·费多,《费多五部剧》,保罗·马库斯译(纽约:Peter Lang出版社,1994年),第 127页。
[7]安东·巴甫洛洛维奇·契诃夫,《樱桃园》,尤金·布里斯托译(纽约:W.W.Norton出版社,1977年)。
[8]列夫·曼诺维奇译《新媒体语言》(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2页。
[9]乔纳森·克拉里,《观察者的技术》,援引自曼诺维奇著作,第173页。
Title:Their Entrance and Exit:Handle Fixed on the Door
Author:Arold Aronsong
Translator:Yang Rui
Back to 460 B.C.,a doorwas first used on the Greek stage,fundamentally altering the rhythm of the tragedy.The door and the illusion it created allowed an intercutting of scenes that had the effect of telescoping time and space.The door hides,and the door reveals.The sense of imaginary worlds it creates is very rich.In the theatre doors represent the passage between the onstage and offstage worlds.The actors enter the stage through a door and they are transformed from ordinary people to characters.The apartment door always unlocked in sitcoms functions something similar.Our stages,movies,and television shows depict rooms with doors,but the doors we see on television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we have encountered onstage.The doorway opens and information flows in;it closes and the information flow ceases.Thresholds carrymagical significance thatmaintains the sense ofmortality.Without doors,there can be no grand exit and thus there is no finality.
theatre,stage scenery,door,metaphor
J80
A
0257-943X(2017)02-0091-12
(作者单位: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译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