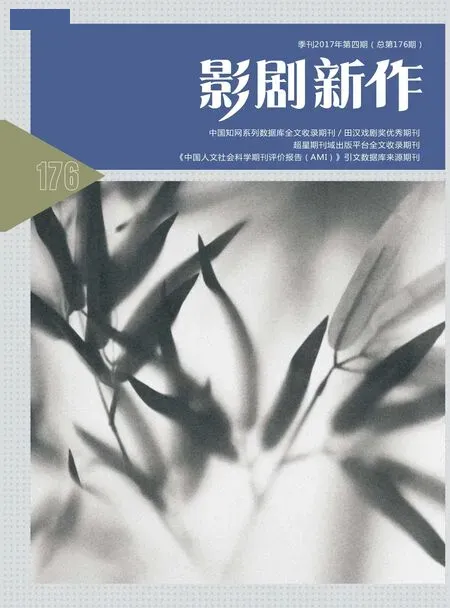玻璃之爱
——浅评同志电影
黛 二
序
世间有这样一种感情--可以不顾一切,生死相许,或凄美悲凉,或脆弱绝决,因为双方为同性,人称为“玻璃之爱”。
同性之恋是一座玻璃般透明且孤寂的城堡,外面的人很少能够走进他们的世界,体会他们的感情。这种感情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水到渠成的自然魔力,而这种魔力源自于人类与生俱来、无以言表、深不可测的孤寂,以及对孤寂无力抵御的巨大恐惧。因为与生俱来,无力抵御,故刻骨铭心。
尽管在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同性之爱还不是件容于理解、易于接受的事, 但它已渐渐从黑暗的角落走进日常生活,并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试图通过电影艺术对这种不同寻常的感情的探讨、理解与解读,让愿意走近它的人们能够更大限度的给予宽容与理解,也让社会对此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认识与理性、负责的评价。
《断臂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臂山
蓝天白云下的策马扬鞭,一路狂奔,空旷山野里的无拘无束,纵情燃烧,断背山下那个热烈而持久的拥抱,成为一种亘古的风景,与远近相连的山脉恒久对视,成为彼此的见证。
谦恭、温润的李安,于不动声色中将人类的渺小和伟大尽现。若不是他,你如何领略断臂山下,白云深处的拥抱是怎样的醉人、销魂?黑暗而冰冷的夜里满溢的激情是如何的自然而然?策马奔腾,互相厮打是如何的无拘无束?无人的时候,当你静静的面对自己心中的这座断臂山时,在人性中最强大与最柔弱的地方,这种浑圆、寂静、孤独、低徊,岂止是一种旁观的感动?
许多时候,友情跟爱情只是一墙之隔,或是一念之差,有些情愫当它发生的时候,就显现出无比的坚强,它凌驾于个人意志和社会规范之上,它从心灵深处起源,在自然中孕育,在寂寞中诞生,在彼此心中扎根,在各自生命中延伸。
在清冷寥远的断臂山同作同息,相拥相携,观云卷云舒,看日升日落,不问世间万事变迁,可能是每一个渴望白头偕老的爱人共同的愿望。然而,世外桃源总止于南柯一梦,这个世界上注定有很多事是他们无法改变的,比如世俗规则,比如人伦道德。然而,他们也注定会坚守一些这个世界无法更改的东西,比如心灵,比如爱情,他们沉默着用生命共守这个秘密。有一种时间和空间都泯灭不去、更改不了的东西弥漫,这就是爱,无论在赤道还是北极,总能润物无声,春风化雨。
实在不忍心责备恩尼斯,并不是所有男人都具备敢爱敢恨的勇气,也并不是所有的恋人都承担得起周遭怀疑、鄙视的眼神,压抑、窒息的气氛。童年噩梦般的经历,早在他心上投下浓墨重彩的影子,注定挥之不去。迟疑、隐忍、畏缩,都是生活打上的最终烙印。所以,即使明明是相爱的两个人也是无处躲避的。杰克关于农场的梦想,关于两个人终此一生的追求,只是捉摸不定难以齐全的幻象,随着恩尼斯的离去而碎成粉齑。
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永远无法走到出那一步,所以断臂山下那个拥抱才尤其显得惊心动魄,感人至深。当拥在手中的幸福再也无法找回时,恩尼斯能做的就是用剩下的大半生时间,来铭记一个叫杰克的人,那个曾经用全部身心去爱他,他也同样深爱的人——一个男人。
爱是相守,是期盼天荒地老。但当它从你手中滑向某一个无法预料的地方,你所能做的,就是把那个人层层叠叠覆盖到记忆里去。
当片尾恩尼斯把那件血衣抱在怀里低声泣道:Kack , I Swear时,泪水已经汹涌淹没了整个世界。而在这个充满了相同或者不同寂寞的世界上,我们却无法回头去牵那个人的手,只能凭记忆里他依稀的模样,追忆曾经发生过的奇迹,而岁月凋落的容颜,镜中的你如何敢相认?
《心太羁》:有一种爱无法宣之于口
19世纪的爱尔兰人奥斯卡·王尔德是一个悠久的传奇。在早年,他的童话《世人的花园》和《快乐王子》里就弥漫着一种淡淡的迷离和忧伤,闪现着至善至美的博爱情怀。他同时还是一位高段位的段子手,他用风趣的语言尽显人间美丑,让人为之惊诧、折服。他在文学和戏剧上的才华受到人们极度的追捧,他优美而丰富的内心、睿智幽默的性格、优雅犀利的言语, 骇世惊俗的言行都使之成为一个极具魅力的人。
事实上,王尔德能够被一个世纪后的人们记住,并不仅仅因为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和行为举止上的惊世骇俗,更因为他与艾尔弗瑞道格拉斯(波西)之间轰动一时、流传至今的“无法宣之于口”的感情。
“无法宣之于口的爱在本世纪是一种伟大的爱,这种爱被误解了,为了描述这种爱我站在了现在的位置。它是美的,是精致的、最高贵的一种感情,它没有丝毫违反自然之处。……这个世界不理解这一点,而只是嘲讽它,有时还因为它而给人带上镣铐。”他在法庭上那段震惊英伦的“无法宣之于口的爱”的声音至今仍然振聋发聩。
1891年,王尔德的剧本《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演出大获成功。这位骄傲的爱尔兰绿孔雀名噪一时,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人们的崇拜与追逐。一次演出结束,他的目光被远处一名美少年吸引,这少年如同用象牙和玫瑰花瓣做成的阿都尼斯,金发飘飘,媚眼如丝,仿佛希腊雕像般隔着人群远远的看着他,嘴角挂着融化冰雪的微笑,这个百合花般的青年名叫艾尔弗瑞道格拉斯。只此一眼,命运就已经注定,他不可救药的爱上了他,开始了像流亡般一路跌跌撞撞的生涯。那年波西21岁,王尔德37岁。
王尔德是一个极端唯美和浪漫的人,对于美有着与生俱来的执着热爱与不顾一切的追求,波西身上的古希腊气息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最致命的诱惑和吸引,他孤芳自赏的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气质,让他在年轻、美貌、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贵族青年波西身上孤注一掷,一败涂地,似乎是合理的选择,也是必然的宿命。
王尔德为他花钱如流水,为了挣钱,他不得不拼命写小说,写剧本。而波西却常常取笑他日趋肥胖的身材,常常抱怨他不读自己的小诗,甚至在当着他的面与其他人做不可描述的事情。这个花儿般的美少年左右了王尔德的悲喜,把他的世界悉然掌握。
一个多世纪前的维多利亚充满了顽固、偏见且极为注重传统礼教。王尔德与波西出双入对于公共场所,公然挑战传统道德规范的行为引起社会上的骚动,当时人们对他异端的言行和服饰恶议有加,对他离经叛道的行为更是严加责难。1895年,他因波西父亲的控告被判有伤风化罪入狱两年。
狱中他写给他的百合花王子的那篇锥心滴血的《自深深处》成为后世经典。为了与波西之间这份“不能宣之于口的爱”,以唯美艺术颠倒众生的王尔德不惜背负罪与罚,甘愿成为世人唾弃的那朵恶之花。多少个月朗星稀的夜里,他隔着铁窗眺望远方,口中呢喃“监狱的樊笼正好考验爱的力量,看我能否使苦水变成甘霖——以我对你那深深的爱。”
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他日思夜想的波西,两年的牢狱之灾让这位骄傲的爱尔兰绿孔雀不仅容貌迅速老去,更是严重地折损了他的自尊心,他躲在柱子后面,远远望着一群青春少年在阳光下恣意的喧闹,他日思夜想的波西穿着黑色长衫,金发飘飘,阳光下,如一抹彩虹腾空乍现,似一株水仙璀然绽放。王尔德情不自禁,一声轻唤,金发美少年蓦然回首,眼中闪烁着星辰大海,脸上的笑容如同艳阳下、山坡前成片的车前子,绚烂如星空,焚心如烈火,波西飞奔而来,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这个镜头始终深深的打动我。三个月后他们彻底分手。
1900年,这位“除了天才一无所有”的爱尔兰绿孔雀死于巴黎一个廉价的旅馆中,终年46岁。在生命的最后,他写道:人生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一种是得到。陪伴在他身边的是一直深爱他,穷困时给他经济支助,遭人唾弃时向他脱帽致敬,最终将骨灰与他一同埋藏的同性爱人——罗斯。而他用生命深爱着的波西却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据说他此后结婚,生子,45年后才离世。虽然在此之前,他无论受到过怎样的伤害,波西永远是他心中最柔软的角落。也许死在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波西手里,比在平庸生活中寿终正寝更符合王尔德与众不同的命运轨迹。
爱上什么就死在什么上。他拼却性命深爱的波西,如同生命原野上遍地开放的罂粟,他拼命吮吸着如同甘露,在巨大的快感中生命渐渐枯萎。“我能够掌控这个世界却掌握不了你的心”,这是天才对自己命运最恰当的注脚。
《心之全蚀》:驭风的男子
1871年9月,法国偏僻的夏尔维勒车站,一个少年迈着外八字、大踏步在泥泞的小道一路狂奔。阳光下,一头散乱的金发,一张青春明媚的脸,一双倔强无羁的眼神,仿佛是给予太阳最新鲜的回报。他纵身跃上火车,仿佛破旧肮脏的鞋子也急切地与家乡告别,他怀揣梦想向着巴黎出发。这个少年叫兰波,从他踏上旅途的这一刻,一场旷世恋情就拉开了帷幕。
16岁的兰波的巴黎之行是应“诗人之王”魏尔伦的邀约。这个被称为缪斯的手指触碰过的孩子,从14岁开始写诗,15岁就写出著名的诗篇《醉舟》,魏尔伦读后惊为天人,于是发出邀请欲与之一晤。
魏尔伦日益衰竭的灵感急需异乎寻常的另类来唤醒,兰波年轻美丽的身体对他来讲更是最直接、最奏效的感官刺激。魏尔伦在诗坛的地位、经济能力既是兰波寄生的最佳选择,也是敲开巴黎上流社会之砖。于是,一场起于各取所需的爱应运而生----当真不是所有的爱,最初起因都那么高尚。
魏尔伦对兰波的爱,除了对青春肉体的迷恋,还有一部分是对这个少年以最反叛、最疯狂的姿态挑战平庸的欣赏,他深知兰波有一种近似邪恶的灵魂,是自己永远都不会有的。因此,这样的“邪恶”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为了兰波,让他放弃优裕的环境,舍妻弃子,而被上流社会唾弃并驱逐文化沙龙,与兰波上演了一遍遍说走就走的私奔。
兰波对魏尔伦的感情相对复杂。
首先是因魏尔伦对他百般宠溺而感激与依赖。兰波自幼缺失父爱,对大他十几岁的魏尔伦的感情中既包裹感激之情,又夹杂着对父亲的依恋。魏尔伦带着他来到海边,第一次看到大海的兰波飞快地奔跑着,跃入海中,又折回头,冲进魏尔伦的怀抱,无法掩饰的欢欣,那是少年的狂野与激动。第一次看日出时,他们在空旷的田野里奔跑,少年如小马儿一样奔腾,那是一次真心的悸动,那是一次真心的心灵放飞。当魏尔伦的岳父把兰波赶出家后,魏尔伦冒着大雨在街上找到他并安置在一个顶楼的陋室里,魏尔伦抱歉地说,只能这样了。兰波将桌子和椅子放在窗户前,眼里掩饰不住的喜欢,他从窗口将衣服一件件地抛到街面,用这种方式表达内心的欢喜。
其次是对他一次次逃避的失望愤怒。因为争吵,魏尔伦把身无分文的兰波丢在伦敦,隔着浓厚的雾,兰波哭着求魏尔伦不要离开,魏尔伦还是冷酷地乘船而去。在布鲁塞尔,兰波决心离开魏尔伦。魏尔伦绝望的开枪打穿兰波的手心,为此而入狱。兰波带着受伤的身心回乡,写下纪念他俩一段恋情的名篇----《地狱一季》,那年,他19岁,从此封笔。
最后应该还有鄙夷。兰波与魏尔伦之间的爱是不对等的,这种不对等是他们之间感情满目疮痍、最终分崩离析的主要原因。兰波虽然接受魏尔伦的供养,但从心里看不起他。一个是来自对年轻美丽的觊觎,一个来自对现实生存的寄生。自始至终兰波没有对魏尔伦说过一个“爱”字,关于这个话题电影里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伦敦一家小酒馆里,魏尔伦问兰波“你爱我吗?”“你知道我喜欢你。”兰波回答;接着反问“那么你爱我吗?”“爱!”魏尔伦坚定地回答。于是,兰波让他掌心向上放在桌子上,用刀刺伤了他的手;第二次是在影片的结尾,垂垂老矣的魏尔伦独自坐在酒馆,像往常一样点了两杯苦艾酒。少年兰波似乎就在他跟前,端起苦艾酒抿了一口。“你爱我吗?”魏尔伦问。“你知道我喜欢你。”兰波回答,“那么你爱我吗?”他认真地说“爱”。兰波让他把手放在桌上,掌心向上。这次少年拿起他的手,在掌心一吻。
跋
生活中,玻璃之爱很少有美满的结局。那些勇敢而执着的人们,总是需要以最大的勇气去面临残酷的生离死别,面临更多世俗的歧视误解,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与毅力冲破外在的重重阻碍。
在电影艺术中,玻璃之爱,愈发显得突兀、迷离,总也摆脱不了分崩离析的结局。或许命运能够给予我们的感情是一个定数,不能奢侈贪求,想要获取更多的时间与更近的距离,就只能连已经拥有的都一并失去。对于爱情,我们心中隐藏着深深的不安和恐慌,害怕悲剧重演。然而,命中注定,越美丽的东西越不可碰触,越珍贵的东西越难以留住,如“玻璃之爱”,脱俗高贵,散发迷人的光彩,彼此也只能远远的尝玩,空空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