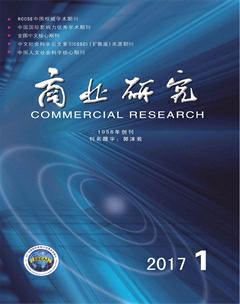股票发行询价制度下的合谋行为研究
冯琳
内容提要:本文以新股发行询价制度为背景,引入“合谋”建立了一个监管机构-拟上市公司-保荐人的三层委托代理模型,具体考察最优防范合谋的机制特征,指出要防范发行询价中的合谋应加强社会媒体对新股发行询价过程中的监督,提高对合谋发行的行为惩罚力度,提高对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的威慑力;并在此基础上对现实询价过程中存在的合谋行为进一步分析,主要包括:防范合谋行为要充分发挥社会媒体的监督能力,公司的透明度与合谋行为存在密切关系,承销商和保荐人缺乏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
关键词:询价制度;合谋行为;防范合谋契约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1-0042-07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股票发行制度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基本功能的发挥以及运行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我国自2005年1月实施发行询价制度至今,管理层对股票发行制度不断进行着完善,然而从实施结果来看,相关的制度改革似乎并未达到所期望的效果,近两年来的股市暴涨暴跌便是最好的说明。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具备资源配置、直接融資、经济晴雨表和财富效应四大基本功能,但中国股市的现实状况却不利于资本市场四大基本功能的发挥;同时,“万福生科”、“奥赛康”等等各种违规发行事件也暴露了中国股票发行制度存在的痼疾。
合谋(collusion)是导致中国股票发行制度存在种种问题的重要原因。中国现行的询价制度源于英美两国的累计投标定价机制(Book Building),本质在于通过建立拟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建立充分沟通的机制,发现市场的真实需求,降低拟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实现定价的最优化[1]。良好的询价制度能够在定价前充分收集“知情投资者”掌握的信息,通过把这些信息有效地反映在发行价格上,减少发行价格偏离公司真实价值的程度,从而提高定价效率。然而,中国目前的询价制度却演变成了拟上市公司和承销商进行利益输送的工具,合谋报高价或报低价的现象屡见不鲜。事实上,对于拟上市公司和承销商而言,保证新股发行成功是双方共同的利益诉求,再加上中国目前的信息披露制度和法治相对不健全的原因,拟上市公司与承销商两者的紧密联系很容易使两者产生合谋行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提出了两权分离后引起的代理问题,并首次阐述了合谋现象的存在,他把合谋现象描述为:“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者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是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2]。”在卡特尔组织中合谋被定义为一种正式意义上的串谋,合谋理论也最早被用来解释卡特尔组织的合谋行为[3]。而后其理论从解释卡特尔组织的合谋现象发展到解释上市公司内部存在的利益输送行为[4-5]。
国外研究组织合谋的代表人物是Jean Jacques Laffont和Jean Tirole(1997),指出由于组织中合谋行为的存在,其对激励机制的扭曲是导致组织运行效率低下的根本性的原因,并建立了组织内合谋行为的一般分析框架-PSA框架[6](即委托人、监管者和代理人的层级结构)。在PSA框架的层级结构中,Jean Jacques Laffont和David Martimort(2000)提出了合谋的两种类型:一类是作为代理人与代理人间的合谋;另一类是监管者和代理人之间的合谋[7]。鉴于合谋会造成组织效率的损失,为保证组织的高效运行,防范合谋行为的产生变得至关重要。Tirole(1986,1992)提出了防范合谋的一般性解决办法,即委托人通过设计一个防范合谋的合同使得其监督人和代理人合谋情况下的损失远远大于其相应的收益,同时认为监督分工对防范串谋有益[8]。20世纪60年代合同理论兴起,从委托代理的角度指出了合谋的存在。合同理论认为合谋的生成取决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激励约束机制,合谋意味着私下的、法外的安排,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而导致的潜在可能性会迫使委托人改变或修改与代理人签订的契约[9]。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在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冲突的假设前提下,委托人如何设计一个最优的契约来实现对代理人的有效激励。
国内目前可以检索到的文献中,对合谋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内的合谋行为,也就是上市公司内合谋行为的研究。公司内部存在的合谋现象一方面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影响了公司的运行效率[10]。部分学者从中国的政企合谋角度分析了合谋行为。聂辉华和李金波(2006)指出政企合谋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率与高事故发生率并存的原因之一[11]。进一步地,聂辉华和蒋敏杰(2011)从政企合谋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矿难频发的原因[12]。总的来看,目前对合谋理论的应用研究大多局限于上市公司内部,最终落脚到如何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更鲜有文献将合谋理论引入到新股发行制度中。
本文借鉴Tirole和Laffont构建的合谋理论框架以及聂辉华(2006)的研究框架,从合谋角度对发行询价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文中的模型将监管机构(例如中国证监会)作为委托人,拟上市公司和保荐人分别为代理人和监管人,代理人和保荐人之间是信息完全对称的,那么拟上市公司和保荐人为保证发行成功,有很大的动机签订契约进行合谋。
二、防范合谋模型的构建
(一)参与者
现实的股票发行询价过程中涉及参与人众多,本文为便于研究,将问题简化,假设新股发行过程中主要有三个博弈主体:监管机构(证监会)、拟发行上市公司和保荐人,三者之间存在着一个三层的委托代理关系,形成了一个总契约。由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新股发行过程中监管机构(证监会)无法准确获得拟上市公司有关新股发行的全部信息,因此监管机构(证监会)作为委托人(Principal)以契约形式授权保荐人作为监督者(Supervisor)来监督代理人(Agent)实现新股的发行上市,本文中的代理人(Agent)即拟上市公司。监管机构(P)的主要职责在于设定主要的规则,在拟上市公司(A)和保荐人(S)存在违规发行的情况下对其实施相应的惩罚措施。监管机构(P)是指监督机构,它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授权,统一监督管理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维护证券期货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①,并依法对上市公司新股发行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保荐人作为监督者(S)负责监督拟上市公司的新股发行过程。保荐人制度最早提出是在2003年1月监督机构召开“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同年12月保荐人制度正式实施。“保荐人制度”是指由证券公司负责对发行公司的上市推荐和辅导,核实公司发行文件中所载资料是否真实、准确和完整,协助拟发行上市公司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13]。保荐人制度核心在于保荐机构责任人问责机制,旨在将上市后的持续督导责任落实到个人。保荐人制度的引入也标志着中国的新股发行制度由主承销推荐制过渡到保荐制。拟上市公司通过实现首次公开募股,获得了自身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效益。自身效益体现在拟上市公司通过上市筹集资金,从而为公司的扩大经营和升级等提供了资金支持;社会效益体现在提高社会闲散资金的利用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定期的强制信息披露可以推动相关行业的良性竞争。
在模型中,本文假定在新股发行过程中,拟上市公司有两种股票发行方案可选,记为C=C1,C2,C1表示拟上市公司采取的高质量的发行方式,在此发行方式下,拟上市公司不存在粉饰财务报表和欺诈发行的行为,信息披露真实、完整;C2表示拟上市公司采取的低质量的发行方式,在此发行方式下,拟上市公司存在伪造财务数据或者欺诈发行的行为,信息披露不实。上述两种新股发行方式的成本不同,低质量的发行方式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资本(比如伪造财务报表),但是新股一旦发行成功,股票的高抑价对公司以及承销商带来的收益颇为可观,要远远高于高质量的新股发行方式,这也是很多公司希望通过新股发行来实现公司上市的原因之一。但是低质量的新股发行方式为社会带来的效益往往是极度负面的,从提升社会福利角度来讲,一方面低质量的新股发行方式为公司带来的收益只是一时的,高抑价的背后往往是新股的长期弱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股票市场具有的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的功能,股票市场会逐步演变为社会闲置资金的“圈钱机”;另一方面欺诈发行更多的是侵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若新股发行过程中拟发行上市公司与承销商以及相关的发行机构之间存在利益输送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监控和制止,那么中小投资者居于劣势的现象就会愈发地明显。上述两点都不利于社会福利的提升。
此外,本文将社会的总收益看作1,公司上市产生的社会效益分为三部分:监管机构的社会效益、拟上市公司的社会效益以及保荐人的社会效益。监管机构的社会效益表现在公司通过上市提高社会闲散资金的利用率,提升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拟上市公司的社会效益表现在公司通过上市筹措资金,为企业的未来发展运营提供资金支持;保荐人的社会效益体现在,通过成功发行新股来提升自身的承销商声誉,从而为自身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二)信息结构
在实际的新股发行过程中,新股发行须先由发审委审核通过。发审委核准通过后,新股发行工作才能正式启动。在这一过程中证监会(P)与拟上市公司(A)之间存在信息不称,证监会(P)无法判断拟上市公司(A)最后会采取何种新股发行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公司(A)来讲占优的发行方式必然是低质量发行方式。证监会(P)授权保荐人(S)对拟上市公司(A)的新股发行过程施行监督,拟上市公司必须按照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制作申请文件,由保荐人保荐并向证监会申报。或者说保荐人接受拟上市公司的委托负责新股发行的所有事宜。本文假定保荐人(S)与拟上市公司(A)之间信息完全对称,保荐人对拟上市公司的具体财务经营状况以及询价公告拥有完全的信息,保荐人也十分清楚拟上市公司采取何种新股发行方式,因此不存在对保荐人的信念修正问题。
在新股发行过程中,若拟上市公司(A)选择高质量的发行方式(C1),拟上市公司与保荐人之间不存在合谋行为;若拟上市公司(A)选择低质量的发行方式(C2),拟上市公司选择与保荐人合谋发行,那么监管机构(P)会有δ的概率发现上述合谋发行的行为,若监管机构未发行上述合谋行为(概率为1-δ)。本文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借鉴聂辉华(2006)中的合谋模型,同时考虑现实的股票发行案例,将第四方监督机构融入到模型中能更好地对发行询价中的合谋行为进行监督。第四方监督机构(社会媒体)发现上述合谋发行行为的概率为ρ,未发现合谋发行行为的概率为1-ρ。上述四种状态具体描述如下:(1) 拟上市公司(A)选择C1,新股发行不存在问题;(2) 拟上市公司(A)选择C2,监管机构稽查未发现问题;(3) 拟上市公司(A)选择C2,监管机构稽查以概率δ发现发行问题,社会媒体未进行报道;(4) 拟上市公司(A)选择C2,监管机构稽查以概率1-δ未发现发行问题,社会媒体以概率ρ进行报道,监管机构(P)获知其为低质量发行。
(三)收益函数
借鉴在Tirole(1960)的合谋理论框架,本文为了简化分析,假定监管机构、拟上市公司以及保荐人都是风险中性的。
监管机构的效用函数为U1=S。其中,S为监管机构的最大化产出为社会效益。拟上市公司的效用函数为U2=aS-C,其中,aS为拟上市公司上市为其自身带来的融资额,a为常数,拟上市公司的融资额随着社会的总效益S的提升而增加,与社会总效益成正比;C为新股发行成本,其取值为C=C1,C2,C1表示拟上市公司采取的高质量的发行方式,C2表示拟上市公司采取的低质量的发行方式。借鉴Tirole(1960)的研究方法,只有拟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的效用不小于其保留效用,拟上市公司才会选择行动,否则不行动。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新股发行过程存在一定的保留效用(机会成本)U-,本文为了简化讨论,将新股发行的保留效用设定为0。
保荐人负责对发行公司的上市推荐和辅导,负责核实公司发行文件中所载资料是否真实、准确和完整,披露比监管部门所知悉的更多的拟上市公司内部信息。在新股发行过程中,鉴于承销商全权负责拟上市公司的新股发行工作,因此保荐人对拟上市公司拥有完全信息。保荐人的收益主要由公司承销收益以及保荐收益两部分组成。保荐人考虑到保荐费用一般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因此不成为保荐人的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本文简化分析将其忽略。此外,本文将社会效益因素纳入到保荐人的效用函数中。本文将社会的总收益看作1,公司上市产生的社会效益分为三部分:监管机構的社会效益(S)、拟上市公司的社会效益(aS)以及保荐人的社会效益,那么保荐人的社会收益为1-S-aS。
综上所述,保荐人的社会效用函数为U3=aC+(1-S-aS)=aC+1-(a+1)S。其中,aC为承销收益,b为常数,保荐人的承销收益与拟上市公司的社会收益成正比;保荐人获得的社会收益为1-S-aS。
(四)博弈时序
参与者按照如下顺序进行博弈:(1)监管机构分别给拟上市公司和保荐人提供总契约(Grand-contract),若拟上市公司和保荐人都接受总契约,那么博弈结束,否则进入下一步;(2)拟上市公司和保荐人私下签订子契约进行合谋发行新股,为了保证子契约(Side-contract)的稳定性,拟上市公司对保荐人进行利益输送T。若保荐人拒绝,则双方按照先前提供的总契约执行,若保荐人默认,则双方按照私下签订的子契约,进行合谋行为的博弈;(3)监管机构稽查发行问题的概率为δ,若拟上市公司与保荐人之间的合谋行为被发现,则监管机构要对拟上市公司和保荐人分别处以罚金FA和Fs;(4)社会媒体发现合谋发行行为的概率为ρ,若社会媒体发现合谋发行的行为,则监管机构也会通过各种公共资源发现其合谋发行的行为。
三、模型分析
在模型分析过程中,本文主要从以下情况进行分析,即代理人和监督者合谋的情形,在此情形下,若保荐人帮助企业隐瞒信息,就可以得到货币化的利益输送。在代理人选择高质量的股票发行方式的直接显示机制下,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为:
U1=Maxa,S,Fs,FAS
下面考虑约束条件。在拟上市公司与保荐人之间存在合谋行为的情形下,最优的防范合谋契约下约束条件分为个人理性约束、激励相容约束以及有限责任约束。分别来看,其合约必须满足如下的约束条件:
结论2分别为拟上市公司上市融资额占社会效益的比例(a*)、总的社会效益额(S*)、证监会对拟上市公司以及保荐人的罚金FA、Fs的最优值。若ΔC表示准租金,那么在有限责任约束下,拟上市公司和保荐人之间一旦被发现有合谋行为,上述两者将会面临着高额的罚金。若处罚金额低于其最优值,那么拟上市公司和保荐人还可以获得一定的合谋收益,那么处罚也难以起到制约合谋行为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明确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对最优契约的主要参数进行静态分析,有以下关系成立:
a*T>0,若拟上市公司获得的融资额越高,那么拟上市公司进行利益输送(T)的积极性就越高。对于拟上市公司而言,保证新股发行成功是最大的利益诉求,在高抑价发行的现实情况下,新股上市给公司带来的融资额是巨大的。因此,拟上市公司也会增加对保荐人的贿赂来保证股票发行的成功。
S*ρ>0,若社会媒体的监督能力(ρ)越强,则监管机构的社会效益(S*)越高。提升社会媒体的监督能力,将发行审核机构的审核过程放置在媒体的监督之下,提升股票发行过程的透明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发行审核机构和保荐人的责任感,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投资人的利益,那么社会效益水平也随之得以提升。
FA*T<0,从拟上市公司角度来看,对拟上市公司的罚金(FA*)越高,则拟上市公司对保荐人的利益输送(T)的积极性就越低。这说明提高惩罚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范合谋行为的发生。Tirole(1986)曾指出,委托人可以通过设计一个防止串谋的主契约使得代理人从中得到的收益不少于串谋受益,因而代理人就没有进行串谋的积极性。一旦其合谋行为被发现,拟上市公司将被处以高额罚金,其从股票发行中得到的收益会远远少于合谋的收益,从而能够有效地防范合谋行为。
Fs*T>0从保荐人角度来看,对保荐人的罚金(Fs*)越高,则保荐人接受利益输送(T)的积极性就越高。在股票发行过程中,一旦合谋行为被发现,首当其冲的是拟上市公司,承销商和保荐人往往也会受牵连,其承销收益也会因此减少,那么保荐人就有较大的动机来接受拟上市公司的利益输送(T),以抵消高额罚金。
Fs*b<0对保荐人的罚金(Fs*)越高,则保荐人获得的承销收益与发行成本比值(b)就越低,即保荐人获得的承销收益越低。这一结论是比较明显的,一旦合谋行为被发现,那么拟上市公司面临着高额的罚金,保荐人获得的承销收益也相应减少。
FA*ρ<0,Fs*ρ<0,若社会媒体的监督能力(ρ)越强,那么拟上市公司(FA*)和保荐人(Fs*)的罚金就越低。这说明了发挥社会媒体监督能力的重要性,监督机构可以降低对作为监督者的保荐人的依赖,从而降低委托人—代理人—监督者之间存在的委托代理成本,提高发行效率。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讲,应当大力发挥社会媒体的监督职能,对于违规股票发行的事件进行及时曝光。
四、对现实合谋行为的进一步分析
中国的股票发行制度有着深刻的制度基础,具有“新兴+转轨”的特点。在现实的股票发行实践中,中国股票发行市场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股票发行问题频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股票发行问题的频出与合谋行为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作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股票发行制度不仅对整个资本市场运行效率的提高和基本功能的发挥至关重要,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也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如何防范股票发行中的合谋行为也就成为股票发行实践中的重中之重。结合上述模型中得出的结论,本文对其合谋行为做进一步地探讨。
1.防范合谋行为要充分发挥社会媒体的监督能力。前述内容已经论证了发挥社会媒体监督能力(ρ)的重要性。由于监督机构不可能对拟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信息拥有完全的信息,而拥有完全信息的保荐人与拟上市公司之间又存在合谋发行的可能性。因此,社会媒体监督能力的高低对于合谋行为的防范也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现实中,社会媒体揭露事件的能力往往会受到抑制。中国证监会“集多重身份于一身”,是市场的监督者同时也是市场的参与者,违规发行的案件通报也会第一时间通过中国证监会进行公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证监会其实已经担当了一部分社会媒体的监督职能,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媒体对于股票违规发行事件的曝光或许要在中国证监会的默许下进行,因此社会媒体披露事件的能力会相应地打折扣。
2.公司的透明度与合谋行为存在密切关系。股票发行询价过程中合谋行为之所以存在,信息披露质量是其关键影响因素。公司的透明度是指公司财务与管理信息的公开披露程度,投资者根据拟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信息作出相应的投资决策。而从近年来披露的“紫鑫药业”、“万福生科”等违规发行的事件来看,拟上市公司存在着伪造财务报表、虚增销售收入等违规行为,信息披露质量亟待提升。2011年,证监会对紫鑫药业进行立案调查,涉嫌欺诈,信息披露不实。2013年,监督机构对万福生科进行公告处分,调查结果显示万福生科的《招股说明书》中,2008年至2010年分别虚增销售收入约12 000万元、15 000万元、19 000万元,虚增营业利润约2 851万元、3 857万元、4 590万元;2011年年报和2012年半年报虚增销售收入28 000万元和16 500万元,虚增营业利润6 635万元和3 435万元。这些都表明了拟上市公司股票发行信息披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改善股票发行的信息披露质量,提高公司的透明度也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体现,而良好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关键在于完善的机制设计。Sheleifer和Vishny(1997)曾指出:“投资者保护程度更低的国家,其资本市场更为贫瘠,好的法律环境能够保护潜在的金融家免于企业家攫取,强化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良好的法律环境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前提和保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首先就是要对涉嫌操纵股票发行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严惩合谋交易和操纵市场等违法犯罪行为,实现对违法事件的“零容忍”,从而提高合谋的交易成本来防范合谋的产生。
3.承销商和保荐人缺乏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在国外,承销商声誉是一种无形资产,承销商声誉的好坏关系到中介机构未来的盈利状况。在中国,承销商声誉高低和收取的承销费用无关。正是这种承销商声誉与承销收益的不关联性,在实际的股票发行过程中,一些质量不高的公司在公司上市时往往会选择有包装能力和善于疏通门路的承销商,承销商通过与拟上市公司合谋发布虚假信息,一方面保证拟上市公司股票发行成功,另一方面保证承销商获得较高的承销费用。按照规定,在发行询价过程中,新股的承销价格区间是通过对机构投资者的初步询价结果来确定的,但初步询价的对象主要由拟上市公司和保荐机构选择,很可能出现保荐机构圈定自己认可的、有一定关系的机构询价,尽可能使发行价格的决定权为自己所控制。对于无需参与网下申购的初步询价商,其报价没有很强的约束和管制,发行商和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拉拢初步询价机构,人为地提高新股的报价。比如,参与初步询价的机构不参与正式的累计投标询价,或者是询价对象对询价回复认可之后不去认购。而对于有意向申购该股的机构投资者,则会联合起来,尽量压低初步询价。然后在网下申购过程中以询价区间的最大值报价,以实现新股低风险的较高收益。
简言之,一方面,部分询价机构或高或低地有目的报价,而不是完全注重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部分询价机构提供的报价也不是真实询价的结果,只是“人情价”;另一方面,询价机构的利益与新股发行价格是割裂的,询价机构没有责任为新股发行价格的高企“买单”,参与询价的机构不参与最后配售的状况也屡见不鲜。这样使得我国新股的询价制度相对“机械化”,流于形式、徒有其表,新股定价不合理。
五、结论
本文认为,造成中国股票发行过程中问题频出的制度性原因在于,由于“询价黑箱”的存在,拟上市公司和保荐人之间存在合谋发行的行为。在一个委托人-管理者-代理人的框架中,本文考察了最优的防范合谋的机制,最终的结论验证了Tirole(1986,1992)提出了防范合谋的一般性解决办法,即委托人通过设计一个防范合谋的合同,使得其监督人和代理人合谋情况下的损失远远大于其相应的收益。本文的模型认为要防范合谋行为主要从两点出发:第一,加强社会媒体对新股发行询价过程中的监督;第二,对合谋发行的行为提高惩罚力度,提高对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的威慑力。进一步地,在此分析基础上,本文也指出了承销商和保荐人缺乏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及公司的信息披露程度低也是影响合谋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对发行询价合谋行为的分析,为研究股票发行问题提供了新的微观视角。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防范合谋模型的设定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委托人目标函数的设定时仅仅考虑了其社会效益,而现实中却并非如此,监管机构在稽查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的隐性成本,在未来的研究中会考虑加入这一因素。
注释:
①监督机构简介: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zjhjs/
参考文献:
[1]BENVENISTE L.M., and P.A. Spindt. How Investment Bankers Determine the Offer Price and Allocation of New Issu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9,24.
[2]亞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12-300.
[3]CHAMBERLIN E. H.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M].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4]潘越,戴亦一,魏诗琪. 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合谋”了吗:基于高管非自愿变更与继任选择事件的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11(2):69-81.
[5]蔡宁,魏明海. 股东关系、合谋与大股东利益输送—基于解禁股份交易的研究[J].经济管理,2011(9):63-74.
[6]LAFFONT J J. Martimort D. Collusion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J].Econometrica, 1997,61(4): 875-911.
[7]LAFFONT J J.Martimort D. Mechanism Design with Collusion and Correlation[J].Econometrics, 2000,68(2):309-342.
[8]TIROLE J H. Hierarchies and Bureaucracies: on the Rule of collusion in organizations[J].Journal of Law, Economic and Organization, 1986,2(2): 181-214.
[9](美)博尔顿,(比)德瓦特里庞. 合同理论[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社,上海人民书社,2008:120-200.
[10]蔡慶丰,李鹏. 代理人合谋与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再分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1):92-97.
[11]聂辉华,李金波. 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J].经济学,2006(10).
[12]聂辉华,蒋敏杰. 政企合谋与矿难: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1(6).
[13]孙国茂.从根本上改革股票发行制度[J].理论学刊,2014(3):50-60.
Abstract:Based on the IPO inquiry system,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collusion behavior to the inquiry system and sets up a principal-agent model of three layers which include the regulator, quasi-listed companies and the sponsors, and studi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optimal collusion-proof behavior, pointing out keys which prevent the collusion behavior: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f social media to the IPO inquiry process, increasing the collusion behavior penalties and improving the deterrence to insider trading and price manipulation. The paper also analyses the collusion behavior in reality, which include the following points: making full use of the supervision of the social media to collusion behavior,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pany′s transparency and the collusion behavior,and there is no an effective incentive constraint mechanism between the underwriters and the sponsors.
Key words:inquiry system; collusion behavior; collusion-proof contract
(责任编辑: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