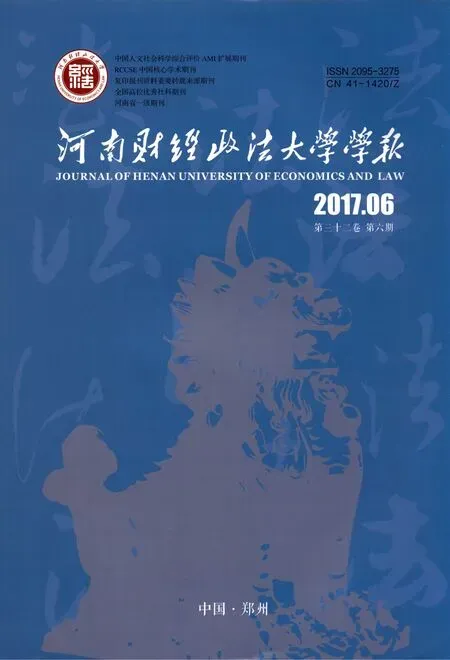指导性案例功能实现的困境与出路①
宋 菲
(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教育院,上海 200042)
①特别致谢:感谢学科组陈金钊教授、王申教授、刘风景教授对本文写作所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指导性案例功能实现的困境与出路①
宋 菲
(华东政法大学 研究生教育院,上海200042)
指导性案例的功能是基于其准法源地位所固有的内部效能。该功能在具体司法中细分为清晰法律、补充法律、弥补漏洞和创设规则等四个方面,并因各自侧重点不同而对应不同的案例类型。当前,指导性案例功能实现主要存在立法与指导性案例衔接不当、重条文轻案例、重裁判结果轻裁判标准三大难题。对此难题,通过制度保障确立指导性案例的司法权威,深入挖掘案例的裁判规则,重视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方法运用,可以作为难题解决的基本思路。
指导性案例;指导性功能;法律解释;裁判规则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在此目标指引下,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同案同判”为诉求的案例指导制度就自然成为改革的表率。案例指导制度自2010年正式建立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已陆续发布16批共87个指导性案例,内容涉及所有的部门法领域。在实际运用中,各级法院也都踊跃跟进,不仅深入学习所公布的典型案例,而且积极参与最高院的案例推选工作。虽然从形式上,司法系统自上而下均高度重视该项目工作,然而七年的司法实践却表明,指导案例的实效远低于制度初创时部分研究者的预估和制度制定者的愿景[1],这反映到现实裁判中最明显的展现就是其运用性差。具体表现为,指导性案例发挥“指导性”功能的效果不佳,存在严重的“援引难”问题*该“援引难”问题可具体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整体运用频率较低;第二,法官隐形援引情况较重;第三,援引质量不高。详细数据可参见2015年和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司法应用年度报告》。该报告主要分析对象是法官的裁判文书,由北大法制信息中心、北大法律信息网(北大法宝)指导性案例研究组编写,并通过北大法宝数据库得以发布。这是国内首次通过大数据分析方式对最高院指导性案例司法应用情况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化的实证研究。。也就是说,该制度建立时所预设的“应当参照”效力并未能较好地实现。对此问题,学界已经从理论上有所关注,并且试图多个方面和角度寻找有效的解决路径。但是,这些研究多是局限于制度层面探讨指导性案例的效力,缺乏立足指导性案例根本功能的分析。不同于指导性案例所展现出来的“应当参考”效力和实现“同案同判”作用,这种以“指导性”为表现形式的指导性案例功能是基于其“准法源”地位所固有的内部效能。它是由指导性案例要素结构所决定的一种内在于案例内部并较为稳定的运作机制。在此之下,“应当参考”效力只是“指导性”功能与外部环境发生关系时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并以该功能为产生根据和前提基础。也就是说,单纯研究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并未抓住“援引难”问题的根本。而能否基于当下的司法实践,充分把握指导性案例的功能,深入分析其实现的困境与出路,将成为解决指导性案例应用难题的重要路径,这是本文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指导性案例辅助确立法源的功能
一直以来,“统一法律适用”被认为是确立案例指导制度的一个重要目标。通过公布具有司法效力的典型案例,明确制定法中的模糊裁判规则,统一新型案件的法律适用标准。在此意义上,指导性案例被赋予了司法上的“准法源”地位。此“准法源”地位又使得指导性案例功能发挥有了理论依据,并作为“应当参照”效力实现的前提条件。具体到司法裁判中,该指导性功能又可细分为清晰法律、补充法律、漏洞补充、创设规则四种类型,并分别在不同的案件类型中得以运用。
(一)源于“准法源”地位的指导性案例功能
对指导性案例的功能,尽管学界众说纷纭,但基本可归为三类:说理功能,参照功能和指导功能[2],而且也都对指导性案例的效力进行了界分。指导性案例的效力侧重外在展现,属于规范法学层面的概念。而指导性案例的功能侧重内在实质,属于社会法学层面的概念。并且,外在的指导性案例效力以其内在的功能为基础。这也正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对效力问题作出如下规定的理论依据,即“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然而,此指导性功能是否能有效地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出来,还主要取决于指导性案例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在案例指导制度建立以前,我国主要是“法律——司法解释”*陈兴良:《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功能之考察》,载《法商研究》2012年第2期。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法律指的是广义上的法律,即由立法机关依据立法权限所设立的一切规范性法律文件。在我国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律、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门规章、政府规章等。的两元法律规则体系,法律是我国最主要的法源,司法解释是对法律在司法应用上的一种具体化规定,也是裁判的重要依据,在我国具有重要的法源地位。案例指导制度建立以后,指导性案例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就成了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在司法裁判中,我们之所以认为指导性案例在我国具有准法源的地位,主要是从确定法源所应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所进行的分析。通常而言,法源确立主要涉及两项内容:一是某项规范性内容是否具有法源地位;二是该规范性内容效力的高低。对于前者,根据定性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制度性权威”和“规范拘束力”两个层面。其中,制度性权威主要从性质角度而言,而规范拘束力则主要从效力角度而言[3]。当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反观指导性案例时,它们因为具有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发布主体,自然具有“制度性权威”;又因“应当参考”的效力规定,具有了指引同案裁判的“规范拘束力”,此“准法源”地位自不待言。不过,“准法源”地位的另一层含义是——它不是法源,只是因满足“制度性权威”和“规范约束力”的双重要求而可以“视为”法源地位,主要存在于拟制意义上。也就是说,尽管指导性案例具有了作为法律渊源的形式,但是从司法实效来看,其分量明显低于制定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而且还受到诸多政策性因素影响。
指导性案例的“准法源”地位决定了指导性案例的功能。在司法中,法源的主要功能是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一种法律规范,法官将法律规范运用到案件审理过程中,以解决案件纠纷。此时,法源提供的法律规范就是法官裁判案件的标准。指导性案例也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一种裁判规则,而提供裁判规则的基本途径就是解释法律、发现法律抑或创造规则。“通过具体指导性案例的案件事实和证据事实对相关法律条文的精细化理解,从而推导和发现解决该案的实际裁判规则。”或者是“当无法通过法律解释从法律条文文义射程范围内获取有效解决规则时,只能采取法律漏洞填补方法推导该案的裁判规则”[4]。也就是说,指导性案例提供的裁判规则是对模糊的、抽象的法律规定运用法解释学的方法进行阐释,从而发现法律规范中隐含的解决待决案件的实际规则。法官在以后审理同类案件时,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就能为其提供一种裁判标准,实现指导性案例对此类案件的指导性功能。
(二)指导性功能的具体展开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与西方判例制度存在很大的不同,如果说西方判例制度的功能是通过先例创设规则直接确立法源,那么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就是发现和总结法官裁判中的适用规则,进而将这些规则性内容用于同案裁判的法源确立和司法选择。具体而言,这种功能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明晰法律、补充法律、填补漏洞和创设规则。
第一,明晰法律。该功能主要是对法律文本含义或司法解释等规定内容的再次强调。具体而言,是指在一些典型或新发案件的裁判上,指明它们尽管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但实质同传统案件“无差异”,可直接适用法律。主要使用的方法是文义解释方法。生成裁判规则的过程是将法律规则中的构成要件与案件事实相衔接,赋予案件事实以法律意义,同时明晰法律在案件事实语境下的运用。如,指导性案例5号对“盐业管理的设定”的法律规定的明晰;17号关于“消费欺诈”的理解,明确了“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的汽车,在发生欺诈行为时,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解的对象;18号对“不能胜任工作”的理解,明确经营者通常所采用的“末位淘汰”考核机制并不能理解为《劳动合同法》中的“不能胜任工作”等。这些案件之所以成为指导性案例,主要在于案件的新型性。但是在法律适用中依然归属法律调整的范围,并不存在适用上的难题。
第二,补充法律。法律是通过语言来表述的,它天然地带有语言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特点。因此,法律的“文义”就包括“核心文义”和“边缘文义”两个部分。如果说,把握“核心文义”是对法律的明晰,那么把握“边缘文义”就是对法律的补充。补充法律的功能就是在法律文义涵射的范围内,充分挖掘其边缘含义。主要提供裁判规则的方式就是将法律的构成要件进行法律解释,尽可能在符合立法文意及立法目的基础上拓展法律规范的界限,扩大其调整范围。通过对法律文义的补充,将各种案件事实是否属于法律规范调整的模糊界限进行明确,为以后类似案件作出指导。如扩充指导性案例2号中的“和解协议”理解;指导性案例3号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界定为包括明示和默示方式,涵盖承诺、实施和实现阶段;11号扩大了在贪污贿赂类犯罪中“利用职务便利”“公共财物”的认定上的主体和客体范围;22号对行政批复纠纷的受案范围进行了扩张,明确了内部行政行为的外化就是具体行政行为且具有可诉性等。
第三,漏洞填补。指导性案例的漏洞填补功能主要体现在一些疑难案件的裁判上。法律的滞后性、语言的模糊性、方法的有限性甚至公权力的干涉等因素都可能构成“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从而使案件变得“疑难”。此时,面对司法者“不得拒绝裁判”的事实,唯有通过利益权衡和漏洞补充方可满足要求。不同于司法解释在弥补法律漏洞时的抽象性和模糊性,指导性案例对于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的漏洞能第一时间发现,进而为统一法律适用找到解决途径。这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说,两者是“一种从抽象到具体、个别到一般的归纳过程”[5]。填补法律漏洞的主要方法是类推适用、目的性扩张、目的性限缩等。生成裁判规则过程就是依据立法目的明确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为疑难案件提供一种裁判依据。如,指导性案例11号理解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时,对行为主体进行扩张,类推适用了受贿罪中关于“利用职权上的便利”的相关规定;与之类似,指导性案例37号结合涉外仲裁执行的特点和现实情况对法律规定的“执行时效期间”起算点进行目的性扩张。
第四,创设规则。这里所讲的创设规则功能不同于前三种功能中对法律的创造。前三种功能是通过法律解释、漏洞填补方法对法律规范进行范围上的明确,而此处指的是法官直接创设规则来裁判案件。法官直接创设规则的依据是法官不能以法律没有规定而拒绝裁判,法官审理的案件在法律上没有做出规定,出现法律漏洞的现象,而法官又无法通过漏洞补充方法予以解决时,就不得已只能自己创设出一条规则,据此裁判案件。此时理解指导性案例创设规则功能的前提是区分法律规则和裁判规则。裁判规则不仅包括成文化的法律规范或法律规则,也包括思维上的裁判标准和司法规律。在此意义上,创设规则就是为案件审理提供一种裁判标准,而大量的指导性案例就是为了明确裁判标准,所以创设规则功能也是指导性案例的重要功能。体现在所公布的案例中,最典型的就是指导性案例15号和58号。指导性案例15号在缺乏现有法律规范的前提下,对公司人格混同的规定进行创制;而指导性案例58号面对我国没有对“老字号”专门保护的立法现实,对“老字号”予以《商标法》上“同等保护”的规则创制。
(三)不同指导性功能所对应的案例类型
如上四种功能并非作者主观列定或只是存在于理论层面,其划分具有特定的现实基础。如果我们根据所公布指导性案例的性质和作用将其划分为“宣法型”案例、“释法型”案例和“造法型”案例三种[6],那么“宣法型”案例主要发挥的是清晰法律的功能,“释法型”案例发挥的是补充法律和弥补漏洞的功能,而“造法型”案例发挥的是创设规则的功能。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如下:
三者之中,“宣法型”案例最为简单,它们通常并不具有法律适用的效力,而主要是对新法的宣示,如通过指导性案例14号和32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所规定的“禁止令”和“危险驾驶罪”予以强调。这些法条所涉及的多是在公民社会生活中频发或者对其有重大影响的内容,也是清晰法律功能的主要价值所在;与之相比,作为补充法律和弥补漏洞功能主要倚籍的“释法型”案例则较为复杂。该类案例在所公布指导性案例中占有最大比例,主要存在于法律适用过程中抽象法律与具体事实相脱节场域,并包括对法律的解释和对事实的解释两种类型。其裁判思路是,面对有待适用的模糊性法律规范,我们首先应该通过解释方法的运用将其明晰化和具体化,并对立法规范缺失的部分进行司法上的填补,从而实现事实与规范的契合。在此过程中,司法者现实运用的解释规则其实就是通过案例所生成的裁判规则,它们对于后案具有必然的指导功能。其实,这也是指导性案例“应当”被“参照”的一个理论根源,即“从指导性案例中提炼出来的案例指导规则本身就是一种比法律和司法解释更为具体的规则”[7]。尽管有学者认为此种提法有失偏颇*此提法的主要反对者有张志铭教授和谢晖教授。张志铭教授从语义学角度进行的分析,“参照执行给裁判者留下了自由裁量的较大空间,似无必须照办的含义,因此,在‘参照’之前加上‘应当’,感觉上是矛盾组合。”具体参见张志铭:《对中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基本认识》,载《法制资讯》2011年第1期。与此不同,谢晖教授明确论述了这一组合的非合理性。他认为,“‘应当’的规范指向是弱强行性规范,而‘参照’的规范属性是限制任意性规范。强行性规范不论强弱,都不应修饰、也不能修饰、更不能改变任意性规范的属性。”参见谢晖:《“应当参照”否议》,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2期。;如果我们将解释法律和漏洞填补功能进一步拓展,就进入“造法型”案例的功能范畴。相对于前两类,“造法型”案例不严格局限于制定法,而是在法律文本可能的意义范围内进行法律类推,创设新的裁判规则。不过可以保证的是,这些所生成的裁判规则依然遵循法的基本原则,其主要意义是面对新型案件拓展裁判思路和提供新的裁判规则。也正因此,此创设规则功能逐步被认为是指导性案例发布的主要参考标准。另外,这种功能还多体现在民商事案件裁判中,如上面所分析的指导性案例15号和58号。
三、指导性案例功能实现的限制因素
制度设立只是方式,司法实效才是目的。在明确了案例指导制度的主要功能是辅助确立法源及其四方面具体展现之后,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分析此“指导性”功能在司法实践中所遭遇的难题。结合当下裁判语境和司法现实,指导性案例功能发挥主要存在三方面限制因素:第一,立法与指导性案例衔接不当;第二,重条文轻案例的司法传统;第三,重裁判结果而轻视裁判标准。对此我们将在下文详细阐述。
(一)立法与指导性案例衔接不当
前面已经厘清,指导性案例的主要功能是辅助确立法源。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立法与指导性案例却存在明显的不对接,这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指导性案例不能发挥补充法律漏洞、缓解立法僵化的作用,并且造成其“准法源”定位不明。对此原因,尽管学者们多有论述,但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裁判者未被赋予解释法律的权利。虽然在具体裁判中,法官一直在进行法律解释,但是其法律解释权的缺失必然导致该解释活动仍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在不具有成文规范之时,相比于主动进行能动解释,裁判者更倾向于“明哲保身”式的逃避解释,这就使得立法与裁判之间的“传送带”失灵业已成为司法的常态[8],这在指导性案例的运用上同样如此。
指导性案例解释功能发挥不足导致无法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所谓法律适用标准就是指导性案例为抽象的法律规范提供一种具体的裁判规则,其生成过程就是通过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对法律规范进行权威性解读,使相对原则的法律条文变得具体化的过程。它是对法律规则具体适用的一种完善形式。换言之,立法机关制定出的抽象法律规范主要是在法律适用中通过指导性案例生成的裁判规则实现其具体应用的,这个过程主要依赖于法官的法律解释权来实现。此时,法官的法律解释权就是指导性案例与立法密切衔接的关键。不过此处的法律解释权主要强调“与裁判过程中法律适用相联系的一项活动,它附属于裁判权,是裁判者适用法律的一个基本前提,有权裁判就有权解释”[9]。
根据我国法律解释体制可知,在案例的裁判上,只有最高人民法院享有法律解释权,具体审理案件的法官并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力。这样,法律解释行为就与具体法律实施过程相分离,法官就成了机械适用法律的工具。在技术层面,指导性案例通过法律解释等法律方法补充法律、弥补法律规范漏洞的目标就缺乏实现的工具。即使我国建立了案例指导制度,在案件的审理中,法官虽然也会适用法律解释技术进行审理,但存在较大顾虑,这样法官就不能充分发现与挖掘法律规范背后的裁判规则,只能保守的运用一些解释技巧从法律规范的表面对案件事实进行剪裁。在严格司法责任要求下,类似案件的审理法官就不敢大胆的运用指导性案例中法律解释规则或裁判规则进行审理,而是依然中规中矩地按照法律的表面规则对案件事实进行审理。此事,实现指导性案例解释法律和创设规则的功能就成为一件“可欲不可求”的事情。
(二)重条文轻案例的司法传统
我国是典型的制定法国家,法官在运用法律规范解决案件纠纷时,更多的是以三段论的论证方式去寻找解决纠纷的方案。法官面对待决案件时最直接想到的是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将法律规范构成要件与案件事实进行结合,形成相互对应的关系,再运用逻辑推论技术完成“法律规范—案件事实—法律判决”的推理过程,这种思维就是演绎推理思维,实现了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过程。而指导性案例的运用主要是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它需要法官运用类比技术识别案件的相似性和不同性,在识别的基础上判断待决案件是否是指导性案例的类似案件,判断之后再决定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是否对待决案件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这个过程实现的是“特殊到特殊”的推理过程。两种裁判思维的巨大差异加重了法官对法律条文的依赖,进而决定了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对指导性案例的轻视态度,故而对法官准确运用指导性案例造成巨大的障碍。
此外,法官转移责任的思想加剧了这一保守态度。法官要对自己所作的裁判结果进行论证说理,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法官将明确的法律条文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虽然也需要进行说理论证,但是相对于援引案例中的裁判规则来说,这种论证却简单的多。在实施错案追究制的背景下,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最先考虑到的是自己担责的问题,当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不能与案件事实相对应时,法官不会想到去翻阅查看案例,他们更多的会依赖司法解释的规范效力去解决疑难案件,在穷尽一切法律规范、司法解释等规范文件之后,他们会将案件层层转移,上报给院长、审判委员会讨论。这种思想使得法官对案例指导采取更加保守的态度,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更难发挥作用。不过可以看到,我国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的司法责任制改革,实现“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将有望改变对指导性案例的保守态度。
(三)重视裁判结果而轻视裁判标准
此项指导性案例功能发挥的障碍来自于裁判者的法治认识。一直以来,实质法治和形式法治就是两项基本的裁判思路。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裁判过程中,形式法治要求严格遵循法律规范,而实质法治则是在法律规范之外,更加强调政治、道德因素对裁判的影响;第二,在裁判结果上,形式法治要求实现裁判的合法性,只要合法就是正确结果。而实质法治则要求实现裁判的可接受性,认为合理性相比合法性具有更高的要求。或者说,相对于形式法治对裁判过程的重视,实质法治更加关注裁判的结果。社会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并非法律专才,它们不关心一个案件的法律程序问题,而是主要考虑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合理性,是一种最朴素的正义观。民众对许霆案、彭宇案、小悦悦案件、于欢案等典型案例的认知和评判就是最好的明证。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法官应该严格做到“铁面无私”,在法律规范和程序之外不考虑其他因素。而只是想强调,在道德评判成本如此之低的自由时代,“民意”很多时候并不靠谱。此时,裁判者如果过于考虑舆论影响,为了避免自己被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而做出倾向民意的判决[10],不仅混淆了法律本身的规范性特征,而且很有可能作出不公正的判决。
为了实现形式法治要求同时兼顾实质法治,最重要的做法就是明确法官裁判的标准或进行解释的准则。通过这种活动,将蕴含在如上司法裁判经验中的规则性内容进行总结和提炼,进而对裁判者的同类行为予以指引和规制,从而最大可能地实现“同案同判”。从指导性案例的功能来看,“指导性”意味着一致性和权威性。此时,发布指导性案例的目的不仅仅是提供法律规范检索或司法解释释明,它更强调运用法律方法产生明确的解释标准和探寻解释规律的目的。此时,那些居于指导性案例之首的“裁判要旨”就成为法官和理论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内容,其中所涉及的诸多法律解释要求和裁判经验等都能为后案的法官在案件裁判中提供援引依据。然而遗憾的是,在相关法律解释问题的研究上,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司法实践者,都并未对此进行系统的抽象、总结和提炼。
四、解决功能实现难题的基本路径
对于指导性案例的援引,最新颁布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实施细则》第十条、第十一条曾提出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参照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由引述,但不作为裁判依据引用。”“在裁判文书中引述相关指导性案例的,应在裁判理由部分引述指导性案例的编号和裁判要点。”由此规定可知,援引指导性案例时,法官应当引述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为裁判结果的裁判理由。从指导性案例功能的司法实践角度来看,要发挥指导性案例的援引效果,实现“指导性”功能,首先在制度上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案例的制度保障,强化裁判要点的“正确的决定性判决理由”的理性权威;其次结合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研究案例的裁判要点,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案例背后蕴含的裁判规则;最后在实践层面主要是重视法律方法特别是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
(一)制度保障下指导性案例司法权威的确立
选择司法功能角度研究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并不等于说是放弃制度上的努力。指导性案例由于具有最高司法机关这一权威发布主体和制度化的运行方式,因而就自然符合法律渊源理论中“制度性权威”的要求[11]。而且,“应当”也是从制度层面上进行的定位,保障指导性案例的制度权威*参见泮伟江:《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1期。在文中作者提出,指导性案例的“应当参照”的效力中的“应当”是借用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最高司法行政管理机构的地位和权力,通过各种法院考评等行政措施和手段从“事实上”实现之效果,“应当”本质上是一种作为事实存在的“内部命令”。,而“参照”是从“实效”层面上进行的定位,它们只是对指导性案例功能的阐述。转化到援引指导性案例作为类似案件裁判结果的论证理由时,首先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指导性案例的正当化进行证成?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指导性案例的制度保障视角入手。换言之,制度保障是援引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理由的前提。即制度保障了指导性案例的正当化,进而使其成为裁判类似案件的理由。这种制度完善应存在于以下两方面。
第一,细化案例公布的主体和案件来源。现行制度规定指导性案例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公布,案例来源于各级法院审结的案件,这种上级法院遴选的机制实际上是剥夺了某些地方法院裁判的“上诉机会”,而且公布案件的标准层次不齐。针对现行制度的问题,在现行司法体制和审级制度不作大改变的情形下,有效的解决方式也许是逐步改变最高人民具有“准立法”性质的司法解释行为,并针对疑难复杂和典型案件作出判决来解释法律适用问题。“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凭良好的公共理性和司法技艺作出被法官和社会公众广泛认同的判决,进而‘内生自发地’‘权威生成’判例(或指导性案例)。”[12]
第二,对指导性案例提供正当性证明。选取审结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时,应由公布主体对该案例进行充分的论证,尽管现行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理由中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了一些论证,但是这些论证还不够,还应当论证“指导性案例的规则要点和法理要点”,“指导性案例对哪一(些)具体法律规则进行了廓清、解释、拓展,以及如何决定的法律和法理依据的正当性证明”[13]。对指导性案例的正当性进行充分证明就使得指导性案例在司法援引中理直气壮,法官审理同类案件时,对指导性案例援引与否就有了具体赞成或反对的对象,在裁判类似案件中对指导性案例的论证就可分为:支持性证明、区别性证明和背离性证明[14]。这种正当性证明的最大实践意义就是加强指导性案例的援引程度。
(二)深入挖掘案例中的裁判规则
随着两大法系的逐渐融合,大陆法系也逐渐加强对判例制度的重视。我国作为典型成文法国家,也逐渐认识到成文法的缺陷,开始运用案例制度予以弥补。实质上,案例制度对成文法的弥补方式主要是结合具体案件深入挖掘抽象法律规范所蕴含的裁判规则,使抽象法律规范能调整新型案例,达到缓解立法僵硬、实现法律统一适用的目的。
指导性案例通过清晰法律、补充法律、解释法律和创设规则四方面具体功能来为之后同类案件提供裁判标准,致力达到“同案同判”司法目标。尽管在实践中,很多法官仍是从“法律规范检索”的功利角度来理解当前的指导性案例,但是从指导性案例的定位来看,指导性意味着权威性和一致性;而从指导性案例的意义来看,最明显的价值正是裁判理由中所揭示的“先例”示范性。正如拉伦茨所认为,发生先例拘束力的不是有既判力的个案裁判,而是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对某法律问题所提的答复。“是在判例中被正确理解或具体化的规范,或者说,是裁判中宣示的标准具有‘拘束力’,后者尚须以‘适切的’规范解释或补充为基础,或以范例性的方式具体化法律原则乃可。”[15]所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公布指导性案例来发挥“应当参照”效力,将一定的法律适用标准及规则运用到后继案件的裁判中,既满足着法治背景下“相似案件相似判决”的基本要求,又把复杂、抽象的法律解释理论转化为简约、有效的法律解释规则,最大限度“激活”和“用足”指导性案例。
在此意义上,研究指导性案例功能就必然转为对案例的“裁判要旨”的分析,从而发现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或法官裁判标准。从当前公布的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旨来看,它们均对法院判决的根本法律思想作了极为简洁的说明:省略案件基本事实,并将判决依据的理由高度概括。而且,不同于大陆法系判例汇编的传统做法,这些“裁判要旨”并非纯粹抽象的“准条文”,而是蕴含着具有指导、启示意义的重要裁判规则、理念或方法,主要解决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的难题。如指导性案例14号对未成年人犯罪“禁止令”适用及指导性案例23号对消费者权利保护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指导性案例18号、28号对劳动关系中弱者的保护,指导性案例17号、23号放宽对消费者购物动机的限制性规定以及指导性案例19号、32号对道路交通犯罪的严格认定等。面对这些“特殊”案例,最有价值的做法就是通过法官的解释和论证活动,发现隐藏在裁判理由中的“指导性因素”,并加以总结、提炼和验证,抽象出规范意义上的法律解释方法或规则,将其参照效力作为该制度是否运行良好的重要标准[16]。因此,对指导性案例中“裁判要旨”的研究,就成为当前法律方法研究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而研究的目的就是挖掘案例的裁判规则,实现指导性案例的功能。
(三)重视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方法运用
指导性案例功能发挥的关键是深入挖掘案例背后蕴含的裁判规则,而裁判规则是通过法律方法的运用来体现。此时,选择哪些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该案必须在法律适用方法上具有指导性。
首先,裁判规则是法律方法运用的结果。从本质上来看,案例指导制度并不能等同于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并且指导性案例生成裁判规则也并非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造法”。法官造法是法官发挥立法者的职能,考虑立法者所应当考虑的因素创造法律规则。而裁判规则生成过程主要是法官在裁判案件时,通过法律解释等各种法律方法的运用将法律规范具体化的过程。其生成的裁判规则并不能脱离法律依据,必须以法律规范作为前提,这种裁判规则只能在普遍性的法律规范遇见特殊性的个案事实时发挥作用,其本质还是一种法律适用,法官并没有超越权限侵犯立法权能。生成的裁判规则是对成文法的细化,它将抽象的、一般的成文法转化为具体的裁判规则,创造性地适用于具体个案事实中。
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方法是关键,它是衔接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的桥梁。这种创造规则的实质是发现已有法律规范中蕴含的法律方法,是对笼统性法律规范的一种细化,是“由粗到细”的创造和解释过程。正如雷磊教授指出,“案例指导制度的作用在于正确解释和适用法律,它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法律适用的活动,而指导性案例主要是用以明确制定法规范含义的解释性案例,并非普通法法系中具有新创法律规范功能的创造性判例。”[17]所以说,在指导性案例的司法运用中,法律方法行使的目的是生成裁判规则,主要功能是创造和解释。
其次,生成裁判规则主要依据法律解释。不同于立法意义上的规则创制,指导性案例生成裁判规则是在司法语境下进行,主要侧重于运用法律解释形成和提炼较为细化的法律适用规则。虽然其运行本质上也可视为一种规则创制活动,但它生成裁判规则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案例来发现制定法解释的方法与标准,这是一个演绎推理过程。此过程虽然在裁判思路上同一般案件具有重要区别,但成文法律规范依旧要作为推理的大前提,而得出的裁判结论也要符合制定法要求。生成裁判规则具有的创造性并不同于立法中的创造性,也不同于“法官造法”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倾向于发现法律,并尽可能阐释清楚法律规范解释的方法与规则。因此,也有学者将指导性案例理解为一种新的法律解释方法,认为案例解释方法不再拘泥于法律条文的文义解释范畴,而是强调“法在事中”的经验主义范畴[18]。指导性案例是结合具体的事实语境来对法律规范进行解释的一种方式,它不断的将普遍性、一般性的法律规范与特殊性的案件事实进行衔接。更重要的是,在衔接过程中,不断地援引各种解释方法进行论证和说明,如文义解释方法、目的解释方法、体系解释方法、当然解释方法、例示性解释方法,以及价值衡量、目的扩张和限缩等。这些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不仅为裁决快速寻找相关法律规范提供依据,而且构成裁判规则生成的重要路径。
最后,法律方法的运用保障了指导性案例功能的发挥。一般而言,指导性案例解释法律的功能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内容上,指导性案例应当包含对法律规范的解释,或者包含对某一或某些法律尚无规定或规定不清的问题上的法律解决方法;第二,形式上,指导性案例的判决书应当包含法官对相应问题的法律解决方案的判决理由,并且通过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对判决理由进行充分论证[19]。此时,一方面,指导性案例在内容上应当是对法律适用难题的解决。这种解决方式包括: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律理解存在较大分歧时,通过法律解释规则对法律解释标准进行统一;法律存在漏洞时,通过漏洞补充或创设规则的方式为法律适用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方式,即提供一种裁判规则。另一方面,法官应当为指导性案例所确定的统一解释标准及提供的裁判规则给出正当性证成理由。这样指导性案例自身才能具有一种强说服力,法官在遇见类似法律适用难题时,才会自觉的去查阅、援引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的功能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五、结语
指导性案例既不同于成文法的制定,也不是司法解释的特殊形式,而是基于法律渊源的“制定法权威”而具有一种“准法源”的地位,这也是指导性案例功能产生的基础。不同于指导性案例所展现出来的“应当参考”效力和“实现同案同判”作用,这种以“指导性”为表现形式的指导性案例功能是其内部固有的效能,并主要展现为清晰法律、补充法律、漏洞补充、创设规则四方面。在司法实践中,该四种功能分别对应不同的案例类型。具体而言,宣法型案例主要发挥的是清晰法律的功能,释法型案例主要发挥的是补充法律和弥补漏洞的功能,而造法型案例主要发挥的是创设规则的功能。该文有关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性”功能分析尽管与当下大多数的指导性案例研究相类似,但不同的是,这种功能视角的切入分析更具有一般性。具体而言,当从功能视角来审视时,指导性案例的价值目标除了通常案例研究所具有的“统一法律适用”并实现“同案同判”的法治目标外,还具有在司法统一的基础之上完善立法的价值,这也正是我们从法律渊源视角来分析指导性案例功能的重要原因。
[1]秦宗文,严正华.刑事案例指导运行实证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4).
[2]王利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J].法学,2012,(1).
[3]雷磊.指导性案例法源地位再思考[J].中国法学,2015,(1).
[4][17]李学成.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功能之反思[J].理论月刊,2015,(4).
[5]陈兴良主编.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69.
[6]资琳.指导性案例同质化处理的困境及突破[J].法学,2017,(1).
[7]陈兴良.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功能之考察[J].法商研究,2012,(2).
[8]宋保振.激活“休眠法条”的法律解释[J].学术交流,2016,(6).
[9]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38.
[10]桑本谦.法律解释的困境[J].法学研究,2004,(5).
[11]Aleksander Peczenik,On Law and Reason,Dordrec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9,pp.313-315.
[12][14]刘树德.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规则的供给模式——兼论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J].清华法学,2015,(4).
[13]张骐.再论指导性案例效力的性质与保障[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1).
[15][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J].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02-303.
[16]刘作翔.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最新进展及其问题[J].东方法学,2015,(3).
[18]陈金钊.案例指导指导下的法律解释及其意义[J].苏州大学学报,2011,(4).
[19]张骐,等.中国司法先例与案例指导制度研究[J].北京:北京大学出社,2016.151-152.
ThePredicamentandOutlettoRealizetheLeadingCaseFunction
SongFei
(East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Shanghai200042)
The function of the leading case is based on the inherent internal efficiency of the quasi-legal source status.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lear law,supplementary law,closing loopholes and creating rules,and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emphases,they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case types.At present,there are three major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ent leading case function,such as improper linking of legislation and leading cases,heavy provisions light case,heavy judge result light judge standard.To this problem,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to establish judicial authority of leading cases,in-depth excavation referee rules of the case,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legal methods in judicial process should be as the basic train of thought of solving the problem.
leading case; leading function; legal interpretation; referee rules
2017-09-02
宋菲,女,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法律方法研究院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法律解释学。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中的运用方法研究”(项目编号:15CFX006)成果。
D901
A
2095-3275(2017)06-0016-09
责任编辑:陈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