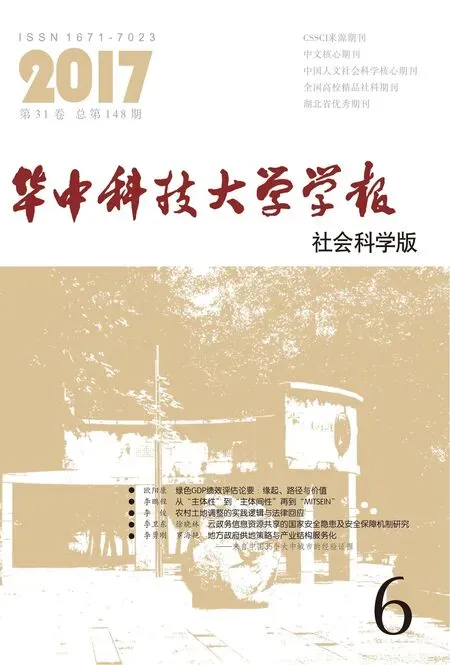农村土地调整的实践逻辑与法律回应
□李俊
农村土地调整的实践逻辑与法律回应
□李俊
我国立法和相关政策从制度规范的角度否定了人口增减原因的农地调整,并将调整范围限定在狭义的法定情形之中。农地调整作为公权力涉入私法的一项衡平工具,在公平分配和保障农地基本利用效率上具有不同的规范路径。从历史实证的角度考察,农地调整制度的“废除”应解释为一项“表面共识”,即“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为完成其村庄治理目标的附属产物。在当前的社会实证考察中,农地调整仍然存在实践需求,其内含的制度意蕴无法借助法定调整模式实现,在三轮承包时采取适当调整承包期限、对新增人口予以经济补偿或其他“可替代性保障”的法技术手段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立足于规范实证,针对集体决议借助农地调整介入私法领域的行为,调整制度还承担着保持最小耕种单位以及特殊情形下整合土地规模等功能,且应当在未来中国《民法典》中予以补充规范。不同的实证考察视角,可厘清中国农地调整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冲突,进而在现行制度框架下采纳“可替代性保障”和“对既有用益物权进行调整”的双向路径,更妥适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农地价值目标。
表面共识;农地调整;可替代性保障;最小耕种单位;规范路径
一、问题与进路
公平和效率一直被视为中国农地改革的核心价值。在农业市场经济活动中,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通常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通过制度去保护农地经营人的利益并促使其提高效率。“三权分置”的农地政策将经营权与承包权相剥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相对独立的集体农地权利结构,也是旨在促进农业经营效率的一种有效手段[1]。与之相应,在农地资源的分配上,公平则作为一项主要的价值标准,并体现在承包权的合理分配上。承包权的分配与经营利益的再调整,在集体所有权的制度框架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土地制度。不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实施之后,承包期内的农地调整因与物权性的承包经营权相对峙,前者作为分配公平领域的一项技术性手段被“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所禁止。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农地承包经营背景下,“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需要匹配土地调整的制度内涵才可能落实公平分配原则,达到农村治理的政策目的。那么,基于实证立场对现行土地调整制度进行考察是落实农地制度法治化的一项必经的过程,重新审视和检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内涵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调整作为一项实现农地公平享有和有效利用的工具,是集体决议、土地管理与私权变更相耦合的结果。以《物权法》为基础,在不与现行用益物权制度相抵牾的情形下,如何实现农地调整内含的公平分配价值乃农地制度设计的关键之一。只不过,农地调整并非纯粹的私权,尤其立足于土地管理和利用的角度时,农地调整应被视为一项附条件的权力规制手段。同时,农地调整并不局限于公平分配,还在于如何更有效、合理地利用农地。那么农地调整的范围也就非常宽泛,既包含土地承包期内调整和期外调整,还可能囊括“未满足最小耕种规模”而规范土地利用的强制性调整,甚至于城乡统一建设中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动态调整等等情形。事实上,农地调整的概念并非严格的法律用语,就其词义而言,是一项为实现公共利益、土地的可利用性、经济效益和公平分配的工具,既含涉以强制性手段对私法的干涉,还涉及农地领域私法自治与强制性规范的界限①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调整意为调弄整治,重新调配或安排,使合于新的情况。。申言之,以符合具体调整目的的方式进行私法规范,在于土地调整内涵在私法中的具体化,其效力根据仍然基于法律规范和国家政策对分配公平和生存保障的法定化干预。
在《物权法》实施的十年过程中,我国农村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城镇化被快速推动并容纳了大量农村适龄劳动力就业,同时各种新型经营主体和资本也进入农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农业主体大量涌现,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速度加快,生产工具和农业科技的发展也进一步提高了农业效率,农业经营的体制和方式也正在经历重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作为家庭联产承包制最主要的载体,应回应这些新的发展,并使得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在符合农地治理目标的基础上与新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相适应。藉此,一方面,在历史实证之下,反思农地调整制度可以挖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要旨,揭示“表面共识”之下中央农地改革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真实意愿;另一方面,在对社会实证予以反思的基础上,党和国家的政策、现行法律规范与农地实践亟须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视阈下予以体系化阐释和论证,尤其在相互抵牾和制度欠缺之处有待立法、法解释和法律适用的进一步完善。
二、农地调整政策的表面共识与隐藏矛盾
(一)达成“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的表面共识
1995年《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意见的通知》(国发〔1995〕7号)强调“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即在农村土地承包期内,除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并转为非农业户口两种情形外,作为发包方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因承包方家庭成员的增减(如婚丧嫁娶、考学、工作等)而部分或全部收回承包地。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的基础上,《物权法》第一百三十条进一步规定:“发包人在承包期内不得调整承包地,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才能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地进行适当调整。如存在法定除外情形时,还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才能进行调整。此外,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应当按其约定。”需要阐明的是,在《物权法》颁布前,“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解决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的诸多问题,即农民缺乏稳定的土地投资预期、土地生产率下降、土地细碎化越来越严重和调地成本太高等顽疾。而在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之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依然有效,且与物权法形成规范与政策上的对应,对稳定承包关系具有更直观的影响力。
农地调整与农地的不稳定利用相联系,其主要原因在于承包期内调整土地。鉴于此,我国为了实现农地稳定的制度目标和减轻农村治理的难度,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在当前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的背景下,土地调整仅意味着赋予集体成员新的承包经营权,而并不剥夺既有的承包权。不过,土地调整制度并不能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完全对应。尤其在公共话语中,通常并未严格区分农地调整的不同内容,因此在导致讨论农地调整时,会因为对概念本身存在误区而陷入混战。或者说,在没有对农地调整的内涵形成有效的对话之前,讨论农地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话语之间、话语与实践之间的背离,甚至否定农地调整也仅仅是一项“表面共识”。事实上,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分析农地调整的相关制度和实践,都无法脱离农村治理的视角,后者才可能揭示农地调整究竟是农村土地实践的需要抑或是基于稳定农村社会的一种“休克疗法”[2]。显然,这种可能存在于农地调整制度、话语与实践之间的悖论,只有通过厘清“表面共识”背后的逻辑才能获以解答。
我国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伊始,承包经营权最初被设计为一项债权性民事权利。土地调整作为保障土地公平分配的重要制度,可以对债权性的承包经营权进行调整。土地承包权的调整与人口增减挂钩,当因自然生死、婚嫁、征地、土地灭失等原因出现人口变动时,农村承包地可以相应作出调整。通常,调整的周期只有三到五年,并且仅需村集体同意即可。调整制度的内涵也就被狭义地局限在因人口变动所导致的公平分配问题上。但是,调整制度在保护了无地或者少地农民阶层利益的同时,这一制度安排却迫使乡村干部和农民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维持土地的稳定利用。那么从村庄治理角度,土地的调整带来的纠纷远多于利益,虽然解决了少部分农民的土地需求并使得农地的分配更加公平,但是无疑增添了农地纠纷数量①在出台“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之前,调地以及解决调地纠纷乃村集体组织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任务。。更何况,村集体或村干部有借农地调整之名获取不正当利益之嫌,甚至还有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的土地调整形式,使得实践中的农地调整更显复杂[3]。此外,由于农地调整建立在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之上,在农地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没有限定清晰的状况下,农地调整必然也给农地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4]。而农村社会的稳定是农村治理中的重要内容,稳定甚至可以“牺牲”部分农民的土地需求,藉此国家政策对于调整的态度是消极的甚至是否定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的根源在于稳定农地利用关系,是在农村治理的需求下达成不调整政策的一项“表面共识”。也即,这一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土地调整所欲实现的公平价值功能,只是从农村治理的角度以牺牲农地分配的公正性为代价来避免调整带来的治理困难。
(二)隐藏于村庄治理下的农地调整矛盾
从历史实证的角度考察,“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在本质上是村庄治理的结果,土地调整的内在需求并未解决。对于集体成员而言,调整的需求取决于承包主体对农地的享有状况。二轮延包后,对于有较为充足承包地的农户来说,税费改革后的农地调整会减少土地所带来的收益。从趋利性而言,这部分农民希望维持富足的土地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因而没有调整的意愿。不过在实践中,对于地少人多的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来讲,如果土地承包的数量和承包期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生变化,那么也会带来不利的结果。由于集体成员资格的取得或丧失等因素的变化,原先的土地分配必然会落后于农村社会的变化,无地或缺地农民通过土地调整来获得生存保障的意愿极为强烈。由此可见,不同的集体成员或具有不同地方性共识的区域,对待农地调整的态度不尽一致。从表象上看,现行的农地不调整政策是官方和农民所达成的一致共识,但其背后的利益衡量才是解答农地治理的关键。
稳定农地的政策导向与避免因调整的滥用共同促成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共识,但本质上并非旨在消灭农地调整所内含的公平分配[5]。也就是说,对承包地不予调整并非实践的真实写照,而是遵从“农地稳定-调整权滥用-不调整的表面共识”逻辑的结果。与其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乃确定承包经营权权属的需要,不如归结于农村治理下农地调整的利弊衡量。因此,在政策的实施上,存在有意曲解法律规范的可能性。尤其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农地实践中,农村“运动”所概括的含义经常超出制度本身的解释范畴②关于运动的研究,社会学界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近世状态的研究早有公论。所谓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其他影响因素,请参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家族、国家与社会——福建美法村的社区史》,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8页。。在农地制度的形成过程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土地制度就与政治任务具有密切关系,甚至诸如大众传播的媒介功能和行政力量都拓展了政策所应当限定的范围。在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多次分离的过程中,基于农村治理而产生的“官方话语”仍然在农地制度的演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作为工具的调整制度之上。需要厘清的是,在从肯定调整到否定调整的过程中,“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将农地调整限定在极其狭窄的空间内,在政策话语层面扼杀了农地调整的灵活性和其应扮演的社会功能。
三、农地调整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实证解读
虽然上述历史实证的解析揭示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表面共识,但是籍由社会实证的角度对这一政策的运行状况予以解读,立法者、政策制定者和法适用者才可能在规范实证的基础上对农地调整予以完善。事实上,关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除涉及承包地调整之外,还关涉农地利用的承包期,甚至于两者在本质上可视为一个问题的两面[6]。在系统考虑承包期和农地调整的同时,还有赖于从政策、规范和村民自治的治理结构中进一步解读农地调整。
(一)“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成为当前农地问题最为突出的矛盾
农地调整概念在使用时存在内容上的差异,在形成“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共识的过程中也并未完全明确。概念的歧义使得概念使用者往往含糊地包括不同的内容,导致因概念本身存在误区而陷入争议[7]。“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作为一项表面共识,其潜在的问题并没有因该政策的实施而获得有效的解决。其直接后果是,农地调整所具有的制度优势在实践中再次隐性地获得重视。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中心的七省调研中,当受访农户被问及“自2003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来本村土地承包经营中主要问题是什么时,居首位的是“承包地调整问题”,共计49.80%的农户选择此项①本文社会实证的考察数据均来源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中心于2015年7-8月对全国七省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调研结果。。
在规范实证层面,除《物权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外,发包人在承包期限内不得调整承包地。不过,鉴于当时的立法者对中国农地制度全面改革缺乏足够的实践素材和完善的配套措施,作为民事基本法的《物权法》除明确承包经营权属用益物权之外,并未协调《农村土地承包法》对调整规则做进一步的细致规定。事实上,在《物权法》实施之后,围绕如何完善具有物权性的承包经营权成为农地政策和农地实践的关键命题。对物权性承包经营权的研究和适用,也逐渐脱离了性质之争,而是探究以承包经营权为核心的各类土地利用制度[8]。那么在实践中,在农地确权等问题尚未完全妥善解决的情况下,农地调整仍然被变相地视为衡平承包经营权益的有效手段,“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因无法满足土地公平分配的实践需求而饱受诟病。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并没有如同预期那样有利而无一害,承包地的调整仍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保持农地长期稳定的制度设计与现实中集体成员对农地调整的普遍认同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冲突。
(二)“三轮延包”时承包经营权的期限
自1998年左右第一轮承包结束后,基于保护承包经营权人的稳定利益和长期保护农地耕种关系,我国农地承包已进入为期三十年的第二轮承包期。不过,该期限的预设并没有将农业轮作、土地改良、气候变化以及农业效益周期作为影响因素进行考量,仍然是基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表面共识所作出的统一规范,其目标旨在稳定农地承包关系和保持土地的“长期”利用。那么,在维持“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的前提下,讨论三轮延包时的承包期限的关键在于如何衡平土地承包的长期稳定利用与承包权分配公平之间的关系。
针对第三轮农地承包的承包期,调研中有33.93%的农户倾向于三十年的规定,而希望确定为十五年的农户占28.57%,希望承包期规定为五十年和七十年的农户则分别占到5.75%和6.35%。需要注意的是,还有25.40%的人选择了“其他”,并作出“承包期永久”和“短于十五年,五年承包期最佳”两种相对极端的回答,且后者所占的比例居多。许多农户表示:“承包地三十年内不允许调整,可能使得缺乏劳动力的农户家庭占有大量土地,反而劳动力充裕的农户家庭无地可种,导致土地分配极为不均”。调研所反映的情况显示,在农地稳定和承包人权利保护的基础上,希望承包期相对缩短的农户更关心新增人口的土地承包问题,认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所产生的顽疾应当通过缩短承包期来解决,承包期限太长会导致土地占有不均衡。相反,希望承包期相对较长的农户出现在耕地面积较少且耕种效益低的地区,认为长时间的农地承包更利于节约调整成本。实际上,对土地承包期限的解答具有地方差异化,甚至在同一地区也会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存在不同的意见,但农地调整仍旧无法脱离“地方性共识”,结合调整占地不均、解决新增人口土地承包权等因素,根据区域的不同差异化地将承包期确定为十五年、十年甚至五年更为符合当前我国农地承包的现状。其结果使得立法或政策通过承包经营权的期限的设置实现了土地调整制度所内含的调节功能②也有学者在社会实证中发现:“无地农民通过家庭内部继承获得承包权已经成为农村社会普遍现象。无地农民群体的存在对当下农村社会而言,未构成严峻的问题;土地之所以不再重新调整,是因为土地调整预期收益低而组织成本高,从而三十年不变的政策从一种外部强制性制度安排成为一种内生制度安排并延续下来。”具体参见商春荣、叶兰:《无地农民与土地调整、土地流转及土地继承的关系——基于广东、湖南两省9个村的调查》,载《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事实上,在用益物权下妥适规定农地承包期限,不仅可以使得已享有农地承包权的集体成员的财产利益获得有效保护,还可以关照到没能实际享有承包权或实际享有承包权不足的集体成员。因此,在《物权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调整承包地的基础上,第一百二十六条“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的规定应立足于社会实证考察的角度予以重新审视。
此外,在农地承包期限届满时,如何确定承包经营权亦是未来规范农地承包制度的关键。只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五十五条一方面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另一方面又规定从事家庭承包经营的为农村承包经营户。虽然《民法总则》这一变化明确了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并以集体成员替代“家户”作为承包权利的主体,但是改变了我国原有的以承包经营户为基础的承包关系。基于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规则,《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农户的概念得以进一步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应构建为农地承包权利的享有者。在三轮延包之前,这一转变应当在当前的确权过程中予以明确,使得公平分配的理念能通过承包制度予以落实。在此基础上,对于符合土地耕种条件且享有承包经营权的集体成员可以继续承包,在符合《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下延续现有的承包权。对于失去成员资格的原集体成员,集体作为发包人收回其承包经营权,并将其原先承包的土地发包给无地或缺地成员。如此处理,农地调整所代表的分配公平价值,在成员权和适当变化承包期的制度协同下才能获以实现,以达到真正的“大稳定、小调整”[9]。
(三)政策、规范与村民自治中农地调整实践
《物权法》从法律制度层面落实了党和国家关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人口增减导致的农地调整问题由《物权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二款规范,并通过引介规范的形式使得《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成为新增人口获得土地的具体情形,也即,“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通过依法开垦等方式增加的土地和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土地都应当按照家庭承包的方式用于调整承包土地或承包给新增人口,以缓解人地矛盾”。“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一方面维护了农民权利和农村社会的稳定,杜绝了作为发包方的集体肆意收回承包地的情形。同时,为了缓解因“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的实施给新增人口带来的困局,在保护既有的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上依然存在土地调整的特殊空间。
在社会实证调研中,隐性的农地调整情形依然存在,甚至还包括处于承包期内的土地。承包田和口粮田的两田制,以及无承包经营权证的历史原因,仍然使得农地调整在不少地方隐性适用①尽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1997年8月27日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且明确整顿“两田制”。不过在调研中,已实行“两田制”的部分村集体,虽然按照规定将承包权明确到户,但是由于承包权并未完成确权,实际上仍然存在“形式上承包到户,实际上处于灵活调整”的模式。。即便在实行了土地延包和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之后,部分村庄仍然按原来约定俗成的惯例,进行承包土地的调整分配。这种约定俗成的承包土地分配形式,在全体村民(甚至包括迁出户口前的村民在内)没有异议的情形下,被视为一项村规民约②参见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年12月11日民事判决书,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10期。。只不过,如同“陈清棕诉亭洋村一组、亭洋村村委会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案”③参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年12月11日二审民事判决书,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10期。,村规民约在纠纷产生时并不具有对抗效力,仍然应以法定的形式确定承包权。在调研中,有23.21%的农户表示调整过土地,其调整原因也较为不一。其中,存在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14户,11.97%)因人口增减导致农户间承包地不均(95户,81.20%)因征地等原因导致失地(17户,14.53%)以及其他原因导致承包地调整的情形。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G村和广东省江门市F村的调研访谈中,不少农户表示对农地调整有很强的现实需求,甚至认为调整是破解土地占有不公、新增人口无地可分、合理提高农地效率的有效手段④依学术惯例,本文在调研访谈中对县级以下的地名和人名均予以匿名处理。。当然,占有76.79%之多的受访农户表示所在的村自《物权法》颁布以来未调整过土地。这些农户认为未调整的原因囊括了法律政策不允许(66.15%)政府不允许(16.02%)村民不愿意(28.68%)村干部(村委会)的原因而未能调整(4.39%)以及11.11%的其他原因。虽然法律和政策不允许是没有调整农地最为直接的因素,但存在农地调整情形的受访农户表示:“如果全体村民同意调整土地,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以下简称《村民自治法》)所表达的集体意志应当优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规定。”遗憾的是,从法规范层级而言,《村民自治法》并不能在无法定原因下对抗《物权法》这一民事基本法。这也充分显示出,保障无地与失地农民是《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和未来中国民法典编纂中不可回避的难题。此外需要重视的是,调研中集体成员所言的农地调整,并不局限于承包期内调整土地的情形,还包含避免土地细碎化产生的调整、因提高农业效率所产生的调整、因规模经营或现代农业所导致的调整等内容。
无论是否存在调整情形,针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农地政策,多达75.60%的集体成员在调研访谈中认为不合理。集体成员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不满的原因在于新增人口无法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来获得调整土地,同时在法律上又无法对已承包地进行调整,导致法律规范与现实需求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上述调研数据一方面显示出绝大多数村户具有调整已承包土地的意愿和需求,期待某种制度能具有土地分配公平的农地调整功能;另外一方面,当前农地调整的意愿并不满足于现行法律所规定的“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因人口增减导致农户间承包地不均的现状使得“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存在弊端,那么通过调整承包期限或者是“为新增人口提供与获得承包经营权相当的权益”成为完善现行法的一项有效路径[10]。
四、后确权时代农地利益的调整模式
(一)完善既有的农地调整程序来实现“大稳定、小调整”
通过对土地调整政策的解析和调研数据的解读,调研组发现二轮承包后的新增人口是引发土地调整诉求的主要原因,尤其在二轮承包完全延续一轮承包分配状况的村庄更是如此。针对新增人口的土地调整,被调农地存在两类形态,即已承包的土地和“机动地、开垦获得的新增土地和收回的承包地”。虽然新增人口获得承包地的最佳方式是依托第一类土地,但《物权法》第一百三十条的禁止性规定已使其无法实现。第二类情形属于法定可供调整的情形,不过在现实中却存在无地可调的局面。例如,其中开垦获得的新增土地主要源于“四荒地”。调研中,有65.48%的农户表示所在的村没有“四荒地”。即便存在“四荒地”,这部分村庄又同时存在“承包后没有登记确权”(50.57%)“村集体未进行管理”(45.98%)“村民抢种矛盾大”(26.44%)和“自发开垦后权利得不到保障”(23.56%)等一系列问题。可见,将新开垦的土地分配给新增人口的规定并不能满足现实需求。此外,在调研中绝大多数村民还表示目前本村没有机动地,也不存在承包地被收回的情形,新增人口寄希望于机动地和收回承包地同样毫无适用空间。
即便如此,现行立法和政策仍然为农村土地调整规定了制度适用条件,为未来的农地调整提供了可能性。从农地调整的启动程序来看,必须存在《物权法》第二十七条的法定情形时才能调整。其关键,在于调整农地需要履行相关的程序,而此项程序又直接涉及调整权的权利来源。在七省调研中,认为“仅需要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即可调整土地”的占有39.68%;认为“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再由政府批准后才可调整承包地”的农户占37.10%。而选择“仅发包方决定即可”、“仅需政府批准”、“依照法律或者政府文件的规定”、“以户为单位召开代表大会”以及“经任何程序都不能调整”等情形的均占少数。在如何进行土地调整的程序问题上,农户在实践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治需求,大多希望亲自参与决定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同时也希冀政府代表的国家权力来介入和平衡各方利益。事实上,立法对于集体成员的决议行为范围已经由《物权法》予以规范,只是需要进一步说明村规民约并不能与民事基本法的强制性规定相冲突,前者无法从法解释的角度排除后者的适用。
(二)缩短承包期作为一项隐性调整手段有益于实现农地的公平分配
无法实现承包期内小调整的逻辑结果是新增人口无法获得承包地,并直接导致“农地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法律规定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成为农地分配不公的批判对象。既有的法定调整方式不同于承包期内的农地调整规则,也不同于缩短承包期限并辅之土地重新分配的制度。事实上,将调整问题与承包期问题相关联,并不失为一项可能的解决方案。从前述“农地期限”的调研情况来看,农户认为三十年承包期过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土地分配在“长期不变”中形成的不公,三十年内可能会新增两代集体成员,而新增人口获得土地的机会又极小。如果在第三轮承包时,缩短承包期限就可能在人口变化(增减人口、妇女婚嫁)的自然周期内重新分配土地,从而解决承包地占有不均的问题,实现本属于农地调整的制度功能。如此,不仅期内调整的诉求不再凸显,而且可以达到一种“大稳定、小调整”模式的理想效果[11]。
虽然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在稳定承包关系上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对其期限的僵化适用就会陷入“个体”所有权的陷阱,使得农地权利的配置无法达到制度的预设目标。在当前“三权分置”的农地权利结构下,放活经营权旨在提高农业效率和保障集体成员充分实现其承包利益,承包权的设置则在与承包期限、农地确权等制度相协调后才可能达到预定的效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法定物权类型,制度的核心在于权利保护的优先性,同时辅以土地长期稳定利用的功能,农地承包经营权人享有权利的时间长短并不必然影响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性质。换言之,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三十年期限相对调短并不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项用益物权,也不会带来明显的负面效果。事实上,在物权法既有规范的基础上,作为财产性权利的承包权和经营权仅仅是性质不同的租赁权而已[12]。在用益物权的私法史形成过程中,优先力和排他力乃用益物权与债权进行本质区分的关键,两者区分的意义在于法效上的差异,并不由权利的期限的长短所决定。立法或政策可以通过严格的法定程序,依据地方性需求而赋予第三轮农地承包不同的承包期。那么,十五年、十年抑或五年承包权,仅仅是一项法律和政策上的选择,承包期的长短只是立法者在设定承包经营权内容时的考量因素,与用益物权的性质无涉[13]。
虽然承包期限的缩短会弱化土地的稳定性,但是这一措施可以相对灵活地满足农地调整所含有的利益调节功能。发包周期的缩短并不会导致农地的不稳定,相反,在承包期和农地调整具有“地方性共识”的基础上,稳定的农地承包制度将进一步理性化和灵活化。当然,短期承包内含的负面法效也会具体表现在农村治理层面,即村委会的工作量相应增加、土地的分配成为村集体的常规事项,等等。藉此,农地承包期可以采用稳定为主、灵活为辅的立法技术,一方面遵照党的十九大报告“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的规定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为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第三轮延包仍然与《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保持一致。但是,该期限的规定仍然是从土地稳定和村庄治理的角度所作的预设,并没有否定农地调整制度含有的公平分配价值。;另一方面,以例外规定的方式,通过严格的法定程序确定有差异的承包期限,从而间接地实现农地调整的法律效果,并满足“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内涵。
(三)基于成员权产生可替代土地调整利益的经济补偿
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政策上明确提出“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并在三权分置的农地权利结构下将成员权设计为集体所有权的一项内在权利[14]。在当前的承包经营结构中,以集体成员替代“家户”作为承包主体,才可以进一步明晰承包权属和利用关系,以落实《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通常,承包权借助成员资格得以实现[15]。从集体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到集体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结构的发展历程中,成员权实际上成为一种承载身份的载体,甚至逐渐成为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权利享有前提[16]。在坚持集体所有权的基础上,基于成员权而构建的承包经营关系成为完善当前农地利用制度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后续修订都应基于成员权来解决农地矛盾和完善农地制度,以落实承包权和经营权制度。
主体资格从承包经营户过渡到集体成员后,农地调整也应当以成员权为基础展开,使得土地调整的法律效果更为明确。不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方式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法定化模式和集体决议模式的争议,在实践中主要通过村规民约、地方立法和司法裁判加以调控。”[17]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标准的认定成为成员权身份确定的契机,也即新增成员通过集体决议而确定,成员权的身份性归为特定人享有,同时区别于以家庭为中心的经营主体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18]。在确定成员权的取得方式之后,集体成员在缺地、无地状态下,可通过“可替代性保障”的法技术手段来弥补其利益,也符合“现代社会中,物权由本来注重对标的物的现实支配的实体权,演变为注重收取代价的价值权”的论断[19]。基于集体所有权所产生的村集体利益与基于承包经营权享有的利益并非一致,在缺乏承包期内进行调整的法规范时,前者所产生的集体利益对无地和缺地农民具有补偿的可能性。如此,由集体所有权所产生的“其他利益补偿”将逐渐替代农地调整的功能,通过集体分红、农村社保等形式来实现如同土地公平分配的价值目标。
(四)公权力对“最小耕种单位”进行调整的强制性干预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农地调整行为,在性质应属于一项集体决议行为。集体决议所产生的调整效力,仅针对集体经济组织依法预留的机动地、通过依法开垦等方式增加的土地,以及承包方依法自愿交回的农地。承包期内的土地调整则出现制度和政策上的双向规定,其中针对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的情形,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条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将村民会议或者是村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作为一项必要要件。我国立法将承包经营权确定为用益物权,就是借此稳定农地关系,将上述调整作为一项例外。
从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的立法情况来看,对乡村土地所有权的调整乃公权力对私权的一项强制性干涉手段,并作为一项积极调整权而存在。其制度主旨在于维护农业耕种的基本条件,并不考虑调整的对象是否属于已明确个体所有权的土地。例如在《意大利民法典》之中,对用于耕作或者适宜耕种的土地,在转移、分割或其他处分该土地的所有权时,以及对该土地设定或者转移他物权时,就必须以“最小耕作单位”为基础①参见《意大利民法典》第三编第二节第二分节第846条,费安玲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也即,农地的利用应当基于一个农业家庭劳作所必需的足够面积,并将先进农业技术规则所设定的农地排除在此限之外。同时,如果某权利人享有的农地在物理空间上包含了由他人所有的低于“最小耕种单位”面积的农地,该权利人可以旨在更好地规划和利用土地为由,向相邻小片土地的权利人支付合理价金,从而请求其出让该土地。当大片土地和小片土地的权利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司法机构可以听取该地区农业行业协会的意见之后作出裁决。同理,《瑞士民法典》第七百零二条在规范公法对所有权的限制中,规定“基于土地的改良、土地的分割和农村耕地的合并,有权制定关于限制土地所有权的规定。”②参见《瑞士民法典》第702条,戴永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此外,大陆法系在私权绝对的基本原则之下,为达成农地整合和整齐规整的目标也可以采取符合法定要件的农地调整,通过保障土地利用的基本效率来限制土地所有权。
因此,农地调整是基于土地的公平分配和农地的理性利用而存在,即便在农地的归属和利用关系明确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作为一项对私权予以法定干预的手段。当前我国的农地调整,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法定农地调整的条件和程序,并通过“可替代性保障”来弥补承包期三十年所产生的弊端,减小“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还应当借助集体意志适当拓宽农地调整的范围,不局限于当前的消极调整模式。基于农村土地整治和资源理性利用的目标,我国农村有必要保持最小耕种单位并适当整合土地规模,从制度规范的角度增加具有严格法定条件的“对既有用益物权进行调整”的方案。后一种农地调整路径是一种针对物权的调整方案,并不能被视为对承包经营权的侵害,而只是一项对用益物权予以限制的具体形态。尤其在中国南部地区,土地细碎化现象尤为严重,在地少人多的普遍状况下,对既有承包权完全不予调整的模式也会制约农地的合理利用。那么,农地调整不仅仅只存在传统意义上“给无地或缺地集体成员分地”,还应囊括“对未保持‘最小耕种单位’的土地进行强制性调整行为”,使得土地调整具备双向路径,也即,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土地”乃原则规定,例外承认对“不满足最小耕种单位”的调整行为③至于如何确定“最小耕作单位”,大陆法系通常借助第三方农业行业协会来确定,并在不同区域的采取不同的数额标准。事实上,大陆法系地方农业行业协会在农地利用中极为重要,比如意大利地方农业协会在确定租金、最小耕种面积、农地仲裁等问题上均具有话语权,甚至在农地司法裁判中起到关键作用。鉴于我国地域辽阔并且具有不同的地理条件和耕种环境,“最小耕种单位”的规定仍然应当考虑中国地区之间自然条件的差异,例如黑龙江省和贵州省对此规定必定不同。此外,地区性差异仍然应当在既有的制度框架内规定,尤其是我国当前并未建立如同大陆法系农业行业协会的情况下,如何因地制宜的确定“最小耕种单位”无疑是一个难题。可行的方法是,各省地方立法机构可以按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所赋予的地方立法权,根据各省的具体情况分别制定。在新修订的《立法法》扩权赋予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之后,甚至于设区的市也可以根据上位法的规定来进一步明确本市的农地“最小耕种单位”,以达到因地制宜的目标。。
五、结语
基于法源的层级和新法优于旧法的适用规则,《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八条应当优先适用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现行政策,也即,农地调整并非被政策所禁止,只是应当在法定条件下予以行使。其矛盾的根源在于,当前农村主要面临着无地可调的困局。在承包经营权设定为一种用益物权之后,“三权分置”的农地权利结构则进一步拓展了农地权利的内容,承包权和经营权均成为财产性权利,而基于集体所有权而派生的成员权成为农地公平分配的身份基础。在“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调整承包地”的制度框架内,立法者在不同区域内对《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所规定的承包期限予以区分适用的方法,更为符合分配公平的价值理念。同时,达成“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表面共识”即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农地的公平分配,但在村庄治理上仍然具有积极效果,其解决方案应当对新增人口给予相应的“可替代保障”,以维护新成员公平享有集体财产的权利。此外,我国应从集约用地和维护土地耕种价值的角度,对未保持“最小耕种单位”的土地进行强制性调整,并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以“但书”条款的法技术方式设置于“物权编”中④对应现行法规范,则应设置于《物权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之中。。
[1]高飞:《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法理阐释与制度意蕴》,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
[2]伦海波:《“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法学解析》,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5月总第128期。
[3]陈锡文等:《中国农村制度变迁6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高飞:《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5]黄华:《论话语的秩序——福柯话语理论的一次重要转折》,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6]高飞:《土地承包经营权稳定与承包地调整的冲突及其解决之道—— 一个社会实证的分析》,载《土地法制科学》2017年第1期。
[7]梁治平(编):《法制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李俊:《罗马法上的农地永久租赁及其双重影响》,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
[9]陈柏峰:《地方性共识与农地承包的法律实践》,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
[10]韩松:《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6期。
[11]赵阳:《对农地再分配制度的重新认识》,载《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4期。
[12]李俊:《罗马法上的农地永久租赁及其双重影响》,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
[13]李俊:《意大利农地租赁合同研究》,载《私法研究》(第19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14]蔡立东、姜楠:《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置的法构造》,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
[15]陈小君:《我国农民集体成员权的立法抉择》,载《清华法学》2017年第2期。
[16]陈小君:《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革的思路与框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相关内容解读》,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4期。
[17]戴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制度研究》,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6期。
[18]韩松:《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成员受益权能》,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1期。
[19]梁上上:《物权法定主义:在自由与强制之间》,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The Logic of Practice in the Adjustment of Rural Land and the Legal Response
LI Jun,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 and Law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nstitutional norms,the legislation and policies deny the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land for the reasons of population increase and fall,and limit the scope of adjustment to the narrow legal situation.As a public right involved in private law,the agricultural land adjustment is a balance tools.And in the field of th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and the use efficiency of farmland,the adjustment has a different normative path.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the “aboli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adjustment system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surface consensus”, which is an ancillary product of the policy of“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eople without increasing the land,or reducing the number of the people without reducing the land”.In current social study, the adjustment of agricultural land is still a practical needs, and the implication of the system can not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legal adjustment mode.In the third round of land contracting,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djust the contracting period,give economic compensation to the new population or other“Alternative compensation ”of the legal means still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egal rule, and collective decision intervene in the field of private law,the adjustment system is responsible for maintaining the minimum cultivated unit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land size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and should be supplemented in the future China Civil Code.The abov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can clarif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heory and the reality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adjustment, and then adopt the two-way path of“alternative protection” and “adjustment the existing interests of the usufructuary right” under the existing system framework,to achieve the farmland value targets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surface consensus; agricultural land; alternative compensation; the minimum cultivated units;normative path
DF45;DF02
A
1671-7023(2017)06-0065-09
李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讲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创新团队计划,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大陆法系农地权利体系研究”(16SFB3034)
2017-09-10
责任编辑 胡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