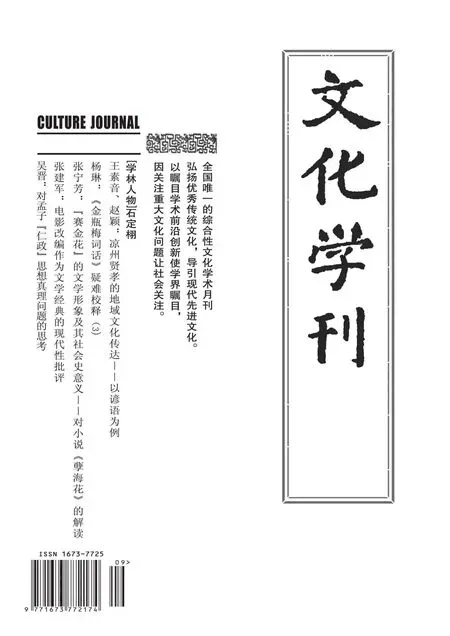张爱玲作品中的生存焦虑
——从《倾城之恋》说起
杨 磊 霍洪波 戴玉竹
(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文学评论】
张爱玲作品中的生存焦虑
——从《倾城之恋》说起
杨 磊 霍洪波 戴玉竹
(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张爱玲的不幸人生际遇,导致她对人性、对周围世界产生了怀疑。因此,她的作品中始终存在一种与现实对抗甚至于否定的抗拒性张力。这些现实与文化之间体现出的生存焦虑,远远超越了她那个时代所涵盖的文化指向,标示出一种后现代性文化情绪。
张爱玲;生存焦虑;后现代
张爱玲在逃离家庭并否定母亲罗曼蒂克爱的过程中,完成了她对人性最初的理解。这是张爱玲在构建小说世界之前,以她的经验对待这个世界的基本心态,它在潜移默化中左右着她的世界观,最终形成了封闭性、狭窄性的生活。因此可以说,正是她所处的家族与时代成全了她。她剖析人性的自私,进而进入人性深层次的悲观,后又扩展到对历史文明的悲观。正如后来她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地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1]
张爱玲的小说总是存有一种“虚无性情绪”,这种“虚无性情绪”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对以家庭为中心的亲情的失望与质疑,同时战争的毁灭性亦让她感受到世事的无常与命运的莫测,让她看不到希望所在。在这紧张的生存环境中,一切都是虚妄,对物质生活本身之外的超越是不允许存在的。她否定了一切,也就走向了虚无。所以她说只看眼皮底下的一点生活,即张爱玲对人生的探寻融入了世俗,从世俗的生活体验中寻求精神的超脱与灵魂的升华。王安忆曾写道:“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是最易打动人心的图书,但真懂的人其实不多。没有多少人能从她所描写的细节里体会到这城市的‘虚无’正是因为她是临着‘虚无’之深渊,她才必须要紧紧地用手用身子去贴住这些具有美感的细节,但人们只看见这些细节。”[2]因此,张爱玲的小说表现出的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及对自身价值的追索是明显的,这种探寻的本身就构成了其与外在世界的张力,即“生存性焦虑”。
一、《倾城之恋》中的生存焦虑与逃离
在这里,生存成为了一种不可逃离的压力,压力来自于外在环境本身的严峻与内在精神超越之间的矛盾。这里展现的是小人物日常性的、琐碎的、略带病态的、不完整的生活,强加在生存压力本身生存条件的匮乏,让他们疲于应付现实生计,整个精神空间都被挤压掉,被实在的生存景象所填充。张爱玲的小说总是在灰暗、腐朽、拥挤、肮脏、单调、无聊的环境中展开生存性的斗争,这里不存在亲情的温暖,兄妹、母子之间的温情,有的只是赤裸裸地为了各自活得更好的、排他性的生存斗争。晦暗的环境就像人心一样逼仄,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敌意,冷漠与无聊的灰色话语,带给读者更多人性的丑陋扭曲与精神上的压力。“恍惚又是多年前,她还是十来岁的时候,看了戏出来,在倾盆大雨中和家里人挤散了。她独自站在人行道上,瞪着眼看人,人也瞪着眼看她,隔着雨淋淋的车窗,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罩——无数的陌生人。”[3]这里的人物都是不完整的、残缺的,这里没有英雄与完美主义者,虽是故事,却更加关注人生与生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性。作者正是通过这种不动声色地展示冷静客观的现实矛盾来引发读者对社会及人生的思考。评议权与思考权亦从作者转移到了读者身上,这大概就算是中国式的《娜拉》吧。
张爱玲更多地关注生活本身,而且只关注眼皮底下的一点生活。文学作品中对生活进行艺术化的修饰与包装,在她这里是不存在的,甚至在客观上是已经被消解了的。她所追寻的不是人生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而是向人们客观地、原生态地呈现生活的本真面目。这里的环境是黑暗、逼仄、压迫性的,将人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最低,使人物的生存本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激发。所以,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总是充满功利性的算计、市侩气,甚至是发霉的。张爱玲用冰冷、犀利又带有部分中国古典韵味的语言将笼罩在人性表面伪善的面纱一层层撕下。
小说写乱世男女之情,战争退为背景成了作家写人的一种生存境遇。在这里,经济利益是在场者,爱情是不在场的,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旨在求生存。“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4],病态的社会培植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毁灭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同样没有深刻的反应……这里,女性在逃离家庭、对世界进行否定后,走向的却是虚无,这一点正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小说在苍凉的二胡声中展开,形成一种典型的“中国情调”,最后在二胡声中结束,前呼后应,浑然一体,给人以艺术的整体美。
二、《倾城之恋》生存焦虑之后现代意识
我们知道,对生存本相的展示应该是左拉文学中自然主义重视的存在主义情绪。“这里所定位的文化品格,是建构于后现代话语与思考之上的”[5],张爱玲关注的是日常性生活,同时以女性意识和文化感受建构起作品的基本框架,在客观上决定了其在价值选择、文化内涵、生存意识上可以实现与后现代文化的沟通与对话。
张爱玲认为生活中不存在形而上的精神超越。所以她一直以敏感的神经、细腻的笔触去开掘生活细节的真实,同时剥离以往作品中作者刻意强加在残酷现实生活身上的五彩光环与华丽外衣,冷静而客观地展示生存本身的残酷性,这与其个人的生存经验与价值体系密切相关。传统与现代的文化错位,父爱、母爱的缺失让张爱玲选择了逃离家庭,战争又让她感到虚幻,这是其创作之前的全部生存经验,周围的外在环境让她感到无奈窒息。因此她对外在世界的情绪是否定的、不信任的,而正是这种虚无性的感受成为了其作品中最基本的文化元素,也促使其在潜意识中生发了对待生活与人生的游戏的态度。“不可否认张爱玲是个追求世俗意味很深的人,她自己也承认,她爱西方的小报,和毛姆,张恨水等人的小说”[6];张爱玲是这场戏剧的主角,亦是唯一的观众,自导自演,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以此来彰显与定位自身的价值。就如柳原对流苏所说的一样,他感觉流苏的举止就像是在唱戏,这也是张爱玲对自身情感的外在投射。可在否定外在世界真实性的前提下,依旧希望借助世俗的生活填满精神的虚无,本身就是“西西弗斯式”的工作。这就决定了其作品中的人物不是文明的承载者,更不是政治的传声筒,他们的生活与故事不是被作者抽象化提升之后的集体性记忆、意志的代表,而是私人化的、个体性的、独立的生存个体的生命体验与辛酸。在此之前,这些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是被所谓的文明与强力意志的主流文化所遮蔽甚至是刻意屏蔽的。
张爱玲所写的是自身的生存体验,她笔下的人物的生存环境是狭小逼仄的,亲情是淡薄的,人的全部价值都显现出对生存或繁殖本身的选择与认同,且人物是生成于旧的原有的文化空间之内的,因此这些人物所选择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父权社会的逃离,并试图建立私人化的价值体系,这使得故事的发生显现在历史的文化空间内,表现出浓重的历史纵深感。她作品中的心理与观众期望在作品中应该完成的,与在现实中无法达成的理想及完美,产生激烈的冲突,使人在阅读后产生灵魂的震荡,甚至撕裂所有对生存本身抱有的幻想和期待。事实上,人是以虚妄缔造、编织着神话,然后将灵魂安放在此,现实生活中的每一次行动,都会以此为目标。超出你的期待,便是幸福,没完成你的期待,便是悲剧。二者的客观展现消解了原有的规则和秩序,让人们对现有的规则,以及价值体系产生怀疑,甚至是否定。对旧有文化的逃离与规避,不仅出于作家的价值选择,更是由人类普遍具有的生存焦虑导致的。
三、结语
总之,从生存主体与外在环境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看,时代的转型期亦是文化大变动期。新文化与旧文化在创作主体意识中的对抗、纠缠,导致创作主体重新进行价值选择,建构新的价值观。这表现在现实层面上便是生存性的焦虑,逃离本身象征着对旧有文化的扬弃,而作品中人物的命运与读者对文本期待构成的落差,正是这些作品的价值所在。
[1][2][5]陈晖.张爱玲与现代主义[M].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4.46.85.52.
[3][4]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40.42.
[6]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39.
【责任编辑:王崇】
I207.42
A
1673-7725(2017)09-0053-03
2017-07-05
杨磊(1994-),男,黑龙江绥化人,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