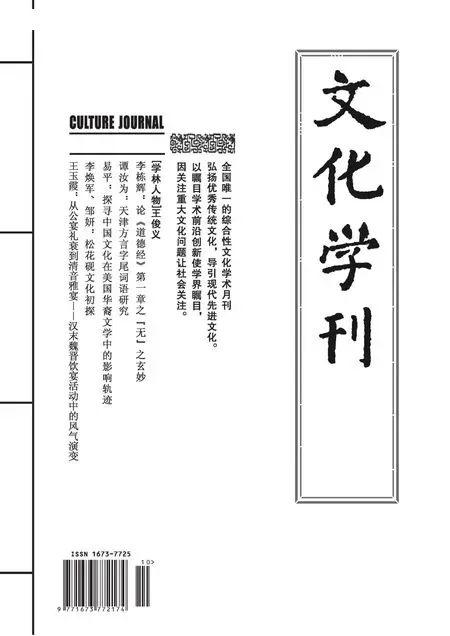翻译社会学视角下《牡丹亭》汪榕培译本研究
朱梅林
(太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责任编辑:王崇】
【语言与文化】
翻译社会学视角下
《牡丹亭》汪榕培译本研究
朱梅林
(太原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翻译学研究在经历了各个时期的转向发展后,回归社会研究是其必然的发展方向。本文借助社会学中的部分理论,如“场域”“资本”“惯习”等,研究译本,将译者及译本置于社会环境中进行全面的分析,为译本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与手段,也为翻译学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翻译社会学;场域;资本;惯习
翻译作为一门跨文化交际的学科,在社会文化交流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其社会性进行研究意义重大。翻译社会学是一门把翻译置于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新兴学科,旨在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翻译现象,把一些社会学中的术语,如“场域”“惯习”“资本”“幻想”等运用于翻译研究过程,通过解读译本中的社会文化信息,并对译者行为进行分析,为译本研究提供新的角度与手段,同时也开拓了翻译学的研究领域。
一、翻译社会学的基本理论
翻译学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与变更,成功摆脱了分支及下属学科的地位,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研究与实践学科,形成了符合自身发展的理论体系。只不过由于理论研究开始的时间较晚,使得翻译在成为独立学科之后的许多年都围绕着“直译”“异议”“归化”“异化”等传统问题进行争论。同时,早期的翻译作品与翻译研究侧重于外国文化的输入,从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本土民族文学及典籍的输出,经历过“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后,站在社会角度来分析研究作品逐步成为了翻译学发展的趋势,正如武光军指出的,“翻译的宏观研究路向有愈演愈烈之势,社会是语言和文化的最大化与终极归宿;从语言到文化转向再到社会转向,这是翻译的宏观研究路向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翻译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的标志,”[1]而翻译学与社会学这两门学科的交汇融合将这一股新鲜的力量带入了翻译研究领域。
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就已开始探索翻译的社会学。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在其出版的《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提出了研究翻译社会学的构想,但这一全新的思想却未在当时引起重视。直至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翻译社会学的热潮。1999年,约翰·海伯伦(Johan Heilbron)所著的《翻译的社会学:文本翻译作为文化的世界系统》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将翻译融入了社会学的研究中。2007年,由Miehaela Wolf 和Alexandra Fukari主编的《建构翻译社会学》一书,建立了翻译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并在翻译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本文主要借助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深入研究影响译本风格的几大要素。
(一)场域
场域是具有自身独特运作法则的社会空间。[2]由此我们可知,场域是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是由社会高度分化后而产生的小的场域,并且斗争充斥着整个场域,个体在其中竞争。各种场域既相互联系,又彼此隔离。[3]
(二)惯习
作为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重要的组成成分的惯习(Habitus)是指在人的成长、家庭、工作、教育及社交等一系列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渐通过学习、吸收其所认识熟知的社会规律而产生的行为倾向和思维模式,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在社会学中,惯习和场域也是密不可分的,惯习是场域的惯习,场域是惯习的场域,两者相互依存,并相互作用产生影响。
(三)资本
资本指人们在其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及话语权是由他们在某一特定场域所拥有的资格做决定的,不同的场域所需求的资本不同。根据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资本有四种形式,分别是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其中社会资本指个体在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俗称“人脉”)和社会义务[4];文化资本是人们在长期经历的教育或职业中获得的一些文化资源,比如著作、译作、文章等;经济资本则是可以用来换取商品或服务的货币等形式;符号资本在这里特指个体在社会中享有的信誉。在各资本的运作过程中它们可以通过相互转化来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同时,Bourdieu指出,场域、惯习、资本三者的概念均是互通的,参与者在各自场域培养惯习,并以此在场域中寻找所需的资本,获取共同认可的利益。
二、《牡丹亭》汪榕培译本分析
《牡丹亭》是明代汤显祖的代表作,是中国昆曲典籍的一部重要著作,因独特的题材与唱腔,以及融合了文化、韵律、典故等经典元素而经久不衰,本文旨在运用社会翻译学理论分析著名语言学家、翻译学家汪榕培的《牡丹亭》译本。
(一)场域及资本对汪榕培翻译的影响
汪榕培先生说,“越是经典作品,译文越应该经过多次翻译。”“还有地域问题,对于同一部作品,英国人、美国人的译文又不一样”[5],这指出了场域对译文的深远影响。
汪先生在早期侧重于对英语词汇学及文学进行研究,其国学功底深厚,一直担任大连外国语大学院长,现任苏州大学特聘教授、翻译系主任,同时担任中国英汉语对比研究会典籍英译学科组负责人等。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古典名著的汉译外数量远小于外译汉的文学作品,极不利于我国文化典籍的推介与发展,基于此,汪先生身体力行,在教学工作之余,开始了漫长的典籍英译研究与翻译工作,他先后翻译了《老子》《庄子》《墨子》《诗经》《牡丹亭》《昆曲精华》等作品,这些为汪榕培先生提出各项翻译理论提供了文化资本。在汪榕培的翻译作品中,场域及文化底蕴对于本国译者的影响表现得非常明显。如:
原文:人间旧恨惊鸦去,天上新恩喜鹊来。[6]
汪榕培译:The scared crow flies away with worldly woes;
The magpie brings in bliss the king bestows.[7]
在中国,“鸦”即为“乌鸦”,是厄运的象征,古时人们相信当这种长有黑色羽毛的鸟出现时,厄运就会来临,其是不祥的征兆;“喜鹊”是一种黑白相间、拖着长长尾巴的鸟,它被认为是好运的代表,而在西方国家,这两种鸟类蕴含的意义却大不相同。“crow”在英语中指“乌鸦”,代表一种非常聪明的鸟类;而“magpie”——“喜鹊”则用来形容“有收集零碎东西癖好的人”或者“饶舌者”。文化的差异,使得两种词的隐含意义完全不同,如果译者单纯直译,不顾及其隐含意义则会造成扭曲误解。
汪先生基于其所持有的深厚的文化资本,及场域(身在中国,为中国典籍译介)所带给他的目标指向,汪先生注意到了两词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含义,因此其在翻译时附加了原有表达的含义,将原有的含义传递给了西方读者,同时,对于“天上”一词,汪先生将其对应为“King”,使异域读者更易理解和接受。
(二)汪榕培翻译惯习对译本的影响
汪榕培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词汇学家及教育家,长期从事英语教学和研究工作,其从早期对文学及词汇学的研究到后期倾力研究典籍英译的根本目的都是要使中国经典文学走出去,他认为这“对于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岂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吗?”[8]经过多年的翻译研究与实践,汪先生提出了“传神达意”的理论,认为翻译应该是“传神地达意”。其中“达意”是翻译的基本出发点,是指字词句章各个层面均能表达思想意义,同时这也是翻译中最难的一部分,也正是由于各部分的分界线不明显,才引发了翻译界的“可译”“不可译”之争。
《现代汉语词典》将“传神”定义为:“(优美的文学、艺术作品)描绘人或物,给人生动逼真的印象。”[9]在翻译层面上,“传神”不仅要求形式上对等,还要求在背景、文化、韵体、语气等多层面相对应。如:
原文:
春归恁寒峭,都来几日意懒心乔,竟妆成熏香独坐无聊。逍遥,怎刬尽助愁芳草,甚法儿点活心苗!真情强笑为谁娇?泪花儿打迸着梦魂飘。[10]
汪榕培译:
When spring departs with chilly pace,
For days I keep a weary face
And sit alone with thoughts in a race.
I’d not have peace of mind
Unless the troubled thoughts declined
And way of life gets realigned!
For him I smiled with hearty cheers;
In dreams I shed large drops of tears.[11]
在《牡丹亭》原曲中,每一句唱词的最后一个字均押“ao”韵,如“峭、乔、聊、遥、草、苗、娇、飘”,这使得曲调朗朗上口,同时也能更加突出杜丽娘情感的丰富。虽然英语也有同样使用韵律的方式,但目标语(英语)多使用头韵的语音修辞手法来体现其节奏感和韵律美,其特点是相邻词首出现相同的辅音,与中文中的末字押韵略有不同,因此如何将源语中的神韵方式及情感准确地传达给异域读者,确也成为了译者面临的一大难题。
汪先生本着“传神达意”的翻译准则,对原唱词进行了分解,并没有刻板地选取同一韵脚作为译本的韵律,而是采用了三个不同的韵脚来具体体现,分别是:“eis”“aind”“i?z”,同时避免了字对字、词对词、句对句的直译,在“达意”的基础上“传神”地展现了杜丽娘焦虑、孤寂交织的复杂心情。
三、结语
从翻译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汪榕培的译作《牡丹亭》,是站在一个更高远的角度运用资本、场域和惯习等理论,在全面综合汪先生自身的经历、其所处的学术环境对其翻译风格及理念影响的基础上,结合汪榕培先生提出的翻译理论对译本进行全方位解析,以便更全面地把握译者风格,为翻译学研究提供新鲜思路。
[1]武光军.翻译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J].外国语,2008,(1):75-76.
[2]皮埃尔·布迪厄.文化生产场[C].剑桥:政治出版社,1993.162.
[3]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论[M].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111-112.
[4]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A].哈尔西.教育:文化、经济和社会[C].牛津,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46-58.
[5][8]朱安博.“译可译,非常译”——汪榕培教授访谈录[J].山东外语教学,2013,(3):4.
[6][10]汤显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13.76.
[7][11]汪榕培.牡丹亭[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231.149-150.
[9]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4.
H315.9;I046
A
1673-7725(2017)10-0164-03
2017-08-05
朱梅林(1987-),女,山西太原人,助教,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