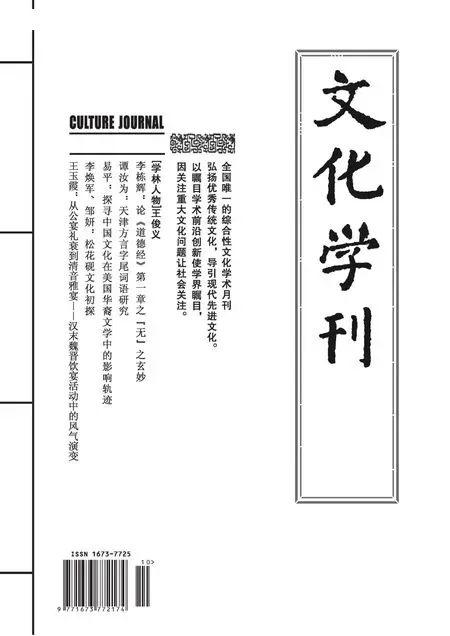“岳阳三醉”故事流变与分析
石 玉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王崇】
【文史论苑】
“岳阳三醉”故事流变与分析
石 玉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本文通过比较吕洞宾三醉岳阳故事在宋元明时期不同文本中的形态,在梳理其流变过程的基础上,探讨此故事是如何在文本体裁、时代背景等多重影响下,逐渐改变其原始面貌的。
吕洞宾;岳阳;道教;故事流变
吕洞宾约为唐末宋初的真实人物,《宋史·陈抟传》载:“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快,倾刻数百里,以为神仙。”从北宋开始其形象从一云游隐士逐步仙化,宋徽宗御封其为“妙通真人”,至南宋成为道教内丹南派的祖师之一,最终固化为通剑术、懂诗文、游戏人间的道教仙人形象[1]。可以说吕洞宾相关传说的形成和流传既有官方的因素,也有民间和宗教的因素,其文本形态亦因时而异。在各种吕祖传说中最能展现其形象特征的当属游踪故事,“岳阳三醉”是出现较早、也较为著名的一个,后世演绎的版本也较多,资料以笔记、戏曲、小说为主,历经宋元明时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现作简要梳理,以观其演变脉络。
一、宋代笔记中的原始资料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吕洞宾传神仙之法”条:
吕洞宾尝自传,岳州有石刻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举进士不第。因游华山,遇钟离,传授金丹大药之方,复遇苦竹真人,方能驱使鬼神,再遇钟离,尽获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灶,第二度赵仙姑。郭性顽钝,只与追钱延年之法。赵性灵通,随吾左右。吾惟是风清月白,神仙聚会之时,常游两浙汴京谯郡。常著白襕角带,如人间使者。右眼下有一痣,箸头大。世言吾卖墨飞剑取人头,吾闻而哂之。实有三剑,一断烦恼,二断贪嗔,三断色欲,是吾之剑也。世有传吾之术,不若传吾之神;传吾之神,不若传吾之行。反是,虽握手接武,终不成道。”
此段文字是较早关于吕洞宾和岳州渊源的记载,虽然没有复杂的情节,但因其标明为吕祖自述,后人多以此作为吕祖岳阳游踪确有其事的证据。于是后来的相关传说在仙道的神秘虚幻色彩中更增加了些许真实的意味,真中之幻、幻中之真恰恰是此类宗教传说独具魅力之处,也正是吕祖形象在演变过程中极具张力、颇为人乐道的原因所在。
关于吕洞宾游岳阳之事宋人笔记中记载最详者,以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为典型,相关的条目有二:
岳阳楼上有吕先生留题云:“朝游北越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今不见当时墨迹,但有刻石耳。先生名岩,字洞宾,河中府人,唐礼部尚书渭之孙。渭四子,温、恭、俭、让,让终海州刺史,先生海州出也。会昌中,两举进士不第,即有栖隐之志。去游庐山,遇异人授剑术,得长生不死之诀。多游湘潭鄂岳间,或卖纸墨于市,以混俗人,莫之识也。庆历中,天章阁待制滕宗谅,坐事谪守岳阳。一日有刺谒云回岩客子,京曰此吕洞宾也,变易姓名尔。召坐置酒,高谈剧饮,佯若不知者,密令画工传其状貌,既去,来日使人复召之。客舍主人曰:“先生半夜去矣。”留书以遗子京,子京视之,黙然不知所言何事也。今岳阳楼传本状貌清俊,与俗本特异 。
又同书:
白鹤老松,古木精也。李观守贺州,有道人陈某,自云一百三十六岁,因言及吕洞宾曰:近在南岳见之。吕云过岳阳日憩城南古松阴。有人自杪而下,来相揖曰:“某非山精木魅,故能识先生,幸先生哀怜。”吕因与丹一粒,赠之以诗。吕举以示陈,陈记其末云:“惟有城南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明日陈行,留之不可。后年余,李守岳阳,因访前事,果城南有老松,以问近寺僧曰:先生旧题诗寺壁久巳摧毁,但能记其诗曰:“独自行来独自坐,无限世人不识我,惟有城南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后为亭松前曰“过仙亭”,旧松枯槁,今复郁茂,得非丹饵之力邪。”
此两段文字皆记吕洞宾在岳阳游踪,而情节不相关,各自独立,已经具有了后世三醉故事的基本要素,而且传闻有据,涉及真实的历史人物,不纯为虚构之语,这是此时期的吕祖传说和后代诸多重新改写或臆造者的主要区别之一。且这种传闻不唯出于一家之言,约同时期的叶梦得《岩下放言》所载就与范致明所记前一段文字颇为近似:
余记童子时,见大父魏公自湖外罢官还道岳州,客有言洞宾事者。近岁尝过城南一居寺,题诗二首壁间而去,一云:“朝游岳鄂暮苍梧,有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其二云:“独自行时独自坐,每恨时人不识我。惟有城南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说者云寺有大古松,吕始至,无能知者,有老人自颠徐下致,故诗云。
吴曾所录石刻直署吕洞宾姓名,范致明为转录亲见吕者之言,而叶梦得的记述视角则愈远了。吕洞宾曾游岳阳之传闻其传播渠道非一,且一直未断歇,虽然都带有一点宗教的神秘色彩和奇闻异事的性质,但记录者们显然是作为真实事件来记述,没有掺入文学创作的因素[2]。这正合于笔记小说“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的创作体例。
阮阅《诗话总龟》卷四十四引《谈苑》:
张洎家居城外,有一隐士,名乃吕仙翁姓名,洎倒屣见之,索纸笔八分书七言诗一章留与洎,颇言将作鼎鼐之意。其末句云:“功成当在破瓜年。”俗以破瓜字为二八,张果参政十六年卒,乃其谶也。仙翁诗多传人间,有《自咏》云:“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
此处引《自咏》一诗与前人所录字句稍有不同,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三入岳阳”变为“三醉岳阳”,虽为一字之差,却使吕洞宾酒醉题诗、潇洒放达的剑仙形象跃然纸上,同时为后世敷衍此故事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张本。由此可见后世流传的吕洞宾故事的主要元素并不是集中出现在一个文本中,而是散见于各处,经过传闻转述,再由后人收集并加以利用,才形成了如三醉岳阳、题诗飞渡这样完整的故事文本。
二、元人戏曲的整合阶段
和宋人笔记中的零散记载不同,元代的吕祖传说已非常丰富,宗教的色彩也更为浓郁,出现了《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卷》这样汇编的专书。其卷五“游戏岳阳第六十一化”一节:
帝君游岳阳,诡名卖药。一粒千金,三日不售。乃登岳阳楼,自饵其药。忽空而立,众方骇悟,欲慕其药,帝君笑曰:“道在目前,蓬莱畦步。抚机不发,当面蹉过。”乃吟诗曰:“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
此和宋代笔记的简略笔调相去不远,但因其为宗教宣传之书,特为突出神仙显化之神异,情节仍较单一。真正形成相对成熟和丰富的文学形态的文本,是此时出现的两种“三醉”题材神道剧,一是谷子敬的《城南柳》,一是马致远的《岳阳楼》。清梁廷柟在《曲话》卷二谈到:“元人杂剧多演吕仙度世事,叠见重出,头面强半雷同。马致远之《岳阳楼》,即谷子敬之《城南柳》,不惟事迹相似,即其中关目、线索亦大同小异,彼此可以移换。”这种“可以移换”情况的出现,正是由于两剧许多情节元素都承袭自宋代笔记。如其中柳树精、梅树精为宋人笔记中所无,但和古木松精有明显关联。《纯阳帝君神化妙通纪》卷三“再度郭仙第十三化”谓“郭上鳌乃老树精后身”,可见这个人物是旧有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发展增加的产物,显示了其故事演变的延续性。
元代戏曲文本有两个特点:一是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情节和叙事结构,宋代笔记中那种分散的情节逐渐固定为较为完整系统的故事文本,这恰恰与戏曲、笔记小说两种体裁的巨大差异有关,戏曲人物要求更加丰满,情节更加完整和曲折,通过对宋人笔记相关材料的改写、合并、剪裁,吕祖游戏人间的仙人形象已得到非常丰满的刻画;二是三醉故事和度化故事的交融合流。通过比较两种剧目,我们可以发现,度化通常作为整个故事的主体,而醉酒、题诗等元素成了推动情节发展和烘托人物、渲染气氛的手段,三醉与三度在情节上相咬合,使故事结构更加紧密丰富。两种剧目除了利用以往笔记资料外,加入了一些虚构的人物和情节,文学创作的属性也趋于明显。
三、明代小说的原创阶段
明代八仙的人员和形象基本定型,吕祖崇拜更超前代。黄汝良《冰署笔谈》曾言: “三教殊门,度世则一。在佛教无如观世音,在道教无如吕纯阳,在儒教无如孔孟二夫子。”此时说部出现了许多新的吕洞宾传奇故事,很多无法在宋元资料中找到依据和痕迹,当是纯为明人臆造者。以三醉故事而言,出现较大新变化的文本是吴元泰的《东游记》。其第二十九回《三至岳阳飞度》写吕洞宾以法术使一老妪家井水变为醇酒而致富,后因其子贪得无厌而收回法术。这个情节的加入和元代两种戏曲相比较,虽然《东游记》也同样是神仙度化主题,但对象由梅柳树精变为卖油老妪,劝诫目的也变为戒除贪念,在原有的宗教色彩上加融入了更多的世俗味,对吕洞宾形象中人的一面有所凸显,联系卖油这一明代小说常出现的元素,这种转变应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
之前的三醉故事中也存在着出世与入世两种思维,如戏曲中吕洞宾在市井卖药救人及大醉等情节,显示了道教与尘世的紧密联系,而飞度洞庭又显示了无比潇洒的出尘离世的神仙风度。但是这两种思维并不显出明显的冲突来,这实际是道教个人修仙目的与世俗社会中民众对道教的实际祈求相调和的结果。南宋以后道教大都在修道观念中强调“内修”与“外用”的统一,竭力在“澄心去欲”的“出世”要求与“外积功德”的“入世”精神间获得一种平衡[3]。张伯端《悟真篇》:“志士若能修炼,何妨在市居朝”。这种宗教的二元性反映在吕洞宾这一特殊人物身上和故事文本演变中,就是真与幻、人与神元素的消长。而《东游记》更出于尘世的视角,以至在真幻人神之际使人有突兀凑泊之感。明人在三醉岳阳等吕祖故事的演绎上,已基本脱离旧有框架,而将更多的时代特征代入进去,和前代的故事文本相比,呈现出更多的原创面貌。这和小说体裁以虚构性为重要特征,以及其接受者对作品娱乐性的期待提升有直接的关系。
四、余论
中国的宗教题材故事大多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在文本改编和增删上也有很大的随意性。吕洞宾由唐末五代宋初时作为真实的人的隐士、剑侠,到宋仁宗时变成道教中的神仙,受到民间的信仰,再到徽宗时上升为 “妙道真人”,成为“仙君”“真仙”,围绕其展开的各种故事文本也随着主人公的身份变化而产生转变。早期笔记中记载的吕洞宾事迹虽然有一定的传奇性,但还不是典型的神仙故事,这应该是吕祖形象处在仙化过程的初级阶段、尚在神、人之间的缘故。各种故事文本在吕洞宾形象的发展中也起了巨大作用,甚至远远大于单纯的宗教宣传。吕仙点化凡人,脱度众生,戒绝酒色财气 ,其实是全真教义的代言人。尤其杂剧是大众传播媒介,吕仙形象借以广泛传播,而且加入了许多人情味,使其神仙形象更为丰富立体,被民间喜闻乐见,成了一个“有求必应”的万能力量,不遗余力地济度众生,甘做“地仙”。他是各阶层、各行业人共同的保护神,已不局限于道教系统内[4]。由于早期故事素材较为简略,反而具有很强的开放型,为后来的故事演变提供了足够大的空间,不同角度的声音按自己的期望和兴趣对角色和故事进行改造,人物形象的变化发展和文本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
通过梳理三醉故事的演化,我们可以看到介于真幻之间的故事比纯为虚造者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叙述者们往往从心理上愿意相信确有其人其事,在幻中寻找真。故事的早期形态真幻掺杂,而在后面的演化过程中,幻的成分在逐渐加大,最初依托的那一点真却作为必要的元素存在于故事文本流变的过程中。
[1]欧明俊.神仙吕洞宾形象的演变过程[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2.
[2]何光岳.吕洞宾与岳阳楼[J].宗教学研究,1984.
[3]苟波.从明代通俗文学中的吕洞宾形象看道教的入世精神[J].中国道教,2004.
[4]党芳莉.吕洞宾传说的早期形态及其在宋元之际的拓展[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1.
I206.2
A
1673-7725(2017)10-0182-04
2017-08-09
石玉(1981-),男,天津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