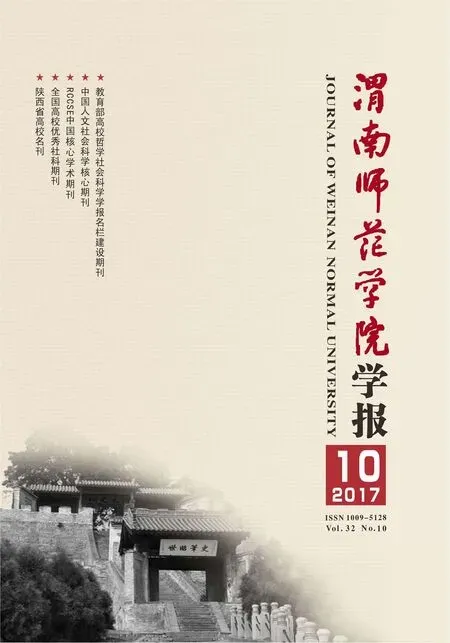论文学批评中的阶级论与结构主义
王 奎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19)
【蓓蕾园地】
论文学批评中的阶级论与结构主义
王 奎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19)
阶级论文学批评曾在特殊的历史时代被极端化歪曲,对文学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消极作用,由此很多人对之避而不谈。通过对它的发展演变进行简单的梳理,可以发现它与西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但相比当下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处境,阶级论文学批评不免备受冷落。由于20世纪中国在文学理论中的失语造成了我们在全球化以来的文学研究中话语权的缺失,要求我们努力在借鉴反思中去寻找、建构本土的理论体系。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论文学批评在新的时代应当被注入新的活力,它仍具有很大的开发空间,值得我们继续探索。
阶级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阶级论”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主流思潮,对20世纪的中国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当它被运用到文学场域中所产生的影响最为突出,无论是文学史的编写,文学理论的建构还是文学批评的实践,阶级论都曾一度成为中国社会普及最广甚至成为全国唯一的思潮。随着“文革”的结束和“解放思想”的号召,中国的思想界逐步走出了唯阶级论的时代,长期的思想禁锢致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外来思想,使得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掀起一波又一波西方的“主义”热潮。在文学活动中,许多尝试学习用西方的艺术表现手法来创作的作家被冠以了“先锋”的名号,为此许多文学批评家也不得不广泛地去涉猎西方文艺理论以适应新的文学环境,1985年之后的“重写文学史”更是开启了一次具有颠覆性的范式转变。
随着学界“语言学转型”的发生,在众多被引进的思潮中,人们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情有独钟。“1985年之后,对各种批评理论的介绍出现突发性高潮,光介绍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译著即达二十几种之多。”[1]结构主义在中国文学中主要是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方式实践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很快被许多中国学者方法论化、模式化了,用这一方法解读文学作品曾一度形成一个热潮,学界一时间涌现出大量的著作,当然其间不乏东施效颦之作,这一热潮并没有持续太久便被后结构主义抢去了风头。无论如何,这些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学研究多元化的发展。进入21世纪,学术中的学理追求有利于人们对历史与存在的客观认识,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用当下人的目光去审视已成为历史的存在时,很多问题已经变得不可理喻甚至荒诞不经,于是回到历史场域,成为许多学者阐释历史的一个前提,也有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真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去关注阶级论文学批评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时,这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会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一、阶级论文学批评的中国化
“阶级”这一概念主要来源于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阶级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产物,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现,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2]643这本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概念在后人的阐释中产生了不同的偏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致是沿着列宁的文艺理论进行实践的。[3]95阶级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似乎也成为无可辩驳的常识,于是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的阶级性也成为“文学的基本知识”。在文学中,“阶级论”作为“反映论”哲学的体现,使文学更为直接地参与到社会现实之中,与此同时,阶级论在“工具论”的基础上使文学肩负起了前所未有的重任,文学不再仅仅是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兴观群怨”的载体,而真正成为关乎国家兴亡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让文学有所担当,这与中国人的“实用理性”[4]29的传统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梁启超肇始的“文界革命”到“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再到左翼的“革命文学”的论争,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论文学观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和知识分子的论战下逐步发展成型。阶级论在中国的形成发展的过程是复杂的,其中掺杂着多种因素,同时也受到多种思想碰撞,如传统知识分子的“文以载道”关注现实的精神、进化论思想的社会化、苏俄文艺论战、拉普和纳普的传播、左翼文学思潮的论争等等,多重复杂的社会背景造就了这一特殊的文学观念,也使这一文学观念在社会变动中多次走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体系中,阶级论文学批评的发生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蒋光慈、瞿秋白、茅盾、郭沫若等人的相关论述,随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逐渐被先进的知识分子介绍到中国,以一种新的启蒙方式来促使中国“阶级的觉醒”。但是,特殊的时代背景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危机感中多了一份焦躁与狂热,可以说,阶级论从一开始传入中国时就被绝对化了。随后以太阳社、创造社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家以“阶级论”为武器对“五四”新文学给予了激烈的批判,过分的情绪化使得这种“阶级论”在中国的现代文学批评中锋芒毕露,而这种“阶级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作是十七年时期阶级论文学批评景观的一次预演。可以说阶级论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体系中从一开始便剑走偏锋。“直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阶级论的文学观终于在中国形成了自己的阐释系统,走向了成熟。”[5]于是文学家不仅仅是“阶级的耳目与喉舌”和“政治的留声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6]822,在20世纪的中国反抗外侵、独立自强的历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内思潮的左倾,“大跃进”的急切心态影响到文学批评的场域,阶级论文学批评逐渐复归了革命文学年代形成的公式化、概念化,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三突出”与“文艺黑线”等极端文艺思潮的出现,“阶级论”一步步被推向了“左”的极端。“文革”结束后,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使得长期被束缚的思想界在挣脱绳索后迸发出新的锋芒,走偏的阶级论文学批评被作为反思的对象弃之一旁,阶级论文学批评也由此逐渐成为历史,少有人问津。
阶级论文学批评最为典型的成果当属20世纪四五十年代前后的一批文学史论著,这些文学史论著大多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理论支撑,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系统性的阶级论文学批评与研究方法。在对这类文学史进行简要分析后,我们可以大致得出它们的一些共同特征,通过这些特征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阶级论文学批评可取之处与不足。首先,这类文学史的编写者都有着明晰的政治倾向性,他们都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对当时的文艺进行价值判断,使文艺成为服务政治的工具。但是也正是文艺对政治的积极参与,使得中国革命运动在千难万阻之前保持着乐观昂扬的战斗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最终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从侧面证明了文艺对于现实社会的强大驱动力。因此当我们回到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历史场域之后,这一特征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其次,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定位时,一些编写者误以“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用阶级划分的方法和政治标准第一的模式来评判作品的价值,甚至作家的出身、立场等都会成为评判其作品优劣的因素,注重艺术作品的内容而轻视甚至无视艺术作品的形式。这给整个中国文艺界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很多人批判“阶级论文学批评”的一个主要切入点,也是我们在面对阶级论时最该反思的一点。此外,阶级论文学批评中常常显示出其复杂性,它常会夹杂社会历史批评的批评方法,同时也有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影子,也渗透着一些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的因素。这与中国当时复杂的思想环境有关,迫在眉睫的危机让爱国知识分子无暇顾及太多,“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很多知识分子面对外来思潮的涌入,在学习与实践中不自觉地“博采”众多思想造就了“阶级论文学批评”的复杂性与独特性。最后,阶级论文学批评给中国之后的文艺思潮带来最深刻影响便是其隐含的直线发展历史观和二元对立走极端式的简单化思维模式。中国激烈的现代性追求中所呈现出的盲目性与危机逐渐显露出来,现实生活的困苦与直线发展的历史观下对未来的美好想象之间形成的反差引起人们的反思,才会有人感叹:“大清国不一定好啊,可是到了民国,我挨了饿!”[7]25对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批判我们还需多一些谨慎。二元对立思维模在机械阶级论盛行的时期得到了恶性发展[8],但尽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被极端化后显现出其强大的破坏力,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彻底否定它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的价值。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的合理利用的典范当属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尽管二元对立同为阶级论文学批评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但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范式却能因之而逐渐被经典化,而曾经盛极一时的阶级论文学批评却因之饱受贬斥。尽管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而且也曾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曾在思想界来势凶猛、震撼全局时所包含的科学冲动,以及它所创建的新范式对于学术研究的巨大意义。通过对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和阶级论文学批评作简单对比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还原阶级论文学批评的本来面目。
二、从结构主义思潮到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
“结构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对20世纪人文思潮的变革有着重大影响。[9]248索绪尔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语言学研究偏向了语言内部结构和语言符号系统,他将日常语言作为其研究的对象,将言语活动分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语言和言语构成了二元对立。这一研究方法影响俄国形式主义,雅各布森和巴赫金受其启发并对它进行了批评与补充。1926年雅各布森将索绪尔的研究方法带到捷克,影响了布拉格学派并使之成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流派之一,之后雅各布森又将火种传给了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这一思潮由此深刻影响了法国,并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结构主义”的热潮,它逐渐被作为一种方法论不断地渗入其他学科,甚至成为当时学术研究中的万能理论。伴随着结构主义在法国的盛行,一大批法国学者诸如拉康、罗兰·巴特、阿尔都塞、托多洛夫等在这片沃土中获取了累累硕果。在罗兰·巴特、格雷马斯、托多洛夫等人的研究中,结构主义被成功地运用于文学领域,产生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批评、语言学结构主义文本分析等研究范式。罗兰·巴特在其《符号学原理》中认为,“概念的二元分类法似乎往往存在于结构的思想中,好像语言学家的元语言‘在深层’复制着它所描述的系统的二元结构。……研究当代人文科学话语中二元分类的突出作用,无疑是极富教益的。”[10]115之后他又在《写作的零度》和《文艺批评文集》中强调文学的语言与写作,文学的语言与言语的二元对立。此外,在格雷马斯多部著作中,都是以二元对立的结构主义分析为其理论基础,包括他所提出的“符号矩阵”也是以二元对立原则为基础而构建的。二元对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很多学者在多个领域广泛运用,并产生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伊万诺夫为二元对立的研究方法及其在研究中广泛运用的合理性找到了生理基础,认为这种普遍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与人类大脑中的二极制有着紧密的关系。[11]592但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中,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要素,对文学文本“结构”的关注才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作为抽象名词,结构主义与结构密切相关,它代表一种新式哲学眼光,或称观察事物的优越角度。”[9]252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具体操作中,既有宏观认识也有微观分析,批评家大多是从语言或叙事结构入手将本来复杂烦冗的对象进行细致的拆解、归类和组合,通过对文本的外部结构分析来探究其深层意义,发现其后隐藏的“符号阵列和音乐总谱”,二元对立仅仅是其文本分析程序中的一个环节,它最终指向的是文本的整体深层意义,力图透过表象的迷雾去指出本质。如托多洛夫通过对《十日谈》语句排列探讨而得出其基本叙述结构;普洛普通过对俄国民间故事进行系统的分析比较,从而归纳出民间故事中人物的31种功能;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通过对恋爱的不同表达方式的分析得出爱情在文本中最合理的表达;列维·斯特劳斯以历时与共时的视角将古希腊俄狄浦斯神话的故事成分排列成四个纵行,呈现出两组矛盾关系,从而找出了俄狄浦斯神话的深层意义。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成果斐然的同时,作为一种思潮的结构主义也遭遇到了危机。
尽管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对科学方法的模仿,但它能否算得上一场真正的科学革命,引起很多学者的质疑。此外,结构主义迅速被推广到许多学科领域,一时成为广泛适用的万能钥匙,但是结构主义并不具有普适性,在各式各样的研究对象面前,结构主义终没能形成一套统一的方法论体系,对这一研究方法的滥用甚至造成拆解有余而重构不足的尴尬,显现出其强烈的破坏力。而这一点索绪尔也有过思考,尽管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能从语言学中扩展到其他领域,但是“没有一个研究课题,能像语言学这样滋生出如此多荒唐观念、固执偏见和奇思异想”[12]386。针对结构主义所显露的种种问题,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鲁兹等一批学者对这一思潮进行反思与革新,后结构主义便悄然兴起绵延至今。对于结构主义的式微许多学者作出了不同的回应,同时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也仍在继续,但是结构主义在文学中的运用所形成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却得到了多数人的肯定。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在“主义”走马灯的时代,在阶级论备受质疑的年代,以二元对立为核心研究方法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文学评论界一闪而过,相反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反而掀起了相对大的波澜,对中国新一代的学者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见出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与阶级论文学批评之间的隐秘关系。
三、阶级论文学批评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
通过简单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阶级论文学批评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之间有很多的相似与不同。首先,二者在最初都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学批评而存在的,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曾具有社会思潮的性质。阶级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阶级观念为其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强调着阶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关键所在,在苏俄革命的实践中阶级的概念延伸到了文学,强调“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13]5。在中国,特殊的时代背景同样促成了“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6]822。由于政治家的倡导,阶级论逐渐成为文学发展的指导方针,并在实践中逐渐发展成为一套较为成熟的文学批评体系。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同样也经历了由社会思潮向文学批评的转变,结构主义虽然最初是索绪尔在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中所倡导的一种研究方法,但是经历了由莫斯科、布拉格再到巴黎的薪火传递,结构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可以涉足许多学科的社会思潮,到最后甚至成为无所不能的万能公式,这与阶级论的泛化极为相似,而这也是导致它们走向误区的共同因素之一。不同的是,阶级论不光牵涉到文学批评,更直接指导了文学创作,这些文学作品由此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成为那一段历史中最为独特的风景。尽管结构主义有着关涉多种学科的雄心,但最终却没有直接影响到文学创作。在这里衍生出的另一个问题便是,文学理论到底能否直接作用于创作主体,为文学创作作指导?这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思考探究。
其次,阶级论文学批评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中都有二元对立的分析方法,将复杂的问题进行简化,通过二元对立的划分突出研究对象包含的内在矛盾,能让很多问题一目了然,这样也有利于批评者从中得出结论。“‘二元对立’作为一种辩证思维则是一种主智思维,它在人类的生存与发现过程中不断地发展真理、不断地创造智慧、不断地探究学问,直至当今仍是一种具有创造活力的思维方式。”[14]257但是在阶级论文学批评中,二元对立分析法具有简单化的倾向,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后就没有再去回归系统,是由复杂向简单的单线性思路。在当时的中国,革命者为组织革命队伍,鼓动农民参与到革命斗争中来,需要这样将本来属于知识精英书本中形而上的理论化为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因此文学作品担任图解政治的任务也情有可原,这也是中国现实革命的需要,但是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一旦成为一种思维定式,走向极端化后,它便成为一种非此即彼的极端对立思维,这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一个“非智因素”。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中,二元对立作为其批评系统中的一环,能很好地理清复杂文本中的逻辑关系,它最后的目的是为探求文本中的复杂性。“结构分析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简单的关系,即:二元对立。”[15]98-99但是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中“‘二元对立’这个概念,不是只讲对立,同时也讲依存”[14]257。在某种程度上,这里的“二元对立”与马克思主义中的“对立统一”有很大的契合点。法国的知识精英在对结构主义的探究与论争中有着相对平和的论争环境,因此,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要比阶级论文学批评有更加学理的倾向。二者虽说都运用了二元对立分析法,都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但在具体操作中是不同的。阶级论中的“二元对立”逐渐在政治环境和当时的社会情绪的干扰下走向了极端,在论争中并没有走向辩证否定,造成了概念化、模式化的错误,甚至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成为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之激烈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之后的批判反思中它也没能继续发展,而是被直接打入了“冷宫”。而结构主义在法国的论争中虽也暴露出其弊端并走向式微,但是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并没有因此而被彻底否定,反而产生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批评家和著作,这些著作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后人视为经典。
此外,阶级论文学批评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都曾盛行一时,拥有广泛的追随者,都可以作为中西两个文化场域下文学批评范式的典型代表。它们的差异也可以代表中西方文学批评整体的差异。通过对这两种批评范式的简要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它们最大的差异之一是其关注焦点的不同。阶级论文学批评关注的是文学作品的内容,忽略或无视文学作品的形式;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虽然也关涉到了文学作品的内容,但它更偏重的是文学作品的形式。中国的阶级论文学批评受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创作,都是在对苏联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模式的学习过程中承接过来的,作为政治的附庸,文学自然也都带上苏联模式的印记。“重视艺术形式的研究是西方20世纪文艺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向”,其成果我们有目共睹,“然而,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学研究中,恰恰忽略或反对研究这方面的问题”[3]35。结构主义自索绪尔在语言学的实践运用后,被雅各布森借鉴而影响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建构,托洛茨基一方面指出“在苏维埃俄罗斯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一学说,是形式派的艺术学说”[16]214,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形式主义能直指诗歌的特质,这一点被认为是“必须的而且有用处”[3]36。但是在斯大林时期,俄国形式主义被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被彻底否定,这种有着情绪化的否定也被直接挪移到了中国,结构主义甚至曾一直被认定为是资本主义的“毒草”,成为无人涉足的禁区。20世纪80年代后的思想大解放为我们的文学研究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也为我们深入反思失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研究范式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以上的论述仅仅是对阶级论文学批评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简要分析比较,这二者的差异还有很多方面有待我们去深入探讨。
四、结语
通过以上几方面的对比,我么可以得出很多启示。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阶级论有其合理之处,促使阶级论文学批评走向误区的是人们对它的过分迷信,简单地将一种社会思潮方法论化,使之成为分析、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法宝。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是一劳永逸的,阶级论并没能像结构主义一样在知识精英的论辩中实现自我否定,也没能在后来者发现其弊端后得到很好的纠正,而是逐渐变成历史。在文学研究中,由于文学革命的激烈改革使得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呈现出鲜明的断裂,也造成了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之间的断裂,古代文论难以适用于现代文学形式的变化,被许多批评家冠以“不成体系”的名号而被弃之不用。这也造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得不借鉴西方文论,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涌入了大量的西方思想,许多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逐渐被中国学者运用到了中国文学的研究之中,甚至已经造成一种理论依赖。与此同时,许多学者不禁痛惜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理论建构中的失语,在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没有建构一套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甚至没有一个理论关键词能载入史册,就连被最广泛运用的阶级论也是在苏俄文艺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我们急需一套本土的理论体系来建立在文学研究中的话语权。阶级论文学批评虽然是一个舶来品,但在几代文学研究前辈的努力中它具有了极强的中国特色,因此,我们不该将之完全否定,而是在继承其精华的同时进行改造创新,使之更具说服力。此外,在对阶级论和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对比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可以说阶级论文学批评的误区与中国特殊的文学批评生态与批评伦理有很大关系,政治化的倾向使很多争鸣变成扣帽子,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有时甚至会有个人攻击。尽管文学无法斩断与政治的联系,但是文学也应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阶级论文学批评被广泛地融入20世纪后半阶段的文学史中,许多文学史编写者在著史时尚未有明确的意识去区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文学史应当注重的是学理的追求和史料的全面,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面貌,而文学批评则应追求的是个性的表达和思想的独特性。在文学研究中,20世纪是理论集中爆发的世纪,但是在中国的社会历史中,20世纪是中国人民反抗外侵争取独立、解放和民主的世纪,对于那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我们也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到21世纪,中国已然傲立世界大国之林,为文学研究提供了空前优越的环境,中国的文学研究也必将在新的时代中开辟一片新天地。
[1] 严峰.结构主义在中国[J].上海文论,1992,(7):139-148.
[2] 冯契.哲学大辞典(上)[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
[3] 李衍柱.时代变革与范式转换[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4]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 王瑜.现代文学史观及其书写实践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7] 老舍.茶馆[M].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8] 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三十年[J].文学评论,2008,(4):8-11.
[9] 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10] [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11]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2] 赵一凡.西方文论讲稿:从胡塞尔到德里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13] [苏]列宁.列宁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4] 朱德发.朱德发文集5[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15] 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16] [苏]托洛斯基.文学与革命[M].刘文飞,张捷和,译.北京:未名社,1928.
【责任编辑 曹 静】
The Criticism Method of Class Theory and Structuralism
WANG Ku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The criticism method of class theory is the main achievement of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But it has been misunderstood for a long time and also has made serious negative impact on Chinese literary study, many researchers avoid revealing anything about it. There is much comparability between class theory and structuralism, but structuralism has a better situation than class theory in China now. China has not get much say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theory, so we have to rethink profoundly and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our own words in literary theory. The criticism method of class theory with a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hould be infused new energy in the new era and there is still great space to explore.
class theory; structuralism;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I0-03
A
1009-5128(2017)10-0085-06
2017-04-25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11&ZD113)
王奎(1992—),男,陕西清涧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