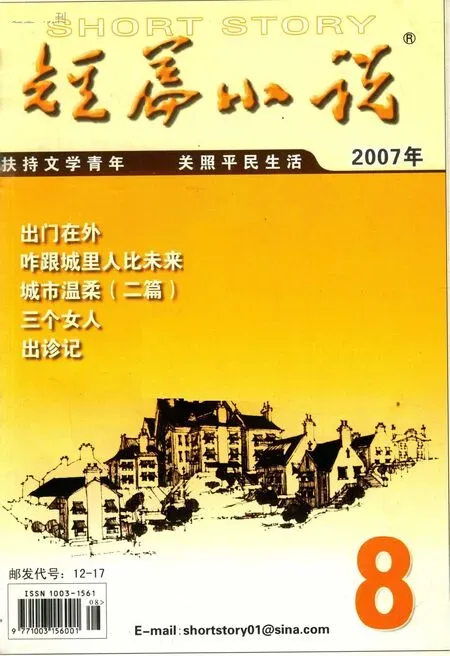嘱托
◎王 刚
嘱托
◎王 刚
人老骨头硬,越老越展劲。屁话,哄鬼,等你们到我这把年纪,七老八十,老胳膊老腿,看你们还会不会这样说?树老心空,人老颠东。人老了,就成了一截朽木,记性被狗吃了。可惜我一生的传奇故事,像装在破袋子里的豆子,边走边漏,几乎全被丢光了。如今,只有一个与我小时玩伴大傻有关的故事,我还能清清楚楚地记起来。
几十年前,我刚三十出头,正是啥都能干的时候。那时候,我强壮得像头蛮牛。不是吹,遇上那些疯颠颠的女人,我一把就能抓过来,像老鹰叼小鸡,把她们收拾得服服帖帖。你们这些小年轻,动不动肾虚,吃伟哥,银样蜡枪头,没出息。
几十年前的一个晚上,我背着沉重的包裹,走到了花嘎村乌都河边。那时候,已是深夜十二点左右,一轮孤零零的月亮高悬头顶,像一只苍茫遥远的狗眼。月光下,花嘎村面目模糊,影影绰绰。那真是一个奇怪的夜晚,狗不叫,虫不鸣,死一般寂静。
乌都河上,有一座年久失修的石桥。月光下,可以看见桥身爬满了枯死的藤子,有点像爬山虎。只要过了桥,就进入了花嘎村的地盘。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蜗牛一样向桥上爬。我累了,腰酸腿疼,吐气如牛。能不累吗?走了那么长的泥巴路。如果是你们,肯定累成一摊烂泥。也许,你们会说,你这老不死的,吹牛不打草稿,谁叫你走路?你为啥不坐车?铁公鸡,怕花钱。后生们,留点口德,你们是含着糖长大的,怎么知道老辈人的苦。那时候,从水城到花嘎,别说车路,鸟路也没有,坐个球的车。没办法,只得用脚板量,老老实实地走。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地爬。说出来吓死你们,从水城到花嘎,翻山过河,至少要走三天。三天,不是一天,你们能走吗?能走个屁,你们的大腿像麻杆,走几步就会喊爹叫娘。
那时候,花嘎穷,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从记事起,我就没吃过饱饭,只能混个半饱。树挪死,人挪活,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十八岁那年,老子一咬牙,吃了秤砣铁了心,背着背包出了门。我憋足劲,像一头蛮牯牛,在外面闯荡了十几年。不是吹牛,我啥没经历过?见过红的黑的白的绿的黄的,惹过圆的方的横的不怕死的,吃过酸的苦的辣的咸的,流过泪流过汗流过血。说句不夸张的话,我过的桥,比你们走的路多;我吃的盐巴,比你们吃的饭多。应该说,我的运气不错,打拼了十几年,总算挣到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摸着沉甸甸的钱袋,我忽然产生了不可抑止的思家之情。我当即决定,带着我的钱,回花嘎,修房子,娶老婆,生儿子,孝顺父母,落叶归根。
那天晚上,我气喘吁吁地爬上石桥,打算在桥凳上歇歇脚。忽然来了一阵冷风,云彩散开,一轮月亮高悬头顶,像一面大大的镜子。那个夜晚忽然变得很明亮,有点诡异。月光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不远处的坟山。坟山上,排列着大大小小的坟堆。每一个坟堆里埋着一个人,每个坟堆里住着一只鬼。老人们说,人有人间,鬼有鬼界。每到半夜,坟里的鬼就会像人一样,推开墓门,走到月光下。据说,鬼们行走在月光中,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哭哭叫叫。有的伸着长舌头,有的提着上吊的绳子,有的把血红的心捧在手里,有的目光如炬,有的头大如斗,有的瘦骨嶙峋,有的胖如西瓜……想着想着,我觉得背脊发凉,像无数的小蛇缓缓爬过。
一阵风吹来,我打了个寒颤。掏出一支烟,吃了一口,将心一横,打算休息几分钟再走。我实在太累了,骨头都快散架了,像一摊摔散的豆腐。坐在石桥凳上,心想,要是遇上个熟人就好了。
有句老话说得好,瞌睡来遇上枕头。我刚吸了半支烟,忽然看见桥那头走了一个黑影。那黑影很黑,就像全身刷过黑漆。干瘦修长,如同一根瘦骨嶙峋的竹竿。他边走边咳嗽,摇摇晃晃地向我走来。我一惊,从腰间拔出匕首,壮着胆子喝问:是谁?再不说话,老子要动刀子了。
那黑影愣了一下,大声喊道,是马军哥吗?我是大傻啊。
大傻?原来是大傻啊!
大傻是我的好伙伴,好兄弟。我没离开老家时,大傻顶着傻乎乎的大脑袋,挂着两条长长的鼻涕龙,像头傻驴,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屁颠屁颠地跑着。那时候,我们天天泡在一起,掏鸟蛋、捉野兔、捞鱼、打柴、割草、放牛、捉迷藏……村里的老人说,大傻就是我的影子,我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
我乐了,喊道:大傻,吓老子一跳,过来抽烟。
我抽出一支烟,弹给大傻。大傻伸出手,鸡啄米一般,把烟抓到手里。我又弹出一支烟,叼在嘴里。哗啦一声,大傻划燃一根火柴,凑过来,帮我点上了烟。借着火光,我发现大傻的手指又黑又瘦,像被火烧过的枯树枝。
此时,月光正好。大傻变魔术似的,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支水烟筒,把纸烟装在烟嘴上,对着烟筒咕咚地吸了一口。你们肯定不知道水烟筒长啥样?那时候的花嘎,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支水烟筒。砍半截竹子,将其关节打通,从半腰处打一个小孔,装上小半截烟嘴,往竹筒里装上半筒水,一支水烟筒就做成了。吸水烟筒,那可是花嘎人的享受,带劲,烟大,过瘾。花嘎的男人,几乎每人都有一支水烟筒。吹牛聊天的时候,每个人都抱着一支,如同抱着一个女人,咕咚咕咚的声音响个不停。
我一把夺过大傻的烟筒,狠狠吸了一口,说,妈的,还是这家伙过瘾。
我和大傻坐在桥凳上,吸着烟,不停地朝天空吐烟圈。
看着身边黑黑瘦瘦的大傻,我忽然想起了多年之前的那个早晨。天空下着小雨,花嘎村湿淋淋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鱼。大傻提着一支水烟筒,肩上背着我的背包,跟着我走出村口。一条黄狗跟在我们后面,摇摆着尾巴,汪汪汪地乱叫。大傻踢了狗一脚,骂道,狗日的,滚。狗叫着跑远了,我们哈哈大笑。走到桥上,雨居然停了,太阳从灰蒙蒙的天空中钻出来,像一个鸡蛋黄。我们坐在石凳上,打算休息一会。大傻掏出一盒烟(那是他用一只大公鸡换来的),笨拙地撕开烟盒,抽出一支,装进烟筒的烟嘴,点燃,递给我,说:军哥,吸一口吧,带劲。那天早晨,我们坐在桥上,一口一口地朝天空吐烟圈。吸了烟,我把背包甩到背上,说:大傻,我走了。大傻追上来,把剩下的烟塞到我手中:军哥,走吧,别忘了兄弟。
一晃眼,十几年就过去了。没想到,我回花嘎的那个晚上,居然在桥上遇上了我的好兄弟---大傻。我们吸着烟,说着话,就像多年前那样。
吸了烟,大傻把我的背包抢过去,甩到瘦削的肩上,迈开大步,走在前面。我提着他那支长长的烟筒,跟在后面,向村庄走去。
天空中飘来一团乌云,一张口就把月亮吞进肚里。天空暗淡下来,朦胧的月光中,我们行走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晃晃悠悠,像两只野鬼。田间地头那些唠唠叨叨的虫子,似乎已经熟睡,没有一点动静。小路两边,是一片片影影绰绰的玉米地,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远处,高耸着几座面目模糊的大山,时不时传来几声夜鸹子的惨叫。
大傻背着包,快步行走在前面。小路时隐时现,凸凹不平,但大傻却如履平地。我跟在他的身后,感觉他黑漆漆的背影轻飘飘的,仿若一团乌云,从茅草上飘过,寂然无声。整条路上,只响着我一个人的脚步声,踢踢踏踏,踏踏踢踢。
一路上,我们几乎没有说话。大傻走得快,像风一样。我跟得吃力,哪有力气废话?我感到诧异极了,这大傻,瘦得像竹竿,顶着个大脑袋,背着那么重的东西,竟然走得那样快。
大概走了几十分钟,我们进入了花嘎村。走到岔路口的时候,大傻站住了。往左走,是大傻家。往右走,是我家。大傻转过身子,对着我。我看不清他的面目,只感觉面前是黑漆漆的一团。大傻将背包放到我肩上,说:军哥,太晚了,我就不叫你去我家了,我们各走各的吧。
村庄很安静,一点声响也没有,死了似的。确实太晚了,我握了握大傻枯枝般的手,说:兄弟,今晚多亏了你,明日再来找你喝酒。
我站在路口那棵大树下,半边弯月亮挂在树梢上。大傻低着头,不说话,也不离开。我喊道:大傻,走吧。大傻忽然向前走了一步,说:军哥,求你帮我一个忙。
我笑了:大傻,谁跟谁啊,我们两兄弟,还用这样客气?是不是没钱了,哥借你。
大傻摇摇头。他站在树荫下,黑漆漆的,像一棵被雷击过的树桩。
大傻忽然向前迈了一步,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军哥,我有个儿子,叫根生,今年八岁。根生很聪明,可惜我很傻,很无用。如果有一天,我不能照管他了,你一定要帮我,把他当你的儿子。
大傻的手指抓进我的肉里,又冷又硬,像铁钩子。我忍着痛,说:大傻,别说傻话。
大傻执拗地说:军哥,你答应我,你要把根生当儿子。
我说:好的,大傻,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
大傻笑了,他松开我的手,说:军哥,明天来我家喝酒。
大傻忽然转过身,他的身影像一朵黑云,一下就飘远了。
大傻走后,我才发现,他的水烟筒还在我的手里。
回到家,父母不停地埋怨我,说我胆子太大了,深更半夜的,怎么敢一个人走夜路。如果遇上不干净的东西,该怎么办?如果遇上强盗土匪,该怎么办?尤其是母亲,一边给我下面,一边絮絮叨叨到讲述着村里人遇鬼的故事。父亲坐在一旁,咕噜咕噜地吸着水烟筒,时不时补充几句,证明母亲说的事情并非胡编乱造。我一边胡乱答应着,一边掏了一支烟,装在大傻给我的那支水烟筒上。父亲的眼睛一下子变直了,他问我:你的烟筒是从哪里拿来的?
我吸了一口烟,笑嘻嘻地说,走到村口时,遇上一只鬼,它手里提着这支烟筒,我吓唬它,它丢下烟筒,跑了。我就把烟筒捡回来了,没想到,还挺好用的。
父亲说,别废话,从哪里拿来的?
我说:大傻给我的啊,我在村口遇上他了,他还帮我背背包呢。
父亲的烟筒啪的一声掉到地上,母亲端碗的手忽然停在空中。他们盯着我,像看一个怪物,眼里露出了恐惧不安的神色。
我诧异地看着他们。好半天,父亲这才结结巴巴地说:放下,放下,别碰它。
母亲哇地一声哭了:儿,你知道吗,大傻已经死了两天了。
这一次,轮到我呆若木鸡了。
父亲点燃一支烟,把他的水烟筒递给我,说:抽吧,想抽,就好好抽一筒。
母亲红着眼说:唉,大傻这孩子,死得真惨啊。
那天晚上,父亲,母亲和我,围坐在火塘边,一夜未眠。守着柴火,父亲吸着水烟筒,给我讲述了大傻这些年以来的遭遇。
八年前,大傻娶了老刘家的女儿翠花。翠花长得丰乳肥臀,是块好地,才嫁给大傻一年,就生下了儿子根生。大傻得意极了,他挺着高高的头颅,像一头长颈鹿,从村东跑到村西,从村南跑到村北。谁曾想到,好景不长,造化弄人。根生一岁的时候,翠花被鬼附身,全身浮肿,疯疯癫癫。大傻砸锅卖铁,带着翠花到处寻医。钱花光了,欠下一屁股债务,人却没了。翠花死的时候,全身肿大,像一个胖胖的气球,恐怖极了。
翠花走后,大傻又当爹又当娘,日子过得紧巴巴,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年后,经人介绍,大傻娶了西村的胡寡妇。胡寡妇无儿无女,长得像只癞蛤蟆,满脸是蚕豆大小的痘痘。有句话说得好,丑人作怪。这胡寡妇,对人笑口常开,满脸春风。暗地里,她的心里却盘着一条毒蛇。当着大傻的面,她对根生有说有笑,给他吃好的,穿好的,喝好的。背着大傻的时候,她就百般折磨根生,拿他当出气筒。胡寡妇最毒的一招,就是用绣花针刺根生的屁股。针眼小,不容易发现,伤不了筋骨,但却疼痛钻心。她威胁根生,不准哭,不准说,不准闹。她还说,如果根生敢乱嚼舌头,她就毒死他。根生只是个几岁的娃娃,被她吓坏了,整天惶恐不安,像只小兔子。后来,有人提醒大傻,叫他多留个心眼。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大傻脱掉根生的裤子,查看他的屁股。明亮的阳光中,大傻看见了屁股上密密麻麻的针眼,像一只只小小的眼睛。大傻狠狠揍了胡寡妇,揍得她跪地求饶,哭爹喊娘。
从那以后,胡寡妇再也不敢打根生了。她对根生百般讨好,呵护有加。人们都说,胡寡妇痛改前非了。大傻家的生活,似乎走上了正轨。
谁能料到,一年前,大傻却病了。他越来越黑,像一块煤;越来越瘦,像一根竹竿。平时能吃能喝的大傻,竟然连半碗饭都吃不完,喝一口水都要喘半天气。有人说,大傻中了“干痨鬼”。这种鬼无迹可寻,钻进人体里,喝血吸髓,铁打的汉子也经不住折腾。被这种鬼缠身的人,没得选择,只有死路一条。没过几个月,大傻就成了一截枯干的木头。以往风风火火的大傻,只能软塌塌地躺在床上,竟然连迈出大门的力气都没有了。
那胡寡妇不过四十岁,正是如狼似虎的年龄。她见大傻不中用了,就背着大傻,和村东的马屠夫睡到了一起。
大傻连气带病,身体如山崩,一下就垮了。他躺在床上,苦苦支撑了几个月,瘦成了一把骨头。他死的时候,眼睛圆瞪,凶巴巴的,谁见了谁被吓一跳。人们都说,大傻是凶死,他走得不甘心。人们还说,凶死的人会变成厉鬼,谁撞上谁倒霉。
大傻死后,胡寡妇又哭又叫,给大傻操办丧事,要让大傻走得风风光光。谁都看得出,这个女人是做给村人看。大傻死后,最高兴的莫过于她了,她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和屠夫睡到一起了。
父亲讲完大傻的事情,吸了口烟,盯着窗外发白的天空,叹了一口气。
母亲说:我儿,你累了,上床眯会儿吧。
我说:不睡了,天快亮了。
父亲说:对,不睡了,天马上亮了,你去大傻家看看,送大傻最后一程。
父亲顿了顿,又说:记住,答应大傻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父亲加强语气,又说:把根生带过来。
鸡叫过之后,天就亮了。我抹了把脸,提着大傻的水烟筒,和父母招呼了一声,径直奔大傻家而去。
大傻的房屋破破烂烂,就像一堆废墟。房屋前的空地上,栽了一棵竹子,上面挂着一束巨大的招魂幡。早晨的风吹来,有点冷,有点凉。招魂幡随风飘荡,发出哗哗啦啦的响声。胡寡妇蹲在门口,袒胸露乳,就着一个盆洗脸。她的身后,站在满脸麻子的马屠夫。他们的心情似乎不错,有说有笑的。我看见,马屠夫弯下腰,捏了胡寡妇的屁股一把。胡寡妇放肆地笑起来,像一只发情的母鸡。我重重地咳了一声,马屠夫闪电般缩回了手,胡寡妇的笑声像被刀子一下切断。胡寡妇站起身,看着我,脸上换上了悲伤的神色。
胡寡妇说:是军哥啊,稀客,稀客。
我懒得和她废话,直截了当地说:大傻昨晚对我说了,叫我把根生带走。
胡寡妇冷笑一声:笑话,他昨晚躺在棺材里,能和你说什么鬼话。
马屠夫瞪着我,手叉着腰,一脸凶相。
我扬起水烟筒,说,这个,你们不会不知道吧,这是大傻昨晚给我的。
胡寡妇的脸一下白了,满脸惊恐,像筛糠一样抖起来。马屠夫看着那根水烟筒,脸一下子黑了,不停地向后缩身子。
我懒得和那对狗男女再说一句话,与其和他们说话,不如和猪和狗和牛说话。他们那副嘴脸,像躲躲藏藏的黑蜘蛛、臭蟑螂,让人看了就想呕吐。我忍住恶心,快速地从他们身边走过,直奔堂屋。做法事的先生还没起床,大傻的老木(棺材)孤零零地停在屋子中央。大傻的遗照,端坐在老木的前上方,一脸愁容,老气横秋,眉头紧锁,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趴在棺材上,蓬头垢面,像一只肮脏的小猫。我摸了摸他的头,他抬起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
你是根生?我问。
男孩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说:你是马军伯伯?我爸爸经常提到你。
我把他抱起来,说:你爸说了,以后你就跟着我。
根生眨巴着眼睛,说:我知道,我爸爸昨晚对我说,他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以后,你就是我的爸爸了。
我握住他瘦瘦的小手,说:,好。
我放下根生,抽出一支烟,装到水烟筒的烟嘴上,点燃,吸了一口,对着大傻说:大傻,来一口,劲大,过瘾。
我把根生拉过来,叫根生给大傻跪下,说,兄弟,我把根生带走了,你放心。
烟雾中,大傻和我四目相对。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大傻忽然咧开嘴巴,对我笑了一下。
埋葬了大傻,我牵着根生的手,鞠了三个躬,准备离开那座新垒的矮矮的黄土堆。这时,突然听见一阵拍打翅膀的声音,一只白鸟从空而降,像一朵雪。白鸟站在沾满黄土的墓碑上,闪动着翅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人群。几个小伙子齐声尖叫,猛然扑上去,想把白鸟逮住。白鸟张开翅膀,带着风声,箭一般飞到空中。它在空中飞了几圈,众目睽睽之下,忽然收起翅膀,落到根生的肩头。它大大的眼睛盯着根生,嘴巴一张一合,咕噜咕噜地叫着。
几个小伙冲过去,想把鸟抓住。根生闪电般捡起一块石头,喊道:不准碰它,谁碰它我就打谁。
人群静下来,有个老头说:别乱动,那只鸟是大傻。
我望着那鸟的眼睛,不由吓了一跳,老天,那分明是大傻的眼睛啊。
每一年清明,我带根生去给大傻挂纸,总会看见那只白鸟。它站在树枝上,像一朵雪。如果你们有时间,就去大傻的坟边看看,那只白鸟还在呢。真奇怪,老子都老成朽木头了,那鸟还是那样年轻,一点没变。
也许,你们笑我是呆子、疯子、老神经病。也罢,也罢,那你们就笑吧。你们看,太阳就要落山了,我可要回家了,如果回去晚了,根生又该着急了。根生那龟儿子,几十岁的人了,还像个咋咋呼呼的毛头小子。每次我出来走走,他总要给我规定回家的时间。如果超过了时间,他就会屁颠屁颠地跑出来找我。那小子,啥都好,就是胆子小,总担心我出啥事情。能出啥事嘛,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阎王爷也没能拿老子怎么样。
走吧,馋烟了,回去好好吸一筒。我一直用大傻留下的那支水烟筒吸烟呢。那是一只有灵性的水烟筒,劲大,过瘾,吞云吐雾。说来你们不信,当我吸足了烟,把水烟筒靠在墙边,它常会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
我知道,肯定是大傻在吸烟。
责任编辑/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