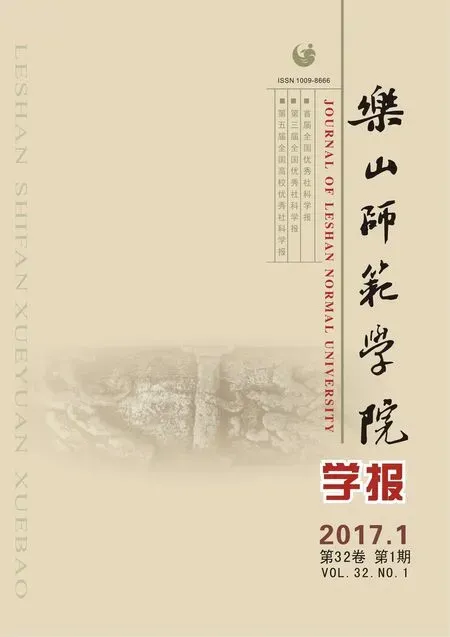从善的内涵论孟子性善
李世平
(中共西安市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陕西 西安 710054)
从善的内涵论孟子性善
李世平
(中共西安市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陕西 西安 710054)
孟子言善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从具体经验事实层面而言的“善行”;另一则是从内在根源层面而言的“善根”。孟子言性和善的内涵是一致的,与善相应,孟子言性也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落实为具体事相层面的仁义礼智之性,另一则是能够成就仁义礼智之性的为善的能力之性。孟子言性和善所具有的两个层面的内涵决定了孟子性善也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从为善的能力之性和“善根”出发而言的性善立本论,为成就道德奠立可靠的根基;二是从仁义礼智之性和“善行”出发而言的性善存养论,解决现实道德的养成。
孟子;性;善
如何理解孟子性善是历来争议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目前学界有认为孟子性善是性“向善论”,[1]189也有认为孟子“性善是一个过程”,[2]46还有从“隐默之知”出发阐明孟子性善的,[3]105-106也有主张应当“从孟子的内在理路出发,体会孟子倡导性善的良苦用心和真实意图”,[4]363进而认为“孟子以善为性”。[4]357后一种观点揭示了孟子所言性和善的内涵是一致的,对此,我们可以从善的内涵入手解析孟子的性善。那么,孟子所言善是何意?换言之,孟子究竟是在善的何种意义上讲性善的?
一、学界对孟子所言善的研究
长期以来,研究孟子性善往往局限于对孟子心性的分析,忽视了对孟子所言善的考察。傅佩荣先生则开始从善的界说入手解析孟子性善,这一新的视角的确丰富了孟子性善思想的研究。但他对“善的界说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1]188如此界说孟子所言的“善”就无法坚持性善,只能坚持性向善。因为以这样的“善”来看,性善就意味着人生已经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已经达成了善行,这显然与人在现实中还表现出恶行这一情况不符。傅先生也明白“如此界说的‘善’当然不可能与生具有,因此不宜说人性本善,只宜说人性向善”。[1]189这样,傅先生只好将孟子性善解释为性向善,“人的本性,既非本恶也非本善,而是具有行善之潜能,亦即向善,只须存养充扩之”。[1]193可见,傅佩荣先生认为孟子性善是性向善,他的这一观点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对善的界说决定的。
傅佩荣先生如此界说“善”,可以追溯到荀子对善的界说。荀子指出:“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今诚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矣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荀子·性恶》)荀子用“正理平治”来界说“善”,“‘正理’是指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即人已经呈现出‘仁义法正’的善良行为,‘平治’是指人人遵守道德规范,共同构建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可见,荀子所言的善着眼于人的具体表现和其表现所造成的社会效果,善就是一个好的社会行为以及产生好的社会效果。”[5]47这样,在荀子看来,孟子讲性善就是认为人生来就是好人、是善人,既如此,圣王礼义在现实社会中还有意义与作用吗?在此意义上,荀子反对性善的确有他的道理。但问题是,孟子所讲性善的“善”果真如荀子所定义的、如傅佩荣先生所界说的“善”吗?如果是,傅佩荣先生将孟子性善解释为性向善,以及荀子对孟子性善的批评无疑都是合理的。
然而,孟子性善之善并非如此简单。牟宗三先生早就指出:“文定(胡安国)谓孟子道性善为赞叹之辞,并非否认性之善,乃只是以为此善超善恶相对之至善,并非表现上、事相上、流相上之相对之善,即并非价值判断上之指谓谓词之善,乃是称体而叹之善,非指谓流相之善。”[6]466流相之善就是荀子所定义的、傅佩荣先生所界说的“善”,是已经表现出的道德行为,但牟先生却认为孟子性善之善不是流相之善,而是“超善恶相对之至善”。在傅佩荣先生对善进行重新界说后,李明辉先生重申孟子性善之善并不是具体事相之善,他坚持认为:“我们亦可以说‘性善’。但这种意义的‘善’是绝对的‘善’即不与‘恶’相对的‘善’,故谓之‘至善’。”[3]110牟宗三先生和李明辉先生认为孟子性善之善乃是“至善”而非具体事相之善,都是不同于荀子和傅佩荣先生对孟子性善之善的另一种理解,如此理解孟子性善之善,当然可以继续坚持性善。那么,这种“至善”究竟是什么意义上的善,换言之,它与事相之善即与傅佩荣先生所言的“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的善、与荀子所言的“正理平治”之善有何关系?
对此,梁涛先生认为:“孟子以前,善作为一个名词,往往指的是善人、善事、善行,善人、善事、善行之所以被称为‘善’,乃是因为符合社会、民众一般认识,所以如果将善定义为‘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的话,那么,它显然反映的是社会、习俗的外在标准。……《孟子》书中虽然也保留了善的这种用法,但孟子‘道性善’却不是这种意义上的善,而是以内在的道德品质、道德禀赋为善,此道德品质、道德禀赋可以表现为具体的善行,因而是善,所以反映的是主体自主、自觉的内在标准,孟子的善可定义为:己之道德禀赋及己与他人适当关系的实现。”[4]341梁先生明确认识到孟子“性善”之善与善行之善的不同,并认为“性善”之善可以表现为具体的善行,即从二者的相互关系来揭示“性善”之善是“内在的道德品质、道德禀赋”。梁先生这些看法发前人所未发,对于推进孟子性善研究的确有重大的贡献。但是,梁先生随后对孟子的善所下的定义却背离了他前面的分析,本来按照梁先生的分析,孟子“性善”之善是“内在的道德品质、道德禀赋”,这样的善是先天的为善的能力,仅仅“可以”实现己与他人适当的关系,但梁先生却将这样的善定义为“己之道德禀赋及己与他人适当关系的实现”,使先天的为善的能力禀赋兼具了现实的善行,最终使孟子“性善”之善不仅是先天的为善的能力,而且也是“己与他人适当关系的实现”。而“己与他人适当关系的实现”这样的善已经是具体的善行了,这正是傅佩荣先生所言的“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的善,是荀子所言的“正理平治”之善。这样,梁涛先生对孟子“性善”之善的定义,实际上是将孟子“内在的道德品质、道德禀赋”之善和荀子“正理平治”之善的内涵结合在了一起,梁先生的这种做法结果使孟子“内在的道德品质、道德禀赋”之善兼具了荀子“正理平治”之善的内涵,而这已经是孟子所言的圣的内涵而非孟子所言的善的内涵了。[5]10退一步,依梁先生对孟子“性善”之善的定义,孟子的性善依然面临着难以成立的理论困境,因为这样的性善仍然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已经实现,这同样有悖于现实。
总之,前人对孟子性善之善的内涵进行了解析,虽然这些解析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他们深入研究、分析的态度是值得我们赞赏和尊重的。也只有在前人解析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进一步推进孟子“性善”之善的研究。本文正是基于前人对于孟子所言善的内涵的研究,利用代入法,分析孟子“性善”之善的内涵。所谓代入法就是通过对《孟子》文本的阅读,结合前人对孟子“性善”之善的内涵解析,形成自己对孟子“性善”之善的理解,然后将这些理解代入《孟子》文本之中,检验这些理解是否符合《孟子》文本前后文之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发现孟子“性善”之善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内涵。长期以来,由于人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总是以某一善的内涵来理解孟子“性善”之善,结果造成此处能够解释得通,彼处就扞格不入,或者彼处融洽,此处却又无法解释得通的两难境地。
二、孟子所言善的内涵分析
对于孟子所言的善,傅佩荣先生界说为“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在《孟子》一书中的确有这样的善,但这并不完全是孟子“性善”之善,像牟宗三先生、李明辉先生所言的超善恶相对的“至善”之善,即梁涛先生所言的内在的道德品质、道德禀赋之善,也是孟子“性善”之善。也就是说,孟子“性善”之善具有两方面的内涵,这两方面内涵集中体现在《孟子·告子上》第六章,具体文本如下: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
公都子先陈述了当时流行的三种人性论,然后问孟子,老师您今天讲性善,他们的人性论都不对吗?面对公都子之问,孟子开始正面阐述他的性善思想,“乃若”是发语词。[7]328“其情”的“其”应当指代上文公都子所述的“性”,“情”作“实”解,[5]21指性的实际情况。“‘可以为善’的‘可以’只表达人具有为善的能力”,[5]23“为”表达具体落实表现为,其中的“善”是傅佩荣先生所界说的“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之善。“乃所谓善也”的“善”就是孟子“内在的道德品质、道德禀赋”之善。“若夫”是转语词,“不善”之“善”也是傅佩荣先生所界说的“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之善。“非才之罪也”的“才”是指前面所言的性的材质。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把孟子正面阐述性善思想的这一部分内容疏解为:
“就性的实际情况而言,(为善的能力之性)能够落实表现出善良的行为,就是我所说的性善。”[5]28要是一个人没有表现出善良的行为,并不是因为他没有为善的能力之才,也不是因为为善的能力之才有什么不好,(而是由于他没有发挥为善的能力之才造成的)。
在孟子正面阐述自己的性善时,依次讲了三个善,第一个“可以为善矣”的“善”和第三个“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的“善”,是傅佩荣先生所言的“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之善,也是荀子所言的“正理平治”之善,而只有中间一个“乃所谓善也”的“善”,才是孟子所要阐述的“内在的道德品质、道德禀赋”之善,这一善也是牟宗三先生、李明辉先生所言的“至善”之善。其实,公都子陈述的当时流行的三种人性论都是从荀子“正理平治”之善即具体的善行出发而言的。从具体的善行出发,可以坚持人性中既没有善行也没有恶行,这就是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也可以坚持“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还可以坚持“有性善,有性不善”论。总之,只要认为善就是“正理平治”、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也就是说,只要从具体表象上、事相上言善就可以坚持不同的人性论。基于此,孟子正面阐述了善的内涵,他不再将善的内涵仅仅局限在具体事相上,而是在具体事相之善的基础上推进一层,将可以表现为具体事相之善的能力也称之为善。
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孟子为什么能够从具体事相之善出发推进一层,将可以表现为具体事相之善的能力也称为善呢?原来在孟子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往往可以将一些概念推进一层来理解,以此揭示这一概念形成的内在机理。孟子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将善的概念推进一层,将可以为善的能力也称为善。荀子将这样的现象总结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①荀子指出当时流行的概念“性”、“伪”、“能”皆有两个层面的内涵:前面所言的“性”“伪”“能”皆是从推进一层而言的,也就是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都是从内在根源的层面揭示“性”“伪”“能”形成的机理,而后面所言的“性”“伪”“能”皆是从具体落实层面、从具体事相层面而言的,“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能有所合谓之能”都是具体表象上的“性”“伪”“能”。这样,荀子认为当时不少概念皆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具体经验事实层面的内涵,另一则是推进一层内在根源层面的内涵。荀子认为一个概念可以有两个层面的内涵,如“能”就有“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和“能有所合谓之能”两个层面的内涵,“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的“能”是指一个人的内在能力,这是推进一层而言的“能”,而“能有所合谓之能”的“能”则是落在具体事相上的“能”,是一个人具体表现出的“能”。虽然如此,但对于善,荀子却认为只有一个层面的内涵,即只有具体事相层面的内涵:“正理平治”之善。从与“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的比较来看,对于善,荀子只讲“善有所合谓之善”,不再讲“所以善之在人者谓之善”,即荀子讲善只讲具体事相这一层面的内涵,不再讲推进一层内在根源层面的内涵。而孟子则不同,他不仅讲具体事相层面的善,而且还推进一层讲内在根源层面的善,即孟子不仅讲“善有所合谓之善”,而且还讲“所以善之在人者谓之善”。
因此,孟子所言的善就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从具体经验事实层面而言的善,也就是荀子所言的“正理平治”之善,亦即傅佩荣先生所言的“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的善,这是“善有所合谓之善”的善;另一则是从内在根源层面而言的善,即梁涛先生所言的“内在的道德品质、道德禀赋”之善,也就是牟宗三先生所言的“至善”之善,这是“所以善之在人者谓之善”的善。“善有所合谓之善”的善是已经落实为现实的道德行为,为了与“所以善之在人者谓之善”的善相区别,我们称之为“善行”;而“所以善之在人者谓之善”的善则是现实善行的内在根据,它能够落实为现实的善行,与具体“善行”相区别,我们称之为“善根”。“善行”与“善根”是我们对孟子所言善的内涵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否得当,仍然需要代入《孟子》文本进行检验。将“善行”和“善根”这两种内涵代入孟子具体阐述性善的文本之中,原来的文本就是:“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行’矣,乃所谓‘善根’也。若夫为不‘善行’,非才之罪也。”翻译成现代汉语则是:“就拿性的实际情况来说,能够落实表现出良好的道德行为,就是我所说的性具有善的根基。要是一个人没有表现出良好的道德行为,并不是因为他没有为善的能力之才(善的根基)。”在文本中相应的善的地方分别代入“善行”和“善根”,文本内容不仅能够讲得通,而且变得更容易理解了。从这一检验结果来看,孟子所言的善具有“善行”和“善根”两个层面的内涵。
三、从善的双重内涵看孟子性善
从孟子言善的双重内涵来看,孟子性善也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孟子言善有“善行”和“善根”两个层面的内涵,在孟子思想中,性与善的内涵是一致的,因此,与善的内涵相应,孟子言性也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落实为具体事相层面的仁义礼智之性,另一则是能够成就仁义礼智之性的为善的能力之性。[5]37-43当然,孟子所言的为善的能力之性与仁义礼智之性、或者“善根”与“善行”之间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为善的能力之性是仁义礼智之性的内在根基,如果没有为善的能力之性,仁义礼智之性就无法实现;仁义礼智之性则是为善的能力之性的具体落实与实现,如果没有仁义礼智之性,为善的能力之性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同样,“善根”是“善行”的内在根基,没有“善根”,“善行”就会失去存在的根据;而“善行”则是“善根”的具体落实与实现,没有“善行”,“善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孟子所言的善有“善根”和“善行”两个层面的内涵,所言的性也有为善的能力之性与仁义礼智之性两个层面的内涵。孟子言性善,性是为善的能力之性,与此相应的善就是“善根”,这是从确立成就道德的内在根基而言性善,我们把这样的性善称之为性善立本论。从孟子的性善立本论来看,它所揭示的是人人皆有成就道德的根据,而不是说每个人已经达成了现实的道德内容和道德行为。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对道德的根据与具体道德内容和道德行为不分,误认为孟子的性善立本论是先天就具有道德内容和道德行为,结果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理论麻烦。当然,孟子也讲具体道德内容和道德行为的性善,这一层面的性善,性是仁义礼智之性,与仁义礼智之性相应,善就是“善行”,但这一层面的性善已经不是先天的,而是关乎后天存养的,我们把这一层面的性善称之为性善存养论。在孟子思想中,仁义礼智之性是具体的道德规范、道德行为,属于人之为人之性的具体落实层面,相应的善也是具体落实层面的善行,就孟子所言的这一层面的性善而言,的确无法坚持“‘性善完成论’。讲得抽象一点,性善是一个过程,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2]46也就是说,这一层面的性善是一个过程,此过程是一个心性修养的过程,即心性存养的过程,因此,我们称之为性善存养论。性善存养论与性善立本论一样,是构成孟子性善思想的一部分。
根据上文分析,基于孟子言善两个层面的内涵,孟子性善也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从为善的能力之性和“善根”出发,确立道德根基的性善立本论;二是从仁义礼智之性和“善行”出发,解决道德养成的性善存养论。孟子一方面从“善根”讲性善立本论,为成就道德确立可靠的根基,另一方面从“善行”出发讲性善存养论。从为善的能力之性和“善根”出发而言的性善立本论正是为了现实的“善行”的达成,而从仁义礼智之性和“善行”出发而言的性善存养论恰恰能够说明“善根”的存在。因此,孟子从为善的能力之性和“善根”出发确立成就道德根据的性善立本论,其目的是为成就仁义礼智之性奠定可靠的根基。而孟子所言的道德修养工夫论,即从仁义礼智之性和“善行”出发解决道德修养问题的性善存养论,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内在的为善的能力之性,达成现实的仁义礼智之“善行”。正如“善根”与“善行”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一样,孟子的性善立本论和性善存养论也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善根”与“善行”二者毕竟不同,“善根”是善的内在根据而非现实的善行,“善行”则表现为现实的善行而非善的根据,性善立本论与性善存养论亦如是,性善立本论是为道德奠定根据的,性善存养论则负责具体道德的养成,二者各有各的内涵,我们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平心而论,我们的前辈不是没有认识到孟子性善在讲什么,而是没有将孟子性善的这两个层面的内涵理出来,结果不是以性善立本论代替孟子整个性善思想体系,就是以性善存养论代替孟子整个性善思想体系,或者是以性向善论取代孟子整个性善思想体系。
牟宗三先生、李明辉先生以及近来的梁涛先生,都有以性善立本论代替孟子整个性善思想体系的倾向。牟宗三先生认为孟子性善之善是“超善恶相对之至善”,[6]466李明辉先生也认为孟子性善之善是“至善”,[3]110这本没有错,但是,他们不仅认为为善的能力之性是“至善”,而且认为仁义礼智之性也是“至善”,这实际上是将需要存养的仁义礼智之性也讲成了先天的,把性善存养论也讲成了性善立本论,于是,孟子性善的双重内涵不见了,代之以单一的性善立本论。梁涛先生亦如是,他一方面将仁义礼智之性视为先天的、超越的,即将现实的仁义礼智之性提升为内在根源之性,另一方面将孟子的善定义为:“己之道德禀赋及己与他人适当关系的实现。”[4]341这样的善既是“善根”也是“善行”,结果“善根”与“善行”不分,“善行”被先天化、“善根”化了,最终也将孟子性善思想的双重内涵变成了单一的性善立本论。
牟宗三先生、李明辉先生还有梁涛先生把人之为人的具体落实层面的仁义礼智之性也讲成性善立本论,实际上等于认为人生而就具有现实的善行,这不仅与现实中人还会表现出恶行这一情形相矛盾,更会在理论上消解道德实践工夫的必要性,即消解孟子一再强调的“扩充”与“存养”工夫的必要性。为此,杨泽波先生主张孟子“性善是一个过程”,[2]46重新强调孟子思想中“扩充”、“存养”的必要性。杨泽波先生讲的性是仁义礼智之性,不再认为仁义礼智之性是先天的、人生而就有的,而是认为仁义礼智之性是“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的结晶”,[2]2这的确是孟子性善理论研究史上的重大突破。但杨先生只讲仁义礼智之性,仁义礼智之性形成的根基即为善的能力之性并没有被单独提出来,加之杨先生也没有从孟子言善之中区分出“善根”,因此,他所讲的孟子“性善是一个过程”,就仅仅是孟子的性善存养论。
如果说牟宗三先生等学者是以性善立本论代替了孟子整个性善思想体系,那么,杨泽波先生无疑是以性善存养论代替了孟子整个性善思想体系。前者是以道德的根基取代整个道德思想体系,道德修养工夫有被消解的可能;而后者则以道德的修养取代了完整的道德思想体系,道德的根基变得暗而不彰。傅佩荣先生另辟蹊径,认为孟子性善是性向善,他的这一观点则是以性向善取代孟子整个性善思想体系。傅佩荣先生的性向善否认仁义礼智之性是先天具有的,他认为孟子“以‘仁义礼智’为善,然后强调个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此四心正是四善之‘端’(《公孙丑上》)。‘端’字用得十分精当,如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必须存而养之,扩而充之,才可以成就善。”[1]193傅佩荣先生认为仁义礼智之性是善,这一善就是他所界说的“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的善,亦即本文所言的“善行”,傅佩荣先生认为仁义礼智之善并不是先天就具有,而是后天“存而养之,扩而充之”所达成的,这实际上就是孟子性善存养论。但傅佩荣先生不讲后天存养的性,只讲先天本有的性,即只讲“具有行善之潜能”之性[1]193,讲善也只讲“善行”,不讲“善根”,结果傅先生只能讲性向善,亦即“行善之潜能”向善。傅先生之所以将孟子性善讲成性向善,主要根源在于他对孟子性善之善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如果认为与“行善之潜能”之性相对应的善是“善根”,这样就可以坚持性善。但傅佩荣先生却没有认识到孟子言善的这一独特层面,仍然以他自己所界说的“善行”与“行善之潜能”之性相应,结果就只能坚持性向善而非性善。
注释:
①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12-413页。
[1]傅佩荣.儒家哲学新论[M].台北:台湾业强出版社,1993.
[2]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李明辉.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M].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4.
[4]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李世平.孟子良心思想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2.
[6]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二册)[M].台北:正中书局,1968.
[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On Mencius’Theory on Human Nature from the Connotation of“Goodness”
LI Shipinɡ
(Department of Philosophical Teaching and Research,Xi’an Municipal Party School of CPC,Xi’an Shaanxi 710054,China)
Two aspects are included in understanding Mencius's theory on“goodness”:one refers to“good action”concerning fact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and the other refers to“good roots”involving internal origin.The connotation of human nature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goodness in Mencius views. Thus,human nature should be interpreted in two sides at the same time:the“four beginnings”as humanity,righteousness,propriety and wisdom shown in practical events by people and the capability to realize the“four beginnings”.Combining the understanding on Mencius theories on human nature and goodness,his view of innate goodness should be clarified in two levels:the basic theory of innate goodness in consideration of the“good roots”and the ability to be good,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to realize morality;the existence and cultivation theory arising from the“four beginnings”and“good action”,helping cultivate morality.
Mencius;Human Nature;Goodness
B222.5
A
1009-8666(2017)01-0101-07
10.16069/j.cnki.51-1610/g4.2017.01.016
[责任编辑:王兴全]
2016-10-3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孟子心性论研究辨正”(项目编号:16XZX006)
李世平(1972—),男,陕西横山人。中共西安市委党校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儒家心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