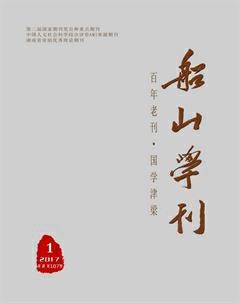王船山对朱子正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李长泰+吴悠
摘 要:
王船山的正心思想是对朱子正心思想的发展,主要凸显了四个方面:一是将心之内涵从朱子的“心统性情”发展为“持志正心”;二是将正心实质从朱子的“去蔽存心”发展为“道心至正”;三是将正心的路径从朱子的“诚意正心”转换为“正心诚意”;四是将正心评价从朱子的“心与理一”丰富为“推至天下”。通过对王船山正心思想的分析,可以得出船山的学术研究方法走了一條正学开新和经世致用并重的路径。
关键词:王船山;朱子;正心思想
南宋朱熹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与《中庸》《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朱熹认为《大学》是儒家道德的入门读物,“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①,将其列为《四书》之首。“正心”是《大学》“三纲八目”中的一目,从致知到修身,如何由物及身,心的桥梁作用十分重要。朱子非常重视正心思想,论述颇多,认为心为身之主,“正心”对为学乃至个人修身有重要作用。王船山也十分重视《四书》,对朱子正心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相关著述十分丰富,形成一系列“四书学”著作。特别是在《读四书大全说》中,王船山对《四书》以往通行的注疏进行札记式的注解,重新论述了《大学》修行的八条目。之后他在继承朱子正心思想的基础上,调整了诚意正心的顺序,对“正心”的涵义做出了新的解释。本文拟从朱熹和船山正心思想的比较视角浅析船山对朱子正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心之内涵:从“心统性情”到“持志正心”
朱子将心归纳为人身的主宰,船山将心归纳为人心的志向。根据《朱子语类》及一些对答文集的记载,朱子对于心性的论述很多,朱子主要认为心是人身体的主宰,统摄四肢及一切思想,提出了“心统性情”说。船山认同朱子“心统性情”的说法,但认为朱子将心作为人身主宰会使心的作用具有二重性。于是,他创造性地引入孟子的“志”来解释心,提出了“持志正心”。
何者为“心”?心自是一个血气凝结的肉团。由于古代医学不够发达,一般也将人体的思虑功能归结于心。从思虑的角度看,心的本体不包含心的生理本体,但心的生理本体却与心的本体有关系。朱子曾按功能具体地将心分为两类:生理心和思虑心,即“肺肝五脏之心”和“操舍存亡之心”。
问: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曰:如肺肝五脏之心,却是实有一物。若今学者所论操舍存亡之心,则自是神明不测。故五脏之心受病,则可用药脯之;这个心,则非菖蒲、茯苓所可补也。问:如此,则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则微有迹;比气,则自然又灵。②
朱子在生理层面确认了肉体之心的现实存在,将其归为形而下,较为粗笨。而“操舍存亡之心”即具有思虑功能的心,则属于形而上,介于性与气两个层次之间,超然于心的生理本体之上,有迹可循,又充满着思虑的灵性。肝肺五脏之心不须多加讨论,于学问一途,朱子自然更注重心的本体在思虑方面作用。
朱子认为心为身体的主宰,他说:“心是神明之舍,为一身之主宰。”③此处的“主”,即是指心的本体就是统帅人全身的最终归宿,具有绝对的自由和自主权。朱子在批评佛教观心说的时候曾言:“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今复有物以反观乎心,则是此心之外复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④朱子在这里反对了佛教在本心以外再立一心,以此心的观照来发明本心的方法。朱子认为心是人身体的唯一主宰,统领身体各部位及感官,也是所有存养工夫的中枢和落脚点。
朱子对心的功能进行归纳之后,又在本体层面对心进行了论述。朱子主要提出了“心统性情”说,“统”字有“兼”“包”义。朱子对“心统性情”一般有两种解释:心主性情和心兼性情,“主”字代表心对性、情的主宰,有一种领导的意味;而“兼”字,则表达包涵的意思,心的作用包涵了性、情的作用。
朱子“心统性情”思想的形成被称为“己丑之悟”。在“己丑之悟”以后,朱子在与湖湘学派张栻等人的辩论中体认出中和之道,认为心承担了中和的作用,加深了对“心统性情”的理解,他认为“中和”的未发为性,为心之体;已发为情,为心之用。这可以从张立文教授的研究成果中得到证明,“心是体,情是心的用。一性浑然,义理全具,这是‘中;七情迭用,动而合乎‘中节,这便是‘和。中和为大本达道,使心、性、情得以中和的和合化解。”⑤心统性情,贯通于未发和已发之间。仁义礼智为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情,而使仁爱、使义恶、使礼让、使智知的原因,就是心。朱子的这种主宰之心包括了性、情两面,并驱使着它们有所运作。
朱子在与张栻的切磋之中,似乎更倾向于心主性情。“统”虽表达出了本体之心对性和情的包涵概括作用,但似乎只是一个等价的并列。而“主”除了包含“统”的作用,还更加突出了心对身体及性情的知觉与主宰作用。此时的心是一个具有强烈能动性的主体,它可以驱使性、情有所行为,而不是仅仅静态地接受性、情的运作结果。
船山同意朱子的“心统性情”说,但比朱子又有所发展。船山思想成熟之后作《读四书大全说》,在书中尊称《大学》经文为“圣经”,尊称程朱一派为“圣学”。在相当程度上受到程朱“天理论”的影响,事实上继承和发展了程朱学说。船山说:
“心统性情”,“统”字只作“兼”字看。其不言兼而言统者,性情有先后之序而非并立者也。实则所云“统”者,自其函受而言。若说个“主”字,则是性情显而心藏矣,此又不成义理。性自是心之主,心但为情之主,心不能主性也。⑥
船山认为朱子的心统性情中的“统”字应当理解为“兼”,表示包涵的意思。他认为如果直接理解为心统性情,性、情的地位将会有所差别。同时,船山也反对朱子将“统”理解为“主”。如果说是心主性情,会忽略掉心的主导作用。船山认为心包涵性、情,但只是情之主,不是性之主。性的地位在情之上,并可以主心,对心有导向作用。此说与朱子的心性论有相通处,反抗了陆王的唯心说。
船山认同朱子的“心者身之所主也”⑦,但却批评其学说中的身意关系不够清晰。他认为朱子将心作为身之主会造成心的二重性,在低层次上以意为心,把心的作用降低到意识层面;在高层次上则统性情,使心的作用模糊不清。这样的话,正心的功用便不会得到实际的落实。“夫曰正其心,则正其所不正,有不正者而正始为功。统性情之心,虚灵不昧,何有不正,而初不受正。”⑧船山将朱子的统性情之心当做虚灵不昧的本心,认为其自然端正,并不需要特意在工夫上去施正它。而正心之心,船山则将它归结为性的产物,与人体的五官百骸一起长出并主宰人的身体,而因其常常在人的胸怀之中蕴藏,便形成了一股力量,创造性地把它叫做孟子的“志”。船山言:
惟夫志,则有所感而意发,其志固在,无所感而意不发,其志未尝不在。而隐然有一欲为可为之体,于不赌不闻之中。欲修其身者,则心亦欲修之。心不欲修其身者,非供情欲之用,则直无可矣。⑨
不管“意”的已发或未发,这个“志”都一直存在。只有有了志,人的听、说、动、言才有了主宰。不管此人的行动正或不正,或者游离与正与不正之间,才与意有了接通处而为意所指导。于是船山说道:“此则身意之交,心之本体;此则条诚之际,正之实功也。故曰‘心者身之所主,主乎视听言动者也,则唯志而已矣。”⑩此志心是身意的中介,且作为心的本体主宰了人的视听言动。志心是思虑的心,掌控着人的一切行为。
二、正心实质:从“去蔽存心”到“道心至正”
朱子将正心实质归纳为“去蔽存心”,船山则将正心实质改为“道心至正”。朱子认为心只有一个,此心类似于神明统摄着人的全身。正心即是存养此心,使心保持本身的清明,避免受到不当情感的污染。船山则认为心有人心道心的区别,看重道心的影响,认为正心需要充分发挥道心的作用,使道心引导人心走向善的方向。
朱子认为心的本体应当像太虚般清明无垢,“设此心如太虚然,则应事接务,各止其所,而我无所与,则便视而见,听而闻,食而知其味也。”(11)还常常用镜子与天平来比喻人心:“人之一心,湛然虚明,如鉴之空,如衡之平,以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体之本然。”(12)他认为人心如镜,需要保持其本体的清明,并从镜喻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存養方法。
人心如一个镜,先未有一个影像,有事物来方始照见妍丑。若先有一个影像在里,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虚明,事物之来,随感而应,自然见得高下轻重,事过便当依前恁地虚,方得。若事未来,先有一个忿懥、好乐、恐惧、忧患之事到来,又以这心相滚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苦留在这里,如何得正?(13)
朱子认为人心如镜般清明,镜中本来没有影像,另有事物来,才能照见。所以人心应当如同镜子一样,去除心中已有忿懥、好乐等各种偏狭的情感,才能让好的情感进驻。不然,心中没有位置,怎么拥有好的情感,怎么能实现正心呢?
但是,朱子并不认为能绝对涤除人心中这些不当的情感,“好、乐、忧、惧四者,人之所不能无也,但要所好所恶皆中理。”(14)他认为各种情感是人天生就具有的,不能消除,只能使用“中庸”的方法使它不至于偏狭。“喜怒哀乐固欲中节,然事过后便须平了。谓如事之可喜者,固须与之喜,然后别遇一事,又将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盖心无物,方能应物。”(15)朱子认为,人必然会有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但不能将处理上一事情时的情绪带入到下一件事情的处理中。只有让这些情感不过分发动,发动时不偏不倚,让心保持虚明无物的状态,才能顺应事物本身的规律去处理事物,使其合乎道理。
船山不同意朱子对正心的理解。他说“如镜先未有象”(16),认为人心本来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光明,有谁能在没有遇到事情的时候时时揣着一个“忿懥”之心?天下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人,在平白无事的时候,也常常感到愤怒。船山在对《尚书》十六字真言进行训义的时候,以公正无私为界限,将心分为人心与道心。道心是善,是一。人心则因为浸染了欲望,所以趋向于恶。如何让道心引导人性向善?于是,船山引入“心统性情”说来实现两者的结合。船山说:
心,统性情者也。但言心而皆统性情,则人心亦统性,道心亦统情矣。人心统性,气质之性其都,而天命之性其原矣。道心统情,天命之性其显,而气质之性其藏矣。显于天命,继之者善也,惟聪明圣知达天德者知之。藏于气质,成之者性也,舍则失之者,弗思耳矣。无思而失,达天德而始知,介然仅觉之小人,去其几希之庶民,所不得而见也。故曰微也。人心括于情,而情未有非其性者,故曰人心统性。道心藏于性,性抑必有其情也,故曰道心统情。性不可闻,而情可验也。(17)
船山认为心有人心和道心的区别,道心是天命之性的显现,是本原;人心是气质之心的显现,是延伸。人心能够统性而不消亡的原因是其来源于天命之性,如果让道心去统领人心,则会彰显天命的作用,引导人心走向至善。圣人以道心为心,心统性情,使人欲符合天理。
船山所说的道心是天下之心,天下之心即是仁心。仁心的自然光明使道心匡扶人心走向至善成为可能。“仁之为德,此心不容己之几也,此身所与生之理也,以此身心与天下相酬酢,而以合乎人心之同然者也。故为仁者以心治身,以身应天下,必存不过之则以自惬天下之心,实有其功焉。故颜渊问仁,问其所以求诸心者也。”(18)船山认为人秉持仁心,自然可以用心支配身体,进而酬应天下。所以,反过来,求之于天下即是求之于心。此心即是道心,道心与天下一贯,用道心去匡扶人心以至于善,即是船山所说的正心。
三、正心径路:从“诚意正心”到“正心诚意”
在如何达到正心的路径上,朱子认为意诚然后心正,船山则认为正心然后诚意。朱子认为八条目是《大学》既定的修行次序,也常常将两个次序放在一起讨论研究。他认为诚意而正心,只有意诚之后才能正心。王船山提出“格致相因”。认为《大学》每两个修行次序前后互为因果,互相成就。船山偏重正心,将正心放在了诚意之前,也认为正心诚意相互辅佐,不能偏废。
朱子极重《大学》,在逝世之前仍圈点章句,对条目次序进行调整修订。他把正心放在了诚意之后,“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19)只有意的实现有了落脚处,正心才可能得以施行。有人问“正心”、“诚意”章,叙述道:“意诚则心正。”朱子曰:“不然,这几句连了又断,断了又连,虽若不相粘缀,中间又自相贯”,“意未诚,则全体是私意,更理会甚正心!然意虽诚了,又不可不正其心。”(20)朱子认为诚意是正心的前提,只有意诚之后才有机会与精力去过问正心,正心是诚意之后的必然结果。然而当意已诚,并不是说个人的修行已到达尽头,要彻底排除内心的染污,寻求正心又成了必然要求。
但对于朱子来说,在“正心”“诚意”两目中他更注重诚意,认为诚意的工夫更加困难,“到得正心时节,已是煞好了。只是就好里面又有许多偏。要紧最是诚意时节,正是别善恶,最要著力,所以重复说道‘必慎其独。”(21)又说:“诚意是无恶。忧患、忿懥之类却不是恶。但有之,则是有所动。”(22)朱子认为能完成正心就已经很不错了,但仍旧需要对一些微小的偏狭进行纠正,此种工夫即是诚意,朱子将诚意当做是区别善恶的关键。但朱子也认为忧患、忿懥等情感不是恶,它们只会对个人品质产生影响,虽然诚意的作用是去除恶,但也需在内心中涤除这些坏念头,不让它们影响个人内心的本然清明。
船山继承了朱子关于心性的大部分理论,但于诚意正心的次序,却有独到见解,“经言先后,不言前后。前后者,昨今之谓也。先后者,缓急之谓也。”(23)船山认为修行次序前后两者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只有逻辑顺序的先后。船山在评析格物致知时提出了“格致相因”一说,即格物与致知的过程并不完全隔绝开来,在格物的同时也要致知,而不是等到先致知完成再去格物。如此,格物与致知互相为因果,互相成就,学问与思辨互相为辅,不能割裂与偏废。正如“格致相因”一样,船山的独特处便是打乱了朱子的诚意正心。船山说:
况心之与意,动之与静,相为体用,而无分于主辅,故曰‘动静无端。故曰正其心者必诚意,而心苟不正,则其害亦必达于意,而无所施其诚。凡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皆意也。不能正其心,意一发而即向于邪,以成乎身之不修。故愚谓意居身心之交,而《中庸》末章,先动察后静存,与《大学》之序并行不悖。则心之与意,互相为因,互相为用,互相为功,互相为效。(24)
船山偏重正心,将正心放到了诚意之前,心意相因,心意互相为体用。同时,船山将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等种种情感都归结于意。认为并不是应当没有这四者,而是说四者的出现是心不正的结果,用《大学》中的话就是“心不在焉”。而如果没有完成正心,已发的意就有可能走向邪路,严重的就会导致修身难以完成,正心是诚意的前提。从正心到诚意,是從内心一步步推向外物,“八条目自天下至心,是步步向内说;自心而意而知而物,是步步向内说。”(25)船山把心当作了修行的中点,向内是静,向外是动,这就与《中庸》末章的“先动察后静存”的次序相同,把正心的作用提高到了修行的最紧要处。
船山用孟子的“持志正心”来解释正心与诚意的关系。他认为心是孟子的“志”,又用“持志”来解释正心,“执持其志”是正心的工夫,“不动心”就是正心的效果。船山认为就正心与诚意关系而言,当意之未发时,无所谓好恶,必须存养“志”;当意之已发,就必须充分发挥“志”的主宰作用,以诚灌意,使意一向于诚。相应地,船山批评了佛教的虚空之说。谓佛教本言“空”,连心也没有,如何能去谈正心。没有了心,儒家所提倡的修齐治平就无从谈起,甚至连落脚处都没有了。所以船山引孟子的“不动心有道”,即有道,心也一定是实有的。因为心有不正,而不是如同明德之心一样本自清明,所以便有修心的必要,即“不动心有道”。
四、正心评价:从“心与理一”到“推至天下”
对于正心结果的评价,王船山与朱子大致相同,都认为正心是实现个人修行的一个次序,不同的是,朱子认为正心的评价要与天理道德合一,船山则认为正心的效果应该达到经世致用。朱子认为“心与理一”,人心与天下一理贯通,都受到虚灵不昧的天理的影响。正心是平天下的一个步骤,从正心依次进阶即可达到平天下。王船山继承了朱子的“心与理一”的思想,又以“格致相因”为中心使用“推”的方法创造出独特的修行理路。将正心推至到平天下,使正心的效果最大化地实现。
朱子看重《大学》两章文字交接处,提倡于事物转折地方体会圣贤深意,常常将两个修行次序放在一起讨论。“正卿问:‘大学传正心、修身,莫有深浅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说,修身是就应事接物上说。那事不从心上做出来!如修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得出。”(26)朱子将正心归为思虑之事,而将修身归为行为举止。思虑都由心上发出,思虑向外发出作用于事物以完成修身。所以心的工夫对其他的修身工夫具有统摄作用,有源流之分。
朱子又言“心与理一”。此心的道理直通天理,所以修心之法必须解除人欲之蔽,使天理流行,重新回到清明的本心上去。在具体行为上,朱子也言:“修身以后,大概说向接物待人去,又与只说心处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则一,但一节说阔,一节去。”(27)理是一个,心和事物的道理是贯通的,只要达到了正心,其他事情自然而然就实现了,就如同天理的流行一样。但这也并不是说上一节实现了,下一节就一定会实现。每一节自有一节的工夫,上面一节工夫实现了,下面工夫的实现就不会太费劲,但同样也需要自己的努力。朱子还特别说明了有一些天资高明的人,只要开头做好了,下面的事很容易就一起完成了。但这也只是在叙述一种特殊情况,并没有否定工夫的作用。朱子又言:
故经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诚意而来,修身者必自正心而来。非谓意既诚而心无事可正,心既正而身无事可修也。且以大学之首章便教人“明明德”,又为格物以下事目,皆为明明德之事也。而平天下,方且言先谨乎德等事,亦可见也。(28)
朱子非常重视德性,他把格物之后的事皆归于明明德,就算是平天下,也必须先修德性,平天下必自修身而来。且认为修身必自正心而来,正心必由诚意而来,皆可以向前一步步推。此处与儒家的“恕”道相合,先修己身,然后才推及外物,达到修己治人的作用。而正心位于新民、明德的中点,居内外之交,也是恕道的推行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船山如同朱子一样,十分重视修行的次序。他说:“大学一部,恰紧在次序上,不许人作无翼而飞见解”(29),认同朱子所说的修齐治平层层递进的效果。至于次序的提升,船山用了“推”的概念。“所谓推者,乃推教家以教国也,非君子推其慈以使众于国。”又说:“教有通理,但在推广,而不待出家以别立一教。”(30)船山所谓的“推”的理论依据沿用了朱子的“理一分殊”。因为天下事物有通理,知一即知十,所以才有了处理事事物物的依据,即在相同道理的情况下推及其他。而不是用一件事物的道理去作用另一件,这样就是在事物外别立一教,反而无法做好事情,无法完成推。
船山认为身心一贯,正心即是修身。这样先持立上天所赐予我的明德之性,又端正心中的仁义并持久地保持它。这就不仅仅是使本心如同光洁的镜子一样只反射光线,而是如同烛火之光能映照他物,推己及人,实现修身的其余目的。“盖所谓修身者,则修之于言行动而已。繇言行而内之,则心意知为功,乃所以修身之本,而非于身致修之实。”(31)船山确认了修身之本在于正心,又说“故立教之本,有端可识,而推广无难。”(32)而身与家、国、天下为一理,依船山的“推”的方法,从正心到平天下,自是一体贯通。
船山认为并不是说只要完成了正心就可以达到平天下,虽说天下一理,但其中细微分差也是需要考量的。他说:“细为分之,则非但身之与国,不可以一律相求,即身之于家,家之于国,亦有厚薄之差。”(33)对于此种差别,就必须依据现实的情况来加以区别对待,依船山列举的曾子教子和天子治国的例子来看,大概就是儒家的“恕”。“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以自身的经验去强硬地要求别人,而是从自身寻求普遍的道理,然后去指导其他的事物。只有寻求到普遍的真理,才能使人家信服然后听从你。所以《论语·颜渊篇》才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因为家国一理,不论在哪里,对待困厄的心情自然都一样。
王船山把《大学》的八条目两两分组并认为它们互为因果。如同讲“格致相因”一样,也可说是“诚正相因”和“修齐相因”。当到达下一条目之后,与旁边的条目就组合成了因果,当一个循环完成之后,推进到下一条目,又照例完成循环,直到完成明明德,到达至善的结果。所以从格物到正心再到平天下,中间经历了数个循环,再加上“推”的方法,以心为节点,勾勒出了王船山的整个修行理路。
综上所述,王船山的正心思想主要把握了四个方面:一是将心的内涵从朱子的“心统性情”发展为“持志正心”;二是将正心实质从朱子的“去蔽存心”发展为“道心至正”;三是将正心的路径从朱子的“诚意正心”转换为“正心诚意”;四是将正心评价从朱子“心与理一”丰富为“推至天下”。通过对王船山正心思想的分析,可以得出船山的学术研究方法走了一条正学开新和经世致用并重的路径,这说明明清思想与先秦、两汉和宋代思想家的观点相比有较大的转型(34),更强调经世致用的学术路径。
【 注 释 】
①(1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页。
②③(11)(12)(13)(14)(15)(20)(21)(22)(26)(27)(2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2、654、345、384、347、343、345、342、342、343、350、351、355页。
④朱熹:《观心说》,《朱文公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74页。
⑤张立文:《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6页。
⑥⑦⑧⑨⑩(16)(23)(24)(25)(29)(30)(31)(32) (33)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954、400、400、401、401、420、410、423、423、433、433、427、430、434页。
(17)王夫之:《尚書引义》,《船山全书》(第二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61—262页。
(18)王夫之:《四书训义》,《船山全书》(第七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81页。
(34)参见李长泰:《论王船山民本政治价值论的重构——兼考王廷相的民本思想》,《船山学刊》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