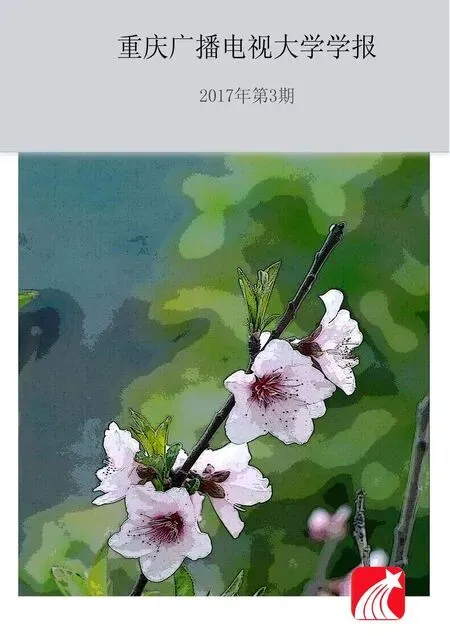论罗兰·巴尔特符号学的社会面向
唐小林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论罗兰·巴尔特符号学的社会面向
唐小林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罗兰·巴尔特是经典的符号学家,他受到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是在批评世界、阅读社会、观察生活事件、参与文化论争的过程中发现符号学的,这些都使他的符号学表现出强烈的社会面向。这突出体现在他的代码理论和神话分析中。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谎言和意识形态伪装的深刻揭露,尖锐地触及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矛盾。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社会面向
一
符号学几乎是“形式论”的共名。从“语言-符号学”到“符号-语言学”,再到“符号学”;*安娜·埃诺在《符号学简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中,就是如此叙述整个欧洲符号学发展历程的。从索绪尔的欧陆符号学到皮尔斯的英美符号学,再到赵元任、赵毅衡的中国符号学;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巴黎符号学派,再到四川大学符号学派,符号学的发展至少经历了五个模式三个阶段。即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模式,以皮尔斯为代表的逻辑-修辞学模式,以卡西尔为代表的文化符号论模式,以巴赫金为代表的“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模式,以赵毅衡为代表的解释学模式。*赵毅衡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中总结为四个模式三个阶段(第11—15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笔者加进了“以赵毅衡为代表的解释学模式”,变成五个模式三个阶段。这反映了符号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也因此完成了它的奠基、起飞,并进入全面发展繁荣的阶段。而其间所涌现出的符号思想、符号理论缤纷绚丽,各领风骚,难定一尊。
一些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应用了符号学的方法,且这些符号学者在学术上接近了马克思主义。这些人包括活跃在20世纪上半期俄国的巴赫金、伏罗辛诺夫等;20世纪下半期美国的詹姆逊,法国的鲍德里亚、德勒兹,英国的贝内特,爱沙尼亚的洛特曼、伊凡诺夫,民主德国的克劳斯,波兰的沙夫、佩尔茨,南斯拉夫的马尔科维奇,奥地利的伯纳德,意大利的罗西-兰迪;近年来还有美国的伯吉森、科克尔曼、温纳林德,英国的杰索普、克雷斯、霍奇,等等。这份名单远远不全,他们涉及马克思主义或符号学的深度和广度各有不同,某些当代学者的思想还正在发展中。*唐小林. 导言:建设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J]. 符号与传媒,2016(秋季号).但不管怎样,罗兰·巴尔特往往不在这份名单当中。他如雷贯耳的名望,是与结构主义的时髦人物福柯、拉康和列维-斯特劳斯联系在一起的[1]12。巴尔特进入资本主义矛盾的方式有所不同,他是从符号、文本,也就是从“形式”进入“文化”,最后抵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深处的。
二
1945年,才29岁的巴尔特,结束了在瑞士埃格勒市的莱赞疗养院疗养后,声称自己已经变成了“萨特的支持者兼马克思主义者”[1]10。他读了马克思的《神圣的家族》,“在政治上他觉得马克思主义是描述现实世界的不可替代的工具,是新社会的希望,从精神角度讲,在这个新社会中一切都成为可能;他那时认为,只有真正社会主义的社会才有心灵的真正自由。”[2]74他后来的《零度写作》,的确“谨慎地参考了马克思和萨特”[2]268,或者说与马克思和萨特的有关文本构成“互文性”[1]106。1955年,他以《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吗?》参加与加缪的论战,公开宣称自己是“左派”,认定自己在政治上只能以“马克思主义方式思考问题”[2]121-123。多年以后,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他在谈到为什么走向符号学的时候还说,“对我来说,一种符号科学能够刺激社会批评。在这一理论设想中,萨特、布莱希特和索绪尔可以携手合作”[1]59。他的《神话学》等系列著述,就是这种“社会批评”的最好实践,他以符码理论和神话学思想,从摔跤运动到广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谎言和意识形态伪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
1954年的5月底,巴尔特和多尔一起观看柏林剧团在巴黎国际戏剧节演出的布莱希特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深受震撼,以惊人的语速说出一句话:“布莱希特是一个思考过符号的马克思主义者”[2]113。这句话在巴尔特的一生中被他多次重复。又过了17年,巴尔特写道,布莱希特对于他依然极为重要。他之所以把布莱希特一直视为典范,不是因为布莱希特的文艺观,也不是因为布莱希特的审美观念,他所看重的是布莱希特“将马克思主义分析与关于意义的思考结合在一起。他是一个对符号的效果进行过深入思考的马克思主义者:这非常罕见”[1]40-41。这对于巴尔特来说,多少有些夫子自道。
三
巴尔特是符号理论操作的高手,更是符号学社会实践的大师。笔者认为,他是符号学面向社会发展史上,贯通索绪尔与皮尔斯的桥梁。
学界素有“索绪尔—巴尔特模式”之称,认为他“是索绪尔的一个最强有力的解释者”[3]134。其实较之索绪尔,巴尔特的符号学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性和批判性。他并没有像索绪尔、皮尔斯那样,试图在不断的思辨中,建立自己系统、严整的理论符号学体系。三十三四岁,他才在“思想导师”格雷马斯的引导下[2]94,听说了索绪尔、雅格布森,读了《普通语言学教程》,知道了转喻和隐喻[2]96。后来即便认识了列维-施特劳斯,因为学术志趣不同,并没有多深的交往[2]132。他运用了索绪尔的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等核心概念及一些基本的符号学思想,借用了乔姆斯基“外延”与“内涵”的符号学术语,但他既不是索绪尔也不是乔姆斯基衣钵的忠实继承人。比如,他“认为符号后面总有承载它的语言,因此与索绪尔的建议相反”,断定“语言学包括符号学而不是符号学包括语言学”[2]241,语言永远先于人而存在,人必须对付语言,语言是法西斯,因为它“强迫说话”[4]183。他显然接触过皮尔斯,在《符号学原理》里将皮尔斯的象似符号、指示符号、规约符号等与黑格尔、荣格和瓦隆的相关概念进行类比[5]。但巴尔特绝不定于一尊,他是符号学家中的“杂家”,是符号学家中的搬运工、泥水匠。他以卡片的方式,采集各家各派的理论观点,用自己思想的“水泥”粘连组织,筑起他特有的、地基坚实、结构紧密的符号学高墙[2]83。这座高墙的砖块,是由马克思、萨特、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布莱希特、拉康、巴赫金、雅格布森、邦维尼斯特等人的思想元素聚合而成[2]144-268。巴尔特不像索绪尔和皮尔斯,他既不是从语言学,也不是从自然科学走向符号学的,他是在批评世界、阅读社会、观察生活事件、参与文化论争的过程中,发现符号学的。符号学带给他的“首先是一种目光和一种直觉,而不是一种理论”[2]267。毋宁说,他更像一个符号分析家,挥舞符号学这把锋利的解剖刀,庖丁解牛式地解析环法自行车赛、自由搏击运动、多米尼西案件、“伴着你”面条广告、皮埃尔院长等各种社会现象,进行文学与文化批评,展开对殖民话语的解构,使“他那个版本的符号”,逐渐成为“批评社会的一种武器或一种工具”[2]102。如果说是生活,是现实,是社会,是复杂的文化斗争,是学院派僵死的教条把巴尔特逼向符号学的,并不为过。巴尔特的符号学因而具有了天然的“社会性”。
四
巴尔特一生著述丰富,涉及面相当广泛。他在《罗兰·巴尔特谈罗兰·巴尔特》中,把自己的学术活动依次分为四个阶段:以《写作的零度》和《神话集》为代表的“社会神学”阶段,以《符号学原理》和《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为代表的“符号学”阶段,以《符号帝国》和《S/Z》为代表的“文本”阶段,以《爱情絮语》和《文本的愉悦》为代表的“道德”阶段[6]。笔者以为,这四个阶段都属于符号学。“文本”分析当属符号学无疑。“社会神学”阶段其实就是典型的社会符号学阶段。“道德”阶段准确地说应该是“情感符号学”阶段。归结起来,巴尔特终生致力于社会符号学、理论符号学、文本符号学和情感符号学的研究。
对于社会符号学,笔者认为巴尔特最大的贡献是“代码”和“神话”理论。这里的“代码”,不是信息论意义上的概念,是符号学领域的“符码”,雅格布森、马丁内都曾使用过这个名称。它是指“在符号表意中,控制文本形成时意义植入的规则,控制解释时重建意义的规则”[7],是隐藏在符号和文本意义后面的“幕后操手”。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使世界变得复杂诡异、深不可测。对于巴尔特来说,世界上没有原始状态的经验,所有的“人造物”,或者人类目光所触之物,都已经被植入了“代码”,赋予了意义,发生了变化。经过重新“编码”,人类置身于自己创造的生活世界之中。
“编码”并非巴尔特的独创,在萨丕尔、沃尔夫和列维-斯特劳斯等人那里,就已经形成这样的传统:我们对世界的经验,只有“编成代码”才能重新体验。人类集体卷入这项“巨大的、隐蔽的、协作的事业之中”,而使“任何人都不能说他可以获得关于一个‘现实的’永存的世界的不可编码的、‘纯粹的’或客观的经验”[3]108。巴尔特的发现在于,这一切都“悄悄地披上了自然性、正义性、普遍性和必不可免性的外衣”[3]109,人们沉溺于此成为“笨蛋”而不自知。巴尔特的所有工作,就是要戳穿这一切,解构和还原“代码”,让伪善的“编码人”穿帮,让光鲜“正确”的意识形态从遮羞布下露出丑恶的鬼脸,让真相来一次阳光下的晾晒。
比如,在巴尔特看来,写作就“绝不是交流工具,它也不是一条只有语言的意图性在其上来去的敞开道路”[4]13-14,而是一件“复杂的社会、政治甚至经济的事件”,内含复杂甚至是华丽的“代码结构”[3]112。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古典的法国写作,并非是“天真无邪”的,也并不“简单地反映现实”。“事实上,它以自己的形象塑造现实,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合法传递人、传播者或者编码人。响应这种写作就是接受那些价值,就是证实并进一步论证那种生活方式的本质。”[3]109即便是左拉的现实主义,也远非“中性”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写作制作术中最绚丽多姿的记号”[4]42-43。写作上“自然主义”的追求,那些“清晰”、“精确”的方法,决非写作的“内部特征”,更非超越历史、超越意识形态的普遍模式。实际上,它是由经济和政治条件所决定的,“它暴露了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最后的历史野心,急于把人类全部的经验都纳入自己对世界的特定看法之中,并把这标榜为‘自然的’和‘标准的’”[3]110。
有学者指出,代码在巴尔特那里作为一股力量,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它都“修改、决定”,最为重要的是“生成意义”,“它远不是单纯的、不受限制的,它和语言把自己中介的、造型的模式强加于我们喜欢看作是‘外在’客观世界的东西时所使用的那些复杂方式十分接近”[3]112。巴尔特的一部《神话学》,就是在无情剖析“由法国大众传播媒介创造的‘神话’,揭露了它为自身的目的而暗中操纵代码的行径”[3]112。不仅文学虚构的世界没有什么“自然”“客观”可言,就连流行服饰、时装、时尚、食物,即全部人类事物都“渗透着编码行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不是一种‘事实’而是关于事实的符号”,不是一个经验世界,而是一个符号世界[3]125。当巴尔特认为全部人类事物都渗透了编码,也就意味着,他完全突破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的边界,而走向了皮尔斯。他给我们的启示,就像皮尔斯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符号的世界中”。符号学家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去破译这些符号。因为经过“代码”的暗箱操作,符号戴上了“能指的面具,隐藏在文字的后面,隐藏在‘自然’的假象、伪善、服装或戏剧中”[2]268。如果语言出于“交流”的话,那么巴尔特还把索绪尔“交流的符号学”带到了皮尔斯“意义的符号学”面前:煎牛排、炸薯条、肥皂粉、洗涤剂、照片、玩具、脱衣舞、占星术、阿尔古尔的演员、贫民与无产者或社会新闻的处理等,在巴尔特那里无不充满社会意义。
五
巴尔特的“神话”,当然不是古典神话学意义的神话,而“是一种言说方式”[8]169,“是指一个社会构造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的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仰的复杂系统:即它的‘意义’系统的结构”[3]135。索绪尔的语言符号是能指与所指的一种意指关系,对非语言系统而言,巴尔特认为,“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联结整体”。能指、所指,以及它们的产物——符号,构成了三足鼎立的关系。比如,一束表达激情的玫瑰花,“玫瑰和激情联结为一体,形成第三物”才是符号。但成为符号的玫瑰花,与原来作为能指的玫瑰花完全不同,前者只有植物分类学上的意义,是一种蔷薇科蔷薇属灌木,在文化上却是“空洞无物”的。而作为符号,这束玫瑰花是“充实”的,意义充盈:此玫瑰已非彼玫瑰,它已被编码、植入新的意义。巴尔特由此发现了符号的二级系统:在第一系统中具有符号地位的东西,在第二级系统中变成了纯粹的能指,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所指,开始了又一个符号化的历程。神话正是作为第二级的符号系统发挥作用[8]173-177,并且不断地“消耗”在第一级系统中确立的那个符号的意义,直至使它成为空洞的能指,被新的意义所取代:最后,玫瑰花的植物意义在激情中悄然离去。根本的原因,是主体意图与文化惯例在此巧妙结合、有效沟通。
就像“代码”普遍存在一样,巴尔特认为神话也无时无处不存在:“凡归属于言语表达方式(discours)的一切就都是神话”。不仅言辞,照片、电影、报道、竞技、戏剧表演、广告等都可以用作神话言说方式的载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宇宙具有无限的暗示性”。世上的每一物都可以从封闭而缄默的存在,转变为适合社会自由利用的言说状态[8]169。只要其被言说,它就必然变为神话。本来一棵树就是一棵树,但他经过诺·迪陆埃的描述,就已经不完全是一棵树了,它身上充满了“文学的自满、反抗、意象”,特定的社会文化被添加到树的纯粹的物质性上[8]169-170。虽然不存在永恒的神话,神话却与历史永存,“因为神话是历史选择的言说方式”。神话不可能从事物的原始状态中涌现,是人类的历史使现实之物转变成“措辞状态”,“人类历史,而且只有人类历史,决定了神话语言的生死”[8]170。当一切人造之物都是“编码“的结果,一切言语方式都是“神话”的时候,巴尔特转动那支生花妙笔,为已经编码的事物“解码”,为已经被神话化的话语“解神话化”,就是在进行猛烈深刻的文化批评和社会批判,其符号学的社会面向就尖锐地显现出来。巴尔特的符号学由此表现出强烈尖锐的社会面向,使那些认为符号学“完全脱离了人具体的生活”,*张兵. 符号学危机的化解:重置身体符号的“坐标原点”[J],学术月刊,2010(10).不食人间烟火,只是自娱自乐的看法,不攻自破。
[1]乔纳森·卡勒. 罗兰·巴特[M]. 陆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2]路易-让·卡尔韦. 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M]. 车槿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特伦斯·霍克斯.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M]. 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9.
[6]车槿山. 代译序[M] //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尔特传.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代译序2—3.
[7]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224.
[8]罗兰·巴特. 神话修辞术 批评与真实[M].温晋仪, 屠友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虹 谷)
10.3969/j.issn.1008-6382.2017.03.001
2017-05-07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高水平学术团队建设项目“符号媒介学”(shgt201601)成果之一。
唐小林,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副所长。
H0
A
1008-6382(2017)03-00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