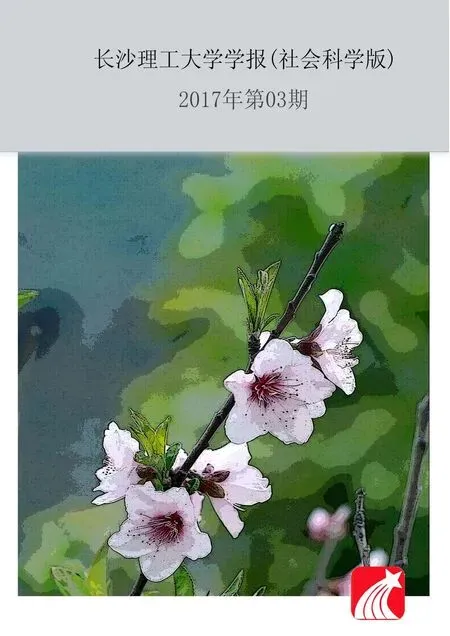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STS关系探析
陈多闻, 蓝茵茵
(1.成都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2.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湖南 长沙 410073;3.长沙理工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4 )
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的STS关系探析
陈多闻1,2, 蓝茵茵3
(1.成都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2.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湖南 长沙 410073;3.长沙理工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4 )
在生存技术、经验知识和农业社会的互动中,生态文明处于襁褓之中,人与自然原始和谐;在机器技术、理论科学和工业社会的作用下,生态文明尚未成形就走向异化,人与自然关系失衡;而在高新技术、复杂科学与信息社会的交织中,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文明被当代人类所渴求并建构,通过人类自身的技术使用实践,通过生态技术的产业化,STS的关系必将走向协调可持续的良性轨道,生态文明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现实。
技术使用;生态文明;STS关系
一、引言
生态文明是近些年我国学者研究和政府战略的一个热点词,关于生态文明的界定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多达几十种。本文所采用的生态文明是狭义的概念,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互动,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并列[1]。任何一种事物的出现都经历了一个过程,着眼于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生态文明理念也一样,孕育、产生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协调互动中。早在1938年,美国学者罗伯特·金·默顿在其博士论文《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首次提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这个概念,并强调要对它们之间“互惠的关系”进行研究[2];而科学、技术与社会(缩写为STS)作为一门学科则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立志于探讨科学技术的本质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本质。“科学、技术与社会是各自相互依赖却又相互独立的变量。STS研究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努力在这些依赖和独立因素中为后现代世界发现新的平衡。……所有的人都要投入重新定义我们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特征这一过程。”[3]一般认为,科学是关于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探索活动和知识体系,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聚焦场,技术则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中介手段,处于中间环节,一方面建构了社会,另一方面也应用了科学,人类正是在技术的使用实践活动中衍生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技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正如我国技术哲学的开创者陈昌曙老先生所强调的,“STS要非常重视其中的T(技术)”[4];技术的本质就在于使用,“技术的使用是所有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5]。笔者从中受到启发,试图立足于技术的使用从生态文明这一实践角度来深入解析STS关系的演变。
二、文明开启:人与自然原始和谐中的生存技术、经验知识与农业社会
人类文明产生的首要前提就是人类,人类是自然界千百万年来物质演化的产物,而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STS关系演化的起点。马克思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6],所以当我们的祖先从物质世界中演化出来时便开始创造着人类历史,当我们的祖先学会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的时候,便意味着人类文明初步形成,STS关系在技术使用实践中已然成型。
翻开历史的画卷,回到原始人类的蒙昧时期。根据达尔文的考证,人类的祖先只是一群特定的攀树猿群,三千万年前,不知道什么原因,这群一直生活在树上的攀树猿群突然离开了他们生活已久的森林,来到了陆地,也许是厌倦了树上的生活,也许是树林已不再适合他们生存,也许是他们想要探索未知的世界……总之,他们集体离开了熟悉的环境,来到了完全陌生的世界。面对这个他们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陆地世界,他们在不得不学会直立行走的同时,还必须学会如何寻找食物以便生存下来。为了生存,他们需要一种工具来帮助他们。在慢慢熟悉环境的过程中,他们找到了石头这种随处可见的简单工具,由此开辟了人类发展史上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在旧石器时代里,人类使用的石器基本维持其自然面貌,很粗糙也很简陋,为了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和快捷,人类不断对其进行加工和打磨,不够锋利就磨成片状,不方便携带就加个木柄或钻个孔系上绳子……自然而然地,人类也就进入到了新石器时代。石器在人类的发展史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有力武器,在使用石器的过程中,人类不断地对其加以改造,发明了人类第一项技术工具——弓箭,“ 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为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7]。
而后,人类又偶然发现了野火的存在,经历了从对野火一无所知到利用野火的过程。一开始,人类以为野火是上天的恩赐,派专人小心翼翼地看守,然而野火的保存实在不容易,给人类的使用带来诸多不便,于是我们的祖先们开始苦苦探索人工取火的各种方法,最为有名的传说就是燧人氏“钻木取火”。人工取火方法的最终发明,也标志着人类第一次掌握并利用了一种自然力,恩格斯对此有很高的评价,“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8]。正是由于人类对火的使用,人类慢慢告别了茹毛饮血的蒙昧时代,进入到了人类文明的大门口。而后,原始人类开始慢慢有了定居生活,又进入到农业文明时代。
不管是在原始时代还是在农业时代,人类所使用的工具就是手工工具,手工工具简而言之就是直接由人手把持并加以操作的工具,比如新旧石器、锄头、扫帚等等,陈凡教授把它们都归之为“经验型技术”,并具有“主要由经验知识、手工工具和手工性经验技能等技术要素形态组成的,而且以手工性经验技能为主导要素的技术结构”[9]。这种经验型技术突出经验的地位与作用,也反映出在农耕文明时代经验的重要性。在人类最初期的经验型技术使用实践中,STS关系也就主要表现为经验科学、生存技术与农耕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个时候的技术主要是经验型技术,也即生存技术,所谓生存技术主要是指满足人类吃、住、穿等需求的手段,仅仅停留在最基本的生存层面,就是以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为目的的技术。生存技术的主导地位决定了这个时候的科学主要是经验科学,科学家主要凭借感觉和观察来获取有关自然本质和规律的种种认识。最典型代表是为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科学家”的亚里斯多德,他通过观察并加以理性思考,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其物理学理论统领了物理学界两千多年,但是到了近代,其中有不少观点却经受不住伽利略的实验检验。可见,这种经验科学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上,缺乏理性推敲。这个时候的社会主要是农耕社会,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自然经济,也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奴隶主和封建君王统治。人们在生存技术的使用实践中摸索着前进,经验性知识不断地积累和沉淀,才得以代代相传。
此时的人与自然原始和谐,相比于改造自然来说,人类更多的是顺应自然,就如其他动物一样疲命于满足生存,生态文明处于混沌孕育期。不管人类使用什么样的技术载体来改造自然——石器、青铜器抑或铁器,都只能是局部作用于自然界。那时候最大的环境问题就是生活垃圾污染或者局部地区资源匮乏,自然界自身的调节机制此时还能够游刃有余,从而使得STS关系整体上呈现出和谐的景象。
三、文明异化:人与自然关系失衡中的机器技术、理论科学与工业社会
生态文明经过了漫长的史前期,还未及成形就开始走向异化,先是在农耕时代,人类开始利用自然力踏上改造自然的征途,然后到了工业时代,人类大举使用机器进军自然,人与自然的原初和谐被无情打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步一步偏离生态轨道。
早在16世纪下半叶,被马克思称之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弗兰西斯·培根敏锐地认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并极力推崇知识的应用。在其代表作《新工具》里,培根充满激情地号召人们要普遍采用实验调查法,强调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虽然始于观察,但也借助于科学实验,因为“自然的奥秘在技术干预之下,比在自然活动时更容易表露出来”,所以培根极为推崇科学的普及和技术的应用,强调“知识就是力量”,要善于把知识转化为改造自然的力量,凭借知识工具向大自然发动进攻,从而不断地逼迫自然卸下神秘面纱,最终能够征服自然。
培根的号召鼓舞着人类加紧了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脚步。工匠们纷纷寻求科学理论的支撑,工匠和科学家开始合作。18世纪中叶,凯伊对飞梭的发明成功,揭开了人类使用机器技术的序幕,而随之以修理工瓦特改良蒸汽机成功为契机爆发的蒸汽机革命更是将人类带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机器时代。机器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以机器生产机器,动力机、传动机和工作机井然有序分工合作,整个社会的生产部门连接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机器系统。机器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手工工具的工具,不再需要人手直接把握操持,这样就直接把劳动者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样,机器的普遍使用使得STS关系序列里的技术也就从经验型技术转变为了实体型技术,所谓实体型技术具有着“由机器,机械性经验技能和半经验、半理论的技术知识等要素形态组成的,而且以机器等技术手段为主导要素的技术结构”[9],对它的使用不再仅凭经验就可以,也需要一定理论知识的储备,比如操作机器者不能是文盲至少要能识字,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因为要能看懂说明书。在这种实体型技术的使用实践中,STS关系也就表现为理论科学、实体型技术和工业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个时候的科学是理论科学,牛顿1687年发表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不仅标志着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也标志着理论科学的形成,在书中,牛顿以欧几里得创立的公理化模式为方法,从公理出发,推导出问题,并且注意辅之以客观事实,从而夯实了整个理论科学体系大厦。随着物理学学科确立了理论地位,其他学科踏至纷来,生物学、化学、地质学等也确定了理论范式,摆脱了经验科学的窠臼。
这个时候的社会有了工人与工程师的职业分离,他们都脱胎于早期的工匠,工人以直接操作机器为职业,属于体力劳动者;工程师以设计机器或管理机器为职业,属于脑力劳动者,“工程师大多数出身于简单工人,既灵巧熟练又有进取心,但通常无文化或靠自学。他们或者是车匠像布累马(Bramah),或者是机器匠像麦多克和佐治·斯蒂芬孙,或者是铁匠像纽可门和摩德斯雷。另有仪器匠像斯米登和瓦特,技工像内斯密司(Nasmyth)或采矿机师像特雷费锡克,几乎和前面几个人无甚分别,只不过对科学较接近些罢了”[10]。
工业革命揭开了技术与科学结合的历程,也推动了STS日趋紧密的联系,在实体型技术的使用实践中,技术因为有了科学理论的支撑,对自然的改造力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座座现代化工厂拔地而起,现代化城市也此起彼伏。正是在人类加快改造自然的进程中,STS关系也开始出现异化,“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11]。人刚刚有可能摆脱大自然的桎梏,却又陷入社会本身缠结的罗网之中。从此,“人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成为人们越来越感兴趣的问题,人渐渐地感觉到自己处于焦虑和不安之中”[12]。
四、文明重构:人与自然系统整合中的高新技术、复杂科学与信息社会
机器技术的普遍使用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和谐,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失衡状态,岌岌可危。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在牛顿时代建构的宏观物体理论认识体系基础之上,又建构起了微观物体和宇观物体的理论认识体系,科学从追求“简单性”为宗旨演化为追求“复杂性”。这个时期的技术形态主要是知识型技术,知识型技术就是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技术形态,技术也随之演进到理论型技术形态阶段,具有了系统的理论支撑和深厚的理论根基,被称之为“高新技术”。这个时候的社会“从技术形态上普遍经历着一场‘技术转型’,就是从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转型”[13],出现了信息文明。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工业革命时代人类大肆改造自然的行为开始一一有了回报,全球问题频频出现,生态系统不断恶化,温室效应、土地干旱、酸雨危害、粮食紧缺、重金属污染等等问题此起彼伏。其中最典型的爆发在20世纪中叶的八大环境公害事件,震惊全球。这八大环境公害事件都爆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美国、日本和英国为主,而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正是工业革命的先行者和主力军。八大环境公害事件都是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加快改造自然的进程中发生的,呈现出一些特征:有六件跟大气污染有关,这直接是大量工厂夜以继日地向大气中排放废气的后果;而有四件则爆发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后起之秀——日本,这是日本为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加紧发展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这些环境公害事件的出现都印证了恩格斯对人类的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4]
在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前,人类开始反思自己改造自然的行为,开始谋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20世纪70年代,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人类反省大军中显得尤为突出。卡逊在书中描述了若干年后因为对DDT等化工药品的使用,人类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没有任何生命迹象的春天,地球被死一般的寂静所笼罩。正是因为卡逊的这本书,美国全面禁止了对DDT的使用,并揭开了国际环境保护运动的序幕。从此,各种反思环境问题的书籍和文章、各类宣传环境保护的小册子层出不穷,小到各种地区环境保护组织大到各种国际环境保护组织纷纷组建,这些不同层面的组建者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伟大事业中,乐此不彼。
在反思环境问题的学者队伍里,罗尔斯顿显得尤为突出,罗尔斯顿可谓是近现代以来主张“哲学走向荒野”的第一位哲学家。他极力推崇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这些内在价值并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是自然事物与生俱来的,并且大声宣布,“在生态学的意义上,人的作用微乎其微,从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来说,细菌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人类”[15],从而解构了数千年来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主体性地位,提醒着人类放低身姿,要从内心深处学会尊重自然系统里的一切事物,哪怕是一缕阳光、一丝清风、一棵小草、一片树叶抑或是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罗尔斯顿的观点虽然有点偏颇,却着实敲醒了人类整体的生态警钟,有忧患意识的人们纷纷着力于从理论上寻求修复人与自然关系的良方,并在现实活动中努力践行。
在当时代,我们已然无法放弃技术,唯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重新设计人类社会所依托的技术方案才能获得一线生机,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美好的社会就是生态社会,建设生态社会要发展生态科技和实施生态创新”[16]。故而,除了要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在观念上要加强宣传呼吁构建一种新的生态伦理观外,我们更要改变我们的客观世界——在实际中推广运用生态技术,实现技术生态化和产业化,使人类社会牢牢建立在低碳环保的技术行为之上。生态技术建立在生态理论的基础之上,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相关成果修复人类改造自然的负面效应,把对自然的损害降到最低,在人类生存与自然生存之间实现最佳平衡,既要建构出“青山绿水”,又要建构出“金山银山”。可见,人类设计、使用生态技术的目的就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和良性互动,从而建构出人类的新型文明形态——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状态既超越了农耕时代人与自然的混沌又克服了工业时代人与自然的异化,是人类在自觉自主尊重、顺应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构建的和谐互动。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种全面和自由建立在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的基础上。在我们国家,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把生态文明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使之成为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并列的重要战略布局。“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7],生态文明已然成为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民生工程。相信不久的将来,生态文明就会在社会主义语境下灿烂绽放。
[1]余谋昌.生态文明是人类的第四文明[J].绿叶,2006(11):20.
[2][美]罗伯特·金·默顿.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6.
[3]Carl Mitcham.In Search of a New Relation between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J].Technology in Society,1989(11):417.
[4]陈昌曙.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2:234.
[5]Rudi Volti.Society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vii.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4.
[9]陈凡,张明国.解析技术[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22.
[10][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M].伍况甫,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342-343.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5.
[12]易显飞.技术创新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研究[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4:112.
[13]肖锋.信息技术哲学的兴起[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3):45.
[14][德]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8.
[15]Holmes Rolston.Environmental Ethics:Duties to and Values in Natural World[M].Philadephea,1988:73.
[16]林慧岳,曾志远.技术的生态边界及临界防控的哲学理路[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7.
[17]骆方金.习近平生态文明观探析[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66.
The Relation Betwe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ENDuo-wen1,2,LANYin-yin3
(1.SchoolofHumanitiesandLaw,ChengduUniversityofTechnology,Chengdu,Sichuan610059,China; 2.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NationalUniversityofDefenseTechnology,Changsha,Hunan410073,China; 3.Changsha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Changsha,Hunan410004,China)
Among the interactivities of survival technology, experimental knowledge and agricultural societ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ves in swaddling clothes, and man and natural lives in origin as well as harmony. Technology use is the bod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 It is in the practice of technology use, humans turned the relationship of STS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this relationship. In the practice of empirical technology use, STS expressed mainly as survival skills, experience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 agricultural community; in the practice of the entity technology use, STS expressed mainly as machine technology, theoretical science and industrial society; in the practice of knowledge-based technology, STS expressed mainly as high-tech, complex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Consequently, the relationship of STS also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occurring, alienating and assimilating. This paper believes firmly that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echnology use of human beings, we can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of STS.
technology use;ecological civilization;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016-10-16
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16BZX032)阶段性成果
陈多闻(1979-)女,湖南怀化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技术哲学、技术伦理学研; 蓝茵茵(1983-)女,湖南常德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科技政策研究。
N031
A
1672-934X(2017)03-0029-06
10.16573/j.cnki.1672-934x.2017.03.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