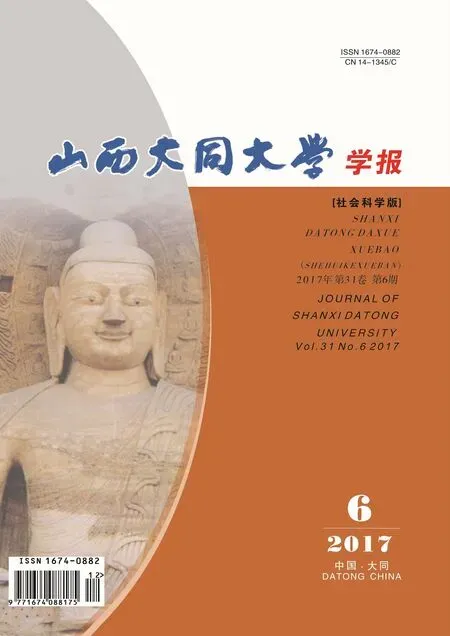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内涵探析
贺腾飞
(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内涵探析
贺腾飞
(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对于文化这个古老而又重要的概念,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诠释,尤其人类学家对于文化的见解更是非常深入。通过人类学的视角可以看到,对文化的认知需从文化本身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从文化内在辩证发展的角度来深入了解文化的重要内涵。
文化;人类学;辩证法
一直以来,文化都是人类学的基本概念。100多年前,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是人类行为与思想的体系,遵循着自然的法则。由此,人类学家对于文化的阐述不断增多,各学派也都从各自立场出发,对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与讨论,但却鲜有从文化本身来探讨文化,而对于文化本身来说,只有了解文化具有哪些属性,内在存在哪些辩证关系,才能深入探究文化的本质。
一、人类学对文化的认知
考虑到人类学通常被视为他者文化的研究,那么“文化”成为该学科最核心的概念也不足为奇。文化是人类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是建立在符号交流的基础之上。人类学家怀特就认为文化依靠着象征化的过程,由工具、装备、风俗习惯、制度、信念、仪式、语言等组成。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由符号组成,也依靠符号传递,文化萌芽于人类习得使用象征的能力时。[1](P29-31)
斯皮罗认为文化是指一种认知系统,即一系列关于自然、人和社会的“命题”,这些命题被纳入有高度秩序且相互连接的结构和网络中。这个命题是公共的,正如索绪尔证明的一样,文化处于符号自身里,符号同时作为被表示者(概念)和表示者(符号载体)起作用。然而当文化命题被社会行动者学到后,它们即成为个人的思想,就像感情一样,它们是个人的,现在处于心灵里。[2](P34-37)
布鲁纳进一步阐述了文化的本质,认为以符号形态呈现出一系列的活动体系是文化,文化具有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从宏观上看,庞大复杂的符号体系是文化的呈现形式,权力、体制、名声等与这些符号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由各种权利、义务、价值观、机会等组成的庞大体系”。这个体系性的整体由这些成分共同构成,对体系中的个人提出了各种要求并施加了种种影响。
从微观上看,个体在文化体系内的各种活动中,经常性需要与文化体系打交道,这个体系可以看成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库,通过有象征的符号性的交换活动,使文化工具能够从中获取,从而形成适合自己的工具包,用来对付这个体系,并构建起一系列的实体与自我能力,从而使自己个人的天赋能够实现。它专注于个体如何建构“现实”与各种意义,以便能使他们在系统之中适应,同时也注意到在此行动中个人要付出什么代价以及他们可预期什么结果。说明人类的自我意识与心灵的存在,都受到文化的约束,外在的或客观的现实只能通过心灵的性质以及心灵所依赖的符号系统才能被人知晓。[3](P6-7)
从内在的角度,文化作为一种认知系统或活动体系,它也会塑造个体的心灵。它在个体表现上与生俱来的方式乃是意义的生成,也就是对于不同场合里的各种特定事物都赋予意义。意义的生成包含了和世界遭逢时的事态以及将此事态置入文化的合宜背景里,以便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虽然意义的产生是在心灵里,但意义的根源和重要性却来自文化,因为它确实是在文化里创造出来的。意义的这种置身在文化事态之中的性质正是它能保证可以商议与沟通的原因。这个意义提供了一个基础来作为文化的交换,在此观点下,知道和沟通在本质上是高度相互依存的。因为不论一个人多么能够在其自身中运思,但所有人都需要在文化符号系统地辅导下来执行对意义的追求,通过文化提供的工具,以我们能沟通的方式来组织与了解我们的世界。
虽然文化本身是人造的,但人类心灵确切的工作方式却通过文化得以形成。文化情境永远都包括学习与思考,这些文化资源是必须依赖使用的。甚至,心灵在本质上和用法上的个体变化,也可以归因于各个相异的文化情境所提供的各种不同的机会,只是这并非心灵功能变化的唯一根源而已。[3](P6-7)
所以,我们如何“认识”文化,如何看待文化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就尤显重要了。比如,在描述“美国文化”或任何文化的具体化过程中会发现其实都只不过是一种文化霸权策略,以图将自身利益强加于所谓“文化”的周围。
二、人类学对文化本质的争论
作为研究的起点,那么,人类学关于文化本质的纷争是什么呢?主要的争论者分为两派。让我们冒着过于简单化的风险,将其标签为“社会制度主义者”和“解释建构主义者”。
“社会制度主义者认为一个社会或一种文化是一系列确定的为了共同生活的安排,并且由像血族关系规则、交换制度、冲突解决方式等此类的生活事实构成。最大限度的文化只能从展示每一社会集体生活方式的规则和习惯做法中推论出。”即文化是一种超有机体,文化并不是内在于组成社会成员的头脑中,而是位于更高的平台上。[4](P193-199)
这种观点认为,任何个体均不了解整体文化,但当作为整体的文化处于个体成员视野之外时,所有成员都被期望遵守其教规。当个体不能遵守教规时,其典型性在于可被教规接受的方式使变种合法化,对此,其他人可能以同样教规的方式加以反映。总体上讲,一种文化会提供相对有限的教规以确认恰当,使对恰当的违反合理化或使之情有可原,并规定对不恰当的补救和惩罚措施。对文化方式的漠然可能减轻,但从不会开脱。即一种文化是外在于其成员的头脑的,但限制着其成员。
这种观点意味着一种文化有自身存在的权利,独立于个体参与者加诸的观点。像优秀的经验主义者一样,他们开始于具体地人种学观察并形成人种学理论。前者是客观的、事实的,后者包含着一致的规则和对事实的解释,以尽可能地赋予其意义。
“而解释建构主义者否认存在自治的、自立的、客观的”事实“,而只存在人种学的观察或其他。事实本身产生于解释。没有任何关于文化的理论能够仅涉及事实而得到证实,相反,理论推动着什么算是事实。事实不可避免地起源于认识者的解释立场.这是因为是认识者赋予它们以事实的地位。认识者通过对其遇到的事物的解释、叙述和赋予意义而达到这点。每个人的事实仅仅是处于各种情境之下的此人赋予意义的方式。”解释主义者质疑制度主义者的基础论,即所谓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对其作为根基描述的确信是否真的在那里存在。因此,任何文化仅仅是每个人在共同生活中力图解释其经验的、互相交涉的结果。人类学家必须寻找原始数据,以供人们自身进行集体解释的、赋予意义的活动。[4](P193-199)
所以,虽然两种观点不统一,但从道德观点来看,它们不过是两种对立统一的理论。因为,一方面,对人群的尊重和对其自身最直接和最有意义的经验感觉的尊重,要求我们认真理解他们的世界及其如何运行。这需要接受这样的现实,即社会就像生命一样,包含着他们自己的解释。如果是这样,我们认为就像吉兹所说“某人群的文化像一个课文的整体,他们自身的整体,人类学家尽力通过处在可能属于人群中的人的肩膀上的位置来阅读。”
另一方面,这并不是“唯一的”现实,因为制度绝不“单纯”是世界应如何被理解的解释。毫无疑问,所有的法律和惯例都是文化的建构,都是社会解释交涉的最终产物。但它们拥有自身无情的存在。
所以,在分析建构主义者的观点中,人类学家扮演着明智的专家角色,拥有训练有素的眼睛。但在解释主义者看来,不存在先行的、裸体的真理可被训练有素的眼睛所发现,人类学家是另一解释者,是一个因远离而有点蒙蔽的解释者。
三、从辩证的角度看文化
从以上争论可以发现,任何文化理论必然是人类学家对参与交涉者解释活动的解释。由此,我们发现文化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内在辩证关系,主要表现在:
(一)所有的文化在本性上,是已经确定的与想象的可能这两者间交涉的妥协物 在任何文化中,均存在思考、感受、行为和与他人交往正确的或合乎规律的途径。这些形成了一种文化公开、规范的结构。该规范变化的清晰度和程度因人们对其的意识而不同。尽管在文化教规性的范围内引导人们生活可能存在着模糊性和复杂性,但大多数成员大部分时间都尽力合乎教规,都受到了同伴成员践行的某类容忍原则的启示。而且合乎教规性主要不是由于畏惧惩罚或复仇的逼迫,而是独特地确信人的适应性,我们称之为“自我”。自我包括如何使与他人的交往形成内在化的最大,让我们深入到人们拥有的各种期望之中。坚持对期望的文化考量,意识到我们的“位置”和我们的作用就是一个道德心和社会适应性的问题。不同的文化创造出不同的自我方式,如“羞耻”和“犯罪”文化。[5](P112)
尽管文化在加强成员自我接受规范所使用的手段方面有所不同,但文化存在着共同的确定事物。可发现所有文化都使用嘲笑来对待规范破坏行为,所有文化都使用羞耻方式控制统治规范的破坏者或可能的破坏者。离开了自我现象及其随从的自尊和虚荣,无论是嘲笑还是羞耻都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所提供的情感要素,被称为身份感。
身份感具有求知功能,身份感将我们与我们依其良好观点而获得自尊的社会团体联结起来,而且身份感将我们固定于该团体指派我们处于良好观点的角色和地位。这种制度化的形式也在塑造思想和行为。这种精神活动实际上总是“有所处的”,也就是说文化能够制度化“处境”。但处境经常可以推翻想象,并以将我们更紧地捆绑于合乎教规性而告终。文化就像存在人类的一种特殊精神能力,逼迫我们超出平常的、期望的与合法的世界,并包含有他人设想着设计出我们的想象。我们经常会超出所处环境,想象出相对于此地和此时的替代选择,创造出反事实的、不存在的、从未经历过的无。
(二)一种文化无论追求的内在一致性是什么,均是交涉中的内在辩证过程,而非某自然过程 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免于文化影响的,但个人也不只是单纯镜照他的文化,这两者之间的互动,一方面对个人的思维投下社群的影子,另一方面也会为文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情感增加某些不可预料的丰富性。在文化中的生活就是一场交相作用,其作用的双方就是人们在机构体制支配下对世界所形成的版本,以及经由个人历史而对世界所形成的另一版本。[5](P112)
人是一个文化存在,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存在,这意味着在人出生之时,自然只给予人最少的、最基本的生存前提,而将塑造自己的任务交付给人自己,这样他才能通过文化活动来充分实现自身的存在。人部分是自然、部分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全部是自然或历史的产物。这个历史和自然的混合物就被称为文化。人类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表现在我们身上的许多行为和特性都不是自然、而毋宁说是文化的产物。这是直接把人和动植物区分开的最为显著的特征。不同于其他完全由自然所引起和决定的生物,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己的创造者。动植物只能接受周围的自然环境,人却能够通过改造自然、促使自然发生深刻的变化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文化对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东西,它构成人本性的一个部分,是人的本质的一个基本要素。
从本质上讲,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从最广义的角度来讲,应该是关于人的一切内容。这不仅仅包括思想观念的问题,还包括稳定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是每一民族或每一时代通过自觉不自觉地历史凝结成的占主导地位的普遍遵守的生存方式,它是稳定于人类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类存在,其核心是道德信仰和价值追求。
从这种意义上讲,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因为不仅人是文化最主要的接受者和最伟大的产物,而且还是文化的创造者。在塑造个体和作为社会的精神形式这两个公认的主要意义上,文化都以个体全面、充分的自我实现为目的。文化最主要的目标是培育作为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人类样本而存在的个体的人。[5](P112)
因此,对于文化的研究应该假借于对人的研究去发现文化的真正意境,而不能单纯地只从文化本身去进行研究。只有在对人的辩证发展的研究中才能彰明较著文化的辩证发展。[6]
(三)文化的辩证交涉具有向心性,它是整合的、有模式可循的体系 文化体系中如果某个部分发生变化,那这个体系中的其他部分也会随着改变。通过观念、价值、判断与象征的组合以及其主要的经济活动与相关模式进行整合而形成文化。通过文化训练,使体系中的个体成员能共享某些人格特质,形成具有特色的核心价值整合了每一种文化,并使不同文化能够有效地区分开来。
文化是一个各部分相互联系的整合体的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张结构、符号、信仰、规律和法则相互作用的网络。它能帮助我们将这些关系整合起来。维系社会的工具和技术是最基础的文化子系统,它与生物-物理环境发生直接互动,这就是所谓文化体系的技术-经济组成。其次是构成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的法则,这些群体组织了劳动,并承担了更高或基层子系统的运行。高于社会组织层面的子系统是社会所共有的关于社会本身和世界的观念。所以,文化概念包括这三个子系统:技术-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7](P95)
文化的这种整合性建立在古往今来整个人类的基础上,让观察者从本文化出发从人类的角度来概括文化,它同时也让我们从其本身来看文化,而不是借助周围异文化的观点。因为大多数文化观念和实践都与文化的其他一些方面有关。人类学家要探索的是其他没有被人想到,或文化实践者本身不以为然的联系。我们追寻的这些联系并不全是因果联系,而是部分-整体、过程,以及隐喻、主题、并列的联系。
因此,从深层本质上讲,文化通过对现实概念控制的竞争而标记自己。在深远意义上,“讲述一种文化”,像写作历史一样,也是一种文学行为。它需要叙述的一致性。反过来,这也需要主题与细节的交织,需要一个有分寸的解释学上的感性。这不仅需要创造性的,还需要批判性的技巧,以使“真正的”故事令人可信。
[1](美)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周云水译.文化人类学-欣赏文化差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美)M.E.斯皮罗著,徐俊等译.文化与人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美)杰罗姆·布鲁纳著,宋文里、黄小鹏译.布鲁纳教育文化观[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4](美)杰罗姆·布鲁纳著,于兆波等译.关注美国法律[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5](意大利)巴蒂斯塔·莫迪恩著,李树琴,段素革译.哲学人类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6]胡存之.文化的辩证法及社会的文化规范[J].求是学刊,2001(03):27-32.
[7](美)约翰·奥莫亨德罗著,张经纬等译.人类学入门—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Culture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HE Teng-fei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Shanxi,037009)
For the culture,the ancient and important concept,there have been som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In particular,the views of the human scientist for culture is very deep.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it can be seen that the cognition of culture should b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itself,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connotation of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culture;anthropology;dialectics
G112
A
1674-0882(2017)06-0094-04
2017-07-25
2014年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民族地区普通中学学生文化认同、族际互动心理状况与民族团结教育革新”(2014-GM-139)
贺腾飞(1979-)男,山西大同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跨文化心理与教育。
〔责任编辑 冯喜梅〕